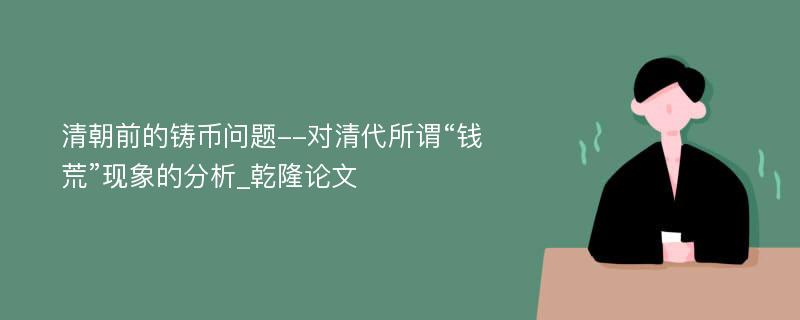
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现象论文,铸钱量论文,钱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代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清代的前、中期始终处于“钱荒”状态中,主要表现为“铜币供应严重不足,导致钱价长期居高不下,即所谓‘银贱钱贵’。”(注:《清代钱荒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笔者感到似不存在这种现象, 清代的这一时期铸钱量并非少而严重不足,银贱钱贵也不是由于钱(即铜钱)少而造成。仅谈初步看法,敬请同好指正。
一
认为清代铸钱量少存在“钱荒”现象,在以下两方面有所忽略。
第一,论述“钱荒”所引用的史料有误,进而导致所计算的铸钱量很小。这条史料来自《清史稿》卷124《钱法》, 是用来说明顺治朝铸钱量之少的,原文是:
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这段话所说的“白铜三成”应是“白铅三成”,把铸钱材料弄错,可不去管它。以下“钱千为万”一句文理颇不通,只要看《大清会典》或其“则例”、“事例”及《清朝文献通考》诸政书的钱法部分,便可知应是“钱千为串”,指一千个制钱为一串,以下“二千串为一卯”则应是“万二千串为一卯”,是指铸钱量最大的单位是以“卯”计,一万二千串为一卯。若叙述正确,应是“钱千为串,万二千串为一卯”,《清史稿》这段话在“万”字之前落了个“串”字,以致误导今人将一万二千串为一卯作二千串为一卯计算,仅为原额的1/6,顺治朝所定的年铸三十卯的36万串也即3.6亿文钱(制钱一个为一文,一串为1000文), 也就成了“年铸30卯是60000串,合6000万文”,仅0.6亿文了。
就此说明,这一万二千串之一卯,是户部宝泉局的一卯钱数,且为约数,实际是康熙后期以前,每卯为1.288万串,以后为1.248万串,或1.2498万串。工部宝源局的一卯,为户部宝泉局的半数,是6 千串左右,以康熙末年计,为6240串。以上在《清朝文献通考》的卷14、卷16中有载。而地方铸钱局,每卯铸钱数也各不相同,普遍比中央二局少。
第二,误将中央铸钱数当作全国铸钱总数,没把地方各省的铸钱数统计进去,且没有利用清代铸钱量最大的乾隆时期的数字,也未对乾隆时期的铸钱数量作考察与统计。
清代的铸钱分为中央鼓铸和地方各省鼓铸。中央铸钱机构为,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二局各设铸钱炉若干座,连年按卯鼓铸。地方则每省各设钱局鼓铸。
据论述清代钱荒的学者说:“能够查到的清代前中期铸币量最多的年份是雍正十年,‘铸钱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六万二千有奇’,合6.8 亿文”,这是《清史稿·世宗本纪》的数字,这一数字实际是雍正十一年的(因《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一年十二月结尾所记正好是这一数字,而雍正十年之数是9.1017112亿文,这也是《清史稿》之一误), 用来说明当时铸钱量,从时间上说倒也可以,关键是这年铸量的6.8亿文, 仅是中央宝泉、宝源二局所铸之钱。乾隆朝所修《皇朝文献通考》卷14说得很明确:
(康熙)五十年以后,(宝泉、宝源)二局卯数、铜斤递经增定,至康熙六十年间,两局各三十六卯……宝泉局每卯用铜……铸钱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串;宝源局每卯用铜……铸钱六千二百四十串。每年共为钱六十七万三千九百二十串云”。宝泉、宝源二局这“六十七万三千九百二十串”,正合6.7亿文。 同书卷15雍正十二年还记:
户、工部议定:见在宝泉局正额四十一卯,宝源局正额三十七卯。向例,宝泉局每卯用铜铅十二万斤,宝源局每卯用铜铅六万斤。每铜铅百斤铸钱十四串四百文。据此,雍正十二年以前,宝源、宝泉二局年额铸即达78卯,为74.256万串,合7.4亿文,也是中央年铸钱数,而不包括地方各省所铸。 如果再算上地方各省所铸的总数,其数额将大大超过这六、七亿文的年铸量。
根据以上考察,笔者还认为,康熙、雍正两朝实录(每年年末一卷之卷末)所载每年铸钱数的几亿文(康熙朝2.4亿文—4.4亿文,雍正朝4.9亿文—10亿文),都是中央所铸,而未包括地方之数, 彭信威认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录所载每年铸钱数为北京宝泉局一局所铸之数,恐亦不确。(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第一,康熙、雍正两朝中央统计之数应为宝泉、宝源二局,且宝泉一局也不会有那么多。第二,顺治朝从顺治四年至十五年,年铸量为10亿文至26亿文之间,其数过大,更不会是宝泉一局。也不会仅是中央之数,即使是作为中央和地方总数,以当时铜源情况来看,此数都令人怀疑,与前后之差别也较悬殊,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实录每年仅作几十万文(49万至67万文),亦不确,应是几十万串,当是以“串”作单位,因未写“串”字,因而比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及雍正四年以后之年铸量相差了1000倍。
明了清代铸钱数量,尤其是道光以前之年铸量,需要对中央、地方分别考察。中央部分,雍正以前实录有载,此处不作列举。乾隆以后,实录每年之末不再记录。现据政书所记各时期的阶段性鼓铸卯数,计算出各时期年铸串数、文数,列为下表,重点放在乾隆朝。
宝 泉 局
年代阶段 年铸卯数史料根据折合串数
(单位:万串)
乾隆七年至 61卯
《清朝文献通考》 76.2378
乾隆十五年 第4999页上
乾隆十六年 71卯同上,第88.7358
至乾隆二十 5008页中
乾隆二十五 同上,第5013页 94.9848
乾隆二十五 年至三十七 下;光绪《大清会
年至乾隆年76卯,
典事例》卷214《钱乾隆三十八
五十八年三十八年法·京局鼓铸. 年以后93.6
以后75卯
乾隆五十九 经常变动 光绪《大清会典37.494至
年以后至嘉 大致在30卯
事例》卷214《钱 93.735之间
庆四年—75卯之间
法·京局鼓铸》.
嘉庆五年 同上.嘉庆九、十
以后至嘉 89.5卯 两年曾减为75卯、 111.696
庆后期 72卯,至十二年
又增至89.5卯.
王庆云《石渠
道光后期 113万串 余纪》卷5113万串
《纪户部局铸》
宝源局年铸总数
年代阶段 年铸卯数史料根据 折合串数(单位:万串)
(单位:万串)
乾隆七年至61卯 《清朝文献通考》 38.1189114.3567
乾隆十五年
第4999页上
乾隆十六年71卯44.3679 133.1037
至乾隆二十 乾隆二十一年 同上 乾隆二十一
乾隆二十一
四年 后为81卯第5008页中 年后50.6169 年后139.3527
81卯(乾隆 光绪《大清会典
乾隆二十五
二十五、 事例》卷890《工
50.6169
年至乾隆 六两年) 部·鼓铸局钱》. 乾隆二十七年
平均
五十八年 70卯(乾隆 后43.743 138.36
二十七年
以后
乾隆五十九 几次变动
同上 18.747至 56.241至
年以后至嘉 大致在30
43.743之间137.478之间
庆四年—70卯之间
以后至嘉86卯同上 53.664
165.36
庆后期
王庆云《石渠
道光后期53万串 余纪》卷5 53万串 166万串
《纪户部局铸》
此表需要说明的是道光后期,由于中央也常停铸,所以不会达到年铸166万串之数。《石渠余记》所记似为当时户部则例的额铸数。
地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各省设局不一,少者仅省局1局, 多者在该省府、州也设有铸局,如湖北省,除省局宝武局外,襄阳、荆州、郧阳也曾设局。设局最多的是云南省,最多时达七、八个。各省省局以外之铸局不固定,常增减、合并,且多数省份并非常年每月连铸,又有增、减卯或停铸现象。所以,地方上每年铸钱的总数量已不易作系统统计。尤其是前几朝。现仅据零散史料,将资料比较集中的乾隆二十年左右、道光二十几年地方各省年铸额作大略的勾稽。见下表。
省份及铸局 年代 年铸钱量
史料根据
(单位:万串)
四川 宝川局 乾隆二十年25.9
《清朝文献通孝》万有
文库十通本(下同)
第4995页下、5005
页中、5011页上.
贵州 宝黔局 乾隆二十三年18.625 同上第4996页上、
5001页上、5012页下.
江苏 宝苏局 乾隆五年以后11.1699 同上第4997页上.
福建 宝福局 乾隆五年以后4.8533 同上第4996页上.
浙江 宝浙局 乾隆五年以后12.8613 同上第4998页上.
湖南 宝南局 乾隆二十年 10.8379 同上第4998页上、
5011页下.
湖北 宝武局 乾隆十八年 17.38
同上第5009页中.
广东 宝广局 乾隆十四年后3.4488 同上第5006页下.
广西 宝桂局 乾隆十四年后9.6 同上第5007页下.
江西 宝昌局 乾隆九年以后6.9888 同上第5001页中.
山西 宝晋局 乾隆二十三年4.09同上第5019页下.
陕西 宝陕局 乾隆十六年后12.14
同上第5006页中、
5008页下.
云南 宝云局、乾隆二十八年76.6175 同上第4981页中、
东川局二局、 4989页下、5000 页下
广西局第7局
、5008页中、5009页
上、5011页下、 5016
页上.
直隶 宝直局 乾隆十年以后 7.28 同上第5002页下。
新疆 叶尔羌 乾隆二十四年 50万文同上第5012页下。
合0.05万串
光绪《大清会典事
山东、安徽、 停铸
例》卷219《钱法· 直
河南、甘肃
省鼓铸》.
总计 221.8425
万串,合
22.18425
亿文
省份及铸局 年代 年铸钱量 史料根据
(单位:万串)
四川 宝川局 道光二十几年19.4143 唐与昆《制钱通
考》卷3页18.咸
丰上海聚珍仿宋
印书局.(下同)
贵州 宝黔局 道光二十几年 8.9773同上页22.
江苏 宝苏局 道光二十几年 11.1821
同上,页14.
福建 宝福局 道光二十几年 4.32 同上页25.
浙江 宝浙局 道光二十几年 12.96同上,页16.
湖南 宝南局 道光二十几年 4.8054
同上,页23.
湖北 宝武局 道光二十几年 8.442同上,页17.
广东 宝广局 道光二十几年 3.456同上,页19.
广西 宝桂局 道光二十几年 2.4 同上,页20.
江西 宝昌局 道光二十几年 4.2037
同上,页15.
山西 宝晋局 道光二十几年 1.7472
同上,页24.
陕西 宝陕局 道光二十几年 9.474同上,页18.
云南 宝云局、道光二十几年 17.0568 同上,页21.
东川局二局、
广西局第7局
直隶 宝直局 道光二十几年
6.0756 同上,页14.
新疆 叶尔羌 道光二十几年
0.1722 同上,页27.
山东、安徽、
河南、甘肃
总计 114.6866
万串,合
11.46866亿文
说明 此数为额铸,
当时因减铸,
实际所铸当
比此数少得多.
说明:此数为额铸,当时因减铸,实际所铸当比此数少得多。
以上所考察的数字,中央的年铸额比较系统,康、雍、乾、嘉四朝也基本是其实铸之数。地方各省年铸总额,乾隆二十年左右之数,应是实际鼓铸量,不会仅是规定额数,因当时正处在银贱钱贵时期,清政府正令各省加大鼓铸量以平抑钱价,且当时滇铜正旺,铸料没有问题。道光二十几年之数,只是额铸数。王庆云《石渠余纪》卷5 叙述:“案今(道光后期)《则例》,各省局出钱岁额,除山东、河南、安徽、甘肃久已停炉,余省岁其出钱一百一十一万余串。自银价愈昂,钱本愈贵,大半皆停炉,余省岁其出钱一百一十一万余串。自银价愈昂,钱本愈贵,大半皆停炉减卯”,其所说的道光后期《则例》所记“各省局出钱岁额”的111万余串,也应是额铸,而非实际铸额,因当时“银贵钱贱”,各省“大半皆停炉减卯”。不过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道光初年以前的银贱钱贵时期的铸钱量,所以有乾隆二十年左右之数,已能说明问题。
根据以上两表考察的数字, 乾隆二十年左右, 地方各省年铸221.8425万串,中央以户、工局各年铸71卯的乾隆二十年左右133.1037 万串计,则年铸总量为354.9462万串,合35.49462亿文。乾隆二十年,全国总人口为1.85612881亿人,(注:《清高宗实录》卷503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人均19.12文。 若以乾隆二十一年中央所铸139.3527万串计,则该年总铸量为361.1952万串,合36.12亿文, 人均19.36文。这一数字,是论述清代钱荒所用之数字顺治八年人均1.4文、康熙元年人均3.7文、康熙六十年人均4.3文、雍正十年人均6.4文的13.83倍——3.03倍。其绝对数量,乾隆二十一年的36.12亿文,是前举论述钱荒问题之最高额6.8亿文的5.3倍,多29.3亿文。清代,中央两局几乎年年鼓铸,如果再加上中央及地方历年积累之铸钱,其社会流通量及人均数将大大超过上述数字。
以上所述是乾隆时期的铸钱量,其顺康雍时期某一阶段中央与地方铸钱总量,因资料缺乏,尚未作统计,更谈不到社会实际流通量及人均数。其实,仅以人均制钱数,也不能说明是否存在钱荒问题,以下分析嘉庆后期以前的“银贱钱贵”的问题,附带对此略谈看法。
二
下面再谈这一时期的“银贱钱贵”问题。
嘉庆后期以前,全国除个别地区、暂时性的出现“银贵钱贱”现象外,总的情况是“银贱钱贵”,即低于政府规定的1∶1000 的银钱比价,制钱八九百文甚至七百多文即可换银一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外国廉价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银钱比价低,政府仍始终以固定的1∶1000的银钱比价衡量钱值,便显得“钱贵”, 进一步说,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概念,并不等于钱自身之贵,更不能以所谓钱少而贵说明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实际情况是钱的鼓铸投放量并不小,只是钱之铸造量赶不上大量白银流入量的增加,所以银钱比价始终在1∶1000的线下。
明朝后期以后,外国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且呈递增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作了不少研究。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随后收复台湾,全国经济发展,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发展,乾隆中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后,并未能减少外国对华贸易量,且不断增加,(注:详见拙著《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9页。)所以白银内流量也一直在增加。关于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学者们也作过不少考察, 据彭信威根据外国资料所作的估计, 道光以前的140年间,大约有几亿两之多。(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
对于当时的所谓“钱贵”,清政府官员也只是直观地认为是钱少而贵,因而主张加大鼓铸量。雍正继位伊始,朝臣便集议指出:“钱价腾涌, 总缘制钱尚少……钱多而价自平”, (注:《清朝文献通考》第4981页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因而增卯鼓铸,且以收买铜器、减少制钱含铜量来解决铜源之不足。乾隆以后,进一步加大京局鼓铸量,并令地方各省复炉、增卯,由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福建、陕西数省复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多省,皆令增炉加卯,(注: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9《户部·钱法·直省鼓铸》,及《清朝文献通考》第4994—5022页。版本同上。)其中云南7 个铸钱局铸炉多时达116座。中央二局,乾隆七年、十六年、 二十五年三次加大鼓铸量,比雍正年间增加了近一倍(77卯:152卯)。 这一时期云南产铜正旺, 自乾隆初至嘉庆十六年,年产量一直在一千万斤以上,只7个年份为900多万斤,(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351页。)也为京局、 地方鼓铸钱文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币材。至乾隆三十五年时,由于“官钱广铸流通”,已是“迩年钱价平减”,(注:《清高宗实录》卷503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因而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由于一些省份已“钱价平贱”,铸钱最多的云南已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一二百文,中央开始令一些省局减卯或停炉,直到嘉庆元年才全部复炉。中央宝泉、宝源二局只是减卯,嘉庆四年“全复旧卯”,至嘉年十一、十二年又增加卯数(见前表)。
正是由于清政府固定地追求1∶1000的银钱比价, 在白银不断流入增加的同步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钱鼓铸量,银与钱这两种货币都呈递增趋势,在社会中的流通量都大量增加,这也是乾隆之时的物价较康熙时成倍增长,呈现较缓和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与“币荒”、“钱荒”的结论恰好相反。上文所谓“官钱广铸流通”,以及民谣所诵“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注:昭梿《啸亭杂录》卷1 《纯皇初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也说明当时社会上制钱流通量之大,而不是钱荒,更何况社会上还流通不少私铸铜钱。
考察清代是否存在“钱荒”、“币荒”,不能只看钱币制钱的数量,更主要的,还要看银的数量,以及它是否满足社会需求量。因为在清代,担当货币职能的主币已是银而不是钱,这与明中期以前及元以前的各王朝时期大不一样。只要白银基本满足了社会需求,担当了主币职能,即使是钱少,也不是真正的钱荒或币荒,而是“零钱”少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银很多而非不足。更何况钱也多,乾嘉时期,以制钱所体现的物价指数也比康熙时期大为提高,康熙初1公石的米价是制钱600文左右,乾隆后期已涨至2000多文,(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除了人口增多抬高了米价外,也说明当时制钱之多而造成其实际上的贬值,而不是币少钱荒或钱少而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