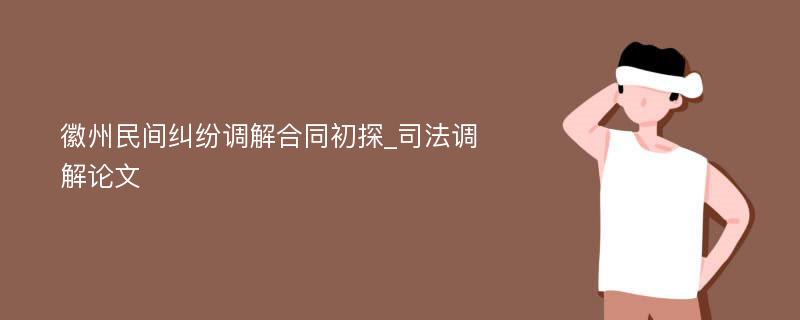
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契约论文,纠纷论文,民间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525(2009)01-001-10
民间调解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民事行为,在封闭的农业生产环境下,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家庭婚姻和财产纠纷两个方面,因此也被称作“户婚田土,民间细故”。所谓细故,是指这些民事纠纷所涉及到的仅仅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却和生活在乡土社会里的人们休戚相关,因为对这些乡民而言,他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几乎都是这些小事,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房舍田宅,乃至于一牛一马,一草一木,都是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大事。民间私约中所涉及到的很多方面,都是由这些所谓的琐碎小事组织在一起的,从买卖到借贷,从析产到继承,每一个细节所涉及到的全部内容,都关系到他们的权利和与此相关的命运。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相对匮乏的环境下,人们只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并且竭力防止这种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依赖人和人之间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社会组织。他们希望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求助于这些群体和社会,以及国家公权力,从情、理、法的不同层面给予必要的救济。在传统社会中独立的人格概念被不断弱化的同时,让每一个失去独立人格权的人,不停地去依赖他所存在的那个群体,当这个群体不能对他施以救济的时候,便企图通过这个群体,向群体所依赖的社会去寻求支撑。当这个社会仍然不能对他施以救济的时候,他不得不越过这个社会,向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国家权力,去寻求最终的救济。每一次祈盼或者寻求,都形成了一个向权威靠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人格的独立丧失殆尽,从而使中国人的契约精神,不但没有能够走向身份的自由,反而极端地走向了权威。民间将这个走向权威的过程和寻找权威救济的过程,习惯地称作——“打官司”。这是一个多么惟妙惟肖,又是多么真切的比喻,似乎每一个人都不能独立地调处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最终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由官员即国家权力的裁判中,其结果是百姓们成了子民,而官员成了“父母”。“讨一个说法”,并非讨一个正义或者自由,而是讨来一个由官方即民之父母的裁判。我们似乎是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只能由父母不断给我们以“教谕”,就好像我们自己不能得出一个让我们彼此信任的评介,而只能听从父母官给我们指明的方向。讨一个说法只能讨来权力的说法,这个说法让所有的人必须听从,而且不允许怀疑。这个说法因为是源于官员的口中,便成了权威的说法,人们只能服从,并且从内心感到“心悦诚服”。这个说法是我们自己讨来的,在讨说法的过程中,把一些人造成了神,或者神的使者的同时,忽略了我们自身的价值。“公道”二字,也时常在传统社会中不断地被使用,“公道”除了泛指社会正义之外,更严格地说指向了公权力即依仗公权力作出的标准,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出现过与“公道”相对应的词汇,相反在中国人的词语中从来就不曾出现过“私道”一词。
“公了”和“私了”成为人们社会中的一组常用的对应性词汇,“公了”直截了当地指向通过公权力的裁判,以极端的权威形式解决民间财产或者权利的纠纷;“私了”的范围显然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的解决方式,由于没有留下足以考察的证据,我们只能在研究中不绝对排除口头解决的存在,但是“私了”过程中,留存很多不同形式或者不同人员参与民间调解的私约文本,这些材料不但丰富了对于传统契约研究的范围,也对我们研究传统社会中民事调解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民事调解,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研究,有的从传统文献中“息讼”观念,对民事调解中有利于消化矛盾,有利于社会安定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并且得出在传统法律被“儒家化”的过程中,民事调解中“和息作用”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极力提倡,并且成为“中华法系”中一个亮点。但是这一结论显然是后人优化的结果,传统社会中所谓“息讼”的观点,正是因为“累讼”的不断发生与重复,因之推出的一种对策。“刑期无刑”不过是一种主张和期望,息讼的社会局面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也同样仅仅是一种主张和期望。然而民事调解的价值不会因此贬低,只是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民事调解和息讼的主张生硬地放在一起,而应该真实地面对传统社会中的民事调解,研究其内部的规律,重新评价传统社会中的民事调解,才能够得出值得世人尊重的研究价值。
在徽州调查时我们采集到很多民间纠纷调解类的文书,对这些文书的属性也曾经产生过不同意见,但最终我们将其归入传统民事私约中加以研究,这是因为这类调解性质的文书,具有当事人合意的意思表达,其内容主要为对调解的约定,有第三方的参与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见证,这和传统契约中中人的参与属于同一属性,另外对于调解约定的违背,还建立了对违约一方的处罚,最后由当事人进行签字认同。这些都属于传统民事契约中的程序要件,因此将这类调解文书归入传统民事私约,是比较恰当的。纠纷调解类的民间私约,名称也带有传统民事契约的显著特征,这类私约的定名常用“清单”、“劝息合同”、“劝议”、“批字”、“劝议合墨”、“合墨”、“遵劝和睦字”、“议据”、“截头文字”等等。我们从中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明朝、清朝、中华民国时期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类的私约,进行比较和研究,以便从中探索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9-1-021)万历三十四年(1606)王鋐卿等因执契争山立清界合同文约(黟县)①
二十二都王鋐卿股、焕卿股与王一朴、王之祯各执契,混争一保土名株树弯山场,因朴祯现砍大培里及株树弯松柴在山。鋐焕二股托中清理,今族众劝息,二家从情公处,将其山埋石定界。除石头本身下崃,焕股已山外,只凭石头降正坞心,上至降自弯心里边以进,系鋐、焕二股管业,自弯心外边以出,系朴、祯二人管业,自定之后,各宜永远遵守。再无得仍前持契混争,如违可罚白银十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准,恐后无凭,立此清界合同文约二纸,各收一纸,永远存照。
万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立清单人 王一朴等(押)
该合同文约中,王鋐卿股、焕卿股因王一朴、王之祯砍伐树木发生土地山场财产纠纷,由于纠纷的双方手中都有对争议标的物的契约,于是王鋐卿、焕卿兄弟请求族众进行调解,最后纠纷双方经过众人的劝息,“二家从情公处,将其山埋石定界。”在调解书中纠纷的双方重新划分了界限,并且在山上埋下界石,结束了这场纠纷。双方还约定“自定之后,各宜永远遵守。再无得仍前持契混争,如违可罚白银十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准”,表明这份调解书具有的效力,如果其中一方违约要认罚白银十两从公,此处“从公”有时也写作“充公”,或者“罚银公用”,表示对违约一方的处罚,并将所罚的白银由族众共同使用。这一表达方式在唐朝敦煌契约文书中已经有发现,被写作“罚银入官”,“入官”与“公用”的意思表达应当是相同的。民间私约中对处罚的约定较为常见,是否对违约一方作出了处罚,现在难以考证,但在约定中明确建立处罚的原则,毫无疑问增加了契约的约束力。这件标本被称作“清界合同文约”,在徽州地区“合同”一词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被普遍地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私约中。
(9-2-无编号)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用图等为谢汪两姓劝息合同(歙县)
立劝息合同张用图、李焕章、李西侯、李鲁詹,今有亲人谢公若即依仁,因啚内二甲汪德泽丁粮未纳以灭甲霸产事,具呈汪去非兄弟即汪然、汪鳌在钮父台案下,汪去非随以斥公案等事具诉,未经催审。今张、李与谢、汪二宅俱属姻戚,且有同学之谊,不忍坐视,近前劝释,先为垫完本年钱粮,以急公事,以全友道,不使终讼。其垫赀候后查清,汪德泽之业以偿前费,回官一事,想上人亦不过化民完粮息讼,衙门自无多费。倘必拘质,两家面同原中告息,不得违议多事。一切费用两造均出无辞。立此劝息合同,一样二张,各执一张为照。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立劝息合同 张用图等(押)
依息 谢公若(押)
汪去非
谢毓英
汪六来(押)
该劝息合同是张用图、李焕章、李西侯、李鲁詹四人主持调解谢、汪两家的财产纠纷所订立的合同。谢公若与汪去非兄弟由于缴纳该年官方征收的钱粮一事发生纠纷,此时谢公若已经将汪氏兄弟上告衙门,“具呈汪去非兄弟即汪然、汪鳌在钮父台案下”。汪氏兄弟也随即进行反驳,但尚未进行审理。张、李等四人,因为与谢、汪两家都有姻亲关系,而且彼此之间曾经是同学,因此“不忍坐视,近前劝释”,决定对双方进行劝息调解。张、李等四人首先代为缴纳本年的应纳钱粮,“以急公事,以全友道”,所垫的费用待查明事实后再由应该缴纳的一方偿还。由于本案已经诉诸官府,但尚未进行正式的审理,因此在这份劝息合同中,张、李等四人还考虑到了官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尽管“上人亦不过化民完粮息讼,衙门自无多费”,但还是约定了“倘必拘质,两家面同原中告息,不得违议多事。一切费用两造均出无辞。”即表示如果一旦官方坚持审理此案,则谢、汪两家和参与调解的人员一起向官方说明,已经进行了“庭外调解”,如果仍需交纳诉讼费用,则仍由纠纷的双方负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劝息合同的立约人是张、李等四人,他们并不是这件财产纠纷的当事人,而是作为第三方主持调解谢、汪两家的纠纷的调解人。而谢、汪等人则在这份劝息合同的最后签字画押,并注明“依息”字样,表示服从该份劝息合同的所有约定。
所谓调解,是指发生纠纷时,在当事人之间,或者由外力参与主持,依据一定的规则,通过劝说、教育、感化乃至施加压力的方式,进行劝解与说和,使当事人之间形成谅解,以达到息事宁人,解决纠纷的方法。这件私约中的调解人与纠纷双方是姻亲和同学,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互接近,甚至应该是平等的,主持调解的一方并不具有权力属性,调解的目的也仅仅是化解矛盾,避免纠纷扩大,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息讼”的作用,但调解人的主观愿望仅仅是“以全友道”而已。参与民间调解的人员的身份地位值得加以注意,对此当代学者也进行了卓有意义的研究。黄宗智先生曾提出“民事调判”的概念,即“民事纠纷的民间调解和法庭审判”,这样一个涵盖性的术语同时包括非官方的和非正式的,也即民间的调解,与官方的和正式的审判。其中也包括黄宗智教授所归纳出的参与民间调解的所谓中间领域或者“第三领域”。这些独立地处于官民之间的领域,形成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在官方与民间二者之间的交搭的空间里,起到法庭意见和民间调解的相互作用。②
在黄宗智先生看来官方的表达应当体现为《大清律例》即国家成文法中,而民间的实践和表达却表现为民间的调解。因此在官方和民间之外,还应当存在一个第三领域,即由衙役、乡保等所组织并且操作的半官半民调处手段。③我国著名学者梁治平先生虽然没有对清代的审判和调解进行专门研究,但他从近代对农村习惯调查出发,认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属于“分工”和“断裂”的不同关系。④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氏则提出清代诉讼裁判的法理学基础应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三个基本原则,而且其中所谓“情、理”的表述,应当被判断为乡族传统的宗法与习惯。⑤
上述学者的研究显然具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源于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所持不同视角。尽管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所具有的法律和习惯的区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但这些研究之间的差异性也为我们探索该命题,留下了值得注意的空间。其中对于民间纠纷调解的作用及价值,特别是民间调解与司法裁判的区别;所谓“第三领域”,是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客观实在,第三领域中的人员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身份,而且这一领域与另外两个领域之间的相关联系;生活在封闭状态下的乡民对所谓“第三领域”的参与是否可以自由的选择,第三领域是否建立了何种规范与规则,这些规则以及通过这些规则的调处的结果,与司法裁判的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此春杨博士进一步提出“如果把调处作为‘第三领域’或者州县官裁决的一种方式,那么都很容易导向这样的结论:‘第三领域’与‘第一领域’、‘第二领域’一样是可选择的,同时具有与前两者相同的法律效力。”⑥
(9-3-无编号)康熙五十二年(1713)汪于嘉与汪师曾汪肇方等劝议合同(歙县)
立劝议中人汪于嘉,今有本啚二甲汪德泽,自顺治初年通户避役在外,逓年钱粮或查业完课或干排赔□至康熙四十二年干排以德泽与德徵亲房不肯赔累,坐德徵代为料理承充二甲户内有土名车田自明堂前后余地约计二亩,于康熙二十九年汪师曾客地承买,康熙三十二年代二甲纳过官等六两有零,四十年册期已经割税,今又轮充二甲正役,户内措办维艰,兼虑日后贻累匪浅,凭中劝师曾量加地价九五色银 正,其银付德徵堂公贮生殖,为后来二甲户役费用,二甲产业在德徵户丁同心协力清查,一同生殖,毋得侵渔强吞,庶常贮充廷公私两,赖自今议后,甲内人丁不得生情异说。立此劝议三张,各执一张存照。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日立劝议中人汪于嘉(押)
遵议 汪师曾伯侄(押)
汪肇方伯侄(押)
汪子芳兄弟(押)
汪符一兄弟(押)
汪彦南(押)
该劝议合同是汪于嘉主持调解,解决本啚“二甲户役费用”问题所订立的劝息合同。“本啚二甲汪德泽,自顺治初年通户避役在外”,因此甲内之事只能由汪德徵代为料理。二甲户内有土地“土名车田自明堂前后余地约计二亩”,康熙二十九年卖与汪师曾。康熙三十二年,汪师曾还代为缴纳了二甲的户役费用。但是当康熙五十二年再次轮到“二甲正役”时,由于汪师曾“户内措办维艰”,已没有能力承担户役费用,因此只能在劝议中人汪于嘉的主持下,协商由汪师曾“量加地价九五色银”若干,并将这笔银钱交由德徵堂“公贮生殖”,用来解决二甲以后缴纳户役费用的问题。此外,在这调解合同中,各方还约定了“二甲产业在德徵户丁同心协力清查,一同生殖,毋得侵渔强吞,庶常贮充廷公私两,赖自今议后,甲内人丁不得生情异说”,使得由顺治初年时汪德泽外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在合同的最后部分,除了立劝议中人汪于嘉外,此次纠纷所涉及的汪师曾、汪肇方、汪子芳、汪符一、汪彦南等当事人也都签名画押,表示将会遵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行事。而其中的“伯侄”、“兄弟”等称谓,则表明了纠纷当事人与劝议中人的同姓亲属关系,可见在当时由亲属或者朋友、同学等作为调解的主持人,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调解人汪于嘉的身份在契约中无法得知,根据调查的结果推知,当时作为民事契约中人的人,在同姓族众中应当具有一定的资质和信义。
(9-4-无编号)雍正四年(1726)吕应珪等立批字(休宁)
立批字吕应珪,缘身曾祖母程氏死后无地安放,借本族叔吕久蕃宙字三千一百十九号山地安放。后因年久朽烂,承族叔吕久蕃将此穴赠身埋葬。今族弟吕其玉等将此号山地尽行卖与何宅为业,身理应起棺让地,因央中求何宅,承何宅念及埋葬年久,不要身起举。日后两姓毋得生端异说。今欲有凭,立此批字为照。
雍正四年十一月日立批字吕应珪(押)
凭中 吕其玉(押)
吕子亮(押)
吕玉成(押)
“批字”是传统民事契约的一种特有形式,具有保证和担保的色彩,有时也在租赁契约中加以使用,在徽州地区民间私约中,批字带有特别说明的意思表达。⑦《雍正四年(1726)吕应珪等立批字》中,吕应珪曾祖母程氏早年去世后,葬在吕应珪向族叔吕久蕃所借的土地上,由于年久,尸骨也逐渐朽烂。后族叔吕久藩将墓地使用权赠予吕应珪。现在族弟吕其玉要将整块山地卖与何姓人家,按照徽州地区的习惯,吕应珪只有对墓地的使用权,因此应当“起棺让地”。但是由于该棺木埋葬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吕应珪不愿意挪动棺木,所以托中人吕其玉、吕子亮、吕玉成向何姓人家求情,求情的结果是何姓人家答应了吕应珪的请求,双方达成了合意,吕氏曾祖母的棺木可以不用挪动。为了“日后两姓毋得生端异说”,所以建立了这份批字,并由吕应珪和三个中人作为见证签字画押,如果将来吕、何两姓人家因为此事发生争执,可以作为凭据。这份调解书不是在出现纠纷以后,对平息纠纷的调解,而是在可能引起争议的情况下,预先作出的互相承诺,因此使用了“批字”,从中可以发现徽州地区民事调解类的私约,具有先见和预防的功能。
(9-5-38)嘉庆十九年(1814)程腾远、詹焕文等劝程森、叶氏守山林合墨(婺源)
立劝议合墨人程腾远、詹焕文等,原眷族程森祖买鸠栗树坞山场,发与叶氏看守。去年腊月森家查悉,胡尚顺盗去该山大竹四根,叶程氏私瞒不报。程森特邀眷族腾远等,向叶氏追究,收回山业,前立守山字约邀还。叶程氏自后中间水坑之西,上至连五,下至坑山场,程森收回管业。水坑之东山场即由叶程氏管业。自今之后,各管各业。叶程氏所欠森家上年租谷七十斤,劝森作补叶氏守山辛力,两无异说,立此合墨,一样两张,各执一张存据。
嘉庆十九年二月 日立劝议合墨人程腾远(押)
程颐娄(押)
程禹三(押)
詹焕文(押)
程森(押)
仆妇叶程氏招弟(押)
同男叶傩兴(押)
书 程煜芝(押)
通过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调解类契约的初步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徽州民间纠纷调解类契约具有格式化的倾向,首先说明调解人,其次是被调解人以及发生争议的事由和经过,再次是争议双方在调解人的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结果。如果有其他约定的,则在调解结果之后列明。最后写明该份契约立约年月以及所有参与立约的当事人和中人签字画押。
上录“合墨”是立劝议合墨人程腾远、詹焕文等人主持程森和叶氏解除看守山场合同以及相关争议所订立的合同。由于当时的合同是用“毛笔墨水”写成,同时体现合同双方的合意,因此也称作“合墨”,多见于合伙类私约、纠纷调解类契约。争议发生的经过是程氏族人程森祖上买有“鸠栗树坞山场”,程森将该山场交由叶程氏看守。去年腊月时程森经过调查发现胡尚顺偷走了该山场上的“大竹四根”,叶程氏作为看守山场之人竟然“私瞒不报”,因此程森特意邀请了同族的程腾远等人,向叶氏追究责任,并要求叶氏返还其所看守的山场,之前所订立的“守山字约”也一并归还。程森与叶氏达成了协议,即“叶程氏自后中间水坑之西,上至连五,下至坑山场,程森收回管业。水坑之东山场即由叶程氏管业。自今之后,各管各业”。此外,叶程氏曾欠程森家去年应纳的“租谷七十斤”,在这次调解中,折抵作为叶程氏的“守山辛力”,即看守山场所得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私约结尾处,所有参与争议调解的当事人都签字画押。由于叶程氏是女性,在传统社会中不具有独立参与订立私约的资格,因此由她和她的儿子叶傩兴共同签字画押,共同组成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
本案中叶程氏,应当是程氏的女儿乳名招弟,嫁入叶家后则改称叶程氏。徽州地区多山,交通不便,女儿出嫁邻村甚至本村异姓的现象较多,因此叶程氏和产生纠纷的程森应具有同姓亲属关系,但私约中未能说明,而冠以“仆妇叶程氏招弟”,且向程森交纳租谷,叶程氏似为程森家佃户。但又从参与调解各方称谓中有“眷族”一词分析,具有亲属关系的纠纷,在当地适用亲族内的调解。
(9-6-022)咸丰二年(1852)方镇洪等人立遵劝和睦文约(休宁)
立遵劝和睦字人方镇洪、镇顺等,兹因于道光三十年九月间,堂兄方灶玄与族叔方时院一时忿怒将院子冒手误伤致命。玄知理斥情亏,浼中登门哀求劝解,愿出衣衾棺椁,斋醮超度,应该承值共用所费资财银钱四百五十两之数。不料灶玄家资稀微,尽作银钱不足三十余两之数,其余无所出处。以致拖累亲房,各自量力愿出,再若不敷支用,镇洪与镇顺二人面说对半承值,两相无异。不料本月间须要归还罗添右先银钱廿两之帐项,须要二人派出,是以口角。因为前后支收不清多寡者,三百余文之数,借一为末之小事而伤兄弟之大伦,是以邻居邀集苦劝,但将前后之事一应说明,二各自愿遵劝,永无生端,其有不愿者,将本收回,应该洪、顺二人派出无辞。亦有不愿收者,名曰本德也。自立之后,务要各守安分,切莫缘木求鱼。二各心平气和,永无反悔,若有悖墨反悔者干罚银钱十两以备酒酌公论无异。恐后无凭,立此遵劝和睦字一样二纸,各收一纸,永远为据。
计开出钱例名于后
方时绣同智六、智七三人产业、房步并会本,共计钱一百八十三千文 时桂出钱七千文 时杜出钱三千一百四十五文
方美章公出钱九百七十五文 时胜出钱一千四百六十二文 时游出钱二千五百廿文 上有出钱十五千二百文
方社灶公会出钱二十五千二百文 镇滪出钱九百七十五文 灶高出钱五千文 仍余不敷镇洪、镇顺二人均派
咸丰二年六月日立遵劝和睦字人 方镇洪(押)镇顺(押)
凭中方同书等(押)
依口代书人方锦云(押)
在《咸丰二年(1852)方镇洪等人立遵劝和睦文约》中,调解人方镇洪、方镇顺的堂兄方灶玄与族叔方时院发生争执,方灶玄一时愤怒,失手打死了方时院的儿子方冒手,应当属于伤害致死人命的刑事案件。方灶玄自知情理难容,因此托中人“登门哀求劝解,愿出衣衾棺椁,斋醮超度”,总计需要丧葬赔偿等费用共白银四百五十两。但是,方灶玄家境贫寒,竭尽所能只拿出三十几两白银,因此方氏族众“各自量力愿出”凑钱,以救助方灶玄,并约定如果仍然不足,剩余部分由镇洪、镇顺承担。此时调解人方镇洪、方镇顺两兄弟“本月间须要归还罗添右先银钱廿两之帐项”,发生了口角,后来经过邻居的劝说,认为不应该为这点小事而“伤兄弟之大伦”,镇洪、镇顺两兄弟重归于好,同意继续合作,主持族众凑钱一事。方氏族人为方灶玄凑钱,具有借贷的色彩,事后方灶玄应当归还,但私约中未表明利息的计算方法。同时在和睦文约中还约定“有不愿者,将本收回”,即不愿意再继续借的,将本金收回,所缺者仍由镇洪、镇顺二人派出。如果有不愿收回本金者,“名曰本德也”,其本金即成为善款,不再收回。于是经过族众协商后,众人共计出资二十四万四千四百七十七文,计白银二百两左右,加之当事人方灶玄拿出三十余两,大约凑足一半或稍多,其余尚有近二百两,应由方镇洪、方镇顺代为付出。同时方氏族人还约定,如果有违约者,将被罚钱十两,用于准备酒席向众人请罪。
《大清律例》卷二十六《刑律·人命》之“戏杀误伤过失杀伤人条”中规定:
“凡因戏以堪杀人之事为戏,如比较拳棒之类。而杀伤人,及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各以斗杀伤论。死者,并绞。伤者,验轻重坐罪。其谋杀、故杀人,而误杀旁人者,以故杀论。死者,处斩。不言伤,仍以斗殴论。
若过失杀伤人者,较戏杀愈轻。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过失,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如弹射禽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驾船使风,乘马惊走,驰车下坡势不能止;或共举重物,力不能制,损及同举物者。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殴杀伤人罪,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营葬及医药之资。”⑧
根据清朝法律的规定,方灶玄“一时忿怒将院子冒手误伤致命”,按律属于斗殴杀人,且死者为方时院之子,当属“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承担斗殴杀人罪,严重者可以处绞刑。即便是按过失杀人,也应当“各准斗杀伤罪”,虽然罪行“较戏杀愈轻”,也应当依律收赎,给付被杀之家。但在调解中将方灶玄的斗殴杀人罪,降为误杀,并且没有报官治罪,而采用了民间“私了”的方式予以解决。
这件遵劝和睦文约解决的是伤害致死引发的纠纷,由此可见,在当时民间宗族调解的范围已经超越了财产性质的纠纷,甚至连人命案件都属于当时可以调解的范畴之内。宗族社会的救济能力,可以通过族众集资的形式加以实现,甚至这种救济淡化了因刑事犯罪而应该承受的法律制裁。
(9-7-030)咸丰九年(1859)汪氏万年山帐(婺源)
咸丰九年四月念一日汪日梅立
万年山祖坟,姚兆达于道光念一年,私下至本啚缮书黄有初谋买山税一分二厘,至咸丰九年三月初五日,身族往坟挂纸,主家林英嫂说及此事,讵兆和于十一日,竟在该山开茔,串同长滩俞汉洋出卖,身于十二日往坟看视,果开在坟傍里边。身十三日,同意开五元位三叔,清华亦舒兄士祖眷,至姚族投词,不能熨贴。十四日,意开同士祖眷,到朱坦宅投约,本日约保仍到亦舒兄家住宿。十五日,约保同前原人至姚家调停,安奠勒石加禁,将茔立碑,改作身家护坟息事。兆和一边税亩未曾割脚,过后半月,长滩俞汉洋,至位三叔家谈及此事,位三叔于四月十五日,复集原中约保,至姚兆和处,将谋买山税退割仍归本户,税签缴回,以全清业。当立议据二张,各收存照,以免姚姓将税复卖他处。身族祖坟茶坦,省得与人混争,故承约中用洋二十二元了事。今将此事缘由一一记明,身族友丁底下捡看,便知来历。
八十八世裔孙日梅书记
《咸丰九年(1859)汪氏万年山帐》为纸捻装,一册,手工抄写,封面题“万年山帐”四字。一件山场纠纷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告诉,引起诉争,后经调解,另一方贴补二十二元将纠纷平息。将这类纠纷情况及调解书进行记录,并传之后人,在徽州地区民间较为常见,被称作《山帐》,或者《山书》、《山凭》等。在《万年山帐》中除汪日梅在开首处书写的引文以外,后面还附有清咸丰九年“万年山议据文”、清顺治九年“万年山业票据”、咸丰九年“向姚兆和诣山开茔理论词文”、“姚兆和加禁勒石碑文”等附件作为证据,以便后人查阅。这次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曾经出示了案件发生前已经建立的契约,作为纠纷时的重要书证。
万年山是徽州婺源大鄣山中的一座小山,地处今江西婺源县北部清华镇附近,汪氏家族祖坟就葬于此山之上。道光二十一年,姚兆达私下里向十六都二啚的缮书黄有初,买得“贞、必两号税亩一分二厘”的土地。“缮书”即“代书人”的别称,以替人书写信函契据和诉状为职业,如果经过官方考核和许可,即成为“官代书”。传统社会中民间识字者不多,因此在乡间存在以替人代书写字为职业的“缮书”。姚兆达所买的土地就坐落于十八都万年山,与汪氏祖坟邻近。咸丰九年,姚兆达之弟姚兆和在该土地上“诣山开茔”,此事被汪氏族人知道后,随即向姚族“词投理论”,但未能解决问题。后经过调查发现,“该山贞字八百八十五号,向系十六都二啚汪日旸户全业,清丈业票,该号四至俱已载明”,即所买得的贞字号土地原属于汪日旸所有,且有官方登记在册和交纳税赋的业票为证。黄有初并不具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在乡约保长及众多中人的主持调解下,姚、汪达成协议,姚兆和则收“洋二十二元”,“将贞、必两号税亩仍退割付汪日旸户下完纳”,以取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并防止姚姓将土地再卖他姓。这件调解契约中记录了多次调解过程,第一次向姚姓族人投词理论,第二次“约保同前原人至姚家调停”,最后“复集原中约保,至姚兆和处,将谋买山税退割仍归本户”。最终在当事人出资洋二十二元后,双方形成谅解。
万年山议据文
立议据人胡锦文、姚汉川、俞汉洋等,缘兆和先兄乖达,买得十六都二啚缮书黄有初贞、必两号税亩一分二厘,坐落十八都万年山。于咸丰九年,兆和诣山开茔,致汪姓词投理论,身等两属亲朋,不忍坐视。今查该山贞字八百八十五号,向系十六都二啚汪日旸户全业,清丈业票,该号四至俱已载明,故劝兆和领价,将贞、必两号税亩仍退割付汪日旸户下完纳,以全清业,以保祖坟。两造心平,不愿滋事。自议之后外姓人等、汪姓坟山界内,毋得再行争端异说,恐后无凭,立议据存照。
咸丰九年四月 日立议据人约保胡锦文押
一样两张各执一张存据中姚汉川等押
依议胡兆和押
汪旺开押
代书臧位三押
万年山业票据婺源县为清丈事
部 院 司 道 府明事奉贞字八百八十五号公正丈量取册申报在案,各号丈过田地山塘,合给凭业,印票业人以等各归户供纳税粮,永为遵守。须至业票者。
十六都二啚五甲汪日旸户丈积步
(附)西至古路,东至水圳,南至俞贤武等田,北至路及胡献福田。
计山税一亩五分七厘正
坐落十八都土名万年山
顺治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俞兴兆书算
向姚兆和诣山开茔理论词文存照
开茔戕祖,欺窵害生,叩验呈究事
被姚兆和
证身祖显龙公历葬贞字号土名万年山界内清业,外姓至今并无戕害。于本月十二日身族友丁至坟挂扫,验被兆和界内开茔,戕祖害生,不得不叩公呈究。
姚兆和加禁勒石碑文存据
加禁万年山所是汪姓祖坟界内,毋许再行侵害,如违呈究。
咸丰九年三月十五日十九都二啚约保胡 锦文等 押
经过调解后,姚兆和在争议的地点刻了一块石碑,碑文为“万年山所是汪姓祖坟界内,毋许再行侵害,如违呈究。”至此双方经过调解,结束了纠纷。这件民事调解私约中,记录了“十九都二啚约保胡锦文”两次参与调解的过程,约是“乡约”的简称,保即保长,胡锦文是十九都二啚的乡约同时也是保长,故连称“约保”。
清朝的乡正、约长、保长、里正等先由民间公举,或者由其前任代为推举,其身份仍属乡民。经过推举后再由州县地方官方加以批准并确认备案,即具有乡约和保甲长身份。地方官方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包括治安管理以及解决民间纠纷,维护乡间秩序等职能。四川巴县清朝的地方档案中,保存了地方官员对于乡保的要求,“(团首)钱债口角细故随时排解,勿令兴讼。”“甲内遇有户婚、田土、钱债、口角等项细故,保正甲长妥为排解,以息忿争。”“一切牙鼠雀角钱债细故,允当善为排解,毋使兹讼。”⑨经过地方官的许可,乡正、约长、保长、里正等具有了调解民间纠纷的身份。
据清《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载:“一、凡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听保甲长稽查。违者,照脱户律治罪,地方官徇庇,照本例议处。凡佥充保甲长并轮值、支更、看栅等役,绅衿免充、齐民内老、疾、寡妇之子孙、未成丁者亦俱免。派兵丁、书役与民户同编,本身免充保甲长。”⑩可以看出,这种纠纷调解的权力,源于这些人员在乡土社会中的自身资质,同时也源于地方官员的授权,这是这二者的结合,使地方乡约保甲长,具有了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身份,但就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言,仍然属于地方乡民身份,而非官方派出之吏员,因此并不能判断为官民之间的独特的阶层,也不应当属于独立于官民之间的“第三领域”,或者相对独立存在的权力群体。(11)
(9-8-无编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桂亭墓地民事纠纷言明字据(休宁)
立言明字人陈桂亭,缘因日纯公祖茔一事与族侄吉祥等争端。蒙亲族再三劝导,不得相争,以全族谊亲族理处,帮补英洋七十七元,交桂手收,作旅费。自后两造均愿息争,各尽其道,所谓和气致祥也。今预有凭,立此言明字照。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立言明字陈桂亭(押)
凭族长 陈长春(押)
见场人 金茂桂(押)
汪焕卿(押)
汪似山(押)
亲笔
徽州地处穷山峻岭之间,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人均可耕地很少,用于安葬的墓地显得十分珍贵。因此由于争夺墓地引发纠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事人陈桂亭因墓地之事与同族侄子发生争端,在亲族的再三劝导下,双方以族谊为重,由纠纷一方陈吉祥补偿陈桂亭英洋七十七元,在“和气致祥”的理念下,达成息争的协议。这份调解协议书称为“言明字据”,表明徽州地区纠纷调解书除了使用合墨、和息合同等外,还使用“言明字据”,作为民间调解私约的一种形式。参加调解的除一名族长外,另有三名异姓见证人,对这三位见证人的身份目前尚难以考证,这与族内纠纷完全由族众参与的现象有所区别,值得加以关注。
据清《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载:“一、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12)这是国家成文法对于宗族设立族长的规定,族长应当是宗族中具有最高身份地位和威望的尊长,作为家族中的尊长,在宗族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但将这种权威延伸到乡土社会中去,就需要国家对其进行授权,以便在家族以外的环境下继续行使其权威作用。政府通过家族尊长对家族进行管理,家族尊长依赖政府的授权和保护,行使对其家族及相应社会的管理权,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沟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试图在民间找到这种权力沟通的有力证据,直至在徽州调查时我们偶然间在徽州歙县发现一件雍正朝的《委牌》,才证实了我们的推断。
《雍正六年(1728年)徽州府歙县正堂给汪氏族正汪文周委牌》:
“奉旨严饬州县设立族正案。当经出示饬行公议遴举去后,今据二十五都一 族正县认前来,据此合给委牌。为此牌给族长汪文周前去,即便遵照先行。奉旨事理族内之中,不时稽查。如有素不务业,游手好闲,为非匪类及行踪诡秘不法之徒,许尔族正据实指名赴县首报,以凭严拿究治。倘有容隐徇情不首,事发之日与保甲等一体连坐。该族正务遵功令稽查,不得借端生事扰民,察出致干未便,均毋故违,须至牌者。”(13)
委牌,也就是俗说的委任状,这件委牌为木板雕印,蓝色水墨印刷,薄皮纸,上有歙县正堂官印。这件委牌的发现,使我们将地方官吏和宗族尊长之间的权力关系,有了更加准确的认知。
除了发现雍正朝委牌之外,我们还在歙县采集到一件清光绪年间雕版印刷的“知县敦请族长调处法律纠纷”的空白法律文书:
“……为此谕仰该_______知悉此事,尔如能出为排解,俾两造息讼,最为上策。此谕仍交地保缴销,若不能息讼,即由该族长告知被告,令其於__月___日午前到城,本(衙)每日於未初坐堂,洞开大门,该原被告上堂面禀,即为讯结。……此因该族长素来公正,言足服人,帮饬传知,并非以官役相待,亦不烦亲带来城,不过一举足、一启口之劳。想该族长必能题本□□爱民如子之意,共助其成,实有厚望……”。(14)
这件文书当属《县谕》,其中对于民间纠纷,以县谕的形式要求知情人予以调解,以达到两造息讼,并将调解的结果报之地方保甲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由该族长通知被告于制定的时间到县城,以便审理。官方认为“族长素来公正,言足服人”虽然不属于官役,也不必亲自来城,但仍要求族长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汇报。表明地方官员不但尊重族长,且采纳族长的意见,从而在族长协助下,实现调解或者作出相应判决。族长的权力源于宗族中的宗法势力,同时也源于地方政府即国家权力给予的肯定和保护,在这两者权力的互相作用下,使族长成为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反之,这种乡土中的权威又再度保护了赖以生存的社会,保护了使其存在的社会,并使这种互相保护在封建社会中得以凝固下来,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运行的基础。
在传统社会中,通过国家权力和成文法的调整,公权力作用下的救济手段,是人们所期待的最终救济,尽管这种救济的作用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因此当国家法律缺失的时候,并不足以动摇那个封闭社会的全部秩序;传统道德和宗法观念的制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私权力作用下的救济手段,被普遍的加以利用,并且成为通行的救济方式,这种私力救济以公权力作为后盾,互相支持又互相配合,形成乡土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行为规则,当出现道德缺失的情况时,乡土社会会以自发和自助的形式弥合这种缺失,并使其恢复原有的秩序,尽管这一恢复将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而这部分社会成员通常属于那个群体中的弱者。另一方面人们采用建立契约的方式,约定确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最大限度地信守这些约定,使他们的生活继续处在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之中。当信用出现缺失的时候,人们又反过来求助于乡土社会中私权力的调整和救济,甚至最终求助于国家法律公权力的调整和救济,“私了”和“公了”了而不了,如同轮回一般地周而复之,使封建社会持续地处于内在的稳定机制中,并且依赖于这一机制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运行了两千余年。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徽州民间习惯调查”中关于传统契约中涉及民事调解的部分内容。
注释:
①本文中的标本序号为调查时原有的分类记录,标本的标题为编者所加,括弧内的地点为契约的发现地。按明清时期徽州的地域,将现在隶属江西的婺源县,仍归入徽州,以保持原有徽州地域环境的完整性。标本中的异体字已经改为标准简体字,个别模糊不清的文字或者无法辨识的文字,用□表示,原有明、清、民国时期的纪年,用括号内加公元表示,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标本中的其他部分为了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②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③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98年版,第132页。
④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⑤[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另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⑥春杨:《晚清乡土社会的民事纠纷调解及其变迁——以徽州私约为起点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⑦批约、批字、批等作为契约定名除民事调解类私约之外,有时还用于租赁类契约的定名。在徽州调查时曾采集到一批“批租合同”、“退租批字”等,表明批字的使用较为广泛。
⑧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
⑨《道光二年六月初五巴县告示》,载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⑩《户部则例》一百卷,清户部官撰,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1)春杨:《晚清乡土社会的民事纠纷调解及其变迁——以徽州私约为起点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12)《户部则例》一百卷,清户部官撰,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3)该委牌由田涛先生采自徽州歙县并收藏,原件为木版雕印单张。
(14)该批文由田涛先生采自徽州歙县并收藏,原件为木版雕印单张。
标签:司法调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