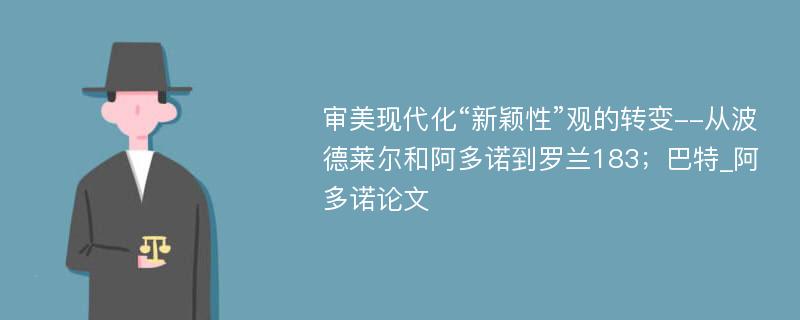
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183;巴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新奇论文,巴特论文,莱尔论文,阿多诺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2—0130—04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转变:“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的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是变化和新奇。”[1] (P2)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这一转变的始作俑者。
在此之前,“新奇”并不具有至高的审美价值,甚或被贬低。在柏拉图看来,对“新奇”的崇拜是应该被禁止的:“没有比这种语言和观念更危险的东西了。”[2] (P553)康德对“新奇”采取客观的态度,认为它“可以使注意力变得活跃”[3] (P48)。席勒则把对“新奇”的爱好视为一种“初级趣味”[4] (P149)。但到了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波德莱尔这里,“新奇”则被视为审美价值的核心。
审美现代性在双重压力下——美学传统和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逐渐达到了内爆状态。现代艺术暴露出自身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感而危机重重。阿多诺在反思现时代的艺术危机的同时,为现代艺术做了最坚决的辩护,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正如比格尔所说,是“新奇的范畴”[5] (P132)。作为解构主义者的罗兰·巴特则把“新奇”看作“全部批评的基础”[6] (P51)。三者都对“新奇”或“新”作了最高的肯定。但实际上,“新奇”的内涵在他们那里,不仅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在波德莱尔笔下,“现代生活的画家”是永远处于精神康复期的病人,他恰如孩童一般,在最高的程度上对任何事物——即便是最平淡无奇的事物——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孩童般的眼里,任何流动中的、偶然的“现代事物”都是新鲜的,具有“新奇”的美,艺术家就是要在普通的、短暂的、偶然的事物上去发现永恒的美。因此,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地表明:他要“建立一种关于美的合理的、历史的理论,与唯一的、绝对的美的理论相对立”[7] (P475)。这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现代性经典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7] (P485)同时,他还认为,每个古代的画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他们的“现代性”就在于他们抓住了他们时代的偶然的、短暂的,因而也是独特的东西并将其同永恒不变的东西结合起来转化成“美”。
波德莱尔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第一个在艺术上提倡现代性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赋予“现代性”以普遍意义的人。[8] (P41)他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而只是表明“美”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所以说,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就历史意义而言是中性的。波德莱尔反对“历史进步”观念,所以他没有赋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任何特殊地位。但是,波德莱尔强调,艺术家要重视时代的特殊美,也就是“新奇”的美。艺术家要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保持同新事物的积极关系,更要感受“现时”,并将这种“现时”体验为“饱满的瞬间”。艺术家要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新奇”的事物,并锻造出新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
“无论人们如何喜爱由古典诗人和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普遍的美,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忽视特殊的美、应时的美和风俗特色。”[7] (P473)“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7] (P486)时髦的生活场景和丑恶的社会现象都被波德莱尔尽收眼底,炼制成纷繁复杂、美丑并置的“现代性”的美,故而有人称“波德莱尔的工作只有在魔鬼般的与仿冒的光照中才可能得到理解”[9] (P9)。时尚就是“新奇”之美,但时尚乃是一个延续不断的平庸化过程。“依照波德莱尔所提出的机智的悖论,天才的任务恰恰是发明一种俗套。”[10]
波德莱尔对“新奇”之物的“礼赞”当然是对物化现实的一种讽喻。时尚确定了被爱慕的商品所希望的崇拜方式,波德莱尔把原本附属于商品意象的时尚变成了具有最高审美价值的“新奇”之物,这种讽喻的技巧让本雅明和阿多诺赞叹不已。本雅明用类似的方式构造了“辩证意象”的概念,阿多诺则将这种“讽喻”看作是现代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最有效的策略,并指出:“继波德莱尔之后,伟大的艺术家一直与时尚结成联盟。”[11] (P330)
艺术家不仅要关注“新奇”之物,还要有“新奇”的表现形式。新奇之美的表现有赖于主体的独创性和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波德莱尔竭力反对摹写“自然”。在他看来,想象力是一种神秘的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王后。“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象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象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想象力的能力。”[7] (P411)
把“新奇”作为审美价值的核心,是对传统美学强有力的挑战。传统美学是要使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并保持和谐的状态,防止灵魂受到“新奇”之美的刺激。但现代美学则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体验到“惊颤”。
阿多诺认为,“新奇”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具有消费品的特征。消费品通过“标新立异”,使自己摆脱千篇一律的批量供应,从而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艺术中的“新奇”是从这一经济范畴中“盗用”的,“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审美补充物”[11] (P38)。艺术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商品社会里是无能为力的,它自身也必须把“新奇”作为自己的价值诉求。但现代艺术的力量在于:忍受着这种自我矛盾而默默地与它的对手——商品交换逻辑——相纠缠,因此成为真正的现代艺术。这种说法含糊其辞,实属无奈。现代艺术的过分“新奇”,实际上是对观众(读者)的拒绝,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如果以“新奇”来招揽观众,则又难以洗刷“拜物教”的罪名,丧失了自主性。
实际上,阿多诺把“新奇”看作是现代艺术对抗拜物教现实的一种策略。对“新奇”的渴求赋予现代艺术“生成”和“运动”的性质。现代艺术之“质”的规定性不是一个坚固的“核”:现代艺术作品必须在运动中凸现其审美的意义,而在同一运动中又要否定这一审美意义;作品必须清楚地表明,对意义的否定也是某种意义,就仿佛在肯定性的表象和毫无遮掩的反艺术之间做某种平衡,两者之间仅有一根游丝维系着。[12] (P15~16)现代艺术同物化现实打的是游击战。
现代艺术渴求成为“新奇”之物,它通过把新的活生生的异质性的成分纳入自身而获得“新奇”的“惊颤”效果,同时它自身也不断地处在自我瓦解的过程之中。阿多诺沿用了王尔德的一句名言:“现实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应当模仿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作品来模仿现实。”[11] (P231)当然,这种颠倒的“模仿”赋予现代艺术以“先锋”的性质。作为人工制品的现代艺术常常把一些反艺术的因素纳入自身,所以作品自身成为异质性因素对抗的场地,是“星丛”,而非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作品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成为等价的,瓦解为绝对的偶然性。艺术作品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结合,它自己的不可能性生动地证明了不和谐是和谐的真理。”[13] (P359)
现代艺术对“新奇”的诉求,实质上是以其“非人化”的面目来抗争现实的“非人化”。所以现代艺术不再追求“绵延”(duration)和“不朽”,“创造永久性艺术作品的努力已遭败绩”[11] (P49~50)。“新奇”不是主体赋予艺术品的独创性(originality),因为独创性总是包含着全新的、闻所未闻的要素,它标记了作品独一无二的特征,但现代作品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风格的毁弃。如果说它有风格的话,那也是在它取消风格之无风格中偷偷引入的。传统的独创性总是和天才,或者某种心灵的突发奇想之上,而现代艺术的“独创性”则是基于对艺术自主性的反思。
“新奇之物是对新奇之物的渴望,而非新奇事物本身”[11] (P57)“新奇”所激起的“惊颤”体验是现代艺术存在价值的最高确证。艺术在物化现实中的“新奇”是作为艺术作品不断生成的“动能”而获得价值的。阿多诺反复强调,“新奇之物作为有待破译的密码,是死亡的意象”,如此等等。究其实,阿多诺的“新奇”之要义就是要粉碎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概念,并将艺术从物化现实中拯救出来。所以,“新奇”不是像在波德莱尔那里,是一个标志着主体的独创性的概念,而是阿多诺式的否定辩证法的“驱力”而已。对“新奇”的渴求迫使艺术消失在遥不可及的遁点,其所指向的就是现代艺术的乌托邦。
罗兰·巴特认为:“新不是时尚,它是一种价值,是全部批评的基础。”[6] (P51)“新奇”对立于“陈规旧套”。而陈规旧套就是重复那些没有任何神奇和激情的词语。通过重复,它们往往会成为一种权势语言。这种重复通过各种公共机构如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等进行。它们具有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是一种“多格扎”[14] (P97)。陈规旧套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重复运作,它塑造了人的“主体”的坚一性。
在巴特看来,所谓的“文学”、“作品”之类的概念何尝不是各种“陈规旧套”的重复运作呢?“文学”是一种套数、一种秩序、一种系统、一种结构化的认知领域。[14] (P93)所以必须要用“新奇”来破除这种意识形态的魔咒,“新奇”的生产方式则是那不断解构、破坏而又编织着的“文”。“文”(Texte)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织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纹理内,自我消融了。”[6] (P76)在“文”的编织中产生了两条边线:一条是正规、从众、因袭的边线,而另一条边线则是变幻不定、空白,它仅是其发生作用的空间而已。文的生产就是对这两条边线之界线的破坏,使得两条边线“交臂叠股”,成就“欲的辩证法”。
“新即是醉”[6] (P52),醉就是热衷于例外;新奇之物,就是对不言而喻之物的抛弃。新奇之物引发的“醉境”是社会性的陡然迷失,随之,主体、个人等一切都迷失了。巴特对“阅读”的经验区分为两种,即悦和醉,这跟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有密切联系。悦的满足来自于“自我”对意识形态的屈服,是一种文化的养生术。但无论何时,社会语言、社会言语方式支撑不住“我”,主体便会发生飘移,就产生了“醉”的渴求,主体的分裂出现了。
“文”追逐着“新奇之物”,就是为了逃避社会的异化。任何固定之物,任何重复之物都会被纳入交换的开支循环之内。为了逃避异化,文必须以“新奇”为自己存在的价值所在。“新奇”并不是创造某种未曾存在之物,而是自身的毁坏,先于任何固定的意义形成而一路撤退。所以巴特在评论他的朋友、新先锋派作家索莱尔斯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拒不因袭。”[14] (P189)
罗兰·巴特对“新奇”的推崇,就是对任何固定、不言而喻、重复之物的弃绝,就连一向最坚实的“主体”也要经受弥散和分裂。所以他所谓的“新奇”不是主体、更非天才意义上的“独创性”。“新奇”对立于任何既成之物,是作为“差异”之物(物化现实的“他者”)呈现的,这和阿多诺的意旨相通。但不同的是:阿多诺的“新奇”主要来自于艺术作品对外在异质性现实事件的反应,是通过把反艺术的东西纳入到自身中而获得的;而罗兰·巴特的“新奇”则是指“意指过程”,文的编织就是对外在现实的拒绝,它只是在“欲”的辩证法的催动下的“互文”。
所谓的“意指过程”就是指能指的不断游离,互相指涉,不再寻求有固定意义的所指,将意义在肉感的范围内来生产[6] (P74)。“文际关系”(inter-texte)则是指文之间的相互因袭,直接的或变相的引用,是“一种往复而现的记忆而已”[6] (P47)。巴特意在强调,任何的文都不可能逃脱这张早已织就的语言和意义之网。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仍是与首次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自那时起,够得上称为现代作品的显著标记是‘新颖’,它将为以后出现的风格所克服和废弃。”[15]“新奇”作为这一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之一便处于这种蜕变之中。
波德莱尔的“新奇”是对个体的“独创性”的推崇,而阿多诺则否认艺术作品是出于主体意志的“独创性”的创造。但是,在让艺术作品同“时尚”结盟,使艺术作品充满商品意象,以此对抗物化现实,以及对艺术之“惊颤”体验的强调等方面,阿多诺是波德莱尔美学遗产的继承者。罗兰·巴特的“新奇”既不是时尚,也不是独创性,而是“文”在身体欲望的范围中的生产,因此罗兰·巴特的“新奇”截然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新奇”。
罗兰·巴特和阿多诺都将“新奇”视为一种“瓦解”的动能和破坏性的力量,从而使得“作品”处于运动和生成之中,以此来抵抗物化现实的交换逻辑;而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作品标识着作为意识形态构造之物的“主体性”的消解。但另一方面,对阿多诺来说,“新奇”的价值不是来自“新奇本身”,而是对“新奇”的渴求,它自身来自异质化的现实;而罗兰·巴特则把“新奇”本身视为价值,是“全部批评的基础”;“新奇”不是来源于外在的异质性的现实,而是“欲的辩证法”在“无限之文”的缝隙处、断裂处的生产,所以,阿多诺和罗兰·巴特又处在紧张的对立之中。
总而言之,他们三者所说的“新奇”的内涵之间既有叠合之处,也存在着分歧乃至对立,这反映出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内部冲突、断裂的场域。但它们的“共性”却无疑地表明: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审美现代性对“新”的价值的崇拜。用杜夫海纳的话来说,“那就是求新,不断地求新。发明的不断增加,不断地加速风格的衰退与更替。在不断增加的发明之中,存在着某种狂热的东西”[16] (P187)。这种对“新奇”之物的“狂热”会不会导致一种价值的“虚无”?当然,在尼采、阿多诺或者罗兰·巴特看来,遵循着某种僵化的价值体系,安然于陈规俗套者才是真正的价值虚无主义。但当“新奇”追逐的仅是消失在无限远方的遁点的时候,或者只是在“无限之文”中围着“欲望”打转的时候,审美现代性追逐“新奇”的动力似乎也已经耗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