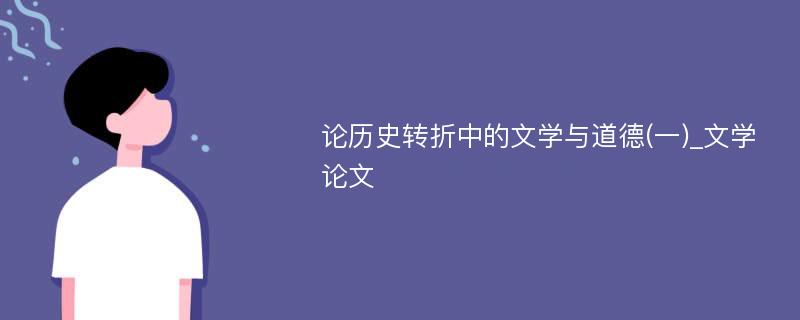
论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与道德(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中,文学属于精神生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中,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抽象中,文学被归入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标志着、反映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般水平,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它的多元功能系统所发挥的诸如政治宣传、道德教育、宗教感化、真理认知、审美娱悦等作用,都无不推动、调谐着人们精神状态的良性转化,提高着人们的综合精神素质。
文学对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但这作用多半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影响人的精神,人的灵魂和品格,而后对物质生产活动发生影响的。例如使人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具有坚韧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去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业绩,等等。
文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因为,社会生活有多么宽广,文学的内容就有多么宽广,与此相应,它发生作用的可能,就有多么宽广。但我们不可能全方位地同时开展对在如此宽广的生活领域发生影响的研究,我们只能抓住一点,提领全局。
经过仔细的考察和认真的权衡,我们决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新时期文学和道德的关系上。这不仅因为几乎所有的对象作为内容的要素,进入文学作品,都要通过道德的中介,才有可能开始并最终完成审美的转化,成为读者的鉴赏对象,而且因为文学作品影响读者,也主要表现在道德上和人格建设上。另外,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来说,道德问题实在也是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文学和道德的一般关系
我们把自己的考察任务设定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德问题,在理论上,是从文学和道德的最一般的关系出发的。这是一种双向的、互补的关系,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道德,都是重要的,而非可有可无的。文学借助于道德,借助于善,借助于理想的人格,而使自己变得充实、纯洁,变得崇高,从而具有撼动人心、净化灵魂的移风易俗的力量。道德则借助于文学使理性的规范,变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变为他们的具体行为,特别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细微活动与冲突。经过作家的铸造与渲染,道德不再是平典的训诫,而是被充分地情化了,并且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活化了。一个形象化,一个情化,这就使一系列正面的道德准则、道德理想,能够向美的界域升华,具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美的品格。正因为如此,文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肩负着道德教化的任务,并且内化为重要的功能。只要文学仍然主要是写人、写人的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这种功能就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正因为文学与道德存在着重要而又互补的密切关系,所以历来的为政者,文学圈里人和文学圈外人,作家和读者,多非常重视文学的道德内涵、道德水平和道德教化作用。孔子强调,诗可以教育人以一定的规范去“事君”、“事父”。臣之事君,要忠;子之事父,要孝,都是着眼于道德的。他甚至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三字,汉代包咸对此的解释是“归于正”,其诠释的角度也是道德的(注:参阅《诸子集成》本《论语正义》,第21页。)。在孔子重道德的文学功能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儒家诗教,讲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类,更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公认为能够系统地反映这一诗教的《毛诗序》就是如此。序文不仅认为《诗经》首篇的《关睢》是一篇美“后妃之德”的作品,而且推而广之,认为诗都是关乎道德风化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所以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注:参阅《十三经注》本《毛诗正义》卷一。)的功能。二千余年来,在儒家诗教的影响下,遂形成一个强劲的以重道德、重教化为基本特色的文学传统。不仅步入仕途的庙堂作家,把这个传统奉为圭臬,就是没有步入仕途,或虽挤进仕途却又被放逐出来的作家,也很少远离这个传统。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注:《史记今注考证》,文学左羲刊行社,1955年版,第3840页。太史公的这个评价,据说来自淮南王安,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辩考》中也曾称引。)其伦理色彩是很浓的。刘勰论文讲“原道”,韩愈论文讲“明道”,都将人伦道德,摆在文学功能的首位。“五四”以后,有了新的文学,有了革命文学。新文学是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新传统,在这新的传统中,尽管价值尺度、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在强调道德,重视道德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变化。鲁迅是向旧礼教冲锋陷阵的骁将,但他同时提倡着现代的人性的道德,而他的为人,更是重气节,重风义。毛泽东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658页。)认为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格。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内容也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被引入歧途,变成了左倾乃至极左政治的说教。这种说教,要么把乌托邦的东西当作实有的东西加以宣扬,脱离了具有七情六欲的现实的人,脱离了有血有肉的生活,谁也做不到;要么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仇、相斗,把人间本来应该有的相爱、相亲、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等温馨的道德情愫通通看作敌对的东西,逐出文艺的园地,直到“文革”中走向兽性猖獗的极端。
新时期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由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急剧的变革,现代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冲破旧的计划经济的僵硬模式,拓展着自己的空间。与此相应,旧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有的崩坍了,有的过时了,而新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虽然开始萌生,但尚未最终形成,于是出现了某种价值的和精神的真空。加上新旧体制转换期所造成的某些难以避免的空隙,特别是旧体制的诸多弊端,这就为绝迹多年的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为沉滓的泛起,甚至为自律不严的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可能。局部的道德的颓落,如唯利是图,物欲横流,以权谋私等,几乎随处可见。道德的颓落虽然只是局部的,而且未必是主流,但却格外显眼,格外让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心。然而,人们往往过于看重了这种局部的颓落,以致一叶障目,以为这就是全部。滑坡之议,危机之论,便不绝于耳。其实,真正的情况并非如此。与局部的道德颓落同时存在的,还有新的道德理想、道德规范的逐步建立,还有传统道德中那些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因素的转化等。这才是当前道德现状中的主流,它与变革中的现实,特别是与正在建立、正在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道德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赖以发展的动力,它的鲜活生命力的源泉,在现实生活之中。一方面,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反映着他们生存方式的变迁,同时,也是这种变迁的组成部分。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其总体而言,反映着社会变革的一般历史进程,能够从中见出这一进程中包括正面和负面,前进和倒退,新生和衰颓等倾向在内的众生相。文学作品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反映,正是如此。首先是客观存在的道德状况,作为描写对象,作为题材,进入作品。进入作品的道德,一般都是作为内容要素而存在,而起作用的。作家由于其所取立场、角度、价值标准等的不同,而对进入作品的与具体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相关的道德状况的抑扬褒贬也就会随之有所不同。然而无论作家主观评价如何,文学作品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它们所从生的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状况。其次,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他也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是芸芸众生中之一员。社会道德状况,对他也有影响。这种影响,在具体作品中,既表现为他的选材角度和评价标准,也表现为他写了什么。这就是说,一部作品的道德内涵和道德水平,同时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最终都可以溯源于现实生活,都可以用现实生活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
应该承认文学领域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道德颓落的倾向,这种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某些方面有加重之势。首先表现在一部分创作中,不是整体上缺乏应有的道德境界,就是具体的描写中不讲究笔墨的干净;写凶杀,则欣赏暴力,血腥四溢,展示残忍、恐怖,唯恐不细;写情欲,又毫无节制,毫无美感,丑恶污秽之言、之情,流泻于笔端,性器官、性技巧,亦不知避忌;有些通俗文学作品,不是适俗,而是媚俗、低俗,拿肉麻当有趣,与等而下之的地摊文学没有多大区别;有些所谓“法制文学”作品,假侦破案件之名,行诲淫诲盗之实,或捏造事实,或诓骗奇谈,根本与法制不沾边,坏人心性,误人子弟;有些严肃文学作品,也出现了追求低级趣味的倾向,媚俗的倾向,这就尤其值得注意。
其次,相当一部分作家,放松了自己人格建设的要求。作品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的道德水平,反映着作家的道德素养。过去,在左的和极左的文化方针之下,片面地强调那种带有歧视性的所谓思想改造,确实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搞得作家一个个低眉顺眼,胆小怯懦,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纠正这种歧视性的政策,总结历史的教训,对于解放艺术创造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无疑是必要的。这也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忽略对自己人格建设的严格要求,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道德上的自律。应该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作品一经出版,便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读者常以千、以万,甚至以十万、百万计。道德水平高尚的作品,对于社会风气的自浇漓而淳正,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道德水平低下的作品,则对社会道德的颓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效应。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有些严肃文学的作家,因为受不了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不能自持,一味媚俗,放松了必要的自律,走失了理想的追求,遂使作品道德水平下滑。
再次,理论批评在九十年代初的几年,对于从道德角度切入的研究,也有所放松,有所忽视。以理论研究而论,在八十年代,研究者在清除以左倾教条主义为特点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时,主要关注点在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在文学的特殊规律,而对于特殊规律和审美特点的强调,又以外在的形象性和内在的情感为主,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理性的内蕴和理性的节制。另外,在强调直观、直觉,强调非理性的情欲,强调潜意识等作为合理的人性因素的同时,也多少忽视了道德作为重要的理性力量对于人的本能的狂暴一面的制衡。受这种理论研究的大流的影响,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道德取向,也就相对显得薄弱。
然而,道德状况的颓落,在文学领域毕竟是局部的,正象在实际生活中道德的颓落只是局部的一样。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认为整个文学界都堕落了。事实上,多数作家还是注意自己作品的应有的道德品位的,他们或在作品中歌颂活跃在改革前沿的新型人物的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业绩与品格;或描写现代企业家的风采,寻觅当代英雄,寄托新的人格理想;或揭露旧体制的弊端,抨击腐败现象,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或反思以往的历史行程,换一个角度看人、看事、看问题,再思想、再认识、再评价,得出新的结论。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历史变革期人们社会理想、价值尺度和道德观念的嬗变,看出在市场经济的格局和发展中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的出现。不管这些规范多数刚刚萌生,尚不完备,如职业道德、质量意识、名牌意识、义利之辨,还有企业文化中与精神风貌有关的东西等。
就作家个人的人格诉求而言,以天下忧乐为己任,关心国运民瘼,时刻以普通人的疾苦和悲欢为念者;疾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睁大眼睛看着给社会进步带来极大损害、极大阻碍的负面现象,并向某些普遍存在的恶行恶毒进击者;砥柱中流者;特立独行者;严格的自我解剖者等,都大有人在。他们的人格同他们的作品一起,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净化社会风气,起着某种表率作用和导向作用。
理论批评界在近二、三年来,开始对文学界和文学作品的道德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相对于例如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稍显滞后,但毕竟自1993、1994年以来,开始有所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由一批年轻的学者发起,虽说有些主张脱离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甚至站在这一发展的对面立论,但人们对于道德现状的某些忧虑却并非空穴来风。人文精神的讨论带有浓厚的伦理内涵,它引导立场不同的学人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持续的思考,促进着整个社会对道德、对人的精神境界和对文化人的操守的重视。其二,一批文学研究家、批评家、理论家大声疾呼地明确提出道德问题来探讨,同时,开始对一些在这方面有明显缺欠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批评,尽管争议颇大。其三,作家人格建设的问题、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道德在文学中的中介作用问题等,都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已有理论上的专门研究启动。
文学中的道德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的变迁,是根本的动力所在。因此,新的道德,只有从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以此为轴心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汲取力量,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服务,才有可能建构起来。文学中的道德,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趋势。
道德的中介作用
道德在人们的文学活动中,起着某种中介作用。这可以从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说。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它作为源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活动的创作过程,或创作阶段;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文学活动的接受阶段,也称鉴赏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道德的中介作用,因为文学活动主体的变换(创作阶段的主体是作家,鉴赏阶段的主体则是读者)而有所不同,但这种作用却都是存在的。
在文学活动的创作阶段,即从没有作品到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产生作品的活动中,道德中介作用是明显的。这里的所谓中介,是指把各种非审美因素转化为审美因素的中介,即先经由道德化而后达到审美化,使原先在生活中不一定具备鉴赏价值的东西变成可供鉴赏的对象。
为什么文学创作中会出现道德中介的问题?这是由文学的对象主要是写人、人的行为和心理这个最基本的前提而来的。所谓写人,实际上是写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与周围的其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协调、统一与冲突、合作与矛盾等。
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起来是非伦理的,规范这种关系的原则也似乎与道德无关,其实不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天人合一”是一个重要的带有核心性的文化思想范畴。这种合一观念,不仅是儒家的伦理思想赖以竖立起来的基石,就是在道家的顺自然的伦理观中,也一样带有本质性。人们不光可以从“奉天承运”、“替天行道”一类正面提法中,看出浓厚的道德意味,即便从至今仍被使用的“欺天行事”、“伤天害理”一类的贬义词中,也不难体会到强烈的伦理评价的色彩来。在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环境意识日渐觉醒的今天,土地荒漠化加剧,大气污染严重,酸雨成灾,草原退化,森林减少,物种消失,再加上温室效应愈益明显,厄尔尼诺现象周期缩短,臭氧层空洞扩大等等,越来越引起全体地球村居民的关注。各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依存关系,生态平衡关系。人们忽视发现,破坏环境,就是破坏自身的生存条件;毁灭其他物种,逆天行事,也就是毁灭人自身。人类达到这样的认识,其意义不下于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达到人是中心,人是目的的人道主义的认识。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对自己族类的独尊扩展为对其他物种的尊重,对大自然的尊重。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环保题材受到重视,环保作品的大量涌现,以至开始汇成重要的创作潮流,是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从这些作品的立意和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换的关系,更重要的也是一种伦理的关系:破坏环境,就是不道德的,就是恶。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反思以往,人们开始体悟到,原来“人定胜天”、“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之类过去一度喊得很响的豪言壮语,也可能包含不道德的一面。西方人到了今天,到了必须面对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恶果时,才忽然发现了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环境意识的萌芽;而中国的环保专家和环保文学家们,则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向自己祖宗的伟大文化伦理观念回归。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环保题材的作品,虽然面对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主要写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冲突,但也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延伸;也可以回过头来变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因素。它是在环保作品中调整与反映人际关系矛盾运动的根据。而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就是道德了。因此,即使是写人与自然的题材,其中涉及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部分,多数都无法回避道德的描写与评价。
至于主要是写人的社会关系的作品,无论是外部的冲突,还是内心的冲突,一般都有着更直接的道德关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人类整体来说,是如此;就个体的社会人来说,也是如此。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总是一些具体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象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们的性格、命运,正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的交叠中,在以他为中心的交叉点上被突现出来的。作家不可能把一个人物的所有社会关系不加选择地照搬到作品中来,那不必要,也不可能。他一定会挑选出与人物荣辱盛衰、悲欢离合联系密切,而又是他最感兴趣,与他的立意不相游离的那些关系,作为落墨的重点。这些关系就其性质而言,并不都是道德的,但作为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依据、价值尺度和善恶判断,特别是作为人物行为动机的自律原则,他借以协调人际关系的约定俗成的规范等,又都不能不程度不同地与道德问题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道德中介能够成立的主要根据之一。这是现实的根据,不是理论家忽然心血来潮,异想天开,杜撰出来的。
文学以宽广的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以经过审美转化了的社会生活为内容。而人际关系,包括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的交叉重叠所形成的网络,则是社会生活的结构。就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有选择地撷取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生活领域、特定的关系网络的层面,加以表现,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每一个特定的生活领域,每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的层面,都生发出文学功能系统的一个相对应的角度,一种相关联的因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文学作品内容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文学与其所反映的生活领域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换言之,文学复杂的、多样的内容,对应着复杂的、多样的现实生活领域和关系网络层面。文学的多元功能系统,即由它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对应关系而来。道德的中介转化作用,就首先发生在这种对应关系中,然后又出现在相关的功能效应中。
政治生活无疑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领域。我们现在固然放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但这并不是说政治活动已不再是文学描写的对象,作家也不必再关心政治。事实上,只要仍然存在政治,政治生活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就不能指望作家不涉足,作品不反映。既然社会生活中有政治,有政治家,既然作品中不能不反映政治生活,不能不写到政治人物形象,而作家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也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那么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也就仍然要起作用。我们自然不一定要象鲁迅当年强调的那样绝对:“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因为也确实存在着不反映,或主要不反映政治生活的作品,但以政治生活为内容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作家政治观点与政治判断的文学作品,具有政治宣传功能,则是不容置疑的。
政治生活本身,并不就是审美鉴赏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的政治因素,只有具备了审美的素质与形态,才能成为读者鉴赏的对象。政治素材从非鉴赏对象,到鉴赏对象,从非审美形态,到具备审美形态,要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道德的中介作用是明显的。这无论从古代、从外国,还是从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屈原的《离骚》无疑是一首经典的政治抒情诗,从中不难感受到诗人的政治主张、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但这首诗中却没有枯燥的政治说教和连篇累牍的政治方略的陈述,诗人反复吟唱的、抒发的是一种特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品德。他认为自己生来就具有一种“内美”,这是他深深引以为自豪的。这种“内美”是一种德性,是他追求“美政”的内在人格依据,也就是他在《桔颂》里托物言志所说的“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因为强调的是九畹贞风,是上下求索,是九死未悔的贞操,是与“萧艾”对立的“兰蕙”的德之馨香,所以就使政治因素充分地道德化了。《离骚》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这情感经过了道德的净化与提纯,又融进了诗人血泪的人生体验和瑰丽的理想光华,便具备了美的素质,足以使读者在鉴赏中获得美的享受与陶冶。诗中最主要的形象,是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支撑点,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人格,在本质上是道德化的。
小说《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的政治纷争,里面写政治谋略、政治智慧的笔墨也不少,如曹操、周瑜、孙权的计谋,特别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部书中,作者对人物的主要评价,展开描写的主要落墨点,也仍然是道德化的。写曹操,主要突出其枭雄的奸伪机诈,以及他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的残忍的利己主义;写周瑜,则主要突出其器量的狭小和嫉恨贤能的品性;写诸葛亮,则除了突出其近仙的智慧之外,更着重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于主君的精神。至于其中的关羽,几乎被描绘成道德化的完人,成了忠义的化身。他是“桃园三结义”的最生动的人物;他的单骑走千里,护送皇嫂,夜观春秋以避嫌,是义;他的人在曹营心在汉,辞谢曹操的高官厚赏,出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是义;甚至华容道违军令而私放曹操,也还是一个义。此人后来的成神,被称为“关圣帝君”,其实是一个颇具封建色彩的义的人格化了的道德神。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作为政治谋略小说的审美属性,主要都是经由道德的中介转化而来的。
在外国的许多政治题材的名著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雨果的名作《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这个近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为描写对象的。但这个题材到了雨果笔下,以人道主义为立足点的伦理判断,盖过了激烈的政治纷争和在这一纷争中的生死对抗。他写孔雀街酒吧里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法国大革命的巨人的聚首,马拉的工于心计,丹东的暴躁专断,罗伯斯庇尔的长于权变,其着眼点无不在人格的伦理评价;他写朗德纳克、西穆尔登和郭文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站在大革命对面的朗德纳克的死硬和他在人格上的刚毅、果决,西穆尔登的冷酷,郭文的仁慈,都很到位。郭文放走了敌人朗德纳克,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精神上的父亲西穆尔登自杀身亡。在这本书中,雨果给了他的主人公郭文一个平静而又辉煌的死,他让人物以死去殉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这是很有深意的。政治冲突,在雨果笔底,化成了人物心理上惊心动魄的道德冲突。《九三年》的崇高的悲剧美,即从这一道德冲突中转化而来。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人权的庄严的大门,呼唤着人道主义尊神的莅位,但它却把人道主义者送上了断头台,使人道主义身首异处。雨果作品的巨大的道德震撼力,正是这样审美地表现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取材于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举世公认托翁是写这种流血的政治的高手。但托尔斯泰是一个道德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就是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理论基石的。因此,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也同样氤氲着浓厚的道德氛围。他对拿破伦有一种深沉的人格上的和道德的厌恶,写库图佐夫的质朴、善良、真诚、爱祖国、爱人民等品质,是对照着拿破伦的造作、虚伪、道德卑劣落墨的。在他的笔下,安德莱、皮埃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就在于能在这些人物深层心理活动的辩证发展中,揭示出他们性格的正面道德素质来,如娜塔莎的纯洁、天真、热情、轻信,皮埃尔的温厚、好心、诚挚等。总之,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经由道德中介而完成审美转化的过程,比任何作家都要表现得远为典型。在托尔斯泰以后的俄苏文学中,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等,都可以归入政治题材,但都突出描写着人物的道德品质,体现着作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理想。这些作品之美,也主要是,或者主要可以归结为道德美、精神美。高尔基就讲过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的话。
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也无疑属于政治题材,但其中的周大勇的形象、彭德怀的形象,也都着眼于人物的政治品格。他们那种勇敢的精神,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精神,正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的条件下,能够把战争引向胜利的保证。作品的崇高的审美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稍后的“三红一创”,也都是政治小说,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多数带有它们所生的那个年代把政治斗争绝对化的痕迹,但它们的成功,如《红岩》,却主要是因为写出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写出了他们面对敌人的酷刑与屠杀时视死如归的风范。这些作品的道德中介作用,也都比较明显。
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政治题材或涉及政治题材的作品,亦为数不少。“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至“改革者”文学的潮流中,大量作品都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成功之作,无不因为人物写得好,而人物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有独特的审美品位的,又无不是因为写好了正面或负面的品格,即经由道德中介,审美转化进行得比较充分的。以近期反思型的作品而论,陈忠实的《白鹿原》所处理的题材,虽不完全是政治题材,却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者摆脱了以往单纯阶级斗争的绝对化的思维模式,放开眼界,取了大文化的视角,写出了白、鹿两个家族几代人身上深沉厚重的传统道德蕴积,白嘉轩、鹿子霖、鹿三、黑娃、朱先生等人物的鉴赏价值多半与此有关。山东赵德发的《缱倦与决绝》,在题材性质上与《白鹿原》接近,却有更长的时间跨度,写天牛庙村几个家族的恩仇沧桑,从1927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其中宁学祥、苏苏、大脚等人物对土地的感情,固然有正面和负面、善与恶之别,但都有一种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拜。这依恋和崇拜,与其说是自然的,还不如说更像伦理的,或伦理化的古老的天人关系。
我们用了大量篇幅,援引了众多的作品,说明政治生活、政治题材进入文学作品所经历的道德中介作用。其实,不仅政治因素要经过道德中介的转化,就是其他因素也如此。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成功演出过布莱希特的《伽里略传》。伽里略是自然科学家,在科学史上有重要贡献。因为支持哥白尼的地动说,而于1633年遭罗马教廷审判,并被判八年软禁。布莱希特写他面临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科学的观点,妥协、屈膝,要么像布鲁诺那样殉自己的学说。他选择了屈膝,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布莱希特通过戏剧的规定情境,在人物极度剧烈的内心冲突中,对其进行了道德上的追究与拷问。写这个作品时,剧作家已离开法西斯统治的德国,漂泊异乡。从作品中能看出在文化专制的敌对条件下,外在环境对科学良知的戕杀,但作家也不放过科学家本人应负的折节责任。作品写的虽是历史,但观众还是不难感受到合围而来的黑云压城的法西斯的魔影,而剧作家本人,是决不会用放弃真理的代价而苟且偷生的。
道德之所以在文学活动中能够发挥中介作用,从理论上看,是与美、善的交叉叠合分不开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里,美和善可以互训,在很多情况下,美与善都是合一的。美、恶可以对提,善、恶可以对提,涵义相近。但仔细考校,善是比美更高一级的范畴。
孔子欣赏武王时的《武》乐时说:“尽美矣,未尽善也。”欣赏舜时的《韶》乐时则说:“尽美矣,又尽善也”。(注:《论语·八佾》,见《诸子集成》本,第73页。)他是以《韶》乐为高,《武》乐次之的。可见,在中国传统美善合一的观念里,实际上是以善为主导的。美,不一定都达到了善的境界,但善的肯定是美的。
有人把中国古代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相传周公制礼作乐,礼以节之,乐以和之。其所节、所和,都是要达到和谐的伦理境界,达到善。礼包含有仪式的部分,但其核心,则是亲亲尊尊的等级性政治伦理。在礼乐文化环境下,无论是政治哲学、人生哲学、艺术哲学,都把个人的人格修养、道德训练看成第一义的东西。所谓“三立”之说,把“立德”置于“太上”,然后才有从政的“立功”,再其次才有从文的“立言”。以从政而言,尊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修身,就是立德;以从文、从艺而言,中国人历来强调道德文章,讲人品、文品,人品、画品,人品、书品,人品、艺品等等,也是把德置于首位,以人品论文品、画品、书品、艺品,自文品、画品、书品、艺品而见人品。
美、善的交叉、叠合,在西方,虽与华夏有别,但也大体相通,也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无论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还是在近代的狄德罗那里,都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上面所举许多作品中的道德中介作用才得以成立。
总之,揭示道德的中介作用,不仅有助于作家更自觉地在创作中加以运用,而且更可以见出道德因素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从而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