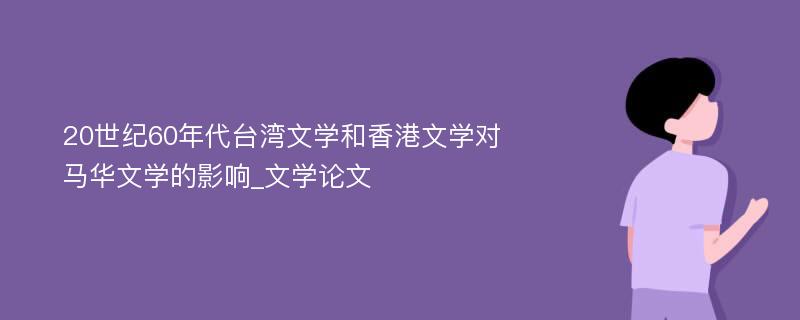
60年代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台湾论文,香港论文,年代论文,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华文学在60年代开始,与台湾、香港两地文学界发生密切联系,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也由此而绵延。台湾、香港两地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是长期而多方面的,特别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即新马分治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流行于台湾的现代派文学,以及香港的言情、武打等通俗性大众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当然,台湾的现代派文学源于西方,不能视为纯粹的中国文学,但它却经过了台湾文学的选择与再创造,其中溶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基因,成为台湾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华文学中的现代派文学,主要地是从台湾传入。
现代派文学是西方众多现代文学流派的总称。她产生于19世纪后期而兴起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要指现代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派、荒诞派、存在主义、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等具有先锋意识的反传统文学流派。其思想特征是表现世界的荒诞和危机,艾略特的荒原意识笼罩其中;其创作目的围绕揭示“自我”的丧失,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之扭曲和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创伤、变化心理、颓废情绪和虚无思想等心理隐曲。其艺术特征主要是运用象征、暗示的手法,藉有限的有形,去寄寓无限的无形;它长于捕捉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意识与潜意识。在创作方法上,力求突破传统,标新立异地表现作者的情绪和倾向,展现作品的内涵,不受时空和客观真实的制约。总而言之,现代派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学,它与哲学的密切关系使它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究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它的标新立异使它的发展充满多意向性,它的对异化的执着表现契合着现代社会的心态。因此,其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更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某些原因,现代派文学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台湾崛起。这些现代派的创作,有小说、散文、戏剧,更多的是诗歌。现代派诗歌在台湾,不仅有创作活动,还有理论倡导与同人组织,同人杂志。诗人纪弦于1953年创刊《现代诗》,1956年宣告成立“现代派”,他们宣称“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笠》诗人桓夫认为:现代诗在台湾的兴起,源于两个“文学的根球”,一是纪弦等人从大陆带到台湾的30年代“现代派”火种,一是本省诗人林亨泰等人受到日本昭和初年现代诗运动的洗礼后所发扬的现代主义精神。那么,当时台湾大批的青年留学美国,归来时带进的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像一场春雨,催动了“根球”的萌芽,促进了现代派文学,包括现代诗在台湾的兴起。台湾现代诗具有其以现代感受为精神内涵,以独创性为技巧特质的鲜明特色:内涵上着重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既包括对爱情的感慨,怀旧思乡式的回忆,又包括现代人在经济转型期中产生的个人失落感、孤独感,以及内心的彷徨苦闷,精神上的颓废与虚无;基调上充满悲观的、非理性的色彩,情调偏于抑郁;技巧上尤其注重意象的营造。美籍华人学者、诗人杜国清先生在《流派与台湾新诗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意象的经营是现代主义作品在语言表现技巧上的一大成就。经营成功者,语言凝练,富于张力和暗示力;失败者,语言晦涩难解,有句无篇,甚至走火入魔,呓语连篇,不知所云。”(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台湾现代诗的这些特征,契合了新马社会的某些心态,致使现代诗一传入新马,就形成声势,风行起来。
现代派文学传入新马,是有其重要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原因的。其时,“新马文艺界断了中国大陆的‘母奶’。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年轻的文艺青年主要依赖西方的‘牛奶’。不谙英文的文艺爱好者,由于母奶难得,就从台湾、香港的‘炼奶’中寻取养料。”(注:柳舜:《寄厚望于中国作家》,载《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集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集,上册,第45页。)此其一。其二,50 年代中后期的新马,面临社会的急剧转型,各种心态纷纭杂乱,既有兴奋的、热烈的,也有彷徨的、迷惘的。现代派文学所具备的特质,令新马华人找到了一个宣泄之所,正是借此酒杯,浇己之块垒矣。最早传入马华文坛的,是台湾的现代诗。50年代末,马华的《蕉风》等几种刊物率先予以介绍、提倡,并很快地于1959年出版了两本小诗集——《美的V 形》和《郊游》,以作先导。这两个集子所收的诗作,绝大部分是台湾现代诗人的作品,少数是新马本地作家所作。之后,又经一些从台湾留学归来的学人的宣传鼓动,现代诗的模拟者渐渐多起来,现代诗创作遂成为60年代初流行于马华诗坛的一股潮流。尤其在马来亚,现代主义的风潮,如热带的季候风,摇撼着原先单一的文坛格局。其时,马来亚的一批文人,结成各式团体,如新潮社、荒原社、海天社等,从事鼓动、创作活动。同时出版同人刊物,以为园地,如新潮社的《新潮月刊》,以发表新小说为主;荒原社的《荒原月刊》,多刊登散文;海天社的《海天丛书》、《海天月刊》,则成为现代诗歌的重要领地。此外,海天社还创办海天书店,专售文艺书籍,一时影响极大。该社成员都是北马文坛的知名文人,有慧适、粱园、忧草、萧艾、慧桦、冰谷、北蓝羚、淡莹、游牧等近30名诗人,声势很大。1963年9月,另一群热衷于现代派诗歌的作者,借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副刊,出版《银星》, 专门刊登现代诗, 至1965年12月止,维持了两年多。而创刊于1962年1 月的《星槟日报》副刊《星艺》,这一时期也成为现代诗的营地。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传入,对长期以来以现实主义为唯一旗帜的马华文学,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震撼。它的意义,决不仅仅在打破那种独尊儒术式的唯现实主义是尊的单一化沉闷局面,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猛烈冲击。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强调对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尤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对于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学意义与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也有其失之单一与狭隘之处;尤其是对文学的审美功能,通常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马华文坛对于现实主义以外的文学,更持排斥的态度,在一些文学史中,20年代的“唯美主义”、“感伤浪漫主义”,被斥为“两股文艺逆流”;至于“李金发式的象征诗”、“林语堂式的幽默闲适的小品”亦被称为“不健康的风气”、“恶劣的文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商酌的批评。现代派文学恰恰对过分强调自然、社会和理性表示反感,而要求写作必需突破传统的只对事物表象进行描绘的作法,着重揭示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物行动的描写,着重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这一文学流派认为,文学艺术是诗人心灵的表现,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和摹写;艺术的创作与功利无关。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观念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观念,是各执一端的。这样一些新的观念,随着现代诗风的传入而注入马华文坛,对马华文学的发展,首先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创作的多元化。现代派诗风对人的生命本体与存在的哲学意义的探索,丰富了诗歌人本的内涵;它对心灵的挖掘,突破了雄踞世界文坛二千年的“艺术摹仿”说;它对诗歌语言与诗歌形体的突破,极大地强化了诗歌的审美功能。总之,创作观念、艺术视觉、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使诗人们获得了更加自由的选择机会,使文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艺术视野的扩展,使诗人们得以凭新的艺术视觉,去审视社会现实。现代派文学一传入新马,便受到人们、特别是年青人的青睐,而形成创作热潮;此后的马华文学,乃至发展至后来新马分治后的马华、新华文学,都走向了文学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主义在反传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继承着某种传统的观念;真正意义上的反传统,必有其历史积累作为基础。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又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互为表里的两种文学精神的呈现。
然而,马华文坛中现代诗风的传入,“在造成喧哗和骚动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混乱。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输入诗歌,造成了价值观念的颠倒和倾斜;非理性的语言,造成诗歌的非诗化、诗意的支离破碎和晦涩;割裂诗歌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关系,导致诗歌与社会现实的脱离,偏执于内在自我,导致诗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冷漠和创作的矫情;反传统与对传统文化的非历史态度,艺术的虚无主义。所有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尖锐的批评。”(注:陈实:《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见《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这一段理性论述,对现代派诗风的负面作用,作了中肯、全面的分析。而这负面的效应,一方面是现代派文学创作方法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诗人创作上的极端所致。其中,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现代派的致命硬伤;而诗人在创作上的走火入魔,是导致作品失去生命力的主要原因。试看当时的一首“现代诗”《七与六》:“拿着手杖7/咬着烟斗6/数字7是具备了手杖的形态的。/数字6是具备了烟斗的形象的。/于是我来了。手杖7+烟斗6=13的我/一个诗人,一个天才。/一个天才中的天才。一个最最不幸的数字!/唔,一个悲剧/悲剧悲剧我来了。/于是你们鼓掌,你们喝彩。”这完全是文字游戏,是没有审美特质的非诗。这样的游戏之作,在当时颇有泛滥之势。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诗,也在马华文坛中生成。牧羚奴、完颜籍、英培安、零点零、贺兰宁、流川、文恺、南子等人,正是现代诗的最早尝试者。早熟诗人周粲的作家身份似乎不能简单地归入现代派,然而,他的系列小诗,此时也在与新诗风的碰撞之下渐滋新质,一如台湾小诗在现代诗风的推动下别具一格。充满诗人气质的周粲,19岁就以诗集《孩子的梦》成名于马华诗坛,此时已相当成熟。他的诗,一直倾向于追求如泰戈尔、冰心般旖丽晶莹而充满哲理意蕴的境界;对于诗歌的审美功能,当然是十分执着的。台湾现代诗风的传入,强化了他的这一倾向。尤其是现代诗注重经营诗的意象这一特点为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艺术参照。他这时期的诗,显示出对意象营造的更加自觉的把握与更为娴熟的手法:
一辆人力车载着一个喝醉酒的水兵
连同酸微的小调被黑夜赶进街的尽头
每座墙都成了一个摄影家
瞄准镜头在猎取光和影
朋友,假如要远行
现在就该起身了
还有比桥栏上更寒颤的风吗
遥远的木屐声象有意制造恐怖
干涸的河床上躺着只死猫
它露出四个牙齿向星星冷笑
在对具象的细腻捕捉、营造之下,“黑夜”被意象化为一连串的狰狞与萧瑟,显示着都市纸醉金迷背后的荒漠与死寂。在具体语义的背后,是诗人对人的自我本体生命及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感触的诗意外化,充满了生命意识与哲学意味。诗的想象空间,还可以让诗自身具备多层意义。这样的作品,显然不是那种呓语式的“现代诗”的摹写品可比拟的,也不是那种只注重内容,却毫无张力的平庸之作可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说周粲的诗是精美的小品,那么,牧羚奴——陈瑞献的诗,则是深邃的篇章。他的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具有无限的冲击力。牧羚奴的第一部诗集以他的一首著名诗歌《巨人》命名,是一部现代派诗歌作品集,出版于1968年。诗人对“巨人”的意象情有独钟,他曾于1964年12月及1966年1月分别写过两首《巨人》的同题之作,1968 年的是第三首。三首《巨人》的共同特征,是热情澎湃地塑造“巨人”的巍峨形象,表达诗人对巨人“伟大人格”的向往与追求,作品洋溢着古罗马文论家郎加纳斯所倡导的“崇高”的美学意义。诗人对“巨人”的感知与创造是渐进的:从最初的“我拙于刻划你崇高的形象/巨人呵巨人”,以第二人称表现崇拜之情,到第三首以“我”入于巨人形象、物我一体的磅礴,表现出诗人的心路历程。第三首中的一段这样表白着:
胆,如蜂巢
密麻着炙手的火山群
我心常云霄
一收腹,即有狮首昂起
而在紫色的华盖下
坐着一个、两个
坐着亿亿万万的释氏
我是巨人
在现代诞生
这种变化,显示出诗人从彷徨中的昂视“巨人”,到寻找到了“现代人类的光荣和自信”,“巨人”正是诗人审视、判断客观世界,剖白人类心灵、主观精神的结果。这一意象,被作者注入了理性主义的色彩,充满了邈远恒久的历史感与宏大深邃的人类自我意识。而这,正是他的诗作与非理性的现代诗的最大区别。
陈瑞献绝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牧羚奴是他用以在文学领域中行世的名字。在诗歌之外,小说、杂文、评论、翻译、印篆、书法、绘画、雕塑、纸刻、佛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他都是可以登堂入室的。正是这位艺术家,为马华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这时期的短篇小说《不可触摸》,也是在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之下的创作。小说运用了独特的空间架构,创造出由现象场景与感觉世界相混合而组成的令人目眩的艺术世界,显示出萌芽中的马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牧羚奴是当时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极具代表性。现代派文学自此在马华文坛找到了它的立足之地,它艰难而顽强地发展着,与现实主义相互丰富着马华文坛。
台湾文学的影响结果,是拓宽了马华文学的发展空间。而香港文学之于这一时期的马华文学,除了影响之外,还起着沟通中国大陆文学与马华文学的桥梁作用。
二战之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都非常密切,特别是它与广东之间,经济自然流通,人员自然流动,民间文化习俗庶几无差,两地的文学、文化可以说是连成一体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文学遂独立发展。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较早、较广的影响的,是它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这类通俗小说,自50年代起,就在新马流行;50年代至70年代,新马的华文报文艺副刊,几乎都少不了这类言情和武侠小说的连载。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金庸等人的精彩之作,更具有无限的影响力。实际上,这类充满中国文化情结的通俗小说,不仅在新马,而且在东南亚的其它国家,甚至世界各国的华人社会,都广为流行。就新马而言,由于这类小说可读性强,它们不仅吸引了大批读者,还掀起了这一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热潮。然而,它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武打、言情小说的极度泛滥,消解了它的文学审美价值;当滥情的、黑幕的,甚至下流的、黄色的因素充斥其间,它就成为正当文人唾弃的对象了。
然而,香港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关系,远远不止于此一层面,它还有着更深层的性质。这就是香港文学界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中,起到了沟通中国大陆文学与马华文学的重要作用。新加坡诗人原甸先生指出,香港文学界在此时对新加坡的援助有三方面(诗人谈的虽然是新加坡的情况,但当时的马来亚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第一,在五六十年代,来自中国的文艺书刊由于政治的原因被严厉禁制之时,香港文艺出版界及时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而“这些礼物是极其珍贵的”,它们使新加坡文艺界在被隔绝的情况下,得以“了望世界、倾听世界,并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第二,香港的文艺界为马华作家提供发表园地。战后,香港文艺界专辟了《南洋文艺》、《文艺世界》、《伴侣》、《当代文艺》和《海洋文艺》等多个文艺园地,一方面介绍马华文艺,一方面为马华作者拓展创作、发表的空间。这些文艺杂志,起到了协助老作家的创作及“磨练”和“培育”新作者的作用,“对新加坡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当时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马华作家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洋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新加坡作者就有近百名,如方修、林晨、钟祺等老作家及莫河、慧适、梅拉、郁人、秃橡、忧草、丁之屏、杰伦、高秀、谢世崖等青年作家。在《文艺世界》发表作品的也有上百名,其中有郑子瑜、鲁白野等成名作家,也有当时还是文学青年、后来成为文学骨干的马阳、鲁彬、岭上青、莫河、列浦、慧适、高青、莎茄、罗林、严冬等人。活跃于《海洋文艺》的新老作家则有李汝琳、石君、周颖南、严思、适民、英培安、蔡欣、泰林、尤琴和李向等人;第三,香港文学界还帮助出版新马作家的著作。新加坡文史学家杨松年先生对战后至新马分治前的20年间(1945—1965年),新马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情况,作了严密的统计。他指出,这20年间,“新马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有三个中心地, 那就是新加坡、马来亚与香港。”其时,在所出版的809本华文文学书籍中,新加坡出版的有537本,占总数的66%;马来亚出版了129本,占总数的16%;而香港出版的是143本,占总数的18%, 还略高于马来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一部分新马的出版机构将书稿运往香港印刷,再运回新马发行的书籍。(注: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南洋商报1982年2月版,第25页。 )在香港出版的几套主要的大型丛书有:赤道出版社编印的《赤道文艺丛书》、青年书局在香港印行的三套共36册的《新马文艺丛书》、《南方文丛》、《新马戏剧丛书》。马华著名诗人铁戈的诗集《在旗下》和作家李过编辑的一套《星月文艺丛刊》也是在香港印刷出版的。当时香港出版马华文学作品的书店和出版社是相当多的,如香港上海书局、香港世界书局、艺美图书公司、新缘出版社、宏智书店、高原出版社、学文书店、友谊图书公司、世界出版社、宏业出版社、宏业书局、激流书店和新月出版社等等,阵容十分强大。香港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低于新马的印刷成本,也是其吸引新马出版市场的因素之一。
香港文学、文化界,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入。不仅如此,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与人文背景,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也成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汇聚之地。香港作家犁青如是说:香港“是中国文学的窗口,它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在目前及将来,它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融汇、整合的圣地;它和亚洲华人地区如新、马、泰、菲、印等地的华文文学容易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它是一个站、一座桥,一道绮丽的虹。”在香港已经回归的今天,它的文学联结作用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