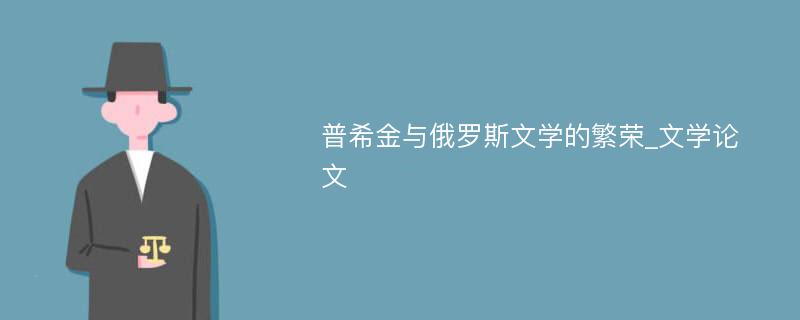
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俄罗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考察了文学勃兴的原因。作者强调文学勃兴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论述了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唤起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觉醒,及其给文学带来的繁荣;强调吸收外来文化对激活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外国文化中有用的异质部分给静止不动的亚洲式的落后文化注入的新血液;强调作家的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总结了普希金和俄国优秀作家群的价值取向以及为肇兴文学提供的宝贵经验。
文学兴衰的规律何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课题,也是一个有开拓性和有社会价值的研究课题。许多理论家和学者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各种因素加以阐述、分析和论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把文学的兴衰只归结为单一的某种原因,显然是片面的,只有综合所有的因素加以研究,才能避免结论的片面性。然而,对这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又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和占有有限的资料所能完成的。因此本文仅就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勃兴,来探讨文学兴起的原因,也难以避免个人认识的局限。
普希金和他的时代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背景和环境来解释文学现象,被西方现代派斥之为“外因论”、“因果式”的研究和“起因谬说”,予以否定。美国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在他的西方文艺学权威性著作《文学理论》(1942)中写道:“我们有些文学名著与社会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就文学理论而言,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目的。①他把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贬斥为“因果性”的“单向线性思维”,认为社会学派不能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这种理论被我国擅于模仿和赶时髦的人看做是“圣经”和“真理”,他们把时代背景、作家与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贬之为“三位一体式”的研究,认为是“拼盘”和“大杂烩”,“取消了文学研究自身的任务”,有的甚至用“教条主义”、“公式化”和“庸俗社会学”等词语加以否定。
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反映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生活,就没有文学。要说明文学现象,就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现象中去考察。离开生活的前提,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对其评价就失去了依据,就会造成对文学现象随心所欲的解释和评价。
普希金开创俄罗斯文学,成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并推动民族文学的勃兴和发展,是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分不开的。普希金(1799-1837)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经历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两次历史风暴,直接影响俄国文学的发展。1812年的反法卫国战争,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促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普希金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诗兴大发,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手抄刊物,针对当时用法语写作的“法国病”,他开始用俄文写诗,并带动同学形成一股新风。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留传下来的近130首诗,全部是用俄文写的。他描写俄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英勇斗争精神的长诗《皇村回忆》(1814)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誉。卫国战争加强了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民的力量、高尚的品质和光明前途的信心。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以他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作家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力量源泉。
亚历山大一世,害怕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会导致专制政权与农权制的灭亡,他采取了极端反动的政策。在国外,他成为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首领,镇压欧洲解放运动;在国内,他重用反动军人、陆军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和反动政客、国民教育部长戈里曾,企图扑灭一切进步思想。激烈的社会斗争,促进人民反抗力量的增强,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在远征国外归来的进步军官中不断涌现。“救国同盟”(1816)、“幸福同盟”(1818)、“南社”(1821)和“北社”(1822)相继成立,终于在1825年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普希金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十二月党人,并与因参加起义遭终身流放的普欣和丘赫尔别凯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得堡时期,他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尼·屠格涅夫、尼·穆拉维约夫、伊·陀尔戈鲁夫、雅库希金、鲁宁等人经常往来,辩论社会各种问题。②1819年他加入了由十二月党人领导的文学政治团体“绿灯社”。南方流放时期,他与十二月党人奥尔洛夫、符·拉耶夫斯基等重要人物交往密切,并结识了“南社”领袖彼斯捷利上校。十二月党人起义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贵族中优秀人物播撒的革命火种,唤醒了人民。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诗人。普希金吸取时代的乳汁,注视时代的风雷,把握时代的脉博,呼唤时代的声音,紧跟时代的步伐,因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面旗帜。十二月党人时期革命斗争的风雷,增强了普希金反专制农奴制的革命意识,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接连写出了《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童话》、《致普留斯科娃》(1818)、《乡村》(1819)等著名诗篇。这些诗篇像一道闪电,划破黑暗如漆的俄罗斯夜空,点燃了积郁在人民心中的反抗烈火,鼓舞人民奋起斗争。他的创作成了时代的敏感的回声。
普希金和外来文化
当东方各民族文化高度发达时,俄罗斯人还处于落后和野蛮的时代。俄罗斯人从1224-1480年遭受到鞑靼两个半世纪的野蛮统治。16世纪才形成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17世纪才得到巩固,但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为改变落后的俄罗斯,努力引进西方文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开办各种学校,派遣留学生,出版报纸,建立科学院。列宁说:“……彼得促进了野蛮的俄罗斯对于西欧文化的模仿。”但18世纪以前的俄国文学比较贫乏,内容多是王公和圣徒的生活,教会文学占有一定地位。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18世纪古典主义作家为数不多又多是模仿之辈,建树不大,没有产生世界影响。
给俄国文学带来声誉,并影响俄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是普希金。普希金对前辈作家进行选择,并做了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他赞赏杰尔查文诗歌的公民激情,对大臣、君主和法官等权贵人物的揭露;剖析了茹科夫斯基浪漫诗章对人物内心的揭示和语言的抒情性、音乐性以及韵律和节奏的变化,承认他是“才华卓绝的诗人”;赞赏罗蒙诺索夫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语言的流畅;肯定巴丘什科夫诗篇歌颂生之欢快和语言的接近口语;赞扬冯维辛是“自由之友,勇敢的讽刺之王”,克雷洛夫是“人民精神的代表。”普希金吸取了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但也看到了他们的不足:“我把杰尔查文读完了……杰尔查文名下只应保留八首颂诗,还有几个片断,其余一切都可以付之一炬。”他说:“诗,在罗蒙诺索夫看来,有时是一种消遣,常常是一种职务上的练习。”对于茹科夫斯基,则认为他的诗篇充斥着神秘色彩和梦幻的描写,败坏了读者的思想。普希金吸收了传统文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抛弃了落后和腐朽的东西。他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扬弃和创新,对前辈作家进行了超越并勇敢地开拓文学的新路,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最终并攀上了新的高度。
普希金在勃兴俄国文学中,接受西方文化是主要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占次要地位。他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不仅形成他的个性意识和文化心态,影响他创作的发展,而且也造成俄罗斯文学的勃兴。
伏尔泰、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表明对诗人普希金连续影响的不同阶段,是诗人创作不同时期的不同座标。法国文学在诗人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形成他幼年时期的文化性格。童年时期,他受的是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尽管他后来说:“这是可诅咒的教育”)他在漫不经心中学会了法文,而且法文比俄文说得流利。七岁时就能阅读父亲收藏的大量的法文书籍,八岁时就能背诵许多法国的长诗。他对法国文学的博学,令他的同学惊叹不已,曾赠给他一个“法国人”的绰号,在反法的卫国战争中,他曾为此懊悔过。他首次诗歌的习作是用法文写成的。少年时代他写的小讽刺喜剧《掠夺者》是模仿莫里哀的《诱骗者》,《托利亚德》是模仿伏尔泰《昂里亚德》的打油诗。伏尔泰的散文对普希金小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伏尔泰的散文是“正确风格的最好的榜样”。他吸取了伏尔泰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散文创作简洁的笔法。诗人轰动俄国文坛的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17-20),它的叙述的形式,平行的论题、离题叙述和幽默风格,都受到伏尔泰创作的影响。他还喜欢拉辛的悲剧,甚至后来他否定古典主义题材狭小,形式拘泥时,依然称拉辛是伟大的。布瓦洛嘲弄贵族和教会的讽刺诗,影响普希金用“讽刺之鞭”抽打亚历山大一世、陆军部长阿拉克切耶夫、修道院长福季、国民教育及宗教部长戈里曾等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1820年后普希金致力于批判法国古典主义,反对它的“沙龙”性质、贵族活动的狭窄取材和限制创作自由的“三一律”,认为“它有着消灭我们年青文学的威胁”。他提倡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学。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是借助法国古典主义而形成的,并保留古典主义文体的单纯、明晰、客观性以及和谐、匀称与语言的精确。可以这样说:没有法国古典主义的培育,也就很难形成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普希金的自由思想、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观念,是承袭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的直接成果。
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受拜伦影响。19世纪20年代,拜伦的影响遍及欧洲。拜伦成了欧洲自由主义文学的领袖和反封建的勇士。拜伦的狂飙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叛逆精神,给放逐南方的普希金极大的鼓舞,他说:“因拜伦而发了狂”。他在《致大海》(1824)中称拜伦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个王者”。普希金的南方组诗是在拜伦影响下写成的,表现了诗人的叛逆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南方组诗确立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和旗帜。普希金的《波尔塔瓦》(1828)中被拐骗的玛丽娅与阴谋家马赛巴具有拜伦主人公的外貌特征,显示出了与拜伦《东方诗抄》的内在联系。《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30)中贵族先进青年与社会对立和诗体小说的艺术形式,都是向拜伦学习的成果。对拜伦的热衷到弃绝,是普希金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换的必然阶段。
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幽禁时期,普希金变成莎士比亚、司各特的信徒。他从莎士比亚那里学习创作历史悲剧的艺术,从司各特那里吸取了创作历史小说的经验。《鲍里斯·戈都诺夫》(1824-25)剧本的创作使他变成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人们常把《鲍里斯·戈都诺夫》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并列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普希金说:“我是按照我们鼻祖莎士比亚的体系来撰写悲剧的”,在性格描绘上,他采取莎士比亚的自由而宽广的性格描绘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人物性格。残忍又胆怯的鲍里斯,性格是复杂的,他既是残暴的君主,又是聪明的统治者;既是慈祥的父亲,又是弑君的凶手。他不是某种罪恶的单一体现者。但普希金效仿莎士比亚时,扬弃了莎士比亚的“编年史剧”的“追求权力并互争权力的个人斗争”的狭小内容,他描写的是人民群众参加并决定自己命运的斗争,远远超过了个人斗争的范围。《上尉的女儿》(1826)中司各特的影响表现在:以家庭纪事的形式,通过个人命运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家庭纪事、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交织在背景中表现人物。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写道:“司各特,他是灵魂中的粮食呵!”他特别赞赏司各特表现历史事件的事实性,把司各特的作品看做典范,认为在司各特小说中“没有法国悲剧的夸大,没有感伤小说的拘谨,没有历史学的庄严。”但是,他不拘泥于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在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寻找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超过了司各特,表现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
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有文化的先进贵族,根据俄罗斯的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冲击,给静止不动的亚洲式的落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普希金具有新的文化性格,他打开眼界,注视和借鉴欧洲文学的成果,才建立独创的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创作经验证明:撒开欧洲,闭门锁国,夜郎自大,抱残守缺的封闭状态是不能勃兴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只有在克服传统文学沉淀的同时,注意外国文学的选择;在继承本民族的优良文学传统的同时,善于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学成果,才能出现文学繁荣的景象。
普希金和俄国作家群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迅速进入世界文学前列,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家群具有优秀的素质。俄国作家为了人民、祖国和社会的解放,向封建专制制度作了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作家伟大的良知。赫尔岑说:“我们的整部文学史,不是殉教者列传、就是苦役囚徒的名单。”高尔基也曾说:“在欧洲没有任何人能在这样难以名状的艰苦条件下创作出这样惊人的美。”普希金呼唤自由的歌声,震撼着帝王的宝座。因此,在他短短一生中遭到两次流放和长期受到监视,最后死于沙皇设置的圈套——决斗中。莱蒙托夫以诗歌促进人民的觉醒,“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他写了《诗人之死》,声讨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惧,也曾两次被流放。他被杀害时,还不到27岁。果戈理“带着他的惩罚的竖琴”揭露贪官污吏,他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引起官场的普遍愤怒,他们叫嚷“果戈理是俄罗斯的敌人,应当用铁链锁起来送到西柏利亚去”,致使果戈理在国内难以安身,不得不暂时离开俄国。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制度斗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被认为是“文学的暴徒在杂志上造反”。他由于写了对农奴制抗议的《给果戈理的信》而面临苦役和监狱的威胁。屠格涅夫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激怒了沙皇政府,1825年借口他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章“违反审查条例”而被逮捕。拘留一个月后,遣送原籍,在警察监视下过了一年半的放逐生活。反农奴制的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领导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写传单揭发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和主编《现代人》杂志,被认为是“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者”。1862年被捕,并流放到西柏利亚。他经受21年的监禁、苦役和流放,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从流放地放回后四个月便与世长辞。著名诗人、《现代人》、《祖国纪事》主编涅克拉索夫被当局认为是“狂妄的共产主义者……为革命拚命地呼号”,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监视。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诵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和筹备秘密印刷所而被捕。并处过假死刑,服四年苦役后,发配到西柏利亚去充军。《谁之罪》的作者赫尔岑被当局认为是“谋叛者”被捕入狱。而后又以“对社会极端危险的大胆的自由思想者”罪名,流放达八年之久。俄国作家不仅用笔,而且用血和生命使俄罗斯文学放出灿烂的光辉。他们不管极权主义者如何残暴、检察机构如何限制,坚贞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有的是革命家与文学家兼于一身,如雷列耶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有的本人虽不是革命的直接参加者,但他们用自己的创作与革命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有的显然不了解革命,但他们正视令人激动不安的现实,深切地关心人民的命运,热情而痛苦地探索真理,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关心人民的命运,注视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使这些作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谁之罪”和“怎么办”以及“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成为他们创作的共同主题。所有这些作家都满怀忧患意识,思考着时代,勇敢地揭露和鞭鞑统治阶级,热情地关怀人民的命运,构成一个有胆识的作家群体。在这批有声誉的作家中,还出现了世界文学中罕见的著名的理论家与批评家。别林斯基对艺术的本质与目的、艺术创作主客观间的关系、典型化、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肯定“自然派”文学的意义,批判“纯艺术论”的虚伪,强调作家的公民责任感和文学的社会效果,他说:“随时都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坏书,但决不能宽恕作家写一本有毒素的书。”别林斯基以文学批评为武器,指导文学向专制制度斗争的精神,为车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继承和发展。俄国作家的先锋启蒙作用,是不断延伸和发展的。俄国作家作为一个独立而又自觉地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的兴起和他们所具有的改变和推动文学发展的雄厚力量,是19世纪俄国文学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文学史的一个新时期,他对俄国文学做了杰出的贡献。他为肇兴文学提供了宝贵经验,这里仅提两点:
首先,作家是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是千百万群众情绪的表达者。普希金从21岁起到他最后被沙皇谋杀,屡遭流放和监禁,不断地受到迫害,但他始终不屈。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自由与正义同专制制度作了不妥协的斗争。正如他所说:“……学者和作家的队伍,无论他们是何许人,总是站在一切教育进军和文明攻势的前列。他们永远注定首当其冲,遭受一切苦难和一切危险。对此,他们不应当畏缩不前,愤愤不平。”③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事业,无限忠诚。当被带到沙皇面前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沙皇的问话:如果在彼得堡,我一定会参加起义的,因为起义的阵营里都是我的朋友。在铁镣高悬的年代,他依然“唱着往日的颂歌”,并且冒着杀头的危险,转托他人把他的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诗篇《致普欣》(1826)、《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送给受难的“同志,朋友和兄弟”,照耀着他们流放的生活。他的政治讽刺诗象犀利的匕着直刺沙皇及其党羽的心脏,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普希金被召到彼得堡总督面前。总督当着他的面命令警察局长到他家去搜查他诗歌的手抄本时,普希金马上说:“伯爵!你这样做是枉然的。那儿你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还是拿纸和笔给我吧,我在此地都给你写出来”,于是写出了他所有的禁诗。这种坦率、勇敢的性格,正是作家信仰、追求、胆识和个性的生动表现。诗人虽遭流放,但这并没有使他的革命热情冷却,反而向封建专制作了更为大胆的挑战。他在《短剧》(1821)中,号召人们把皇帝从宝座上颠覆,用锋利的刀剑杀死暴君。他在《致达维多夫》(1821)中赞美争取自由的革命家,渴望俄国发生革命,痛饮一杯革命的“血酒”。他在南方组诗的开卷篇《高加索的俘虏》(1820)探索了时代“英雄”的典型,在《强盗兄弟》(1821)中歌颂了百无法纪、不屈从命运的强盗的反判精神。他在《巴赫契萨拉依的喷泉》(1821)中遣责了掠夺、屠杀人民和享乐腐化的的野蛮鞭靼帝王,借古代传说中女主人玛丽亚被囚禁的命运向沙皇专制的社会发出了抗争,向不自由的生活提出了抗议。他在《加甫利倾》(1821)把讽刺的投枪对准“天国的皇帝”,对封建正统观念表现了大胆的挑战。在《茨冈》(1823)中,受沙皇迫害的游荡诗人把自己同穷困的游荡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唤起他们振作觉醒,给他们的悲剧主题增添了思想的光辉。
普希金在敖德萨流放时,他的上司伏隆卓夫对诗人进行公开的侮辱,想叫诗人屈尊俯就他。可是在诗人眼里伏隆卓夫不过是喜欢阿谀、追求功名的浅薄官吏而已。诗人正直的性格敢于向比他地位高的人挑战,用讽刺诗来回敬伏隆卓夫。俄罗斯诗人决不向上司谄媚,他要求尊敬自己。诗人独立不羁的性格,不屈的精神,“吻着枷锁”弹唱“正直的声音”,“令伏隆卓夫的妻子神往,甚至两人间发生过一段浪漫史。
诗人在艰难处境中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体会更深刻了,与人民的心更加贴近了。他在《安得烈·雪尼埃》一诗中写道:“自由、法律在哪里?在头上仍只是斧头统治我们。我们推翻很多帝王。可是我们又把杀人犯和刽子手选为皇帝,噢,可耻!可怕!。”舆论界认为这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回声,政府把它看成是政治案件。保存诗抄的青年军官被捕,普希金多次受审讯。紧接着,彼得堡大主教指控《加甫利颂》的作者犯有国事罪。诗人还因当众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而大受申斥,悲剧对君王的随便处理和让壮阔的人民的洪流冲向皇宫,使沙皇大为恼火。沙皇责令诗人将该剧改成“类似瓦尔特·司各特那样的历史故事或长篇小说。”诗人回答得非常干脆:“很遗憾,我既然写成了,就没办法改。”普希金服膺真理,无所畏惧,刚韧不折的精神是令人称赞的,他所受的迫害也是令人吃惊的。他在给宾肯道夫的信中悲愤难言地写道:“没有别的俄国作家比我受到更严酷的迫害。”普希金是有独立心灵的作家,他以独立性格塑造了自己作品的人物。
其次是作家对自己的神圣职责有明确的认识。时代感、使命感、责任感和为人民幸福抛洒热血的献身意识,成为作家的价值观念。他在走出皇村学校校门的第一首诗《致娜·亚·普柳斯科娃》(1818)中写道:
我只会把自由颂扬,
只会向自由献出诗篇,
我来到世上,并非为了
用那羞怯的缪斯取悦沙皇。
学生时代,他在《欧罗巴导报》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诗作《致诗友》(1814)是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创作宣言,表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他敢于逾越悬崖陡壁、叠障险峰,愿意过着作家的贫寒生活,当作家不是为了显赫的名声,不是为了取悦达官贵人。作家的神圣职责是“既有健全的理性,又给我们教导。”一个严肃的作家不能口是心非和“挥笔乱涂,浪费纸张”。他认为创作是高张的精神活动,要经历“思虑与痛苦”和感情的波动,好的诗不“那么容易写成”。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这种艺术观和审美观。他认为“以色情描写刺激想象力为目的诗篇,有损于诗歌的尊严”(《对批评的反驳》。与“出卖自己的自由,对着偶像叩头”的作家相反,普希金为呼唤政治自由,用语言把人们心灵照亮而选择了作家的神圣职业。普希金“最先感觉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第一个确定文学的社会意义。他是把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并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敏感的作家。他的创作影响俄罗斯文学茁壮的成长和健康的发展。因此他写道:在先帝统治的最后五年里,他对整个作家阶级的影响比内阁要大得多”。看来,文学的兴衰与作家的素质,关系极为密切。
注释: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12页。
②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0章。
③《对批评的反驳》,见《普希金集》第7卷,第198页。
标签:文学论文; 普希金论文; 十二月党人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俄国沙皇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