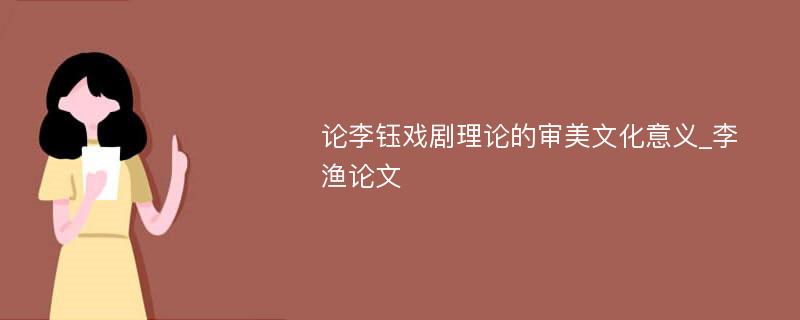
论李渔戏曲理论的美学与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戏曲论文,美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渔在清初戏曲界是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创作与理论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就其戏曲作品乃至人品而言,他在历史上所受到的评价毁誉不一。但仅就其戏曲理论而言,总的说来还是褒多于贬的。即使在今人的眼里,李渔的戏曲理论仍有其价值:
戏曲理论批评发展到明代,经过一代理论批评家的总结探索,扩大了研究领域……如果说(王骥德)《曲律》在古典戏曲理论批评的体系方面完成了草创的任务,那么不妨说,李渔在它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闲情偶寄》中的曲论,组织周密,条理清楚,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1]
这段话可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价。也就是说,在今人看来,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戏曲理论除了若干具体的新见解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李渔戏曲理论的主要价值是集前人之大成的理论总结。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从《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的目录所涵盖的范围与层次来看,确乎比王骥德的《曲律》更全面,纲目、层次也更清楚。[2]
然而另一方面,李渔《闲情偶寄》对于戏曲理论的贡献似乎还不仅仅是个理论总结的问题。当然,许多研究者都已指出过,李渔关于戏曲的结构、人物性格塑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新见解,因此可以说李渔不仅对前人的理论作了总结,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对《闲情偶寄》中所阐发的理论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李渔的戏曲理论中有许多观点实际上与王骥德等前代人关于戏曲的思路很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渔不是总结了前人的理论,而是开始了一种新的戏曲研究方法:他的理论具有前代理论所不具有的特殊的美学意义。这就是本文所打算探讨的李渔对17世纪以后中国戏剧美学建设的意义。
一
研究《闲情偶寄》的人大都注意到,李渔把戏曲的“结构”问题放到了全书的第一章。此前的戏曲研究论著中似乎没有人给“结构”问题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不无道理地认为李渔强调“结构”的重要性是针对历来人们忽视结构问题所作的一种纠正。至于李渔所说的“结构”一词的具体涵义以及在《闲情偶寄》中对“结构第一”思想的具体阐述,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地重视过。有的研究者注意到李渔在“结构第一”章中以“工师之建宅”为喻说明结构的重要性,与王骥德《曲律》中论章法的命意很接近。照此看来,“结构”的意思与章法差不多,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文章的各部分之间的组织联系。李渔讲结构第一,无非是强调一部作品的整体布局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结构第一”,那它的重要性就很有限了。事实上,李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结构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对戏曲的结构有自己的看法。李渔关心的是,戏曲结构的核心是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主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对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3]
这里所说的“主脑”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之类。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他认为《琵琶记》中蔡伯喈“重婚牛府”、《西厢记》中张君瑞“白马解围”是他心目中可作为“主脑”的“一人一事”,显然指的是核心关目,是统系全局使之不至于成为“散金碎玉”、“断线之珠”的中心情节。传统戏曲的主要成分是音律、词采、关目三样,明代戏曲批评的两大流派——吴江派与临川派各主音律与词采一端,关目则很少有人特别强调,更何况元曲拙于关目人所共知,亦未妨其成为一代艺术顶峰。相形之下,李渔对关目的重视似乎有点过分。李渔自己也说“填词首重音律”,他之所以把结构放在第一是因为音律有书可考。因此,人们往往把“结构第一”看成是一种救敝补偏的偏激之论。
然而细绎李渔关于结构的论述就可以看出,结构决不仅仅是个文章布局的问题。在《闲情偶寄》的“结构第一”章下包含了七款内容: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和审虚实。这七款内容中,戒讽刺讲的是立言谨慎、勿作人身攻击的创作道德问题;脱窠臼讲的是故事要有新意,勿蹈袭前人的创作态度问题;戒荒唐讲的是故事要贴近人情,勿以荒诞不经为新奇的创作风格问题;审虚实讲的是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这四款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属于叙事内容方面,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观念即组织安排和布局章法问题无关;只有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三款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组织结构问题有联系。因此,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李渔在“结构第一”的章目下所谈论的问题大多其实文不对题。究竟是李渔错了还是后人的理解有问题?我们再来仔细研究一下李渔在“结构第一”章中关于结构重要性的一段话: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
这段话就工师建宅之喻而言,确乎与一般人所说的“结构”一词的意思并无不同。王骥德《曲律》中论章法一节在讲到“章法”时所用的正是这个比喻:
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4]从这几句话来看,两人所说的“结构”的意思似乎差不多,都是章法布局的意思。然而通观李渔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说的结构的涵义不仅限于此:所谓“制定全形”、胸有成局,归结到创作问题上来,就是后面总结的“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结构的具体涵义是“奇事”,是“命题”。这就是说“结构”不是把现成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的形式构造,而是这各个部分赖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对于戏曲创作来说,这个根据就是“奇事”或“命题”。一般人(包括王骥德)在谈论结构时指的是对形式的组织安排,而李渔在这里所说的结构却是包括了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艺术构思活动。这种艺术构思活动的中心就是“奇事”,或者用他在“立主脑”一节中的说法——“一人一事”。
李渔关于结构的论述,对戏曲创作(严格地说是戏曲文学创作)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这就是以“事”,或者说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戏曲之不同于散曲、更不同于诗文之处就在于它的叙事性,这一点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在戏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叙事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元曲虽然称一代之盛,大多数杂剧作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叙事性在作品中的重要性。王国维在谈到元曲的特点时说: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5]
元杂剧作者并不是没有探索戏曲叙事的艺术性,否则就无法想象《西厢记》那样成熟的叙事作品如何产生。但这种探索毕竟不那么自觉,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或方法。而到了明代的吴江、临川两派进行音律与词采之争时,叙事性的问题同样被忽略了。王骥德的《曲律》被称为明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谈论的仍然不过音律与词采两端,戏曲的叙事性问题仅在“论章法”、“论剧戏”等处稍稍涉及。总之,在明代戏曲理论家的眼中,戏曲首先是“曲”,即由曲谱填词构成的单支曲子;然后才是“戏”,即整本或整出具有叙事情节的戏曲作品。戏曲欣赏实际上也是着意于声腔和词采而不是故事。李渔拈出叙事性来大加强调,决不仅仅是拾遗补阙的问题,而是戏曲观念的某种转变。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叙事艺术或者作为正统史传写作的工具,或者成为传奇小说。前者所要求的是雅正简洁,不同于后代发展起来的叙事艺术;后者则被视为小道,一直未被代表高雅文学传统的文学批评所重视。戏曲在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地位是在元曲时代奠定的。王世贞《曲藻》第一条说: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他给元曲乃至明传奇以很高的评价,把它们置于古典诗词发展的过程中与诗经、骚赋、乐府、唐诗、宋词并列。他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明代人对戏曲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明人心目中的戏曲其实首先是散曲,是与诗词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学样式,这是将本来比较靠近通俗叙事文学的戏曲拉到了更高雅的传统艺术一边。
戏曲创作的典雅化是明代戏曲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明代前期先有高则诚倡“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而后又由“文庄元老大儒”作一些《五伦全备记》之类的迂腐之作,明代中期有王世贞提倡“词家大学问”,诸如此类的创作与批评所提倡的无论是道德精义还是学问素养,总归与王国维所说的元杂剧的“自然”显然有了相当大的距离。至于后来的吴江、临川两派的争论中,临川派尚意趣、词采的主张固然表现出向文人趣味靠拢的典雅化的倾向;而主张“本色”的吴江派对音律、声腔的苛求实际上是另一种典雅化,即追求精细的听觉韵味的倾向。无论哪一种典雅化,都表现出对戏曲叙事性特征的忽视。有人说王世贞的《曲藻》所品藻的是“曲”而非“戏”,[6]其实可以说这在明代文人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
叙事艺术受到批评家们的关注大体上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了。自李贽、叶昼到金圣叹等人的《水浒传》评点,冯梦龙、凌濛初等文人的拟话本创作,都表明这一时期文人对通俗叙事艺术的兴趣在增长。戏曲创作方面,经过吴江、临川两派的反复论争,到了明末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剧作家李玉。李玉的作品如红极一时的“一、人、永、占”四种和《清忠谱》、《万民安》、《千忠戮》等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体现出戏曲创作发展的趋势。他的作品题材引人注目的现实性、故事情节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剧中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以及普遍存在于作品中的历史和社会悲剧色彩,这些构成他的作品特色的东西正是属于叙事艺术的特征。李玉之后洪昇、孔尚任的不朽之作《长生殿》、《桃花扇》也与李玉相似,进一步发展了戏曲的叙事性特征。
自明末到清初,戏曲批评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在这部书中,金圣叹对《西厢记》抉隐发微,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李渔对金圣叹的评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读金圣叹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7]
当然,李渔在称赞金圣叹的评点“晰毛辨发,穷幽极微”的同时,也指出他的评点“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这就是说,金圣叹评点的长处和缺点都在于他所重视的是戏曲的文学性。而他的评点所关注的文学性并非如明人那样重在“词采”,即词句的诗意文采,而是整体的叙事艺术特色。他在“读法”中概括《西厢记》的主题时说:
《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8]
在这里,他如同分析评点《水浒传》一样,把整部《西厢记》看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文章的中心则是人物。尽管金圣叹的分析有忽略音律的片面性,但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分析戏曲作品的方法确乎在戏曲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从李渔的对金圣叹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观念对他有很大影响。
但仔细比较一下金圣叹与李渔对《西厢记》叙事特点的看法,会发现一点微妙的不同:金圣叹认为《西厢记》的中心人物是双文(即莺莺),而李渔却认为是张君瑞。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原因在于两人的不同分析角度。金圣叹认为《西厢记》说到底只是写了一个人,就是莺莺。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西厢记》的美学追求集中地体现在莺莺这个人物形象上:“《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然双文国艳也,国艳则非多买胭脂之所得而涂泽也。抑双文天人也,天人则非下土蝼蚁工匠之所得而增减雕塑也……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净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龌龊也。”[9]他是从审美理想的角度分析作品的主题和中心人物的。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美学观念应当说抓住了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李渔的分析思路是抓住“一人一事”为中心:
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
根据李渔的观点,叙事艺术的中心问题是整个故事如何围绕一个关键行动展开。叙事艺术的中心究竟应当是人物形象还是人物的行动,这在叙事艺术研究的历史更加源远流长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就是个老讼案。叙事理论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主张的是情节为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行动第一;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影响更大的黑格尔则主张人物是现代艺术的真正中心;而20世纪的叙事学理论又重新关注起叙事艺术中行动的意义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把文学研究划分为三种形态——动词(或词语)、句法和语义,其中所谓动词(或词语)形态研究他指的是文体学、修辞学等方面的研究,语义形态研究包括了传统的实证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等方面,而句法形态则指的是对叙事艺术中人物的行动逻辑的研究。他指出,直到本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对句法形态进行认真观察之前,这个方面一向是最不受重视的。“但从这时起,它却成了学者们——特别是被归于‘结构主义’倾向的学者们——注意的中心问题”。[10]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叙事艺术的研究比起西方来当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至于戏曲叙事性的研究就更少了。然而李渔关于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观点却是个相当明确的叙事句法观念:所谓“一人一事”的意思,用今天话来说,就是由推动故事行动发展的最关键的行动者(“主语”)与关键行动(“谓语”)构成的一个基本的陈述句——结构主义者所关心的故事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渔的观点在叙事艺术研究中是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新颖的思想。
从人物性格塑造的角度分析和评价叙事艺术,这是明代后期小说批评中发展起来的新观念,其代表作就是叶昼、金圣叹等人对小说《水浒传》的批评。如果说小说(尤其是《水浒传》那样的长篇小说)叙事与戏曲叙事有什么不同的话,应当说前者有较多的篇幅和描写手段来刻划人物性格,而后者则由于舞台演出的要求更强调故事的戏剧性冲突。李渔和金圣叹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小说叙事与戏曲叙事的不同艺术要求的表现。李渔批评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是“文人把玩之《西厢》”而非“优人搬弄之《西厢》”,实际上说出了他与金圣叹的叙事艺术观念差异,两人对《西厢记》中心人物的不同看法正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金圣叹的叙事理论是小说叙事理论,而李渔的叙事理论才是戏曲叙事理论。
二
《闲情偶寄·词曲部》的第二章《词采》第二款“重机趣”说:
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则得词中三昧矣……
予又谓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性中无此,做杀不佳。人问性之有无,何处辨识?予曰:不难,观其说话行文,即知之矣。说话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脱,行文不板实,一篇之内但有一二段空灵,此即可以填词之人也。
这段话虽然是放在“词采”章中讲,其实表达的是他对戏曲风格的整体要求。更进一步讲,这里所说的“机趣”,实际上是他的审美趣味的中心。
在《闲情偶寄》的“结构”章中,李渔揭示了戏曲艺术的叙事性特征,这也是整体的特征。而在“词采”章以下,李渔则进一步分析了戏曲艺术中各个具体方面的要求和内在的审美特征,“机趣”就贯穿在这些分析中。如在“音律第三”章的“别解务头”一款中,他强调“曲中有务头,犹棋中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灵,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务头也。”他在这里虽然并没有具体解释“务头”一词的含义,但不难看出他所指的就是有灵性、有“机趣”的精彩之处。书中“宾白”一章是李渔标新立异的一章。他自称:“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11]可见他对宾白是很重视的。研究者们较多地注意到了他对用宾白刻划人物性格的见解,如在“语求肖似”一款中所说的“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等言论,就是人们为了证明他的性格理论而乐于引用的。但他对宾白的关注远不仅仅是为了描写性格,更重要的是通过宾白更能够畅所欲言地施展才情、驰骋想象力。他要求宾白语言的“肖似”性格,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技巧问题。就在上面引用的言论之前他写道: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快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
语求肖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灵感和想象力的需要。“宾白”章的第六款“意取尖新”标榜的“尖新”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替代“不中听”的“纤巧”二字,其实所要求的正是机趣:
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对于机趣的关注,在论科诨的章节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在李渔之前,王骥德《曲律》曾谈及科诨的问题。他认为插科打诨的用处仅在于“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如若安排勉强,不如不要。[12]而在李渔看来,科诨却是大文章:“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他要求科诨要“戒淫亵”、“忌俗恶”,同时更要避免板腐:
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
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13]
他对科诨的重视其实就是对作品中机趣的一种要求。从以上所引用的论述来看,他主张的“机趣”与迂腐、鄙俗相对,是一种鲜活、尖新、翻俗为雅的情趣。
文艺作品由载道、言志、缘情而转向“趣”,这是晚明以来文艺思潮的一个突出趋势。李贽、袁宏道等人所提倡的“童心”、“性灵”等精神表现于文艺作品中就是要有“趣”。他们的“趣”包括童子之趣、俗人之趣等,总之是发自真心、发自性灵的“真趣”,正如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所说的: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
显然晚明文人所提倡的“趣”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表现出晚明时期特有的“狂人”式的精神风貌与审美趣味。李渔所说的“机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晚明趣味的影响,这从他反对迂腐,主张“抑圣为狂,寓哭于笑”等等说法中就可以看出来。然而他的“机趣”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晚明的“趣”。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时期比较激进的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如李贽、公安派诸人所倡导的“趣”侧重于率性而发、不避俗陋的真性情;李渔虽然也重视性灵,也不避俗,但他同时更加看重才情。他要求的不是真率,而是尖新,他的“趣”是“机趣”,就是说要有机智,有灵感和想象力。他本人的戏曲创作就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形象说明和典型范例。如他的代表作《风筝误》,不仅以关目的奇巧著称,而且在许多词句和宾白等等细节上都表现出他富于机智、幽默感和想象力的趣味。在第六出《糊鹞》、第八出《和鹞》等出中都有几段揶揄书生韩琦仲的宾白和唱腔:
有趣的事,不见他做;没兴的事,偏强人为。良民犯何罪孽?动不动要捉我会文做诗;清客有何受用?是不是便教人烧香着棋。好衣袖被香炉擦破,破物事当古董收回;好髭须被吟诗拈断,断纸筋当秘笈携归……
他做出来的事,就是惹厌的。横也是一首诗,竖也是一首诗;他就打死了人,少不得也把诗来偿命!
纸鸢儿,又轻又巧;才放手,上天去了!只怕臭诗熏得天公恼,遣天兵,把诗人尽剿。我将那代笔的名儿直报,念区区,生平不作孽,望乞恕饶。
剧中对书生韩琦仲是肯定和褒扬的,上面的这些话表面上看也是在讽刺花花公子戚施的不学无术。然而细细品味起来,这些宾白和唱腔句句机锋侧出,借题发挥嘲弄、揶揄文人书生的迂腐气。鄙视、嘲笑冬烘学究和酸腐秀才,这几乎是明代以来重性灵、才情的慧业文人共同的爱好。明代文人中流传、汇集的这类笑话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殃及孔孟。然而比较起来,李渔的揶揄少了几分嬉笑怒骂的尖刻,多了几分机智之中的幽默感。李渔的“机趣”既是对晚明之“趣”的继承,也是对那种狂放无忌的“趣”所作的一种反拨。
三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戏曲理论与前代戏曲论著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对戏曲演出问题的重视。《闲情偶寄·演习部》用了五章十四款(外加《声容部》的“歌舞”一款)专门讲述表演问题,在这方面的论述中亦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如“选剧”要求从学古本入手,得腔板之正,而后间以新词,演出时调剂冷热以求合人情;“变调”要求根据演出的需要缩长为短、变旧成新等等,都显示出他对戏曲演出规律的精通。相比之下,前代戏曲论著在这方面的研究要薄弱得多。王骥德《曲律》中虽对戏曲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但对于创作与演出的关系却谈的不多。惟四卷第四十章“论曲亨屯”讲到戏曲作品的“遇”与“不遇”,所谈论的实际上就是戏曲演出条件与效果的好坏问题。他所说的“曲之亨”的条件包括:华堂、青楼、名园、雪阁、画舫、花下、柳边、佳风日、清宵、皎月、娇喉、佳拍、美人歌、娈童唱、名优、姣旦、伶人解文义、艳衣装、名士集、座有丽人、佳公子、知音客、鉴赏家、诗人赋新篇、座客能走笔度新声、闺人绣幕中听、玉卮、美酝、佳茗、好香、明烛、珠箔障、绣履点拍、倚箫、合笙、主妇不惜缠头、厮仆勤给事、精刻本、新翻艳词出;而“曲之屯”的情况是:赛社、醵钱、酬愿、和争、公府会、家宴酒楼、村落、炎日、凄风、苦雨、老丑伶人、弋阳调、穷行头、演恶剧、唱猥词、沙喉、讹字、错拍、删落、闹锣鼓、伧父与席、下妓侑尊、新刍酒败喉、恶客闯座、客至犬嚎、酗酒人骂座、席上行酒政、将军作调笑人、三角猫人妄讥弹、村人喝彩、邻家哭声、僧道观场、村妇列座、小儿啼、场下人厮打、主人惜烛、家僮告酒竭、田父舟人作劳、沿街觅钱。王骥德在这里对演出所提出的要求包括表演水平、欣赏者水平和演出的环境氛围等各方面。与李渔对戏曲表演问题的研究相比,《曲律·论曲亨屯》中提出的各项条件不仅显得粗疏琐碎,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李、王二人关注戏曲表演问题的不同视角。简单地说,王骥德谈论的是自己对戏曲演出的趣味要求,而李渔谈论的是戏曲演出的一般规律,即如何满足大多数欣赏者要求并进而提高欣赏者水平的问题。
李渔对戏曲表演问题的看法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基于他在指导戏班进行戏曲排练和演出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认识。如他在讲到戏曲唱腔中人声与丝竹吹合伴唱的关系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丝竹喧宾夺主,“戏房吹合之声,皆高于场上之曲”。产生这种弊病的原因据他说是这样的:
从来名优数曲,总使声与乐齐,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即有高低轻重之别,以其教曲之初,即以箫笛代口,引之使唱,原系声随箫笛,非以箫笛随声,习久成性,一到场上,不知不觉而以曲随箫笛矣。[1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戏曲表演的训练情况十分熟悉,因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便能够切中肯綮。在“衣冠恶习”一款中他谈到当时舞台演出服装的毛病:
妇人之服装贵在轻柔,而近日舞衣,其坚硬有如盔甲。云肩大而且厚,面夹两层之外,又以销金锦缎围之。其下体前后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为之,此战场所用之物,名为“纸甲”者是也,歌台舞榭之上,胡为乎来哉?易以轻软之衣,使得随身环绕,似不容已。
显然,李渔不仅对当时舞台演出的风气十分了解,而且观察仔细,见解不俗。这种以演出效果为依据所作的细致深入的分析批评不仅在演习部,而且在全书的其他部分亦随处可见,尤其是“宾白”、“科诨”、“格局”等章,这些以前批评家所论甚少的内容都是与舞台演出效果有密切关系的东西。如他在“词别繁减”一款中对宾白写作的看法:
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
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戏曲剧本写作的要求,就是要设身处地,“手则握笔,口则登场”,认真地体验演出效果。李渔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分析与后面《演习部》的内容相互映带,构成比较系统的关于戏曲演出的论述。
李渔对戏曲演出效果的关注和熟悉与他个人长期编演戏曲的生活经验分不开。他经常带着家庭戏班出入于缙绅豪富之家,搬演各种新旧曲目,在当时很受欢迎。这种戏曲演出的经验使得他在谈论戏曲理论时对实际的演出效果问题非常重视,从而形成了《闲情偶寄》中戏曲理论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研究范围、深度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比明代戏曲批评家更加大众化的趣味倾向。
李渔一生靠卖文、编剧为生,据他在书中自称“谋生不给,遑问其他?只好作贫女缝衣,为他人助娇,看他人出阁而已”,甚至喟叹“窃恐饥来驱人,势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为数十口家人筹生计乎?”景况似不尽如意。也许他的实际生活并非果真困窘如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生计是靠他的创作劳动和他人的欣赏来维持的。因此,对于李渔来说,关注戏曲演出效果是十分实际的而且要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后代学者往往对李渔的人品有微词,觉得他终日奔走于富豪之门,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而且以文媚俗,写些研究声色之娱的“闲情”文字,未免有辱斯文。的确,就《闲情偶寄》一书而言,《词曲部》和《演习部》在今天看来可称为研究艺术的有价值的论著,其他部分的价值就比较可疑了。像《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所谈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常识,虽说小道可采,毕竟难免玩物丧志之讥。至于《颐养部》教人行乐,《声容部》教人欣赏女色,更令人觉得俗不可耐。但是,如果撇开文人自命清高的标榜,应当承认李渔所研究的“闲情”并非他个人的嗜痂之癖,他不过是在迎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娱乐趣味而已。从整本《闲情偶寄》来看,无论所谈论的是艺术、生活抑或是狎邪情趣,都体现出世俗化、商业化的情调。李渔戏曲理论的文化意义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去认识。
明代以来商业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社会文化的繁荣,文艺活动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社会需要的影响和推动。从文艺活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到明代时,文艺活动的商业化趋势已经很突出了:私刻的通俗小说泛滥于市,文人的书画甚至赝品都成为畅销商品,戏曲艺术当然更不在话下,从一开始就是与商业化的市井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文艺理论方面,明代还没有能够反映文艺活动的这种商业化的新特征。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限定了文艺活动的功能在于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方面,这对于商业化的文艺活动来说显然是片面的。当沿用传统的观念来认识、解释商业性的文艺活动时,不免会变成一种不着实际的腐套或矫饰的话语。明人在为戏曲和通俗的拟话本小说进行道德辩护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如高则诚在《琵琶记》中所说的“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欣欣子对《金瓶梅词话》意义的解释:“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换之事”,都令人感到空洞肤廓甚至虚伪。传统的文艺观念显然难以解释新的文艺活动现实了。
李渔《闲情偶寄》所表现出的大众化、商业化观点表明对文艺活动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对文艺活动的商业性特征的关注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是一种堕落,而从文艺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文艺活动走向大众化、商业化,自然而然地要求对文艺活动的研究能够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对于戏曲艺术而言,这一要求就更为实际和迫切。明代的戏曲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毕竟还是局限在文人趣味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戏曲艺术当作文人把玩的案头文学和浅斟低唱的散曲来对待的。随着戏曲艺术的进一步繁荣,眼界更开阔、更实际的研究便显得更加需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渔的戏曲理论不仅仅是戏曲理论研究本身的发展和创新,而且是近古戏曲文化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注释:
[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参看上书296—299页关于《曲律》与《闲情偶寄》纲目的对比。
[3]李渔《闲情偶寄》卷一《结构第一·立主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王骥德《曲律》二卷《论章法第十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引自《王国维戏曲论文集》8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6]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闲情偶寄》卷二《填词余论》。
[8]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同上书卷四《惊艳》回前批语与第六节批语。
[10]参看《叙述学研究》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闲情偶寄》卷二《宾白第四·词别繁减》。
[12]《曲律》三卷《论插科第三十五》。
[13]《闲情偶寄》卷二《科诨第五》。
[14]《闲情偶寄》卷二《授曲第三·吹合宜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