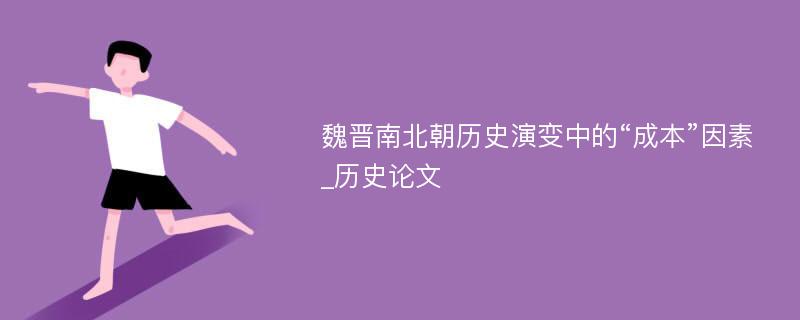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因素论文,成本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902(2011)02-0018-05
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如果以一个新的视角观察之,或许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下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内数事合而述之,供治史者参考。
一种制度或一个政权,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是否能够存在下去,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要看他的行政功能和维持其存在的耗费之间的效费比,由此就牵引出本文所谓的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
先从政治而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行政运作中的成本问题之所以经常产生严重性和紧迫性,是因为中土历朝都是一个实行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国家,它的行政系统是要对一个泱泱大国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它对内保持社会稳定,对外维护疆土的安全,就要维持一个相当规模的体制。
能否维持这样一个体制,就涉及了所谓“行政成本”的问题。如何估量中国古代这个行政成本,简而言之,就是官府的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之比。收入多支出少,国力就强盛,反之则衰弱,甚至有亡国的危险。当然事实上要更复杂些。收入,要看是否是杀鸡取蛋般的苛政;支出,要看是有效支出,还是无效支出。前者指的是维持官吏、军队、官衙、监狱等费用,这些都是稳定社会政治和取得财政收入所必需的。后者是指皇室的浪费,官吏的贪污等。无效支出越少,行政效能就越高,即是所谓治世。政治清明与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实这种现象的深层是涉及行政成本问题的。
不过由于中国古代朝政缺乏一种黄仁宇先生经常所说的毛病,即“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1],所以行政系统的效率难以考察,国家机器运行中的成本问题平素很难量化地彰显出来。只有在非常时期,无论是朝廷实行变法还是引起农民起义等社会动乱,都是反映行政制度出了毛病,或者说社会已经不能承担维持它的成本。同样在危机或分裂的状态下,尤其在分裂或割据的时代,如在本时期,由于彼此之间往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有可能对照比较,把各种制度与政策举措的合理性从行政成本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统治成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可以暴露得更清晰一些,成为诸朝诸国兴亡的原因之一。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试先从门阀政治阐说之。
门阀是中古时期(魏晋至五代)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成为在当时政治体制中的一股特殊的势力。这股势力在其巅峰时期的东晋甚至能与皇权“共天下”[2],即所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3]这种情况之产生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则是当时社会经济承担不起高度专制集权的行政系统之结果。
引起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魏晋之间的人口因战乱而大量减少。
东汉晚期黄巾起义,接着军阀混战,尔后三国鼎立也是战争不息,兵祸联结加之大兵过后必有凶年,使得中国的人口降至秦以后二千年间的最低点。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及逃散造成人口剧减的凄惨景象不难在魏晋时人的诗文里见到。如曹操的《嵩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4]。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5]。傅玄《放歌行》:“旷野何萧条,顾望无生人,但见狐狸迹,虎豹自成群”[6]。又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云:“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7]与这些诗文相印证,如史称东汉献帝回洛阳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8]。
西晋末与汉末时一样,永嘉变乱之后,“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9]。一如《晋书·食货志》所总述:“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饑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三国时“天下通计”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此尚不及东汉全盛时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即使是在被称为“晋之极盛”的平吴后武帝太康元年,全国人口总数也仅“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10]。这些户口数字大约在当时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肯定会有一些荫户、逃户之类不在其数,也就是说当时的实际户口应该大于此数,这也是历代的户口田赋统计中经常会出现的通病。考虑到当时是门阀社会,又常在战乱时期,依附豪强大族而成为朝廷难以统计征收赋役的荫户会更多些,但这种现象不会改变三国两晋时是两汉以降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基本事实,因为当时那些私荫户依然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少数,且朝廷随时可以用“土断”等方法使他们重新成为官家的纳税户。
完全可以设想如此稀少的人口是不足以承担自秦汉发展起来日益复杂的专制集权行政系统,那系统包括着众多的官吏、将士、宫室、官衙、驿站等等。而且因为权力都有着“控制欲”和“寻租”的天性,这些体现权力的机构规模和人员数量都有着自我发展的倾向,所以它们的存在无一不需要巨额的花费。而人口稀少所造成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缺乏导致官府租赋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以致朝廷行政资源空前匮乏,无力迅速重建一个功能齐全的专制集权统一国家,承担不起一个强大行政机器所需的各种费用负担。
而门阀政治除了表现在其代表家族或人物把持朝政外,还具有二个主要特点。其一是士族一般都拥有私家部曲,如河东薛强“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赵郡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葛荣起兵时,其子李元忠“率宗党作垒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11],其中武装者实际上就是李氏之私部曲。当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被委以军职时,其所属部曲也就有了官兵的身份。如东晋柳祖逖被朝廷任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12]。因此祖逖麾下的军队骨干,是他的族人和部曲宾客,有着浓厚的家兵色彩,并身经百战,所以他死后祖约能代领其军,继续成为东晋北境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这样的部队至少并不需要中央朝廷负担全额的军费。其二是由门阀来把持地方政治,即地方上主要官属都由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至少是在南北朝时,地方官,尤其是佐吏的俸禄皆由本地支出。北朝在孝文帝太和前根本没有俸禄。南朝“宋武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13]。虽然南齐后来对秩俸多少作了“定格”,但只是立个统一的标准,钱还是要地方支出的。而地方财政的好坏与门阀大族的表现大有关系,官吏的收入既然依靠地方财政,门阀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这也能说明地方主官采取清静无为的态度为何被当作时尚,因为当时社会基层,尤其在农村,基本上由大姓士族所控制,官府插手不一定会平稳局面,甚至会被视为“察察之政”而遭非议;另一方面因地方人口较稀等,郡县的财政资源一般是不丰裕的,而在政事上的有为,都要通过消耗资源来实现。这两者加起来,做官无为反而是符合实际的了。
上述二条说明了由于门阀政治的影响,朝廷能在军事上和地方行政上,大大节约开支,从而能使国家财政的支出能和其收入相匹配,使行政机器在一个较低的成本上运行。这样,门阀政治在当时的存在就显示了一定的时代合理性。
魏晋南北朝是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当时所谓的“五胡”,后来都化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这中间当然包含着很多因素,而其中一些因素之发挥,竟是“成本”作为潜因在悄悄地起着作用。
首先,这里说一下关于语言流通的成本问题。语言是为了交流,是保持社会中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一种语言就是一件工具。但是个人或群体是否采用这工具,就要看使用此工具所付代价(如语言学习的时间与精力等)和达到使用目的之价值之间的效费比。作为语言的高级表达的文字系统当然也是如此,不过文字流通所需成本要更高,因为还要加上书写文字材料(如笔墨、简帛、纸张及书写印刷费用等等)的工本。而与语言文字流通价值最相关的是它的流通量,其流通量愈高,使用价值也就愈大,与使用成本的比值也就愈高。
当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域、同一社会人群中流行时,两种语言之间就会自然发生竞争和交融,具有比值高的语言文字会慢慢地一边把对方顺势淘汰出局,一边从对方语言中进行某种吸收,如词汇谚语等,从而使自身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流通量,更具有竞争优势。若有政治的干涉,如用暴力长期禁止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会改变一定的结果,但此时已不是语言间的自然竞争了。
其次,语言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尤其在古代中国。现代对“民族”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在中国古代却是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族群文化特征的整体认定,因为这种文化特征是其行为准则的基础。当时绝大多数的民族差别不在于体貌特征,而在于文化心理,所以“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14]。即所谓“首不加冠,是越类也;足不蹑履,是夷民也”[15]。通过考古所得人骨之科学鉴定,“无论是汉晋时期的鲜卑人、辽代的契丹人还是元代或近代的蒙古人,在种族人类学特征上的确是颇为一致的,均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16],从而证明他们都与汉族有着极近的血缘关系。
既然如此,所谓民族融合就是在文化上的同一。这种同一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基层是表现在风俗及日常生活习惯上;其上层则表现在语言文字及思想心理上,其实系统的思想表达或成型的心理活动也都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根基的。语言是思想意识的载体,语言文字混同了,思想心理上的隔阂就会淡薄,乃至消失。这样,文字的作用在民族关系中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后世给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字”[17]政策对中国统一之意义的高度评价,是不过分的。
再回头说本时期,从公元311年永嘉之变到公元589年隋重新统一中国。二百多年时间里进入中原的“五胡”,已与汉族打成一片,应该说融合的过程还是很短的。其所以能如此,和当时少数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有很大关系。一是那些少数族语言都是适合游牧生活的,对农耕社会而言,大量缺乏适合农耕生产和生活的词句。因此一旦生活在中原,交流时在词汇上还是语法上都有理解和表达的困难,造成很大不便。由于游牧生活较为质朴,原来的话语系统相对历史悠久的汉语来说词汇含量小而语法简单,词句要迅速扩容改造也很困难,更难使占有多数的汉人放弃原来语言而接受它,于是为了在同一地域内互相交流和共同生活,不得不最后放弃原有语言了事,并学习汉语言文字,借此以对新事物的认识与表述。如本时期的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18]。这样学习汉语言文字就成了少数族进入农业文明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二是文字因素也是很关键的。这些少数族使用的语言,都是符合游牧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且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字系统。因为文字虽然植根于语言,但没有文字的语言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语言,当其与别的附带文字的语言共同使用时,必然会被逐步淘汰。虽然本时期一些少数族已经在农业地区建立了政权,成为统治民族,但都没有创建本民族的文字系统与其母语相配合。所以他们在治理国家时,不得不借用汉字为工具,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新情况,其中包括行政制度和法制。汉文的政治和法律用语跟传统的制度与观念是相一致的,所以一旦行政命令法律条文用汉文来表达,它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中国传统制度的框架。以此来治理国家,被治理的少数族民众也只能接受汉语言文字。这两点加起来,使得在中原生活的少数族众要坚持原来的语言十分困难,不仅是普通人,就是少数族统治者也无法承受如此代价,于是不得不最后自己放弃了事。所以尽管有统治者的倡导,“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须“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19]了!北朝后期“鲜卑语、胡书”与“煎胡桃油、錬锡为银,如此之类”[20],都成为一种专门技术了。于是使用汉字也成了少数族统治者在汉地建立政权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顺便提一下,或许是出于对本时期这段历史的认识,自唐以后入主中土的少数族统治者,如契丹、女真(满)、蒙古等,都努力创造其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保持其作为统治族的民族特征。一般这些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速度也大大减慢,除非这个民族丧失了统治地位,这些立足未稳的文字也自然而然地被淘汰,成了一些今天难窥其全貌的死文字。
对成本的考虑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情况改变而变化。魏晋南北朝期间曾经产生二个比较具有特色的制度,即田制和专役户制度,它们在唐代以后基本趋向于消失,因此也可算是本段历史的特点之一。
如果遥远的井田制最多只是传闻和概念上的影响,那么历史上的所谓田制几乎都集中在本时期:如屯田、占田、均田等制,而均田制在隋及唐前期的存在虽然引人注目,实际上只是本时期制度上的一种延续。所谓专役户是被迫至少服一种专门役的贱户,最早出现的是三国时的士家制,即兵户,后来还有盐户、牧户、官户、乐户、隶户、吏户,以及统称杂户的“百杂之户”[21]等等。这类专役户在本时期很多,隋唐以降虽没有完全消失,但在社会上已经是一种很局部很边缘的现象了。
这二个制度都是和汉晋之间人口的大量丧失而为秦以后人口最稀少的时代相关,当然那个时候土地有了相对多余,财富得失的关键点就在于劳动力。中国古代以农立国,财政税赋主要来自于农,而当时农业的发达又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为了加紧对人口的控制,其实也是抓住了主要财源,因为当时正是体现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于是这就关系到朝廷生存赖以财源,进一步关系到政权的存亡强弱,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足以考虑了。本时期历朝政府建立或维护这两个制度,都是为了保证朝廷有足够的赋役资源,防止户口被大族豪强荫隐而导致流失。因此不计成本地增设官员,以将专役户另籍管理,及专司登记分配田地等都是值得的了。
田制之兴废的原因之一,也和行政成本有关。所谓田制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对普通农民加紧实行人身控制的一种手段。它在允许农民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前提下,把他们更直接地纳入官方的行政管理之中,藉此征收租赋,所以户调式、课田制、三长制等等都是与其配套的,虽然这些制度使行政事务多了起来。当一些妨碍收入的时代特征转弱或消失时,主要是人口增长,劳动力显得越来越充裕,朝廷财赋收入就不需要田制和专役户来保障,田地也不怕没人来种,花费大量行政资源来进行劳动力控制就不紧迫,这些制度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因为维持田制和专役户制,都需要很多官吏,当地多人少变成地少人多时,将土地不断重新转换分配,以维持制度的实行,会有更多的相关事务要处理,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官吏来操作,这就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的提高。因此,官府就会改弦更张,变更体制。这是由于人是活动的,土地是不动的,盯住土地进行管理显然要比依照人头实行管理要省事得多,即行政管理成本可以小一些,于是一度盛行的田制和专役户制就式微了。
所以成本是与收入相对的,究竟要不要重视成本因素,还要看对收入那一头重要性的估量。两者重要性之比,才是一种制度取舍的关键所在。
从上述对社会政治演变中的成本因素之解析,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
甚至南北朝时代军事上之北强南弱,军队后勤供应所花成本之高低,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在南北相争中,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异地征战的困难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
所以江左的东吴或东晋南朝若要对北方有所行动,必须开凿或疏通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草服装,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22]。东吴也曾“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23]。桓温与刘裕北伐时也都开凿水道以利军事,如桓温在太和四年北伐时“凿鉅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24]。刘裕北伐时多次用舟师,曾“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并命部下“即舟遡流,穷览洛川”以“欲知水军可知之处”[25],还曾在义熙十三年闰月“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26]。这中间由于淮河水系通过人工堰渠调蓄能够相通江河,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27]。反例如桓温于太和四年(369年)三月率“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但由于“时亢旱,水道不通”,在先胜一仗后,“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28]。
这也是屡次北伐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但要开凿水道,费工费时费力,还要视水文气候如何,后勤补给的成本高得很。而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现成的水道,后勤供应的成本小,方便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再加上原有的骑兵优势,中国军事史上的北强南弱,不能不说与此无关。
再如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儒家提倡德治,即通过教化为主,使民众惯于自我约束,从而和强调外在约束,进行法治的法家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办案打官司无论对民众还是对官府来讲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法令滋章则必然需要很多的官吏来执行,行政成本或社会成本就很高,不符合农业社会的节约精神[29]。在对待四边的方略上,儒家推行的是王道,其实就是一种反对穷兵黩武,以怀柔安抚为主的政策[30],能最大限度避免战争。大规模或连绵不断的战争,不管是输是赢,都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会给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带来不可忍受的负担。即使“开边”成功,新占领的土地往往因难以农耕而无法为国家提供租税收益,反而需要内地的钱粮支持,得不偿失。儒家主张实施王道和德治,内外俱以和为贵,能使社会经济免受大的伤害,也就有利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从上述两点而言,儒家标榜的仁政,都是为了减轻行政成本的政策理念。这也能够解释,本时期虽然玄学与佛学十分风光,表面上是在引领着时代意识的潮流。但实际上支撑社会价值观念的,却是儒家思想。后世所谓魏晋玄学大家者,几乎无一不涉及当时之经学,“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31],其中包括王弼的《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于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32]。其实即使是玄学和宗教,都是体现以意识导向为先的治国理念,于此与儒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点。而推重道德教化为先,正是一种低成本治国的方略。上述说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如何,都是与此相关的。
总之,成本意识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在“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在生活中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这种态度的存在除了大量的谚语可以证明外,其拜神中的功利性亦足可反映,发财、免灾、生子、升格等等愿望能否实现往往决定着一般信徒对其所求神祇的信仰程度。
上述从成本角度回视一些历史现象,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这么看的。古代的当事者虽然不一定有行政“成本”那样的概念,但做利弊得失的比较绝对会是有的。正是古人以其智慧经常做这样的比较,成本因素也类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才会在历史的演变中发挥其无形的作用。本文试图将这种潜因素勾描出来,也是对古人顺势应变智慧的一种学习体会。
标签:历史论文; 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汉朝论文; 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