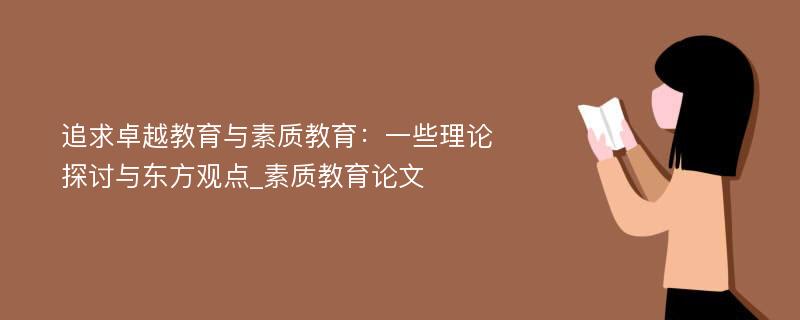
追求卓越教育与素质教育:一些理论的探讨与东方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追求卓越论文,观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卓越与素质:一些定义上的困难
如果说80年代是追求卓越教育(Excellence in Education )的年代,那么,90年代就是寻求素质教育的年代,美国自1983年出版了一系列的“卓越报告书”以来(Task Force,1983),就引起西方社会对卓越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后,当“全素质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一词出现之后,“素质”一词也渐渐大行其道。
可是,不管是“卓越”还是“素质”,两个词都含义甚广。卓越和素质的定义,对不同时、地、 人来说都不尽相同, 正如狄玛和柯扑(Timar & Kirp,1988)所说:“卓越改革之所以复杂,是由于它并不是一套固定的政策,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况而行之有效。”早在六十年代,加德纳(Gardner)就为卓越概念的复杂性下了注脚。 他说:“在知识领域上有很多种卓越。一种卓越的知识活动带来了新的理论,但另一种则发展了新的机器。一种想法认为卓越要在教学中表达出来,而另一种想法却认为研究才是卓越的最佳保证。一种想法认为卓越必须靠数据来支持,但另一种想法却以为卓越有如诗词般的意象……。某种卓越需要通过教育制度来达到,但另外一种则要在教育体系以外才能体现出来”。(Gardner,1961)
如果卓越难以定义,要为素质下定义就更加困难。随便涉猎一下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者谈及素质或品质时,都是用素质或品质以外的东西来表达,如:品质控制、品质保证、素质管理、服务质素等等。由此可见,卓越对不同的时地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而素质在依附着不同的词汇时,它所指的东西,就相应地有所改变。斯图尔德和韦舒(Steward & walsh )也特别指出这一点:“素质不可以从用途和使用者的经验分割开来。所以,一种服务对某一个使用者来说可以说是有质素的,但另外一个人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原因是他们两人的需要不同、要求不同、期望不同。因此,要提供有质素的服务往往要同时考虑到被服务者的背景如何,他们会如何对该项服务作出评估,以及他们在哪一种情况下接受该服务。”(Steward & Warsh,1990)
素质的定义
尽管困难,但是澄清概念还是必需的。素质的概念似乎跟传统功能主义的现代化概念有点分别,而且带点后现代的意味,追求卓越和追求素质都代表了对完美的追寻,但两者却有微妙的不同。卓越的概念一般联系着竞争、成就,以及经济的发展,这种概念取向在美国80年代的一系列的卓越报告书中十分明显,而素质则比较侧重用家庭和顾客所要求的标准、有关组织自我定义的远景(vision building)、 素质保证与管理的程序、以及自我完善的机制(Murgatroyd & Morgan, 1992,Kaufman & Zahn,1993)。“全素质管理”或素质保证的观念往往将“素质”变成达到“卓越”的工具,并不将它当作自身的目的。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素质,倾向于否定传统而外在的卓越观,而强调一个组织的自我个性,以及素质定义的弹性。这种特点,在香港1996年出版的《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又名《优质学校教育》)中就表达得很清楚:“我们建议教育署应鼓励学校各展所长,发展优质教育,以保留学校的个性和特质,学校应根据本身需要,设立校本管理制度和制订课程,达到优质学校教育的目标……”(教育统筹委员会,1997,第3页)。
但是,当素质的定义偏向强调个性和自主的时候,素质的定义同时变得相对化。亚当斯(Adams)在总结素质的概念时, 也勾画了这些特点。他指出素质的定义包括了以下各点:素质的意义多样化;素质反映个人的价值观;素质是动态的,它的意义因时因地而改变;素质的意义囿于价值体系、文化和传统(Adams,1998,p.11)。
亚当斯所列举的素质的定义,可以说是上面的讨论的最佳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素质定义的个性化、弹性化和相对化的同时,他也指出素质的意义系于价值体系、文化和传统。事实上,当我们留意一下东西方文化体系对素质的讨论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同的侧重点,上面的讨论,主要代表了西方近期有关素质的讨论。但是,东方社会对同一问题的讨论方法和重点,看来却很不一样。
有关素质讨论的一些东方观点
在东方社会,有关教育素质的讨论,某些方面与西方的讨论相似,但整体的基调和方向确有不同。台湾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在1995年颁布了两期咨议报告书,在《第一期咨议报告书》中,卓越与素质的概念明显地有所分别。报告书有一节提及“追求卓越的原则”,指出台湾教育的发展“在量的方面已有良好成就,但在质的方面仍难令人满意。今后的教育改革,应以教育品质的不断提升为主要考虑。”在论及提升教育品质改革的方向时,咨议报告书就列出五大方向,包括教育人本化、教育多元化、教育科技化和教育国际化。这些方向,尤其对人本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侧重,也反映了上述的个性化和弹性化的特点。但是,它们却同时表达了台湾教育改革者的教育理想。譬如,在谈到教育人本化的时候,报告书说:“教育是要栽培一个完整的人、使其能以充分实现自我为目的,而不应受制于职业市场、政治目标或其它意识形态等特定的需要。吾人应发挥人类内在的理性,借重科学与民主的方法,以及人文价值的观念,认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充分了解本土的环境历史及文化,并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潜能,为人类的福祉贡献心力,进而建立和谐、守法、富足的社会,创造和平、繁荣、洁净的世界。”(1995,第20页)很明显,一方面,它融合了素质个性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审议会的教育理想,而这些教育理想是跟他们对人、对社会的价值观紧紧扣在一起,也和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重视相连。
报告书也列举了一系列的教育目标,进一步为教育素质提升的方向作出比较明确的诠释。这些目标是:①自律的道德情操、②自我了解的能力、③适应变迁的能力、④尊重他人的能力、⑤关怀他人的情意、⑥革新创造的能力、⑦手脑并用的能力、⑧高尚的生活品味、⑨团队合作的精神、⑩民主法治的精神,(11)科学技术的智能、(12)终身学习的习惯、(13)生态环境的关怀、(14)开阔的世界观点(1995,第1页)。
十年前,日本的教育审议局在1985~1986年间,发表了一连四本的教育改革建议书。建议书的一个着重点就是教育素质的改革。审议局的第一号报告书说:“要促进教育改革,必须要经常改进教育的素质和教育研究。”(Council,1995,p.13)跟台湾的审议会报告书相似, 日本的审议局报告书也为教育素质明定方向。这些素质改革的方向是:①重视个性发展、②重视教育基础、③培养创造力、思考力和表达的能力、④增加选择的机会、⑤将教育环境人性化、⑥过渡到终身学习的体系、⑦适应国际化、⑧适应资讯时代(Council,1995)。
很明显,日本在教育素质改革的过程中,重新检讨了他们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是教育改革方向的重组,另一方面是教育理想的重新定位。在这个教育理想的定位过程中,个性化和人性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重点,但是另一个重点却是整体理想的重拾,就是对教育环境的重视、对终身学习的重视、对国际化的重视,以及对资讯社会的重视。
香港的素质教育改革有较重的西方色彩。教育统筹委员会的《第七号报告书》比较突出所谓西方“全素质管理”的倾向,例如鼓吹建立素质文化、明确责任制度、质素保证的程序、以多元化教育体制增加选择机会、重视效率与成本效益等等。此外,正如台湾的报告书一样,素质与卓越的概念也分别开来。报告书其中一节提及“推广学习质素文化的观念,促进学生个人成长,鼓励学校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俨然成为了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推出一个几乎全西化的素质管理观念的时候,一如台湾和日本,香港的报告书也不忘提及香港整体的教育理想或方向,它说:“我们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不同场合发表对教育的理想,他认为教育是培养青年人:①德、智、体、群、美的全面发展;②中英兼擅,能讲流利的粤语、普通话和英语;③具备自学能力和求知好问的态度;④肩负起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责任;⑤放眼世界;⑥既可以吸收现代科技及思想,又重视中国传统;⑥具备坚强意志、勤奋进取的精神和应变能力;⑦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亦尊重法治。”(教育统筹委员会,1997,第7~8页)
素质教育在中国内地是讨论的热点。事实上,“素质教育”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内地90年代教育的新词汇。中国内地对素质概念的讨论甚为激烈和尖锐。正如黄甫金说:“众所周知,人们对‘素质教育’存在相左的看法。”(黄,1996,第2页)。他指出, 在中国内地有关素质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先天论、后天论和融合论。先天论者认为“素质”是指有机体的生理特性,而这些特性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后天论者认为,“素质教育”中赋予“素质”的涵义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思想品质,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行为习惯”、“读一般书报、写作一般文章的能力、基本的计算能力、自学能力”、“具有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劳动本领”,等等。这些对素质的要求,是后天社会所附加的。融合论者则认为,所谓素质,就应当指人们先天自然的和后天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和品质而言。具体地说,素质就是人们身体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专业的和心理的一系列基本特点和品质的综合(黄,1996,第9页)。 其它的种种分析在中国多得不胜枚举,例如,熊川武也分别归纳了中国现时对素质讨论的五种理论,即先天说、双刃说、片面说、包容说和失值说等(熊,1997,第1页)。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加赘述。
但是,尽管意见纷纭,中国内地的众多讨论都对现时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教育工具化状况十分不满,转而发出一种对内在教育素质的渴求。1993年2月的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指出, “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引自袁,1997,第1页)。袁振国说, 在中国,素质教育是这样一种理想,首先,它倡导在教育中每个人都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第二,素质教育倡导的是在教育中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第三,素质教育倡导的是每个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除了指出素质教育是一种理想,袁氏也指出素质教育是一种价值观。他以为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价值观的否定和更新,是根据时代变化、社会发展的形势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素质教育是强调以人为对象,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其次,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有个性的发展;第三,素质教育注重教育的可接受性,更注重教育的可发展性;第四,素质教育是指向大众主义的教育。他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本位,以学生的可发展性为本位和以大众教育为本位的素质教育,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
从上述的分析看来,在中国内地,对素质的看法虽然众说纷纭,大体而言,也是朝向个性化、多元化方面发展。但是,在中国内地,更明显的特点是,素质教育的争论,同时代表了教育理想的争论,以及教育价值观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检讨教育在当今社会应发挥什么作用、应扮演什么角色、应怎样针对时弊等等。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追求素质可以说是90年代的世界大趋势。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对素质定义都有激烈的讨论。基本上,整个趋势都在强调素质的个性化、弹性化和多元化,但是,东西方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分别。在西方,讨论的焦点似乎侧重在品质控制、素质管理,进而倾向寻求一个能够达到自我完善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主要特点是确立一些监控和管理的明确程序。在这种大前提下,西方社会对素质的概念较倾向以顾客要求为主导,素质的意义也因而显得比较相对化,因此,素质本身就变成了比较模糊的追求完美的概念。
在东方社会,从上述的文献看来,对素质的要求也是倾向于强调人本化、个性化和多元化。但是,东方社会的讨论则较倾向将素质教育的讨论变成教育理想的讨论,东方社会的最大关注并不在于程序与机制,而在于素质的概念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这些新的理想和价值观能否切中时弊,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这么一来,素质教育的讨论,就变得较具争论性和激烈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内地就更为明显。
但是,东西方的讨论特点,也许能够互补不足。东方并不太关注程序与机制,这大概是东方社会应该向西方学习的;相反,西方也许太注重程序与机制,以及顾客为本的素质要求,因此,素质在西方反而显得空洞并缺乏“个性”。这一点,也许是东方社会在素质的探求上可以作出贡献的。二千多年以前,儒家思想就倡导人皆可教和人皆可以臻善的主张和理想。不知道今天东方社会执着于教育素质的理想探求,是否根植于东方传统对教育的期望与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