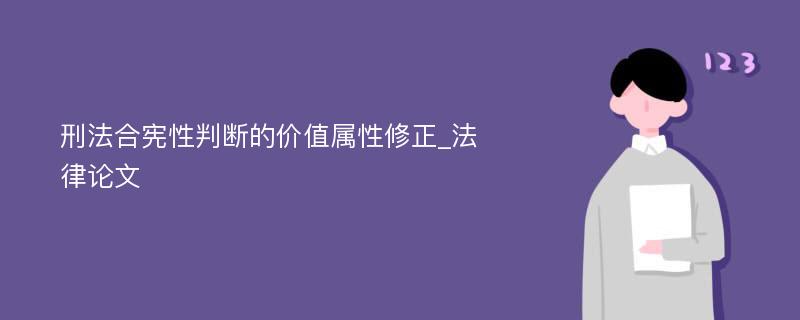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辩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14(2008)01-0069-(10)
一、问题意识及研究进路
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规格与标准,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符合了犯罪构成,法官判断定罪的过程表现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过程。因而,如何正确理解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性质,就成为对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在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属性上,我国学者常常认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形式的、事实判断,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判断过程。如,有学者在批判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时,指出:“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其实只适用于一种对实害行为‘贴标签’的流水化处理过程,即对大量的、反复出现的犯罪只需适用构成要件的规定性简单地作出判断即可……根据形式要件的符合即可得出实质上构成犯罪的结论。而一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模糊不清或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关节点上,则构成要件提供的标准便全无用场。”[1]181 很显然,这一批判是建立在将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理解为形式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犯罪的认定分为两步:第一步,看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如果不符合,则直接排除其犯罪性(形式判断);第二步,如果符合犯罪构成,再看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如果是则不认为犯罪,如果不是才认为犯罪(实质判断)。[2]68
在此,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属性被看作是形式的事实判断,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被化约为解决某一行为“是”或者“不是”犯罪的事实命题。“而所谓事实认识、事实判断可以被看作关于所知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认识或判断”,[3] 如甲问乙:“这是什么”,乙回答说“这是桌子”,乙陈述的就是事实,表达的是事实判断的命题。然而,犯罪是否成立能否被化约为“是不是”犯罪的问题、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能否被化约为事实判断的问题大有可疑。即便如此,以“是”或“不是”这种直陈句形式出现的命题也并不一定都是事实判断。因为,价值判断的语言表述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价值句也可能以陈述句的外观出现。[4] 如,马丁·路德·金的黑人示威者脖子上挂着“We are man?!”的标语牌,没有比这话更像事实陈述的了,然而谁又能否认,这更是对把黑人不当人的制度性事实及其体现的价值观的根本挑战,[5] “是一个比‘应该把我当作人看’更能表现价值倾向的价值判断”。[6]
然而,“犯罪作为一种价值事实,将主体的评价‘融合’其中,行为仅仅是可以评价为犯罪事实的客观基础,而主体的评价才最终确定是不是犯罪”,“主体的评价对于犯罪事实的成立与否具有关键性的影响”。[7] 犯罪的这种“主体评价性”说明,与其说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毋宁说行为“应否”成立犯罪,与此相应,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属于价值判断,而非形式的纯事实判断。
下文将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三个方面,力图澄清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属性的认识误区,证明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判断属性,犯罪行为的成立毋宁是“应不应”成立犯罪的问题,并进而说明,价值判断不但是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而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8]244
二、价值判断: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
(一)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法官根据犯罪构成对案件事实所作的判断,判断的标准是立法者预定的犯罪构成,判断的对象是经确认的案件事实,判断的结论是案件事实符合或者不符合犯罪构成。既然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依据法定的犯罪构成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因而,作为判断标准的犯罪构成的性质如何,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属性。详言之,如果犯罪构成是形式的、价值中立的,则以此进行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也只能是事实判断;反之,若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外部表达,则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则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
立法者在立法时需要决定哪些行为不应构成犯罪、哪些行为应构成犯罪,这就体现了立法者对什么应是犯罪行为的判断。立法者进行这一判断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依据一定的要素或标准进行。这些要素或标准在立法上就体现为犯罪构成要件。如果犯罪构成要件只是立法者所作的事实判断,如果犯罪构成要素是立法者如同自然科学家探求自然规律那样从犯罪行为本质中挖掘出来的客观事实,那么,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犯罪圈的大小、具体犯罪的构成要素就应是始终如一的,正如地球永远围绕太阳转一样。然而,实际上不同国家、相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犯罪圈的大小、具体犯罪构成要素总是呈现差异、变动的特点,究其原因,是立法者价值评价变化的结果。“立法以价值判断为依据是明显的,例如先有‘因被欺诈或被强迫而向他人转让了财产权的人,可请求其恢复财产权’的价值判断,然后才有依据该价值判断制定的‘现在对该财产所有或占有的人必须返还’的规定”,[8]244 由此可见,“立法不过是一定价值判断的记录”。[9]620
笔者认为,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价值命题。这表现在:
第一,一个国家犯罪圈的扩张或限缩、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是立法者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
立法者应当适时进行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应当合理划定本国的犯罪圈。然而,立法者并非随心所欲进行犯罪化或非犯罪化,而总是依据一定标准进行考察。
这一标准,在宏观上就是社会生活需要,立法者总是根据本国的社会生活需要来划定犯罪圈。当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社会生活对安全的需要大于对自由的需要时,立法者总是倾向于扩大犯罪圈;反之,当社会治安形势良好,社会生活更需要自由时,立法者就更易对一些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以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为例。我国自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大量的经济失范行为、经济违规行为涌现,交易安全、市场有序化的需要日渐凸现,在这种背景下,立法者就扩大了经济犯罪的犯罪圈,1997年《刑法典》分则第二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迅速扩充即是这一需要的反映。既然社会生活需要是立法者划定犯罪圈的现实标准与宏观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主体对客体的需要或者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因之,立法者根据社会生活需要进行犯罪圈的扩张或限缩就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在微观上,立法者进行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标准就是某一类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某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时,立法者就会把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反之,当刑法典中规定的某一犯罪,其社会危害性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降至较低程度甚至消失时,立法者就会将其非犯罪化。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充满价值评价意蕴的概念,某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增加至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或下降至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本身就是立法者价值评价的结果。“主体性事实是因主体不同而不同的客观事实,这是主体性事实与客体性事实、价值事实与‘科学’事实不同的经常可见的表现。科学上所说的事实,对于所有人来说,只要客体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而价值事实则是:尽管客体是一个,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事实。”[10]270 犯罪显属价值事实,受主体评价的影响与左右,犯罪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价值评价。如冬天将海南出产的西瓜长途贩运到北京交易,行为还是那个行为,在1979年《刑法典》就被立法者评价为投机倒把罪,在1997年《刑法典》就被立法者评价为合法行为。“如果法律没有将其犯罪化,任何人都不能将其视为犯罪,这种行为也就不具有犯罪的意义。只有法律说内幕交易是犯罪,这种原本就存在的行为才获得了新的属性——犯罪。”[11]11 可见,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是立法者依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变化所作的价值判断,是主体进行价值评价活动的表现。
第二,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本身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表现,是立法者对行为类型价值评价的法律表现。
立法者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将具有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刑法上的犯罪。“事实上,刑法总是将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类型化为构成要件的行为;立法者在规定构成要件时,必然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实质的评价。”[12]114 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立法者规定的刑法必须为裁判者提供一个明确的判定犯罪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固然可以作为立法者选择犯罪行为类型的标准,但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充满价值评价意蕴的概念,裁判者若直接根据社会危害性来认定犯罪,则有易出入人罪、侵犯人权之虞。因而,立法者必须将自己对行为所作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外化为一个明确的、可供裁判者操作并遵守的标准。这一标准在刑法上就外化为犯罪构成。犯罪构成就是立法者对某类行为社会危害性评价的法律表现,是裁判者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实际上,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犯罪构成实际上是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构成。”[13]130
刑法规范不仅是裁判规范,而且是行为规范。立法者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并非对生活现实的行为类型的简单事实表述,而是表达了立法者强烈的价值评价,这种价值评价在刑法上通常是否定的。“立法者并不是要描述事实,而是要调整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事实。”[14]57 立法者就是通过表达出来的否定价值评价,告诫人们什么是刑法禁止做的行为,如果做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会招致何种法律后果,籍此刑法规范就发挥了行为规范的机能,调整了人的行为方式。“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或行为方式,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14]52 一个完整的刑法规范总是由假定(法定构成)和处理(法律后果)组成。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内含了“禁止故意杀人,如果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为规范,表达立法者对符合故意杀人法定构成的行为的否定价值评价、从而告诉人们杀人是禁止的,刑法规范发挥了行为规制机能。“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在事实构成所描述的事实行为中什么才应该是适当的、‘正义的’”,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评价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14]61
第三,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设定取决于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
犯罪构成包括共同犯罪构成与具体犯罪构成,共同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所有犯罪都必须具备的,例如法定年龄、故意或过失、危害行为等,而某些犯罪除具备共同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外还必须具备特殊构成要件要素,例如行为对象、行为手段、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动机等。犯罪构成是对生活行为事实特征的法律概括,是生活行为在法律上的定型。然而,生活行为具有诸多事实特征,并非所有事实特征都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有的事实特征能提供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甚至作为认定犯罪的主要证据,但并不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者并非随意设定犯罪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依据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大小来选择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特征理所当然必须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否则对犯罪的成立是没有意义的。能否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衡量某一事实特征能否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标准。”[13]130 以故意杀人罪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前者只需具备法定年龄、危害行为、主观故意等共同构成要件要素,而后者除需具备共同构成要件要素外,还需具备特殊构成要件要素——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出现这种差别,主要因为对于故意杀人罪而言,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手段与行为对象(是未成年人或者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正常人)对行为成立犯罪并无决定性影响,不管在何种时间、地点,采取何种手段,针对何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都成立故意杀人罪,行为时间、地点、手段、对象或许能影响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但不影响该行为的定性;而就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而言,一般情况下捕捞水产品是合法的行为,只有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立法者把行为地点、行为时间、行为手段作为该罪的特殊构成要件要素。再如,“立法者在规定某罪的主观要件时,一般只规定其是故意或过失即可,较少把主观动机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加以规定。只有当主观动机足以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或有必要借助主观动机来区分此罪与彼罪时,立法者才把主观动机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规定。”[15] 立法者之所以把牟利或传播动机作为走私淫秽物品罪的特殊主观要件要素,是因为只有出于上述动机走私淫秽物品的,其走私的数量才可能比较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可能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立法者之所以把高利转贷动机作为高利转贷罪的特殊主观要件要素,是因为这里的高利转贷动机起到了区分高利转贷罪与贷款诈骗罪的作用。
综述之,既然犯罪圈的扩张或限缩是立法者价值判断的结果,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对行为类型价值评价的法律表现,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设定取决于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基于此,犯罪构成必然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表现,犯罪构成应当是价值命题。
(二)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裁判者所作的价值判断
“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14]61 由“犯罪构成属于价值判断”的论证结论完全可以推导出“依犯罪构成进行的判断当属价值判断”的结论,因为司法裁判过程就是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具体化的过程。不过,考察法官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思维过程,可进一步有力证明笔者“价值判断是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之观点。
长久以来,法学陷入了“完满体系的演绎思维”中,认为法官的工作“无非只是将现有的案件与法律文字作比较,不必考虑法律的意义与精神,当字义是诅咒时,就诅咒,是赦罪时,就赦罪”,法官的判决无非是“制定法的精确复写”,因此“他需要的只是眼睛”,法官只是“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16]72-73 然而,令实证主义法学遗憾的是,“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17] “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中介,没有价值评价,就没有判决结论的证成”。[18] 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只要承认法官就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的裁判活动是一项司法活动,就不能否认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
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裁判者所为的价值判断,排除法官的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完成从法律规范到案件事实的判断过程,就无法得出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结论。因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法官依据法定犯罪构成对案件事实所作的一种判断,判断的大前提是犯罪构成,判断的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判断的过程就是寻求案件事实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同一性,所以下文也将从这三方面来论证笔者的主张。
第一,作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大前提的犯罪构成本身需要通过法官的价值判断与衡量来达致妥当的理解。[19]
实证主义法学试图将法官限制在严格的逻辑的语法的解释上,然而,“法律发现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包括着创造性的、辩证的,或许还有动议性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20]21-22 这表现在:
首先,犯罪构成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评判,表达了立法者保护某种法益的立法目的,法官解释犯罪构成时应当注意使立法者的保护法益之目的得以实现。如前所述,犯罪构成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而法官作为“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者”,在解释与适用犯罪构成时应当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倾向。法律解释的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方法,无不体现了法官对立法者价值取向的个人理解。“在将实际法律关系的特征与法定构成要件靠拢时,人们总是会做出一些价值取向。人们要对法定构成要件做出解释,特别需要注意立法者所做出的价值取向。”[21]126 “这种解释已不是文字解释,而是实质内容或价值观的解释,已属于实质推理的范围。”[22]346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立法者所意欲保护的法益,法官则必须通过有效的司法活动对行为人进行处罚,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重新实现立法者保护法益的目的。因为,“当法律追求特定的目的(利益保护),法官必须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实现该目的”。[21]116
其次,犯罪构成中规范性构成要素、开放的构成要件的存在,需要法官的价值评判性解释。[19] 犯罪构成中存在不少诸如淫秽、猥亵、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公文证件等需要法律评价、价值评价、文化评价的要素,这些要素的规范性含量惊人,需要法官的个案评价来把握。另外,在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中,也存在“开放的构成要件”(Offene Tatbestaende),即“是指构成要件中对相关犯罪类型不法的描述并不完备,构成要件的规定仅勾画出部分的不法内涵而已,对于未尽部分,需要法官在具体个案中补充确定”。[23]195-196
最后,犯罪构成需要法官把自己想象成立法者,从而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合理解释。犯罪构成是立法者对生活现实中的类型行为的法律定型和价值评价,法官在解释与运用犯罪构成时固然要特别注意立法者的价值倾向与立法目的,然而生活现实是如此无限丰富且变动不居,完全可能出现立法当时没有预料的情况。新的生活现实能否包含在犯罪构成的含义当中,就需要法官作出同时代的解释。“这些文字包含了含义的法律后果,参加立法的人甚至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法官和法学家在其后的解释中会将其揭示出来。因此,人们常说,法规比立法者更聪明。”[21]134 法官解释犯罪构成固然要尊重立法的原意,但当立法原意无法确证或立法原意没有预见到的新生活现实出现或遵循立法原意会得出不公正的个案结论时,法官应把自己想象成立法者,考察立法者在当下而非立法当时会如何处理,从而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犯罪构成解释。“在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时,他应当更多地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出发,想象立法者的目的,从精神上忠实于立法者。”[21]116 法官应该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想象立法者如果面临此种情况会作出怎样的价值衡量与选择。
第二,作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只有经过法官的价值判断才能得以形成。
事实在刑法推理中有三种类型:一是未经剪裁的生活事实,即实际发生的情况;二是案件事实,在生活事实与犯罪构成进行交互解释后产生的可以作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事实;三是犯罪构成事实,经过判断后符合了犯罪构成的事实。兹将建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的过程演示如下:
第一步,证明生活事实的存在,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该步属于事实判断。如,现实生活中乙突然死亡,首先应该确认乙的死亡是自己行为招致还是他人行为招致,如果是他人行为招致则是何人招致,经查明甲的行为招致了乙的死亡。这一过程属于事实判断过程,即确认某一事实是否存在,遵守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是获得真实情况的根本保证。该过程确认的还仅仅是未经剪裁的生活事实,还不足以成为判断小前提的案件事实。
第二步,使生活事实与犯罪构成发生关联、相互靠近,需要法官的价值判断。这一过程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将生活中的事实与规范相拉近,另一方面则将规范与生活的事实相拉近”。[16]188 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张明楷教授正确地指出:“必须以构成要件为指导,围绕着可能适用的构成要件认定案件事实。”[24] 以构成要件为指导认定犯罪事实,反映的是将规范与生活事实拉近的面向。然而,如何选择“可能适用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案件事实呢?笔者认为,法官在选择“可能适用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不可避免的对待定事实有“前理解”,法官总是根据自己对待定事实的前理解来选择法律规范。“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前理解,法律人就必须漫无计划、漫无目的地翻阅法律,看能否找到一点适当的规定。”[16]113 将事实向规范拉近的过程必然有法官的先前理解,否则向何种规范拉近将是一个盲目的过程。例如,在德国刑法有携带武器强盗属于加重强盗的规定,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使用浓硫酸强盗的事实,于是在司法判例和刑法理论上发生了“使用浓硫酸强盗”是不是“使用武器强盗的”争论。这里,“只有当我们把携带硫酸强盗这个现象,‘先前理解’(设证)为加重强盗罪的可能案件,我们才会碰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先前理解’为其他的案件,例如,杀人未遂,那么硫酸是否为‘武器’这点就根本无关紧要”。[16]113 在此点上,笔者又不赞成张明楷教授“不能先确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后寻找可能适用的《刑法》条文”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法官总是对待定事实性质有一个初步的预先判断,否则,不可能有针对性、有方向地寻找可能适用的犯罪构成,进而无法“围绕着可能适用的构成要件认定案件事实”。当然,法官对待定事实性质的预先判断,并非案件定性的最终结论,只是“一种初步的,暂时的方向上的帮助”,[16]113 法官可以也应当根据待定事实与犯罪构成拉近过程的逐渐深入,调整、修改自己的预先判断。事实上,将待定事实与犯罪构成靠拢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步骤往往表现为经证明的生活事实——法官的前理解——根据“前理解”寻找犯罪构成——解释犯罪构成、认定待定事实——若犯罪构成与待定事实无法靠拢,修改自己的预先判断——继续找法……直至犯罪构成与待定事实能相互靠拢。法官的目光来回穿梭于待定事实与犯罪构成,“‘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逐渐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提出法律问题始,而以对此问题作终局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终”,[25]184“这种形成过程,一直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16]133 在生活事实与犯罪构成相互拉近、靠拢时,法官一直在进行创设性加工,法官的价值判断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将生活事实变为案件事实的逻辑中介。
第三步,形成案件事实。通过生活事实与犯罪构成之间的相互拉近、靠拢,借助价值判断的桥梁作用,与犯罪构成立法旨意、价值取向相符的生活事实最终确定为案件事实,而那些不具有犯罪构成立法旨意、价值判断的一般生活事实剔除在法官的视野之外。经过价值评价、价值比较这个中介环节,生活事实中的法律价值(生活事实的法律意义、生活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显现出来,生活事实转换为案件事实,一个与法律规范相适应的小前提得以形成。[18]
第三,大前提的犯罪构成与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同一性通过价值判断予以确认。
“法律判断形成的核心不在于从大前提到小前提的推论,而在于如何处理事实与规范以获得大小前提,这是法律应用的最困难之处。”[26] 找准并妥当地理解了作为大前提的犯罪构成,确认了与犯罪构成相靠拢的案件事实,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最困难之处基本解决,接着只要运用价值判断确认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即可。确认二者的同一性,不仅要求案件事实符合犯罪构成的字面含义,而且要求案件事实与犯罪构成的价值判断相吻合。“通过对认定的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进行价值比较,才能完成大、小前提之间双重同一性的认定,才能完成对法律事实的司法归类。没有价值评价和价值比较这一环节,大、小前提之间的双重同一性无法得到确认,从而无法实现由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转换。”[18]
综述之,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就是法官寻找、获得大、小前提并确认二者之间的同一性的过程,法官的价值判断、价值比较、利益衡量是贯穿始终的逻辑中介,这其间“在法官的身上,实现抽象的正义制度和个人的正义的这种生动活泼结合,因此,法官是法律生活的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在他身上,个人的正义和制度的正义的对立,通过个人的、社会道德的决定而被克服”。[27]186
(三)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
我国学者常常认为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形式的、事实的判断,其原因除不了解我国犯罪构成的属性与法官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思维过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影响。论者经常受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属于形式的事实判断理论的影响,因而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属于形式的事实判断。本部分将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变迁以及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比较的层面,来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应是价值判断。
1.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变迁
20世纪,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体系经历了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历程。[23]121-124
古典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理论史上第一个成形的犯罪阶层体系,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德国学者宾丁(Binding)、贝林格(Beling)、李斯特(Liszt)。[28]9 古典犯罪论体系认为,确立犯罪成立应具有三个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29]7 古典犯罪论体系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行为的主观面与客观面被断然切割,所有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条件,都属于行为构成与违法,而所有主观方面的犯罪因素都属于罪责。[30]121[31]65 其二是在构成要件的理解上,认为构成要件是中性无色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也是中性的、无价值色彩的判断。某种生活事实该当了构成要件,也只能认为有符合某种犯罪类型的事实存在,但并非表示该事实构成犯罪,甚至不能表明该事实是合法还是违法,必须在违法性阶段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判断后,方能确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如,根据宾丁的构成要件理论,“构成要件的意义仅限于对任何一行为外部的描述上”,“根据该观点,构成要件还没有表明违法性的任何内容”。[30]302 贝林格也认为,“构成要件是对犯罪类型的客观描述”,“构成要件里不存在价值判断”,“对构成要件的判断是站在严格中立的立场上的”。[29]178,147
在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下,既然把构成要件视为价值中立的现象,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也只能是事实的判断,排除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故符合构成要件并不能表明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这样的优点是,“在其背后,存在着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的思想。认为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的罪刑法定主义,必然地要求纯客观的、记叙性的构成要件”。[32]51
然而,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具有以下缺陷:其一,既然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是形式的、实质判断,符合构成要件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价值中立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何以能成为违法性的判断对象?既然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不等于是犯罪,甚至不能表明合法或违法,那么,贝林格的犯罪构成体系中违法性判断就应是积极的判断,即对符合了构成要件的行为积极地判断其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必备要素。恰恰相反,贝林格的犯罪构成体系中违法性判断并非积极判断,并非要判明行为要具有违法性还必须具备哪些积极要素,而是消极的判断,只需判断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具有阻却违法性事由,如果没有阻却违法性事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就具有违法性。然而,对一个价值中立、不能说明合法或违法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何以只要没有阻却违法性事由就能积极说明其具有违法性呢?只需消极判断如不具有阻却违法性事由就可断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具有违法性,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恰恰是构成要件已经包括了价值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已经内含了对行为的实质、价值判断。贝林格的犯罪构成体系显然在逻辑上前后矛盾。其二,贝林格的古典犯罪构成体系的出发点虽然是贯彻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机能,但由于把构成要件看作是纯客观的、没有价值的记述,排除了主观的、实质的、价值的要素,构成要件的判断没有实质内容,这样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范围就被扩大,反而有损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如出版淫秽物品犯罪,“淫秽的物品”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但由于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不承认规范的、价值的构成要件要素,出版淫秽物品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出版物品”,这样一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范围就被扩大了许多。所以说,“虽然贝林格(Beling)的出发点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但什么样的构成要件概念更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旨意,还不可一概而论”。[33]96 其三,构成要件既然作为犯罪类型的描述,应该还有个别化机能。但如果构成要件仅限于客观的、形式的、记述的要素,并不能发挥构成要件的个别化机能。如,由于不承认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并无不同,构成要件就没有起到区分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死罪的个别化作用;由于不承认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盗窃自己的物品也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其四,方法论上的缺陷。古典犯罪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初,深受当时风行19世纪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影响。[28]74 经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整个19世纪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不仅盛行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而渗透到一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在法学上,就是力图把法学变得像数学一样精确、可以计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与当时形式的罪刑法定相结合,就产生了古典犯罪论体系。古典犯罪论体系借助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犯罪行为当作一个自然物体,把法官当作机械师,认为法官可以像机械师精确地解剖机械构造那样来解剖犯罪行为,于是犯罪行为的主观面与客观面被机械切割、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被截然分开。但正如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在法学上的方法论局限一样,以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为方法建构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也具有方法论上的缺陷。
贝林格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一经提出后,就有不少质疑。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不致矛盾,贝林格在1930年出版的《构成要件理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贝林格提出了犯罪类型的指导形象(das Leitbild)的概念,作为犯罪类型的指导形象,“既可包括客观的要素,也可包括主观的要素”,“这种指导形象就是法定的构成要件”。[29] 至此,贝林格的构成要件就具有征表违法性的意蕴。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贝林格的构成要件,在作为违法性“征表”的意义上,与违法性是有关系的,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34]27
这种以19世纪自然主义与法学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强调构成要件的客观性、记叙性、价值中立性的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引入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后就崩溃了。新古典犯罪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得到了发现与承认。迈耶(M.E.Mayer)从构成要件的分析中,发现在若干犯罪类型规范中,存在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Normative Tatbestands-Elemente)。迈耶认为,“法定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Erkenntnisgründe)”,“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价值决定的意蕴”。[35]182,183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如盗窃罪中的“他人财物”、淫秽物品犯罪中的“淫秽”等,都需要法官的评价,而不能仅由经验和感觉所认识。迈耶把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称作是“不真正的构成要件要素”,认为它们也属于违法性要素。[35]182,183 麦兹格(Mezger)进一步指出“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有效根据(Geltungsgrund)和实体根据(Realgrund)”。[36]182 在麦兹格看来,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可详细地分为三类:一是需要经验知识评价的因素(Elemente Kognitiver Beurteilung),比如欺诈、誓言、侮辱、危险行为等;二是需要法律评价的因素(Elemente mit Rechtlicher Bewertung),比如监护、公务员、公文证件等;三是需要文化评价的因素(Elemente mit Kultureller Bewertung),比如虐待、卑鄙行为、猥亵行为等。[35]191 另一方面,主观构成要件要素(Subjektive Tatbestands-Elemente)由德国学者黑格勒(Hegler)首倡,后经由迈耶、麦兹格发扬光大。[37]33 如,麦兹格将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分为三类:目的犯(Absichtsdelikte)中的主观目的、倾向犯(Tendenzdelikte)中的内心倾向(如猥亵行为的猥亵倾向)、表现犯(Ausdrucksdelikte)中的内心表现。[36]172-173
由贝林格的中性无色的构成要件到迈耶的作为违法性认识根据的构成要件再到麦兹格的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实体根据和有效根据,可以看出,与古典犯罪阶层体系相比,新古典犯罪阶层体系中的构成要件“不再是无价值判断色彩的描述而已,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判断成分”,“构成要件要素从无价值判断内涵,改变成为具有价值判断的成分”,[37]36 构成要件在整个行为评价结构中分量不断加重,价值评价意蕴不断增强。新古典犯罪论体系虽然承认了表现犯、倾向犯、目的犯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但对故意与过失在构成要件的地位并未论及。或者说,在表现犯、倾向犯、目的犯这些特殊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之外,是否还存在作为一般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与过失呢?这个问题是由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完成的。
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是在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吸收目的行为论的观点而形成的。目的行为论的基本构想是威尔策尔(Welzel)提出来的。威尔策尔认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关系并非“裸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有目的意义的关系”。[38]718 根据该观点,一个杀人行为,只有在行为人有意识和有意志地向这个目标前进时,也就是故意杀人时,才能存在。威尔策尔进一步认为,“完全分割主观构成要件与客观构成要件是不可能的,客观构成要件依赖于主观的运作定律或至少与主观的运作定律有关”。[38]720 最终,“目的行为理论得出了一个体系性的结论:故意,虽在古典体系和新古典体系中被理解为罪责形式,并且人们在理解不法意识时也把它作为必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在一个归结为因果控制的形式中,就已经作为行为构成的构成部分表现出来了”。[23]122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与目的行为论的结合就表现在,人们虽然拒绝把目的行为论作为行为理论,但接受了目的行为论的最重要的体系性结论:主观构成要件与客观构成要件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故意应转移到主观性行为构成。这样就形成了新古典犯罪论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即在承认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表现犯、倾向犯、目的犯等特殊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新古典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把故意、过失作为一般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加以承认;与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不同,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把犯罪阶层体系细分为故意犯阶层体系与过失犯阶层体系。
至此,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完成了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暨目的综合论体系的演变。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古典犯罪论体系那里,构成要件只是客观的、记叙的、价值无涉的要素,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也是中性无色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事实并不能表明合法或违法,还需进行第二步、第三步的判断。可见,古典犯罪论体系力图清楚切割行为的事实面与价值面、客观面与主观面,试图建立起由事实判断至价值判断、由客观至主观、由行为至行为人的清晰定罪过程。在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中,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特殊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发现,使得构成要件具有相当程度的实质的价值判断内涵,构成要件符合性成为了违法性判断的认识根据与存在根据,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与违法性判断变得难以区分,不可截然分开。在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那里,构成要件不但包括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特殊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连原属于责任条件的故意与过失也成为故意犯与过失犯的一般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以至于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与有责性判断也如此紧密相联。
在当代的德、日,尽管还存在着构成要件的违法类型说与违法有责类型说的争论、二阶层说与三阶层说、四阶层说的不同,但这些都是在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新古典暨目的论的综合体系框架内的纷争,后二者成为当前最有影响的犯罪论体系。毋庸置疑,主张构成要件中性无色、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纯属事实判断的古典阶层体系已经被摒弃,现代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不断添加构成要件的内涵。“构成要件在评价结构中的分量不断增加,已经从贝林格认定的类型化规定,从形式意义转变成实质内涵,构成要件不再只是揭露出犯罪类型的形态,更揭示行为类型的不法内涵。构成要件已成为规范评价的类型化状态。”[37]42 可见,构成要件已经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描述,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也不可能是独立于违法性判断之外的事实判断,事实上二者如此紧密难于分割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它们合并成一部分——不法构成要件。
2.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
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体系包括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在结构上,我国犯罪论体系有异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前者是平面式、一次性的综合评价,后者是递进式、逐层深入的评价。在内容上,我国犯罪构成包括了相当于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主要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学者经常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在同等含义上使用,但是我们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同于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当中的构成要件。我国犯罪构成及其要件是认定犯罪唯一的规格和标准,行为符合了犯罪构成要件就成立犯罪,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其他任何标准;而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只是认定犯罪的条件之一,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之后通常还要进行违法性、有责性判断。
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常受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理论影响,往往认为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只是形式的事实判断。这一认识存在以下两点误区:第一,认为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就是形式的、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第二,将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混同于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关于第一点,上文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的变迁已充分说明,把构成要件看作是形式的、客观的事实描述的古典阶层体系早已崩溃,当前起主要影响的新古典阶层体系、新古典既目的论综合体系无不重视构成要件的价值意蕴,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已与违法性判断难以截然区分、甚至被一体化。关于第二点,上文已述,我国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不同于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如果说在大陆法系古典阶层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看作是形式的、客观的事实判断,导致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增多从而有致过于扩大犯罪圈之虞的话,它还可通过违法性、有责性判断进行补救;而在我国,由于犯罪构成符合性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如果把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看作是不具实质价值内涵的事实判断,则只能导致两种局面:或者犯罪圈被不当扩大,不具有应受处罚性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如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00元的行为也被认定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构成行贿罪);或者在法定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之外,求诸其他标准。
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变迁以及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可看出,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是价值判断的体系,其中构成要件判断的价值意蕴不断增强;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作为认定犯罪的唯一规格,也必然是充满价值判断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学者看到了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但认为我国犯罪构成“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地、一次性地完成”,“缺乏评价的层次性”,所以,应该学习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评价的层次性,“犯罪论从现在的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的构造,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换言之,要确定犯罪是否成立,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从客观到主观、从事实到评价、从形式到实质的顺序进行判断。”[39] 笔者对此并不赞同,理由有三:其一,如前所述,随着构成要件价值意蕴的不断增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已成为“规范评价的类型化状态”,构成要件判断与违法性判断关系已早非贝林格的古典阶层体系那样清晰——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事实上二者关系如此紧密难以截然分清,以至于不少学者提出将二者合一。其二,即使是贝林格的古典体系,其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在法律推理方法上也不可能是纯事实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复合过程。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虽然属于三段论演绎推理,大前提是法定构成要件,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然后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符合或不符合的结论。然而,在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之前,重要的是找准大、小前提,即准确找出作为大前提的法定构成要件并妥当地解释,认定案件事实。如前所述,找法与认定案件事实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法官根据自己对待决事实的前理解来寻找规范,然后根据自己对规范的前理解来理解生活事实的意义,之后或者调整自己对待决事实的前理解寻找新的规范,或者调整自己对规范的前理解以使所找的规范能够涵摄待决事实,直至大、小前提确定。整个这一循环往复的寻找规范与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都是通过法官的价值判断完成。因而,从法律推理方法上讲,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不可能纯属事实判断,而是表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复合特性。其三,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并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无层次性。事实上,建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小前提的第一步一对生活事实的证明就属于事实判断。一旦生活事实被证明,接下来的将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互拉近、靠拢,形成大、小前提并确认二者同一性的过程就是价值判断。可见,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并非周光权教授所说的无层次性,而是先运用事实判断证明生活事实存在,再运用价值判断使生活事实与规范相互靠拢。
(四)小结
论述至此,结论呼之欲出: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因而,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
三、余论:价值判断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进一步言之,价值判断不仅是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而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刑法问题集中体现在行为定性和刑罚裁量。在行为定性阶段,除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以价值判断为核心外,实行行为的认定、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判断、犯罪停止形态辨析、共犯与正犯的区分、一罪与数罪的辨别,等等,都端赖法官的价值判断。在刑罚裁量阶段,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质上就要求法官首先对行为之“罪”与行为人之“危险”做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然后运用价值判断裁量一个相称的刑罚。诸多刑罚制度端赖法官价值判断才能适用。如,法定的“可以型”量刑情节要求法官根据案情做出“可以还是不可以”的从宽量刑,多功能的量刑情节要求法官选择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裁量缓刑要求法官首先判断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适用死缓要求法官判断被判死刑的被告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裁定假释也需要法官断定有条件的提前释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切都是法官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目的选择的过程。
因而,可以说价值判断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法官的利益衡量、目的考量与价值评价贯穿刑法问题始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国刑法应确立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12]95-152[19][40] 价值判断又具有主体特性,不同主体价值判断的结论可能各异,法官的价值判断确有随意性而致侵犯人权的危险,这也是为何实证主义法学力图把价值判断排除在法学之外的原因。实际上,价值判断应否在刑法问题居核心地位与如何保障合理的刑法价值判断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事实证明,仅因价值判断的主体特性而试图将价值判断排除在法学之外既无可能,也因噎废食。关键并非价值判断在刑法适用中能否避免,乃是如何保障刑法价值判断的合理实现,而此问题容笔者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2007-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