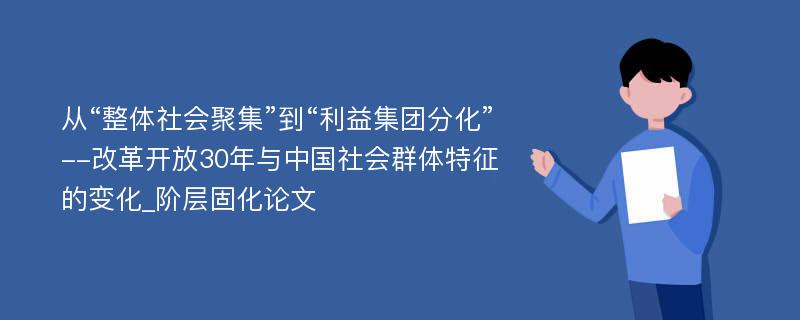
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碎片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笔者曾经有过不少分析,比如提出了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贫富差距的变化等等。然而,有一个方面,以往的文章分析得不充分,这就是: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特征的变化,从改革以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演变为今天的“碎片化”的利益群体。
什么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呢?我们知道,在社会分层的分析模式上,一直有分歧,有争论,其中,一派主张采取巨大的社会群体的分析模式,另一派主张采取分解成小的群体的分析模式。[1]前一派的分析对象是巨大阵营的社会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比如阶级、阶层阵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后一派则主张应该将这些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分解,分解成小的群体来分析,比如小的职业群体,木匠、瓦工、工程师、医生、经理、教授等等。前一派的观点认为,只有“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才可以解释社会上重大的利益冲突,解释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比如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著作中,马克思剖析了法国社会发生的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剖析了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马克思的分析模式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模式,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当时法国社会的整体聚合体有: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等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也是延续了马克思的这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模式。后一派主张小群体分析模式的则认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层面上,人与人真实的社会互动是在小的群体里发生的,人们的实际组织也是小的职业群体,在人们为利益而冲突的现实中,并不能找到“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阶级的痕迹,而是各种小的“社团”在活生生地发挥作用。这一派的理论代表如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索伦森(Jesper B.Sorensen)等。
笔者认为,两派分歧的关键还不是分析模式,而是分析的对象,即作为实体的社会群体、社会上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究竟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还是分化成了小的群体,哪一种是真实的存在。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真正地联合成了社会的聚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组织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就是证明。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时候,发动了广大农民,从1924年到1949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规模之浩大为历史罕见,这些大规模的冲突当然也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真实体现。而对于西方社会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确实找不到巨大的社会阶级的痕迹。所以,出现小群体的分析模式也是符合西方社会的现状的。
问题是,改革以前我国社会群体的真实的构成模式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其特征是属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为什么说改革以前中国分层特征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呢?笔者试陈述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与中国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中,阶级对立是十分明显的。冲突的双方都形成巨大的阶级阵营,比如在土地问题上形成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正是这三次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结果,所以,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激烈冲突的各个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延续。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以及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冲突的继续。
第二,在财产分层的阶级被打碎以后,我国建立的是身份制度,而这种身份制度形成的是巨大的身份群体。身份群体之间界限十分明显,身份群体之间流动十分困难,于是,巨型的社会聚合体就更加固化。中国当时的四大社会聚合体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虽然在这四大社会聚合体内部也有差异,比如,国有企业工人与集体企业工人就有差异,但总的体制还是统一化,企业、单位的经济类型比较少或比较单一,再加上统一化的管理模式,以及统一化的收入分配体系等,都强化了这些社会聚合体。此外,当时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也是强化这些巨大的社会聚合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也与当时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这种巨大的聚合体之间的冲突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实践,都在强化这种整体聚合体,比如:划阶级成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及四清运动等等。
第四,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与当时的社会总动员的模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国家对于资源的全面配置,国家采取统一化的、集中的政策干预资源的配置,并且通过多种手段对于收入分配进行全面的干预,由此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当然也就具有了很强的一致性特征。换言之,是国家统一的或“整体划一”的政策,塑造了“整体型社会聚合体”。
那么,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改革前,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促成了具有强烈政治特征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而“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形成后更促生了各种各样冲突性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派性斗争、“两派冲突”,就是最典型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与重大社会冲突互为因果的例证。“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企业、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医院等等,都分裂为两大派,而这些分散在各个单位的两大派,经过各种联合又形成了更大的聚合体。两派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甚至在1967年至1968年的一段时间,酿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所以,笔者认为,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特征,与政治运动、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为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应该在政策导向上避免这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形成或出现。这也是对于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方面的经验教训的一点总结。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以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逐渐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碎片化”为特征的社会群体。所谓“社会群体利益碎片化”是指,群体内部的利益更为分化和个体化了。笔者所说的“利益碎片化”是针对改革以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而言的。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群体模式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而改革以后,这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出现了瓦解的趋势,社会群体内部分化、细小化、原子化、个体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因为,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塑造“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社会原因,改革以后都逐渐消失了,比如,上文所说的革命战争的原因、身份制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计划经济原因等都不复存在。既然资源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整体性配置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用市场配置的方式,那么,作为获得资源的社会群体,也就更少具有整体的特征。市场是倡导个体自由竞争的,其结果自然是导致了利益的碎片化。
上文已经说过,“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是比较容易引发整体利益冲突的,改革以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面内战”,也再次证明,“大型社会聚合体”的社会结构,容易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与此相反,“碎片化”的社会群体则将利益分解、分散,虽然个体化的冲突会出现得更为频繁,但是,却将冲突限定在个体的、碎片的、分散的状态下,大规模的、整体的冲突失去了社会基础。所以,从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阶级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的特点,反而起到了阻止大规模、整体型社会冲突发生的作用,发挥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从现实的社会状况看,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虽然农村农民为占地、征地、土地纠纷,城乡工人为工资、劳动福利、就业条件,城市居民为拆迁、住房等等,发生的矛盾冲突事件增多,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局部的、小群体的、个体的,恰恰是印证了利益碎片化的趋势。
笔者在过去的分析中曾经指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分化开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积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不尽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当然是不好的,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们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比如,过去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就业于按照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国营集体企业中,那时候涨工资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涨工资的命令。如今绝大多数就业者就业于各种类型的公司和企业之中,涨工资是千百万公司和企业自己的事情,大家不用“齐步走”,不会产生“共振”。就业者的利益被众多类型的公司、企业所分化。
利益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从过去的那种仅仅追求整体利益,转变为今天的追求个体利益。每个人都追求个体利益,这样追求利益的方向就非常不一致,这样就形成不了整体的社会运动。社会就不会产生整体的冲突。
最近的变化表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在此,笔者试剖析利益分化的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改革以后,经济利益确实分化了,产生了贫穷与富裕的巨大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是环环相交叉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身份制关系。比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他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不是市场型的经济地位差异的区分,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指标愈来愈突出。但是,新的阶层产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身份制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实际情况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与传统的身份制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阶层与身份并存,在阶层内部会有很多身份群体。比如,近30年来,我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膨胀。然而,由于原有的身份制的存在,我国产业工人内部有众多不同的身份群体,其内部的差异性一点不小于外部的差异性。目前在我国工人的内部,既有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也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家庭企业劳动的工人。即使在同一个单位里面,也存在着几种不同身份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总人数虽然十分巨大,但是,却分化为很多小的利益群体。
第二,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公安部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的实验,但是,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和控制还是很严格的。新近的改革特点是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区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上海、广州、北京等特大城市曾推出了“蓝印户籍”,“A、B、C户籍”等区分多种户籍的政策。因此,其结果是,在同一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户籍利益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的小的利益群体。除了户籍以外,还有地域的巨大差别。近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反而是差异更大了,比如,到2005年底,北京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3.91倍,而上海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39倍。所以,不同区域的农民收入有巨大差别,虽然都叫农民,但其内部的分化很严重。从大的地域上看,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或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省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都有明显的经济差异,虽然都是农民,但在不同区域经济地位会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差异远远大于阶级阶层的差异。从微观的层次上看,群体内部分化的特征更为突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如,新近对于城市“新白领”群体的研究发现,城市新白领内部是一个分化的群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2]又如,对于乡镇企业工人的研究发现,工人分化为很多小的地域群体、老乡群体的现象非常普遍。[3]
第三,体制的差异与阶级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我国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变迁和体制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体制改革大步推进,迄今为止,由传统的国有、集体体制覆盖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新产生的体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等。这些还只是一些大的分类,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要复杂得多,比如:承包的、转包的、出租的、租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交管理费式的,除了登记了的正式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没有登记的非正式单位,其管理方式更是花样繁多,不同体制的单位,其工资制度、收入体系、福利体系均有巨大差别。中国目前的收入构成、工资体系、福利体系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体制的“碎片化”与阶级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就更是形成了利益的碎片化。比如,失业本来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但是,在我国当前却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利益“碎片化”的群体,很难说有什么边界。且不说笔者以往的调研已经证明失业与“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的群体交织在一起,[4]仅就失去工作这种现象看,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比如分为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等情况,再加上不同单位对待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下岗者待遇很不一致,失业者的利益也碎片化了。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利益碎片化的现象呢?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5]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正如达伦多夫所讲的减缓的方面。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或断裂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我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有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
总之,笔者用“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现象解释改革前的重大冲突,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社会冲突,而同样的道理,改革后的大的聚合体的分解,社会群体的碎片化和群体利益的碎片化,恰恰可以解释今天虽然冲突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是,并没有导致全局风险的重大社会冲突的发生。这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