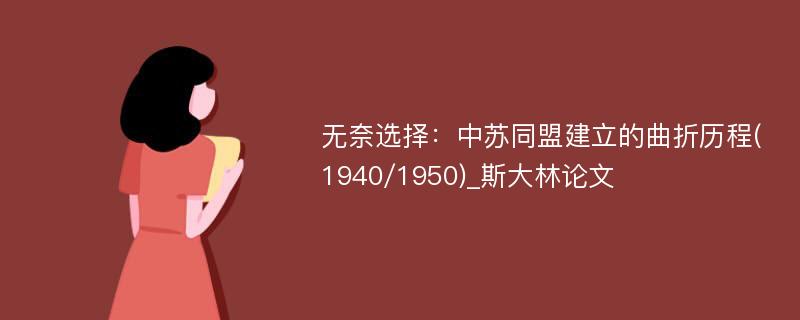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曲折论文,历程论文,中苏论文,无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中苏同盟如何走向破裂一样,在冷战国际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中,中苏同盟的形成也是各国学者之间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关于中苏何时开始结成同盟,牛军认为,1945年10月苏联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并与中共形成一种战略关系,这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①文安立提出,苏联人于1946年4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②盛慕真则认为,中苏结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数十年中,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逻辑延伸”③。柯伟林赞同这一说法,并指出中苏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是预先注定的,是由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中共监护人的地位所决定的。④关于中苏结盟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是主导因素,认为中共和苏联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是两者走到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作为对立因素存在的美国也起了很大的反面推动作用。⑤至于斯大林(J.Stalin)与中共政权得以建立的关系,多数学者都认为苏联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俄国学者认定,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只是由于苏联的援助才有可能。⑥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是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中共的利益,中共之所以能从当时复杂艰辛的局势中闯出来,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和智慧。⑦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对苏共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中共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的主要追求是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本文则着重讨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总体评述。
一、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F.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⑧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1930-1940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却比较紧张。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⑨这些史事都是经过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⑩这种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11)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12)。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Paniushkin)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V.Chuikov)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13)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14)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在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15)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Service)见面,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16)。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17)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8)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19)当时,另一篇美国专家福尔曼(H.Forman)发自中国的报告还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A.Lincoln)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20)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21)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Stilwell)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22)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23)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Gauss)被迫辞职。(24)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P.Hurley)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25)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颇有些无奈地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26)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27)。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28)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29)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30)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1)。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2)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33)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34)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令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35)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扰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其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36)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G.Marshall)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H.Truman)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37)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38)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来愈严重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39)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从东北撤军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资料表明,在1949年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为主,目的在于帮助中共取得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的控制。军事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苏军撤退时赠送或遗留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40)第二,通过朝鲜供应或交换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以缴获的日军物资为主)。(41)此外,由中共掌握的旅大地区各工厂在苏联占领当局默许和鼓励下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自然也可以算是苏联提供的间接援助。(42)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此期中共曾得到过苏制的武器弹药。(43)苏联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公开和积极得多,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贸易往来为中共提供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从1946年底至1947年底,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亿卢布,翻了一番。(44)第二,在旅大地区向中共移交了大批工厂,还帮助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对中共政权的物资供应。(45)第三,派遣大批专家协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帮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建立铁道兵部队,并以贷款或易货方式为中共提供铁路物资8760万卢布。1948年底中长铁路全线通车。(46)此外,战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现金援助,目前看到的材料至少有1946年的5万美金。(47)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乃至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48)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三、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因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因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J.Tito);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因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美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49)美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50)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51)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52)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53)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54)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A.Zhdanov)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55)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56)
没料想,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国民党要求美、英、法、苏四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57)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58)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59)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于12日给斯大林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60)
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传说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61)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62)无论如何,把这一时期有关的档案文献联系起来看,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N.Roshchin)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63)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64)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他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苏联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65)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66)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缘于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的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67)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说法。(68)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做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个,最多时也没超过7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不算朝鲜战争)。(69)这充分表明中国此时在苏联国际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A.Vyshinskii)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I.Kovalev)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70)。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A.Mikoyan)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71)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72)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73)其实,全面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74)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75)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76)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Stuart),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77)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78)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但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双方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惟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
四、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在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就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出对斯大林的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却不敢掉以轻心。随着政权易手,中共在这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实际了。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的多。”(79)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政府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80)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81)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做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重新起草的完全对立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82)
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北的主权,那么就无法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也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迫斯大林做出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83)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得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则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上。(84)争论的结果是,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85)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刚刚确定的对华新政策。(86)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87)。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是可靠的同盟,就可以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88)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重要的措施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89)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90)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做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91)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92)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93)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梳理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所以,中苏结盟的过程并非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认知和认可,经历了重重曲折和不断选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其核心在于是否忠于莫斯科)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更加关键和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宣布“一边倒”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两国领导人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反过来,中苏同盟的建立则预示着冷战格局从欧洲扩展到亚洲。
(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1944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1949年已不复存在。
(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所以,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隐患。
注释:
①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 2期,第183—185页。
②[挪]文安立(O.Westad)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③Michael 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86.
④William C.Kirby,"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No.188(2006),p.890.
⑤比较突出的看法参见如下论著:Michael 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文安立:《冷战与革命》;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外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Ъорисов O.Ъ.Cоветский C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о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M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дъ,1977; Ледовский A.M.Переговоры И.B.Стaлина с Mao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 1,c.23—47.
⑦参见[德]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Michael H.Hunt,The C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Foreign Policy(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⑧关于战时中苏关系的研究,参见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59—80页;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⑨参见Панцов A.B.Как Cталин помоr 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6,№2,c.75—87;A.V.Pantsov,"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Issues & Studies,No.41,No.3(September 2005),pp.181—207。
⑩Панцо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r Mao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6,№2,c.84—85.
(11)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均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57页。关于西安事变中苏联与中共关系的研究,详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13)《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ABПP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oп.25,п.200,д.8,д.28—29。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256页。
(15)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的详细情况参阅[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袁武振:《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1999年3月;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6页。
(16)[美]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17)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of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August 23,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4,Vol.6,China(Washington D.C.:GPO,1967),pp.604—614;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18—229页。
(18)关于毛泽东向苏联通报的情况,见Димиитров Г.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Климент Оxридски",1997,c.416—417。
(1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March 13,1945,FRUS,1945,Vol.7,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69),pp.273—278;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党史通讯》第20—21期(1983年),第14—18、19—22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29—230、231—232页。
(20)转引自Ъажaнов E.П.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уроки прошл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2,c.7。
(21)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62页。
(22)[美]约瑟夫·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卡特:《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54—159页。
(23)参见[美]巴巴拉·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518页。
(24)卡特:《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66—168页。
(25)详见[美]约瑟夫·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0—317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1—4页。尽管谢伟思在1945年4月躲过了一劫,但1950年3月终于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被捕入狱。关于这批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包括谢伟思、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雷蒙德·卢登等人,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美]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27)转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28)笔者关于“联合政府”政策的研究,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6期。
(29)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7,1945,FRUS,1945,Vol.7,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ABПРΦ,ф.0100,оп.33,п.244,д.14,л.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A.M.,Мировицкая P.A.(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ПИМ,2000,c.37—40。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4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137、190、238—239。
(31)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ABПРΦ,ф.0100,оп.33,п.244,д.1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ⅣК.2,c.68—71。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3页。
(33)《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8—9页。
(34)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35)详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36)关于苏军占领东北时期对华政策左右摇摆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37)章文晋:《周恩来和马歇尔在1946年》,《中华英烈》1988年第2期,第13页;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9(Washington,D.C.:GPO,1972),pp.148—151。章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
(38)关于中共在马歇尔调停时期的立场和政策分析,中国学者已有非常深入和到位的研究,详见章百家《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牛军《论马歇尔调处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9)苏联红军撤离中国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毛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4—135页;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72页。
(40)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Ъорисов О.Ъ.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к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c.138、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41)到1947年6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又有52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1986年3月,第197—200、202—204页。
(42)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43)这一点,也为当时美国的情报所证实。《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1947年6月25日)、《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44)缅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0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Ⅳ,К.2,c.344—347。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45)详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1995年编印,未刊;笔者1996年5月采访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记录,2002年10月26日采访欧阳惠(时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记录,2008年8月1日采访王伟(曾任大连港务局书记)记录。
(46)缅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0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344—347。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3—64页。
(47)见周恩来亲笔签字的收条(1946年10月1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38页。
(48)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即将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讲了这番话。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c Mao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c.79.
(49)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第239—247页。
(50)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13,1948,NSC 34,DDRS,CK3100371087—CK3100371119.
(51)《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330页。
(52)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攀比上升的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第273—283页。
(53)《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6页。
(54)参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9—64页。
(55)详细论证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56)毛泽东一再求见斯大林而未果的详细过程,见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7)希望和谈是国民党方面的一致意见,但主张“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是李宗仁的主意,而蒋介石以为,外交部照会四国政府,表明力主结束内战,希望他们从旁协助,“但不要求其斡旋或调解,以免干涉我国内政”。见李宗仁呈蒋中正建议书,台北,“国史馆”藏,革命文献·国共和谈,002/020400/030/00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224页。
(5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908页。
(59)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0页;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1949年1月10日),AПР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9,оп.1,д.31,л.54—5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11—14。
(60)以上往来电文见АПРΦ,ф.39,оп.1,д.31,л.61—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15—25。
(61)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c Mao Цзэдуном,в январе 194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c.132—140;Рахманин О.ъ.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В.Сталина и Mao Цзэдун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c.87—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530—532.
(62)笔者期待着中共中央档案的开放,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63)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4、26,March 8,1948,FRUS,1948,Vol.7,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3),pp.112,117—118,133—136;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12.1/002,第60—63页;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0,December 1,1948,FRUS,1948,Vol.7,pp.558—560,627。
(64)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第384—387页。
(65)罗申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会谈备忘录(1948年12月9日);罗申与印度武官托卡尔会谈备忘录(1948年12月29日),АВПРΦ,ф.0100,оп.41,п.276,д.19,л.82—84、80—8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1,c.488—489、494—495。
(66)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1948年12月27日),АВПРΦ,ф.0100,оп.42,п.296,д.117,л.7—23。
(67)1949年2月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莫斯科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被捕,她在《明天的中国》一书中把毛描述为亚洲的圣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称为亚洲的圣经。[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研究报告(1949年12月2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第560—568页]可以认为,斯大林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在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68)顺便说一句,关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69)Адибеков Г.М.,Андерсон К.М.,Роговая Л.А.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Каталог,Тoм Ш,1940-195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1946-1947年莫斯科对中国问题并没有特别关注的情形,从当时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来:“显而易见,我们驻满洲军方和其他代表并没有把所有情况报告莫斯科,莫斯科也没有经常向大使馆及时通报情况,而只限于中央简要指示里所列举的情报。”“苏联大使馆对情况的掌握很有限,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Крутиков К.А.В гоминьдановском Нанкине,1946-1948 год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4,№2,c.138、147.
(70)见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71)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备忘录(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ΑПΡΦ,ф.39,оп.1,д.39,л.1—95,Ρ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33—93。以下所引西柏坡会谈内容均出自这些文件,不再出注。
(72)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Φ,ф.3,оп.65,д.606,л.1—17//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c.109。遗憾的是俄国没有公布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不过可以认为,米高扬所说都是斯大林授意或同意的内容。
(73)米高扬报告列举的主要是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内容,见Проблеемы дaльнего восгока,1995,№2,c.105—107。学者对此的反应见Goncharov,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pp.41—43;Кулик Ъ.Т.Советско-китйский рaскод: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PAH,2000,c.73—74;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269页。
(7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42、136—137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75)详见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1949年2月6日),АПPΦ,ф.3,оп.65,д.444,л.32—34;库梅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7日),АПРΦ,ф.3,оп.65,д.363,л.12,Р 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88—89、147、548。
(76)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Φ,ф.45,оп.1,д.329,л.1—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148—151。访问过程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19—424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7—221页。
(77)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7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8—1479页。
(79)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2卷,第425—427页。
(80)中国领导人对这—任命颇感失望的表现,见[俄]齐赫文斯基著,陈之骅等译《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81)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9年11月10日),АВПРΦ,ф.07,оп.22,п.96,д.220,л.52—5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T.V,К.2,c.218—219;АВПРΦ,ф.0100,оп.42a,п.288,д.19,л.81—85。转引自Кулик ъ.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c.75。
(82)笔者关于中苏条约谈判详细过程的论述,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83)这就难怪蒋介石会私下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中共,甚至不在于苏俄,而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月24、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8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9,1949,FRUS,1949,Vol.9,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p.463—467.
(85)Reel 2,NSC 48/2:The Position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Paul Kesaris(ed.),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1977(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0),pp.111—119.
(86)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4、19—34页。
(87)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p.104。
(88)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30页。
(89)早在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朝鲜半岛南方的几个港口具有战略价值,应该置于苏军的掌握之中。外交部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1945年9月)、外交部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1945年9月),АВПРΦ,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8,1993,pp.9—11。
(90)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158页。
(91)NSC68,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April 14,1950,FRU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77,pp.237—292.有关NSC68文件的全面分析,见周桂银《美国全球遏制战略:NSC68决策分析》,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102页;Ernest R.May(ed.),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Interpreting NSC 68(Boston,New York:Bedford Books of St.Martin’s Press,199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3—247页。
(92)详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93)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159—208页。
标签:斯大林论文; 莫斯科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苏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同盟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蒋介石论文; 军事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