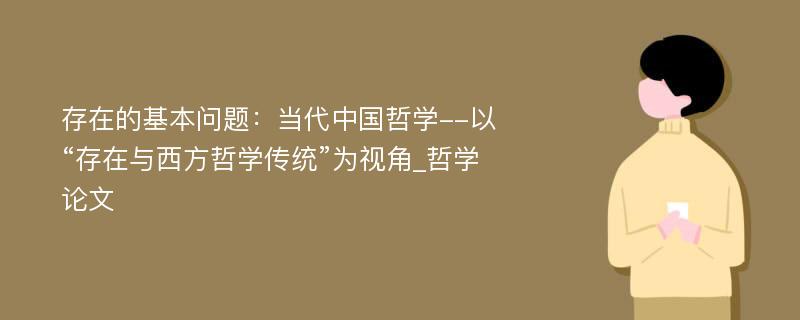
BEING: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从《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弊病是,人文学者缺乏必要的学术敏感,没有形成正常的、理性的学术争鸣的氛围;虽然出版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共同讨论的问题却越来越少。近年来,哲学界围绕Being的意义问题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是一个例证。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Being的意义以及与其相应的中文概念,发表了很多精彩的意见,如果相互讨论切磋,本来可以形成一个哲学热点。但事实却非如此,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很少注意别人的意见,更没有分辨自己的意见与别人意见的同或异,深入讨论产生这些同或异的理由是什么。孤立地看,他们意见中的大多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刊之论;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意见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独白,缺乏对话,没有彼此间的参照。对于同样的主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但却没有展开学术争论,形成学术上的热点问题,这种现象在国外学术界是罕见的。对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对学术发展是否有利,值得我们加以检讨。
为了引起学术界对Being的意义问题的共同关注,宋继杰博士把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和译文集辑成书,分上下两卷,以《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以下简称“本论文集”)为题,于2002年10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以为本书可以促进哲学界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哲学界对此书的反应甚是冷漠,关于Being的意义的文章依然在没有参照别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大都收入此书)的情况下发表。为了打破学术麻木的僵局,我愿以书评的形式,大力宣扬Being的意义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
一
Being的意义问题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海德格尔说,西方哲学的传统是形而上学的传统,而形而上学正是以Being为研究对象的。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形而上学的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规定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内涵就是Being的意义的辨析、阐述和应用、扩展。这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纯粹的、最核心的部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其他部分已经或正在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如自然哲学分化成物理学,认识论正在向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向分化。惟独形而上学坚守西方哲学的核心地位,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却是常变常新。即使到现代,形而上学也没有丧失活力。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存在论通过用Existence来阐发Being的意义,建构了一种新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称自己的存在哲学为“基础本体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副标题是“现象学的本体论”,最能表现存在主义和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因为“本体论”(ontology)是对Being(on)的研究,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只是这些哲学家要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而不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来标榜自己的学说而已。分析哲学也有类似的情况,充满着关于Being的意义的分析,但却避免用“形而上学”的字眼。分析哲学在其早期虽然表现出强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关于Being的意义的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与逻辑思维和语言用法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用语义实在论和逻辑本体论代替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没有消解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是多元的,“道”、“天”、“心”、“性”、“理”、“气”等可以并立。但形而上学不满足于多元并立,而是要确定一个最高的原则或原因;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以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为核心,都可以把另外的范畴串起来;比如,可以把中国的形而上学解释为“道学”,“天人之论”,也可以解释为“心性之学”,还可以解释为“理学”和“气论”,等等。这些解释都有根据,因为中国哲学基本范畴的多元性决定了中国形而上学的多元形态。但西方的形而上学形态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Being。
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一元的,而中国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多元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哲学中是否有一个与Being相对应的概念?如果有的话,这一概念是什么?这首先是翻译者遇到的问题。日本学者最早用汉字“有”翻译西文的Being;后来西方的翻译者把《老子》中的“有”和“无”分别译为being和non-being。经过中西文的“双向格义”,与西文Being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概念被确定为“有”。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普遍用“有”来翻译和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Being;港台的中国学者至今仍然这样做。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人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人们对Being的翻译和理解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悄悄的”意思是没有经过学术争论的、想当然的变化。这一变化也是从翻译开始的。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Being(德文Sein)译为“存在”。这种翻译具有权威性的依据,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论述:“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being)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exist)。”(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0页。)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又明确地把“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规定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说的“存在”,依然是Being。在此问题上,主张存在为第一性的是唯物论,主张思维为第一性的是唯心论。在前苏联理论家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定义的指导下,出于把西方哲学史当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脚注的需要,把Being理解为“存在”,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人们甚至没有提出问题:为什么在一切西方哲学的著作中,Being的意义都是“存在”(existence)?用“存在”代替“有”的根据和理由究竟何在?
从“有”到“存在”的转变的一个例证是对黑格尔著作的翻译。贺麟先生在《小逻辑》1981年新版前言中说:“过去我一直把Sein译成‘有’,把Existenz译成‘存在’,显然不够恰当。”(注: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前言第ⅩⅩ页。)译者没有交代过去的译法为什么“显然不够恰当”的理由,但却意识到这一改变所造成的问题。首先,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Sein和Existenz是两个不同的范畴:Sein是大范畴,构成逻辑学第一部分的内容,Existenz是第一部分中的一个小范畴,是构成Sein的一个环节。如果把Sein译为“存在”,那么它与Existenz如何相区别呢?贺先生主张把Existenz译为“实存”。但接着又产生了一个问题:Existentialism是否还能像通常那
样,被译为“实存主义”呢?翻译可以有各种变通方法,但问题的关键是,把Existenz翻译为“实存”能否表达原文的哲学含义?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Existenz指一般事物的存在,并没有“实”的意思,中文中的“实存”指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而Existenz和其他逻辑范畴一样,是超时空的。另外,存在主义所说的Existence虽然有时间的意义,但也不必然地具有“实”的意义;而是与人的体验不可分离的生存过程。
很明显,把《逻辑学》中Sein翻译为“有”,把Existenz翻译为“存在”,既可突出黑格尔所要说的“本质”与“存在”的区别,又可以避免把Existenz翻译为“实存”而造成的种种误解。但是,这个并不复杂的学理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才有机会自由表达。通过对黑格尔著作翻译中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关于“存在”与“有”意义同异的研讨。
除了主张用“存在”和“有”来理解西文的Being的两种主张之外,90年代又出现了第三种主张。这一新主张认为,中国哲学中并没有与西文Being相对应的现成概念,必须用一个新造的中文词汇“是者”,才能准确地表达Being的意义。严格地说,这也不是新主张,早在40年代,陈康先生就指出过:“根本困难乃是on和它的动词einai以及拉丁、英、法、德文里和它们相当的字皆非中文所能译,因为中文中无一词的外延是这样广大的。比如‘有’乃中文里外延最广大的一词,但‘有’不足以翻译on或einai等等。”他的理由是,“有”相当于希腊文echein(即英文having),它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中的一个属性范畴(现译为“所有”或“状态”),只是一个说明on的意义的较为次要的范畴。他建议对此类词采用音译的方法,比如,把Ontologie音译为“翁陀罗己”,将 S
ein音译为“洒殷”。(注:陈康:《论希腊哲学》,汪子嵩、王太庆编,商务印书馆1 9
90年版,第436页注释1。)陈先生的高足汪子嵩、王太庆先生主张,用“是”翻译西文动词to be,用“是者”翻译其名词形式Being。“是”在中文中不是哲学概念,中文中甚至没有“是者”这一词汇。两位先生之所以主张启用这两个术语,是认识到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一个与西方哲学中这一意义极其重要的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只能采用直译的方法;直译所用的术语虽然冷僻,但却忠实地表达了Being的原义。否则,用现有的概念来翻译,虽有“达”或“雅”的通畅,但却没有满足“信”这一翻译的基本要求。如果人们在读到通顺的译文时,觉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家表达的是与我们中国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相似的或相反的道理,那可不是一件妙事。相反,如果我们对表面上看似乎不太通顺的句子多一些思索和理解,那么,冷僻词的使用也未尝没有好处。
王太庆先生在正式发表他的主张之前,曾与笔者有过多次的讨论。我虽然同意引入新的中文词汇翻译和表达西文Being的意义,但不同意用“是者”完全取代“有”和“存在”,而认为三者可以并存,各有各的意义。在Being的意义问题上,这可以说是第四种主张。虽然我与王先生的主张有所不同,但觉得与他的讨论对我观点的形成增益良多,我不能单独发表自己的观点。王先生也有同感。于是,我们俩人于1992年在《学人》第四辑上分别发表了论文,阐述各自的主张和理由。在文章的结尾处,都向对方表示了谢意。但遗憾的是,在收入本论文集时,只保留了王先生对我的谢意,却删去了我对王先生的谢意,这是不公正的。尤其是王先生已经谢世,我更有责任表明他在此问题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包括对我的重要启示。
二
1992年之后,出现了不少关于Being的意义的文章,使我们感到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不但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研究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关注这一问题。但仔细一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中国当代哲学已经不能离开西方哲学这一重要的参照系,对Being这一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中国当代哲学性质和对象的理解。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哲学包括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分别说明Being的意义问题在这三大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用汉语来理解和表达西方哲学的思想。中国人与西方人所研究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媒介的不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思想的转换。西文Being所对应的中文概念究竟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关系到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水平和质量。如果笼统地把Being理解为“存在”,可能会从一开始就产生误解和偏差。比如,巴门尼德残篇之三: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For the same thing is there both to be thought of and to be)(注:英文译文见G.S.Kirk等编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2nd.ed.,Cambridge,1983.),这句话过去被译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被当做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最早命题。这里的关键词组estinte(it is)被译为“存在”;如果把它译为“所是的”,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所思的与所是的是一回事。”“所是的”指系词“是”所能连接的一切判断,“所思的”指思想内容。巴门尼德在这里只不过宣称了“思想内容与判断是同一”的道理。他认为,这是知道系词用法普遍性的人都懂得的自明真理。正是依赖这样一个“共同的、我将再三强调的出发点”(残篇之五),他后来关于“是者”的论证才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如果不是这样,把巴门尼德的论证的前提当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那么,他的思想就被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而且,他没有为这一前提提出任何理由,他的唯心主义是完全武断的,荒谬的。这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漫画式的解释。
对Being的意义理解,也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性质的理解。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是”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西方学者对此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古代汉语中系词的用法不发达,反映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不发达,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以Being为对象的、以逻辑论证为方法的思想体系。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指出:“古汉语的句法接近于符号逻辑,它有一个存在量词‘有’,这避免把‘存在’误读为谓词,并和系词(包括表示等同、关系的特殊系词)区别开来。”虽然“古汉语在主词和形容词的谓词之间不用系词,并且没有一个系词的共同符号”,但却可以用各种单词和词组替代系词的连接作用。(注: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1989,p.412.)葛瑞汉的阐释可以导致两个结论:第一,是否使用“是”作为系词,与是否具有逻辑思维并无必然联系;第二,中国哲学的对象与系词“是”无关,并不能说明中国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的成分,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中西形而上学性质不同、研究对象根本不同,没有可比性。我们现在选择什么中文术语来理解和表达Being,实际上是对这两个结论做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回应。如果把Being理解为中国古代哲学常用概念“有”,或中国现代哲学常用概念“存在”,恰恰表明了中西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共同性和可比性;如果把Being仅仅理解为“是者”,那么很可能因为“是者”不是中国哲学的概念而否认中西形而上学之间的共同性和可比性。]
最后,关于Being的意义的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重要作用。恩格斯把Being等同于存在(existence),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自从托马斯做出esse(to be)与ens(being)的区分之后,ens在经院哲学中几乎就是“存在”的代名词,但直到16世纪,经院哲学家才创造出拉丁文existens表示ens的意思。恩格斯的很多同时代人也把Being的意义等同于存在,特别是费尔巴哈和其后的唯物主义者把Being理解为“物质存在”。恩格斯也是在此意义上理解Being的,并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把Being理解为与思维既相对立,又相同一的一对范畴,由此提出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这是恩格斯对Being意义理解的唯物主义传统和黑格尔主义的背景。但我们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的理论背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来自传统的哲学理论,与本体论的中心范畴Being的意义有着尤其复杂和深刻的联系;这些联系不是“物质存在”这一种意义所能概括的。更重要的是,通过Being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论证的风格,是一个逻辑上自治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但同时也把理论的正确性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马克思的哲学是“说理”的哲学,但哲学的彻底性在于Being这一根本道理。正是依靠彻底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与论敌的争论中不断地被论证、被发展,才能成为我们时代“活的哲学”,而不被僵化为教条。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正在通过对Being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全面揭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性,充分展开马克思著作中的逻辑论证的成分,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的“说理”的哲学,而不只是一些论断和结论的简单拼凑。
三
从本论文集收集的各种观点来看,中国学者对于Being的意义,至少有下列五种观点。
1.Being的一般意义是“存在”;如韩林河的文章“何谓存在”所示。最近,孙周兴更为明确地说:“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把名词的on,Sein,Being译为‘是’,把Ontologie(我们译为‘存在论’)译为‘是论’。可谓用心良苦,但不待说,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汉语本身的非语法特征,比如说,并不能使汉语具备词类的形式转换功能,因而对于增进义理的理解并无多少益处。”(注:孙周兴:《形而上学问题》。)
2.Being的一般意义是“有”;如叶秀山、邓晓芒文章所示。
3.Being的一般意义是“是者”;如王路等人文章所示。另见俞宣孟的著作《本体论研究》。(注: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Being在希腊哲学中的一般意义是“是者”;对Being在全部哲学史中是否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存而不论。如汪子嵩、王太庆文章所示。
5.不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还是在希腊哲学中,Being都没有一般意义;“有”、“存在”、“是者”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译法。
我本人持最后一种观点。我在本论文集中虽然没有看到批评的意见,但却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学友陈嘉映在他的个人论文集《思远道》中,对我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说:“赵敦华先生提出,estin/Sein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意思不同,宜分别译作‘是’、‘有’、‘在’或‘存在’。他对estin/Sein这个词的梳理颇有见地,但最后这个结论,我却不敢苟同。西方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语词,无过于Sein,极大量的讨论都可归结为要厘清这个词的各种含义有哪些内在联系。若依各个哲学家的侧重不同而径以不同的词来翻译,这项任务就消失于无形了。”(注:陈嘉映:《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陈嘉映也承认Being这个词有“各种含义”,我也并没有否认这些含义有“内在联系”。所以,他与我的分歧只是在于,用不同的词来理解和表达Being的各种意义,是否就一定会取消“厘清这个词的各种含义有哪些内在联系”这一哲学的根本任务?这里所说的“各种含义的内在联系”,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Being(on)的“中心意义”,亚里士多德归之为“实体”,但他在厘清“实体”意义时,仍然不得不用不同词和词组来表达,它们分别相当于后来所说的“是者”、“存在”和“本质”。以后的哲学史中极大量的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还是:Being的各种意义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是把“有”和“是者”的意义维系于“存在”,还是把“存在”和“是者”的意义都维系于“有”,或者是把“存在”和“有”的意义都维系于“是者”?这三种主张都各有各的道理。从哲学史上看,存在主义者持第一种主张,本质主义者持第二种主张,而以希腊文的原初意义为依据的人持第三种主张。主张把Being的各种意义归结为某一种“内在联系”,这实际上是要在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学说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我们不主张做这样的选择,这是因为,哲学史上的某一派别关于Being的意义的解释都企图把其他解释统一起来,但统一的结果总是产生进一步的分化,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把其他解释真正统一起来。我们不妨用哲学史上的事实说话。
我们知道,Being的普遍意义来自于“是”动词在印欧语系中的广泛用法,哲学家对Being的思考,是以“是”动词的意义为基础的。据本论文集中的卡恩的文章“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究之回顾”(上卷,第499~509页),在Being成为希腊哲学概念之前,“是”动词已在日常语言中大量使用。据他对最早的希腊典籍《荷马史诗》的统计,“是”动词至少有三种最常见的意义:(1)系词的连接意义,如Sis P;(2)表真的意义,如it is true that p,it is the case that p;(3)指称存在的意义,如there is a S。
巴门尼德第一个把Being作为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和统一原则,他在阐述Being的统一性时实际上是用“是”动词最常见的系词用法来统一其他两种用法。如前所述,系词在判断中的普遍意义被他哲理化,成为“所想的和所是的是一回事”这样一个原则,从此出发,他证明Being是真理之路,即,“是”动词有表真用法;又证明Being是“不变的一”,是在时间上永恒、空间上与自身等同的圆球(sphairon),即,“是”动词有指称存在整体的用法。
巴门尼德把Being的意义统一于系词意义的观点遭到后来智者的反驳。比如,智者高尔吉亚用与巴门尼德同样的方法证明,如果系词也能够指称存在,那么将无物存在;如果系词也能够表真,那么人们将不能认识事物,或无法把对事物的认识表达出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借巴门尼德之口,反驳“是者是一”。他用逻辑推理证明,不管如何说,“是者是一”和它的反面“是者不是一”或“不是者是一”都可以成立。在《智者篇》中,他又说明“是者”与“不是者”的意义是相通的,“按某一方式,不是者是一个东西;另一方面,是者在某一意义上不是一个东西。”(注:《智者篇》,237a。)按照柏拉图的“通种说”,“是者”和“不是者”的意义渗透在“动”与“静”、“同”与“异”的关系之中,贯通了对立的关系,使得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性质能够被事物同时分有。如此看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分有说”是以牺牲巴门尼德所证明的Being的意义的统一性为代价的。
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做了统一Being的意义的又一次努力。他承认Being的意义是多样的,但肯定多样意义中有一中心意义,即实体(ousia)。但ousia不过是希腊文“是”动词的阴性名词形式,其意义仍然离不开“是”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比巴门尼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是”动词为基本的逻辑功能,建立了一个逻辑体系;他于是得以根据“是”动词逻辑功能与“实体”意义之间的对应性,系统地阐述关于“是者”的学说。
“是”动词的逻辑功能有三种,与此相对应,“实体”的意义也有三种。(1)系词“是”在判断中的意义是“属于”,“S是P”的意义是“P属于S”。系词的功能意味着,属性依附于实体,只有实体才是独立的、在先的“是者”,是“是者”的中心意义,而属性则是派生的、次要的“是者”。(2)“S是”表示S是自身,如说“There is S”。在这样的用法里,“是”指称S的存在。这意味着,只能做主词的个别事物专名指称第一实体,而表示种属的通名指称第二实体。(3)定义的形式是“S是Df”。被定义的词与定义的位置却可以互换而意义不变,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与“有理性的动物是人”的意义是等值的。这是因为,“是”在这里表示等同关系。两者之间的等同意味着,定义表达的本质就是实体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形式和本质是第一实体。”(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30b 5。)
比较(2)、(3)两处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先说第一实体是个别事物,后说第一实体是本质。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种关于第一实体的学说,两者是矛盾的。按照我们的分析,这两种说法有不同的逻辑根据,分别与“S是自身”和“S是Df”这两种逻辑形式相对应。这两种逻辑形式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也不能说由此而产生的两种关于第一实体的学说必定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不容否定的是,这里确有矛盾。
首先,我们应该理解,本质、定义和形式对于亚里士多德是同义词,并且,“形式”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词(eidos)。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第一实体是个别事物,那么它究竟是个别事物的存在,还是它的本质?希腊文中没有“存在”和“本质”这对概念,亚里士多德用“这一个”(tode ti/that it is)和“其所是”(ti estin/what it is),分别表示事物的存在和本质。他用这两个不同的词组表示第一实体,本身就蕴涵着存在主义和本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再者,“这一个”是个别的存在,而“其所是”是本质属性。这样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第一实体到底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亚里士多德试图用实体的个别化原则,把本质个别化,把个别化的本质作为第一实体。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本质是不能被个别化的;因为本质由定义表达,而根据他的逻辑,定义的一般形式是“种 + 属差”,任何定义必然是普遍的,而不能是关于个别事物的定义。如果一定要为个别事物下定义的话,那也只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直指定义,即指着一事物,说它是“这一个”。这样一来,又回到了第一实体是个别事物的立场,仍无法与第一实体是本质的立场相调和。
以上分析说明,亚里士多德虽然用实体理论统一“是者”的意义,他的统一把“是”动词的不同用法综合在一个形式逻辑的体系中。但如果进一步追问“是者”的语义学的意义,那么就会产生实质上的矛盾,这就是他的第一实体学说的内在矛盾。后世的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一般说来,唯名论和存在主义倾向于把“是者”归结为个别的“存在”,而实在论和本质主义倾向于把“是者”的意义归结为普遍的本质。“有”这一中国哲学概念的动词意义指“具有某种规定性”,“无”指“没有任何规定性”,“有”和“无”的名词意义分别是“有名”和“无名”,“名”相当于定义及其表达的本质。“有”的这些意义与本质主义对Being的理解相对应;因此,“有”也是表达Being的意义的一个中文概念。
西方形而上学史表明,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Being的“是者”、“存在”和“有”的意义统一起来,更不必说后来的唯名论与实在论、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争论过程了。我们承认这三者各有依据和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各行其是,随意地选择一个表示Being的意义。相反,这向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根据对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著作、同一著作的不同语境,理解Being的意义。Being没有固定的字典意义,需要我们以形而上学史为依据,说明在什么样的理论或上下文中,“有”、“存在”和“是者”各自的适用范围。
同时,我们不必为在中文里找不出一个与Being相对应的词汇而感到遗憾。诚如现代分析哲学家所说,形而上学的争论产生于语言的困惑;其中最大者莫过于Being的困惑。当哲学家用这一个词表示极其广泛的对象时,认为它有惟一的或统一的意义;他们坚持自认为合理的那一个意义,把其他的意义都归诸其下,由此产生出无休止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用不同的词表示Being,至少可以提醒人们:Being在不同理论背景中有不同的意义,不要为追求惟一的统一意义而走上独断主义。以Being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很难摆脱独断主义的梦魇,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术语来化解关于Being的种种独断解释,未尝不是幸事,何乐而不为呢?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文化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读书论文; 巴门尼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