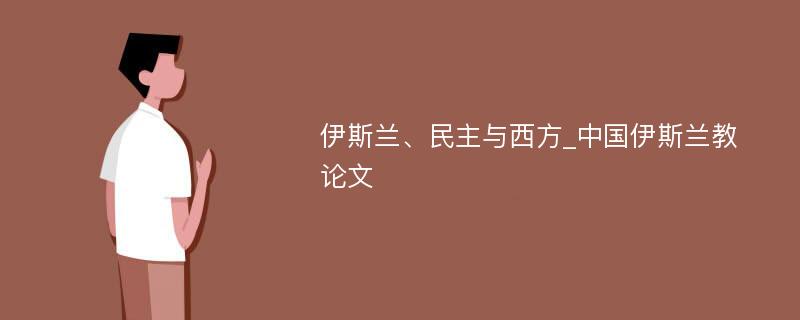
伊斯兰教、民主与西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中民译)
【编者按】自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迅速;对此,以亨延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正以“文明冲突论”制造新的“冷战”理论模式。本文及《西方自由民主与伊斯兰的撞击》一文对当今伊斯兰复兴的热点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对西方的态度作了评析,对于认识冷战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有参考价值。
一
继伊朗伊斯兰革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神权政体十余年之后,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术语再度出现。不仅在中东,而且在北非、西非到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从印度到中国西部,伊斯兰教日益作为一种确定的力量介入政治议事日程。伴随着共产主义的挫折,伊斯兰教正逐渐被错误地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未来竞争对手之一。
现阶段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始于80年代晚期,它明显区别于1979年的伊朗、1982年以后的黎巴嫩以及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叙利亚的小规模组织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伊斯兰运动,两个显著的差别在于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构成和策略都有别于早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二
伊斯兰复兴的第一阶段更多地与什叶派穆斯林即所谓的伊斯兰教派相联系。除伊朗革命外,诸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达瓦组织也控制了什叶派居住的阿拉伯半岛的东部边缘,他们可以被解释为最明显而又持久不衰的激进主义。然而,现阶段的伊斯兰复兴更盛行于主流逊尼派之中,该派至少占全世界穆斯林的35%。逊尼派伊斯兰教还广泛传播于构成伊斯兰大家庭的75个国家。除黎巴嫩、伊拉克、伊朗、也门等国家,逊尼派居绝对多数的国家横跨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其岛屿、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区域,穿越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延伸到中国西部、南亚以及远东的印度尼西亚等人口稠密的穆斯林国家。与象征着第一次复兴的极端主义——政治大灾难诸如大规模自杀、劫持人质不同,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力图以在其系统内部而非在外部发挥作用为特征。 例如, 1989年以来,伊斯兰主义者的各种不同组织参加了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国会选举。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穆斯林运动得到了4000万人民的支持,并于1989年举行和平集会敦促政府当局进行民主改革。
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场运动中,选票取代子弹而成为人们崭新的偏爱物,其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普遍反映人们已认识到80年代激进主义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例如伊朗的孤立导致的是经济退步而不是进步。共产主义遭受挫折,也清楚地表明了极权主义统治及其与西方对抗的危险。伊斯兰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多元化和相互依赖是90年代的主旋律。
合作尚未完全取代对抗,但在重要的地区伊斯兰主义者不再简单地对他们所厌恶的事物愤怒地大打出手。在经历了以停滞状态、殖民主义和失败了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试验为标志的若干世纪之后,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迫切地感觉到他们必须做出富于建设性的选择。在导致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转变的相同因素的深刻压力下,更多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在试图使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条与现代生活、政治竞争以及自由市场之间达成和解。然而只有少数伊斯兰主义者有了合适的或者完整的答案。“伊斯兰就是答案”作为普遍的运动口号仍处于过于简单的萌芽状态。
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不是孤立的,在20世纪末期,宗教变成了变革世界中生机勃勃的动力,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人们不仅努力消除其腐败的、效率低下的体制,而且试图找到能够维持其生存的选择。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宗教为其提供了思想、本体、合法性及深层结构。从变动的角度看,佛教在东亚,天主教在东欧、拉丁美洲和菲律宾,锡克教和印度教在印度,犹太教在以色列,已转变成为人们确定奋斗目标和进行社会动员的信仰。
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内部的种种努力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渴求——它使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而持久,因为伊斯兰教不仅提供了一整套精神信仰,而且提供了一整套社会统治规则的重要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不仅面临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寻求立足点的挑战,而且它正处于一种重要而又深刻的历史进化时期,人们日益认为伊斯兰教正处于新教改革运动同等重要的历史关头。信仰的传统作用诸如领导、组织、优先权、解释权都需作详实的考察。
变化的焦点甚至反映在名称上。第一阶段的伊斯兰复兴以一系列组织为标志——它们诞生于黎巴嫩、埃及和以色列占领区——被命名为“伊斯兰圣战”、“圣战”;然而近期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遍布从突尼斯到塔吉克斯坦的所谓伊斯兰复兴党组织而著称。伊斯兰与穆斯林国家及其体制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从多种角度看,伊斯兰社会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西方在16和17世纪所经历的相似广阔背景下,他们正在重新界定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伊斯兰教所面临的挑战之所以越来越严峻,是因为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不利于改革或者试验。伊朗革命过激行为的幽灵、黎巴嫩恐怖主义分子的狂热仍继续影响着西方和本地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尽管与此相反的迹象也在增长,伊斯兰教仍广泛地一再被错误地视为天生的极端主义。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影响与发展在不断扩大,它仍被错误地视为一种独立的,僵化的力量。
三
新生的伊斯兰主义的光辉耀眼地闪耀在穆斯林世界的两个地理边缘地带:北非和中亚。在这两个地区,自1990年以来,伊斯兰教已变成了社会主义统治的首要挑战者。在西方经历了与伊斯兰的若干年紧张关系之后,开始重新界定双方关系之际,这两个地区发起了挑战。
阿尔及利亚已变成了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容性试验的首要例证。1988年当人们的不满情绪酿成至少400人死亡的骚动, 沙德利·本德杰迪德总统结束社会主义一党统治之际,伊斯兰激进主义在阿尔及利亚崭露头角。在三阶段过渡进程的第一阶段,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1990 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它取得了地方议会60%的席位和市政议会55%的席位。自从领导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主义八年战争就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解放阵线(FLN),令人困惑地屈居第二。
自从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选举作为多党制的首要支柱,因为支持伊斯兰主义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拒绝。近30年效率低下和日益腐败的统治拖垮了民族解放阵线。据估计到1992年,阿尔及利亚2500万人口中至少有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5亿美元的外债将近占其石油收入的70%,政府几乎无力去平息民众长期以来由于住房短缺、失业、教育低下、社会设施发展缓慢而产生的满腹牢骚。年龄在30岁以下占人口总数63%的民众大多数没有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记忆,对其怀有依恋感的则更少见。相反,如果说生机勃勃的伊斯兰主义者尽管没有一个详尽的方案,但他们提出了合法的、令人感到亲切的选择。伊斯兰主义者的承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无病呻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选举在政治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自从伊朗革命以来没有一个伊斯兰政党曾取得如此势如破竹的胜利,也没有一个伊斯兰政党以民主的方式彻底击败了一个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但是,世界上的首例伊斯兰民主却未能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在第二轮选举的五天前,由国防部长尼泽领导的一场“白色政变”迫使本德杰迪德辞职。此后的几周内,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被取消,组织被取缔。至少有8800名伊斯兰拯救阵线和哈马斯组织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有人声称是30000 人——被后来的前线组织集体遣送到南撒哈拉沙漠的集中营拘禁。政变后,为镇压叛乱,民族解放阵线分裂成若干个宗派集团,而反对党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反对行政会议的力量。在混乱中,伊斯兰拯救阵线构成了推进艰难民主进程的左翼力量。尽管在骚乱中警方和军队在关键的清真寺设置了警戒线,但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者一再主张克制。“军队在其策划的剧本中为我们设定了我们不愿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能对他们的挑衅做出反应”。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人阿伯德卡德·哈沙尼告诫数千名穆斯林。尽管伊斯兰拯救阵线是一个由多数派参加的、有助于不同标准的激进主义的运动,它们对伊斯兰民主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在防止流血冲突方面本质上是一致的。
四
对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而言,阿尔及利亚不仅是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容性的一个试验例证,它也是西方能否和伊斯兰教和解的一次尝试。就此而言,西方开创的记录仅仅稍强于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会议。
阿尔及利亚政变后,西方的反应显然是被动的。美国国务院在官方性地对阿尔及利亚民主进程受阻表示“遗憾”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几个欧洲国家政府允许行政会议的代表进行官方访问解释他们的方案与目标。一些国家甚至考虑提供援助。美国的反映显然是不够的,他表明白宫宁愿选择一个警察国家,也不愿意选择伊斯兰民主政体。
然而,阿尔及利亚是有争议的伊斯兰民主的最佳试验场之一。首先,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它深受毗邻的西方的影响,不象在地理上远离西方的伊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迄今为止,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分子对西方仍十分敬畏。
第二,伊斯兰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伊斯兰沙里亚法的贯彻执行,沙里亚法作为伊斯兰法律核心或法律渊源——其步调并非与西方的利益有必然的不可相容性,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与西方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却是沙里亚法居于统治地位的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的两个。
最后,让伊斯兰主义分子在公共机构中任职比使其作为秘密组织活动于政体之外更可行。政变富于讽刺性地纵容了暴力,在很大程度上象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要求的压制一样,在第三世界点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
遗憾的是时间将一去不复返。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分子最终将居于主导地位,问题在于伊斯兰拯救阵线将产生何种影响。伊斯兰拯救阵线发表声明指出拒绝对话和压制政策势必导致其支持者诉诸武力,从而使其转向支持他们的右翼力量。解散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命令诱发了富于战斗性的反应,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势必影响到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部分。当伊斯兰主义分子积极推进其民主进程时,西方固有的反伊斯兰情绪暴露无遗。这种认识的长期影响将超越出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政变的最终结果将以高昂的代价波及每个人。
五
伊斯兰主义情绪增长的另一个新的关键性地带是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自从1991年莫斯科政变后,五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纷纷独立,它们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中四个国家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堡垒。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唯一的例外,但共产主义者仍然象它的邻国一样控制着它的议会。
中亚政治对于伊斯兰教并不陌生。从8世纪晚期开始, 伊斯兰教一直是统一该地区的力量之一。在中世纪成吉思汗和帖木尔统治土耳其斯坦时期,伊斯兰教以其在本地区的伟大成就和不朽业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和艺术贡献而辉煌灿烂于一时。尽管大部分游牧部落与家族中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直到19世纪沙皇俄国吞并土耳其并开始贬抑伊斯兰教之前,伊斯兰教一直维持着自身的繁荣。
布尔什维克革命反对授与该地区自台,在后来的六年内战中,伊斯兰仍是强有力的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之一。1920年独立的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为了防止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民族运动的发展,斯大林异常专制地把土耳其斯坦分成五个现存的国家。20年代和30年代,俄罗斯移民潮水般地涌入中亚地区。
尽管经历了70年的宗教压制,6000万穆斯林的大多数仍设法通过家庭和非法清真寺的教育和实践活动保持其信仰。自从1990年苏联通过“信仰自由”法律后,中亚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伊斯兰复兴,一些人估计在这一与俄罗斯、中国、伊朗、阿富汗接壤的矿藏丰富的战略地带,每天都有10座清真寺开放,注册的宗教大学及神学院急剧增长。伊斯兰复兴党的各种分支机构,对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们最终于1991年设法在莫斯科作为合法政党进行了注册登记,但他们的活动在中亚五国的四个国家仍受到限制。
不象其他穆斯林国家,中亚五国从未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向民主开放的历史,甚至在唯一有由共产主义向民主转换的总统的吉尔吉斯,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民主仍是一个不相容的概念,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自由。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运动领导人认为,民主被充分理解并扎根于社会之中至少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实现。在其他地方,诸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别里克(Birlik)和塔吉克斯坦的民主党等民主组织,目前吸收的主要是小知识分子。
相对而言,在经历俄国150年殖民主义统治后, 中亚五国转向文化寻根是十分自然的。他们开始转向使用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而放弃了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西里尔字母,生活模式和生活习俗也正在复古。因此,伊斯兰教必将成为影响中亚地区未来的主要因素。
然而,伊斯兰教在官方领导人反对非官方伊斯兰教的斗争中经历了一场浩劫。在共产主义统治期间,中亚地区的伊玛目和清真寺在国家同意的条件下惨淡经营,从而也受到了国家的控制。70年代晚期,持反对意见的穆斯林转入地下,号召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统治,在秘密的清真寺中开展宗教活动。大多数新的清真寺是地方人民私人建设的,并与非官方的伊斯兰教有关系。处于克里姆林宫控制之下的塔什干中亚穆斯林理事会努力清除官方领导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在此阶段,伊斯兰复兴党的主流派有了其适度的目标,多数中立派围绕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和教阶统治的结束,正重返伊斯兰文化并对酗酒、吸毒、卖淫不予法律保护,许多与以色列没有敌对关系的穆斯林国家正在同中亚建立关系。在中亚唯一的操波斯语的国家塔吉克斯坦,伊斯兰领导人发表声明拒绝伊朗模式,与此同时指出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差别以及西方和俄罗斯对激进的伊斯兰国家的恐惧。
遍及中亚、北非的伊斯兰主义者都在令人信服地谈论要创造一种自己的伊斯兰民主模式。即使在单一的组织内,他们的意见也各不相同。一些人主张从世俗的土耳其借鉴民主,而从巴基斯坦吸收伊斯兰政府的实践经验,然而他们又认为两个国家都不能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模式。极少数人主张除向有“伊斯兰教守护神”之称和圣地所在地的沙特阿拉伯求得财政援助外,别无所求。所有人都声明伊斯兰民主的种种主张都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和言论自由,但必须对酗酒、卖淫等非伊斯兰活动施加严厉的惩罚。
诸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许多伊斯兰主义者也正在与新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合作。当新的民主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动员数千名支持者在杜尚别进行和平祈祷仪式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之际,中亚的共产主义统治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
象阿尔及利亚一样,地区性和国际性的考验提前到来。中亚政体对允许所有党派在体制内部而非外部发挥作用的真正多元化耽搁时间越长,更加痛苦的、敏锐的伊斯兰教向“旧体制”发起挑战的危险性越大。
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着命运的考验。乌兹别克领导人已恢复宗教假日并归还苏联时代国有化的宗教财产。然而与此同时,它又禁止宗教党派参与政治,严禁神职人员参加公共机构选举。在哈萨克斯坦,世俗的反对党已经合法化。与此相反,独立以来的第一批政治犯却是以哈萨克神话领袖命名的伊斯兰政党安拉党的七个成员。他们被指控“侵犯了总统的荣誉与尊严”并进行非法集会。遍及中亚各地的重新命名的共产党组织正声称他们要重返权力舞台摧毁政治化的伊斯兰教。
西方也对中亚的伊斯兰教持矛盾性态度,西方官员走访新的中亚国家,鼓励他们在苏联统治结束后要与世俗化的土耳其开展竞争,而不是与其伊斯兰近邻伊朗。
象卡特政府在对并不了解的伊朗伊斯兰主义对话前就采取了敌对的态度一样,布什政府在中亚和阿尔及利亚犯了同样的错误。西方现在仍没有吸取冷战的重要教训:同化远比在矛盾中逐渐瓦解竞争对手更为有效,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非真实。如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西方扮演对包括伊斯兰主义在内的真正民主开放的鞭策者,远比容忍排除伊斯兰主义的极权主义制度效果更佳。
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并不热衷于步伊朗后尘。与此相对应,伊朗也没有去中亚进行重大干预的资本和意愿。在波斯湾和其近邻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之后,伊朗的热情特别集中于经济发展以防止整个地区陷入一潭死水。
实质上,伊朗1992年4 月的集会和国会选举体现了伊斯兰运动狂热支持者的深刻变化。为了终止对伊朗实行开放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阻挠,伊朗总统阿里·阿克巴·拉夫桑贾尼推行了对3000多名不合格候选人的1/3 进行保护的方案,其中包括40名教区阿匐。大多数是反对私有化、外国投资和向西方提供建议等经济改革的坚定的伊斯兰革命者。
改善伊朗革命在国内践踏人权的状况,改革伊朗革命在国际上的极端主义战略仍有着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但是,德黑兰释放关押在黎巴嫩的美国和英国的人质问题上所提供的帮助,以及在沙漠风暴计划中的中立态度都深刻表明伊朗企图和解的愿望,甚至至少表明它在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方面所作的让步。虽然伊朗与伊斯兰民主仍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它今天的所作所为与早年的伊朗革命时期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
西方和伊斯兰的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过去十余年的冲突——对抗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缩影——没有必要再作为双方关系的范式。不幸的是,尽管强有力的事实表明伊斯兰仍有其政治要求和未来潜力,美国与其盟国仍没有更强于在霍梅尼强行使伊朗的什叶派脱离巴列维王朝控制之后的明确的与伊斯兰进行斗争的战略。
伴随着伊斯兰主义情绪的蔓延与扩张,西方有两个明显的选择,一个是利用这种重要的时机——民主与伊斯兰双重高涨——迫使穆斯林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走向政治多元化,并接受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结果。采取早期就支持其民主化的步骤,一旦他们拒绝或放弃民主原则时,西方在掌握新的伊斯兰政府中就会居于强有力的地位。
应该鼓励的是缓解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未来几年对于民主和伊斯兰的发展进化国样重要。两千多年来,民主已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人类所面临的下一个全球性挑战,决定于民主是否适用于包括伊斯兰社会和儒教社会在内的东方国家。反之亦然。
第二个选择是试图以支持和资助这些国家政府镇压伊斯兰主义运动,与其进行对抗并限制其扩张,这一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将与同共产主义进行挑战的代价同样高昂,范围也同样广泛。与以一个为失败的经济体制所支配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同与一个充满魔力般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古老信仰和文化进行挑战是截然不同的。此外,象在冷战中一样,美国还不得不培植索然无味的同盟国,许多献身于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国家——从阿萨德的叙利亚到卡扎菲的利比亚也同样反对民主。
这种选择——一种绝对公开地阻止伊斯兰主义运动达到权力顶峰的政策——也表现了西方的恐惧:害怕多种多样、情况各异的伊斯兰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手段的反西方势力。与此相对,更大的危险在于西方阻止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企图将导致东西方关系将以更深刻的矛盾以及接踵而至的血腥历史而分裂。
伊斯兰复兴运动显然既使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
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伊朗革命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穆斯林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