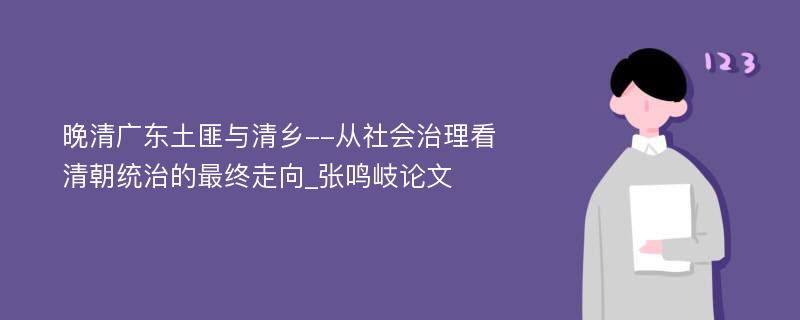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乡论文,盗匪论文,清末论文,广东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1-0092-10
进入晚清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日渐增多。在南疆广东,盗匪问题发展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广东盗匪不仅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直接危及当权者的统治。官方如何应对匪患,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治理问题,其成败得失,为我们审视清末王朝统治状态及地方社会的情势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本文将侧重考察政府清剿盗匪政策的实施,以具体探讨清末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及其社会治理的能力①。
一、“粤东之盗,甲于天下”
19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1899年11月澳门《知新报》的一篇文章称:“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粤盗之案,其不报不详者且勿论,即如报章所载,几于无日不书,无地不有,墨为之罄,笔为之秃,已令人可惊可骇。”②此番言论虽有夸张,但其所反映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类似的言辞常见于清末报章。1897年1月《申报》的一篇文章曾说:“近来广东之盗贼横行无忌,甲于各省。”③《广东日报》也刊文指出:“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④清末广东的匪患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官方也并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且多方渲染。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与会、土、械斗各匪、洋盗、盐枭互相出入,其情节实与寻常盗匪迥异”⑤;1901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陶模也向朝廷奏陈,“广东素称多盗,近年日益加厉”⑥。官方在答复谘议局“保护内河航路”议案时,也声称,“近数十年粤省盗风猖獗,甲于天下”⑦。
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何种程度?一些零散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信息,如:在沙田相对集中的东海十六沙,“打单掳劫,历数十年,居民久视为固然”⑧。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三十年(1904)之间,“贼匪堂号以数十计,人数以千百计,打单掳勒动逾田租之数,明目张胆悬红勒收行水”⑨。广东谘议局的报告说,清末最后的十余年内,处于粤桂边界的信宜县,“无时不抢,无地不抢,无日不抢,无物不抢,一年之间劫杀案多至三千余件,其中无力纳衙规及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尤不胜数”⑩。报纸也有消息说,在清末顺德县东马宁一带,“贼匪传闻总过千余人”(11)。1906年,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3年之内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共“获办”“积年打单抢劫掳劫之匪”9910余名。仅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至十月围剿香山县沙匪的行动中,官兵就“剿捕格毙获办著要各匪不下千余名”(12)。从“剿匪”战果来看,广东盗匪数量实属可观。19世纪末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的谈话中提到,在广东,“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13)。孙中山所说的“山林剽悍之徒”未必尽是盗匪,但联系革命党人早期的策略来看,其主要的还是会党绿林分子。1915年中国机器总会估计,广东的绿林有30万之多(14)。由此推断,清末广东的盗匪规模当超过10万人(15)。
“粤东盗甲天下”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广东也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6)。虽然在清末广东,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到处裹胁饥民攻城掠地,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广东各地股匪,人数多则数百人,少或数十人,但匪帮多,且大多数情况下又是各自为匪,互不相属,从而造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广东盗匪又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当时的官员有这样的印象,“广东盗案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17)。当时的海关报告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18)这也使盗匪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更显突出。而且,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且不乏新式利器,“无一盗不持械,所持之械无非洋枪洋炮”(19),“凡七响十响、无烟手枪、无烟马枪,匪党无一不备”(20),使盗匪更难对付。有舆论就说:“顾何以广东之盗乃肆无忌惮一至于此?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足以与官军抗衡故也!”(21)这些因素对清末广东匪患的“名声”膨化有直接影响。
清末广东盗匪与反清革命运动也有一定的关系。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及酝酿的革命计划中,会党是依靠的重要力量。在晚清广东,“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作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22)。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23)。革命党人对会党的发动利用,也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例如,1895年筹划的广州起义中,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号召北江会党准备参加(24),后因事机泄露而失败,孙中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25)。1900年,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约东、西、北三江若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26)。马王海即当时东江一带著名绿林人物陈海;区新则是西江一带赫赫有名的绿林首领,“枪械精利,党与众多”(27)。1907年6月邓子瑜发动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绿林、会党在七女湖起事。其中孙稳被惠州一带绅商指控为“平日以抢劫为事,乡里迭遭其害,妇孺皆知”的“剧盗”(28)。1909年革命党人计划发动新军于1910年正月初旬起义,广州地区著名盗匪李福林所在的大塘乡是筹备起义的重要据点,朱执信常驻大塘,负责南海、番禺、顺德、三水等处的民军策应工作(29)。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绿林首领陆领、邓江在顺德乐从响应配合。在1911年广东光复运动中,以绿林盗匪为主干力量的民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0)。这也是清末广东盗匪问题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绿林盗匪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出于何种动机,盗匪借革命旗号大肆活动,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更大动荡,“四乡群盗,面目改变,日益猖獗。其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其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于是闹捐毁抢亦曰革党也,立堂打单亦曰革党也”(31)。另一方面,盗匪壮大了反政府的力量,成为直接威胁政权统治的危机因素。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小则抢劫掳赎,大则纠党置械,显著逆谋”(32);两广总督袁树勋也强调,“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漫难图之忧”(33);张鸣岐亦指出,广东盗匪猖獗,“纠伙每至数百,劫掠动辄全村。加以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匪,勾结革党,暗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村乡,四通八达,兵多则逃散,兵少则抗拒,竟敢抢劫兵船、营房,戕毙弁勇。屡于获盗讯供,据称劫资置械,约期起事”(34);社会舆论也反映,“从前贼匪不过志在得财,近日更有结党联盟,蓄谋不轨”(35)。在此种情形下,以平常的做法已经难以应对广东的盗匪问题,地方官员一面强调“匪情”,希望引起社会与朝廷的重视;一面推行非常措施,调集军队清乡,以军事手段对付盗匪问题。
二、“示以军威”
在清末广东的文献中,清乡的提法,较多地出现于189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官方所称多为“查办匪乡”、“清厘积匪”、“清查匪乡”等等。它的出现与晚清以来政府在基层社会控制力的衰弱有关,“迨绿营既裁,兵力愈形不及,故有清乡,以资攻剿”(36)。何谓“清乡”?1913年8月,广州总商会将清末广东清乡之法概括为:“水陆分防严密,复设各处行营为办匪机关,委用熟悉缉捕能员,分带土著营勇,同时大举,按乡清办;随时随地购线踪缉,遇有大股匪徒,则会合剿捕;仍责成旧日正绅与各属商会,同负保民攻匪之责;编查各乡村保甲,举出房、族正副,密报匪名,到拿捆送,以清内匪,并给械办团,以辅兵力之不逮。内清外捕,则思过半矣。凡此数端,皆属清乡要素。”(37)
清乡首先主要运用于匪患较为严重、盗匪相对集中的地区,其后渐渐变成一种通行的做法。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至光绪十三(1887)年五月,全省分为三路“查办匪乡”,“盗匪、会匪、斗匪一体惩办”,共正法积匪906名(38);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至光绪十九年(1893),在盗匪问题突出的南海、番禺、顺德三县“查办匪乡”,仅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至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就获匪372名(39);光绪廿四年(1898)前后,水师提督何长清在广州府属清乡,“凡绿林暴客花红甚巨者,莫不知畏逃匿,东窜西奔欲为漏网”(40);光绪廿六年(1900),水陆提督设立营务处及缉捕总局,在广州府属及清远、北江一带分五路清乡,“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41);光绪廿七年(1901)至廿八年(1902),全省各州县同时并举,“按乡办盗”,就地惩办(42);光绪廿九年(1903)至卅二年(1906),全省分为五路,“派拨专员分赴各属,协同地方文武,举办清乡”,3年共获办“积年打单抢劫掳劫之匪”近万名(43);宣统三年(1911),全省同时并举,又分五路清乡,著匪重情“军前惩办”,寻常盗案,解交州县讯办(44)。除了大规模的数地同时清乡外,县一级的清乡一直不断,“清乡委员”如同常设的官员派驻各地,“各处行营及多盗各州县特派清乡及审案查案等员,帮同办理”(45)。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46)。清乡之法被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所沿用,成为清末广东治盗的“不二法门”,并延续到民国初年。
具体而言,清乡的主要步骤有四:调集军队下乡围剿盗匪;责成地方绅民指攻盗匪;就地惩办盗匪;督办团练以为善后。清乡的主要手段是调集军队下乡,“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47)。1900年底署理连州知州李家焯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清乡,带勇1200名,另有巡船12只在河面游弋梭巡(48),清乡行动中用兵的规模,可见一斑。岑春煊“五路清乡”时,甚至“改定通省营制,概以二百八十人为一营,分派中、东、西、南、北五路,划清地段,各办各乡”,责成专守,不准随意调动(49)。1911年的清乡中,两广总督张鸣岐动用了所有的军事力量,就连新军及从广西调来的龙济光的营队也被派往“素称多匪、地势扼要”的顺德、番禺、花县、从化及英德、清远等县驻扎,“专办清乡”(50)。从各地调来省城镇压黄花岗起义的23个营,除留3个营防守省城内外“军装、子弹、火药各局库及藩库”等处外,其余也都被分派各地“责成认真清乡”(51)。出于清乡的需要,地方文官也赋予了统兵大权。陶模推行清乡,“派出弁勇均归州县节制”(52)。1902年,顺德知县王崧被委派总办肇(庆)罗(定)一带清乡,“原扎肇罗各安勇悉归节制调遣”(53)。无论何种形式,军队是清乡最主要的力量。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曾直言不讳称:“本督院深维治匪清乡专资兵力,各营将现统防兵,责无旁贷,所有清乡搜捕事宜,嗣后即专责重统兵营将。”(54)清乡实际上无异于一场调集军队对付盗匪的战争。
军队下乡围捕,“线人”提供的盗匪情报很有限,更多的是依靠地方绅耆“保良攻匪”。清乡中,官府要求地方绅耆主动举报和“捆解”本族本乡的盗匪,“若子弟出外为非,责令绅董、约长、族长,按名交出,如在本乡为匪,尚未破案,即须开所犯事由实迹,禀送到官,以凭讯明惩治”;“若著匪远扬,即令具结立案,日后潜回,由该乡族捆交或报官引拿,傥敢包庇纵容,一并惩处”(55)。为配合清乡,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颁布了专门的《防盗清族章程》,规定族中有匪,则责成族正族副“即率族人捆解到官严办”(56)。1907年惠州知府陈兆棠办理清乡,发布告示要求各约绅房族,“务将族内各匪速行按名捆送惩办,以期拔尽根除”(57)。有的清乡官员还强迫族绅交匪,番禺县小洲乡著名盗匪简亚廉,在清乡兵勇前往围捕时闻风逃走,清乡委员便将当地绅耆简佩和、简鸣仪“解回番禺县押候,勒限捆送惩办”(58);南海县上淇乡生员陆朝,也“因责交巨匪有辫领,押留数次”(59)。官府甚至向族绅勒缴“花红”,以达缉匪目的,1903年南海县西樵著名盗匪区新、区湛被官兵捕杀后,官府责令村中庇匪各绅缴交2万元“花红”,“以为窝庇巨匪者戒”(60)。据称在1907年,仅顺德县龙江一乡,官方就列出200多名盗匪姓名,要求当地士绅捆送(61)。各地士绅在指攻盗匪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不少士绅还因指攻盗匪惹来杀身之祸,南海县上淇乡的陆朝因有“指攻之事”而被族匪枪杀(62);顺德县团绅卢天骥因指攻盗匪并自告奋勇办团,被匪绑走戕害,弃尸野外,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63)。
为配合清乡,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倪文蔚以广东“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其情节实与寻常盗贼迥异”为由,奏准在广东恢复就地正法(64)。此后“就地正法”在广东一直伴随清乡政策而沿用(65)。光绪廿六年(1900)李鸿章任职广东,专门设立缉捕局并开设各路行营,以审办处置所获匪犯。这种做法在后来的清乡中也被沿用。陶模督粤时,“且有当场拿获,准先行惩办,随后录供禀报”的做法(66)。1909年广东咨议局讨论“停止就地正法”议案时,议员提出“非有就地正法,即无以清乡”的反对意见,结果议案没有获得通过(67)。张鸣岐大办清乡,规定“缉获盗匪,责成各印委详讯确供,如系土匪、会匪、游勇,有杀掳焚劫,啸聚抗拒重情,即在军前惩办”(68),把处决盗匪的权力“下放”给具体负责清乡的官员。清乡政策从其一开始就以严厉的杀人手段加以推行。1907年的报纸说:“江浦行营自前年冬再行开办之后,先后审明正法盗犯已二十余批,每批动辄三四十名,合计已千余名。”(69)行营是清乡时审讯处置盗匪的主要机关,这样的行营在全省还有几个。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有文章说:“晚清之末,营务处岁杀几千人。”(70)陈炯明称惠州知府陈兆棠清乡时,“杀三千余人”(71)。清末负责广州地区清乡的江孔殷曾说:“清乡又不能不出于杀人。”(72)有人回忆,其在顺德县清乡时,仅大良(顺德县治所在)一地被杀的人,就难以统计,“尸横原野,血流成渠,整个大良城充满阴惨景象”(73)。清乡实为“重典治乱”之策。
清乡军队不可能常驻乡村,在清乡同时,官府也鼓励并支持地方士绅恢复乡局、兴办团练,以期强化对乡村的控制,肃清匪患。1886年郑绍忠在东莞、花县等地“清厘匪乡”,要求各地“在县城设公局一所,市、镇、大乡各设分局一所,遴选公正绅士,经理局事”,劝谕各乡绅董,就地筹款,“妥办团练,以助守望”(74)。陶模订立的“捕盗章程”也要求地方绅耆、乡团团长等清查户口,“取具十家互保,以后如有为匪之人,互保者不能举发,即予连坐”(75)。岑春煊督粤期间的分路大举清乡,也大力鼓励地方办团防匪(75)。1911年在籍大绅邓华熙(曾任贵州巡抚)牵头专门组织了一个“筹议广属清乡善后所”,声言“清乡后凡有筹办团防,联络乡族,以清盗源,本所征集舆论,力与维持”。两广总督张鸣岐批准其成立,且要求广州府“转饬所属各县遵照,遇有清乡善后事宜,随时与诸绅商办”。广州的官绅曾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清乡善后之策,意见集中于大力兴办团练及联防办团方面(77)。在当时,兴办团练被视为巩固清乡成果的重要措施,而成为清乡的主要环节之一。
三、“兵来贼去,兵去贼来”
尽管清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动用的兵力也越来越多,所杀的人也不少,但是,多年的清乡却并没有遏止广东盛炽的盗风,结果往往是“兵来贼去,兵去贼来”(78)。张之洞督粤时分三路“查办匪乡”,“各属盗贼仍复猖獗异常,肇(庆)属之开平、鹤山,广(州)属之番禺、顺德等县劫案视昔尤多,且有逞凶拒捕者,汛弁乡团时为贼所刃毙”(79)。1890年代末,水师提督何长清在广府各县清乡,“匪徒即闻风远扬,然未几仍恣横如前,终未能根除尽拔”,各地绅耆仍然纷纷上省请兵剿捕(80)。吴祥达在惠州办理清乡,也是“兵来贼去,兵去贼来,军门东驰西逐,疲于因应,而地方亦终无肃清之时”(81)。番禺县沙湾、茭塘一带,办理清乡的知县刚一离开,“匪势复张”(82)。清远县的盗匪在清乡后反而更加横暴,“从前不过滨属(指清远县滨江)受害而已,今则蔓延四境”(83)。顺德县自岑春煊派员开办清乡起,持续了数年之久,“迄未蒇事,而各乡劫掳之案,日见其多”(84);1911年大办清乡之后,“营县连报抢劫勇厂枪械,杀人劫掳时有所闻”(85),乐从、容奇等处的盗贼,“迭与官兵接仗,而匪风仍未稍戢”,以致清乡军队动用开花大炮(86)。
清乡的实效比预期目的相差甚远。末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也承认“以前历办清乡,往往劳师糜饷,委员视为例差,毫无振作”(87)。更有人讽刺说:“清乡二字,命名本属甚佳,而揆诸事实上,则殊多乖谬。天下安有许多剽悍凶猛之徒,日惟株守其乡闾,以待官兵之掩捕者乎?又安有预定一大举围捕之日期,声明某日则到某乡,并声明到某乡即捕某匪,而该匪犹未觉者乎?倘以是而办清乡,吾恐办至宣统九十九年,各乡亦必无肃清之一日矣。”(88)此类批评在当时报纸上还能看到不少。舆论认为清乡不能真正起到弭盗治匪作用的原因,“则在于清乡之流弊,层见迭出,而莫可胜穷”(89)。据各种反映归纳,清乡的弊端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官员腐败、疲玩。1907年营务处承认,“各处清乡审案等员,操守廉谨勤慎办公者,固不乏人,而请托贿纵,颠倒是非,假公济私,疲玩因循者亦所不免”(90)。清乡委员是具体负责实行清乡的官员,而有关清乡官员腐败的情况,却可以经常在当时的报纸上见到,如办理番禺县沙湾、茭塘两地清乡的清乡委员蔡某,与当地局绅邬某,“朋比为奸,所到之处,婪索夫马,勒缴花红,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当地人送了他一个“蔡阎罗”的称号(91)。清乡委员黎炳新到清远英德一带清乡,不但“捕务决不经理,每以抹牌消遣”,且“招集棍徒,花天酒地,流连宿娼”,即使离营数里之许的劫案也不派兵缉匪,还纵勇枪毙民命(92)。委办恩平县清乡的凌启瑞则敷衍了事,迟迟不下乡,下乡40余天内未获一匪,而开支却在百两以上(93)。清乡官员的腐败疲玩直接窒碍了政策的落实。
其二,军队骚扰地方。清乡中,军队藉捕盗之机行抢劫之事,比比皆是。有人反映,负责清乡的李准所统带各军毫无纪律,“到处滋扰,以致匪势蔓延”(94)。在饶平县上饶一带,“各兵勇到处藉搜匪为名,肆行抢掠,人民不堪其扰,纷纷迁避,大有十室九空之象”(95)。1907年水陆提督发布的文告中也承认,“近闻各营下乡捕匪,多有不加约束,任令兵丁藉端搜取财物者,实属形同盗贼”,要求各地地方官及清乡委员随时就地稽查举报(96)。1911年5月,清乡军队在高明县藉捕抢掠,“见槓开槓,见柜开柜,银洋虽二三毫亦取,衣物则绸缎夏布甚至牙擦练、漱口盅、男女鞋,无物不取”,“种种骚扰之处,难以枚举”(97)。由于此类问题既严重又相当普遍,两广总督张鸣岐曾特派暗查委员数人分赴各地,专门密访调查(98)。清乡军队藉捕盗而扰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以致当时的报纸常用“贼过如梳,兵过如篦”来批评政府的清乡。
其三,缺乏士绅的有力配合。清乡之法,“以局绅为耳目”(99),两广总督张鸣岐也称,“清乡大要,全在联络官绅以保治安”(100)。但不少地方士绅,或“亦惧祸及,各相匿避”(101),而不敢指攻;或因著匪远扬,迫于官兵勒缴,以鼠窃狗盗之辈塞责;或诬良为匪,“向与己有睚眦之怨者,诬之为匪而捆送之,又或绅与绅不和,则于其子侄之游手好闲者,攻之为匪”,以达报怨的目的(102)。
有些乡绅,甚至与盗匪沆瀣一气,庇匪滥保,坐地分肥。时人称,“贼匪所以能藏匿乡中,恃有包庇耳,然地痞之包庇,十居八九;劣绅之包庇,十居一二”。劣绅庇匪还严重削弱了士绅缉匪的积极性,“清乡官吏勒令交匪,则责诸乡闾属望之正绅,而包庇之劣绅,反以绅名不彰,竟得置身事外。及正绅悬红购缉,或侦悉匪踪,密报营汛,则劣绅反暗通消息,使匪得衔恨以图报复,而焚烧屋宇者有之,劫掳杀害者有之”,士绅为顾身家性命,只好敷衍塞责,甚至“匿迹家居,噤口不谈公事”(103)。“正绅”不敢出头露面,又为“劣绅”把持地方事务提供了机会,一些地方的乡局也渐渐为“劣绅”所控制,而发展成为庇匪的机关。时人披露:“乡局之设,初原以乡团等名,借为弭盗之计,而不知久之未有不从而庇盗者。乡局之绅士愈大,即乡中之盗贼愈恣,其在蛇鼠一窝,买赃庇匪,公然以乡局为发财之地。”(104)以致官府也不得不将严惩“劣绅”列入清乡的内容(105)。1911年9月,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将“向以庇匪著名”的顺德县士绅冼瑞衔就地正法(106)。在官方来说,大张旗鼓地处死冼某显然是“杀一儆百”的做法,地方“劣绅”庇匪之风已到了不得不杀的地步。当时舆论就说,“自有庇匪劣绅出现,清乡已成具文”(107)。
其四,勒缴”花红”,成为官绅谋利的手段,反助长了盗风。对不能当场拿获的盗匪,通常以悬赏“花红”的手段“购缉”,旨在激励缉匪。原则上,“花红”一般由该匪族人和当地士绅筹缴,“多由绅士将犯属屋宇禀封备抵”(108)。自勒缴“花红”成了清乡的内容后,清乡也随之出现了另一番情景:“地方官于既缴花红之后,遂置匪于不问,匪族亦以遵缴花红,遂可藉免充匪,其谨慎者,不过以此塞责,其不肖者,更将缘以为奸。始仅责成匪之父兄,继遂推至匪之亲属,甚者及于疏族祖祠,真匪饱劫掠之资,平民受追呼之惨。而地方官之视追缴花红,更重于勒交匪犯。”(109)某种程度上,勒缴“花红”已由清乡手段变成了官员清乡的目的,有人将清乡讽刺称为“清财”,“清一乡之财也”(110),其结果是,“广东盗风如故,广东之花红亦如故”(111)。
其五,严刑竣法下滥杀进一步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重典治乱原本是不得已的非常手段,可是,清乡“就地正法”所杀者往往为“鼠窃狗偷”之辈,甚至是良民。有报道说,“自设营务处以来,年中统计斩决人犯,在马头者,有八九千人之多,其中枉屈受害,在不可知之数也”,据营务处的亲兵透露,“各审案委员俱不细诘人犯口供,但见其体格魁梧,便指为大盗,逼其承认案件,否则处以苛刑”(112)。1909年谘议局议员陈炯明批评,“近年各路清乡缉捕,戮杀最多,而防勇妄为诬拿,奸吏藉以恣睢,其间疑罪枉杀称冤者,实有所闻”(113)。两广总督张鸣岐也承认,“其中实有不免冤抑枉滥之弊”(114)。杀人本来就是治标的手段,不可能根除盗源,而滥杀则又势必进一步激化矛盾,“处心积虑成于一杀,于是民不聊生,罔知死所,为匪死,不为匪亦死,毋宁为匪而劫掠犹可冀须臾暂缓乎?势必负隅相抗,作困兽之奋斗”(115),结果是盗匪愈清愈多,愈杀愈凶悍。
民国初年,陈炯明说:“满清时代清乡,弊端百出,民未见利,先受其害,兴言及此,良足痛心。”(116)本来,清乡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非常手段而已,尽管统治者将之视为治盗的“要策”而相继沿用。但由于推行不善,流弊丛生,“营勇不能缉捕,约绅择噬善良;官则信用门阍,绅则侵蚀公款”(117),清乡不能缉贼,转致扰民。清政府的清乡政策并没有为解决广东的盗匪问题找到真正的出路。
四、结语
作为一种持续的、大范围的普遍性社会动乱的表现形态,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已经不是治安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它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征,亦是统治危机的体现。如何应对危机,其实是检验一个政权或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清政府大规模动用军队下乡清剿盗匪,推行非常手段,意在摆脱危机、强化控制,本身说明了日常化的社会治理机制陷入困境。在清朝,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系统:一是通过各级官员、附属于地方衙门的胥吏、差役以及分散驻扎于地方的军队直接建立对地方的统治、管理;二是依靠保甲制度以及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社会“自治”性权力结构,强化对地方特别是乡村的控制。两个系统“双轨并行”,互为制约与补充。在清末时期的广东,随着传统绿营制兵的窳败并逐渐退出地方防务,后起的防营又不能分散驻防,地方防务日见空虚,捕务废弛(118)。“保甲本是古法”,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基层控制制度,其功能就在于维护地方社会的秩序。到清末时期,保甲制度仍被认为是安良弭盗之良法。两广总督曾国荃在给徐闻县令的批复中明确指示:“办团防以资捍卫,编保甲以清盗源,尤为当务之急。”(119)刚毅来任广东巡抚,“下车伊始,即以整顿保甲为事”(120)。但实际上,传统保甲制度在清末广东并未得到有效的恢复。尽管官员多次重申,“无如各官绅士庶皆视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121)。就是报纸上多次提到兴办保甲的省城,也是“虽行之有年,然皆有名无实”(122)。在清末广东,保甲制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与保甲相辅而行的团练,亦被视为打击盗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法宝”。1904年,广东同乡京官曾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实行清乡团练事宜,以挽危局”,称“尤必有团练,以佐声援,而要非兴复省团练,无以稽查、联络声势之助”(123)。由于盗匪问题的影响,团练旧法一直在清末广东得以沿用、延续。实际中,官方大力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因为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便在地方团练问题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当权者在地方办团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结果团练也不能有效地消弭匪患,“虽迭经札行团练,以为地方自卫之要图,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遇有大伙强盗肆劫,则缩首蛆伏,任其饱掠,莫敢谁何”(124)。总体而言,在寻求解决盗匪问题出路的实践中,无论是规复旧时的保甲团练制度,还是推行新型的巡警制度(125),都没有使政府在基层社会恢复有效行政控制权力。这是清末时期广东盗匪问题日益严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推行“清乡”的主要背景,它直接反映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败。
即使在非常规背景下的“清乡”也事与愿违,并不能有效地遏止广东的盗风。表面上看,政府清乡不成功的原因来是其流弊所致,其实,归根到底,清乡所出现的流弊都是清末政权衰败的具体体现。吏治败坏,军队腐败,本身就是清政府统治衰亡陷入困境的表象。而士绅的分化与背离,以及滥杀之中法律威权的失落,更多地显示出清王朝统治没落的深层原因。士绅虽然仍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但从根本上说,却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在乡村地区,士绅与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清乡靠士绅,本身就有激化社会矛盾的一面,盗匪仇杀地方士绅就是典型事例。在清乡实施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士绅阶层本身业已出现严重的分化,上层士绅可以成为清乡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但乡村社会的中下层士绅,有的避而远之,有的却成为清乡的阻力而被喻为“劣绅”,甚至成为盗匪问题的“催化剂”,江孔殷曾在“声讨”顺德士绅冼瑞衔时,无可奈何地指出:“凡做绅士,如系绝不理事,固不至于保匪,即不肯攻匪,亦不过不主张杀人而已,两者皆可以说得过去,至于有钱则保匪,无钱则攻匪,此等绅士不为匪仇杀,必至教匪杀人,日日杀贼而不杀及制造盗贼之人,我甚为盗贼代抱不平。”(126)可见,士绅已经无法为地方政权治理匪乱、恢复社会秩序,提供有力的配合。传统官绅一体化的统治秩序与控制体系,在清末广东的清乡中,已显露出离析崩溃之势。在这种背景下,清乡当然难有成效。另一方面,“清乡”体现了“重典治乱”的基本策略,在清乡中,杀人不可谓不多,就地正法一直被沿用,但是盗匪依然猖獗如故,盗匪愈杀愈凶悍,无论是真的“愍不畏死”,还是执行者“偷梁换柱”以致滥杀无辜,王朝的法律因失去其本有的公正与威严,而不能成为控制社会、维持秩序的有力武器。正如有清代法制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法律体制既因未能提供有效的救济而助长暴力,且又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违法者手中的工具而发挥作用,那么,在这些方面,它也就削弱了人们指望它去支撑的社会价值”(127)。作为国家机器的法律,其威权的衰退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政权的没落(128)。
清乡的不成功也正好说明了没落的清王朝政权已无力解决广东的盗匪问题。当这些社会秩序破坏者积聚于反清革命的旗号下之时,衰败的政权也只能是回天无力了。清末革命党人在广东数次发动武装反清起义,不少盗匪人物卷入其中,有时甚至成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的力量,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军风起云涌的局势,最终成为广东光复的重要因素。而且,出身于绿林盗匪的民军势力,对民国初年广东的政局与基层社会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地域上讲,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特殊历史现象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却有时代的共性,清政府应对广东盗匪问题的处境对深入理解清末基层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历史,以及民国社会的“匪化”现象,提供了又一具体的视角。
注释:
①近代广东盗匪问题已为学界所关注。邱捷先生曾在《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军政府的清乡》(《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和《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二文中,以广东盗匪问题作为考察清末民初地方政府社会控制力的重要因素。文章重点分析了民初革命党人的执政能力,对清末广东地方政府应对盗匪问题的措施论述相对较为简要,而所提示的“团练”“清乡”“军警控制力”等问题对了解清末地方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即是受之启发而做的初步探讨。
②《纪粤盗愤言》,《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③《论广东盗贼之多》,《申报》1897年1月22日。
④贯公:《说贼》,《广东日报》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⑤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2-374页。
⑥陶葆廉辑:《陶勤肃公(模)奏议》卷1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21页。
⑦《广东咨议局第一次会议报告书》,广州:粤东编译公司宣统元年排印本,第47页。
⑧广州香山公会:《东海十六沙纪实》,“盗匪之潜踪”,广州1912年铅印本。
⑨广州香山公会:《东海十六沙纪实》,“东海十六沙纪实书后”。
⑩《信宜县匪风猖獗事》,《广东咨议局报告书》,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无页码。
(11)《顺德盗贼甲天下》,《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9月30日。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2-455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3页。
(14)蕙:《广东之兴业弭盗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4月6日。
(15)近代广东盗匪的名称有多种,常见的有“海盗”、“洋盗”、“山贼”、“沙匪”等,“沙匪”指在沙田区收禾票、打单勒索的盗匪。
(16)关于“粤东盗甲天下”说法的分析,可参见拙文《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7)杜凤治:《南海回任日记》,“光绪三年七月廿九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
(18)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5页。
(19)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74页。
(20)《两广官报》,“军政”,辛亥年第12期。
(21)《论广东多盗》,《申报》1894年2月1日。
(22)钟锡蕃:《清乡刍言》,《冈州星期报》1912年第9期,第1页。
(23)有关近代广东的会党与盗匪的关系,可参见拙文《近代的会与匪——以广东为例》,载《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
(2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25)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页。
(2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6页。
(2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40页。
(28)《惠州绅商请勿释放剧盗》,《申报》1910年3月5日。
(2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04页。
(30)有关民军在广东光复过程中的作用,可参见丁身尊:《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周兴樑:《广东军政府裁编民军新论》(《孙中山研究论丛》第8集,中山大学,1991年)。当然,民军也对清末民初广东社会造成了许多破坏性影响。
(31)《广东各团体因乱事布告中外团体书》,《时报》1911年8月26日。
(3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3-455页。
(3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78-479页。
(3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82页。
(35)《严防匪徒拜会》,《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0月28日。
(36)《广东同乡京官奏请实行清乡团练折》,《时报》1904年11月7日。
(37)《总商会详陈清乡办法(续)》,《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9月23日。
(38)《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京报全录》,《申报》1887年10月17日。
(39)《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京报全录》,《申报》1891年8月1日。
(40)《歼厥渠魁》,《岭海报》1898年7月4日。
(41)《五路缉匪》,《知新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一日;《示严缉盗》,《申报》1900年9月3日。
(42)陶葆廉辑:《陶勤肃公(模)奏议》卷12,第19-20页。
(4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3-455页。
(44)《辛女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82-483页。
(45)《严饬地方官查察清乡各员》,《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9月19日。
(46)《袁督整饬吏治之空文》,《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3月17日。
(47)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80-381页。
(48)《粤东谈屑》,《申报》1901年1月16日。
(4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3页。
(50)《两广官报》,“军政”,辛亥年第1期。
(51)《补录粤督电奏派营防剿布置情形》,《广东时报》1911年6月23日。
(52)陶葆廉辑:《陶勤肃公(模)奏议》卷12,第20页。
(53)《清乡示谕》,《亚洲日报》1902年7月1日。
(54)《两广官报》,“军政”,辛亥年第7期。
(55)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2534页。
(56)《粤东水师部巡李太守防盗清族章程》,《申报》1901年10月2日。
(57)《惠府陈守办清乡示文照录》,《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8月20日。
(58)《勒绅捆送著匪》,《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5日。
(59)《族绅竟死于委员之手》,《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8月15日。
(60)《论功行赏》,《申报》1904年1月17日。
(61)周鹗芬:《论乡绅交匪之难》,《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日。
(62)《族绅竟死于委员之手》,《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8月15日。
(63)《卢天骥被匪戕杀情形》,《申报》1911年7月31日。
(64)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72-374页。
(65)光绪廿四年(1898),奉朝廷旨意,规复旧制,广东曾暂停“就地正法”,但光绪廿六年(1900)李鸿章任职广东,开办五路缉匪,又奏准恢复“就地正法”。
(66)段云章等:《陈炯明集》上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67)《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广州宣统元年排印本,第68页。
(6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83页。
(69)《杀人如麻何畏愍不畏死耶》,《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3月28日。
(70)《本报荆天刺地志叙论》,《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8月30日。
(71)段云章等:《陈炯明集》上卷,第20页。
(72)《江孔殷上张督清乡意见书》,《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5月20日。
(73)黄亮伯等:《辛亥顺德民军起义见闻汇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
(74)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2534页。
(75)《捕盗文言》,《申报》1901年3月22日。
(76)《粤督岑云帅除盗安良示》,《申报》1903年7月22日。
(77)《两广官报》,“军政”,辛亥年第8期。
(78)周鹗芬:《论清乡宜查察局绅》,《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21日。
(79)《岭南纪事》,《申报》1886年9月20日。
(80)《羊城仙迹》,《申报》1899年4月20日。
(81)《海天霞唱》,《申报》1904年12月20日。
(82)《独谭令能办清乡耶》,《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12月5日。
(83)《愈办清乡而贼匪愈横暴》,《广东时报》1911年7月12日。
(84)《顺德绅士禀请派员防剿之督批》,《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26日。
(85)《顺德清乡划分两路办理》,《广东时报》1911年7月13日。
(86)《准给开花炮剿匪》,《时报》1911年7月21日。
(8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83页。
(88)《这般清乡可笑,这般大举清乡尤可笑》,《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7月8日。
(89)《不忧清乡员弁滥刑只防清乡员弁索贿耳》,《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3月11日。
(90)《严饬地方官查察清乡各员》,《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9月19日。
(91)《在押委员蔡尧钦之罪状》,《广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八日。
(92)《委员果有此劣迹,非清乡直扰乡矣》,《广东时报》1911年7月13日。
(93)《清乡委员竟以因循敷衍了事耶》,《广东时报》1911年6月23日。
(94)《廷寄粤督查覆李准参案》,《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17日。
(95)《饶平清乡近闻》,《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96)《严禁藉捕为盗之文告》,《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20日。
(97)《高明清乡之骚扰》,《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8月14日。
(98)《派员密查营勇下乡之骚扰》,《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8月12日。
(99)周鹗芬:《论清乡宜查察局绅》,《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21日。
(100)《粤省官绅大会议清乡办法》,《时报》1911年8月1日。
(101)《广东之盗贼世界》,《时报》1911年8月26日。
(102)周鹗芬:《论清乡宜查察局绅》,《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21日。
(103)周鹗芬:《论乡绅交匪之难》,《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日。
(104)《论龚臬议就乡局改设巡警之善》,《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8月30日。
(10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5页。
(106)《粤督处死庇匪劣绅》,《时报》1911年9月27日。
(107)《顺德黄连乡又遭巨劫》,《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1月15日。
(108)《严饬地方官查察清乡各员》,《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9月19日。
(109)袁树勋:《奏请严禁缉匪花红永远裁革折》,袁荣法编:《湘潭袁氏家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14页。
(110)《时评(一)》,《顺德新报》第6期,宣统三年元月。
(111)袁树勋:《奏请严禁缉匪花红永远裁革折》,袁荣法编:《湘潭袁氏家集》,第114页。
(112)《营务处者枉杀城也》,《广东日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13)段云章等:《陈炯明集》上卷,第19页。
(114)《就地正法既不准,格杀勿论又如何》,《广东时报》1911年6月15日。
(115)《粤东弭乱感言》,《时报》1911年9月5日。
(116)段云章等:《陈炯明集》上卷,第106页。
(117)《禀揭清乡实情》,《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三日。
(118)可参见拙文《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的论述。
(119)王定安编:《曾忠襄公(国荃)批牍、年谱》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82页。
(120)《论粤垣整顿保甲事》,《申报》1892年9月30日。
(121)方濬师:《岭西公牍汇存》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537页。
(122)《论粤垣整顿保甲事》,《申报》1892年9月30日。
(123)《广东同乡京官奏请实行清乡团练折》,《时报》1904年11月7日。
(124)周鹗芬:《论乡绅交匪之难》,《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日。
(125)关于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及其效果,可以参见拙文《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26)《粤督处死庇匪劣绅》,《时报》1911年9月27日。
(127)[英]S·斯普林克尔著、张守东译:《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
(128)有关清末时期盗匪问题中的法律问题,将另文专题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