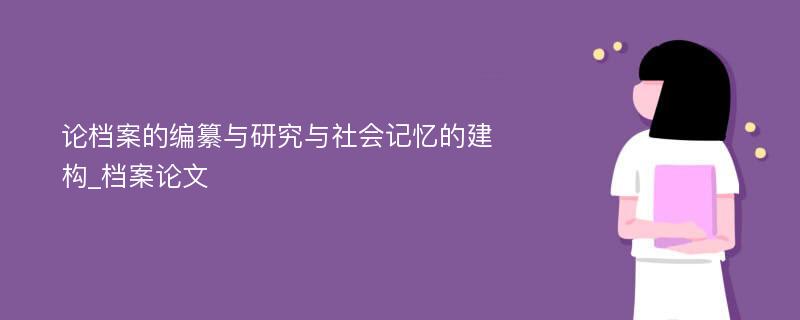
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档案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记忆”对于档案界而言早已不是新名词了,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还专门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近年来,档案界以保护和传承社会记忆为己任,开展了各类以“××记忆”为名的活动,旨在关注档案在社会记忆中的特殊意义,并借此进一步完善档案的形成和保护。本文试图探讨档案编研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重要性,以及为构建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对档案编研提出的要求。
一、社会记忆的构建需要档案编研
之所以特别讨论档案编研对社会记忆构建的作用,是因为档案本身与社会记忆并不能完全等同,档案要真正成为社会记忆,其中还需要经过社会认知、记忆重构的复杂过程,因此,能够使档案信息传播更广泛、可读性更强、社会影响力更大的档案编研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
1.“档案”不等于“记忆”
由于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真实的记录,所以人们经常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相提并论,以至于说到档案就自然地将其与社会记忆等同起来,“档案是社会记忆”、“档案馆是记忆库”之类的话亦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得到强调和重申,以引起各方对档案的重视。然而无论说这些话的语境和目的如何,从严格意义上讲,尽管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构建密不可分,但是“档案”不等于“记忆”。
从字面上看,“社会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其表现形式无非是一些文本记录、仪式和文物等,档案在其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形式毕竟是形式,“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并不是记录和史实本身,“社会记忆”不能和传统的文献记录划等号。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言:“集体(哪怕是家庭)记忆就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而是对过去的‘重构’。换言之,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构建。”①
较早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相联系的国际档案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不能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认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由于认识到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非中立性,便有可能“发生了一次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建构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②在这里,社会记忆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与历史角度相区别的更广义的看待过去的视角和模式,而此处“档案”只是作为历史记录被探讨在社会记忆的模式下应当如何形成。
由此需要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档案是重构社会记忆中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社会记忆传递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各种事物和行为,例如纪念仪式、身体习惯、口述历史以及包括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在内的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社会记忆虽然比历史具有更加非正式的程序和更广泛的文化分布,但历史之于社会记忆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减少因记忆控制或缺失造成的损害和信息衰减,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验,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所不能替代的优势。
其次,档案记录本身并不一定能直接成为记忆,而是需要经过社会选择、认知和情感认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社会记忆是社会化的心理、情感和知识建构过程,它与历史记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录可能一致,也可能完全对立,二者是相互补正、相互校验的。因此,在充分肯定档案对社会记忆的补正、保存和传递等功能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档案若想从历史记录成为社会记忆,必须经过社会的认知和情感认同的过程,这也是历史记录转化为社会记忆,或者说历史记录“社会记忆化”的必经之路。
2.被认知才能被记忆
尽管社会记忆的构建与形成过程和机制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被认知才能被记忆,特定的档案记录首先必须进入当下人们的认识和情感领域方能真正参与到社会记忆的构建中去。而与人们约定俗成的纪念仪式以及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等相比,档案作为一种形成和运转过程均具有一定封闭性的文本记录,其广泛传播、社会认知和情感认同更需要一些“推手”来促进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即为能够提升档案信息价值,主动提供档案信息社会服务,使档案信息广泛传播的编研工作。为了使档案记录在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有必要通过档案编研工作使档案记录的内容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得以认知,引起情感共鸣直至被“记忆”。
举例来说,现如今人们对清朝的记忆大多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以及相关的影视、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的,藏于档案馆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被社会所广泛认知的档案,则只能是历史记录,尚未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随着清代档案的公开展览,一些优秀的档案文献纪录片(如《清宫秘档》)和据此编纂的书籍(如《清宫档案揭秘》)的广泛传播,使社会公众对档案中的清代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于是公众的相关记忆中增添了相关内容。在此过程中,档案记录中的描写和记述得到广泛认知、理解及情感认同,从而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记忆。可见,尽管清代档案早已公开提供利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历史档案中存在了很多现代公众阅读理解的障碍,导致大多数人对这些档案知之甚少,所以档案编研在使这些档案记录“社会记忆化”过程中发挥的“推手”作用十分突出。
二、构建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对档案编研的要求
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的特点,在构建社会记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补正、校验、保存及传递作用。“在严格的意义上,社会记忆只有保证记忆能够传递才有意义”③,而作为一种刻写实践,档案记录本身就具有记忆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功能。所以,档案工作者有责任为构建真实、完整的社会记忆而努力,在档案编研方面则更应当注意这些要求。
1.真实记忆:客观选材、适度阐释
消失的或是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偏差的社会记忆如何恢复,档案记录是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相比其他文本材料,通过档案这种原始记录形成的记忆与历史的真实更加接近,档案编研在进行档案信息加工和传播时自然应当充分保持并利用这种优势。为此,档案编研应做到对档案记录予以客观的选材、适度的阐释,具体要求包括:
首先,选材是体现档案编研客观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选择即将广泛传播、影响社会记忆的档案材料时应当全面、客观,避免先入为主。例如,戊戌政变关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真实情况,袁本人在《戊戌日记》中有详细记录,而梁启超有《戊戌政变记》,倘若先入为主地认为袁是卖国贼,其日记不可信,而仅仅选择梁启超的记述,必会造成片面的记忆。而更严重地则是,事实证明,恰恰是袁世凯讲了真话,梁启超讲了假话。④这样一来,偏信所谓“正面人物”而选材的结果只能与想用档案补正社会记忆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应当基于述而不作的适度阐释原则,客观地梳理档案记录的历史背景,引导读者客观认识档案内容,避免纯文本阐释的负面效果;将零散的记录按一定的主题和内在逻辑组合到一起,系统地、联系地解读和看待档案材料;科学地考证档案内容,进行文字校勘注释,还档案记录以本来面目,便于读者认知和理解,等等。
2.广泛记忆:多角度选题和选材
社会记忆本身即是多维的、立体的、广泛的,由多个社会群体的多种集体记忆和无数个人记忆整合而成,如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于他们自己的集体记忆。在档案馆中藏有与各类群体和个人相关的记录,如何将这些记录用以补正社会记忆中的缺失和偏差部分,也是编研工作应当思考的问题。显然,通过展览和相关信息的编辑出版、公开传播,及时将档案中的历史记录公之于众,被更多人记忆,对于避免“历史的遗忘”而言,显然是比让档案深藏闺中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
社会记忆的广泛性对档案编研选题和素材收集提出了相应要求。首先,既然档案编研的意图是面向社会,被广大群众所认知并记忆,档案编研选题就不能仅仅考虑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为专家学者服务,还需关注社会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人群的需求;其次,在素材的收集和选择上,不仅应挑选出馆藏中的各类相关材料,还应当发挥档案编研一贯以来对社会材料的征集功能,通过广泛征用社会上各种官方的、民间的记录以及私人记录来丰富内容,使档案编研成果与社会公众紧密相连,使人们在档案记录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便于构建更加完整的社会记忆。
3.深度记忆:细节的挖掘
不难发现,现如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少不了一些记录历史细节的书,这实际上也是迎合了人们追溯记忆的一种本能和需求。历史教科书上看不到的细节往往却是重构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由于这些细节不为众人所知,而且通常更加生活化、通俗化,也更易被人们所接受、记忆和传递。“细节里面有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记忆。记忆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记忆细节。细节不但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心理奥秘。”⑤人们希望通过类似的记录来建构更加完整、真实、深度的社会记忆,而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历史纲目,档案记录中并不乏这样的细节,只是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挖掘。
由此,档案编研的选题应不拘泥于反映重大事件的宏篇大作,一些档案中的琐碎细节如果按照一定的主题和逻辑加以串连,同样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引起情感共鸣。如果说历史课本告诉人们结论,那么档案编研就应当提供生动、真实的叙事题材;如果说历史太多地过滤掉日常细微的生活与情感,只剩下位于主流的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那么通过档案的编研阐释穿连幸存下来的点滴记忆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4.生动记忆:形式的改变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社会记忆亦如是。然而,档案记录长久以来的形象似乎只是一些“尘封的历史”,即使已经可以面向公众提供利用,也鲜有人问津,导致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难以“社会记忆化”。对此,档案记录的内容自然应当更加丰富多彩,这在今后档案的形成中必将有所改观,同时,通过档案编研改变一些档案原件的刻板形式,增加其生动感和吸引力,亦不失为一种主动积极开发现有档案资源的有效途径。
基于档案原件的信息内容,编研人员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方法的加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赋予档案记录以崭新的面貌和生命,使历史中尘封的人物和事件鲜活起来,更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记忆。具体的方法包括:改变档案信息的体裁和叙事方式,如对平铺直叙的档案记录采取突出重点,悬念设计,故事化的叙述等方式使其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胜;转变档案信息符号形式,将文字转变为声音和图像等更为直观易明的形式;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如电视、报纸、书籍、网络等,扩大档案信息的受众群,增强档案信息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等。总之,通过编研加工,使档案信息被更多人“记忆”,从而充分发挥档案的“记忆库”功能,积极参与到社会记忆的构建中去。
注释:
①王纪:《有选择的社会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②[美]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构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
③[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④《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9日,D21。
⑤《记忆历史深处的细节》,《科学时报》1999-01-07总第14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