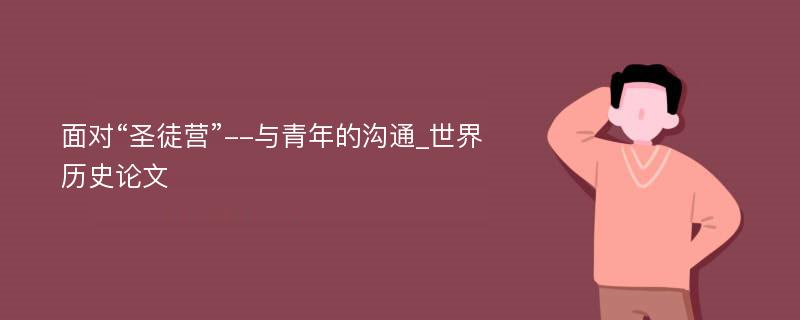
面对“圣徒的营地”——与我们的青年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营地论文,圣徒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初,当我们开始策划这次调查时,我们想得很简单。鸦片战争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了,中日甲午战争过去一百年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快五十年了。人们在忙忙碌碌地生活,而中国的一些基本问题似乎仍未解决。一位中国作家忧虑而激奋地写道:“不改本性的西方学界幻想中国变成一堆无能而献媚于他们的小国”。他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一些外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具体计划,考虑把中国分成十五块还是二十块;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已经有创见地发现,“统一比分裂好”仅仅是一个“常识的谬误”。对于这一切,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未来,中国未来的主人——中国的青年们到底怎么看?毕竟,未来是由他们决定的;毕竟,他们的生活取决于中国的未来。但也许,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遥远的:历史上的战争,他们只从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也许还是作为一种消遣收看的。未来,又有谁知道呢?即使是现在,据说他们已是相当“个性化”的一群,关注自己的发展超过一切,对于“中国与世界”这样的问题已不感兴趣。
情况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对我们的青年搞一次调查,看看那次战争对于他们还意味着什么,看看中国对于他们还意味着什么,看看他们究竟怎么看今天的世界。以此作为我们对于那场使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的大战的纪念。
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促成我们的问卷于5月30日公开见报了。随之而来的四面八方的反应使我们这时才意识到,有意无意间我们已做出了中国新闻界此前还没有记录的事情: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第一次调查了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主要是政治历史问题)的看法。
见报当天,本报社调中心的电话铃声前所未有地响个不停,人们多是询问可不可以复印、复制我们的问卷;询问我们对年龄有什么限制,不是青年了还可不可以参加答卷;北京地区的读者询问到中国青年报的路怎么走……
第二天,5月31日,200多封信到了。
第三天,6月1日,一下子涌来2000多封信。
再往后,每天加上三个小时的班,都已弄不清当天究竟到了多少封信。负责回收统计的同事只能记个大概数,比如“两麻袋”、“四麻袋”、“八麻袋”。
按省分拣、拆封、打号、编码,随着回寄量“加速度”的增长,报社越来越多的同事志愿加入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的应届毕业生们每天穿城而过来报社帮助工作。
问卷刊发后的第七天,全国除港、澳、台外,各省级行政区都有读者寄来了他们的回答。到6月20日,我们的统计数字已由五位数跃升到了六位,超过了10万份!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星期,社调中心的邮件仍是全报社最多的!
开始我们还为这种出乎意料的反响雀跃,越往后一天比一天心情沉重:十几万热心的青年,把他们的答卷交来了,我们的答卷怎么写?有那么多的青年在来信中希望我们“一定如实地统计出结果,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青年的看法”。
7月14日,调查结果以数据版的形式见报了。在很短的时间里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世界几大通讯社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报社即对此做出了反应,将中国青年对“二战”等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予以了迅速的转发、转载。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驻华机构也开始不断将电话打到报社,希望能“交流”一下信息和看法。
一位国内的朋友看了我们的统计数据后,第一句话问:“你们的数字是真的吗?”我们说:“是真实的。”这位朋友的第二句话是:“这么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感觉。在我们陆续发表的分析报告里,我们力图保持客观和冷静,这是社会调查的“职业规范”。但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在我们即将结束这一调查及系列报道的时候,我们想写下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和那十几万名曾向我们敞开心扉的读者交流。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青年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中国贯串绝大部分世界历史,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是把西方文化的特色同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物以及作为欧洲文明的现代中心的法国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2000多年来,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具有高度文化修养,极其多样化并富有经验;具有控制、协调和处理人口众多的大国的能力;有效地使用应用技术去提高生产和维持比19世纪欧洲国家大许多倍的人口生计的组织才能。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胜过其他地方。
“在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许多特征方面,中国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主要以功绩为基础的官僚机构,直到19世纪这还是一个有效能的样板。它可能在效能方面仍旧是一个样板,以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个人来处理大量的问题。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人已表明他们具有理财、安排劳力和为创建公共事业而进行必要的资源计划的能力,并已达到直到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尚未达到的水平。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拥有一个至少是理想的‘开科取士’制度,在这里主要依靠教育和功名来取得晋升。尽管2000年来这个制度一再地被大肆诋毁,但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超过它的东西存在。不论‘高度文明’一词意味着什么,中国早已创造了它,至少比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人和西方人要早。的确,未来世界的学者会认为,欧洲在16世纪或17世纪以前也许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种族优越感和对难学费解的语言的厌恶学习能够说明这样的感觉,欧洲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是相等的,说不上哪个更优胜。中国已经表明,在学习和吸收他人乃至征服者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就一个非现代社会来说,中国的文化程度极高,工商业和市场也很发达。最后,在约翰·杜威实用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西方现代化批判的基本原理的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已在2000年前为中国所接受了。”
这是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于中国文明的评价。请原谅我们引用了如此之长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评价,因为这样的评价如果由我们自己来写,也许会受到许多指责。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书架上,在我们周围的学界中,实在找不到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明的公允评价。旧有的赞颂之词早已被认为是陈词滥调,新的智力又多被投入到寻找中国文明的“劣根性”上面。因此,我们不得不借用外国人的评价。然而,对于中国文明的最终评价,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做出,对于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
然而,中国人爱中国吗?一位美国教授到中国讲了几个月的课,他临走时说:“中国人都爱美国。”这位美国教授的话全面还是片面且不评说,我们注意到,当国内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中国人最钟爱的国家仍旧是中国时,却曾有人评说:“中国青年太封闭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部世界有多精彩。”“他们这么回答,只不过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爱中国吗?我们有时也搞不清。我们平时听到的,太多是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明,对于中国人的不满和鄙夷。我们猜想,许多在填写问卷时表达了爱中国的感情的中国青年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中国青年与他们一样,也爱中国。但绝大多数中国青年确实是从心里爱着中国。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应该不应该爱中国?为什么爱中国?怎么解释爱中国的感情与对中国文明的批判?
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伟大的,这一点世有公论。作为中国人完全可以为此自豪。当然,中国的古代社会并不是天堂,那里有不义,有专制,有酷刑,有饥荒,有战争;但是,当我们对此进行理所当然的谴责时,我们不该忘记,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超过中国文明的东西存在。中国在近代落后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赶上去。今天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文明是强势文明,而中国文明不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中国文明。因为当你对于一个文明进行评价时,你的尺度必须是几千年,而不是几百年。而在几千年中,中国文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领先于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当西方文明以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球时,多少古代文明殒落了,而中国文明没有。它应战了,进化了,重新站立起来了,多半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你可以说,中国在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时,没有日本适应得那么快,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一生,对于我们上下几代人来说,确实影响重大。然而对于一个文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瞬。我们的思想界,对于中国文明的批判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我们也不能不向我们的青年,向我们的后代指出:在评价中国文明时,切忌以蠡测海、轻易定谳。
近代以来,外侮频仍,国运不举,以致在中国对中国文明进行正面评价竟成了一件易引起“众”怒的事情。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没有展现:它富有进取精神,力求在自我批判中前进;它宽容,容许对于自己的指责乃至诋毁;它也强大,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攻击。无疑,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文明的批判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在这里只想告诉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后代,在对中国文明进行批判时,不必丧失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信心。
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史,十二亿生生不息的中国人,足以使每一个炎黄子孙不须妄自菲薄,更用不着挟洋人以自重。
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家园
近几年在我们和其他一些机构所做的多次社会调查中,中国青年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强烈的爱国心。中国青年为什么爱中国?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自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家园。这是大多数中国青年切身感受到的东西。
有人会说,现在的世界正走向全球一体化,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仅仅因为是中国人就爱中国,这未免太狭隘。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些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实在还不全面。我们无意贬低这个世界在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取得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个世界仍旧是划分为民族国家的。国与国之间的界线,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线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事实中更多的是远不那么浪漫的政治历史成份。
我们的调查显示,我们的青年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并不那么想当然。这使我们感到欣慰,也使我们有些惊奇:已经很少有人谈论这个据说正在成为地球村的世界不那么浪漫的一面了,他们从何得到这些现实而冷静的观感?然而,我们不谈论的一面,西方人倒是在坦率地谈而又谈。
“现在,那支来自地球另一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舰队已经布满了大约五十码开外的空旷的海面,这是支布满锈斑、吱嘎开裂的舰队,老教授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在看……他把眼睛贴近镜片,他首先看到的是手臂……他开始数,冷静而不慌不忙。但这是一片手臂的森林,无法数清,那些手臂高举着,一起在空中挥舞,全都伸向附近的海滩。皮包骨头的枝桠,棕色的和黑色的,为一丝希望所激动。全都裸露着,这些瘦如干柴的甘地的手臂……一只船上就有三万个生灵!”这是一幕恐怖的场景,这些瘦如干柴的生灵最后淹没了海滩,淹没了西方的城市,淹没了整个西方文明。
这幕场景出自一本22年前出版于巴黎的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这本书在当时受到谴责,因而流传不广。然而,最近又在西方世界受到政治学者乃至反移民团体的重视。作者拉斯佩尔(JeanRaspail)在该书的前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创作这部幻想小说的缘起:“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的唯一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锇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
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我们的一位中国学者说:“我过去没有想到西方人的心理这么阴暗,我们中国人应该知道西方人是怎么看非西方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读了这些材料,我们并没有觉得西方人应当受什么责备。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存空间,无论过去是怎么得来的,今天,这些毕竟已是他们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别人分享,不愿意像辛德勒那样用自己的财富救人一命,也很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认为这部小说确确实实坦率地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存在着两个(或许更多)营地,一个是西方人的营地(“圣徒的营地”),另一个是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的营地。那个幸运者的营地不愿意接纳不那么幸运的人。如果幸运者们愿意像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伸出手来帮不那么幸运的人一把,自然是好事。但就“圣徒的营地”之外的人们来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
我们并不否认,在西方存在着另一种思想,这就是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着力介绍的,被称为之“丰饶世界”(Cornucopian Hopes)的自由派思想,即通过市场力量、政府干预的日益减少,精益求精的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消费市场的建立相结合,会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全球繁荣”,全人类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断的现代化使得全球的生产与生活水平趋于一致。
但是,正如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和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评论《圣徒的营地》时提出的那样:“即使是最狂热的自由市场原则信奉者,也回避了主张任何数量的人口都应该被允许在这个星球上自由移动。”因此,自由派的思想中就有了一个被淹没在华丽的词藻和貌似严密的逻辑中的不易为人所见、却是致命的缺陷:只要人口的自由移动是不允许的,只要你去美国还得办那极难得到的签证(你要留下来并找职业就得拿到那张更难到手的“绿卡”),“地球村”的假设就并不成立。
还须看到的是,西方世界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一点我们的调查显示我们的青年似乎已经看清了,但也有人还是存着糊涂的良好幻想。上述两位美国学者坦率地指出:“下个世纪初,拉斯佩尔的‘7亿白种人’很可能面临两个非常不同的挑战:非洲的崩溃和亚洲的崛起。”西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世界其他部分过上好日子的。他们既怕世界其他部分太贫穷,以致人们都挤到他们的营地讨生活,又怕世界其他部分发展快了,会威胁到他们的优越地位。
既然存在着不同的营地,既然我们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可预见的将来必须在自己的营地中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爱我们的营地,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唯一的家园。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就没有中国人的地位。这是现实,决不是什么“狭隘”。即使是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爱我们自己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2亿人口的家园,把它建设好,也堪称是对于世界的巨大贡献。如果我们考虑到西方学者提出的上述背景,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主义者对于世界和平很可能比“地球村”论者更有实际的贡献。
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
中国,这个中国人唯一的家园的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青年对此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和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巴西这些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优越的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很少的。和日本及欧洲那些资本高度密集,科学技术与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资本基础是薄弱的,我们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是落后的。不要说达到西方世界那种过度的丰饶,就是让12亿中国人都过上安定、体面的生活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毕竟已经为我们建设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理解,中国青年在此次调查中对于中国的未来表示出的乐观,不是别的,而是意味着一个认同:走向21世纪的中国青年将为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他们将把21世纪的中国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一定是最富裕的,但它将是伟大的。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青年中的绝大多数认为国内的安定团结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最重要因素。不仅仅是中国青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稳定是人权的基本保障,没有稳定就没有人权。而统一是稳定的必要前提。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群体聚合到了一个国家之中,这是中国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抛弃这一宝贵的遗产,必将使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陷入
这样那样的纷争;分裂的政治实体和分裂的市场将使我们的后代子孙在一二百年之内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无论西方人和中国那些有创见的人说些什么高明的主意,中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基础比之西方国家,甚至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是薄弱的。因此,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要走的道路是艰巨的,也许还是独特的。我们的经济必须较快地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靠不断地加大投入维持,而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就此而言,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科技昌明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高低。这个社会的行政体制应该是廉洁的、有效率的。这个社会的新闻媒介应该是有道德的、主持正义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建设性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文明在建立相对进步的现代国家制度方面的成就和启示,然而,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演进也不能割断其与该社会所内在的文明和历史轨迹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创造性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社会血肉相联的现代国家制度。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能保卫自己的社会。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中国人更应记起我们的前辈在那次大战中经历的屈辱与苦难。3500万死难与伤残的中国人命令我们建立一个足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国防。我们的调查显示,今天的中国青年仍旧崇敬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无论他们有过多少失误,他们毕竟把一个在近代受尽欺凌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了外国的入侵,中国人民也不用担心遭受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苦难。中国人永远缅怀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认同于他们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远见卓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着不义者侵夺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可能,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强大得足以保卫自己。
最后,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还将是一个胸襟开阔,与世界其他各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处、平等交往的社会。中国的文明具有博大的胸怀,在历史上,它曾以比西方文明远为开放、远为慷慨的善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它没有以自己无比强大的力量奴役他们,而是容许他们在这片高度文明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从而形成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今日的中国,已不处于那种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前景,也将因此而更为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