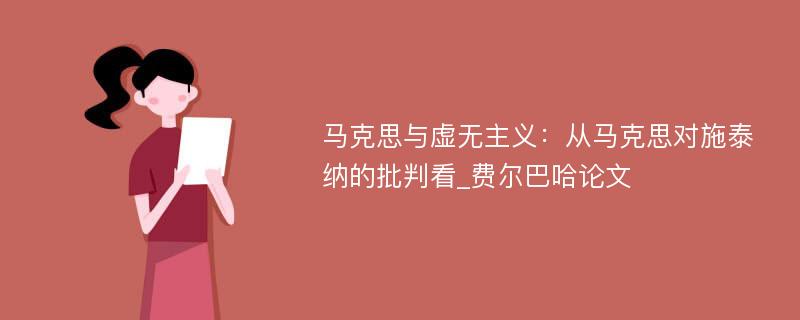
马克思与虚无主义: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角度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虚无主义论文,角度看论文,施蒂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对实践的崇拜、对经验世俗的崇尚、对超验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伴随着汉语思想传统中道德意识的弱化和本来就有的对实用理性的崇尚,促使当代中国思想对世俗性存在的崇尚不断加强,而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也在急剧扩展。作为这种扩展的结果,“反对超感性价值,否定它们的存在,取消它们的一切有效性”的虚无主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如德勒兹所说,这种反对和否定“不再是借更高价值的名义来贬低生命,而是对更高价值本身的贬低。这种贬抑不再指生命具有虚无的价值,而是指价值的虚无,指更高价值本身的虚无”。(德勒兹,第217页)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而今日益兴盛的虚无主义苗头,与对形而上学和超验性存在的拒斥、对“现实性”或世俗性的弘扬彼此呼应,并相互强化。
施蒂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以虚无主义问题与马克思遭遇的思想家。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思想最先遭遇到施蒂纳时,因为当时没有虚无主义问题的困扰而是在寻求反封建反宗法的支援意识,所以把他看作是反权威、扬个性的斗士,那么,正在遭遇虚无主义困扰的当代中国就没有理由再误解和轻视他了。鉴于施蒂纳而非费尔巴哈才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后影响了马克思的人(麦克莱伦,第141页),而马克思在某些方面又接受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同时,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65%的篇幅是用来批判施蒂纳的,而只有大约10%的篇幅才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所以,我们再继续轻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而仅仅关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是一个重大缺憾了。虽然如洛维特所说,施蒂纳与同期分析同类主题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尼采相比不够优秀,甚至还“差得远”(洛维特,第28页),但施蒂纳对虚无主义的更早发现,以及与马克思的直接相互交锋,使得马克思对施蒂纳虚无主义的批判显得更重要。如德里达所说,凭施蒂纳的独创性和勇气,或他的哲学-政治学的严密性,“即使没有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没有反对他,施蒂纳的著作也是应该阅读的”;加之海德格尔后来曾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见费迪耶等,第59页),而施特劳斯又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仍是一种精致的虚无主义,由此,马克思批判施蒂纳虚无主义的篇章获得了更强的讨论价值。
普遍性与神圣性、本质性相通,而现实性更多的是与特殊性(个别性)、尘世性相通。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结构中思考问题,恰是从一种普遍使命出发来思考对待现实之态度的哲学所必然面对的根本问题。普遍性的本质如何应对特殊性的现实?神圣性的崇高存在如何应对尘世中的粗俗现实和低级存在?整天与纯粹的本质存在打交道并思考普遍性存在的理论(哲学),如何应对以特殊性和个别性为特质的经验现实?以普遍性神圣本质存在为伴的哲人如何应对在日常存在中无法上升到普遍本质、而只能滞留在经验个别和世俗层次的大众?进一步地说,自从路德开始在经验现实中寻求神圣、确立信仰以来,自从笛卡尔要在自我内部挖掘内在的神圣以来,这种把人内在的神圣性本质发扬光大的思路,应如何看待作为经验主体的“人”——不管是笛卡尔式的思考者,还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者、费希特意义上的行动者,抑或马克思意义上的群体行动者——之内在的神圣性?如何看待其本身具有的能够依托起知识与行动的确然性、能够成为某种承担起多重负荷的原始基质的特性?这种人应如何确定自身?他能确定哪些东西为自己内在的神圣?为了实现这样的神圣,经验现实必须作出什么样的让步或改变?这些问题一直是力图弱化甚至弃绝主体的神圣性、超验性和普遍性维度的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施蒂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激进地询问:“人”何以要把神圣性当作自己的内在品质、甚至内在本质?把这种以前放置到“人”身上的所谓神圣性品质拿掉,不让它成为人活动于世的负担和累赘,让“人”自身轻轻松松地按照当下即是自由生存不行吗?
施蒂纳正确地看到,两千多年来,在西方人们总在致力于使原始神圣的精神还俗,路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致力于这一点,其策略就是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在世俗存在中发现神圣性。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其终点就是把神圣性彻底置换为世俗性,以世俗性完全取代神圣性。这也许就是最为激进的拒斥形而上学、拒斥现代性的策略。下面将会说明,对这种激进的选择马克思采取了怎样的批判性态度。
二、施蒂纳的路向
如果说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追求抽象过了头,那么施蒂纳对抽象的拒斥过了头;费尔巴哈对“人”的规定不够现实,施蒂纳则是在这方面现实过了头;费尔巴哈仍未走出形而上学,而施蒂纳则危险地彻底抛弃了形而上维度。马克思的立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开辟一个有效的历史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搭建一个现代构架,使费尔巴哈虽努力却仍未能发现、而施蒂纳匆匆走过却埋没了的那些启蒙价值,在这个构架中展现出来,获得较为充分的实现。
施蒂纳当然并不认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以纯粹主体为指向的主体概念,也不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对这个主体概念的重新解释,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解释。对他来说,这些思想家所谓的“主体”都是普遍者,都是以某种普遍的存在压抑、贬低和诋毁人的特殊性、个别性、惟一性,而他的“主体”则只是指人的个别性、惟一性和特殊性的存在。他用惟一者(Einiger)替代自我(Ich)。这个“惟一者”,实际上就是费希特所谓既不与外物也不与外人有任何关系的纯粹自我主体,在与外物和外人必然具有关联的现实世界中的激进投射。所谓激进,就是在与外物和他人必然具有关联的经验世界中力图摆脱掉必然性的关联,仅仅保证一种偶然的关联,一种以自我的偶性、任意性、随机性和不知因为何种原因变化的境况为转移的不确定性关联,即没有任何必然性和确定性关联的自我任性状态。康德、费希特所谓不与经验存在发生关联的纯粹主体,只是一种超验性存在,令人想起上帝的圣洁存在。在现实社会中,康德和费希特都非常清楚,这种既不与外物也不与外人有任何关系的纯粹自我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施蒂纳想必也肯定知道它无法纯粹地在现实世界中立足。他不会要求他的“惟一者”与外物和他人切断任何关联,而只是要求惟一者与外物、他人切断任何必然性的关联,不能纠缠于物质事物,不能跟着他人走、被他人同质化:既不能成为物质事物的奴隶,也不能成为他人的奴隶,包括不能成为他人相互认同的某种理想状态的个体或集体“人”的奴隶,更不能固定地成为某种物性存在或某种群体的同质化成员,把自己委身于一种靠思想虚构出的神圣共同体而丧失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施蒂纳要求他的“惟一者”也不能与他人共同痴迷某种思想、原则和理念,因为一旦如此,也就意味着变成了与他人同质化的模式人,丧失掉了“惟一者”的基本品格。这也就意味着,“不盲从于他人”也包括不与他人共奉同一种“思想圣物”,不让这样一种“圣物”奴役自己。既然无法从根本上彻底切断与物质事物和如此之“思想圣物”的关联,那就致力于把这些物质事物和“思想圣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有兴趣时把玩一下,不喜欢时一脚踢开,什么东西也别想让我为它服务和牺牲;个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最有价值的存在,任何存在都不能置于个我的前面和上面。
按照施蒂纳的逻辑,真正自主自为的存在(即“主体”的首要含义)首先不能是物质事物的奴隶。纠缠于物质事物的主体,不是真正的自主自为者,而且这种屈从于物质事物的生活,是落后于近代的“古代人”的生活或儿童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写照。当人认识到真正的生活不是与事物斗争的生活,而是同事物分开的、仅仅是内在性的生活时,他就成了近代人。近代人开始不为物质事物、而只为“人”自己存在。施蒂纳也体会到,这种“自我”(Ich)、“内在性”、“精神”具有一种神圣维度,包含着浓烈的神圣性。为了战胜死亡和外在生活的无意义,每个人都必须充分发动自身具有的这种神圣力量。这种神圣力量当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在性之中。当这种“精神”从近代启蒙哲学和浪漫主义所界定的个人主体身上,转向后来民族主义、阶级论所主张的群体主体身上时,群体成员所认定和主张的那种“精神”就更为强烈——施蒂纳从中看出一种平庸性(Mittelmaessigkeit)并以此作为理由之一而拒斥它:被崇奉的“精神”不但仍然是某种压抑个我真正的自己的普遍之物,而且越来越演变为某种平庸的、无个性的东西。
作为从青年黑格尔派中杀出来的施蒂纳,深切地体会到如下的思想“进步”链条或逻辑:第一步:外在于主体的神圣上帝的高高在上,没有渗入主体自我之中;真正的主体是上帝,“人”还没有主体的品格。这是现代思想开始前的逻辑,是现代思想所反对的起始点。第二步:神圣维度渗入主体自我之中,成为主体本身的一种内在品质;主体本身成为一种自主自为的神圣性存在,比如采取绝对精神的形式:这样的主体就是有了肉身的上帝,仍然高高在上。从笛卡尔到黑格尔都处于这种状况。第三步: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批判这样的主体,把神圣存在还原为“人”、“类”、“自我意识”。即拒斥了过于超验性的神圣存在物,迎来了仍然含有神圣维度和普遍性维度的某种理想型存在,如“类”、“自我意识”等。但是,施蒂纳认为这仍然还不够,应该继续向前走,因为这些“人”、“类”、“自我意识”中仍然隐含着明显的神圣性和普遍性维度,这个维度仍然高高在上地对个我构成压迫性的、威胁性的存在。对施蒂纳来说,从纯粹的、与主体人处于不同层面的神圣性存在一步一步向现代的迈进,其最终的逻辑结局就是第四步:把主体身上的神圣性、普遍性维度完全剥离掉,使每一个个体自我完全自由地存在和“发展”自己。在第四步这里,作为个体人的“自我”才真正具有完全的自我完满性、完全的自足自立性,自己凭借自己的内在所有,能够不借任何外物便足以自我规定、自我支撑、自我存在。在施蒂纳看来,这才是笛卡尔开始的主体自我沿着现代演变路线进步的最后的逻辑演化结果。他相信“自己比别人预先看到了这个即将发生的历史步骤”,相信自己发现了未来。他由此狂傲地呼吁,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中,每个独特的自我都将成为自己世界的所有者。这就是黑格尔那世界历史不断发展论的最后一个推论,即精神发展继政治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和人道的自由主义之后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最终阶段的开始(见Lwith,pp.134-135)。在这个阶段,真正值得自我崇尚的存在——与众不同的个我,才真正替代物质事物和思想事物成为自我主体的立足根基和价值目标,并从而使得崇尚自己的个我真正摆脱了受制于他者的奴隶状态。
施蒂纳早早地看到了后来霍克海默、海德格尔等人用不同语言说出的如下状况:主体性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化,使得个人主体的自主性与个性丧失了,一种平均性、平庸性的生存伴随着安全、例行化的增加与强化而日益甚嚣尘上。这足以构成施蒂纳反对在群体意识形态中存在的“思想圣物”的理由。他看到,日益大众化的现代社会对个人自由、个人独立的弘扬,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国家保护个人、个人依赖于国家、国家对个人进行压抑和统治的情形。如洛维特所总结的,“法国革命不但没有解放市民社会,而且相反,却导致产生出了一种听话、温顺和需要保护的国家公民。”(Lwith,p.314)个人的这种依赖性与个人的平庸性密不可分:现代市民都相信金钱是真理,期求国家或社会的保护,希望过温顺、平庸的生活——在他看来,市民阶级的原则既不是在先的出身,也不是共同的劳动,而是平庸性:一点出身、一点劳动,而自身不断生息的财产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对施蒂纳来说,处在这种生存状态中的人都处在空无中,都失去了任何崇高的价值,是平庸性的甚嚣尘上,而不是什么解放与自由。这就是崇尚普遍精神性的内在主体论沿着启蒙逻辑不断运作的必然结果。崇尚内生性普遍主体的现代性运作使个人主体最终仍然受制于世俗的国家、社会,仍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三、马克思的一个批评
“惟一者”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实际表达。作为这样的表达,它仍然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施蒂纳的这些思考根本没有超出他所在的资产阶级社会。毋宁说,这仍然是施蒂纳所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状况的某种反映。施蒂纳推崇的那些“独自的东西”如自私、自以为是、坚持己见、特殊性、自爱等等,不都仍然是小资产者日夜盼望实现的理想吗?在施蒂纳主张的个性、独自性后面,仍然隐藏着私有财产这种普遍性力量的支撑。所以马克思说:“现实的私有财产恰好是最普遍的东西,是和个性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直接破坏个性的东西。只要我表现为私有者,我就不能表现为个人——这是一句每天都为图金钱而缔结的婚姻所证实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3-254页注释)施蒂纳激进地否定掉物质财富对个性的意义之后,支撑“惟一者”的实际上就只剩下非普遍性的思想、精神、态度了。马克思批评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的话也可以用到施蒂纳这里:“力量就在它们的意识中,因为它们是从自身中、从自己的行动中、从批判中、从自己的敌人中、从自己的创造物中汲取力量的;人们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获得解放的……”(这是典型的内在性自我观),“遗憾的是,终究还没有证明,在其内部,即在‘自身中’,在‘批判’中有什么东西可资‘吸取’”。(同上,第106页)无甚确定性东西可取,这就是虚无,在虚无世界中当然怎么都行;可一旦迈入实际生活,那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施蒂纳论述独自性的整个篇章:“归结起来,就是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从而聊以自慰。”(同上,第358页)
一切都是“惟一者”自我的手段,包括别的“惟一者”在内。主张多样性、否定掉普遍性的统一规范之后,不就为弱肉强食原则开路了吗?不就陷入了一种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普遍性是否存在和需要,直接影响到高贵个体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问题。尼采说过,普遍的平等依赖于一个高于我们的“神”,在它面前我们才是平等一样的。“没有高人们,我们都相等;人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相等!”(尼采,第291页)“神”或“上帝”在这里就是一个普遍的元代号,为所有的个体提供一个元根基的符号。依靠这种利奥塔所谓的元根基,或施蒂纳所谓的“思想圣物”,平等才会成立和存在;而一旦否定掉这个根基,平等也就被弱肉强食取代了。形而上学维度的彻底消解,就会直接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这是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时早已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
针对施蒂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马克思强调普遍性秩序的意义。基于主体的惟一性反对其普遍性,并由此反对基于“他者”、“非我”而设置的法律规则,在马克思的眼里,这就是在否定现代法权的进步意义。对此,马克思指出了两点:(1)法的关系最早反映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粗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当这种关系“不再被看作是个人的关系,而被看作是一般的关系”后,“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普遍性在这里与其说标志着统治性,不如说标志着文明性。(2)以拥有独自性的“惟一者”个人来反对普遍性蕴含的统治性,势必得出一个只对个我有效的道德戒条,“即每个人应为自己找求满足并由自己来执行刑罚。他相信堂吉诃德的话,他认为通过简单的道德戒条他就能把由于分工而产生的物质力量毫不费力地变为个人力量。法律关系与由于分工而产生的这些物质力量的发展,联系得多么紧密……”(同上,第395-396页)这种类似于后来尼采的路子充其量只能适用于少数的“超人”,而无法成为更多人的生活选择。
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获得社会关系的支持、获得更发达和充实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才是个性实现的必备前提。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马克思很明白,个人自救的方案是不适用于劳动阶层的。在生产关系不够发达的水平上,独自性实际上就是社会性在分工体系下强加给个人的,而且与个人的出生家庭、地域等等偶然性情况直接相关。没有普遍法则保护的独自性和个性,可能只是不发达、不完善的社会关系很偶然地加在个人身上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施蒂纳把社会性“加给个人的偶然性说成是他的个性”(同上,第508页)。这也就是说,不分具体的历史场合,不看看是否具备必需的社会物质条件,就一味地主张惟一性,很可能会陷入荒谬。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惟一者”的某些特性,其实在获得了社会历史的根基之后,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马克思所改造而接受的,如形成人的多元性、完整性,上午打鱼、下午作诗、晚上批判;这个根基就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呈现的自由时间和社会关系的普遍规则,而不能凭空想象,不能当下施行。
四、神圣性维度的保持与价值内在性
自康德以来,近代实践主体的普遍性维度中就蕴含着一种超验的目的、价值。实践主体不但要把自己的准则普遍化,要使这些准则能被所有的理性存在者作为律法接受下来,而且也蕴涵着一种普遍的目的在内。实践被规定为实现或趋近这些普遍目的的行为与过程。以下诸种普遍目的:自由自主,不受他物统治尤其是不受自己创造的客体统治(非异化);所有人在目的上平等;生存具有整体性;在自己与他人相同的普遍性生存得到基本保障并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使自己独特的个性能够实现,自身的创造性潜能得以发挥,自身内在的各种主体性品质可以得到全面而非片面的发展,等等,都是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德国浪漫派那里继承下来的实践主体的“普遍目的”。以生存的整体性为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这种整体性反对的是两种片面性,即作为抽象公民的“政治人”和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人”。这两种“人”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残缺的,当然不足以支撑起解放和自由来。缺乏社会经济根基的“政治人”的片面性不言而喻。而“经济人”作为陷入分工体系中的个人,就是与生产力分离的大多数个人,就是生产力不属于他们反而逼迫和压榨他们的那些人;而与生产力分离就意味着“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同上,第75页)。这种人与作为公民的政治人一样,也是抽象的人。不过同时,马克思说,生产者与生产力的分离并非彻底的分离,他们还通过劳动与生产力保持着某种联系,只是劳动者对这种劳动不能自控和自主,这种劳动只是维持生命的必需手段:“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惟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同上)只有自主的劳动才能够支撑起价值理想;把“普遍目的”建构在自主劳动的根基上,才能为那些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价值理想奠立一个经验性根基,使它不再表现为飘在空中的“抽象”。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普遍目的”原来被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放置在“纯粹主体”、“绝对自我”、“绝对精神”、“原我”等内在性主体之中,那么在否定了作为哲学原点的“纯粹主体”、“绝对自我”等内在性主体之后,马克思把它们放置在哪里呢?它们被放置在哪里才能确保其生存下来并生根、发芽?
这里涉及到两个重要的、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是否批判了以及是如何批判内在性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谓“现实的人”。
我认为,通过批判施蒂纳,马克思对超验理想价值生根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很明白,这就是存在于“现实的人”之中。“现实的人”不是仅仅盯住现实之物、没有超越性理想追求的人,而是顶天立地的人,即既立足于现实大地、又内心中装载着价值理想的人。“现实的人”中包含着一种超验价值的内含。这一概念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像学界近年来较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完全拒斥内在性形而上学,反倒是在价值理想的维度上赞同和认可了某种内在性超验价值。
对“现实的人”,张一兵教授曾指出,施蒂纳“的惟一者是现实存在的个人”,“施蒂纳的这一观点直接被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张一兵,第421页)。其意思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稿原是从客观的社会总体出发来确定“人”的,而第四稿则直接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行论说了——这是马克思看了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后受其影响所致。这一观点非常重要。虽然沿着“现实的个人”这个起点走下去,最后到达的仍然是使“人”成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劳动(活动本身、关系系统及其他条件),而“现实的”一词就意味着要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某些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塑造,从而使人自身的“现实”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相互牵扯和相互塑造,而不是仅仅挖掘自身内在的、独有的东西并使之生发和成长起来;如阿伦特所说,“世界的现实性是以他人的参与及自身向所有人展现为保证的”(阿伦特,第199页)。但“现实性”的含义就如此简单吗?现实性能完全退到尘世性之中来解释吗?也就是说,“现实性”之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的神圣性维度的内涵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恰恰体现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与“从客观的社会总体出发”的区别。
尼采认为驴子和骆驼是现实的:它们只能感受到自己身上背负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称为“现实的”,对这种现实的肯定只能是忍耐、默认、自我负担、承受。施蒂纳的意思也差不多。如果说施蒂纳会对他自己的“惟一者”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作出区别,他肯定会说,“现实的人”如果不追求惟一性,不把个性和特殊性当作自身的立足之本,而是向大多数的他者、向普遍性和整体性作出诸多妥协,那么他就会滞留于平庸性而超不出资本主义社会,超不出自由主义的巢穴。“惟一者”的惟一性意味着拒斥和摆脱种种社会性联系对自己的纠缠,拒斥和摆脱强制性的活动,意味着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崇高。马克思对此肯定不认同:他会认为,即使有对现实之物的忍耐、承受、默认,那也只能是暂时的,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摆脱这些不公正的背负而达致轻松的、共同的自我实现所承担的历史代价。也就是说,对现实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当下迁就和肯定,并不意味着对超验理想的背弃和忘却,而只是为了更好和更进一步地实现它而在当下所作出的一种辩证行为。换句话说,“现实性”的含义之中包含着一种拒斥纯粹世俗化解释的意蕴。它表明,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迁就、对世俗性存在的认可必须与对某种超验价值理想的认同和追求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否则,放任世俗性,让其主导一切,就恰好等同于反对崇尚物质事物的施蒂纳了。在马克思看来,人没有背负是不可能的,对人的整体使命的背负和以此为基础的极少数人的放松——这恰是施蒂纳的主张——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富有历史使命感、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群体,往往与某些群体丧失这种使命感、责任感,丧失这种创造历史的能力,并陷入贪图享受、逃避责任、能力颓废直接联系在一起。对主体的普遍性维度和神圣性维度的放弃,恰恰就是这种贪图、逃避和颓废的表现。
所以,在思想上,在是否保持“人”的神圣维度、是否保留施蒂纳所谓的“思想圣物”这一点上,马克思不但不认同施蒂纳,反而通过激烈地批判施蒂纳而在思想路向上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更为接近,即:必须保留一种神圣维度于“人”的规定性之中,必须拒斥否定现代性基本目标和价值的虚无主义,否则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就会没有根基,维系于某种合理的价值理想并力主向实现这种理想的国度逼近的社会发展论就会被多元并行或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价值主张所取代;从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也就没有必要了,也就可以被施蒂纳的“真正的自我利己主义”所替代了。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的“惟一者”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
五、形上学批判的限度及结论
许多学者用“感性的人”注释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其道理是相似的。从施蒂纳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感性肯定不是彻底的感性,因为它维系着理性、超验性的意义——它无法用感性存在证实或证伪,也无法用感性来取代。而施蒂纳的感性明显切断了这种与非感性的联系,而把自己彻底放逐进了瞬间、片段、偶然、裂变、易变、空无、消耗、享受和最后的死亡中。这意味着,施蒂纳沿着从现实中、从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来理解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理路出发,走向了把感性至上化并彻底告别形上学的极端之路。
我国学者中早就重视马克思对施蒂纳之批判的是吴晓明教授,他与张一兵教授一样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吴教授的一个观点我有不同看法,这个观点就是:“惟一者”仍然是形上学的东西,仍是被封闭在内在性之中的“我思”或意识。(吴晓明、徐琴,第27页)在吴教授看来,“惟一者”这个试图超出概念、逻辑和反思世界的词,不仅在来源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是完全依循概念、逻辑、反思原则而被制订出来的。不过在我看来,与其把施蒂纳的“惟一者”看作是逻辑抽象,不如把它视为一种价值应该,一种当下虽然不能很好地做到却仍须努力的理想目标。而且,“惟一者”不是概念,而是可能性,是一种在逻辑上被揭示出来并在价值理想层面提到崇高地位的可能性立场和生活方式。如施蒂纳所说,“从我自己出发我所能做的事是很少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然而这些很少的事却是一切,比为他人的权势所允许,为道德、宗教、法律、国家等的训练所允许我从自己出发所做的更好。”(施蒂纳,第196页)德里达说得对:“惟一者只不过是普通场所,是聚集观念或理想的、自律化的整体性的空间,因此它本身不就是众幽灵的躯体吗?”(德里达,第182页)施蒂纳试图通过“惟一者”给精神一个形体性根基,让个我自己承担原来由普遍的众多同质化主体共同承担的普遍、必然的功能与任务,并通过把这种普遍必然性存在碎片化的方式来消解压在个我头上的那个普遍必然性存在的威权与貌似的强大,使个我在面对庞然大物爆炸后的碎片时重新变得威力无穷。这里的关键之一在于,概念只能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而“惟一者”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必然的,所以,“惟一者”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超出概念的东西——它至多是一个试图给“精神”以现实形体的“幽灵”,而不再是全然不顾形体和肉身或与形体和肉身无关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施蒂纳的努力效果如何,他不会也不可能返回概念论立场了。在我看来,施蒂纳的“惟一者”不再是封闭在内在性之中的“我思”,那种把普遍、必然、永恒、神圣等四重含义包含在其中的“我思”,而是可能性的、偶然性的、片断性的、个性的、当下即是的偶在,是抗拒形而上学主体的个我所是。这样一来,施蒂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终结便走过了头,陷入了把普遍性、必然性、神圣性维度统统拒斥掉之后所必然引发出来的虚无主义、个我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深重困境之中。个我在这些困境中还如何能够存在下去,并按照是其所是的内在要求成为自己蕴含的所是?
就此而论,从经验主体与超验主体关系的维度来看,施蒂纳的“惟一者”让马克思重新思考的问题就不再是“类”是否还能作为评判现实的基础,不再是是否应该更着重强调“人的”“现实”、“感性”方面,把“人”、“主体”向感性、经验维度方向进一步移动,而是“现实的人”(或用我们的话说“经验主体”)在告别原先的“抽象性”、“超验性”和“神圣性”之路上应该走多远,应该在哪里刹住步伐;或者应该在普遍、特殊与个性、在神圣性与世俗性、在抽象超验性与具体经验性等等之间保持一种怎样的辩证结构才是合理的,才能与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协调一致起来。通过施蒂纳的刺激,马克思不能不充分考虑、不能不提醒自己:从抽象维度向感性维度靠拢、从神圣维度向世俗维度移动肯定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所直接面临的尴尬与行将陷入的危险,令马克思意识到不能无限地反抽象而倡导感性、世俗,不能过度地强调唯经验性存在才是现实存在,更不能在可直接感知、有形有状的经验性存在与现实存在或有价值存在之间划等号,否则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值得忧虑的是,反内在性形而上学、反超验存在,不恰当地理解“感性”与“现实性”,这种态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世俗化和庸俗化理解:越来越多的人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彻底以“感性存在”取代神圣性存在,以“现实性存在”替代具有超验性意义的存在。诸如下述做法:彻底拥抱世俗化,整天盯着吃穿住,更高的文化需求被看作是次要的或可有可无的,经济财富和经济增长被夸大为一切,与经济需求难于协调的一切都被视为点缀或虚妄,极尽奢华之能事、极力讲究吃穿住却毫无更高的理想,被某些人看作是践履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不恰当的理解俨然已把虚无主义当成了唯物史观的逻辑结论。所以,重温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可以明了唯物史观的主体性意涵、辩证法路向、价值形而上学含义,明了遏制虚无主义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所在。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政治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