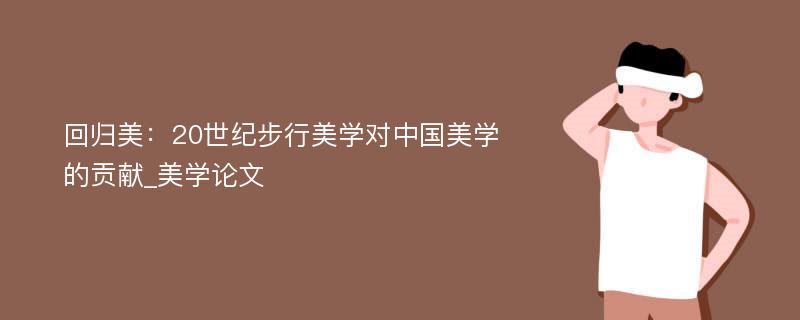
向美还归:散步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世纪论文,美还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趋势的一种反映,20世纪的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译介和重新组装是其主流,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融会性创见并不甚多。另外,中国20世纪社会生活的长期动荡和泛意识形态化,也使美学研究一次次偏离常规方向,成为政治的隐喻。在这种背景下,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让美学向美本身还归,就成为修正美学的研究思路,并在新的基点上重构当代中国美学的重要课题。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散步美学”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具有了崭新的意义。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美学发展的几个误区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格局中,哲学美学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散步美学作为艺术美学的一种,它的价值正是在和哲学美学的对比中得以彰显。所以,探讨散步美学的价值,首先必须面对哲学美学的一系列研究误区——
1.哲学美学理论品位的上升与审美品位的下降构成巨大反差,政治化的求真与文人化的求美之间日益失调。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源远流长,但作为学科形态出现的中国美学,却是原产于西方,后经日本传入的舶来品。所以,西方美学的一系列弊病一直成了中国美学家不得不承受的遗产。比如,诞生于德国理性主义土壤上的德国古典美学,虽然其创始人鲍姆加通给它作出了“感性学”的定位,但从其介入美学研究开始,就走上了与感性相背离的道路。于是,美学作为哲学的婢女,其哲学化程度一直是衡量其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就中国美学的发展而言,本世纪前50年的老一代美学家,虽然他们都有接受西方美学的学术背景,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深厚造诣,有效地稀释了美学研究中的哲学性,字里行间透示出文人化的自由性情。这一时代,不论是讲求“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他们总还是试图架起东西方美学沟通的桥梁,并朝着互补融会的方向发展。但解放后,中国当代美学不仅与传统美学精神相疏离,而且也割断了与西方现代美学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依托的德国古典美学成为惟一可讨论的话题。作为这种学术状况的反映,可以看到,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直在几个基本的哲学概念之间兜圈子,其表现出的理论的粗陋浅薄,一方面意味着美学研究水平的倒退,另一方面,这种假美学之名讨论政治、以哲学观之争代替美学沉思的方式,又使原已非美的哲学美学笼罩起浓厚的意识形态阴影。在这种背景下,美学学科审美品位的下降有其必然性。另外,在80年代的美学热潮中,虽然美学研究日趋多元化,但理性启蒙的沉重主题,依然意味着美学研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话语,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流派的重新翻炒,则使中国古典美学的神韵进一步隐匿不见。
2.情感生命的欠缺、生活方式的单调、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哲学美学家审美能力的钝化。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大多出身于学院派,其学养或止于哲学,或由哲学而偶涉艺术,像宗白华、王朝闻、高尔泰等有艺术实践经验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他们长于在理性思辨的王国里自由驰骋,但对于艺术和自然,却难说有多少独到的感悟和鉴赏力。学术研究中偶尔需要一些艺术实例作点缀,也大多止于重炒古人或西人的剩饭。当然,这种美学家感官普遍迟钝的状况,除教育体制、个人才情的因素外,更多缘于20世纪中国长期的经济贫困和社会动荡。对于一个从小就将求生存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知识群体来讲,审美活动已显奢侈,更谈不上受到良好的情感教育和艺术训练。尤其解放后的前30年,美学家几乎生活于与美绝缘的环境里,谈论的大多是政治话题,参加的大多是政治运动。外出旅行,面对山川河岳,抒发的大多是革命豪情;一人独坐书斋,则忙于写形形色色的思想总结或反省材料。这种文化背景,对人政治嗅觉的培养大大高于审美嗅觉。另外,从当代商品社会给美学家提供的角色定位来讲,想培养出博大的审美心胸和敏锐的鉴赏力依然困难重重——大学校园是他们生存的世界,书斋是学术的家,经典是对话的朋友,学生是单一的听众。这狭窄的生存界域明显限制了美学家们的视野,单色调的生活也必然使他们感觉钝化,情感萎缩。于此,美学的单调乏味具有必然性。
3.美学体系的霸权、主义的论争,一次次淹没了对具体审美对象的常规性观照。
中国20世纪美学向体系化、学派化方向的发展,应该说肇始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体系的产生既说明中国美学日渐走向成熟,但此后的发展,又证明它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比如,伴随着80年代的美学热潮,美学研究者对一系列美学体系的制造呈一时之盛,似乎一篇千字美学论文的发表,就意味着一个新体系的诞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些所谓的美学体系,大多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注:李泽厚:《美学译文丛书·序》,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谓的美学家也有被时代浪花淘尽的危险。首先,这些体系大多是上承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遗绪,把从哲学的假设出发、探讨美的本质作为研究重心。这种研究方法,从西方美学史上看,早已被判定为永远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无效劳动。同时,这种围绕美的本质旋转的美学,往往是围绕几个主题性概念兜圈子,从中很难见到对自然、艺术、生命之美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次,随着西方现代美学流派在80年代的重新引入,中国新生代美学家为体系的建构增加了新的内涵,并为东西方美学的重新接轨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学识缺乏积淀,主体精神苍白,他们往往成为西方某一美学流派在中国的代理人,体系也成了某一西方体系在中国的翻版。这类体系,在80年代的文化启蒙时期,确实给美学带来过荣耀,也满足了公众的求新猎奇之心,但是,由于它以追求震惊效应代替了对审美对象的常规性观照,以对异域的狂热代替了对民族美学精神传统的沉思,这就导致了理论体系与现实疏离,并缺乏历史感。同时,体系之间的争强斗狠也使美学家失去了应有的平常心和审美心胸。多了追风赶潮的学术浪人,少了精神家园的真诚守护者;多了学术论文中的言词刻毒,少了惺惺相惜的同情。
4.五四以来“以美拯救世界”的善良愿望,以启 蒙话语干预社会的学术目标,使美学学科承载了过多本不应承担的负荷。
人们往往因为追求美而至善,这是席勒以降美学家主动承担起沉重社会使命的理论起源。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命题,此后,中国美学家一直怀抱着“以美拯救世界”的善良愿望。尤其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美学家以启蒙话语干预社会,以强力批判成就现世的荣耀,成为重要的学术目标。这种学术承担无疑是沉重的,也是崇高的,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做出了贡献。但是今天看来,这种以“美学王”自任的自我膨胀,又未免显得太堂·吉诃德:首先,美学研究者忘记了美学作用的限界,只是一味向外扩张,忽视了美之根性的无力和脆弱。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美学家美学之不足而辅以哲学,哲学之不足而辅以政治,政治之不足而辅以行动,结果往往出而不入,往而不返,其浪游之魂魄已非美神可以召回。其次,张扬启蒙精神的美学大多以反主流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其美学理论浸染了意识形态性——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因对抗而超越,而是因对抗而互补。因此,它可能在社会矛盾激化状态时成就一副勇者的形象,但反抗对象的消失,必然意味着其理论生命的寿终正寝。再次,对自然、艺术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观照应该是美学的立足之本,引导人诗意地面对人生应是美育的最基本功能。由此看来,过于强化美学的社会性使命只能是从业者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仅重视向外的扩张,而忽略向内的回归,美学必然会变成无根之学。
以上,我们对中国百年美学发展的诸种不正常状况进行了反思,并以此作为“美学失美”的原因。面对这些也许过于苛刻的责难,人们当然可以提出种种理由为其辩护,认为美学非但不是一团糟糕,而是随着时世的推移,愈来愈显示出茁壮的生命力。比如,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的美学除了拥有大批专业研究者以外,它的精神几乎渗透到自然、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心理学家都有相应的美学言论、文章甚至著作出笼。在中国百年美学发展史中,“美学热”连续不断,在1917年至1927年、50年代、80年代这三个时期,美学展示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动人景观。从美学学科形态的发展来看,美学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似乎每种生活、艺术门类都可以衍生出一个美学分支。但是,如果我们以旁观者的姿态,静思这一片喧闹的景观,就会发现繁荣背后隐匿的危机。可以认为,大批自然、人文科学家对美学研究的介入,正是美学逐步丧失其独立性的开端,它至少证明美学家没能圆满解决自己的问题,以至引来了其它学科对美学的学术殖民。就中国而言,美学虽然在本世纪三次大的政治文化变革时期成为显学,但它并没有表现出恒久的生命力。往往当社会进入相对有序或更加血腥化的时期,美学就慢慢失去了影响力。像本世纪的三次美学热潮,加在一起也不过30年,剩下的70年,它则成了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由此看来,在世纪末,确实有必要关注美学发展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并在整理前人遗产的基础上,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一条稳定、恒常的道路。
二、散步美学的一般规定
在现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宗白华先生留给后学的文字止于一本诗集、一本文集和一册译文集,在历次政治、文化运动中,他也是置身边缘而非中心。但是,由他在1959年自名的散步美学却没有被任何一个时代忽视。(注:最近有学者称,宗白华创立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散步学派,这种说法不恰当。因为宗白华在当代虽不乏研究者,但却既少同道,又乏传人,更遑论发展者。单个的美学家是无法被称为一个学派的。)解放前即有“南宗北邓”之誉,今天拥有的影响更是殊有匹敌。那么,散步美学为什么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散步美学是一种自由主义美学,它植根于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的精神土壤。在对庄禅境界、魏晋风度的追慕中,为自己寻到了一片非意识形态性的净土。
宗白华认为:“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以此种姿态为依托的美学必然是以精神自由为其神韵的美学。从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看,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两相对立的思想阵营,但也明显存在着摒弃左右而守其中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今天看来,无论知识者的政治姿态趋于激进还是偏于保守,都必然会面临政治左右学术,甚至代替学术的危险。这种学问虽然可能造成时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意识形态的瞬息万变明显会带来学术的短命,甚至为学术生涯涂上永难抹去的污点。由此反观宗白华,他一生极少与政治攀援,即便是50年代惟一的一次对高尔泰《论美》的“疑问”,也是立论平和,丝毫不见当时美学论争中意识形态话语压倒美学话语的时代性特征。很明显,在现实单色调的政治预谋之外,他拥有一个更加博大的超越性的审美时空,这里足可以使他洗炼情感,作逍遥之游。当然,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选择并不是宗氏的首创,从他对庄子、魏晋名士、王摩诘、苏东坡的倾慕,以及对一系列受烟云供养的山水画家的追述中,可以洞悉他对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美学精神的情感归依。
2.价值中立原则。散步美学既有意回避来自主流文化的“绝对命令”,也不以救世者自居,用美学话语去演绎关于未来社会的启示录。它“避重就轻”,牢牢抓住“艺术的人生态度”这一核心。
从宗白华先生一生的为人为文,人们能够得出的比较直观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美乡的沉醉者”。对待艺术作品,他很少作一锤定音的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同情的领悟和描述。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退潮,文人梦想的驰骋正处于跨越一切限界的巅峰状态,但23岁的宗白华却渴望“一种解放超脱的安宁”,“我现在正渴望到一个寥无人迹的森林中去,忏悔以前种种无意识的过多的热望,再来专心做一种稳健的适宜的狭小而有实效的小事业”(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很明显,作为美学家,宗白华从青年时代就明白自己的职分,对逾矩而入于政治不抱幻想。同时,虽然他自称“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但他的唯美主义并不是一面自我标榜的与现实对抗的旗帜(如王尔德),或以反政治来展示一种艺术家的政治观,而是从艺术中洞悉人生,为真我的存在开启一片自由天地。这种心无旁鹜、以艺术价值为第一价值的自我定位,正是他和好友郭沫若、田汉相区别的地方。综观宗白华一生留下的文字,总是给人一种逸世绝尘之感,没有“遵命”的制作,也很少对抗的激情,时代的变迁几乎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明显的印痕。如果没有一种生命的沉静之气,没有对精神家园的真诚守护,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李泽厚先生在《美学散步·序》中曾慨叹:“你看(宗白华)那两篇罗丹的文章,写作时间相距数十年,精神面貌何等一致。”(注:见宗白华:《美学散步·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精神沉思的超时代性,明显和他进退有矩、执中而行的人生态度相因果,和那些随波逐流、最后自迷其踪的文化人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对于中西艺术,他既激赏西洋油画体现的“人类不朽的青春精神”,又服膺中国画艺“秋天的明净”;对于现代与传统,他既对“五四”以后的白话诗由衷赞美,又对古典艺术一往情深。很明显,如果他在伴随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古今中西之争中自置囚牢,就不可能如此左右逢源,进退自如。
3.人生、艺术、自然是散步美学三位一体的观照对象。人生的艺术化、艺术的自然化是其走向自由境界的路径。
宗白华认为,“美的真泉在自然”,而“惟有艺术才能真实表现自然”(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由此看来,自然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是一个至高的范畴,艺术在这里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和魂魄。当然,宗氏所言的自然并不是西方心物二分的死寂世界,而是处处显现出鸢飞鱼跃的动相。自然之所以成为一切艺术的范本,原因就在于它“无时不在动中”,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生命精神。艺术的最后目的也正是对于这种自然动象的表现。同时,就美学与艺术、自然的关系而言,宗白华认为:“美学的研究,虽然应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但向来的美学总倾向以艺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为是惟一研究的对象”(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在这里,艺术之所以成为“惟一研究的对象”,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然、人生真义的冷凝形式,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1920年,宗白华曾这样设定自己一生的工作:“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从以后的学术历程来看,人生、艺术、自然确实构成了他诗性宇宙的整体轮廓,而这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和谐共融,就在于它们都以生命的自由展示回应着整个宇宙的生命律动。至于宗白华自己,他的美学研究、生存方式也是充分艺术化的。从他早年的“拾石雨花,寻诗扫叶”,到晚年的“拄杖挤车,一睹艺展”,都可以看出他不但是人生、艺术、自然相融观念的提倡者,而且是卓越的实践者。
4.以“平常心”静观世象之变的主体人格,以真性情与美相游的美学个性。
抗战晚期,宗白华先生作《团山堡读画记》,其中一段话很能说明作者对世象之变的态度——“在这狂涛骇浪的大时代中,我的生活却像一泓池沼,只照映着大保的松间明月,江上清风。”(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面对当时倭贼入侵、 国破家亡之命运,人们当然会从中感到他对国家民族未免太不负责任。但是就此也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不可与语时务的方外之人,是桑达耶那式的“永恒的世界”的渴慕者。这种不以人间烟火为烟火的主体人格虽然大可诟病,但却有效保证了他对审美王国的固守。也许,在上帝和凯撒之间,各有自己分管的事务,一个美学家能种好自己的田园已相当不错了。在本世纪历次社会动荡导致的人生沉浮中,宗白华始终保持着散步者的闲逸姿态,防止在众声喧哗中迷失了宝贵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基本没有出现过步调错乱、因文失节、过后又后悔不迭的现象,能得此正果,应和他葆有的这份平常心有关。另外应该提及的是,他的“不识时务”,并不是赵七爷式的韬晦或庄周式的滑头主义,更多是孩童式的表里皆白使然。如他所言:“这里是童贞的世界,这童贞的世界就是桑达耶那所常住的永恒世界。”(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他的作品中浸润的美丽、飘逸、 空灵应该是这种童贞之心的显现。
5.美文的美学。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主要依托于三种理论背景——西学的背景:尤其是康德哲学、歌德的诗和罗丹的雕塑;旧学的根基;主要集中于中国古典山水诗画;创作实践:诗集《流云》。这三个方面共同熔铸了宗白华美文的美学风格。首先,在他学术的成熟期,虽然倾力于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但往往因有西方当代美学、艺术理论的视野而自出新意,像他引入的时间、空间、节奏、韵律等范畴,有效解决了传统艺论“欲辩已忘言”的尴尬处境,达到了体情与析理、描述与明辨的综合。当然,在借用西方现代理论范畴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时,他是有所筛选,有所舍弃的,其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炫耀学识,其著述绝少见到鹦鹉学舌、生搬硬套的当代恶习。其次,他的美文风格来自于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积厚之功。我们今天一般把美学史搞成了单色调的美学思想史或范畴史,原因无非在于视野的狭窄和古典艺术修养的缺乏。宗白华先生1980年就提出要重视中国人美感发展史的研究,并自认“美学就是一种欣赏”。这种认识虽然有些绝对,但却抓住了美学失美的根本原因。第三,诗歌创作实践培养了他富有穿透力的直觉,使其能够以感性化的语言直接洞见审美对象的本质。宗白华一生寄情于文学和艺术,不但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情境”,而且他的诗歌创作实绩也堪称美文中的精品。这种创作和鉴赏实践如源头活水,不断注入理性的河床,其著述的空灵和亮丽,因此具有了必然性。
6.心摹手追以求传神的研究方法。
从宗先生留下的著述看,他缺乏动辄数十万言的宏篇巨制,多是在乘兴赏玩的前提下,侧重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凝神观照和解析。这种微观的研究方法看似缺乏大气,但其对古典艺术神韵的传达,却使人深感搔到了痒处。与那些隔靴搔痒的长论相比,其价值不言自见。就对艺术的沉溺程度、体验功力和兴趣的广泛性而言,在现当代美学史上能和宗白华比肩而立的不多。30年代,他在南京购得数十斤重的佛头,80年代依然置于案头,并深感它的存在使满室生辉。他不但广泛涉猎常态的艺术形式,对工艺美术以及针头线脑式的小玩意,如牙雕,也备加倾情。也许,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具象化观照,妨碍了他理论研究的宏观性、综合性,使其研究成果生动而破碎。比如,他对“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描述的分量要大于史论的分量。另外,包括他对中国艺术意境、诗画的空间意识、晋人的美等问题的经典性论述,也明显有将“赏艺札记”拼装组合的嫌疑。但是,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来讲,人们缺乏的正是这种与艺术血肉交融的“前美学”沉溺,以及一针见血穿透问题的直观和细腻。那些动辄数卷的煌煌大著,以及看似严谨的逻辑构架,大多是只顾自己理性思辨的快意,而不惜造成对美学史真相的不负责任的歪曲。关于这种艺术美学与哲学美学的优劣之分,英国人科林伍德曾在其《艺术原理》中作过评判:哲学美学往往沉溺于逻辑的迷宫,不管它多么胜任理论工作,却往往因为事实基础的薄弱而归于无效。艺术家型的美学家熟知自己所谈论的内容,能分清艺术的事物与非艺术的事物,这是一种富有成效和价值的活动,是构成艺术哲学两个步骤的第一步。(注:刘熙载:《艺概·文概》。)据此可以认为,宗白华作为艺术家型的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虽然有诸多缺憾,但毕竟非常稳健地跨出走向理想美学形态的“第一步”,其价值应该高于“因事实基础薄弱而归于无效”的哲学美学。
三、散步美学与哲学美学关于体系问题的对话
如前所言,虽然宗白华的散步美学在中国近百年的美学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在今天哲学美学占主流的时代,它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地位。没有体系、不成系统是人们对它的最直观的印象。为了加强这种美学形态与哲学美学的对话和沟通,关于体系问题,兹辨析如下:
1.体系有概念的逻辑体系和艺术语言的潜逻辑体系之分。散步美学以精辟的语言、直觉的穿透力去追逼艺术的真谛,去点化、呈示艺术的最高灵境,才是一种真正符合美学自身品性的形象思维逻辑。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潜在体系,如“草蛇灰线”,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具有真切的内在规律性。刘熙载评庄子云:“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注: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这“骨”,正是形象思维的逻辑;这“分数”,正是潜在体系的基本构架。
2.体系有“有我体系”与“无我体系”之分。按照哲学美学的传统,美学是一种科学而非艺术,祛除自我的介入是建立客观化美学体系的前提。所以,在康德、黑格尔这些典范性的美学家的著作里,体系中的“我”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但是,这种对“我”与体系的强行隔离,是和人的审美旨趣、个性根本相悖的。正如狄德罗所言:“我认为事物最好的秩序就是需要‘我’在里面的一个秩序,如果‘我’不在里面,即令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同时,“有我”并不是建构体系的天敌,相反,这“我”像太阳一样,使看似散漫的美学论文围绕它旋转,并以人性的光辉进行普照。具体而言,这种体系是以“我”为圆心、以形象思维为半径、以艺术理论为弧线画出的体系之圆。在体系的核心处,散步美学家以实存的“我”代替了让人难以捉摸的理式、理念,使理论体系更显出人性的温馨和情感的统摄性。
3.体系有自在体系和自为体系之分。在哲学美学的传统中,美学是哲学的附庸。像哲学需要形而上学一样,美学如果没有关于终极问题的假设,没有逻辑的演绎,似乎就不成其为美学。所以,哲学家型的美学家在介入美学问题之初,总是有强烈的体系欲望,以此确立自己精神创造的真理性和学术阵地的坚不可摧。这种为体系而美学的方式,可称作自为体系。但散步美学却没有如此强烈的体系癖,他们认为,美学是思想的艺术,而非思想的科学。他们宁愿将精力用于对艺术的具体阐释,而不愿意为搞一个庞大而空洞的体系去劳心伤神,认为这除了羁绊人审美的自由意志,并无其它的作用。当然,这种不以体系为第一要义的美学心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失去了内在的一致性。相反,他们体系的“神经”,都隐含在对艺术辨析的血肉之中。这种美学,像一席没有菜谱的盛宴,哲学家型的美学家总是将最大的精力用于设计体系的“菜谱”,而散步美学的菜谱则已被宴席上具体的菜肴充分表现了。这种消融于理论过程的体系,是无心而天成的,是一种自在状态的存在。
4.从文体风格的角度看,文章的长短更和学术价值没有关系。散步美学家的短文是将审美者的理论思维和艺术体验充分浓缩的晶莹形式,它短而不泛,短而不浅,短而不枯,短而不谬。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充满了这种散步式的美学短论,片言只语往往能对艺术穷形尽相。也就是说,以最精悍的语言去表述最广博的思想,这才是美学研究应追求的佳境。
收稿日期:1999—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