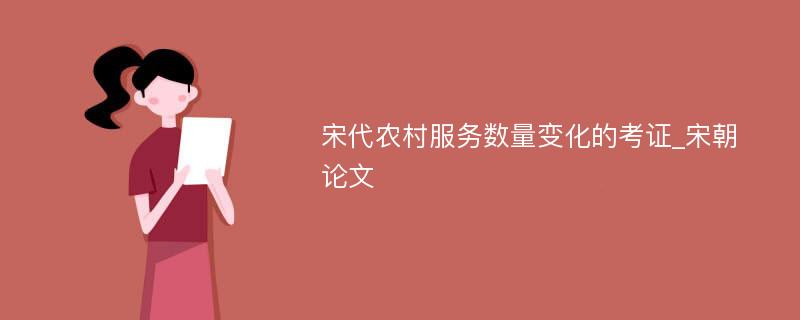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人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的职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户服役地点的不同,分为州、县和乡役,在乡村服役者即为乡役人。南宋陈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设“乡役人”条,孙应时等所撰《琴川志》卷六也有“乡役”的记载,说明这一名称已为时人接受。两宋期间,不但乡役名目有所变化,而且有从轮差到雇募,再到差募并用、名募实差的充役方式的变化,乡役人数成倍增长则是其中又一较为显著的变化。中外学界对于宋朝职役制度已多有研究(注:聂崇岐、孙毓棠、黄繁光、王曾瑜、漆侠、雷家宏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请参见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总第87期(2003年8月),增订后转载于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另外,美国学者Brian E.Mcknight(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版),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东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创文社1986年版)等也多有研究。),但是,对乡役人数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却鲜有探讨,故作此考述,以补其缺。
一
两宋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之差役)乡村民户中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注: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下同)。)。此外,三年一次攒造户等簿,也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共同承担。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四月,诏令废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随之废除。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设,最初意在部分恢复府兵制,减省养兵费用,增强军队候补者的战斗力,并藉以加强地方社会的治安管理(注:《宋会要》兵二之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华书局点校本;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然而,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两宋乡役之制,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承担乡役之责。虽此后又有元遹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所谓“兼差”之制(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已有研究如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承蒙黄教授慨赠大作,谨此致谢),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关“兼差制”则参前揭Brian E.Mcknight所著之第四章。)。
赵宋王朝给乡役人所设定的社会角色是“民”,是“庶人在官者”,是国家用来“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注:《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役法上》,第4299、4295页。),其身份并非是“官”。在贵官贱吏的宋朝,乡役人并非由中央直接任命,其社会地位很低,除王安石变法时外,一般情况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报酬,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更没有国家权力象征的官府印信,所以不能构成一级政权。对于广大应役的乡村主户中的上户而言,尚有充役为吏的某些好处,而对于乡村中下等主户甚至部分客户而言,却往往成为自家一项沉重的负担。(注: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吏户》,载《新史学》第四卷第一期,1993年3月;并其《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9页,第333—346页。)但是,宋代乡役人却又是介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官与民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在填补县政和乡治之间“权力空隙”的诸多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中介性枢纽作用。国家政令,大凡须由州县政府转交于乡役人,方能最终落实于乡间;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经由他们上达于州县乃至朝廷。国家对于广土众民的控制、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尤其是政府敛于民间的各种财赋,也端赖于他们的运作和努力,国家机器方得以正常有效地运转。
二
北宋前期的里正、户长、乡书手和耆长、壮丁等乡役的设置,现存史料几乎没有具体人数设置的记载。但是,依据当时设置名目和士大夫的一些议论,可知这一时期大致的设员情况。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七月,范仲淹在一道奏疏中反映河中府河西县“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馀户属乡村,本县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于乡村差到”(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四部丛刊初编》本。)。所谓“乡村差到”,应指乡役人。按上述数字,河西县主户中平均每4—5户就轮差乡役一人,但其中并不包括乡村客户在内,这与后来保甲法中“通主、客[户]为之”(注:《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载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第5297页。需要强调的是,担任保正长者须是主户。)所算出的比例是有差距的。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十一月时,李觏云:“今夫大乡或二、三千户,小者亦数百户。与其使耆、壮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乡千百户出力?”(注:李觏:《直讲李先生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其中的乡役人数并不确切。同样,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文彦博有“比近三两乡合差一里正”(注: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七《奏理(里)正衙前事》,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的建议;熙宁年间,司马光曾说“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衙前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均未提及其他乡役。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在上奏中说,先前“五等之有差役,一乡不过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注:《长编》卷三二四,元丰五年三月乙酉。)。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知靖江府胡舜陟说:“……若祖宗时,于人户第一、第二等差耆长,第四、第五等差壮丁,一乡差役不过二人而已。今保甲于一乡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数百人大小保长……”(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并六五之八二(靖江,一作静江,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与前引《宋会要》的记载相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下同)。)只说此前一乡之中有差役二人,是未将户长等负责税收的役人计算在内,但这则资料同样反映出这一史实,即熙丰以前乡役人数是比较少的。根据以上文献中仅存的吉光片羽,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熙丰前,乡村中一乡(注:按宋初以来,职役制度沿袭唐五代旧制,王安石变法初期,仍然设置一都管辖范围为500户,与唐一乡之制相当。因此前并无相关变化的记载,故此处暂按一乡500户计。日本学者河上光一也推测,这时乡役的推行是以100户左右为单元的,合于唐朝一里百户之制,参见其(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一文,载于《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的乡役人员大致在10人左右。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保甲法规定,以乡村中相邻近的每10户为一小保,设小保长一人;以50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以500户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二人。不久,又改为以每5户为一小保,设小保长一人;以25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以250户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二人(注:《宋会要》兵二之五;《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而揆诸中国传统社会之实情,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紧密交织、聚族而居和亲善友邻的乡土社会中,以5户为一单位,设置小保长催税一事,能否真正贯彻到实际之中,或者说,小保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治理理念,通过现存史料还很难加以说明。关于南宋保甲制的编制,可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点校本,第866—867页)、《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一载乾道九年十二月详定一司敕令所修立法条等。)。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已有保甲法混同于乡役法的记载(注:《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载:“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乡村每主户十至三十轮保丁一充甲头,主催租税、常平、免役钱,一税一替……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壮丁法。未有保甲处,编排毕准此。”)。另据“元丰本制”云:“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保]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注:《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役法下》,第4329页。)朝廷的诏令和现存南宋地方志中所载的有关规定,也与上述熙宁八年之制大体相同,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注:如《宋会要》食货一四之四七至四八并六五之一○一载绍兴五年四月十六日朝廷敕旨云:“于‘大保’字下添‘通’字,‘选保’字下删去‘长’字。及绍兴九年四月四日敕旨,于‘都保’字下添‘通’字,‘选’字下改‘大’字为‘都’字,‘保’字下删去‘长’字。自此差役极便。绍兴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明……故有是命。”类似更改,似都无害于熙宁八年之制的宏旨。)。
现存南宋时期的史料,则反映出熙丰之后乡役人数增加的情况。如前揭绍兴五年时胡舜陟就说,自从章惇、蔡京等将经过他们改造的募役法推行于东南地区,“以二百五十家为保,差五十小保长、十大保长、一保正、一保副,号为一都”。这样一来,“今保甲于一乡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数百人大小保长,不若耆长、壮丁之法为宽”(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六五之八二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记事。而据《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二一载淳熙元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诸路州县,一都之内,保正凡二,而保长凡八。”同前六六之二六载绍熙二年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张叔椿言:“夫有乡则有都,有都则有保。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税用保长二人。二年之间,为税长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数少则上中户为之而有余,保长之数多则中下户为之而不足。州县之间,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长,不理役次,固有朝辞保长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户俱受其困矣……”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引绍圣二年二月详定所言:“乡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长八人。”似有身为保正副而兼任同都保内大小保长者,则一都之中,乡役总数为50人,如此,则一都役人比熙宁之制少12人。近见杨宇勋先生《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集刊之31,2003年6月版,第267页注释)亦有相似的疑问。两宋是否皆然,当再详考。)。而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时,知常州郑作肃说:“一都之内,当执役者,都副保正凡二人,大保长凡十人,小保长凡五十人。”(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记事。)据上所述,“以一都计之,则废农业者六十人”(注:《宋会要》食货一四之一九。),反映出乡役人数的增长变化情况。换言之,这些史料与熙宁八年的制度规定是一致的。南宋人舒璘以徽州歙县为例,论说南宋役法弊病云:该“县三十七都,每都税[长]二人,则一税不过七十四人,转而为十,则一税将差三百七十人……是向也一税之内,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祸;而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祸”(注:舒璘:《舒文靖集》卷下《论保长》,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溧阳县均赋役记》载陆子遹所记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时,建康府溧阳县自从推行义役后,溧阳县“而赢役户凡得保正三百六十有七,保长二千八百八十有七”。),同样反映出乡役人数的成倍增长。
现存明朝天一阁方志中还有三则相关史料,兹摘录于下。
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据唐华亭一县,统乡十三,则里正六十五人也。宋制:熙宁以前……熙宁以后,曰保正曰保长,据《嘉熙便民省札》,华亭诸乡苗税旧例,差保长三百人有奇。(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68页。)
宋分乡、吏二役,旧以人户等第差充……乡役:旧有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分主赋税及烟火盗贼。中间罢里正,募耆长。熙宁行保甲法,令五家为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都有都保正副,专一逐捕盗贼等公事。而耆长、户长专督赋税。其后,耆、户长亦废,保正副遂兼其役。本县二十里,为都三十有四,保正副六十八人。嘉定间,簿林榘创义役,每都为十甲,大保长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人。小保长每甲五人,共一千七百人。乡书手十八人。(注:《嘉靖惠安县志》卷七《职役》,(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65年影印本。)
役法之弊久矣……淳熙六年春……县十四乡三十五都,保正凡五十四人,而当役之家实四百三十五,视力高下,出田有差……(注:《嘉靖淳安县志》卷一四载录[宋]胡一之《义役记》,(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65年影印本。)
今按:依上所载,宋时华亭县单保长一役就差有三百多人,比之唐朝差里正65人,已多出5倍。惠安县有34都,差保正副68人,正好与宋制每都设保正副二人相符;而嘉定后的乡役人数,大小保长数即达2040人,也反映出其间乡役人数的增长。至于淳安县的记载,其35都中当役者达435人,依熙宁之制,应是指保正副和大保长而言。下面,我们再根据成书于南宋淳熙九年的《淳熙三山志》(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一四《版籍类》做成下表,来考察其中的变化情况。
表1 北宋时期福州乡役人数情况
时间 户长
耆长
壮丁
乡书手
保正副
大保长
催税甲头
承帖人 乡役总数
熙宁七年4441592 62 2098
元祐元年1304431614 2187
绍圣元年834 3555 5211 82910429
表2 两宋福州各县乡役人数情况表
县分时间 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保正副大保长小保长乡役总数
熙宁 21 1037 154
67289
闽 元祐 21 1037 154 222
县 绍圣 6060
淳熙 1037 47
熙宁 11 5 49 148 213
连 元祐 11 5 49 136 201
江 绍圣 6666
淳熙 5 32
60
302
1520
1919
熙宁 28 9 44 201 282
侯 元祐 28 9 44 201 282
官 绍圣 7171
淳熙 9 44
7171
熙宁 11 4 55 70
长 元祐 11 4 52 196 263
溪 绍圣 4151 155
淳熙 4 55 175
851 4355 4355
5440
熙宁 8
4 32 98 142
长 元祐 8
4 37 92 141
乐 绍圣 4141
淳熙 4 26
4878
熙宁 16 7 73 248 344
福 元祐 16 7250 273
清 绍圣 419
419
淳宁 4 442 372
372818
熙宁 11 4 26 76 117
古 元祐 11 4 16 94 125
田 绍圣 8484
淳熙 4 6 7681
398
1874
2439
熙宁 4
3 18 92 117
永 元祐 4
3 18 100 125
福 绍圣 7474
淳熙 6
3 28 9673
316
1030
1552
熙宁 4
2 16 22
闽 元祐
清 绍圣 4747
淳熙 2 17 53
47 2341170
1523
熙宁 6
3 20 64 93
宁 元祐 6
3 20 64 93
德 绍圣 5656
淳熙 3 30 30
46 2301151
1490
熙宁 6
3 24 84 117
罗 元祐 6
3 26 90 125
源 绍圣 3333
淳熙 3
3 26 326 180720961
熙宁 16 8 43 176243
怀 元祐 16 8 176200
安 绍圣 5151
淳熙 8 33 35195
上面两个表格中的数字统计,未必完备,但仍可反映出以下问题:
其一,在表1中,熙宁元年时,乡书手还是乡役之一,到元丰和绍圣之后,则因已上升为县役而不再列出(修撰于南宋嘉定时期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则明确将其划为县役人)。表2中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所出现的乡书手,或是福建路所推行的兼差制。
其二,根据表2中福州地区有关年份的民户总数,我们对淳熙年间乡役人数在民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做一大致测算。据《淳熙三山志》卷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福州民户总数为321284,而该州所辖诸县乡役人数,据现存史料的统计为16486人,所占比例为21.3%。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福州,每5户左右就有一人充当乡役。这与每5户设一小保长的熙宁之制是相符的。
其三,表1中显示,福州一地元祐元年的乡役人数为2187人,而到绍圣元年则上升至10429人,比前者多出8242人,后者约为前者的5倍。表2中显示:连江县淳熙年间有乡役1919人,熙宁年间为213人,淳熙比熙宁多出1706人,后为前的8.8倍。长溪县中,淳熙年间乡役人数为5440人,比熙宁年间多出5197人,后者为前者的19.7倍。宁德、罗源等县也有大致相当的比照。另,福建路个别地区的个别年份也有差派甲头催税的情况,但在表2中并没有显示。而倘若再依各地每20—30户(一般应接近30户)设立一催税甲头计算,以一都250户计,每都应有8名左右的催税甲头,若非兼差,基层乡村负责税收者则又有增多(注:据《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三并六五之七七载绍兴元年九月十二日臣僚言:“……大保长催科,每一都不过四家……今甲头每一都一料无虑三十家……”可知。另汪应辰《文定集》卷五《论罢户长改差甲头疏》载,潼川府中江县差甲头862人,怀安军金堂县差甲头700人。又据真德秀言,福建路浦城县七十二都,每年差144名保长催督夏秋二税,见《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四部丛刊初编》本。关于一都催税者仅有大保长四人,朱熹曾说:“……大保长既是中下之户,而一年之内轮当催税者四人……”但他又同时又有“……见役十大保长轮差催税……只令十大保长各催本保人户官物……”之说,均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据《朱熹集》第866—867页。这和前揭《宋会要》均与熙宁之制不符,尚需详考。)。
其四,分析表2中的数字,我们发现,各县并未严格按照熙宁之制设置乡役人员,而只是与制度大体符合而已。如,就连江县淳熙年间的乡役而言,保正副为60人,则大保长应为300人,小保长应为1520人,而史料的实际记载却是大保长302人,小保长则实为1520人;再以长溪县为例,元祐年间的乡役人数是263人,而淳熙年间缺少大保长的记载,却同时兼差有耆长、壮丁和乡书手。再如,古田县淳熙年间设有81名保正副,那么,按规定,则大保长的人数应是405人,小保长的人数应有2025人,而实际史料的记载,大保长只设398人,小保长只设1874人;再看永福县的情况,淳熙年间,该县设73名保正副,那么,按规定,其大保长、小保长设置的人数应该分别是365人和1825人,而实际史料的记载却分别是316人和1030人。其中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闽清、宁德、罗源等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当。总之,从中既可以发现前后乡役人数的增加,也可发现其中的人数设定并非十分严格。这或许既与中国传统社会构成中,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越到基层,管理机制的控制力就越显松弛的特点有关,似也与王安石等在制订保甲法之初,就有因地制宜的规定有关(注:《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载朝廷准司农寺奏请:“……但及二百户以上,并为一都保,其正、长人数且令依旧。即户不及二百者,各随近便,并隶别保。诸路依此。”并《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第4300页。),即各地可以因民户多少以及“其风俗利害,各有不同去处”(注:《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转运常平司据知平江府长洲(一作常州,误)县丞吕希常陈请。据史料记载,各地还出现了如下现象:如《宋会要》兵二之二○载元丰四年正月判尚书兵部蒲宗孟言:“开封……十大保为一都保,保外别立副都保正各一人,及二小保以上亦立大保长一人,五小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附别保。隔绝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长一人,四保亦置保正一人。”又《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八八载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十日权知复州章焘言:“湖北、京西州县有户口稀少去处,其都分名额悉无改并,每遇都副保正阙,官司依旧随都选差,则是频并。欲乞今后每一都人户若不及五大保处,即合并接邻近都分人户通行选差都保正一人……候人户各及一都之数日,仍旧选差。”得到朝廷的允许。又,《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九○载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朝廷也批准了处州遂昌县丞黄揩的奏请“……兼契勘州县差募保正副,依法系以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材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缘州县乡村内上户稀少,地理窄狭,并有不及一都人户去处,致差役频并。今看详,欲下诸路常平司行下所部州县,委当职官将都保比近地里窄狭,人烟稀少并不及十大保去处并为一都差选,仍不得将隔都及三都并为一保,如内有都分人烟繁盛,山川隔远,更不须拨并。其并过都分,从本司保明供申……”再如《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一载乾道九年十二月时,详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条云“……诸村疃五家相比为一小保,选保内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通选都保内有行止、财勇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余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长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保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附大保,大保附都保”;以及宋金边界地区因民户稀少而合并都保等等相关记载。另,在狭都户贫处,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论差役利害状》还有以下的议论:“其狭都十大保长内,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诸县每年夏税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轮差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长”,据《朱熹集》,第866—867页。)等因素,而确定都保、大小保的具体设定。
通过上面的两个表格,还可以发现,宋神宗熙丰以后,福建路等地乡役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史实。这相对于北宋初期而言,增长数量确实是比较大的。虽然现存史料仅江浙、福建等地的记载较为详备,其他地区的相关史料却相对缺乏,但是,参照熙宁八年的朝廷诏令,南宋时期朝廷的屡次诏敕以及各地官员的反映,大致可以说,北宋熙丰后、整个南宋时期比熙丰之前乡役人数的增加,应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上溯隋唐,我们再看有宋之前乡村管理体制中设员的情况。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二月,隋高祖的诏制云:“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注:魏征:《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页。)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注: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63页。依同书第68页王永兴先生所做校勘记云“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疑‘如’下脱‘不’字。这一推断,颇有道理。)则反映出中唐以前乡村管理体制的状况。与宋朝并存二百多年的金朝(公元1015—1234年),也大致沿袭上述隋唐两朝的乡村之制。其500户中所设管理人数,一乡五里在6人左右;村正的设置,似乎只在少于10户的村落才能设置一人,而具体人数设置却难以确定,但考虑到平原与山区的区别,以及古代人口较少,并且为了合力耕作和共御盗贼,一般在平原聚族而居的村落,人户稍多,则村正人数较少;偏僻山区、湖泊的居民,则多散居各地,一乡所设,应该稍多。中唐以后,乡里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后期的乡村管理体制中,则在原有设置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书手”等役名,五代时期则又出现了“耆长”、“三大户”等。这时,乡村管理人员较此前大致已有所增加(注:李锦绣先生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探讨了唐朝后期州县乡村胥吏的增加及其作用,见其《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里胥典正与地方财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06页。)。上述似乎可以表明,乡村管理人员是逐渐增加的:北宋前期,乡村社会中还没有大量增加管理人手,直到熙丰之后,才出现了大量增加的现象。由唐朝初期500户中仅设10人左右(唐后期设置数量上的变化情况,现存文献并无更为明晰的记载),到宋神宗朝以后,每500户中多达120人左右,乡役人数增加了数倍之多,这一变化是极其显著的。
三
由唐入宋,特别是在宋神宗朝以后,乡村社会中何以出现乡役人数大幅增长这一现象,其中是否蕴涵有唐宋之际社会变革、国家权力极欲渗透到基层社会,以强化政府对乡村的治理等史实(注:最近,黄宽重先生《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拙文《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对此进行了讨论。拙作浅陋,纯属初步涉及。其中诸色乡役、县役的社会效用较之县尉、巡检等,似乎更能反映出唐宋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努力,但尚有待进一步详加探讨;黄先生的大作则跨越唐宋,视域广阔,挖掘甚深。),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又可以申述并印证哪些史实,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下面,谨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的角度,稍加探索。
唐中叶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随着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过去乡村赋税征收的体制,与此同时,民户有了更多流动的自由,且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因事设职是行政管理体制中惯常的道理。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势必要求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适时应变。
第一,魏晋南北朝以降,迄于隋唐,门阀士族开始走入城市,他们在乡间的统治力量逐渐减弱,原来在宗主督护制下,士家大族强有力控制乡村民众的现象不复存在(注:参见韩昇先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唐五代和宋初,国家控制力难以抵达乡间,更缺乏支配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似乎可以说是乡村发展史上的一个无序化时代。入宋后,统治者势必要采取措施,以弥补前此“权力空隙”,加强国家对乡间的控制。乡役人数的增加,以及宗族重新出现等,都是宋政府为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注: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同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页。),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注:陆贽:《唐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评定户等,征税派役。自中唐入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注:《唐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已大致反映出两税法之后计算民户资产、评定户等的繁难。类似论说,宋人尤多。梁太济先生对此有精详研究,参其《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今据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参阅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乡村税收人员的工作日趋复杂化了,工作量也大大地增加了。这样一来,就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及时有效地完成上述各项事务(注:本处参考了王棣先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两文中的部分研究。)。这是中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乡役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三,按“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注:《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1页。)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人口相对固定的户籍制度,乡村民户对于地主的人身依赖渐趋淡化,有了一定的流动自由。在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宋代,佃户还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起移权,流动性也相对增大(注:参见先师漆侠先生《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朱瑞熙先生《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38—43页。陈明光先生《唐朝两税预算形式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见氏著《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民户的自由流动,和灾荒、战乱等因素导致的民户流移,不但使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也进一步给评定乡村民户的户等、征收赋税等带来了难度。由于宋代田产、户等以及其他家产的变动是极其频繁的,有限的人手难以胜任评定户等、征派赋役等繁难的工作,所以,在基层社会管理中,不但要增加乡村社会治安人员,而且也往往差派他们承担催税的任务。第四,乡役人数的变化,也是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尤其是与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的。自宋仁宗朝以来,三冗三费和积贫积弱、边境等问题就日益突出出来,此后,赵宋朝廷就陷入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窘局。疆域大为缩减的南宋更是如此,国家财政也更显窘迫,地方州县财政同样日益匮乏(注:参见前揭《王安石变法》(增订本),第18—27页。并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第三章,第257—268页;汪圣铎先生《两宋财政史》第一编诸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包伟民先生《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95页。两宋差役、募役之争,以及乡役人并无官方支付的报酬,而沦为“职役”,都是和国家财政状况密切相关的。这也是两宋期间役法中有“名募实差”现象及其一再更革的原因所在。)。既然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并确定根据产业的多少缴纳赋税,那么,具有这样或那样背景的形势户官户、豪强民户就会想方设法隐瞒田产,贫穷不能自存的民户则只能蔽身于形势户,诡名挟户(隐户)、诡名寄产、诡名挟佃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并成为宋朝一大社会痼瘤(注:参阅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诡名挟户》,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5期。)。总而言之,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其所要求于乡役人者,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及时、足额完成税收任务,以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行;第二,保证基层社会秩序的安定。为了应对上述各种压力和社会变动,就需要向乡村民户征收尽可能多的赋税,以保证国家财政的运转。国家赋税本已沉重,而这些官无俸给的地方吏役还会对民户有更多的侵剥,这就导致乡村民户负担的增重。剥削量的增加,无疑又会引起民众各种方式的反抗,一些铤而走险者就时不时地对地方政府构成威胁。随着财政税收和乡村治安管理问题的突出,如何避免中唐五代以来基层社会失控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从税收和治安两个方面,加派替政府管理广土众民的乡役人员,也就成为宋神宗和王安石们治理国家的要务了,有关乡役问题自然也就引起了此后宋朝君臣更多的关注。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在这一时期,乡役人数也就发生了数量上的较大增长。宋代乡役人数的增长,其社会作用固应重视,然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另外,这一增长从某些方面也显现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趋势,但是,考诸于两宋社会之史实,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一趋向并非宋王朝政治制度的治理理念所在,而是从保证国家财政和政权稳定的角度,所转化出的一种统治意向。(注:习作先后承蒙王曾瑜、李治安、汪圣铎、黄宽重诸先生惠赐教益,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