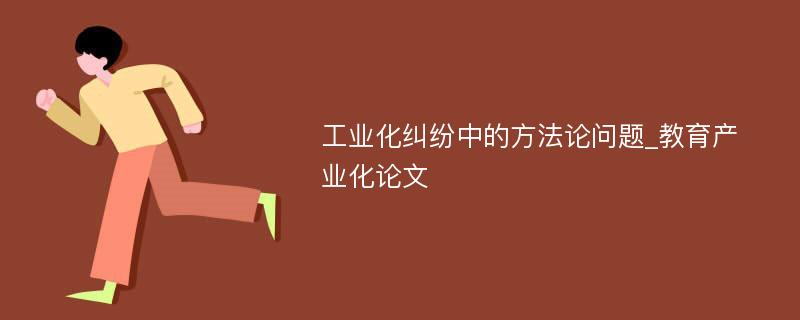
“产业化之争”中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5-0110-03
本文主要不在讨论产业化本身,不对产业化是否成立作出直接判断,而主要就产业化问题讨论中涉及到的方法论问题谈一些看法,并且,本文只就高等教育产业化讨论的范围而不泛指整个教育领域来叙述。
一、关于“化”
有人说,其所以反对产业化,关键在反对一个“化”字。意思很明白,提产业是可以的,提产业化是不可以的。
教育产业的概念早已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明确了。关于教育产业的提法,恐怕没有人直接反对了。中央的提法是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教育产业。可是,既然有发展,就会有变化,必然有变化。
产业化的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变化吗?如果指的是变化,那么,产业化就是指产业发展,产业变化。
如果所谓化不是指变化,而是指绝对化,似乎就不好了,恐怕不能绝对化。
是绝对,还是相对,这是个方法论问题。
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工业化,这个化好像不是绝对化,工业化并不是不要农业了,不要商业了。那时,工业化的指标是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而不是100%,不是绝对化。是化而非绝对化。
那时,也提出了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传统了,现代化的指向、程度、范围都有相对的含义。也不是绝对化,化非绝对化。
现在提干部年轻化,同样具有相对的意义,不是一律都只要三四十岁的人,六十多岁的人不是仍然可以当省长、部长吗?我们多少还带有一刀切的性质。格林斯潘七十大几了,还刚刚从联储下来;七十出头的人还参与竞选并选上了的例子也不少吧。艾略特当校长当到75岁,之后还做了十几年名誉校长哩。这都含有相对意义,并非越年轻越好。
产业化是不是绝对化?是不是一切都是产业?一起都讲钱?是不是讲产业化就是排斥公益,就是不讲精神面了?化均非绝对化,为何以为产业化乃绝对化?
不是现在还有许多化的提法吗?数字化,意味着凡与数字无关的都不要了吗?自动化,意味着一切手工都不重要了吗?
化,究竟是绝对化,还是发展变化,某种相对的变化,还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某种和谐,这是个观察事物的方法问题,是否影响到了人们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看法呢?
如果我们不是首先确立反对或者赞成的态度,而是首先弄清楚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可能更有利于心平气和地讨论。
二、我们反对的是什么
近日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事实上讲了许多客观探讨的话,文中的一些修饰语并不能让人们忽视它所说的不少平静论说的内容。比如,它说:“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推卸自身办教育责任的借口。”[1] 这表明,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为借口,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责任。若以此为借口而推卸了,那不是教育产业化的错,错在以之为借口。
又比如,它说:“有必要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部分教育服务特别是辅助性的教育服务也可以采取产业运作方式,但是不能把这些等同于整个教育的产业化。”[1]“适当地”、“一部分”,这些词表明的正是相对性,是相对变化,而不是绝对化,不是“整个”。如果产业化指的是相对变化,这段话就不意味着它反对教育产业化;如果指的是绝对化,结论就不同。所以,这段话也是很客观的。
还比如,该文指出,“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在少数地区出现了教育政策上的偏差”,“将公办学校挂牌出售”,“高收费、乱收费”,“这些局部现象被误认为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1]。这里,文章指明了这是一些“局部现象”,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现象本身不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这是很正确的判断。然而,这些现象是不是教育产业化本身呢?如果高等教育产业化就等同于高收费、乱收费,就等同于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人们有理由加以反对;如果高等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乱收费”的代名词,并不是“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代名词,反对的理由何在呢?所以,也有个方法论问题。如果为了反对一个事物,就把它等同于坏,反对的理由就有了;然而,它是否等同于坏呢?为了赞成某个事物,就把它预设为好,理由也有了;然而,它是否等同于好呢?这些判断当然与思想方法有关。
三、是派生,还是本身
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1]。其实,这些措施恰是有利于教育产业健康发展变化的,这恰是在文章前面的相对性理解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教育产业和谐变化之所需。这样,我们着重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名词用语之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容易导致一些错误行为。对此,同样面临一个方法论问题。是这个提法本身不好呢,还是它“导致”的东西不好?如果是本身,则有相应的结论;如果不是本身,那就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可能“导致”的东西发生,结论又不一样。
人身上长了一个肿瘤,是那个肿瘤不好,还是人本身不好呢?
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一些东西,是“导致”的那些东西不好,还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好呢?计划经济亦曾导致了不少东西,是这些东西不好,还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呢?事实作了结论,中央正式文献也作了结论。计划经济本身不好,所以,要根本改变;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划时代变化。市场经济本身被认可,但市场经济可能也导致一些不好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之更好。
我们的教育是否真切地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划时代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呢?
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市场经济,又过了一些年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提出了人权观念,这样,在我们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和谐的观念系统,人本的观念系统,改变着长期存在的非人本观念。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是体现人权的经济,教育是否深刻意识到中国社会发生的如此深刻的变化呢?
想当初,在市场经济于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中,疑惑和迟钝的是哪些领域?“警惕啊”,“防备啊”,这一类惊恐之语主要出自何处?其中,是不是也有思想方法问题?
四、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大家已经看到了,然而,这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根子在哪里呢?
为什么有的国家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程度更高却没有这类问题的缠绕呢?
为什么海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就在于提什么产业化而又有些学者认为恰在于没有真正实行产业化呢?而且,未必就只有这两种情形,未必高等教育的是与非就取决于对产业化的否定与肯定。
如果高等教育的问题真出在产业化,那么,真的让它成为“过街老鼠”,问题不就全部解决了?真会是这样的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质的差别在哪里?教育如果未曾对这一质的差别有所感悟,会有可能为中国在近20多年发生的划时代变化而真正感动过吗?会真的受到过震撼吗?
这一划时代变化绝非只是表现于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行政者是万能的。基于这一假设,其管理便是直接性的,支配性的。基于这一假设,便认定经营者必须是被直接管理的,消费者是被支配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于大学的直接管理大量存在并越来越增加着,扩大着,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细。这是基于一个假设:行政者才是走正路的,万能的,大学是盲动的,易走上邪路的,是不是这么个假设呢?
还有,物质与精神是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呢?钱是不是一定不干净的呢?强调产业是不是一定会抛弃伦理道德呢?说更宽一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意味着不要精神文明呢?是否还是那个“富则修”的理论才有效呢?
五、分歧真那么大吗
反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人反对乱收费、高收费,赞成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人,也是反对乱收费、高收费的,而且反对这样乱来的态度之坚定一点也不差。
反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人主张大学要把学术、把精神放在优先的地位,赞成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人也是持有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同它相适应的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习俗等也是更先进的、更高一个层次的”(北大教授赵靖语)[2]。
反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人认为不能推卸政府对教育的责任,赞成产业化的人也这样认为,只是还认为政府在对高等教育大力投资时应尽量不采取无偿投入的方式。
这样看来,分歧究竟有多大呢?未必就是一个“化”字之争?
再者,既然中央已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教育产业,这就意味着要扩大教育产业,改革教育产业,增强教育产业,在扩大、改革、增强和发展中难道不会有巨大变化?
不说“化”字,可不可以说“变化”二字呢?更重要的是,为了认真贯彻发展教育产业(当然也就是发展教育事业),我们可不可以更多地更优先地集中精力地考虑如何来促进教育产业的巨大发展变化呢?我们是否认真地考虑了发展高等教育产业?是否有切实发展这一产业的实际构想?是否正大力增强大学在人才市场、科技市场、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呢?是否有让我们中国高等教育在大力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同时让我们在世界教育贸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盘算呢?是否有让中国在世界教育贸易中占有更大份额的追求呢?是否有一个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产业的同时如何大力提高我们大学的精神境界的战略呢?是否认为大学是可以在更高水平之上把精神与物质和谐统一起来的机构呢?是否认为这种和谐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呢?这样是不是才真正称得上是在积极贯彻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产业的方针呢?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优先地充分地考虑,就去争论该不该说“化”有什么意义呢?优先地充分地考虑了,相信分歧就更小了。如果以为反对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是政治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那么,这个思想方法就更有问题了。更多的是实际地做,用更好的发展、更多的成就来说话,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产业更加发展壮大起来,这是根本。
实在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改革还亟待深入,根本的出路在改革,真心实意地切切实实地进行改革。
标签:教育产业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