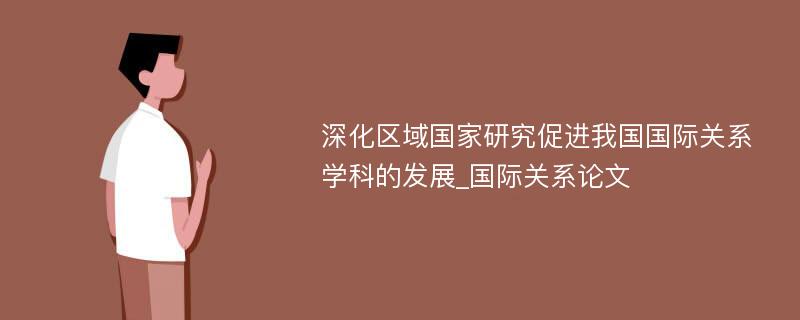
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别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学科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被分为特殊的与普遍的两大类,前者是本土和地方的,后者则是普遍和一般化了的。[1]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区研究就属于前者,而通常被作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则属于后者。地区国别研究的深化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地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1.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 地区与国别研究一般称为地区(区域)及国别研究,在中国一般习惯地称为地区国别研究,也可简称为地区研究。 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个部分。后者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详尽个性特征,前者则致力于在对比抽象各种地区现象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揭示作为一类国际关系现象的普遍性规律。与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追求普适性、规律性的一般知识不同,地区研究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基于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 如果将国际问题研究划为国际关系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当前现实问题三个部分,那么地区与国别研究就其基本属性无疑更接近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依赖的经验素材无非来自历史上或是当代正在演化的国际关系实践。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地区研究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归纳、综合和演绎。而国际关系史也是对各个地区国别史的整体综合与超越,其未来研究的深化有赖于地区国别研究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关系历史细节及其内部根源与互动的还原和呈现。随着学界对于主流欧洲中心叙事以外更多非西方区域国际关系历史兴趣的增强,地区研究在丰富和填补同期的区域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从上述地区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到,地区研究不仅是国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际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2.地区国别研究与国家地位 地区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涵盖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人口、语言到社会等诸多兼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学科领域,作为一种跨学科门类的地区研究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更确切地说是冷战和争霸所催生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中,弱小国家通常只能盯住大国,而全球性大国却不得不随着国家利益的外延扩展去深入理解由地区和国家所构成的全部世界。 地区研究是一项颇费成本的长期战略投资,需要不间断的经久投入,其道理类似于国家对于供养军队和发展军备的投入逻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哪里爆发,时刻保证一支广泛而能干的专家储备队伍就成为大国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必要代价。而保持这种对于其他地区的深入了解不仅为明天的大国地位上了份保险,也是维持一个开放、好学和批判的国内社会的重要条件①。大学以及智库的区域研究成为区域知识及其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但保持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有时甚至意味着需要忍受为研究者和学生频繁的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近似于度假、旅游式的多种活动提供资助。它的投入成效的衡量往往是模糊和难以言说的。如果危机确实爆发了,地区研究专家和储备人才或许有机会证明这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应急储备投资是富有战略远见的;但更为成功的地区研究相反却致力于预防危机,通过敏锐的警觉和灵巧的外交手腕使可能的危机消弭于萌芽状态。面对这一奢侈的事业,即便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经历过多次的意志动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都一度大幅削减对于地区研究的经费支持,直到“9·11”事件后才出现昙花一现的短期反弹。因而绝大多数国力有限的国家宁愿使用有限的资源来制造真实可见的武器弹药,但许多国家可以拥有强大军备,却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发展起发达的地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拥有领先的国际关系研究。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力量的崛起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真正体现其霸权的地方在于他所拥有的对于隐藏于其他国家内部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体系、地方经济与人文地理所具备的无可匹敌的知识和了解。这种了解建立在一个个由兼具对当地社会的语言掌握、历史敏感、深入体验和知识兴趣的学者、研究生、本科生所组成的知识群体之上。查尔斯·金不无自豪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或是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省一级单位的地方政治问题的掌握研究证据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他的话可能是片面的,但却是事实。[2](P90),这正是发达的地区研究所提供和体现的全球性大国的智识根基。而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优势往往会延续到霸权之后,地区研究的发达程度往往也是国际关系史上霸权兴衰在学术领域的投射。欧洲依然是美国以外地区研究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则是其中的翘楚。拥有百年历史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昔日帝国利益富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享有的蜚声世界的学术声誉和非凡实力无疑也是旧日“日不落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权投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落日余晖。 二、中国地区研究的相对滞后 尽管近3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众多不足,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地区国别研究的发展滞后和欠发达。 1.中国地区研究的欠发达与不平衡 在学科建制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是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政治学二级学科的方式存在的,地区研究实际上仅仅是国际关系学者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而已。如同许多学者意识到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更多的国别地区研究专家而不仅是国际问题专家。考虑到地区研究独特的知识属性及其习得过程,比“理论化程度”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真正的地区研究专家需要经历一种被政治学者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称之为“浸润而后突破”(soaking and poking)的过程,也即需要学会所研究国家或地区难懂的语言、深入了解当地陌生社区的生活、弄明白它复杂的历史与文化。[2](P94)更直白地说,地区研究者需要先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知识、经验、思维构成的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中去,在此基础上又得走回来,回到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知识中来。依靠这种在对象国实地生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者能够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知识的不断更新。[3](P91)它追求的是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的一种“复合”效应。[4](P64) 基于地区研究的上述特性,一个高水平的地区研究学者不仅具有关于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而且必须较为熟练地掌握本地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是官方语言,甚至应该包括当地的方言③。如果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的队伍及其培养,能够合格的恐怕仅有对美日俄以及个别欧洲国家的少数国别力量能够达到标准。这就形成了研究对象与当地语言的断裂,以至于众多号称某地区、某国家的专家学者却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而仅仅依靠英语世界的第三方知识来展开研究。苏长和就认为,我们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认识过多的依赖于西方的英语学术世界,缺乏客观和以我为主的认识体系,存在被误导的风险。[5]当然,这一情况在作为当前地区研究知识主要供给者的美国也正日益回潮。30%的美国该领域研究者表示只掌握英语一种工作语言,50%以上表示他们在工作中很少甚至从不引用非英语的资料。这种现象被视为美国地区研究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2](P92)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们窘迫的发现这种过于依赖英语学术世界的有色望远镜的局限和不足。姑且不论是否“我们中间真正愿意懂得中亚、南亚等区域人民的人太少”④抑或“忽视了西亚北非地区深度的区域国别研究导致的自身知识、信息和人才储备不足影响了参与地区冲突治理的能力”,[6]即便仅就沿线涉及的66个国家的40多种官方语言而言,国内目前教授的就只其中20种,在这20个现有语种中有11个在读人数不足100人、8个不足50人。[7]目前国内开设语种最多的专门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能够提供的70个语种尚不能覆盖我国建交国家涉及的约95种通用语言,也不及美国哈佛大学90个语种的教授能力。纯语言专业的数字尚且如此,其中能够从事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就更加不容乐观了。因此,即便不使用“落后”这样扎眼的词来冒犯尽管为数不多却依然存在的真正地区国别研究专家,对于总体的地区研究来说,谓之“不发达”、“欠发达”却也是事实。这种“欠发达”的表征归结起来是两点:一个是地区研究要求的“浸润然后突破”式的人才队伍及其后继储备培养的不足,另一个则是地区研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即对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以外国别地区的“浸润而后突破”的专家及其后继人才的严重不足。 2.中国地区研究相对落后的原因 如果说一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体落后,或者直言说是其理论化、国际化程度过低,那么,随着国际关系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崛起,地区研究的依然滞后就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落后,而要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观念上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中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在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分属不同学科和学院,且相互之间联系并不密切。一方面,外国语言是与文学联系在一起,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基本隔绝,根本不可能就国际问题研究方向进行所谓“浸润而后突破”的持续培养和研究;另一方面,除部分外语类院校和极少数综合性大学外,绝大多数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只重视英语,即使是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语专业在师资队伍和招生人数上也都已出现萎缩,更遑论其他非通用型的小语种专业。在中国,尽管地区研究被置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下,但在最基础性的语言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上却一直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就使得在此情况下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地区研究人员对于除使用几大通用语言的主要大国以外的广大国别地区的研究不得不借助于英语世界的第三方知识,从而固化了英美世界在地区研究领域的知识霸权地位,也隐藏着苏长和所说的“误导”甚至于思维“美英化”的隐忧。随着中国崛起和与外部世界的日益深度交融,除了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各行各业对于兼通对象国别(区域)的语言和国际关系状况的应用型人才的用人需求日益高涨,而这就高校国际问题的教学研究而言也意味着大学专业人才“供给”与社会用人“需求”的脱节。 其二,专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两支力量研究倾向明显背离。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主要有两支基本队伍,一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的有关院所及相关部委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院⑤;另一支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相关院系⑥。前者具有比后者更为雄厚的专业人才和文献资料优势,他们的研究范围总体上几乎覆盖了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长期跟踪和从事地区研究的重要阵地,但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侧重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及对策研究,在综合分析与宏观理论指导方面深度不够,同时因受到当地语言和田野调查等方面的限制,就整体而言离“浸润而后突破”的水准也尚有距离,但依然是目前国内地区国别研究最强劲的力量。而后者人才培养规模占优,研究队伍人数众多,但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生培养中因广泛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模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只能放在基本理论和宏观分析方面;同时因受到师资队伍编制和教学资源的限制,即使是有地区研究也只能是集中在主要地区与主要大国方面。随着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招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这种培养模式也造成同质化现象严重。教育部先后实施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相关国别区域基地和“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两批次大工程都旨在聚合各高校中现有的地区研究力量以强化其理论和政策研究,迄今仍没有在有效融合两者优势强化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当然专业研究机构中的现有体制安排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大国偏向,对于中小国家的跟踪研究也仍有待细化和深入。这种重理论轻实际、重综合轻解析、重大国轻小国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和关注程度。两支队伍的研究倾向因此出现了分化和背离,最终使他们各自具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其三,国家公派留学机构在资助派出人员的规划设计方向上的失衡。出国留学对于所有学科都有重要意义,[8](P112-114)但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地区研究尤甚,区域研究与国际化教育和交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国家公派留学主要资助方向集中在美欧发达国家。留学人员个体出于自身研究兴趣和国外研究水平的考虑,绝大多数也愿意前往各方面条件更为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因此,考虑到地区研究对于国家特别是大国的重要意义,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采取激励措施以保证前往各个国家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的相对平衡和代际传承需要。教育部自2010年起开始实施“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每年的选派人数在1 100到1 350间波动,尽管只占当年全部公派人数的3%—5%,本应能基本满足对于各个地区国别研究人才储备培养的基本需求,但其对于国际问题研究与外语类人才的区隔使其在严格标准意义上的“地区研究”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上的应有成效大打折扣。在“一带一路”倡议暴露出我国地区研究方面的不足后,特别是该项目自2015年起开始将为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人才支撑作为主旨更新后,相应的更具针对性、战略性的规划调整和完善也应提上日程。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必然要面临语言问题,因此,美国大学从获得资助开展区域研究伊始便一直强调外语教学的重要性。[9]国家层面的留学资助计划如果能在国际问题研究的指导下结合地区研究所需的语言和其他专业知识形成长期定向培养计划,无疑将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加深对国外地区与国别的理解,从而提升地区研究的水平,进而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更上一层楼。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加强外语与国际研究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大学人才培养中基本理论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完善公派留学的规划设计是提升我国地区与国别研究的重要途经。 三、加强地区研究推动国际问题研究 1.加强地区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 地区研究的相对滞后构成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短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则把这一点更为突出和紧迫的暴露了出来,相关实务部门亦有抱怨在制定和规划方案中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获益甚少。中国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必须对外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深入的理解和足够的知识准备。强大的软实力、话语权和发达的公共外交需要建立在发达的地区研究基础之上。地区研究由于其需要大手笔、长时间“烧钱”的性质使其成为“一门大国特有的研究门类”。[5]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自我的认知不得不反过来仰仗至少也是深受地区研究发达的大国的影响。在我们矢志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征程中,有必要发展自身的地区研究以检验和校正以往依靠英美世界提供的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知识,以自己的“眼镜”来重新发现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理论和开展精细化的对外交往。 2.加强地区研究是中国国际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具有鲜明的大国属性,以至于国际关系研究被视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⑦。然而近年来,与中国崛起的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相一致,在长期引领国际问题研究的美国学界哀叹“理论已死”而转向基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折中主义”之际⑧,以秦亚青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过程建构主义”⑨、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⑩、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11)为标志的宏观理论范式上的开拓性进展也在逐步呈现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中国崛起”。就其理论创造的知识来源而言,除了唐世平走的是完全“西方知识体系内的和平崛起”,阎学通和秦亚青的理论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借助了“地区研究”提供的知识背景,只不过这一地区恰恰是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及其历史经验而已。 因而,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而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突破可能需要更多的有关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的知识来提供经验素材。秦亚青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近出现的“知识转向”中获得启发,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通过思维分析获得的普适性通则仅仅是一种表象性知识,在此之外还存在着由行为者历史、经历、文化和过往实践构成的地方的、具体的背景性知识;这种背景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为者的行为逻辑,其存在也为基于文化背景、实践经验、思维方式的地方性知识预示的多元理论发展打开了空间,在知识论层面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合法性基础。[10]这种对于不同地区背景性知识的获取主要依赖的正是地区研究的发展。通过地区研究的发展提供的广大非西方地区和西方世界内部国别和地区的精细化经验知识素材,无疑将真正有助于将当前主要理论赖以立足的西方“普遍性知识”还原其“地方性知识”的本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甚至于整个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3.加强地区研究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建议 自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以来,各高校普遍加大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基于自身特色推出了不少新的措施。例如,清华大学率先在当年启动“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于2012年开始招生、北京语言大学2014年起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在已有自设二级学科“中东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在2015年起也在政治学硕士点自设“区域学”专业招生。 坦率地说,比起开设地区研究专门学位点,更重要还在如何操作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真正在地区研究的后备人才培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针对上文分析指出的造成我国地区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现状以及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6年“两会”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专场记者会上的答问(12),我们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就强化地区研究特别是其人才培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暴露出的我国地区研究的不足并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上新台阶。 其一,强化外语学习硬性要求,提供更多语种选择。国际问题研究对于英语有着较高要求,地区研究更是要求深度掌握对象国别地区的通用语言,掌握对象国别地区的语言才能深入理解研究对象,掌握英语才能及时了解占主导地位的英美同行的研究动态。因此,对于发展国际问题研究导向下的地区研究而言,通常需要学生同时掌握英语和研究对象国别地区两门外语。美国本科教育通过其通识博雅教育理念,通常以要求在人文领域选修课程形式实现双语要求。国内北京大学也已在博士生阶段要求国际问题研究专业学生修习两门外语,但可选语种基本仍局限于几大主要通用语言。为强化地区研究、培养高质量相关储备人才,有条件高校可从本科阶段起强化这一要求,通过校际合作和聘用母语外教的形式为国际问题研究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多语种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的多重选择,提升语言学习在国际问题研究类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比重。 其二,扩大跨专业合作力度,允许个性化培养需求。地区研究本质上是一个跨专业研究领域,全球化时代任何专业都有其国际化面向的知识要求。在地区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提供的专业学位项目都是具有高度针对性的,例如一个国际管理学位可以有中国、日本、中东等体现在学位上的针对不同国别地区的具体方向细分,从而大大提升了专业的精细化。英国本科教育多实行双学位项目,甚至有“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三个学科方向相融合的项目,在为学生提供多学科知识和视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目前如人民大学在本科生中已有“国际关系—新闻学试验班”和“PPE”等跨专业合作项目,未来有条件院校还可逐步在强化地区研究的大方向下,推动学生在“国际关系(特定国别地区)+双外语(其中一门为对应国别地区的通用语)+”的模式下自主选择地区研究涵盖的经济、历史、管理、新闻、社会、法学等多学科中的一个,采以跨学科导师组形式实现个性化培养需求,以适应地区研究的全面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的高度市场化的用人需求。如同袁贵仁部长指出,高等教育转型关键是调整专业设置,核心在人才培养模式。 其三,加强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实现理论与政策并重。上文在分析问题时提到专业研究机构在地区国别相关的具体问题、文献资料、政策研究和专业人员队伍上较之高等院校的优势。袁贵仁部长也明确指出,现有高等教育过于集中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造成同质化和就业上的结构性矛盾。地区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样可以有学术型和应用型的区分,学术型人才可以在长期钻研的基础上从事和发展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的理论研究,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以为外交政策和涉外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化有深度的服务。现有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可以借鉴协同创新平台的模式,加强与高校以外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聘请专业机构人员参与课程教学和定期讲座的形式,为一部分有志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学生提供更偏实务和政策性质的培养计划,也为学术型人才了解政策研究提供便利。 其四,适当调整公派留学项目结构,适应地区研究人才成长需求。从培养地区研究专门人才的内在要求来说,目前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采取的既要求前往研究对象国又派往发达国家的双留学目的地模式是最适宜的。前往研究对象国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同时前往在该研究对象(国别或地区)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有助于进一步在自身经验基础上把握国际前沿动态,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水平,值得借鉴。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现有的“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的选拔要求和培养机制以使其更具针对性。该项目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项目应全部调整为外语加特定国别地区的复合型人才项目,其余不掌握或不准备学习对象国语言仅以特定国别地区为研究课题的人员可全部调整至“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等其他一般性项目中去。同时应加强对该项目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派出对象国的规划设计,首批可先覆盖“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以满足眼前需求,采取在一定时段内分别前往对象国一年以及英美研究该对象国的主要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半年的复合形式,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均可参与的自愿报名和基地推荐相结合方式,并在派出人员回国后对语言基础和专业基础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加大资助力度并对合格者可给予一定程度奖励以鼓励和引导留学方向。同时为满足地区研究要求与研究对象国别的定期交流的需求,对于已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业的符合语言和专业要求的研究人员,按照自愿申请方式准予不受5年内不得重复申请留基委资助项目的现有限制。 以上四点的落实对于现有的大学学科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不小的挑战,但对于发展地区研究并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跨越式发展都是大有帮助的。 自改革开放以后引入国际关系学科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质的飞跃,无论从教学研究队伍、开设专业院校、在校学生、学术期刊、出版著作、学术团体等各方面规模指标衡量,都已是全球范围内唯一可以比肩美国的。近来随着国内学者在宏观理论建构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也在质量上进一步拉近了与美国同行的距离。相对而言,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另一块的地区研究明显滞后,也制约了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创造上的进一步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以此为契机加强地区研究正当其时。1957年苏联抢先发射人造卫星带来的“卫星时刻”将美国的地区研究从原先私人基金会推动的零散事业变成了从立法和财政上获得全面保障的联邦事业,带来了美国地区研究的迅猛崛起,奠定了其在地区研究领域的智识领先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带来的现实需求和部分院校在地区研究人才培养上的大胆创新和先行先试,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校将会投身于地区研究的发展及其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二十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时,那将会是以地区研究为着力点开启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继续崛起的又一段“新征程”。 ①Charles King,"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Foreign Affairs,Vol.94,No.4,2015,p.90,pp.97-98;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F.福山:《学术界何以有负于国家:区域研究的衰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在美国,“理论化程度低”通常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批评质疑地区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王逸舟教授在2006年也曾以此为标准,评估认为“中国的国别与地区研究水平并不算高”。参见Christopher Shea,"Political Scientists Clash over Value of Area Studies",The Chronicle of High Education,Vol.43,No.18,Jan 10[th],p.A13-A14; Robert H.Bates,"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A Useful Controversy?",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0,No.2.1997.pp.166-169;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涉及中国研究的可选开设语种除了普通话还细分有藏语、蒙古语、粤语和闽南语;美国哈佛大学仅在非洲研究方面就能开设24个语种的课程。 ④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片建立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八个研究机构;部委所属机构以外交部下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家安全部下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最具代表性。 ⑥据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9月,中国高校共有115家设立了一个以上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60所高校招收国际研究类本科生,93所招收国际研究类硕士研究生,26所招收国际研究类博士研究生。 ⑦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Vol.106,No.3,1977,pp.41-60;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432-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⑧David A.Lake,"Theory is Dead,Long Live Theory: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567-587;[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⑨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8,No.1,2016,pp.33-47. ⑩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11)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31-55,该文中文版可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Shiping Tang,"International System,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7,No.4,2014,pp.483-506. (12)记者会全程文字实录与视频参见:“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答记者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zhibo/20160310d/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