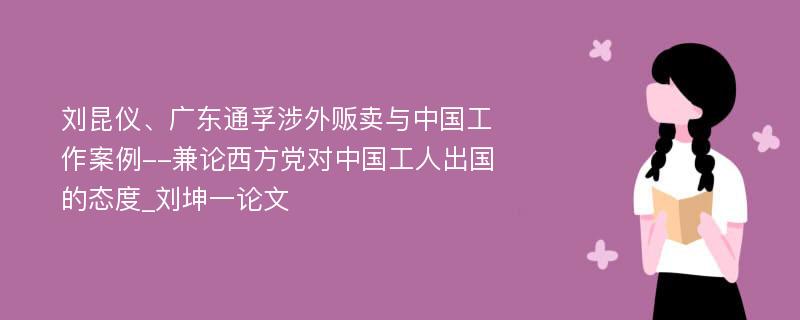
刘坤一与广东同孚洋行拐招华工案——兼论洋务派对华工出洋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工论文,洋务论文,洋行论文,广东论文,派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契约华工出洋,始于18世纪之后,在19世纪50年代后进入高潮,至20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在这前后约200年的时间里,出国的华工逾一千万人次,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长期以来,由于上述过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侵略扩张、殖民者掳掠人口为奴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华工出洋进入高潮之际,又值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阶段,办理者多是历来被认定有媚外倾向的洋务派,因此,华工出洋成为中外交涉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
刘坤一(1829-1902年),字岘庄,清末重臣,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光绪初年出任两广总督期间,在广东这一中国契约华工出洋最早、人数最多的地区,在华工出洋进入高潮之后,曾作为洋务派当政中的直接出面者,办理了以美商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华工出洋的中外交涉案件。目前,对洋务派在华工出洋问题上的流行看法,是洋务派不仅签订了一系列出卖华工利益、帮助殖民者的条约,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较之他们之前的当政者更“变本加厉”地不顾民众死活,等等。但是,若能较客观和冷静地观察一下刘坤一对同孚洋行拐招华工案等的处理,即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诚然,从方法论上说,处于广东一隅的刘坤一的所作所为,并不足以概定整个洋务派对待华工出洋的基本态度,但是,由于事件的特定时间和地区的代表性,以及事件涉及到的李鸿章乃至总理衙门的关系,却又较完整地反映出了一定时期交织在华工出洋上的多种矛盾及其走向。
一
刘坤一对美商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案的处理,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氛围。
1860年,英、法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强迫清政府将允许华工“自愿”出洋写入条约,使诱骗中国民众充当苦力,即18世纪以后在中国沿海出现的,将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对象的海盗式贸易进入了“合法化”阶段。自此,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西方殖民者更是蜂拥而至,争相掠贩人口,加之这时国内灾荒不断,阶段矛盾激化,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清统治者对闽、粤民众的疯狂镇压而促成的民众大批逃亡,契约华工的出洋达到了高潮。
秘鲁也是这时蜂拥而至的西方殖民者之一。虽然在1874年之前中国与秘鲁并无条约关系,秘鲁不能“合法”地在中国“招取”契约华工,但在所谓的“利益均沾”下,在各列强的庇护下,到19世纪70年代初,它却已在中国通过各种手段,诱骗了“不下数万人”①。更为严重的是,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为后起者的秘鲁较之老牌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残暴野蛮,使在秘鲁的华工陷入了最为悲惨的境地,就连当地的西方人也认为华工受到的待遇,是“俱非人能受者,与猪狗一般”,“华工所受之苦,较之黑奴更甚千万倍”②。这样,1868年末,不堪忍受的在秘华工历尽艰辛,终得以通过美国驻秘鲁公使向清政府要求保护③。
1874年6月,清政府在英、美等国的诱迫下,与秘鲁订立了《中秘通商条约》,但鉴于此前秘鲁对华工疯狂虐待的事态严重性,清政府还是坚持在条约中写入了只许民众“自愿”往来,“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严行禁止不准在澳门地方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等条文④。所谓“自愿”,除了强调出洋华工是自己自由选择前往之外,清政府就是要想去除那些“别有招致之法”,即诱骗、拐架、囚禁等方法,限制苦力贸易和猪仔贩运,达到英、美当局在那时香港所标榜的那种赊单工,即所谓的自愿自费的“自由移民”。澳门一贯是掠贩人口的老巢,是苦力贸易的罪恶渊薮,各通商口岸,亦是殖民者掠贩中国民众的主要场所。显然,客观地说,清政府意在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应,对凶残的秘鲁新殖民者在中国诱骗华工做苦力进行方法上和地域上的限制,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秘鲁在华拐招华工有所约束;同时,也据此希求秘鲁以“自由移民”身份对待在秘华工,改善华工的待遇。然而条约签订后,秘鲁方面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虐待在秘的华工依旧,故清政府在派陈兰彬、容闳正式出使美、秘、古等国谋求保护华工的同时,于1875年末将容闳此前奉派秘密前往秘鲁调查的真相公诸于世,使中外舆论为之哗然,特别是赴秘鲁华工人数最多的广东地区,更是群情激愤。
在因秘鲁虐待华工而激成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态势下,1875年9月,刘坤一从署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并于1876年1月行抵出洋华工问题最尖锐、民族感情最激烈的广东就任。刘坤一生长于闭塞而民风强悍的湘西,加之自幼饱读儒家经书,具有十分传统而强烈的民族色彩。如他在到任广东之前的十年江西巡抚的生涯中,当目睹在一系列教案中传教士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和大炮刺刀的支持,“从中把持,务遂其欲而后已”⑤,认定“天主教之败坏民风,有碍吏治,难以言罄”⑥后,便借江西人士排外的正统意识和力量,屡屡抵制传教士的传教之举,结果是“洋人屡来屡却,至今章门尚无教堂”⑦。另一方面,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从异途进身封疆高位的他,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一分忠诚,一直以为朝廷“安民”为己任,并因之受到朝廷的赏识获得高升。因此,在对待在秘华工问题上,当清政府为安抚民心而通过《中秘通商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以及公布容闳调查结果表示了基本态度后,在粤中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刘坤一就更加重视新的“安民”问题——华工出洋了,例如1876年6月,他据奥中人士之请,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在美洲各地设立领事,“庶奥人不至常多欺陵”⑧。接着又分别致函南洋大臣沈葆桢及驻美国公使陈兰彬,请设法保护华工。
这样,在《中秘通商条约》对秘鲁诱招华工做了一定的限制,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态势下,甚而在刘坤一等地方督抚有了上述较为明确的欲保护出洋华工的倾向出现后,秘鲁已很难直接自己出面诱骗华工了。但是,秘鲁从1820年获得独立后,从国外输入劳工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就是其立国的国策之一。参加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人口,以诱骗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契约劳工,即廉价的劳动力后,使秘鲁殖民者尝到了极大的甜头,这就自然难于使它放弃这一实质上在中国沿海进行的海盗式人口贸易。于是,在上述历史态势和氛围下,秘鲁殖民者采取了暗渡陈仓的手法,它与设在广州的美商同孚洋行联手,“每年给该洋行银一十六万,以五年为率”⑨,由同孚洋行出面拐招华工送往秘鲁,这样,该洋行随即在广东番禺暗设了所谓江元记栈,开始以垫支路费为条件,以出洋时必由地方官点名并保护为词,欺蒙招揽华工。
与同孚洋行拐招华工的行动相配合,1877年12月,由美国驻粤领事林干出面,要求刘坤一出具告示,向民众声明在秘鲁找工容易,工价甚高等等。对此,刘坤一认为是“近于设法招致,为条约所不准行”⑩,当即予以拒绝。加之秘鲁派来运载华工的船只在香港被标榜只搞所谓“自由移民”的港英当局驱逐,秘鲁这一次拐招华工的第一轮行动即告流产。然而,秘鲁以往在厦门一带拐招华工时,曾得到当地地方官相当的配合,从而认定“中国地方官于此事无不乐从照办”(11),积极筹备再次行动。这样,一面是不拐招到华工决不罢休的秘鲁殖民者,另一面是遵清政府命令且民族色彩极强的欲禁止秘鲁拐招华工的两广总督刘坤一,一场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
二
1878年5月,秘鲁殖民者直接派船抵达广东黄埔,志在必得。同时,江元记栈加快步伐,大肆拐招华工。然而,也正是这些放肆的活动,露出了暗设的江元记栈拐招华工的尾巴。5月10日,该江元记栈被痛恨其所为的居民报官,随之被查封。这样,不仅使拐招之事又一次搁浅,而且,江元记栈的包头还不得不供出了拐招实情及后台,惩办拐匪案随即转为中外交涉。
案发后,林干即闻讯赶来面见刘坤一,称同孚洋行是照1860年的条约办事,而且秘鲁也可以“利益均沾”,振振有词,气焰嚣张。在这凭借不平等条约的林干的挑畔面前,刘坤一何以应对呢?其实,林干的振振有词,只是侵略者的一面之词。因为尽管清政府在列强的刺刀下被迫开放海禁,对华工被拐卖出洋的事实予以承认,而且承认中也不乏将生计无着的民众推出外洋的因素,但鉴于列强所谓的“契约”,实际上是先垫船资,然后以还船资为由,长期甚至终身盘剥华工,为了体现“皇仁”,固结民心,清政府即于1866年制定了《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其中对华工出洋做了细致的规定,而有的对列强拐招华工有一定的限制,如要民众自愿,招工必须中外一起设局,不得外方私自设立,要通过中国官府,等等(12)。因此,这对刘坤一而言,无疑有了交涉的准则。加之,1875年8月,清廷还密发了“设法保护在秘华工严禁暗中在华招工”的谕令,就更使刘坤一不仅有理有据,也有底了。于是,他便逐条对林干进行了驳斥。林干“无理混事,哓哓不服”,数次交锋后,改口称这次只是搭客而不是招工,妄图以此避开拐招的实质,双方陷入僵局。
不过,自感有理且不满秘鲁拐招华工的刘坤一并没有被上述僵局所束缚。5月14日,他照会林干,指出同孚洋行“私设店铺,招聚数十人,发给盘费,议给身价,前往秘鲁当工,以不准招工之国,招致内地民人出洋,即是拐卖猪仔”,正是中国禁止之例,要求林干“应即饬令停止招工,将船驶出外洋”(13)。同时,还采取了禁止拐招的实际行动,令粤海关盘查被拐招之人,对同孚洋行的过关船只严加检查。秘鲁驻中国公使安禄谟原来对这次的“招工”抱有极大希望,眼见刘坤一如此强硬,不免气急败坏,于是便加紧了与林干的狼狈为奸。6月3日,林、安两人率美国海军官兵多人以旁听为名,突然闯进海关公所正在盘问被拐华工的现场,竟将在场的华工强行带回同孚洋行。不仅如此,4日,林、安等再度率兵到刘坤一处进行“要求”。刘坤一忠于职守,不为所动,守定条约“往复辩论逾时之久”,终使安、林等“默然退去”,并使之将被强行带走的华工交还。应该说,一个弱国的地方官能在武力的威胁下守定立场,据理力争,是值得肯定的。6日,粤海关再次传问被拐招的华工,在已无威胁的情况下,华工纷言被拐真相,一些人当场“掷票而去”。证据确凿后,刘坤一乘胜追击,令将已被骗上船的华工“尽数提出,不准出洋,并照条约,将该轮罚办,以昭炯戒”(14)。
安禄谟当然对刘坤一的处理不服,即北上津京,串通美国公使何天爵与中方进行交涉,虽然安禄谟在数次交涉中,或“一味软磨”,或“复以此事相纠缠”,但总署特别是谈判大臣李鸿章,却“毫不为动”,或“据理驳斥”(15),坚持维系刘坤一所办结论,使安禄谟无功而返。至此,美商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案,以中方守定条约而获胜结束。
应该说刘坤一具体办理的这一案件,在那时的华工出洋问题上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因为清政府的《续定招工章程条约》由于对外国殖民者进行了一些限定,所以列强一直不予承认,清政府只是单方面坚持施行。因此,这次的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案,实际上是1866年的章程公布及有关限定秘鲁拐招华工的条款制订后,中外双方一次最大而公开、直接地对上述条款能否实行的较量。刘坤一是这次较量中中方的首当其冲者和案件的主要处理者。他早在抚赣期间与列强的交涉中,就得出了他常津津乐道的“守定条约”的交涉方略(16),这时更由于国内特别是粤中民族情绪的影响,使他在整个交涉过程中表现得坚定而有民族气节,而且分寸把握得颇好,故而大受称赞,如总署认为他“自系按照秘约办理;甚为妥协”(17)。李鸿章也说:“此案粤中办理甚为得法。”(18)而在客观效果上,刘坤一守定条约办理的结果,不仅挫败了秘鲁在中国沿海一次大规模的拐招人口的计划,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清政府有关条款的权威。总之,在禁止殖民者拐招华工上,通过处理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猪仔所反映出来的刘坤一,乃至李鸿章及总署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且客观效果也是有益的。
三
那么,刘坤一,乃至李鸿章和总署禁止秘鲁违约招工,是否意味着他们不主张华工出洋呢?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他们在整个华工出洋上的态度进行透视。
其实,他们在华工可否出洋问题上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刘坤一而论,如就在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案刚结束,西班牙殖民者又接踵而至,在广东诱招华工,面对民众中不断有人前去应招的状况,他颇有感触地说:“夫广东有人满之患,准其出洋谋生,原地方官所愿意。”(19)就极鲜明地反映出了他对待华工出洋的基本态度。那么,他为何要主张华工出洋呢?1879年8月,德国要求搭载:“自备川资”的华工前往檀香山,他就此事致南洋大臣沈葆侦说:“鄙意以广东盗贼之多,甲于他省,推其原故,实因习于游荡,迫于饥寒,年来诛杀之惨,时觉恒然于心。……如使此等穷民、游民前往外洋谋生,而不至有日(即西班牙,时译日斯巴尼亚——引者)、秘两国之阱陷,又何必锢其所在,必留之于内地为盗受诛耶!”(20)可见,他的这一番表白,正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赞成华工出洋,虽然有解决民众生计的因素,或说将此作为解决无力应付的社会生计问题之法,但更主要的或说在根本指向上,还在于将此作为消除社会动荡、防止人民起义的妙方,是首先站在清王朝的基点上,是他在抚赣时形成的“宽猛得宜”的安民之术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
无庸讳言,刘坤一采取赞成华工出洋作为他在广东这一口岸地区为清王朝安民的策略,也有其客观因素。如前所述,中国出国华工人数从19世纪初逐渐增多,而这时国内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耕地不足而人口迅速增长,这方面沿海的广东尤其明显。据统计,1661年到1812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广东的人口增加了近20倍,耕地仅增加了27%,每人平均耕地以25亩降到1.67亩(21)。到鸦片战争前夕,总人口更达24,634,100人(22)。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人多地少的状态下,地权还被高度集中,极端繁荷的租税和各种超经济的剥削,使广大农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逃生。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式工业的建立有可能吸收流动人口,但在刘坤一督粤之际,广东的新式工业除官办的规模不大的机器局和火药局,以及刚购买来在进行修建的黄埔船坞等外,民办企业方面,只有陈启源于1874年开设的有“数十缫丝釜位”的继昌隆缫丝厂,虽然数年之后该厂规模有了扩大,且整个广东的缫丝业也有了包括新式企业和手工工场的厂家“百数十家”(23),但这时对广东巨大的过剩人口的容纳来说,是极有限的,况且,新式企业的建立,还有冲击旧有手工业,产生新的失业人员的另一面。如1881年,因手工缫丝者无力与机器竞争,纷纷破产,发生了手工缫丝业行会“锦纶堂”捣毁陈植榘等开办的机器缫丝厂——裕厚昌丝厂的事件,使继昌隆也被迫迁往澳门。而广东是中国最早与外国通商的地区,受外来影响较大,从明代起,就有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的现象,因而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构成和加剧的人多地少的状况下,广东成了全国契约工出洋兴起最早、人数最多的地区。换言之,广东民众的出洋谋生,带有某种一定历史态势促成的自发的、必然的趋势,因之在这一意义上,刘坤一赞成广东民众出洋,也有应客观需求的一面。
而且还必须注意到,刘坤一从其固有的为清王朝恤民和“安”民的思想出发,他所要求和赞成的华工出洋,主观上并非是要配合西方殖民者买“猪仔”,这从他设定的下述有关华工出洋的措施上明显地反映出来。首先,在他看来必须是使华工正当出洋,也就是所谓的“自愿”,而非被拐骗。他认定衡量的标准,关键是“自备川资”与否,以为只要是“自愿”并“自备川资”,就可以避免委身于人,倍受折磨的待遇了,他办理同孚洋行替秘鲁拐招华工一案,就是以此为原则的。实际上,从前面提及的清政府制定的,或说由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出面制订的有关华工出洋的几个条约,基本上均有此含义,换言之,刘坤一认定的这一衡量是否是“猪仔”、“苦力”的标准,正是他对清政府有关态度和立场的理解与执行。其次,在他看来另一个必要的措施,就是华工出洋后必须保护,而这种保护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设立驻外使节,利用万国公约和有关中外条约进行。如前所述,他为此就曾多次致函总署要求,并致函已有的驻外使节谋求保护华工,等等。他一再强调:“保护出洋华民,乃中国应办之事,自有之权。”(23)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同样不可不注意到的是,虽然他主张华工出洋特别是广东的华工出洋,有符合客观趋势的一面,甚而在一般意义上,民众走出国门也有打开眼界的可能,但这种赞同中首先带有将无生计的民众推出国门,从而为清王朝求安定之意。而更就他所说的保护出洋华工,即他设定的华工出洋方略与实际效果而论,由于是将一切寄托在所谓的领事权上,而那时作为弱国的清政府所具有的领事权,在那列强争雄、强权政治的现代世界中效力是那样的微乎其微,更由于那时西方殖民者对华工实行的是贪婪、欺诈和残忍的“东方盗人制度”(25),因而刘坤一乃至清政府不免一上来就棋输一着,他们所强调的“自愿”和“自备川资”,并不能保证华工避免贩卖“猪仔”和“苦力贸易”的陷井,他们所强调的领事权的保护,最终也不过是几乎毫无效果的官样文章。如1879年经刘坤一核准是“自备川资”并批准搭乘德国轮船前往檀香山的华工,抵达后,“果有甫经上岸即被揽夹押去勒工扣银,逼立合同情事,仍不免于诱贩猪仔之故智”(26)。总之,在西方殖民者阴险狡猾和野蛮残酷的掠夺下,刘坤一及他所从属的洋务派,他所效忠的清政府对复杂而凶险的世界政治认识的片面和欠缺,使得大多数出洋华工无法避免被奴役被侵害的悲惨命运。
注释:
①③《秘鲁华工向美国驻秘公使诉说苦情求援禀文》,同治七年十一月中旬,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96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禀贴》光绪元年十一月,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05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中秘通商条约》,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01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刘坤一,《各属教案已与各国使臣妥议完全结折》,同治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刘坤一遗集》(一)第216页。
⑥刘坤一:《复黄元善》,同治九年三月十七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312页。
⑦刘坤一:《复王爵堂》,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520页。
⑧刘坤一:《致总署》,光绪二年七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377页。
⑨刘坤一:《致总署》,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428页。
⑩刘坤一:《札复美国林领事稿》,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华工出国史料》,第一辑第三册,第1103页。
(11)《总税务司呈秘鲁人致在华洋人函》,《华工出国史料》第一辑第三册,第1084页。
(12)参阅《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华工出国史料》。第一辑第一册,第161页。
(13)《刘坤一札美国林领事及札柏税务司稿》,光绪四年四月十三日,《华工出洋史料》第一辑第三册,第1108页。
(14)刘坤一:《致总署》,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923页。
(15)参见《北洋大臣李鸿章呈报在津与秘使辩论情形致总署函》;《直隶总督李鸿章为美领事自拟秘鲁招工和议等致总署函》,见《华工出洋史料》第一辑第3册,第1134、1149页。
(16)可参阅《刘坤一遗集》(四),第1809~1810页。
(17)《总督为查秘鲁诱拐华工事致粤督刘坤一函》,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华工出国史料》第一辑第三册,第1082页。
(18)《北洋大臣李鸿章为美使包庇同孚洋行与秘鲁订合同运华工事致总署函》,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华工出国史料》第一辑第三册,第1139页。
(19)刘坤一:《致总署》,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432页。
(20)刘坤一:《复沈幼丹》,光绪五年八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467页。
(21)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页。
(22)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3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3)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58~46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4)(26)刘坤一:《复总署》,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五),第2523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