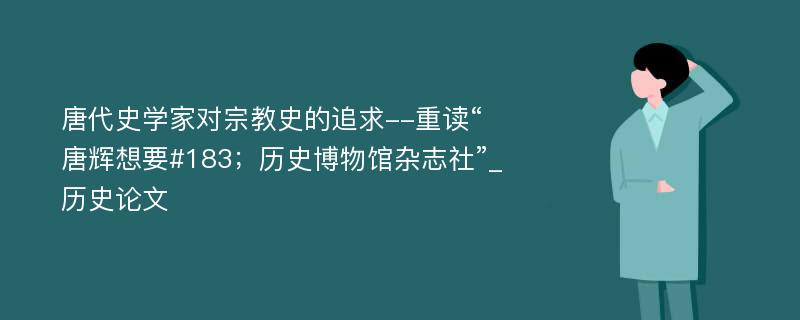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183;史馆杂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史论文,杂录论文,史家论文,唐代论文,会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4-0104-06
一、问题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从史学本身的属性和要求来看,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著《史通》,有“直书”与“曲笔”的专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揭示和概括。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激励着那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发出许多真知灼见,把史学思想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设立史馆,成为皇家的专职修史机构,往往也成为直书与曲笔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唐会要》中关于“史馆”有专卷记载,其中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细目。[1](卷63,64)近重读“史馆杂录”,对于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似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深感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而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史馆杂录”所载有关修史诸事,都与史馆有关,也就是与官修史书相联系。
唐初设立史馆,以其作为国家的修史机构。[2](卷43,《职官志二》)这一重大措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在于: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发挥了史家群体的修史作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命史馆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全部告竣。[1](卷63,《修前代史》)对此,唐太宗十分满意,他奖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显然,若非皇家出面,以史馆为基础,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这是做不到的。唐太宗晚年诏命重修《晋书》,[4](卷81)史馆汇聚了众多人才,以两年多的时间,新修《晋书》面世,也说明了史馆修史的成效之高。[1](卷63,《史馆上·修前代史》)
此外,史馆的设立,也为在史馆修史的史家提供了历史文献方面的便利,使其得以在公事之余浏览文献,完成自己的私人撰述。如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北史》,即属于此种情况。[5](卷100,《序传》)后来《南史》、《北史》得到皇家认可,唐高宗还为之作序(序文已佚),故也列为“正史”,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互为参照,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也撰修完毕。
唐初先后修成八部正史,成为中国古代官修前朝史“空前绝后”的盛举,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皇家设馆修史,为撰写本朝史提供了保障。以唐代而论,历朝实录的撰写连续不断,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6](卷58,《艺文志二》)只是到了唐末,社会动荡,有几朝实录未曾属稿。实录的撰修是撰写“国史”的基础。史家徐坚、刘知幾、吴兢、韦述等都参与过国史的修撰。至韦述时,国史已写成113卷。[1](卷63,《史馆上·修国史》)唐代官修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五代后晋时,在分裂、短暂的时期,史家们仍能写出《唐书》(即后人所称《旧唐书》),正是从这种积累中提炼出来的重要著作。
第三,唐代设馆修史,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从而展现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今存“二十四史”,构成了这个宏伟历史画卷的主体。其间,元代后期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史学活动,如同唐初撰修前朝史一样,也显示出最高统治集团的雅量和器识。
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这里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当然,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弊端,从刘知幾在唐中宗时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的上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写道:“知矮自策名士伍,侍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他说的“五不可”是:第一,群体修史,各人自我称许,意见难得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第二,资料不完备,具体表现是:“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第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撰史之人“能无畏乎”!第四,多人“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故修史者无所适从。第五,事关体裁、体例如史书断限、史事取舍、叙述丰约、如何分工等等,无人过问、“指授”,无所“遵奉”,以致“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卷63,《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刘知幾所反映的史馆修史的情况,主要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史馆修史状况并非如此,即使出现过某种弊端,也不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严重。
尽管如此,刘知幾所指出的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有的弊端是十分严重的,此其一。其二,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实际上刘知幾所言还不能完全概括,比如行状所记是否可以凭信?大臣密疏是否可以入史?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并不是刘知幾都可能涉及的。可见,史馆修史所存在的弊端是很突出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刘知幾采取了辞去史职,退而私作《史通》的做法。[7](《自叙》)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正直的史家都应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必须面对现实,提出适当的主张和建议,坚持撰写信史的原则。《唐会要》的《史馆·史馆杂录》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史家这种追求的足迹。
三、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唐代史家追求撰写信史的目标,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并不限于史馆修史,如杜佑撰写《通典》之严谨,韦述强调“大丈夫奋笔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不可也”,[8](卷10,《讨论》)李肇为补国史之不足而著《唐国史补》,[9](《序》)像这样的一些事例都与史馆修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唐会要》中的“史馆杂录”条所提供的史实,毕竟可以使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唐代史家坚持直笔、追求信史的精神。
唐代史家的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主张帝王不亲自观览国史
《唐会要·史馆上·史馆杂录上》起首记载了唐太宗和朱子奢、褚遂良、刘洎、房玄龄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已,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这里讨论的是帝王不览国史的传统及其原因。应当指出,朱子奢对唐太宗所问的回答是机智而得体的。所谓机智,是指他肯定唐太宗“举无过事”,相信“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所谓得体,是指他没有正面否定唐太宗亲览国史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唐太宗这样做或许会留下不好的历史影响,最后归结到帝王不亲览国史这一传统的合理性。唐太宗读到这通上表,暂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史载: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大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1](卷63,《史馆杂录上》)
在同朱子奢讨论数年之后,唐太宗又向褚遂良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褚遂良的回答比起朱子奢的回答更加明确:帝王不览国史,是含有希望“人主不为非法”的深意,即具有历史监督的作用。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表明他是很在意这个历史监督的作用的。褚遂良的回答很直率,即在守君臣之道和守史官之职二者之间,他只有放弃前者,坚持后者。在场的刘洎讲得更加直白,君主的“不善”,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之人”都会“记”得的。当然,“天下之人”所“记”,影响于当世;而史官所记,则影响于“悠悠千载”,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这一番问答,真切地表明了从朱子奢到褚遂良、刘洎等,是坚决恪守史官职责的。可惜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最终还是在房玄龄那里“退却”了。房玄龄作为监修国史,负责修史事宜,终于同意把国史送呈唐太宗观览。人们或许不必怀疑唐太宗亲览国史“以为鉴诫”的真诚,但他作为一代明君,改变了人君不亲览国史的传统,给后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终究是一个缺憾。房玄龄的“退却”,同样也应视为这位名相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过失。
(二)不取“人情”,坚持直笔
《史馆杂录下》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张易之、张昌宗密谋,“将图皇太子”,矛头首先对着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并试图利诱大臣张说作伪证,“证明”魏元忠支持皇太子早日即位。张说“被逼迫,乃伪许之”。后经大臣宋璟、张廷珪和史官刘知幾等鼓励、劝说张说,不要被张易之等所利用:“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于是张说面对武则天和朝臣说:“臣今日对百僚,请以实录”,并“厉声言魏元忠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这些话,使“百僚震惧”。武则天无法给魏元忠定“罪”,乃将魏元忠贬官、张说流放。《史馆杂录下》继续写道:
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张说身居相位,见史馆所修《则天实录》记载那段往事,总觉得不甚光彩,故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希望予以修改,并借口这是刘知幾所修。而正直的吴兢说明真相,绝不改写,屡屡抵制张说的“祈请”,被同事称为董狐式的良史。
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刘知幾对张说说的“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吴兢对张说说的“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充分显示出了史家的良知和信念。此事被后人写入《旧唐书·吴兢传》,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兢的《贞观政要》一书,始终受到后人的推崇,这同他坚守史家撰写信史的原则,自有密切关系。
(三)明确史书立传原则
《史馆杂录下》载路隋(亦作路随)论史书立传原则,写道: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史臣路隨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稺、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这一段议论,把史书中人物立传的基本原则讲得十分明确。其核心思想是:从历史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功名”,即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从道德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品德高下、善恶与否。这是一个大前提,但并不是最终的标准。最终的标准,还要看其“功名”是否“足以垂后”,“善恶”是否“足以为诫”?答案是肯定的,则可立传,反之则不可立传。这个史书中人物立传的标准,极其鲜明地排斥了以“富贵”与“贫贱”为立传的标准。同时,按照这个标准,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史书撰述中,对历史人物的处置,必然会使“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的变化。
路隋所提出的对史书中人物立传标准的见解,是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才可能提出来的,也确是史家们在史书编撰过程中经常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关于列传部分,他的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卷100,《太史公自序》)从字面上看,这里强调了“功名”,没有强调“善恶”。但是,在司马迁笔下,“扶义”之人,就是“善”的表现,当无疑义。唐代史家刘知幾论史书的人物立传,提出这样的见解:“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7](《人物》)从字面上看,刘知幾只是讲到了“善”与“恶”及其是否可以“示后”、“诫世”的原则,而没有提及“功名”。其实,他在作具体分析时,也讲到了历史人物的“功烈”。总之,司马迁说的“功名”,其中不乏道德的含义;刘知幾说的“善恶”,其中也包括了功名的因素。路隋所论,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功名”和“善恶”都明确地提出来了。
当然,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功名”和“善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不论在是否可以立传的问题上,还是在对历史人物作具体评价时,都要因人而异,不能作简单的处置。路隋议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要打破以“富贵”与“贫贱”为划线的标准。从路隋议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十分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人物立传原则。同时,从对于信史目标的追求来看,史书是不应当把那些“德不修而轻义重利”之人作为“垂于后者”而写入史书的。
(四)提出行状不足以取信
史书为人立传,不可轻信行状。对此,史官李翱提出深入的论证。《史馆杂录下》记:
[永贞]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制可。
李翱代表当时史官所上的这一长篇奏议,针砭了当时作史的一大弊病,即以个人行状为传记的依据。李翱认为,这种弊端一方面表现为对传主的“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造成传记“不实”;另一方面表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既有悖于古风,又不合于实录。为此,他提出改进行状的写法,即“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只有这样,行状才有其可信的价值。行状是个人历史的反映,个人历史又可能与国史相联系。因此,李翱的奏议,实为当时修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李翱所论,还涉及什么是“事实”这一命题,而他所说的“指事书实”、“指事说实”,都同“事实”相关联。他说的“史氏记录,须得本末”,既反映了史书记事的特点,也多少预示着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出现的必然性。
(五)修史不载“密疏”
“密疏”是指大臣给皇帝的秘密上疏,不为外人所知。《唐会要·史馆杂录下》记唐武宗时大臣们对实录载密疏一事,提出异议: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日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敕旨:“宜依奏。”
这里提到的几种情况,如“禁中之语”、“宰臣及公卿论事”、“藩镇献表”、“居要官启事者”等等,都与撰写实录、国史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提出对这些文献的可征信性提出适当的要求。这个适当的要求是:并非“得于传闻”,“须有明据”,“昭然在众人耳目”,否则不得记于史册。其中,特别提到“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而“密疏”得自私家,“实难取信”,建议“密疏并请不载”。从政治上看,关于“密疏”问题,不能完全排除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有关,反对以“密疏”入史自然事出有因,孰是孰非,另当别论。但是,从史学上看,反对以“密疏”入史,强调凡朝廷奏章“须朝廷共知者,方可记述”,旨在保证这种重要文献的可信性,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的信史目标,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总之,中书、门下的这一道奏章,集中反映了当时官修史书中对历史文献的公开性、可信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这同上文关于行状的议论,颇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信史观点的强化和提升。联想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以此说明对于历史文献的去取之由,与这一强化和提升,当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五个方面,表明唐代史家对于信史的追求,有一种始终不渝的执著精神。尽管信史的目标难以企及,尽管在追求信史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这种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既洋溢着那些正直史家的良知和操守,又总是在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信史。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尊敬。
收稿日期:2006-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