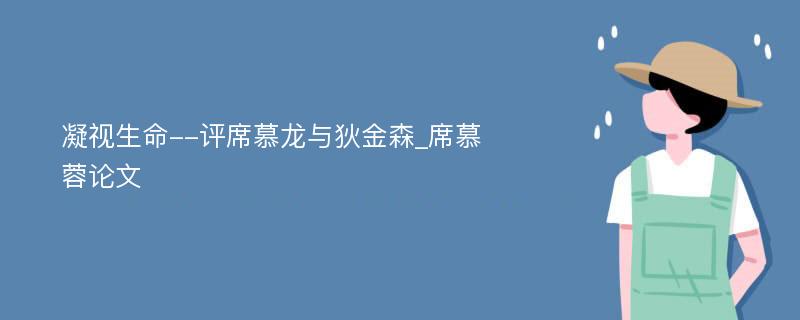
凝望人生——席慕蓉和迪金森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森论文,人生论文,席慕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悲剧的人生
使我们感到沉重
灵魂才会满足于
温和亲柔
——〔法〕莫莱亚《绝句》
惋如一位曾让我们心动的情人,许多读者在一刹那间以自己的方式阅读并理解了席慕蓉,为了惊异、为了叹息、为了感动,却少有人知道爱米丽·迪金森。这位被称作“艾默斯特修女”的美国女诗人,以其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惠特曼一起,创造了美国诗歌的新纪元。读她的诗会发现,她们对生活和爱情、悲剧与永恒的理解,竟如此相似。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东方和西方命运炯异的两位诗人,神关鬼照地达到了心灵的契合,写出许多美妙的诗篇。
一、心路历程
1830年,爱米丽·迪金森出生在美国的艾默斯特小镇,在受完中等教育后到一所女子学院就读。不足一年,即自行退学。初涉爱河的少女疯狂地爱上了一位远比她大、已有妻室的牧师。强烈的爱慕和严酷的现实使她深受折磨,她只能把爱深深埋在心底。天真活泼的爱米丽变得忧郁起来,她弃绝了社交,25岁开始足不逾户,除做家务外只用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她的诗写在信笺上、报纸边缘、信封的背面,随手涂抹,自然流露,不受约束。她一生大约创作了1775首诗,生前只发表了十首,有七八首还是友人从她的信中抄录下来隐名发表的。她不愿意让她的诗顺应流俗,“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她认为“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
迪金森的诗描写最多的是爱情和痛苦。她以一个少女无望的隐痛承受了生活和爱的不幸,对痛苦有一种极深的体验:“受伤的鹿,跳得最高/我听猎人说过/那不过是死的极乐/……欢乐是痛苦的铠甲/用它严密包裹好/免得有谁见到了血/惊叫:你受伤了!”(作品165号)。
盖林嘉在《勃拉姆兹的一生》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艺术家……要创作真正能表现出人生一切高度的作品,必须深深潜入充满悲欢的人生的漩涡中。”迪金森正是如此。蘸裹着回忆,她竭力在诗中理解着爱的含义和价值:“我一直在爱/我可以向你证明/直到我开始爱/我从未活得充分——我将永远去爱/也可以向你论证/爱就是生命/生命有不朽的纯真……”“爱,生命之先/并向死亡之后延展/是世界的原型/创造的起点”(作品549、917号)。同时,她对爱情产生了无比的热情和幻想:“他的声音又在门口响起/我觉得那音调依旧/我听见他向仆人打听/有没有我这样一个……我们交谈,随意而闪烁/有一种施放测锤的味道/一方,羞怯地/试探着另一方的深浅/我们散步,我把狗留在家里/月亮,温柔而体贴/只陪我们短短一程/然后,我们单独在一起……。”(作品663号)
她热爱生活和生命,一直在努力探索、解释和表达生的含义。她也明白生之无常,“我们输,因为我们赢过”(作品21号),但在爱情与现实、幻想与生活、精神与感觉的矛盾中,她的的确确是个爱的失败者。她只好运用美丽的谎言,对抗客观的失败和内心的渴望,由此进入形而上的永恒和悲剧的境界,弥补甚至取代有限的人生,直接面对悲剧、失败、绝望等哲学范畴的内涵。她的诗也因之超越世俗,显示出平静的精神追求。在与环境不协调的时候退回内心,存希望于绝望之中,存欢乐于痛苦之中,以主观想象对失败、自尊进行补偿。诗成为她生命的寄托。无限延伸的幻想和精心编织的梦,掩饰了生命的不足,使她的诗整个弥散着心灵柔曼的光环。“造一个草原只需要苜蓿和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上梦/如果没有蜂,有梦也足够”(作品1755号)。在她的诗里,除了用安详、麻木来描写内心的痛楚之外,更多的把绝望写成满足、恬淡、心安,运用了许多安抚和想象,平复心中的伤痕。“心啊,我们快把他忘记/当你忘毕,请给个信息/好让我立即开始/快,免得迂延/又把他想起!”(作品47号)。这种企图掩饰,却又无法遮掩的感觉,以及强差人意的苦涩,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
迪金森的诗中,爱情、自然、生死、永恒是揉合在一起的。在她一生的意识里,由失落的爱情引导出的基督思想和永恒观念其实没有区别,生即为死,死即为生,生为徭役死为乐土。她对死亡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崇拜和安详,与生的痛苦和有限相对照,死亡成了归宿,成了无限和永恒:
“因为我不能停车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车等我/车厢里只有我俩/还有永恒同座/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遐/以回报他的礼貌……那一天,我初次猜出/灵车朝向永恒”(作品712号)。
实际上,一个不能享受痛苦和绝望的人又如何能真正理解希望和幸福。中国人历来信奉“示知生,焉知死”,其实不然。理解了生死的关系,才能真正弄懂生的理由、存在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才会明白人生之味,在于生命的过程。理解生死,悟及人生,迪金森才会在诗中抒写出对世俗的轻视。在她著名的《我是无名小辈,你是谁》中,她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无名小辈,你是谁?/你也是无名小辈吗?/那太妙了,咱俩是一对/不要声张,他们会嫉妒我们/做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可真受罪/炫耀着自己,招摇过市/像只青蛙成天鼓噪着自己的名字/生活在人群羡慕的沼泽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渐渐与直觉、非理性言欢,这时出现的迪金森,以宗教似的沉迷、顿悟和直觉切入人生,转换、品尝悲剧和痛苦的滋味,无疑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新潮。她对内心痛苦、矛盾、怀疑的体验和对死亡、永恒的阐释与20世纪心理结构不谋而合,她简朴、直接的表现方式也启示了后人。因此,1916年前后,也就是休姆或庞德时代,她被意象主义者奉为先驱,并极深的影响了整个美国诗坛。她被认为是自萨福以来最优秀的女诗人。
一百年后,在东方,一位蒙古族血统的少女以另一种方式接受了谬斯的青睐。席慕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台湾女子,迅速蔓延到青年人的心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形成继大陆琼瑶热、三毛热之后的又一个热潮。作为纪弦、余光中、郑愁予之后第一个引起轰动的女诗人,她的诗同样也让许多中老年人入迷,为她诗中所流露出的少女的情怀、中年的怅惘、浓烈的感慨和淡泊的意趣。席慕蓉本不是诗人,是画家。写诗只是她业余的收获。与迪金森相比,她的生活是祥和美丽的,她更多地直接领受了成功与获得的喜悦。她写诗,为的是“要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怀念那一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她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写诗,“只是安静的等待,在灯下,在芳香的夜晚,等待它来到我心中”。与迪金森存希望于绝望不同,席慕蓉是为了追求完美。她把自己放置于现实和虚幻之中,度量无常,试探人生,体味生活和理想、命运与期望这样那样的分寸。“世间应该有这样一种爱情,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爱,那么,就让我的诗来作它的证明;假如在世间实在无法找到这样的爱,那么,就让它永远地存在我的诗里,我的心中”。她对生活认真而不拘泥,她的诗也同样灵秀而不古板。她向人们展示一幅幅色调和谐的生活图画,像一条河,带着爱情的追求、年华的惆 怅和沉重的乡愁等人生意趣自在地流淌。她以些许的忧愁为色彩,描抹人生的美丽和遗憾。在平静的生活中,“心是有一点悲伤和怅惘的,但是也同样含着感谢……藉着它曾经发过的光和热,让我写出了一些自己也很喜欢的诗句”;同样在平静的生活中,了悟绝对和无限本不可求,于是,“藉形象上的一点茫然,铸成境界上的千年好梦,而对此一点永恒,亦只是怀念,并无追想,”“对一切都不再强求”。(以上均出自席慕蓉诗集序跋《此刻的心情》和《一条河流的梦》)。
基于此,她的诗永远是怅惘的,也永远是美丽的。在这里,她已经无意识地走近了永恒和无限的精髓。凭着东方人的延展和直觉,她在诗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风姿绰约、清逸飘香柔美愁怨的意境,“总是,要在凋谢后的清晨/你才会走过/才会发现,昨夜/就在你的窗外/我曾经是/怎样美丽又怎样寂寞的一朵/我爱,也只有我/才知道你错过的昨夜/曾有过,怎样皎洁的月”(《昙花的秘密》)。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份幽怨,这份叹惋,这样美丽的意境,清醇的情调,微弱而与世无争的隐忍的心愿!在热烈痴迷的恋情之外,谁曾想到有一份不太经意的期望,等你分享?
席慕蓉的诗以古典的情怀、温柔的阐释和静默的感悟,触摸诗的灵魂,丰富和继承诗的审美价值:“若你忽然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我如金匠/日夜捶击敲打/只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饰/不知道这样努力地/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光泽细柔的词句/是不是也有一种/美丽的价值”(《诗的价值》)。这叫我们想起迪金森的诗——“诗人,就是从/平凡的词意中/提炼神奇的思想/从门边寻常落英/提炼精纯的/玫瑰花露……他自己,是他的财富/超越时间”(作品448号)。
席慕蓉以纤细的格调品尝生之欢乐和痛苦,以顿悟的形式检索时光、缘份、青春、克制、爱和美的东方含义,清雅精纯,女性之柔婉无处不在、心灵之净洁无所不存,隐忍其表,执著其中。在她整个诗的构建中,为我们酝酿了一个可感可知的纯粹东方女子形象,沉静,文雅,美丽,贞洁,娴淑,执著:“在陌生的城市里醒来,唇间仍留着你的名字/爱人我已离你千万里,我也知道,16岁的花季只开一次/但我仍在意裙裾的洁白,在意那一切被赞美的被宠爱与抚慰的情怀……”(《16岁的花季》)。又如《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的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席慕蓉,为爱而生,也因为爱而获得自身的价值。在她的诗里凝聚着一个理想,充满了奉献的渴望:“如果你喜欢/请饮我,一如月色吮饮着潮汐/我原是为你而准备的佳酿/请把我饮尽吧/我是那一杯/波涛微微起伏的海洋/紧密的封闭里才能满贮芳香/琥珀的光泽起因于一种极深极久的埋藏……”在这首《佳酿》里,作者奉献出一个诗人全部的感情和浓烈的爱意。在这种奉献中,诗人也最真实、最完整的拥有了自己,寻到了自身的价值。
这和迪金森在生活中的隐忍和奉献,何其相似!“我缀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多少,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称我的份量/锱铢必较,毫厘不爽/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价值/一滴,幸福的琼浆!”诗人的满足和欣喜洋溢于表。一滴幸福,奉献一生,有多少人能理解这种价值,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种追求本身,才是唯一无可比拟的价值。圣哲彼德拉克说:谁要是走了一天,傍晚走到了,他就该满足了。
在迪金森的诗中,多是痛苦的满足、苦难的超越、怀疑的欣喜和矛盾的自慰,而席慕蓉的诗在对忧愁进行美妙描述的同时,体现出悟极人生的平静、执著和融释。让我们来读读她的《盼望》:“其实,我盼望的/也不过就是那一瞬/我从没要求过你给我/你的一生……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诗人把对生活的感受,对时光、对永恒的感受,倾注在幻想的一瞬间,一生的期盼,一生的感叹,一生的遗憾,在回首的刹那便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消融。
席慕蓉描述最多、感受最深的是时光。作为生命、爱情、希望和忍耐的条件,时光记录着命运的全过程。在她看来,时光造就了这一切同时又对这一切进行否定,时光在这里成了沧海桑田的主宰和见证。在时光的左右下她获得回忆的权利和对未来的梦想。她在《时光九篇》的扉页上这样写着:“献给时光,那永远建立在不败之地的君王。”
随着时光的流转,她深深体会到了强烈的愿望与具体现实的冲突。“我深深地觉得,世间有些事物是不会再回来的了……而我站在黑暗的夜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怨的青春》序)。理想的尽善尽美,人生终极追求以及具体时空的合理性障碍,形成无可回避的矛盾。在这种冲突中,作者尽显其悲。欲望不能满足,追求不能达到,欲望和追求本身却表达了生活的缺陷。一种抽象模糊的愿望和现实的距离,形成作者极深沉的大彻大悲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诗人凭借其敏感、爱恋和痴迷的观注,超越现实,超越狭隘的悲剧观,探索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并以此跨过世俗的功利得失,把思考的意向延伸到现象界的边缘,触及到爱和时间、死亡、存在的哲学意义。当她睥睨了生命之极本无所成,亦无所虑,更无所求,故无所忧,便在《见证》中写道:“……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换作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今天的我,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要知道关于今夜,到底是有雨,还是有雾。”一沙一界,一尘一劫,诗人的豁然,使狭义的悲剧转换成泛意的悲剧,升华成对时空、命运、永恒的深层揭示。生的随意死的绝对,时间的有无空间的虚实,人生的偶然命运的必然,使诗人顿悟。“我爱,何者是实,何者是空,何去何从”(《艺术家》)。诗人永远在解不解之结,爱得出神入化,如醉、如狂,却静默如初,不再计较取舍、成败。不求、不贪、不怨、不欲、不纵、不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虽然过程极其美丽,极其壮观,或者极其悲切,极其执著,结果却都无所谓了。这正是理想的东方女性精神境界,也是与人生中永恒因素相徘徊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但她的诗并未就此停住,也没有沿着空灵、虚妄继续走下去,而是像禅所说的那样,永无止境的感受和理解生命的含义。她常常把失望看作希望,把痛苦升华为永恒的欢乐,在她的诗中,照常无数次咏吟着那些“常常被人在太迟了的时候,才记起来的那一种爱情”(《短歌》),在悟与不悟之间,用这种矛盾,体现一个平凡女子的情怀。也正是这样,才“独怜幽草涧边生”,寻到了这样一种《美丽的心情》:“假如生命是一列/奔驰而过的火车/快乐与伤悲,就是/那两条铁轨/在我身后,紧紧相随……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清明的/酸辛,所以,也只有/在太迟了的时候/才能细细揣摩出,一种/无悔的,美丽的,心情”。
迪金森,一个信徒痛苦的怀疑和义无反顾的奉献;
席慕蓉,一个普通女子平静、矛盾而又隐忍的追求。
二、悲剧的含义
能看透命运并触及灵魂的人,一定对生活拥有强烈的渴望和敏感的知觉。这两种机制,又正是诱发悲剧的契机。两位诗人如此,读懂她们的人亦如此。
有人曾说,席慕蓉的诗所传达的信息,无非是无怨的青春与无瑕的美丽。青春无怨否?其实有怨。但在席慕蓉的诗中,此怨并非怨尤,而是一种婉约美丽的伤感。《无悔的人》也并非无悔,如果你在一生中真挚的爱过,悔与无悔便没有区别。如果你拥有信念、拥有美好的一瞬,就真的无悔于一生,也真的可以无怨于青春。“情到深处人孤独”,“爱到深处无怨尤”,这里有一个价值转换的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迪金森的这首诗:“如果记住就是忘却/我将不再回忆/如果忘却就是记住/我多么接近于忘却/如果相思,是娱乐/而哀悼,是喜悦……”(作品第33号),这种矛盾的感觉其实人人都有过,很容易引起共鸣。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她们的悲剧观,理出悲剧的本质涵义。
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仅指出了悲剧的一种表现和一种价值。我们所理解的悲剧,应该是现状与企图超越现状的欲望之间的冲突,这是它的起因。通过冲突双方的对抗、覆盖甚至毁灭,实现或揭示一方永恒、真实的价值,才是它最忠实的涵义。所以悲剧不仅是事物发展必不可少的趋势、起因、过程,也是主体价值体现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是一种心态、色彩、情绪,在哲学上是一种状态、矛盾、过程,在艺术上是实现美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幻想超越了现实,悲剧就会产生。一切与命运和不可逆转的现状发生冲突的行为都构成悲剧。没有超越的欲望就没有悲剧;同时,没有悲剧也就不可能实现超越。归根结底,它构成悲剧现实的和形而上的两种价值。通过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悲剧比其它艺术形式都更加突出地提出有关人与人格处境的种种问题。一旦人们意识到悲剧,就会带着新的焦虑来面对他所有终极的限制,以有限和短暂为坐标,理解无限和永恒,实现对这些限制的超越。
悲剧的价值是在失败与毁灭中,是在暂时不可转的劣势下,在隐忍、退让、保全、牺牲等状况下实现的,悲剧美也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价值转换,实现悲剧的快感、对悲剧体味静观欣赏的愉悦陶醉、自信和崇高感、光荣感、美感。生命在悲剧的矛盾对立中呈现出迷人的牺牲的光彩。这一瞬间,使我们清醒的看到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无论矛盾的对立面如何变化,作为矛盾即悲剧状态中的生命的活力以及对欢乐的希望总是存在的,不管它隐隐约约,或是显而易见。这是悲剧快感的基础、本源。而悲剧效果,恰恰是人生一大营养。个体的痛苦和暂时的毁灭,在这里不是惊惧和忧虑,而是激奋、欢乐和期待,唤起被肯定的快感。在尼采看来,这就是酒神精神,即站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上看待生命个体的痛苦,对于生命个体来说,一切创造和毁灭都是积极的、欢乐的,作为生命个体,我们应体会到这种欢乐,从而使生命本体和个体同一,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肯定。在悲剧的过程中,我们因为体味到终极存在的价值而脱离现象界,变成真正的快乐者。
席慕蓉和迪金森深深明白并寻找到了这种价值。
席慕蓉的悲剧因素大多是融解在诗意之中,作为美的情绪的真实而又直接的体现。她在《馈赠》中这样写道:“……就让火熄灭了吧/我会清楚地记得你的泪水像星光一样/而我的痛苦一经开采/将是你由此行去那跟随在诗页间的/永不匮乏的矿脉”。又如《悲歌》:“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可是,我一直都在这样做/错过那花满枝头的昨日,又要/错过今朝。”她最出色的一首诗《在黑暗的河流上》站在悲剧的立场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她的审美意趣。在这首诗中,用作者所理解的《越人歌》和作者所领悟到的越女的结局,极抒生命之悲。在她看来,越女的悲剧其实不是单恋的悲剧,而是现实的必然。有许多的心愿我们无法实现,有许多的梦想无法企及,过多的困扰和阻碍限制了我们,强烈的渴望和极微弱的满足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些美好的心愿因之而更加纯净美丽,洋溢着情感的魅力。
和席慕蓉有所不同,迪金森诗中的悲剧因素明显是对自己悲剧人生的关注和表现。迪金森的诗,整个充满了达观的、听天由命的思想,她自己也就在这种隐居生活中寻找一丝一点的快乐。如《今天,我是来买笑的》、《救世主,我无处可以诉说》、《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在品味悲剧情绪的时候,用悲剧的价值弥合人生。这种达观与宗教有相似之处。宗教的精神是超理性的,它把感觉、概念、象征看作是人上升到静观的基本准备,而静观,又达到对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的超越。迪金森虽然不是教徒,但她的精神是属于“上帝”的,她的虔诚和宗教情绪构成她内心深处真正的宗教精神。她的隐居也逐渐发展成为宗教性的自我克制,在这种状态下寻找悲剧的价值,其实已直接从悲剧中提取了美的因素和永恒的意义。
用女性特有的执著和专注,席慕蓉和迪金森在克制、隐忍、等待中透析着悲剧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固有的含义。她们不断用信念、爱心、宽容和真诚,化解得与失、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绝望同期待的界线,无分彼此,不论成败。在她们的诗里,这一系列矛盾奇迹般的协调成同一种价值,难道死不是生,痛苦就不能是欢乐吗?她们凭直觉跨越了这些哲学范畴,实现美的感知。“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一切我们爱过与恨过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残缺的部分》)。“幸福和遗憾原是一体的两面”(《雨季》)。
悲剧是诗的最高形式,它暗含了许多精辟的辩证思想。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悲剧是人类向自我实现运动的经验之一,在人穿越煎熬、痛苦、死亡等有限情景时,由于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事实的坦然接受,得以超越这些情景,体认到自己真实的存在,从而接近无限而永恒的隐秘“上帝”。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绝对意志里。“我们的生命意志是用象征性的、梦幻般的表现形式来表达那些达不到的欲望”(《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
悲剧的价值转换完整地解释了悲剧的本质涵义,“生命,其实到最后总能成诗,在滂沱的雨后,我的心灵将更为洁净”(席慕蓉《雨后》)。
人们在悲剧中看到痛苦、毁灭和死亡,亦在悲剧中看到欢乐、希望和生命在承受痛苦,经历毁灭、面对死亡中所展示的辉煌。
三、诗美艺术
席慕蓉和迪金森的诗作,都是两位作者内心情感、审美意识、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等与外在现实相区别、相矛盾、相交融的主体表现。在哲学地分析了悲剧对于主体价值转换的功能之后,我们进一步从诗美艺术的角度,具体谈谈席慕蓉和迪金森诗中悲剧主体的感知和表现过程。
对现状的不满足、对美和完善的渴求和对悲剧的超越心理,构成强大的情绪机制,影响了诗人的感知。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去看取的世界,必然是经过心灵转化的形象,因此,外在与内在的界线也就混淆而模糊。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伯格森《形而上学导言》)。通过直觉、观照得来的感受,就很直观形象,甚至一些带有抽象性质的心理和时空概念,也变得有声有色,形象分明,栩栩如生。迪金森《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就这样写着:“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如果一年后能够见你/我将把月份缠绕成团/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免得,混淆了日期……如果确知,聚会在你我的生命结束时/我愿意把生命抛弃/如同抛弃一片果皮……”,又如她的《冬日的下午》:“冬日的下午,有一种斜射的光/令人压抑,象有/教堂乐声的重量……”,再看看《预感》:“预感,是伸长的阴影,落在草地/表明一个个太阳在落下去——通知吃惊的小草/黑暗,就要来临”,这些,都是在感情的影响和直觉的参与下获得的特殊的心灵瞬间感受。
受限制和对完美的渴求,所积累的强大的“感性动力”(该词源于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感性动力,是一种创造动因,也是人的自然生命力。高尔泰先生认为现有的状态是受限制的状态,有生命就有需要。有了限制,有了需要,有了痛苦,才有生命、力量和热情。这些,都是感性动力的体现。)直接冲涌着生命去参与感知,去热情的拥抱生活,使一切都染上感性色彩。这在席幕蓉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两本诗集里,俯拾皆是。迪金森的《亲爱的三月,请进》就更为直接。所以当代文学家唐努埃尔·德孟多利奥在评价女诗人时这样说:“在她们身上,一种动人的、生活在难以名状的神秘中的永恒激情把幻想、思想及精神和肉体的感受都融为一体。不言而喻,她们具有强大的抒情力量。”
在艺术表现上,两位诗人的技艺也很独到精纯。她们善于从矛盾中发现落差,从对比反衬中展示美。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之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美学》第一卷第124页)。在痛苦中揭示欢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死亡中验证生存,是她们惯用的手法。席慕蓉《子夜变歌》的绝望,正补托出盼望与希冀,以及拥有盼望与希冀的主体之可贵,突出被损害的生命之美——“终于明白所有的盼望和希冀/不过是一场寂寂散去的夜戏/此刻再来向你描述/我如何自疼痛的苏醒里成长/想必也是多余……”平静的体味痛苦、绝望和死亡,其实是体味永恒、欢乐、生命和希望之极致。又如席慕蓉的《诀别》,明知可即却偏要逃避的爱,情义更深更浓:“请原谅我不说一声再会/而在最深最深的角落里/试着将你藏起/藏到任何人,任何岁月/也无法触及的距离”。
比喻、通感和想象,也是两位诗人惯用的手法。“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席慕蓉《乡愁》),“名声是一只蜜蜂,它有一首歌,它有一根刺,啊,它也有翅膀”(迪金森作品第1763号),“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它栖息在灵魂里”(迪金森作品第254号)。迪金森还善于用递进和关联的手法,层层相剥,步步推进,在她的《头脑比天空辽阔》一诗中,就分别用了“比天空辽阔”、“比海洋更深”、“和上帝相等”几个比喻,依次递进。她那著名的《我为美而死》是这样写的:
“我为美而死/刚躺进坟墓/一个为真理捐躯的人/也抬进了房间/他悄悄问我为什么而毁灭/我回答“为了美”/他说“我是为真理——/一回事,咱俩是兄弟……”。
当以上感觉和手法在内心得到统一,产生通感,在她们独立的个性中还原到最直接的人生体验,诗便自然的流露出来,达到浅显的效果。“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向远方/这渠道最穷的人也能走/不必为通行税劳伤/这是何等节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迪金森作品第1263号),“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席慕蓉《渡口》)。所不同的是迪金森更多的用比喻、描述的手段,对人生作形象、现状的展示,而席慕蓉则多以象征和叙述,体现命运过程本身。
四、凝望人生
诗是进入一种态,一种适合自身生命发展的精神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去感受、体验或者消享人生。大度的人生,泰然自若;敏感的人生,细腻温柔;热忱的人生,如痴如醉;执著的人生,心无旁鹜,坚韧而且承受——“我相信,爱的本质-如生命的单纯与温柔”(席慕蓉《我的信仰》)。
诗是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情感、希望,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必要延伸、肯定和外化的形式。它不存在什么理论,只有经验、迷狂与智慧。艺术必要与不必要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故艺术家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靠近高级的生存方式。艺术不必告诉人们什么,只让人感受生命这种或那种状态。现实主义艺术揭示生命在现实中受主宰的被动形态,浪漫主义展现超然的内心,现代主义则提供荒诞的现象,追索变幻中的价值尺度。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依附什么样的主义,堆砌什么样的内容,那些把艺术看作是生活附庸的人,永远都只能与伪艺术同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善于享受人生中的赏心乐事,而且还能达到享受痛苦的境界,痛苦越甚,从中获得的享受越多,越强烈。他能从痛苦中获得平静生活中无法摄取的心灵的财富。
迪金森留下的近两千首诗,以及席慕蓉写下的那几本诗集告诉我们,生活意味着感觉和思索。席慕蓉在《七里香》后记中写道:“所有繁复的花瓣正一层层地舒开,所有生命中甘如醇蜜、涩如黄连的感觉与经验正交织地在我心中存在”,“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成熟的果园”(《禅意》)。这些人生体验,汇成创作的源泉和产生灵感的契机。她们的诗之所以有魅力,正因为她们像萤火虫一样用细腻的生命在痛苦中聚光。简单的表现、暴露和宣泄苦难很难成为真正的艺术,包容并超越苦难,享受超越的痛苦和痛苦的超越,才能步入艺术的殿堂。
克尔凯郭尔认为孤独的个体的存在是根本的。忧郁、恐惧、战栗、痛苦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或基本经验。当然,他忽略了超越这种基本状态的快乐与希望。所以,无论席慕蓉和迪金森怎样夸张失败和痛苦、隐忍和退让,无论怎样去吹胀幻想和期待,自慰和纯美,都不为过。她们不是过客,是生活的赏识者。对爱的渴求、对生命的珍惜、对欢乐的向往,促使她们凭女性最敏感的直觉进入诗的境界,不断品味死亡,展示绝望、转化痛苦和描抹忧伤。“当我猜到谜底,才发现,一切都已过去,岁月早已换了谜题”(《谜题》)。尽管她们吟咏的多是“人生无奈”,但她们毕竟从自己的角度真实的面对并拥有了这些无奈。
“整个上午,我都用在/努力调整步伐好进入行列/整个下午,我又要为/寻找原来的自己而走出人群/为了争得那些终必要丢弃的/我付出了/整整一日啊,整整的一生!”(席慕蓉《诗的成因》)。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痴者自痴,迷者自迷,读她们的人是否也从这份痴迷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意趣?
标签:席慕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