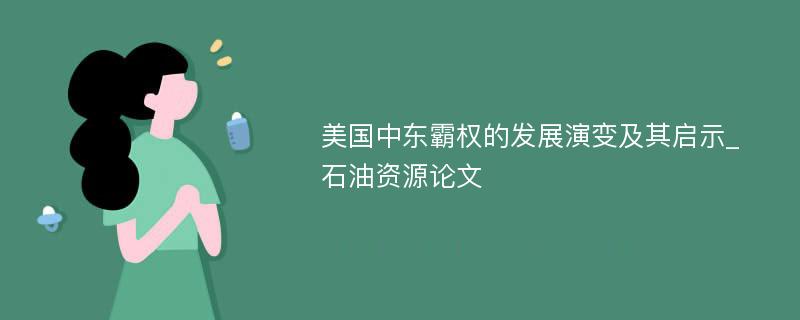
美国中东霸权的发展演变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发展历程基本同步。美国的中东政策服从于其整体对外战略,其在中东的境遇演变实际上是美国霸权在全球嬗变的缩影,具体发展轨迹也和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一样,经历了兴起、鼎盛和(相对)衰落的过程。 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轨迹 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阶段划分,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北层国家(指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国)、新月地带、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时间节点。如果以中东国家对待美国的基本态度倾向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期盼与亲近、欢迎与接纳、失望与批评等3个阶段,总体上反映了美国中东战略在不同阶段的进展和限度。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时间节点,在北层三国和新月带是二战结束,在马格里布地带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在海湾国家是1971年的英国势力撤出。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比较一致,多数国家都是2011年的“九·一一”事件,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三国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69年的“九一革命”、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卡塔尔、巴林和吉布提3个小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另当别论甚或忽略不计。 (一)美国与中东关系的被期盼和亲近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意、西、俄等欧洲列强是在中东影响较大的外国因素。19世纪的近东问题,1878年列强争夺近东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英、俄对波斯和阿富汗的争夺,19世纪末德、英、法、俄围绕巴格达铁路问题的博弈,20世纪初法、德、英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等国对中东的势力范围瓜分等,构成了列强侵略和掠夺中东国家的基本历史轨迹。殖民化、半殖民化与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贯穿着欧洲列强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始终。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美国不仅没有卷入与中东国家任何长期的、血腥的冲突,没有直接统治过中东国家或者发展肮脏的帝国主义制度,反而因为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等激动人心的立场而被中东国家普遍看作是与英法殖民行为截然不同的充满善意的国家,是进步的代表和象征。① 经济上,由于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的揭黑努力和反托拉斯运动的洗礼,洛克菲勒创立的美孚被迫一分为七,分家后的新泽西美孚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寻求新的机会,成为推动海湾地区从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晋身为战略资源富集地的探索者典型。②根据1928年签署的《红线协定》,美国获得了自由分享海湾石油资源的机会,加州美孚、德士古、新泽西美孚和纽约美孚合组的阿美石油公司在拥有海量石油蕴藏的沙特大获成功,不仅与沙特结成了安全换石油的稳固盟友关系从而确立了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支配地位,而且标志着美国取代英国中东霸权地位的开始。 文化上,美国在中东地区建立的文化机构曾备受尊敬,如开罗美国大学、波斯美国学院、伊斯坦布尔罗伯特学院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等。这种优越的地缘政治状况以及与中东国家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是美国对中东事务“整体超脱”战略的必然结果。和所有的旁观者和批评者一样,尚未深度参与中东事务的美国对当事者英国的很多批评总是很正确,总能够很容易地占据道义制高点,自然而然地迎合了中东国家和民众反对欧洲列强,尤其是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期望,被超越现实地视为他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当然的同盟。客观地看,中东国家和民众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愿望在一些议题上可以实现,也确曾不同程度地实现过,但期望它能够永远实现或者在所有议题上都能实现却注定会失望。 (二)美国与中东关系的受欢迎和被接纳阶段 得益于国民经济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扎实崛起,国内政治的持续深度变革,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财政成本为美国确立其工业和财政力量提供历史机遇,长期血腥战争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美国树立全球领导地位敞开了大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间20多年的艰难博弈和权力扩张,美国最终跃上了世界诸强之巅的全新地位。 在冷战期间,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中东乃至世界的当然霸主,其在中东的国家利益通常被认定为3个有关联的领域,即确保石油供给、支持以色列和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些利益,美国与不少中东国家建立了密切而稳固的长期同盟,例如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列维时期的伊朗、萨达特时期的埃及等国。1953年,美国与英国联手颠覆了伊朗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府,并恢复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1955年,美国积极推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集体对抗苏联以及埃及、叙利亚、阿富汗等亲苏国家。在1968年英国势力开始退出海湾后,美国积极帮助稳定地区形势,发展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良好关系,多渠道抑制苏联的影响,保障石油供应。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遏制苏联势力,支持“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即“七党联盟”)在阿富汗的抗苏战争。在阿以问题上,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干预来恢复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平衡”。 在冷战体系坍塌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为了确保在全球的霸权,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首先,美国迅速填补苏联和俄罗斯战略收缩后在中东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沙特、土耳其、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家派驻军队,常年在海湾附近维持一个航母战斗群,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保持友好政策,尤其注重发展与海合会六国、土耳其、埃及等温和派国家的关系,支持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主要派别以保持对阿富汗的影响力。其次,美国以维护现状和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扶持温和派,打压激进派,不容许任何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努力保证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既在1991年通过联合国框架率领多国部队恢复科威特主权,对伊拉克实行十余年的封锁遏制;又主动打击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和激进势力,防范逐渐控制阿富汗大部分领土的塔利班政权,动用武装力量的目的在于威慑遏制而非强行颠覆政权,中东基本实现了美国治下的大体稳定。 与此同时,因为具体政策中对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美国中东政策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导致阿富汗这个“恐怖主义熔炉”出现了后冷战时期特有的冲突,反人类的恐怖行为被作为依靠种族和宗教力量驱动的、反对现政府的政治武器。③从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1993年)、利雅得美军军营爆炸案(1995年)、宰赫兰美空军住所爆炸案(1996年)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美国使馆爆炸案(1998年)、也门美国“科尔”号军舰爆炸案(2000年)和“九·一一”事件(2001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九·一一”事件既是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在这一阶段互动发展的结果,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推动双边关系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美国与中东关系的被批评和被憎恨阶段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遇到了严重挑战。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小布什政府随即把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强调到了极致,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化世界观看待国际问题,把恐怖袭击明确定义为是对美国式民主和自由制度的攻击,希望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来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专制和暴政土壤,一度把武力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主要手段,把拓展民主看作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责任的一部分,“寻求和支持每一种民族和文化中的民主运动和机制,达到在世界上结束专制的终极目的”。④在2001年、2005年两次就职演说和2002、2006年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指引下,以“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军事力量推广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布什主义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中东处在布什主义的心脏”,推行全面变革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涵盖了除以色列外的所有中东国家,这一时期的中东政策因之是布什主义的最集中表现。⑤事实上,小布什政府以“十字军东征”式的激情和使命感介入中东事务,对外战略主要服务于反恐与民主改造中东这两大互相联系的目标,政策指向由此前的维护稳定和渐进式发展转向了全面的社会改造和秩序重塑,武力改造伊拉克,民主改造整个中东。⑥具体而言,美国以强大的军事行动在阿富汗展开反恐战争,把伊拉克当作践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试验场,推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缓和、国内和平与南北分立,将巴以和平进程置于反恐与民主改造两个范畴之中,重组温和伊斯兰国家阵线,孤立和遏制中东地区力量失衡的受益者和“被崛起者”伊朗。⑦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打击、单边主义举动、武力推广民主等做法,确实在具体实施中多处碰壁。“大中东民主计划”也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布什总统的任期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其留下的政治改革积淀,包括对民主政治必要性的基本共识,对家族统治合法性、选举公正性、领导人任期和权力世袭等问题的公开讨论,却使得中东国家民主化的内部环境有所改善,并成为引发2011年后中东剧变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既然国情复杂的中东国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都未能探索到适合的发展道路,甚至在伊斯兰勃兴以来的近1500年间始终是分裂多于统一,有着弱者反抗强者特征的恐怖袭击并不必然地代表着正义对非正义的反抗,数次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都没有太深触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也是事实,布什政府反击恐怖主义威胁的诸多举措也就应该看作是一种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实践,是对此前被忽略或者未尝试的社会治理选项的尝试性运用。事实上,所有重大的中东事务在布什政府时期都基本延续着原有的发展轨迹。一直被夸大地视作中东问题核心的巴以问题并没有恶化多少,以色列正在融入包含所有中东国家的地区安全体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的扩散确实是国际社会必须关注和认真应对的严重问题。伊朗一直就有着充当地区领袖乃至世界大国的强烈梦想。 悲观地讲,既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难解的中东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彻底根除新近出现、却已成为全球政治公害的恐怖主义,作为旁观者提出的合理建议与参与者能够具体实施的策略建议之间往往有很大距离,作为旁观者间接感知与当事者的切身感受在很多时候并不一致,因此,对反恐的阿富汗战争和武力移植西方民主的伊拉克战争的评价就最好交由阿富汗和伊拉克人,对二者最终效果的评价甚至只能交付历史去检验。 总体上看,随着二战后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日益广泛,不同的利益目标导致了具体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矛盾,其中东政策在巴以冲突的刺激与催化下慢慢引起了中东国家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从20世纪前期的被羡慕、被欢迎到20世纪后期的被批评被憎恨,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形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反差,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美国从中东事务可有可无的旁观者变成了无法回避的深度参与者,就在于全球化时代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作为旧体系的霸权国,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已经不可能得到所有相关方的满意,有时甚至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袖手旁观被骂,参与不当挨批,在相关事务上嘲笑和埋怨美国“是唯一比足球更流行的全球性运动”,⑧夸大来自美国的威胁和持久地唱衰美国在一些国家几乎是肯定不会犯错的政治正确。宏观地看,这种转变蕴含的时代必然性,就是“美国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代表,在承接了欧洲强势地位的同时,也成了伊斯兰世界表达仇恨和愤怒的焦点”;“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具有内在的历史关联,经历了从反西方到反美国的历史性演变”。⑨ 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和现实 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美国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4个层面,各个层面的所占比重和优先次序在不同地区表现也不同,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对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评价因子必须结合各项具体的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总的来看,在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中,美国四项国家利益目标的实现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经济外交最成功,价值观外交最矛盾,安全政策最失败,领导地位滑落最无奈。⑩ (一)成功的经济外交 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全面垄断着国际石油市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供应了盟国90%的石油需求,在1940年生产了全球63%的原油,而中东只生产了全球5%的原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30年间,西方资本继续维持着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地位,国际油价走势基本平稳,原油标价长期维持在1~3美元之间且与实际售价脱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英美石油公司的价格战期间甚至更低;变化之处仅在于开采地从美国本土扩大到世界各地,美国滑落为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自1971年起真正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沙特、伊朗、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供应了全世界1/3的石油需求。廉价充足的石油供应是西方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从石油美元、油气定价权和资源控制权三方面重新确立了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首先,美国与欧佩克在1975年达成协议,将美元与石油绑定,规定世界石油交易大多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确定了石油美元持续至今的影响。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牢固掌控着石油定价权,垄断了全球范围的主要石油期货交易。第三,作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资本几乎涉足全世界所有产油国,通过军事打击、经济合作、投资、协商对话等手段实际控制了全球近70%的石油资源,与中东产油国构建了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机制化经济制度,扩大产油国对美国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最后,美国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74个军事基地,驻军30万人,运用强大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掌控大量境外能源资源,并在世界所有产油区及重要运输通道充当着“国际警察”的角色。(11) 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70年代供应不足的石油危机一度重创了美国和西方经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此后的历届政府都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持续累进地促进美国能源独立。到2011年,作为世界第三大产油国的美国不仅能源自给率已经达到了接近完全自给的80%左右,只有17%的进口石油和0.5%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中东,在中东的直接投资仅占美国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的2%。(12)不仅如此,新能源技术的突破还使得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在2000~2010年间增长了11.3倍,在2009年成为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并有望带动北美地区在2020年左右成为能源领域的“新中东”。(13)换言之,由于摆脱了对中东能源的绝对性依赖,中东乱局已经不太可能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产生太大影响。美国对中东地区秩序稳定的关注,就是确保石油以可接受的价格稳定地供应市场,从而确保霸权意义上的石油安全利益,即确保盟友的能源安全以维持美国的战略信誉,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独自控制中东地区的能源供给。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实质上就是对觊觎中东地区霸权、挑战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地区性大国的惩罚。 对盟国的援助是美国中东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必需,“中东稳定”(Middle East Stability)的外援预算项目长期是国会两党的稳定共识。(14)受援国很多时候也将美国的支持看作实力的象征,而不仅仅是购买先进的军事武器。以色列是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受援国,每年接受的援助额在30亿美元左右。埃及是美国在全球的第二大援助国,在1948~2011年间共接受了美国716.24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之前的年均援助额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其中13亿美元是军援),之后由于非军事援助资金从8.15亿美元削减到了2.5亿美元,年均援助额降至15亿美元左右。(15)在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国计划在2014年撤军完成后每年提供41亿美元援助,美国2013年的援助阿富汗资金是25亿美元。就是对约旦这样的中东小国,美国在1952到2012年间也援助了79亿美元,2014年的援助金额因为叙利亚难民问题而从6.6亿增加至10亿美元。 (二)矛盾的价值观外交 在对外政策与国际交往实践中,一国政府总是尽可能以本国民众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诉求参与世界事务,依此展开的对外交往活动称之为价值观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16)对美国而言,因为深厚的宗教传统和独特的意识形态,“天赋使命”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着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承命意识和理想情怀,渴望把美国的自由信仰和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从卡特的“为人权仗义执言”到克林顿、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支柱,以“人权、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就是美国价值观外交最突出、最长久、最常用的表现形式。 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在相当程度上不啻保障并拓展国家利益的工具,甚或与利益结合达到外交政策的“名利双收”。在最近数十年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中,美国支持民主,反对独裁,经常将道德支持和国家利益合并。在这种外交方针指引下,美国把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的以色列视为特殊盟友,把高度西方式世俗化的土耳其视为传统的战略伙伴和北约盟国,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两国发展经济,坚定地履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竭力推动美—土—以军事同盟。1991年,老布什总统出兵海湾保护科威特国家主权,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秩序。2001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兵阿富汗重创“基地”组织的同时,高调宣布解放了一个“独裁国家”。2003年,美军再次出兵伊拉克,主要目标就是希望树立中东民主样板,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免类似武器未来被恐怖分子用于袭击美国。对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立场,兼有避免中东进入核装备竞赛和保护以色列的双重考量。(17) 虽然外交行为的价值负载在国际政治日益“后现代”与价值化的当代已经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国等有着深厚宗教情结与价值情感倾向的西方国家更拥有强大的民意根基,然而由于价值观外交的价值负载和利益负载并不总处于一致状态,尤其当国际政治行为中预期道德成本和预期道德收益的“相称性原则”得不到保证时,相关行为导致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就得不到有效化解。为了避免和摆脱价值观外交的这种困境,历届美国政府在稳定与民主、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总是首先站在代表稳定和利益的现政府一边,而当形势不可为时则凭借深厚的非政府组织外交顺势站到了取而代之的民众一端。这种思路指导下的具体中东政策也导致了美国与中东国家复杂的双边关系以及参与中东事务时的双重标准。 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美国选择性地对待中东国家的现政权和民众的民主诉求,庇护温和派国家的“独裁总统”和“专制君主”,漠视中间派国家的民众变革诉求,指责“激进派”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并支持其内部的民众运动。这种选择性介入中东事务的政策在表面上有自相矛盾之处,被言之有据地批评为自私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是一种有口头高调但缺乏实质性行动的伪善的价值观外交,(18)客观上也确实激化甚至直接产生了很多地区矛盾。但事实上,面对错综复杂且高度碎裂化的中东国家,任何国家恐怕都很难制定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对象国的参与策略,只能在具体议题上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制订具体的参与策略。美国价值观外交在中东地区的差异性实施,本质上也是深度参与中东事务后结合内外各方面因素所进行的全面考量,也是出于最大化维护美国在中东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实践中也确实在价值观外交的价值负载和利益负载之间演绎出了多种组合。与沙特长达70多年的能源换安全合作关系是美国漠视价值观外交价值负载的最典型成功个案,与伊朗关系在1979年前后的逆转则是美国强化价值观外交价值负载的最典型失败个案。 (三)失败的安全政策目标 在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安全利益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短期内也确曾实现了这两个安全目标。而借助沙特、以色列、土耳其、埃及等多个中东盟友的支持,美国始终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扩张限制在阿富汗、叙利亚、南也门等少数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更成为压垮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从较长时段看,这两个目标本身及其为之配套的相关政策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后果。由于世界各大宗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复兴时期,苏联解体带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重组又让各主要宗教势力趁机介入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生活。20世纪80年代集结在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战士成了此后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源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是其中的典型。与此同时,鉴于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源自宗教、意识形态和历史等多重因素,是一个长时间都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美国中东政策偏袒以色列的基本特点还将长期存在,这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普遍不满,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更是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美国的主要理由。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所应对的挑战领域逐渐从传统威胁延伸至非传统威胁,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被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尤其严防两者的结合,确保美国不再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特别是遭受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安全利益是美国中东政策着力最多的目标,其他对外政策目标都必须服从于这一根本利益,但由于目标和手段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背离,安全利益反而是实现程度最低的国家利益目标。具体的表现有三:一是强化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担忧和仇视,反过来也恶化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陷入了以暴制暴的怪圈。二是反恐遭遇了越反越恐的逻辑困境。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攻击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而为了抗议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伊斯兰极端势力只能更多地依赖恐怖袭击等非对称手段显示力量。第三,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获取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因,需要在国际和各地区范围内建立起和平、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国际关系,将一些国家称为“流氓国家”并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只会刺激一些国家更强烈的拥核愿望和企图。 (四)滑落中的领导地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霸主地位确立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强调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的责任,认为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其实是在履行其全球领导者的责任,是在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地区秩序和石油供应等公共产品,让搭便车的其他国家不需要依赖也能够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19)这在长时间地和平时期确实是一种现实。但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从“一超”向“首强”的普通大国化滑落速度出人意料,在维持全球秩序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从喀布尔、加沙到开罗、哈拉雷,美国已经充分暴露了自身的能力限度,一些既定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越来越难以致力于解决传统安全隐患以及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国际形象在部分地区持续恶化,作为国家软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信誉明显下降。伊朗更坚定地寻求核保护伞,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的“石油换安全”契约面临新的变数。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等国的新领导人因为不大可能违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很难认可美国的关注重点。部分阿拉伯民众始终认为本·拉登并不是“九·一一”事件的唯一真凶,美国和以色列也是“九·一一”恐怖袭击计划的参与者。(20)2013年9月,美国针对巴沙尔政权一度箭在弦上的军事行动戏剧般停止,对盟友的承诺被看作是“基于政治权宜和短期舆论而非根本原则”,与俄罗斯签署的“化武换和平”协议的签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失败之一”。(21)多年盟友沙特更是指桑骂槐地批评安理会就巴以问题、叙利亚流血冲突和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事务持双重标准,没有能够真正行使其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引发了让世界惊愕的挑战联合国权威的“安理会风波”。(22)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世界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加分散、更加网状化、更加亚洲化的世界。2011年之后的中东正不易察觉地迈向“后美国时代”,也许会在某些角落变得更有民主色彩,却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安。(23)从本·阿里到萨利赫,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奥巴马政府终结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以及创立一个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的主要外交目标已经完成。(24)悲观地看,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拥有老布什和克林顿所享有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自由度。(25)美国总统继任者的最艰难工作,就是让美国人习惯美国在世界影响力处于冷战以来最低点的事实。(26) 美国中东霸权的相对衰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从乌尔、底比斯、波斯波利斯到罗马、长安、开封、佛罗伦萨和纽约,人类的辉煌如过眼烟云。有记录的人类社会在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后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但权力的更迭过程本身却可能滋生混乱和动荡。连英、美那样的和平权力交接都曾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更遑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泛滥、新技术和非政府力量如此强大的今天。然而,正因为如此,当一度被视作财富代名词的美元越来越丧失强势地位,当阿富汗和伊拉克乱局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一种象征,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开始伴随全球化传遍世界。这种不安全感的背后,就是曾在单极世界中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美国地位的动摇,不仅认为美国从冷战结束的那一刻就开始衰落,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大老板约束的“中上层管理者”角色;(27)同时还担心素有孤立主义思想传统和现实基础的美国不愿意在一些地区事务上发挥影响,担心世界会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失败而更不稳定。(28) (一)美国中东霸权的衰落表现 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在多个领域都开始衰落。第一,西方两个世纪来对中东的军事影响由上升转趋下降。在1955~1979年间,西方的军事渗透一度涉及中东国家的军火供应和高层指挥系统等多个层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建立了32个军事基地以确保西方盟国的石油供应。(29)但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就一直被削弱,1980年撤出伊朗,1983年撤出黎巴嫩,1993年从索马里撤军,2003年后撤出在沙特的驻军,2011年撤离伊拉克,2014年撤离阿富汗,在中东的常规军事力量很多时候已经不能转化为对当地的影响力。由于北约对阿富汗的重建已经仅限于使之不能沦为“失败国家”这个最低安全目标,2012年“撤军之年”后的联军军事残留已经具有了与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留下的碉堡、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遗留战争残骸相同的象征意义,美国在“帝国坟场”阿富汗不确定的仅为失败的程度而已。(30)第二,西方与中东的商业关系呈现下降趋势。美欧国家曾经是中东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但随着产油国“向东看”政策的实施,西方曾经的经济优势正在发生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将超过2/3的原油出口到远东,自2002年起一直是中国原油进口的首要来源国,输往美国的原油不到总出口量的1/7。第三,虽然美国给予以色列、埃及、约旦等国的大规模援助曾经长期发挥着作用,确保这些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在相关议题上的合作,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蔓延整个西亚北非的民众运动、土耳其越来越强的自信、伊朗的强硬与“核崇拜”、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受阻等,都正塑造着中东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结构,西方在中东将不再拥有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代理人。第四,西方民众对本国政府参与中东事务的支持越来越弱,越来越质疑以惨重代价推广美国价值观是否值得,开始质疑推广美国价值观本身是否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31)呼吁降低外交成功的标准,重新审视正在寻求的外交目标以及能够承受的代价,追求利益和成本相称的结果。(32)2012年初,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得不偿失,一向支持反恐作战的共和党阵营也首次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不值得为阿富汗战争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阿富巴”战争已经到了越打下去越不利的“收益递减地步”(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33) 世界仍然需要美国,但美国需要改变,这一趋势在2008年后的出现既始料未及又不可避免。说始料未及是鉴于由来已久的国际政治背景,即全球强烈的反美情绪和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一度甚嚣尘上的军事打击迷思;说不可避免,则是因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群体,“金砖国家”(BRICS)代表的新兴市场还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和竞争力,金砖时代更多是一个概念而非现实。(34)更重要的是,中、俄、印等新兴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然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平衡,但在全球范围仍然缺乏重新梳理国际关系所需的实力,美国在全球安全、商业、外交乃至文化方面的领导能力依然对各国政府及个人的投资决定有着相当影响。在2014年围绕伊拉克境内“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武装的国际博弈中,无论是“伊斯兰国”武装的攻城略地、伊拉克政府的臝弱不堪,还是美国对空袭时机的精准把握、地区国家对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欢迎态度,就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国际政治现实。 美国人越来越不愿出动军队发动单方面军事打击是不争的事实,曾在2009年宣称要在世界推进民主进程的奥巴马总统如今已大幅偏离价值观外交,说得更多的反倒是如何保护盟国安全及保障石油供应等具体利益。(35)但一方面因为2014年乌克兰和伊拉克局势的大起大落,美国国内主流舆论已经对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收缩政策大为不满,批评是“过度收缩”和“回归孤立主义”,(36)另一方面也因为对“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的空袭很可能会变成一场新的战争冒险,会将美国卷入一场和武装极端分子们进行的更长期、更昂贵的军事冲突,奥巴马授权美军空袭“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的8分钟陈述,启示和2003年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本质上区别不大,后冷战时代美国将“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进而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干预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具体参与过程中,首先由于传统的民主意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三权分立架构造就的权力制衡,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目标和战术运用经常混乱而矛盾。“九·一一”事件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肆意挥霍反恐旗帜下一度拥有的高支持率和道义力量,阿富汗战事未了便挟重对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磨刀霍霍。发动倒萨的伊拉克战争却对必然会随之出现的权力真空未预设答案,不仅因指责沙特等温和派国家支持恐怖主义而致使后者未能及时填补空缺,更因药不对症的民主化改造而让伊拉克教派冲突加剧,致使坐大的什叶派与跃跃欲试的伊朗形成了某种呼应之势。其次,由于把理想目标作为外交的主要动机,在每次人道主义面临挑战时都优先考虑武力解决,几乎看不到动武的终点。(37)在1798~1993年期间,美国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案例高达234次,冷战期间的对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有125次,1990~2012年间先后对外出兵40多次,其中对他国进行强力军事干预10次。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动武的理由也从“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反恐战争”发展到“美国特殊论”、“大中东民主倡议”,理由越来越抽象,适用范围越来越扩大,对外动武甚至一味追求颠覆政权。第三,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固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推翻一个政权,因应具体事务的手法始终细腻而老练,包括以领导者而非主宰者的角色在中东地区发动了3场战争,在炫耀武力的同时注重外交斡旋等,但随后却总是不可避免无法自拔地陷入了协助被占领国进行“国家建构”的泥潭。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十年反恐斗争中,美国逮捕了12万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并将其中3.5万人被绳之以法,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并扩散到更多地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已经陷入了两难困境,美军离开必将导致权力真空引发内战,继续驻留则会受到财政困难和人员伤亡的煎熬,未来最可能的出路就是有悖最初战略意图的“再扶植一个独裁者”。(38) (二)美国中东霸权衰落的相对性 客观地讲,“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Pax-Americana)确实没有为中东带来持久和平,甚至还激发了许多超出其控制能力的地区冲突,从巴尔干半岛经中东到中亚的动荡弧线区已然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导致这一状况诚然有美国的傲慢自大等内在因素,粗鲁而虔诚的小布什就被当作了诸多过错的挡箭牌,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把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当成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被处绞刑的萨达姆就因为被看作是唯一不被美国和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的阿拉伯领袖而在部分人中间享有“殉教者”的荣誉。但小布什政府没有制造恐怖袭击和中东流血内斗,奥巴马政府的诸多纠偏措施也没有对中东乱局产生多大实质性影响。(39)伊斯兰世界自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遇刺以来一直就是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阿拉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融合不彻底、地域特色浓厚的民族,历史上的统一时间不过百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同时具有分裂性、发育不健全、地区至上主义流行等先天性缺陷,任何参与中东事务的外来力量都不可能八面玲珑,没有谁能提出并真正实施一个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浪漫的法国人曾严格按照数学公式设计了黎巴嫩的国家权力架构,但最终也难免灰头土脸走人的命运。克林顿政府对中东和平协议的最后冲刺以第二次巴勒斯坦抵抗运动(Intifada)的爆发告终,而布什政府最后一年的中东政策引发了巴以间的又一场战争。(40)事实上,无论是卡特的伊朗战争、里根的黎巴嫩战争还是布什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政治声望因为参与解决中东事务而得到提升,中东甚至被调侃为“专门坑总统的地方”。(41) 从本质上看,“美国的难题不是力量不足造成的,而是力量以外的因素造成的,或者更精确地说,美国面临的问题在于问题本身而不在于力量不够用,这是症结所在”。(42)曾经在伊拉克战争中几乎取得完胜战绩的美国军队,其主要困境就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之设定了超过其自身能力限度的目标,不仅追求以刺刀在传统氛围浓郁的伊拉克推行西方式现代制度,而且想一蹴而就地移植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取得的民主成果。迄今为止,美国的主权和自身国家安全并未受到太大威胁,美国的力量和地位仍然优越,霸权位置仍然稳固,很多时候仍是不少国家比较信赖的外部安全力量。因此,尽管有人结合罗马帝国、中国大明王朝、法国波旁王朝、大英帝国以及苏联快速崩溃的史实,从帝国覆亡与财政恶化的关联度上悲观地预测美国已经走到了崩溃边缘,(43)但基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发展惯性以及美国只是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的客观现实,基于中东失误在美国全球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性以及国际政治的强大发展惯性,几乎可以肯定,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伊朗和叙利亚等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给仍将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目标,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框架仍将仅限于局部性修补而不会大变,所谓的整体战略收缩实际上很难落实。(44) 美国参与中东事务对中国的启示 对正逐步涉足中东事务深水区的中国外交而言,要掌握和娴熟运用相关外交技巧仍有长路要走,美国的中东政策及其实践得失就是中国中东外交成长的有益借鉴。 (一)中、美参与中东事务的渐行渐近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和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基本趋势。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的一连串乱局中徒耗军力财力而无所建树,始自布什政府后期的“撤出战略”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开始实施,其在中东通过军事和贸易关系而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开始衰减。在2012~2013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总额下降63亿美元,虽然因为石油进口减少导致与沙特和伊拉克的贸易分别下降30亿和60亿美元,但对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曼等国的出口下降才更反映问题。相反,由于2001年入世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所形成的巨大能源渴求和商品生产能力,为了维持国际能源秩序而与中东国家形成一种新的多极平衡联盟;也由于部分中东国家的“向东看”倾向以及利用对华关系来抗衡美国的政治需要,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2009年以来,中国与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国在医疗保健、能源勘探,采矿和铁路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十多项重大合作(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权力精英们,尤其是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非常羡慕中国如何在拒绝西方制度、维持本国体制的情况下实现经济飞跃。有民意调查显示,23%的阿拉伯人认为中国是他们更喜欢的全球超级大国,选择美国的只有7%。(45) 中、美在中东有利益分歧,存在着一些潜在甚至可能无法避免的冲突,但由于双方在中东格局中的分量并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外来参与者,无论是自身还是外界的预期都有着不同的内容,更由于双方在全球层面还有着基本的合作框架和几乎不可逆转的合作趋势,日益重视在可持续发展、恐怖主义威胁等特定议题上的合作,中、美在中东事务上的利益重合点越来越多。中国虽然反对美国在处理防扩散问题的双重标准和军事打击迷思,对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和施压举动等抱有负面看法,但基于战略利益考量和现实的地缘政治考虑,也逐渐严控对中东的进攻性武器出口,加大对政权更迭国家的重建援助。 “九·一一”事件以后,虽然中国担忧美国势力进入中亚会实质性地影响西北边疆安全,美国政府也对中国打击“东突”势力的行动指手画脚,但由于美国反恐战争越来越步入攻坚阶段,对“东突”等中国的切身利益诉求给予了一定认可,更由于对恐怖主义活动认识的逐渐深化,中国也逐步配合美国的“反恐”斗争及伊拉克重建等议题,官方层面没有对相关事务发表过带有情绪性的批判言论,与美国在情报和反恐等层面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多。2007年1月,中国在帕米尔高原摧毁了“东突”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美国则在索马里南部边境地区对“基地”非洲组织的秘密基地展开空袭。这两次反恐行动都采取先发制人战略,都没有公布与恐怖组织相关的足够细节,中、美都对彼此的反恐行动不予置评。 这种有限度的默契与合作,既表明中、美在反恐方面确实存在着共同利益,能够在操作层面进行配合,同时也表明中、美间的合作依然是一种议题性合作而非战略性合作,具体交往取决于对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从更深层次看,中、美双方由最初对各自反恐行动存在的认识偏差逐渐转向了对共同利益的有限度维护,至少都程度不同地开始正面看待对方不同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对外参与中的渐行渐近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集的缓慢形成过程。基于此,美国学界始终有声音呼吁对中国采取融合而不是孤立的策略,与有潜力塑造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的中国建立一种以选择性合作为基础、以限制分歧和影响为共识的关系,“尝试把中国融入21世纪的最高层理事会,应该是新总统及其团队的头等要务”(46)。 美国是现存国际体制的霸权国,其最大利益就是维系现存国际体系的运转,在危机地区尽快建立某种次级地区秩序,因而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容许其他国家搭乘便车。这是中、美在中东事务上渐行渐近的另一个推力,当然也是一种霸权体系的应有之义。在阿富汗,虽然美国在2001~2013年间的重建费用(10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二战后英国和德国的重建费用,在2014年结束军事驻扎后还将继续对阿富汗提供每年60~100亿美元的资助,领导北约军队勉强为阿富汗提供了某种基本秩序,但如果不允许其他外国公司进入,缺乏工作机会和税收支撑的阿富汗依然是极端分子的庇护所,重建任务遥遥无期。虽然对这幅亚洲地缘政治的未来景象颇有怨言,但在这种两难局面中,美国实际上也只能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如果美国快速撤离或大力削减在巴阿边境的反恐力度,塔利班和极端主义势力将很快控制坎大哈乃至整个阿富汗,中国的投资利益固然会遭受损失,但美国却必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不仅必须直面从中亚绵延到印度的这一激进的伊斯兰地带,还将因为丢脸的失败而丧失国家尊严和盟友的信任。因此,作为体系霸权国的美国在阿富汗除了继续战斗之外别无选择,同时还必须容忍具有地缘优势的中、印、俄等国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纽约时报》为此大声疾呼,阿富汗应当是美国作为陆上干涉者的最后一个地方——美国正在那里卷入伊斯兰内部纷争,为其他国家的战略野心火中取栗。(47) 不仅如此,中东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地希望引进其他国际力量来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给自身营造更均衡的发展选择和外部环境。自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阿拉伯世界动荡以来,虽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尚未做重大改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保留强大军事存在,在科威特依然保留1.5万驻军,在卡塔尔建有前线指挥部,斥资5.8亿美元扩充“第五舰队”,2007~2013年间共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了750亿美元武器,全力支持海湾诸国提升自卫能力。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因应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日益凸显重要性,在其他地区的整体战略收缩已经对美国中东外交的战略信誉造成了即时的严重损害,摇摆不定的实用主义中东政策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48)埃及的将军、沙特的王子、以色列的政客以及中东的其他保守势力似乎都认为奥巴马是个弱势总统,他们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己,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势力因而被当作了重要的平衡选择。 (二)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油气动力 由于国内石油消费增长快速,中国1993年在数量上成为油品净进口国,1995年在贸易金额上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净进口国,原油消费接近全球消费总量的15%。从1993年起步到2004年的1.227亿吨和2007年的1.968亿吨,中国原油进口首次破亿历时11年,而超过2亿吨仅用时4年。2010年,中国原油消费量4.29亿吨,进口2.393亿吨,对外依存度55.8%。2013年,中国原油消费量4.89亿吨,进口2.8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7.39%。(49)“小马拉大车”的石油消费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从外部寻求石油供应,必须积极开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 除了生产落后于需求的内部因素外,现存国际石油格局也决定中国必须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石油。表面上看,海合会国家的原油储量和出口量都很大,是世界市场安全、可信赖的石油供应源群体,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群体,似乎只要与政局稳定的沙特、阿曼、科威特等国保持联系,或者在海合会框架内与之保持良好的多边关系,中国就可以稳定地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系数。但2005年以来的油源多样化努力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虚幻性。为了锁定几个长期供应国并增加直接进口量,中国领导人曾先后多次访问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希望增加直接进口原油数量或签订长期的直接购油协议。然而,由于海湾国家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严重依赖西方石油公司,政府所掌控的份额油数量有限,实际上无法满足中国直接购油的愿望,双边石油贸易只有少量是直接进口现货,大部分交易仍必须通过国际期货市场进行。(50)虽然具体的原因和时代条件有所不同,但与美国在20世纪积极介入中东事务一样,中国在21世纪初期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也有着很深厚的能源因素推动。 国家利益的层次是根据受威胁的程度来界定的,受威胁最大的利益往往被视作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以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常态互动以及深度合作往往被忽略,引人注目的倒是双方不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动荡的中东一直充当着中国的“油库”,超过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从沙特和伊朗的进口占中国石油进口的1/4左右。虽然一直有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深入探讨,油气年输入量仅占中国消费总量2%(2012年)的中亚油气管线被夸张地寄予厚望,甚至有过对“马六甲困局”这样极端化命题甚或伪命题的激烈辩论,但实际上,在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现存国际体系内,中国在中东微弱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并没有成为寻求能源安全的显著障碍,对规则的遵守和利用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超过2/3的进口油气依然从东线的海路输入,维系着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3的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转,主要起着战略配合作用的南线(中缅石油管线)、西线(中亚油气管线)和北线(中俄石油管线),无论在现实上还是经济性上都还承担不起供应中国油气进口的重担。在全球化时代,能源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军事与政治问题,石油的政治味再浓厚也仍然是一种可以买到的商品,其主要交易场所是国际原油市场而非战场。由于目前的全球油气供应总体上并不短缺,中国的能源问题因而不是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而是买不买得起、怎样买更划算的问题,还有怎么样节约用油和合理用油的问题。中国的能源安全,主要是预防突发性的国际动乱、恐怖活动、区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而不是所谓的“美国遏制”或国际限制。(51)如果否认国际社会的理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中性和国际油气市场的经济性,基于极端化假设和偏激情绪而人为夸大中国的能源安全,认定主要大国都在别有用心地对待中国,一个孤独的中国要愤怒地面对一个可怕的世界,不安全的就是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能源供应,需要解决的是整个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当然,正因为如此,中国对中东事务的未来参与走向才更值得关注。一旦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或试图在该地区战略收缩,拥有足够政治影响和军事投放能力的中国似乎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动力去填补这个真空的国家。而只要中国对中东事务变成无法回避的深度参与者,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形象就非常可能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从被羡慕和被欢迎迅速滑落到被批评和被憎恨。这是充满诱惑的参与前景,也是危机重重的参与方式。 (三)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美国镜鉴 回顾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状况,至少对中国的中东外交有着心态定位、战略选择、战术实施、效果预期等四方面的深刻启示。 第一,中国行为体应该以从容的心态稳健地参与中东事务。具体而言,就是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推进与中东国家关系,做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而不是领导者,将有限的外交资源用于推动重大的中东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坚定支持中东国家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支持中东国家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热点问题,支持中东国家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支持中东国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中国行为体应该继续秉持沉稳姿态,既不幻想能够一蹴而就地在中东拓展自身影响,也不认为暂时地超脱就会如何地被边缘化和利益受损,始终客观冷静历史全面地看待自己和别人,在守住服务国内建设这一根本的前提下稳健地参与中东事务。 第二,中国行为体应该对深度参与中东事务在战略选择上秉持审慎态度。所谓审慎,就是指现阶段的中国外交首先必须明晰自身的能力限度,明晰具体参与的目标和结果预期,先易后难,宁实勿虚,在现有国际格局和地区机制的框架内谋求自身利益,推动而非主导中东问题的解决。如果忽略中东事务本身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忽略不同行为体对国际体系认知、感受和策略选择上的代际差距,不从参与者的角度思考解决措施并防范失误,仅仅以旁观者的角度肤浅解读他国参与的不足和失误,试图以抽象的政治理念和空洞的口号愿景因应实际的具体问题,那么对中国能够顺风顺水参与中东事务的任何断言都将是不切实际的假设。 第三,在参与中东事务过程中,中国行为体应该采取多元外交格局的合力形式整体参与。在具体的整体外交体系构筑过程中,中央级的国家外交机构,包括外交部和与之有特殊指导、配合关系的中央外办,应该主抓国家外交机构问的“外交”互动,放手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与对象国相应行为体的“外事”互动,在新的层面上寻求放权与集权的平衡。事实上,只有尽快改变以往外交部门参与中东事务的孤军作战状态,构筑涵盖全方位行为体的多层次、有弹性的总体外交体制,通过与对象国相应行为体的全方位、同级别整体互动,中国的中东外交才能以行为体的多层次性、广泛性营造必需的战略纵深和空间,以全方位行为体的对外参与保障中东外交的丰富性和延续性。 第四,中国行为体应该时刻关注参与中东事务的有效性。作为中东舞台上的后来者,中国的中东外交要减少对外参与中的曲折和反复,在指导思想上就应该尽可能将对外参与重点服务于国内发展需要并顺应国际体系变革大趋势,在具体过程中保持与参与国的深度友好并有若干长期的高质量战略盟友和足够的战略配合力量,尽量避免具体参与结果的反复和徒劳。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相关的中国行为体必须放弃全输全赢的极端化观念,避免悲观失望和狂热冒进两种情绪和倾向,排除短视和急功近利的“盲点”,找到与他国互惠互利的“平衡点”,提纲挈领地做好做深每一个具体的参与对象,在争取参与结果最大化的同时积极防止反复和徒劳,最终由点及面、扎实地拓展在中东的影响力并实现双赢。 客观地讲,美国确实是罗马帝国以来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帝国,也是治下秩序最有活力和制度最完善的帝国,然而以美国无与伦比的软硬权力尚且在各种安全困境和危机中步步涉险,更遑论羽翼尚未丰满且正处于发展机遇期的中国。虽然中国在中东事务上一直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也能够部分地通过自身努力达到目的,但现阶段在中东战略利益的实现主要还是利用了美国的失误。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都能够理性地互相看待,在维持中东稳定这个大目标上保持一致,中、美就应该能够在一系列重要的中东事务上开展合作,中国就很可能成为美国正在寻求的缺失的那块拼图。(52) 从过去500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现在并不是历史上最富裕、最强大的时期,相对文明程度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比,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如鸦片战争前后,人均收入长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部门主导的社会发展面临“转型陷阱”。国家的经济规模不等于国家实力,从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只能得出中国应该更深入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和重要跨国问题的结论,如果就此引申出应该承担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政治责任恐怕就有点武断和冒进。英国在统治地球1/4的较长时段里从来都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53)而晚清王朝在最后20年即便衰落也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4)但恐怕没有人否认“日不落”帝国长达200年的全球霸主地位,当然也没有人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对外割地赔款看作是清政府应该承担的对外政治责任。鉴于历史上众多帝国最终衰亡的一个共同因素,就是它们过度庞大和伸张的外交布局超过了自身的安全需要和能力限度,现阶段参与中东事务的中国国际关系行为体,还必须以更宽广的视角务实理性地审视中东事务,以更从容的姿态稳扎稳打地参与中东事务,审慎参与,整体参与,争取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和最大化。 注释: ①高祖贵:《伊斯兰世界:美国的霸权支轴》,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8期,第2页。 ②储昭根:《波斯湾石油:一个世纪的博弈》,载《南风窗》2010年第21期,第82~84页。 ③[英国]理查德·克罗卡特著;陈平译:《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④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March 2006,p.1. ⑤Mary Buckley and Robert Singh,eds.,The Bash Doctrine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New York:Routledge,2006,p.104. ⑥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8、14页。 ⑦Richard.G.Lugar,"Beyond Baghdad",The Washington Post,Jan.30,2007. ⑧Thomas L.Friedman,"Never Heard That Before",The New York Times,Jan.30,2010. ⑨高祖贵:《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分析》,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21、22页。 ⑩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6~18页。 (11)于汶加、马晓磊、闫强:《浅析美国能源独立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载《中国矿业》2013年第9期,第15页。 (12)Walter Russell Mead,"Why America' s in the Gulf",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28,2007. (13)钱伯章:《页岩气助推美国石化工业》,载《中国石化》2011年第12期,第47页。 (14)Josh Rogin,"Congress prepares 'Middle East Stability' funding package",Foreign Policy,Feb.15,2011,p.24. (15)Jeremy M.Sharp,"Egypt:Transition under Military Rule",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June 21,2012,p.22. (16)李建华、张永义:《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第66~67页。 (17)《叙利亚化学武器和美国人道德立场》,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16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2-12/16/content_1774656.htm,2014-05-30。 (18)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Mass:Balknap,1981,p.147. (19)Walter Russell Mead,"Why America's in the Gulf",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28,2007. (20)Michael Slackman,"9/11 Rumors That Become Conventional Wisdom",The New York Times,Sept.8,2008. (21)Tom Nichols,John R.Schindler,"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Collapses",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16,2013. (22)Editorial,"Saudi Arabia's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Nations",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18,2013. (23)Ray Takeyh,"A Post-American Day Dawns in the Mideast",The New York Times,June 8,2011. (24)Jeffrey T.Kuhner,"Obama's Islamist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Times,March 31,2011. (25)Helena Cobban,"Barack Obama,and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15,2008. (26)Massimo Calabresi & Al Janadriyah,"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Superpower",Time Week,May 19,2008. (27)Fred Kaplan,"Downsizing our Dominance",Los Angeles Times,Feb.3,2008. (28)"Weakened Superpower Harms World Stability",Yomiuri Shimbun,Jam 4,2008. (29)David Ignatius,"In Syria,U.S.Credibility Is at Stake",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9,2013. (30)Gideon Rachman,"The West Has Lost in Afghanistan",The Financial Times,March 26,2012. (31)Derek Chollet,Tod Lindberg,"A Moral Core for U.S.Foreign Policy",Policy Review,No.146,Dec.2007 & Jan 2008. (32)Richard N.Haass,"Defining 'Success' Down",The Washington Post,May 14,2009. (33)Helene Cooper and Eric Schmitt,"U.S.Officials Debate Speeding Afghan Pullout",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3,2012. (34)Jim Yardley,"Acronym Is Easy,but Common Ground Is Hard",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8,2012. (35)Editorial,"What Obama Must Do For Syria Peace Talks",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 21,2013. (36)钟声:《“伊战错误论”缺少道义负疚感》,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7日。 (37)Henry A.Kissinger and James A.Baker III,"Grounds for U.S.Military Intervention",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8,2011. (38)张云:《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是否衰弱”的老课题》,载《联合早报》2011年1月3日。 (39)Jackson Diehl,"A World of Trouble for Obama",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20,2009. (40)Jackson Diehl,"Road Map to a Gaza War",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7,2008. (41)Jeffrey Goldberg,"Obama's Syria Pause Only Delaying the Inevitable",Bloomberg,Sept.11,2013. (42)林利民:《复杂挑战下的能力限度》,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14页。 (43)Niall Ferguson,"Complexity and Collapse:Empires on the Edge of Chao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0,pp.30~32. (44)牛新春:前引文,第23~24页。 (45)Andy Polk,"China:A Major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The Diplomat,April 1,2014.108. (46)Richard N.Haass,"China:Don't Isolate,Integrate",Newsweek,Dec.8,2008. (47)Robert D.Kaplan,"Beijing's Afghan Gamble",The New York Times,Oct.6,2009. (48)David Ignatius,"In Syria,U.S.Credibility Is at Stake",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9,2013. (49)钟健:《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收减“油门”》,载《经济参考报》2014年3月7日。 (50)赵学昌:《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全面展开》,载安惠候、黄舍骄、陈大维、杨健主编:《丝路新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51)杨光:《中国石油安全的假问题真问题》,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33期,第78页。 (52)Andy Polk,"China:A Major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The Diplomat,April 1,2014. (53)Michael Beckley,"Don't Worry,America:China Is Rising but not Catching Up",The Washington Post,Dec.14,2011. (54)[英国]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标签:石油资源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中东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 伊朗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