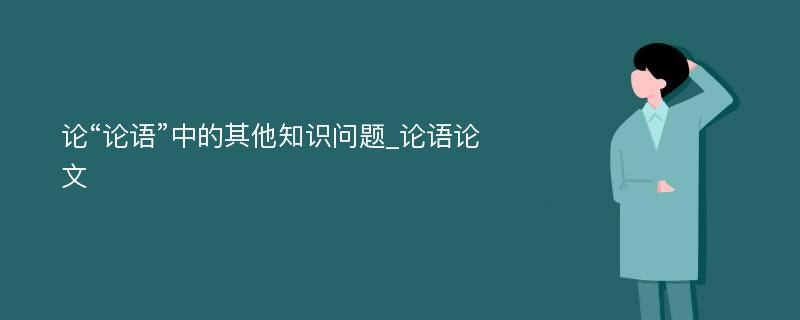
论《论语》中的他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国人来说,《学而》作为《论语》的开篇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事物往往因熟视而无睹。《学而》看似简单,细究起来却内涵丰富。“学而时习之”,是同一主体的自我区分、自我提升问题。“学”是主体的初始状态,“习”是主体的追加状态;“习”是在“学”的基础上进一步精思、巩固、熟练和提高。“有朋自远方来”,讲的是不同主体的共处问题。“远方”点明“朋”与“自我”之间的空间距离,但这里不仅是空间距离。不同人乍然凑聚,必有素质高低、观念差异与矛盾碰撞,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人不知而不愠”,是讲主体之间的认知障碍问题。“人不知”表明沟通不畅,自我不被他者理解、认可与接受,这意味着主体之间的对话失败。“人不知而不愠”,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熹就说:“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①
由此可见,《学而》不简单,它依次揭示了同一主体内部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而时习之”主要是自我在不同阶段的能力提升问题,可概括为自知问题;“人不知而不愠”则涉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沟通、相互承认的问题,可概括为他知问题。自知问题当然重要,新我与旧我拉开距离,不断超越自我,这是很紧要的自我发展。然而,单是自我发展还不够,还需要把自我发展的结果作为价值实现出来、展示出来,这就离不开自我与他者打交道,因此他知问题也非常重要。自我的价值、才华能否被他人与社会所了解和承认,这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一个人再自我努力、自我提高,倘若得不到他人认可、得不到社会承认,则在社会中就很难立足、很难发展。可见,他知问题不是单个人的问题,而是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也不单纯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个人生存与发展、价值实现的根本问题。
历来讲《论语》者众,但对他知问题还重视得不够,也很少论及。尽管近年来也有人引入西方的主体间性概念来讨论“仁”的问题,但多是从道德实践角度讲人际关系协调问题。本文讲他知问题,是想突出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认知、相互承认问题,尤其是强调如何对待自我不被他人认同、承认的他知障碍问题,由此揭示这一问题在儒家传统中被日益遮蔽乃至取消所导致的弊端,进而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探讨必要的、可取的应对之道。
一、他知问题在《论语》中的出现
直接或者间接提到他知问题的表述在《论语》中可谓大量存在着。孔子自身的经历与遭际在《论语》中屡有述及,其中很多就涉及孔子本人被当时社会上的很多人理解或者误解的问题。孔子有自知之明,《论语》中不乏夫子自道式的言论,然而是否被他人接受、认同则是由不得他的。
比如《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段话表明叶公作为外人是不了解孔子的,这是孔子不被人知的一个客观事实。更值得重视的是,孔门内部、尤其是作为重要弟子的子路也不能说就深刻认识了、理解了孔子其人。子路的无言以对表明其对于孔子在认知上存在着困难。不理解还是其次,更为严重者,子路对于孔子甚至产生过怀疑与误解,比如《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已经闹到了要赌咒发誓的地步。
不光是子路,即使其他高徒,对孔子也未必能认识到位。比如《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段话当然表现了作为第一高足的颜回对于孔子的推崇以及自我谦抑,但也说明了孔子作为认知对象而言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有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颜回对于孔子尚难以明确定位与准确把握,就更遑论他人对于孔子的认识之如何远离本真了。所以,基本上说,孔子生前就不被当时大多数人所认知、认同、认可。
然而,任何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总要经由他知环节,尤其是“士”这一阶层,必须通过社会评价与承认机制来争取自身的地位与权力,进而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当时来讲,“士”的评价话语权首先掌握在国君、大臣这些人手中。在专制时代,个人的价值认定与实现程度,只能依赖于当权者的所谓“知遇之恩”。孔子周游列国屡遭挫折,甚至有“陈蔡之厄”,本身就证明了这种他知机制的彻底失败。有些当权者甚至公然蔑视、诋毁孔子,比如《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下文又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这都表明孔子在当时的尴尬境遇与他知困境。
可悲之处还在于,孔子不仅在当权者那里得不到认可,即使一般人对他也多有误解,甚至给出否定的评价。比如《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又如《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前者的否定性评价尚不那么尖锐,后者以“佞”字来论孔子就简直是一种侮辱了。因为就孔子而言,他是最讨厌“巧言令色”的,而如今却被名为“佞”,真可谓莫大的羞辱。所以,《宪问》亦记载了孔子的感叹与无奈:“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孔子自身所遭遇的他知问题是多么严峻。不仅门人弟子不能准确认识他、恰当评定他,而且上至当权者下至普通人也都对他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乃至恶评。那么,如何看待他知问题?是漠然置之,还是正视?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他知困境,面对误解与不认同,孔子自己并未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孔子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也会有牢骚无奈、内心委屈,甚至也想到过放弃,比如《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且孔子自己一直渴望着他知,对于广泛的社会认可抱有期待。他对“以道名于世”或“以道行于世”始终抱有幻想,而对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情况则明显不甘。比如《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其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卫灵公》中有对于“名”的渴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子罕》中又有对于“无闻”的警惕与“出名趁早”的提醒:“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以上都表明,他知问题的确是《论语》中屡屡道及的问题。一方面,孔子自己渴求获得社会认可,也积极地寻求被他人接纳的途径;另一方面,他确确实实遭遇了太多的他知挫折。从这个角度讲,他知问题就是孔子一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直接导致了他追求一生、颠沛一生的悲剧命运。
二、对他知问题化为自知问题的反思
尽管《论语》开篇就已经揭示了他知问题,而且孔子一生都遭遇着他知障碍,但是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强调得更多的,却是自知问题。甚至说,儒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知问题转化为自知问题。这样一来,他知问题就被自知问题遮蔽了,乃至说,被取消了,被从问题域中清除掉了。这一倾向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着,而在后世更是愈演愈烈。对此倾向,就有必要深入反思。
我们先来看几则《论语》中孔子对于他知问题的论述:
《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宪问》:“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卫灵公》:“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里仁》:“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由这几则可以看出孔子的基本思维模式、言说方式,其完整的格式可以概括为:“不患……,而患……。”“不患……”是针对他知问题的否定式表述,认为他知问题不足挂怀,自我不需要他知的支撑;“而患……”是针对自我而言的,是强调自我调整、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关键在于弥补自我的缺陷(“不知人”、“无能”、“不能”),只致力于营造他知的可能性(“求为可知”)。然而一方面,既然他知问题屡被道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孔子对于他知问题的无可回避,从反面证明了他知问题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从根本上讲,他知始终是自我修养的目标,自我强化自己最终仍是为了他知,只是暂时地不被他知而已。但另一方面,孔子又对他知问题一味采取“不患”这样的否定态度,于是他知问题就又被屏蔽掉了,被置换为“己不知”、“己不能”的问题。这样,他人问题、外界问题单纯归咎为自我问题,只需做好自己,他知与否根本无需过问。朱熹斩钉截铁地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作甚!自家为学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后真能不要人知尔。”接着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为善乃是自己当然事,于人何与。譬如吃饭,乃是要得自家饱。我既在家中吃饭了,何必问外人知与不知。盖与人初不相干也。”②话虽讲得高妙,但“为学”与“为善”的问题是否就与他者彻底绝缘呢?周全的讲法应该是这样:先以自我修养为主,暂时不考虑他知,以免分心干扰,只要自我努力,最终会被他者认可,即是说,自我与他知只是先后、主次问题,但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而非漠不相关、乃至根本对立的关系。
真正来讲,他知问题是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双向沟通、相互认知、相互承认的问题,它涉及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的两个方面、两个环节。他者作为自我的异己者,必然与自我有区别,作为独立的存在者绝非可有可无,绝不可无视,而他者本身就是决定自我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因素。自我存在的价值绝非仅靠自我单方面确证就能决定,而必须依赖于他者的他知认定。同样,他知认定的问题、他知障碍的产生,绝非仅靠自我单方面努力就能解决,它涉及他人的问题,更涉及整个社会认知机制、评价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比如当时世人对于孔子的诸多误解,就不单纯是孔子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单凭孔子自我修养就能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他知问题之所以成为严重的认知障碍,导致圣人贤士不受认可、不被重用,是因为当时社会的人才选拔、任用、评价机制出了问题。这是关系着政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本问题。只要人才选拔、评价机制被少数人垄断,只要当权者把持着话语权,那么诸如孔子、颜回这样的人才就只能听人摆布、被人遗弃,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死局就牢不可破。
但是,儒家偏要对于他知问题置而不问,屏蔽掉这些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只片面强调自我因素。于是,他知问题变成自知问题,个人得不到社会认可的机制问题化约为单方面的自我奋斗、自我提高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讲法,倘若自我在他者那里遭遇了认知挫折,不被承认,不被认同,这都不能怪社会、怪他者。要怪的话,只能怪自己没能耐,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怨天,不尤人”。但实际上,按照儒家自己的说法,孔子的自我努力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圣人地步,但个人遭遇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第一高足颜回的天资修养也已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界,不但生前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甚至死后连棺椁都是问题。这表明单靠自我努力、自我奋斗、自我提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单靠闭关自修,自省自励,不考虑社会因素、他者存在,不主动介入他知机制的改造,其实与闭门造车无异,是注定行不通的一条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千百年来,儒家仍然义无反顾地这么践履、这么偏执,这就需要进一步寻求其深层根源。
他知问题之所以被转化为自知问题,从儒家自身来讲,是与其一意“内向化”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的。中国至少从孔子开始,就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新趋势,就是把社会发展、个人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归结到单个人的自我学习、自我提高上来,假如是太平盛世,社会认可机制基本正常,这么做尚可说得过去,而若是乱世之秋,还一味闭门自修,不管其他,就显然是错误之举。所以,对于儒家的一切“归己”、“返己”的原则也应该从两面去看。
当然,儒家的观念表述有时好像很重视他者的存在,比如“仁”范畴就是强调主体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协调的。比如《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种思维方式、行事方式看似采取“由己及人”的外推方式,看似是“由内向外”的外化进路,但实则仍是基于“内在性”、“返己性”的原则立场,“能近取譬”即是强调以自我为基点。《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就明确地规定了“仁”以“克己”、“由己”为基本路径。《卫灵公》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都是强调把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建立在自我认知、自我克制的基础上。
可见,他知问题之所以被自知问题取代、遮蔽,就在于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所呈示的“内向化”与“责己”倾向。梁漱溟先生曾把这一倾向称为“向里用力”:“力气无可向外用之处。他只能回环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责怨、自鼓舞、自得、自叹……一切都是‘自’之中。尤其是当走不通时,要归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的向里用力。”③但问题在于,这种“向里用力”的套路从孔子时代开始,已经实践了千百年、无数次,其效果到底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三、他知问题的中西对比及启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知问题一向不是问题,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自我问题。外在因素、他人因素,一向被屏蔽掉,只是片面地强调做好自己、克制自己。但是,西方传统恰恰不这样,西方的“外向化”倾向一直是最为突出的。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学人在理解孔子时,也往往从外向沟通的角度来讲。比如,德国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讲“仁”时,强调“人存在的意义在于沟通”④,美国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甚至把孔子称作“沟通大师”⑤,这样来讲孔子就实在有趣,于此亦可见西方人的“外向性”倾向之根深蒂固。
真正讲来,中国儒家传统讲道德学问,向来是强调“不逐物”乃至“不及物”的,即是说,他者这一维度一般来讲是不考虑,或者至多是次要的。这一点从孔子就已经萌芽,而在后世则达到极致。对于心逐于外,儒家一向是戒惕恐惧的。《礼记·乐记》早就郑重其事地警告:“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段话讲得危言耸听,对照历史教训,也确实切中肯綮,尤其是切中西方文明的弊端。但问题是,中国传统完全走向极端了,只偏重“内圣”而开不出“外王”,也是不可取的。
西方文明重视外拓,势必强调外在征服而逐物。一方面,是自我必须征服自然,获取外在的客观占有,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必须实现于社会,甚至是要征服社会,获得他人的认可,“为承认而斗争”。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双重性的追求表现为《精神现象学》中所列举的“主奴意识”。简单地说,所谓“主人意识”就是片面的自我意识,只坚持着空洞的自为性而不及物,不主动从事物化活动,偏于“我性”而无“物性”,形成空洞的不着于“物”的“自我”;所谓“奴隶意识”则是片面的对象意识,溺于直接的物质劳作,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偏于“物性”而乏“我性”。主人不亲自劳动,必须以奴隶的劳动为中介来满足自己,这样他就是非独立的,反而在生存上依附于奴隶;奴隶则埋头劳作,其自我意识只能体现为对主人的恐惧,故也是从属的。⑥
《孟子·滕文公上》也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孟子的论述中,也具有类似黑格尔所讲的“主奴关系”的两重性,即在物质生活上,“劳心者”依附于“劳力者”,而在精神层面上,“劳力者”受“劳心者”统治。但黑格尔由此两重性看到了两者都有的片面性。“劳心者”空有“心”而不动手,故不能客观化其自身,“劳力者”空有“力”而无“心”,故不能由物返己,彰显自我。故双方都只具有片面的独立性,要么偏于身,要么偏于心而已。传统儒家作为“士”的代表,其职业属性当然以“劳心”为主,但这既是其优势,又恰是其短处。“士”空有“智性”的超越而无“物力”的展示,正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故不能直接占有物质资料而须经中间环节、社会认可机制,通过所谓“学而优则仕”,来获取一定的物质享用权。可见,“士”的自身生存本具有天然的依附性。孟子的错误即在于认不清这一致命缺陷,即是说,“士”若得不到认可,就无法成为“治人者”,所谓“食于人”就无从谈起。因此,儒家的悲剧性就在于,其价值主张恰恰与其职业本性相背离,其本性依赖于社会认可机制,而其主张却公然无视社会认可机制,偏要万事不求人而由己做主,反而可能弄得自己没饭吃。
黑格尔则由“主奴意识”看到了偏于物性与偏于我性的各自缺陷,主张两者之间建立相互承认的机制,这就强调了他知的重要性,强调了异化、外化、客观化的必要性。而儒家的自我意识则不然,仅仅停留于片面的内在性与空洞的自我性。一方面不主动外求,不去逐物,这样就陷于思想的空洞抽象;另一方面还不追求他知,这就切断了与他者的交往与沟通,等于断送了自我获得认可的机会,这就陷入了盲目的自我性。传统儒家发展到极致,只能是日益主观化、自我化,止于片面的内在性,而无法与外部世界真正打成一片。因为外部世界、他者始终被儒家看做是漠不相关者、于己无涉者,只需要一心返己、向内追求就行了。这样,他们所追求的,与黑格尔所批判的并无二致:“自我意识的这种自由对于自然的有限存在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它同样对于自然事物也听其自由,不予过问;这样,自身返回就成为双重的。单纯思想中的自由是只以纯粹思想为它的真理,而纯粹思想是没有生活的充实内容的,因而也只是自由的概念,并不是活生生的自由本身。”⑦
当然,站在中国传统的立场上,肯定会主张一种“内在的充实”,比如《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但是,这种“不可知”实际上是排除了他知维度的东西,是空有自我确证而缺乏客观认证的东西。那么,这种“神圣的内在性”会不会是一种盲目自信呢?既然他知被屏蔽掉了,极端的自知自证与宗教迷狂如何区别呢?倘若把一切外在性摒弃掉,把人自身的所有物性掏空,那么剩下的除了思想的空洞、纯粹的抽象还能是什么呢?这种片面否定式的思维方式无非是“我知我”这样的抽象同一性,因为它只是一再地说“我不需……”,一再地回避、逃避客观外化的证据。这样,儒家的追求就难免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自证”,这种“自证”既没有“物证”(因为它不逐于物,不着落于外物),也没有旁证(因为它不期待他知,不需要他者的认可),那么,它就可能沦为一种“孤明自证”!
然而,笔者的本意并非是说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完全是对的,中国儒家完全是错的,而是想指出西方思想有值得中国儒家借鉴的地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当然也有严重的弊端,但是其“主奴意识”的相关论述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为它既指出了附着于物性的必要性(奴隶制作器物),又指出空泛其身的自我意识的弊端(主人空有欲望而不寓于物),更指出两种意识之间相互承认的必然性。而儒家哲学的弊端则在于空洞地主张“德性之知”,而有意贬低“见闻之知”,只偏重于道德自我的挺立而忽略了物欲自我的满足,尤其是忽略了不同意识之间的相互承认问题。对此问题,美国哲学家米德的观点也与儒家哲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我。由于它是一个社会性自我,所以,它是一个通过它与其他人的关系而得到实现的自我。它只有得到了其他人的承认,才能具有我们希望它所具有的那种价值观。”⑧
令人惋惜的是,本来他知问题早在《论语》开篇就已经提出,但是这一问题却很快被遮蔽过去。“人不知而不愠”,问题恰在于“不愠”这一自我调适机制,它有意地缓解与减轻了他知障碍、他知挫折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导致对于他人的否定性认知不加考虑,乃至自我麻痹,陷入自我设置的“保护罩”之中,完全无视他者的存在。真正可取的态度则是:无论他人承认不承认自己,无论他人如何误解、诋毁自己,自我都应该积极地面对这一异己的刺激,与之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直至形成良好的认可机制。而反观儒家传统,甚至包括孔子在内,当面对异己存在的时候,当自己遭受严重误解的时候,主要的应对手段却只是“反躬自省”。“反躬自省”当然是必要的,但却绝不应该是唯一的,更不应该因此陷入自我小圈子而成为一种关门主义,彻底屏蔽掉门外异己的声音。
霍耐特说:“在社会现实中,对人的发展进步负责的道德力量,就是为承认而斗争,这就是黑格尔和米德的基本观点。”⑨这一“基本观点”虽不尽可取,但“为承认而斗争”却毕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它构成了值得正视的他者维度。真正讲来,单纯地采取自我维度,片面地只顾加强自己,或者单纯地采取他者维度,片面地只顾迎合他者认可,两者都是错误的;自我认知、自我提高与他者认同、相互承认,这两者应该是双向度的良性互动关系。既要从自我做起,自立自强,也要积极回应他者的质疑与异议,积极介入与他者的互动对话,进而积极改进、完善整体的评价与认可机制。
从现时代的要求讲,儒家需要接受他者的维度,必须应对他知障碍的挑战。一味地坚持内在充实性,片面地排斥外在性,或者说,一味地追求自我确证,片面地排斥他知、旁证的客观认证,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比如,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牟宗三先生,虽然也想借助康德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化,但其思路最终缺乏他者的维度,他所鼓吹的“智的直觉”因其强调“本心呈现”⑩而仍难免于主观自证、内在孤证的嫌疑。作为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儒家哲学,必须主动地迎接外部对抗,正视他知问题,承认他者维度的合理性,阐明他知对于自知的积极意义;而非像通常那样一旦遭遇他者的抗拒就缩回自家小天地,这实际是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蜗牛伎俩。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页。
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④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主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⑤郝大维、安乐哲著,何金莉译:《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4—373页。
⑥⑦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7—131、135页。
⑧丁东红选编,丁东红等译:《米德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⑨霍耐特著,胡继华译:《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⑩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1—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