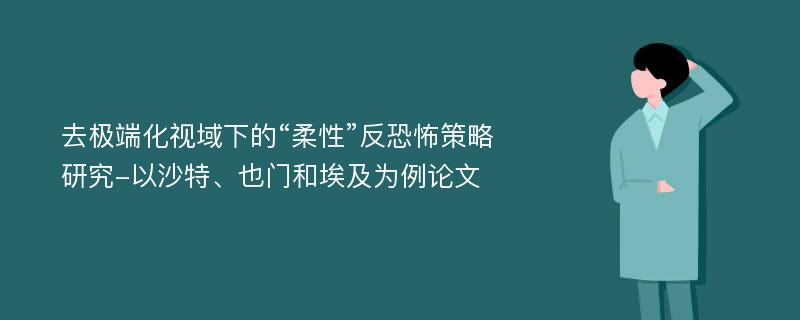
○犯罪学研究
主持人:郑 群,金 诚,刘 鹏
去极端化视域下的“柔性”反恐怖策略研究——以沙特、也门和埃及为例
兰 迪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3)
摘 要: 以强硬打击为主的传统反恐怖模式难以遏制恐怖主义的增长,过度依靠武力可能诱发更多的暴力回应。当前“四溢化”的“伊斯兰国”具备很强的暴力威胁能力。“柔性”反恐怖策略以去极端化为内核,在探明恐怖主义致罪因素的基础上,对恐怖分子和社会危险分子施以预防性的干预措施,促使其摒弃极端思想,重新融入社会。中东地区长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扰,以沙特、也门、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在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去极端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我国的去极端化可以遵循“刚柔并济”策略、“教育和挽救”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模式和“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并重”的方向。
关键词: “柔性”反恐怖策略;伊斯兰去极端化;恐怖主义犯罪;沙特;也门;埃及
一、传统反恐怖模式的局限
以“武力打击”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反恐怖策略,强调以彻底消灭恐怖主义犯罪为终极目标,具有“硬式”反恐怖的基本特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即为传统反恐怖模式的代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策略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遏制性措施,例如镇压、追捕、击毙和摧毁,具体表现为派遣地面部队、特种兵、实施空袭,以及运用无人机发动“斩首行动”;二是消极的保护性措施,注重维护相关人员和基础设施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方法包括扩大情报和安全部门权限、动用监听、监视设备以及识别危险分子。[1]
然而事与愿违,当“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因受到反恐怖联盟的强力挤压而呈碎片化后,“四溢”状态下的“伊斯兰国”恐比“建国模式”的“伊斯兰国”更加令人头痛和棘手。
废酸原液在硫化反应槽与Na2S反应,在反应槽内经过搅拌桨的充分搅拌混合后,加速其均匀反应,反应后液通过浓密机沉降,浓密机底流用铜砷压滤机过滤分离出砷滤饼,压滤机滤液与浓密机上清液汇合后送往石膏工序以降低废酸中的酸度。各硫化反应槽、浓密机及滤液槽等处逸出的少量硫化氢气体进入除害塔用10%的氢氧化钠循环液吸收后排空,反应生成的硫氢化钠送往硫化钠溶液系统,供硫化反应槽使用。详见图1。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现状
首先,2018年以来国际恐怖活动并未因“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暂时受挫而停止,全球恐怖袭击仍然频发。伊拉克、阿富汗、英国、突尼斯、喀麦隆等国家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袭击方式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汽车冲撞碾压、武装攻击和绑架人质等。恐怖活动正在由“动荡弧”和冲突热点地区向全球四散外溢。
其次,遭受严厉打击的恐怖组织往往会“化整为零”潜伏下来,等待适当时机试图“东山再起”。2018年8月23日,“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突然对外发声,指出“虽然目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地区受损,但不必因此而担心。追随者们应当继续接受‘恐惧和饥饿’的考验。会有‘好消息’给那些‘耐心坚持’的人们”。[2]无独有偶,“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亦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号召“所有的极端分子团结一致打‘圣战’”。[3]
见笑啦,这一墙的鬼画符,嘿嘿,业余爱好而已。我觉得,方言一头系着历史,一头连通民间,凡俗中有高雅,平易时却生动。从上殿说起吧。我父亲原先有一阵子对“牵猪牯”蛮投入,乐此不疲的,一有活干,他就美滋滋吆喝一声:上殿喽!上殿当然是庄严的事,他蛮讲究,热天白衬衣藏青长裤子,再热,袖口领口都扣得紧紧的,其他季节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管钢笔,很粗硕的那种,露出黑黑的半个大头,特别显眼。哦,他最重视梳头,一旦有头发翘起,就叫我奶奶帮他抹把菜油。
(二)打击模式的不足
传统的反恐怖模式在应对当代恐怖主义时显得尤为“捉襟见肘”。
推荐理由:古希腊人的历史是世界史中最不可能成功的成功史,希腊文明是一个奇迹。希腊奇迹的产生有着厚实的观念基础,希腊人先于其他古老民族抢占第一个科学制高点,是在认识论领域,而不是像许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在自然哲学领域。浸淫希腊古典学问三十年、两度翻译荷马史诗的陈中梅先生,深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探索希腊奇迹成因。
首先,恐怖组织与个体恐怖分子活跃于“幽暗之处”,而当代科学技术更使得恐怖主义“如虎添翼”。暗网技术、无人机技术、核技术与生化技术提升了恐怖主义的反侦察能力、抗击打能力与攻击能力。本处于被动状态的反恐怖力量极易逾越权力边界,试图以无节制的克减自由作为代价来换取安全与和平,从而更有可能陷入恐怖组织“行动—镇压—反抗”的陷阱中。
埃及的集体去极端化的成功之处在于,“伊斯兰团”与“圣战组织”自1997年开始就再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的记录,并且还积极加入到批判恐怖主义的行列中去。
再次,“硬式”反恐怖容易促使政策制定者忽略恐怖主义背后的社会根源,放弃对治本策略的探索。恐怖活动频繁的地区,往往是社会矛盾较为集中的区域,存在诸如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秩序动荡、国家治理能力欠佳以及政府供应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等社会问题。反恐怖工作应当着重从综合治理角度出发改善社会土壤,清除利于恐怖主义“病菌”滋生的社会条件。“重打击、轻治理”往往难以使得反恐怖政策获得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反而会成为恐怖组织宣扬极端主义的素材和事例。
在完成宗教对话之后,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组织的共364名极端分子获得释放。为了获得释放,被关押的极端分子要与政府达成一项协议,表明自己已经放弃了极端思想。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求极端分子的家庭或部落成员为他们提供担保,也就是要对于他们释放后的所作所为负责。极端分子在释放以后,还要接受政府当局为期一年的监督。[13]
综上所述,子宫颈癌外科手术经历了130年的发展历程,手术路径经历了经腹、经阴道,开腹、微创手术,输尿管内侧入路、外侧入路,根治性子宫切除、根治性子宫颈切除,传统根治术、保留神经手术等历史变迁和进化。相信随着材料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临床医生的不断努力,未来微创手术会使得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
二、“柔性”反恐怖模式与去极端化
相较于传统的“硬式”反恐怖策略,“柔性”反恐怖策略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建立在对恐怖主义罪因机理的正确认知基础上,“柔性”反恐怖策略主张运用社会、法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的综合方法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柔性”反恐怖策略并非一味反对打击模式,必要的制裁能够成为预防的坚实“后盾”,惩罚可以为治理争取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柔性”反恐怖策略坚持理性的犯罪观念,试图统筹协调打击与预防、治标与治本之间的关系,实现对“硬式”反恐怖策略的补充和完善。
“柔性”反恐怖策略的核心是“去极端化”,支柱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其一,一般预防是指通过综合手段强化社会一般公众对极端主义的免疫能力,特别是避免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潜在“危险分子”逐步激进化,从而在社会与极端势力之间树立一道“防火墙”。其二,特殊预防是指在监狱或社区内,通过干预措施或者矫治手段,促使已经激进化的个体(包含初步具有极端化倾向的人以及在极端主义思想支配下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摒弃错误的观念,改过自新,并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重新成为遵纪守法的正常公民。其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功能具备互补性。充分发挥一般预防的功能,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个人激进化现象,最大范围减少恐怖主义犯罪与极端主义犯罪的数量,有助于集中精力开展罪犯矫治工作。充分发挥特殊预防的功能,一方面能将改造好的人员作为典型起到示范效应,敦促恐怖分子尽快自首,脱离极端场域;另一方面通过对极端化个体的分析研究,了解其激进化的过程与原因,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一般预防政策奠定理论基石。
5037 陈 燕,华 山 “沉浸式”对外汉语项目现状和存在问题———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爱丽丝国际语言学校为
以预防为主旨的去极端化需要深入到恐怖分子的思想观念体系之中,打一场“头脑和心灵的战争”。首先,去极端化的主体包括政府与社会两个部分。去极端化工作主要由政府负责。政府扮演着去极端化的制定者、实施者、推动者、支持者和指导者等角色。去极端化工程浩大,单纯依靠政府难以完成。社会在政府的推动、指导和支持下开展预防工作,深入参与到去极端化的行动中去,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其次,去极端化的客体包括已经被审判、监禁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具有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的高度危险的人。再次,去极端化的措施包括专业知识再教育、心理辅导、咨询,以及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工作。最后,去极端化的目标是通过运用上述手段促使被极端主义思想左右的人彻底放弃他们头脑中暴力、偏执、激进的理念,让他们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变化应当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来促成这一转变,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价值的文化语境之中。就去极端化的本质而言,坚持去极端化意味着当局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成功的反恐怖策略不应将终极目标定位于消灭所有恐怖分子的肉体,而是要尽可能确保恐怖分子可以认真倾听法律的感召,重塑他们对法律的忠诚感和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反恐怖活动中的去极端化,汲取了犯罪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一,虽然犯罪学领域更为关注普通刑事罪犯,但是在“将被矫治者改造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作为犯罪对策的目标之一”方面,针对普通刑事犯罪人的矫治工作与针对恐怖分子的去极端化并没有什么不同。“去极端化与犯罪矫治的共同点都是对那些背离了社会一般规则的人实施‘再参与’‘再教育’以及‘再融入’。”[5]其二,与去极端化更为相似的,是针对有组织犯罪开展刑事处遇措施而发展起来的犯罪学理论。例如,为了促使犯罪帮派、极右翼政治组织和普通犯罪组织的成员成功脱离出来,需要强化“推”和“拉”的因素。前者是指通过破坏组织结构、扰乱组织秩序、颠覆组织文化等方式来降低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力;后者是指通过为成员脱离组织提供物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刺激和动因来增强个体放弃组织成员身份的可能性。这样的犯罪学理论同样适用于针对恐怖组织成员的去极端化的行动。
去极端化的目标可分为“放弃极端思想”与“脱离恐怖组织”。前者是指极端分子的思想由极端转为温和的过程:承诺并且信守诺言不再参与或从事暴力活动,以致于暴力极端化明显被减弱。后者是指简单地改变极端分子的行为的过程:不再参加恐怖组织或者从事恐怖活动,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必然放弃了极端思想。脱离恐怖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极端主义思想,前者并非后者的充分条件。单纯的脱离可能是物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强迫的。真正的去极端化应当触及恐怖分子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改变其行为方式。一方面,个人参与恐怖活动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从仅为恐怖活动的正当性辩护到实际参与恐怖袭击的不同情况。同理,不同人对极端主义思想信仰的程度也可能存在从零(毫不信奉)到一百(坚定信仰)不同的等级情况。这说明矫治过程具有复杂性,但并不意味着矫治计划应该放弃治愈人的灵魂的终极目标去退而求其次追求避免人再次实施某种行为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恐怖分子脱离恐怖主义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或者由于政府日益严厉的制裁性反恐措施,或者由于国家加强了对退出者的物质奖励,或者社会一般公众基于某件恐怖袭击的严厉声讨,等等。但是,恐怖分子的“脱离”带有暂时性与条件性,一旦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推”和“拉”的因素效力减弱),那么退出者依然可能“重出江湖”、重操旧业。因此,惟有极端分子经过理性思考和利弊权衡之后决定放弃暴力极端思想、重新确立其对法律的忠诚,才能保证其彻底远离恐怖主义。
总之,去极端化的核心在于改变信念以重塑行为。
根据检查结果诊断为咽颊炎链球菌性脑膜炎,给予对症治疗。头孢曲松(罗氏芬)2 g,每日1次静脉滴注,共15 d。20%甘露醇125 mL,每12 h 1次静点;氨酚羟考酮片330 mg,每6小时口服1次;氯化钾缓释片0.5 g日3次餐后口服。用药第7天脑膜刺激征消失,但仍自诉头痛,颞部为主。用药2周后复查腰穿。压力160 mmH2O,脑脊液生化蛋白387.8 mg/dL。葡萄糖及氯化物正常,脑脊液常规:无色,透明,不自凝,细胞数8×106/L,潘氏试验阴性。外周血T细胞亚群正常。2018年3月30日患者出院,头痛症状完全缓解,脑膜刺激症消失。出院后未再次就诊。
三、沙特、也门与埃及的去极端化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也门与埃及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反恐怖主义实践经验,特别是在伊斯兰去极端化方面效果显著,值得我国借鉴。
目前,很多中小学班主任主要依靠学校来任命,但是在班主任上任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培训,导致班主任的发展能力不足。部分学校虽然组织了班主任培训工作,但是由于方法单一等因素,导致培训的效果比较差。在培训的过程中没有主动地转变班级管理的理念,表现在过分地强调常规管理,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等关注度不够。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导致班主任的个人能力原地踏步,难以满足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一)沙特
为遏制“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对沙特国家安全造成的持续性威胁,2003年起,沙特制定了一项去极端化制度,名为“预防、矫正和善后关爱”(Prevention,Pehabilitation,and After-Care),简称“PRAC”战略。[6]
1.预防。预防的指导思想是为社会提供温和版本的伊斯兰教义,帮助社会了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引导社会远离极端主义。
(1)批驳极端势力的激进意识形态。其一,内政部设立宣传指导部门,聘请教职人员和学者,阐释正确教义,批驳极端言论。其二,文化信息部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介向社会开展宣传活动。
(2)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沙特的青少年激进化问题严重,引发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关切。其一,政府联合教育机构,在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国家安全与反恐怖宣传活动。其二,强化对教师队伍的监督,对于利用教师身份在校园内传播极端思想的人施以严厉制裁。其三,为避免青少年在校外接触极端文化,政府为年轻人建立娱乐、休闲和社交场所。其四,密切关注舆情,建立政府与社会沟通渠道,及时回应社会群体的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上述问题都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和方式予以应对。
(3)斩断极端主义的渗透渠道。其一,加强对宗教机构的监管,严厉查处宣扬极端主义的教职人员。其二,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增强对含有煽动、宣扬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的查堵力度。其三,指导和帮助社会团体建立专门的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网站。
最后,为了生存的恐怖组织会根据打击策略的重点进行调整。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国”为了适应反恐怖压力做出了诸多变化。其一,将战略中心从中东地区向南亚、东南亚转移,试图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建立第二个“国家”。其二,加强与全球重要恐怖组织的联合,甚至包括以前存在竞争关系的“基地”组织。2018年11月7日,俄罗斯情报部门指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不仅采用相同的渠道、方式来获取资源、补给和进行招募活动,还使用各自成员为对方行动部队补充人手。[4]其三,在组织结构上强调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通过赋予分支机构、恐怖小组与个人更大的攻击权限,以加强恐怖袭击的不可预测性。其四,在攻击模式上,鼓励运用简易爆炸装置、汽车碾压碰撞以及无人机等方式实施恐怖活动。
埃及的集体去极端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独立的调解委员会主导,内政部提供一定的支持。该委员会主要由温和穆斯林中的教职人员、前穆兄会成员、律师和学者构成。委员会与被监禁的极端组织领导人展开对话,要求领导人说服组织成员放弃暴力恐怖活动,条件是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组织成员、改进狱政条件、结束无限期羁押、释放组织成员的家属、取消酷刑以及重新开放从事宣教的清真寺,等等。但是,第一阶段的去极端化终以失败告终,一方面是由于调解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多数恐怖分子的质疑,另一方面是恐怖组织内部的领导人对于是否放弃武力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997年卢克索大屠杀事件和2001年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埃及民众对恐怖主义开始愈加厌恶,而“伊斯兰团”和“圣战组织”在长期与政府的武力对抗中已筋疲力尽。1997年7月,在监狱服刑的“伊斯兰团”领导人首先发布了一份单方、无条件和永久放弃暴力的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埃及政府确认极端组织领导人放弃使用暴力、走温和穆斯林之路的愿望是真诚的,从而重新开启了去极端化的行动。这是集体去极端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埃及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包括:为监狱服刑的极端分子提供不同宗教观点的书籍,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义;改善服刑人员的待遇,逐步取消对服刑人员探监的限制,以鼓励他们主动放弃极端思想;鼓励领导人解散武装力量;允许监狱内部的领导人同其他服刑的普通极端分子见面,允许“伊斯兰团”的其他领导人参观有该组织成员服刑的监狱,以帮助领导人劝说服刑人员改过自新;允许一些组织的领导人出版批判极端思想的书籍。例如,2002年“伊斯兰团”的领导人在出版的书籍中指出,杀害普通市民、游客与安全人员的做法是错误的,针对不遵守“沙利亚法”的穆斯林使用暴力是错误的,伊斯兰教是禁止“圣战”的。2008年,“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公开出版《揭开扎瓦西里的骗局》一书,从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方面论证了应当放弃暴力和“圣战”的理由,并强烈批评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与战略。[17]
3.善后关爱。沙特政府为被释放的极端分子提供的帮助包括就业机会、经济资助,甚至小汽车和住房等。沙特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既可能是私营部门也可能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沙特政府认为,鼓励被释放的极端分子接受政府部门提供的职位很重要,因为这些人以前认为政府是“不合法”的,现在他们接受了政府的职位,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极端思想。[10]
(二)也门
在2000年美国驱逐舰爆炸案与2002年法国油轮受袭案发生之后,也门政府逮捕了很多也门国籍的恐怖嫌疑犯。2002年,也门政府制定了一项宗教对话项目,用以矫治这些服刑人员。这项宗教对话项目构成了也门反恐怖战略的核心部分。执行该计划的组织是由也门前法官哈穆德·希塔领导、由5名宗教教职人员组成的宗教对话委员会。该矫治项目建立在一个核心理念的基础之上:政治性的屠杀平民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能够证明恐怖主义的核心原则是错误的,那么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削弱恐怖主义的支持基础。[11]
对话方式有两种:直接对话与间接对话。前者是进行口头辩论,后者是进行书面辩论。对话规则强调在对话过程中要相互尊重。哈穆德·希塔指出,大部分的极端分子都是一些被欺骗的普通人,如果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诚布公地讨论,是有可能弃恶从善的。宗教对话委员会与被关押的极端分子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讨论:(1)也门是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是不是根本上反对穆斯林利益的?(2)也门缔结国际条约的行为是否违反伊斯兰教法?(3)也门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民选总统是否违反《古兰经》的规定?(4)杀害非穆斯林是否具有合法性?[12]
最后,由“伊斯兰国”碎片化和外溢引发的外国武装战斗人员的回流问题日趋严重。对于这些具有本国国籍且在本国潜伏下来的危险分子而言,传统的战争模式难以适用,单纯的刑事司法模式亦难以缓解恐怖主义的威胁。
从临床用药安全监测网上报的内容看,构成用药错误的因素由用量、品种、给药频次、数量、给药途径、溶媒、适应证、规格、配伍、禁忌证、重复给药、给药时间、遗漏给药、剂型、患者身份、相互作用、疗程、给药技术、给药顺序及其他(共20项)构成,从药品的调剂过程看,用药错误由涉及接触到药品的人员、设备、环境、制度、工作量等原因构成。
(三)埃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去极端化历程。在1997年至2007年间,埃及最大的两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团”和“圣战组织”先后宣布放弃暴力。与以往尝试令个人脱离极端主义的方式和路径不同,埃及的去极端化是有组织地去极端化,即促使极端组织集体放弃武力,被称为“集体去极端化”。
埃及的集体去极端化借鉴了以往同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斗争的经验。[14]但是“伊斯兰团”与“圣战组织”同穆兄会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并不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同时也不反对民主选举制度;前两个组织则更加暴力,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更加激进和极端,均号召运用武力方式建立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15]仅20世纪90年代,上述组织策划、实施的暴恐活动共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因此,对“伊斯兰团”与“圣战组织”进行去极端化的难度远高于穆兄会。
“伊斯兰团”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认为穆兄会过于软弱,从而开始用更加激进、暴力的方式解读萨义德·库特卜的作品,从而产生了“塔克菲主义”。自70年代始,“伊斯兰团”频繁发动暴力袭击,如1981年实施了暗杀总统萨达特行动,1989年至1997年针对埃及政府、外国游客和埃及的知识分子采取暗杀、爆炸、投毒等恐怖行为。“圣战组织”则是在1982年至1983年间从“伊斯兰团”中分裂出去的一个新组织,原因在于同“伊斯兰团”存在意识形态和战术上的分歧。例如,“伊斯兰团”更倾向于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开宣教来发动群众,暴力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圣战组织”更具有秘密性特征,宣称实现政治变革的方法惟有依靠暴力军事行动。1996年以后,“圣战组织”进一步分裂,其领导人之一扎瓦西里宣布加入“基地”组织,成为仅次于本·拉登的二号人物。[16]
2.矫治。沙特实施的矫正计划的目标是,使正在服刑的极端分子能彻底放弃极端思想与极端行为,重塑身份认同,融入主流社会。[7]2004年,沙特内政部设立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矫正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作。咨询委员会具体由四个分会组成,它们是宗教分会、心理与社会分会、安全分会与媒体分会。[8]咨询计划是矫正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典型特征是与计划参与者(被监禁的极端分子)进行宗教讨论和辩论,使其改变错误的世界观,另外还为他们提供广泛的社会帮助、心理辅导等。矫正计划还包括心理辅导咨询、职业培训、艺术治疗、体育运动等内容,关注被关押者思想的改变、自尊的培养,医治个人心理创伤,帮助犯人释放后更好地融入社会。[9]沙特当局要求,服刑的极端分子通过矫正获得释放的条件是,他必须真诚地放弃暴力和“圣战”信仰,并且要让参与矫正计划的工作人员相信,他在释放以后不会再走上武装暴力的道路。服刑的极端分子获释后,要定期到政府有关部门报到,要继续在监禁期间与其对话的学者见面。
2)重视项目化的过程考核。传统的高职大学英语课堂上,学生普遍认为只要期末根据教师所给定的复习重点临时抱抱佛脚,就能应付期末考试。而对于英语学习来说,在期末英语考试中,考试内容只有一小部分的听力考试,其余都是笔试,不能全面反映学生在一个学期内的学习成果。因此,在英语考试方面应当增加考试内容,将学习的过程纳入英语期末考评中,增加其占考评的比重。在核心素养培养下的英语课程考核应当包括对学生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方面的考核。
其次,“打击至上”的反恐怖模式忽视了恐怖分子个体罪因的形成机理,容易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恐怖分子的产生与其内心的紧张感有关,暴力不过是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纾解紧张感、压力感而被迫选择的一种释放方式。很多时候,遏制恐怖主义应当从“如何化解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紧张感”的角度入手,而不是滑向“挫折—攻击”的暴力循环模式的窠臼之中。
总结新闻内容:新闻标题往往是读者获取信息的捷径,这就要要求新闻必须要恰当的总结新闻内容,而不能仅为吸引眼球胡写乱写,扭曲事实。新闻标题中出现的内容应与新闻内容匹配,标题中的观点需在文内被论证。新闻标题要用精炼易懂的语言写出一篇报道中最有价值,读者最想知道的部分。
四、域外去极端化的启示
(一)反恐的总体策略应坚持“刚柔并济”
如上所述,“打击至上”的反恐怖模式难以实现对恐怖主义的根本遏制,但也不能认为,消灭恐怖主义应当放弃武力的方式。“柔性”反恐与“硬性”反恐并非对立关系,坚持“柔性”反恐怖策略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硬式”反恐怖手段;相反,“柔性”反恐怖策略的贯彻施行必须以严厉打击恐怖主义为前提。故而,绝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而放弃基本原则和立场,对恐怖分子过分妥协、退让。一个科学、合理的反恐怖方案必须调和“柔性”与“硬性”、打击与治理、治标与治本手段之间的比例,做到“刚柔并济”和“标本兼治”。
具体言之,通过严厉打击和镇压的方式戳破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妄图利用暴力和恐吓来实现政治目的的“美梦”,促使他们主动提出放弃暴力的倡议。同时,还应当辅以去极端化的方式来帮助可改造者顺利完成改造,特别是要鼓励恐怖组织的领导者“回头是岸”,以带动组织内部其他成员主动放弃暴力方式和极端思想。
(二)改造罪犯应重视教育和挽救
在反恐工作中,绝不能因为“恐怖分子不好改造、难以改造”而放弃对此类服刑人员的矫治工作,进而一味采取消极、隔离的方式来控制其再犯罪的可能,特别是要严格慎用“终身监禁”的方式断绝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期望。首先,放弃对服刑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改造,有损国家的正义形象。国家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国家对本国公民负有保护权利、保障自由以及促进全面发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绝对不可推卸的。放弃对公民基本义务的做法容易给敌对势力的言论攻击提供借口。其次,放弃对服刑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改造,既不利于促使他们改过自新,也会给羁押机构带来过度压力。特别是,我国《刑法》为极端主义犯罪配置的刑罚一般较轻,实施了该类犯罪的人员终究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如果缺少相应的处遇措施,一则无法实现对此类人员的特殊预防,还有可能导致其在监狱内部发生交叉感染,进而发生思想上的“病情恶化”。最后,放弃对服刑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改造,不利于实现恐怖主义的一般预防,不利于通过改造好的“模范人物”所产生的示范效应,鼓励社会上潜在的危险分子放弃极端思想和行为。
在教育改造涉恐怖主义犯罪、涉极端主义犯罪的服刑人员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加强针对服刑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应当给服刑人员普及必要的文化知识、民族知识、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出于分裂国家的目的,散布大量错误言论和信息,例如为了鼓吹“新疆独立”宣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否认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如,为了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宣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否认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又如,为了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攻击政府,宣称“共产党和政府压迫我们的民族”,等等。绝大多数的服刑人员就是在这些错误、荒谬的信息、言论诱导下产生实施犯罪念头的,因此,必须针对这些业已形成的错误思想进行针对性的纠正。其二,加强针对服刑人员的心理干预。针对恐怖分子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恐怖分子都是心理正常的普通人,因患有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而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比较罕见。但是,大量的恐怖分子是在仇恨、愤怒的动机支配下实施恐怖活动的。“残酷社会现实、艰难的生存环境,或者家庭、亲友的不幸遭遇都会使个体形成一种对敌人势不两立的仇恨认知,进而迸发出迫切报复的愿望。”[18]因此,在针对服刑人员的矫治中,应突出对此类具有仇恨动机的人员的心理化解辅导。另外,在长期单调、枯燥的服刑生活中,服刑人员极有可能形成孤僻、绝望、愤恨、抱怨等心理,也需要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予以正确地引导。
(三)主体构成应倡导政府与社会共治
去极端化如果要深入人的内心,就必然需要细致、全面的工作,特别是要避免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除了必要的监督外,还要为其提供可替代的新生活方式作为选择。
恐怖分子一般具有强烈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源于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严重断裂在其内心的投射。申言之,只有在所追求的物质或精神目标缺乏现实的可以尝试的手段,并将这种窘迫归结于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才能将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内化为主体真实的信奉,并作为指导其暴力行径的惟一、神圣的指南。因此,去极端化不仅需要颠覆那些荒谬的既有观念,还需要弥合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异,重新搭建起通往人生幸福与自由的桥梁。监狱内的矫治工作只是去极端化的必要条件,而刑释后的“善待”才是完成去极端化的关键。例如,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居住条件、继续教育的机会、技能培训和必要的创业资金等。
每个民族大体上属于各自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态、军事军情、民俗风情、生活习惯都会在语言中有所表现。这种表现无不被民族文化所包含,形成各种类别的文化现象,比如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而当这些文化用语言进行表达时,经过翻译这一工具来置换,就出现了跨文化交际中词汇的盲区、多义、误解,甚至是由于延伸词意的不同带来麻烦。所以说,商务英语仅仅是专业英语的范畴,也不是掌握了专门的词汇和技巧就可以得心应手的,必须要和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通盘考量。否则,不但影响了翻译内容的偏差,而且失去了作为商务英语的独特作用。
当然,细致、全面的去极端化工作必然是任务繁重、成本巨大的,是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完成的。因此,必须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到去极端化的行动中去。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沙特的经验,建立一些诸如“服刑人员及其家庭帮扶委员会”“服刑人员保护委员会”“家庭调解委员会”等的社会组织,鼓励志愿者参与到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安置工作中,为上述人员的再融入社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后茬玉米播种前,处理T5、T6土壤碱解氮含量显著高于处理 T3,处理 T4、T5、T6 之间差异不显著,处理T4显著高于处理 T1、T2,处理 T4、T3之间差异不显著。其中处理 T6、T5、T4、T3 土壤碱解氮含量相较于前茬收获后分别增加 36.38%、34.64%、26.33%、8.40%,处理T1、T2土壤碱解氮含量比前茬收获后分别增加2.81%、2.05%。数据表明,试验小区经半年的休养其土壤碱解氮含量都有所增加,其中含有沼肥处理的小区土壤碱解氮含量增加显著,并且施加沼肥比例越高的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增加越多。
(四)目标选择应强调去极端化和反极端化并重
除了对特定的恐怖分子和危险分子的去极端化以外,还需要针对极端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根本性的反极端化,例如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为公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极端主义是一种理念范畴,反极端主义就应当做到“针锋相对”的“文化对冲”,在意识形态领域给予极端主义以“致命一击”。我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在特定地区更加强调和关注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问题。然而,是否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平与是否会受到极端主义的蛊惑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在校学生施恐制暴或出境参加“圣战”的案例。从理论上分析,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甚至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依然具有受到极端主义蛊惑的可能性,这与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宗教知识有关,同其能否运用文化知识来正确阐释自己或者同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处境有关。
首先,缺少相应的宗教文化知识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蛊惑。例如,我国当前在少数地区出现的“泛清真化现象”,多数人是在对宗教充满热情但又对教义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盲目跟从了别有用心者。再如,埃及的“伊斯兰团”中大量高层领导人均为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大多修习理工类专业,对于伊斯兰教的知识并无过多了解,才容易为激进思想所俘获。因此,必须加强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工作,特别是要大力培育温和穆斯林的力量,使广大信教群众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避免偏听偏信、偏执和激进。
其次,极端主义者在宣教过程中往往会注意将“事例”(例如本国或全球穆斯林“受歧视”现象)与“理论”(只有通过“圣战”才能保护本国或全球的穆斯林)结合,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现实中,一些有文化信仰的人因为人生经历而感到苦闷、压抑,尝试寻求通过价值观念引导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口,因此,也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的挑唆。必须承认,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缺陷有关。知识包括工具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而我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更加关注工具性知识的灌输,在价值性知识的教育方面存在观念陈旧、方式单一、方法老套的问题,难以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某些人如果不能从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就自然容易向“似乎更有说服力”的极端主义势力靠近。
对此的解决办法是,要加强对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解释和教育工作,使理论更具有实用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为此,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做形式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例如不能以“是否会背诵十二个词语”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准。重点应在于受教育者是否能够正确解读这些词语的含义,能否运用这些词语所蕴涵的理念来解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再如,不应将“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19]民主也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即“允许你说,也允许我说”。坚持民主的理念,就能够有效地反对极端主义“只能听我的,其他都是妄言”的错误观念。又如,法治的基本蕴涵是要将遵从法律规范的外部要求内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准则。基于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想,每一个公民均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负有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义务、职责,而在法治社会,这种义务和职责依据法律规范的形式展示出来。因此,生存在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无论是否信教,无论信仰哪种宗教,都应当将服从法律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第一准则。坚持法治的思想,能够有效反对极端主义提出的“教法高于国法”的荒谬论调。
参考文献:
[1]Rohan Gunaratna,Jolene Jerard and Lawrence Rubin.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and Conuter-Radicalis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2011:1.
[2]巴格达迪近一年来首次“现声”:IS的损失是真主的考验[EB/OL].(2018-08-23)[2018-11-20].反恐怖主义信息网,http://cati.nwupl.edu.cn/fkzx/wpzb/2018/08/23/20101429869.html.
[3]“基地”再发视频,扎瓦希里时隔一年多现身[EB/OL].(2018-08-25)[2018-11-20].反恐怖主义信息网,http://cati.nwupl.edu.cn/fkzx/wpzb/2018/08/25/21215729898.html.
[4]俄安全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有联合活动迹象[EB/OL].(2018-11-08)[2018-11-20].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11/08/c_129988947.htm.
[5]Rohan Gunarata, Jolene Jerard and Lawrence Pubin. 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sation: New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3.
[6]John Hogan and Kurt Braddock. Rehabiliting the terrorists: Challeges i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es[J].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0(22).
[7]同[6].
[8]Christopher Boucek. Saudi Arabia’s “Soft”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nd Aftercare[J]. Carnegie Papers, 2008(97).
[9]Abdulrahman al-Hadlaq. 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the Saudi Experience. in Rohan Gunaratna, Jolene Jerard and Lawrence Rubin. 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sation: New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64-65.
[10]Sonia Verma. terrorists “Cured” with Cash, Cars, and Counseling: Controversial Saudi Rehab Program Aims to Reform Jihadists Returning from U.S. Prisons[J]. The Golbe and Mail, 2008(11).
[11]同[6].
[12]Rohan Gunaratna, Jolene Jerard and Lawrence Rubin. Terrorist Rehabilit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sation: New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111-117.
[13]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De-Radicalization Initiatives and Identify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S.-Based Initiatives in Multiple Settings[EB/OL]. (2009-09-01)[2018-12-10]. START, www.start.umd.edu.
[14]Hamed El-Said and Jane Harrigan. Deradicalizing Violent Extremists:Counter-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me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M].New York:Routledge,2013:76.
[15]Hamed El-Said and Jane Harrigan. Deradicalizing Violent Extremists:Counter-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me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M].New York:Routledge,2013:78-80.
[16]Hamed Ei-Said. Programme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J]. Developments in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2012(1).
[17]同[16].
[18]兰迪.恐怖主义个体罪因[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5).
[19]张景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综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6.
中图分类号: D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40(2019)02-0085-08
收稿日期: 2018-12-18
作者简介: 兰迪,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反恐怖法学、犯罪学、中国刑法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去极端化视域下的‘柔性’反恐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CFX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 鹏)
标签:“柔性”反恐怖策略论文; 伊斯兰去极端化论文; 恐怖主义犯罪论文; 沙特论文; 也门论文; 埃及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