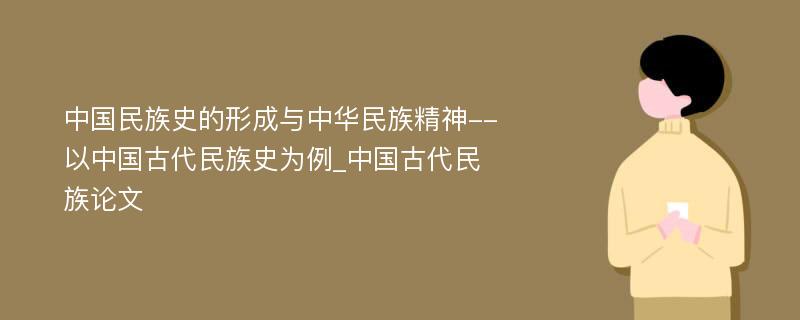
中国民族史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以中国古代民族史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为例论文,中华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1-0117-05
一、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与中国人的爱国传统
“中华民族”的称谓,始见于清末民初,其是在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日重、民族危机渐深的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现的中国务民族的总称;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自觉凝聚、自觉区别于外国人而自然形成的共同称谓。
中华民族前身的融合和统一之历史非常久远,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在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前身的多元与融合,就已经露出端倪。距今六七千年前,我国众多的原始人群,创造了许多新石器文化,既各有特征、独立存在,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例如,在辽宁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玉龙饰物出土,有圆形和方形祭坛出现,这说明,东北夷的先民早已接受了中原华夏族先民的龙的观念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是夏朝,接下来是殷商和周朝,夏人居伊、洛,殷人居河,周人居岐、澧,都在黄河流域。其周围还有淮夷、于夷、方夷、人方、土方、羌方、戎方、荆蛮等交错而居。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一些少数部族的名字消失了,融入到夏人、殷人、周人为主体的族群中,统称为华夏族。所以华夏族从一开始便包含多民族的血统和多民族的文化。到了汉代,原来的华夏族居住的范围更广大了,与周围族群交流、融合的机会更多,这就形成了更大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华夏族改称汉族,虽不是民族共同体本质的改变,但标志着它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包含了更多的民族血统和更丰富的民族文比。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现象,是持续不断的和大量的。
在少数民族不断融入汉族的同时,也有很多汉族人融入到不同的少数民族中。以蒙古族为例,蒙古在攻金、宋时,俘掠汉人众多。成吉思汗攻金,一次就强迁河北10余万户到漠北,有一技之长者,从事手工业劳动,多数人则从事畜牧业。道士丘处机曾在漠北看到“汉匠千百人居之”,“燕京童男女及工匠万人居作”[1]。南宋人徐霆也在漠北看到,当地牧奴之中,“汉人居其七”[2]。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族势力衰落之后,特别是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明朝政治腐败,沿边大批汉族兵民为逃避明朝压迫,纷纷逃往蒙古地区。到万历初年,逃到土默特地区的汉人已达十多万。[3]这些自愿投顺的汉人,得到了俺答汗的善待,分得了牛羊、帐篷和耕地。这种类型的汉人,后来都逐渐蒙古化了。在其他民族之间,这种民族成分的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正因为各民族间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少数民族从不自外,不少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如拓跋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不少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国号也都采用历史上华夏族—汉族的国号,例如在十六国时期,匈奴刘渊在汾水流域称帝,国号汉。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自称为夏后氏之苗裔,称大夏王,国号大夏。羯人石勒建赵国,都襄国,史称后赵。鲜卑慕容皝自称燕王;其子慕容俊进而称帝,并说自己称帝是“为中国所推”[4],等等。
如果说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沿袭中原王朝的国号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那么众多少数民族政权都争相采用中原王朝旧有的国号,就一定具有一种普遍的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众多的少数民族都对中国历史有强烈的自觉的认同感。这种历史认同,在元代由蒙古族丞相脱脱监修,由汉、唐兀、畏兀儿等各族史学家共同编修的《辽史》、《宋史》、《金史》中进一步得到体现,首次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不同地区建立的对立王朝列于平等的历史地位,把汉族、契丹族、女真族的历史都作为我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辽史》、《宋史》、《金史》一视同仁地作为中国的正史。这一原则得到广大汉族的肯定,一直延续下来,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后来明人为其修《元史》,亦为正史。
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具有的这种历史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它导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所以当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我国各民族才做到了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誓死反抗。
二、关于民族交往中的共同进步与团结互助精神
自古至今,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各自都深受益处。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各族的交往是最多的,真正形成了互相不可分离的关系。汉代,匈奴通过和亲、“赏赐”、互市等方式,从汉地得到了铜器、铁器、陶器、缯絮、金银,以及其他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被掠和自动流亡到匈奴的汉人,又为匈奴输入了种田、凿井、筑城、打造兵器等先进的技术。北方游牧民族的折叠坐榻,在东汉时期传入了中原,被称为胡床。胡床的使用,又导致高腿家具的产生,使汉族一向席地而坐的习俗也改变了。此后,胡桃、胡萝卜、胡豆、胡麻等,也相继传入中原。唐代,唐与突厥在受降城互市,唐输出缣帛,突厥输出马。唐将这些戎马助军旅,并作为种马,国马得到改良,“由是国马益壮焉”[5]。唐朝的汉族工匠,还把纺织、刺绣、酿酒、制碾硙、制纸墨、平整土地、除杂草、水力碾磨等技术,传播到了吐蕃。
在经济技术的交流中,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契丹、女真二族,原来都是比较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到后来,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都发达了,社会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在经济技术交流中,汉族的社会进步虽没有发生质的变革,但社会生活却变得精彩起来,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众所周知,与我们生活最为密切的种棉纺织技术,是在宋元之际,一路由海南黎族传入长江流域,一路由新疆维吾尔族传入陕西;而制作毛毡毛毯的技术,是在元代经蒙古等北方民族传入的;西瓜的种植,是从回鹘传入契丹,又从契丹传播至中原;白酒的制作技术,是元代色目人传入的。火炕、火锅、饺子、煎饼等常用的设备和食品,也是由北方民族传入的。这些品种和技术的输入,使人们永远受益。
通过文化领域的交流,各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高,精神生活丰富了。文化的认同,更拉近了各民族的距离,密切了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原来多没有文字,对外交往只能使用汉字,族内记事也只能结绳刻木或代代口头相传,极为不便。而通过民族交往中的文化借鉴,一些民族便创制了能记录本族语言的文字。如契丹族是在汉人的帮助下,借用汉字的某些笔画,创制出表意的契丹小字。蒙古族在成吉思汗时开始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称为回鹘式蒙古文;忽必烈时又令吐蕃人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它是以梵文、藏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而成,俗称“八思巴文”,但并未推广开;元代后期,回鹘式蒙古文渐又通行,并得到进一步规范,成为现在的蒙古文。单从文字的创制过程看,我国不少民族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并且依赖这种密切关系,促进了本民族的文化进步。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很深的。在汉代,匈奴已仿汉例,单于之号都加“若鞮”,即汉语“孝”之意。魏晋南北朝之后,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更是崇尚儒学,重视教育,极力吸收汉族的封建文化和统治权术。北魏拓跋焘更开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祀孔子”的先河。[6]汉族的史书和儒家典籍在少数民族地区广为传播,吐鲁番地区就出土过唐代本的《毛诗》、郑玄注《论语》、《尚书》、《孝经》、《千字文》、《晋史》等。
在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方面,各民族间的交流是很多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十六国时期,接近西域的凉州地区,吸收了天竺和龟兹的许多乐器和乐曲,并与当地汉族音乐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凉州乐,其风格粗犷激昂,受到北方民族的普遍欢迎。西域和北朝的音乐又直接对唐代音乐产生了影响,唐代十部乐中保留了好几部西域乐。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在中原民间也广泛流传。美术方面,西域的晕染法,在唐代也传到了中原。以北朝时的《敕勒歌》、《木兰辞》为开端的歌曲,经过辽、金诸朝北方民族的发展,形成很有特色的北曲,而元曲则是其发展的高峰,并以这些曲调和唱腔为基础,形成了元杂剧。这些都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在政治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紧密团结、相互依赖的事实也是大量的。几乎历朝历代,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有重用外族人士的记录,有的甚至形成几近联合政权的程度。早在汉与匈奴严重对立的时候,汉就以胡人赵信为翕候、前将军;以生于汉地的胡人卫律为出使匈奴的使者。后赵信战败,又被匈奴诱降,单于尊他为“自次王”,极受重用;卫律后来也被匈奴重用,被封为“丁灵王”。从十六国至北朝,其政权基本上是以各族统治者为主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隋、唐的政权中,少数民族官将的数目也不少,唐太宗时,突厥各部首领仅在京任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者就有100余人,差不多占朝廷武官之半数。[7]在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中,后唐政府任职的147名官员中,汉族90人;后晋85名官员中,汉族73人;后汉39名官员中,汉族33人,汉族官员人数反都多于少数民族。[8]
上述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事实,证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是常常要互相依赖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团结互助的。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匈奴单于曾发出“匈奴本与汉为兄弟”的感慨。[9]当汉朝罢撤西域都护时,西域人又有所不舍,“流涕稽首,愿得都护[10]。金代杂居一起的女真与汉人,甚至有“今皆一家”的感觉。[11]一旦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断,各族人民都会努力去修复,甚至采用“以战求和”的极端办法。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多数不是要消灭对方、改朝换代,而只是要求“和亲”、通关市。所以,才有元顺帝死后明廷遣使致祭、蒙古俘虏明英宗后又将他送还等戏剧性的历史镜头。
三、关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人格力量的内化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但他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以顽强的精神,坚韧的毅力,改造生存环境,建设家园,开发边疆,保卫国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令人起敬的是那些被朝廷移民实边的民族先人。他们在更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无畏的拼搏精神及对国家无限忠诚的品质。如清乾隆年间,为保卫新疆伊犁地区不被沙俄吞侵,清廷陆续从各地调遣携眷之满、蒙古、索伦、锡伯等族官兵,到那里屯垦戍边。锡伯族军民率先在伊犁河南岸的荒原上,边挖渠边屯垦,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伊犁地区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东西长200里的人工开凿的大水渠,即察布查尔大渠,并很快开垦了78700多亩荒地,解决了锡伯族的生存和扎根边疆问题。后来,锡伯、满、索伦、达斡尔、蒙古等族官兵,又在伊犁河北岸开凿了一条200里长的“皇渠”,在塔尔巴哈台地方开凿了一条60多里长的阿布德拉大渠,在博尔塔拉地方开凿一条50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在托古斯塔柳地方开凿了一条20多里长的“锡伯渠”[12]。这样,迁徙万里来戍边的锡伯、蒙古、满、索伦等族军民,不仅都建成了安家立业的牢固家园,而且为开拓和发展西北边疆的农田水利贡献了力量。他们还以此为基地,与其他清军一起,浴血奋战,先后平定了英国殖民者支持的张格尔叛乱、阿古柏的侵略、“苏丹汗国”的分裂势力,收复了被沙俄占领十年之久的伊犁。在惨烈的斗争中,有时连屯田官兵也缺少粮食,以至用树皮充饥。他们忍受着千难万苦,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变。仅在反抗“苏丹汗国”分裂的7年斗争中,锡伯族的人口就从2万多减少到1万3千多,约7千余人死于兵燹饥饿之中。[13]驻守边疆的各族人民,为反对分裂势力,反抗外来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各民族杰出人物,更灿若群星,举不胜举。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制定法律,创立文字,还制定了吐蕃历和计量制度,大大地推动了吐蕃的社会进步;推行与唐和好的政策,对促进唐蕃和好关系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采用适应中原地区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制度,使蒙古政权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成为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从而使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数民族完成全国规模统治的朝代,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在这些建立千秋伟业的帝王之外,更多的人们是在自己有限的舞台上,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如,回回人赛典赤,元时任云南行省第一任平章政事,他勤政爱民,在云南“创庙(孔庙)学”多所,发展教育;大置民屯,开垦大量荒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对云南的开发和改善百姓的境遇,多有贡献。赛典赤的后裔郑和,在明初曾率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开辟了中国到红海和东非沿岸的航道,比哥伦布发现新航路早八九十年。他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杰出的先驱者,他的组织才能、胆识和探险精神,令世人景仰。
总之,中华民族历史极为丰厚,有很多宝藏还有待挖掘,有很多营养值得吸收。我们要善于将民族历史的知识内化为人格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繁荣昌盛,以造福各族人民。
〔收稿日期〕2002-02-16
标签:中国古代民族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宋朝论文; 突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