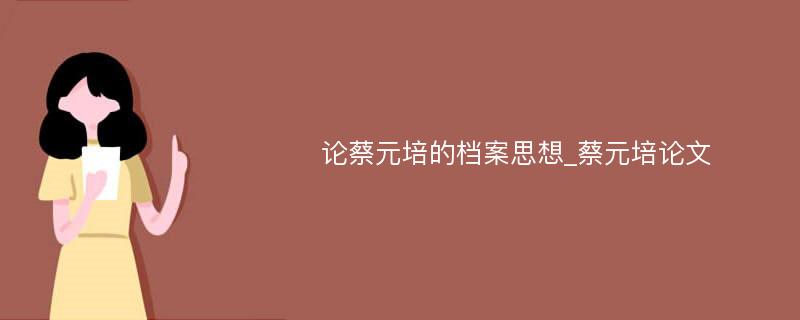
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蔡元培论文,思想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是以“开明正直,笃厚诚挚,博大谦抑”而著称的伟大教育家、杰出的学者。他在文化事业的很多方面卓有远见,对档案的看法也表现出睿智的建设性的眼光。
一
蔡元培先生认为,档案是历史研究最应该珍视的直接材料,“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
我们知道,在唐以前,人们对档案作为史料是不太重视的,到了宋人编纂《唐志》,才于史部设立诏令奏议一类。清人修《明史》,花了很长时间,知道利用《明史纪事本末》,却不曾记起内阁大库所收藏的档案文献。清之后,北洋政府设馆编修清史,也不曾运用故宫收藏的大量公文档案。总之在二十年代以前,档案并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而参与文化学术。针对这种情况,蔡先生表示了对旧史撰修不重视档案、不重视直接材料的不满。他说:“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因为“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而惟有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他以为,“以前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视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是以后治史者所急当纠正的”。譬如民国初年修清史而不充分利用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就是一个很大的失策。他殷切希望能从重视档案入手“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愿望由于他率先领导的档案整理而真正得到了实现。
蔡元培先生主张著史与保档相结合,希望建立大规模专门性质的档案馆。他认为“当时之简”与“勒成删定之书”应予并重,只重视撰修之史,而不重视保管原始材料的做法,就会导致无考稽依据,因而也就“不足垂示”将来。他痛感“吾国史书不可谓少,但其所根据之材料,皆散失不传,无由比照勘对,良为可惜”,这种“轻视史料,无意保存”的陋习自应马上改变。他对“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十分羡慕,认为只有设专门的档案收藏保管机构,“史料与修成之史”才会“有并存共在之可能”。他对成立故宫文献部的热情积极(沈兼士任文献部第一任主任就是尊重先生的意见),足以看出他在促使档案收藏保管专门化方面的努力。
然而,蔡元培先生并不主张凡文皆档或凡档必藏,而是强调进入档案馆的文献必须经过认真的鉴别挑选。他甚至认为历史上的档案之所以散失殆尽,也有“数量太多到无法保存”的缘故。他认为档案馆应是一个科学有序的保藏档案的地方,若仅以“堆积”、“次序凌乱”以致无从翻检,则失去意义。
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档案开放利用的主张。他说整理档案的目的,一则在于更好地保管这些档案原件,二则在于“公布于世,以副众望”,以资学术研究所用。他反对档案秘不示人的传统,也反对少数人或个别机构将档案垄断封锁,而是应该充分向学术开放。他介绍国外的见识,说欧美国家的文件,“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即便颇为敏感的外交档案,“慎重保存”的同时,“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蔡元培先生既有中学的传统根柢,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广泛见识,他所设想的档案机构是一种紧密与学术文化相结合,一种集妥善保管与开放利用为一体的与西方档案馆性质相似的文献机构。事实上,按照他的宗旨办起的故宫文献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一开始便是和学术文化密不可分的。
二
蔡元培先生对档案的重视,以及他在史学上为实现“新体之历史”而力倡注重档案的主张并非徒于口头,而是体现为自身的积极实践和对他人实践的热情肯定。这小可从民国七年,“命秘书处将校中档案完全清出”交陈钟凡整理北大校史得见,大可从呈请历史博物馆部分档案拨归北大整理这件影响甚广的事来看。
1922年初,一面是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出卖档案给纸商,8000麻袋事件正遭到社会各界口诛笔伐,一面是北大国学门成立不久,对近世史料求之不得。蔡元培对出卖档案,“缺乏公共心”的做法严厉斥责,并深感抢救的迫切。当他获悉历史博物馆尚存一部分幸免的档案时,便即刻呈请教育部将这批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他在呈文中高度评价内阁大库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在学界有广泛的利用需求。他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誊黄、报销册、试卷等甚夥,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为快。”蔡元培的呈文深得时任教育次长的陈垣先生理解,因此他的建议获得了“可有裨于史学,且可使该馆所存有问题的历史材料,亦得具有统纪,用意甚善”的评价。但这1502麻袋档案并没有迅速实现转移,而是“经过几翻波折”,且“最后因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奔走,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搬运过来”。可见,先生对这批珍贵档案免遭厄难且能为学界所用功在头筹是毋庸置疑的。
蔡元培先生对这批档案整理的严肃认真也是大家所称道的。当档案陆续运至北大后,他即刻召集了沈兼士、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15位学者讨论整理办法。他指出,对档案的整理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他建议组成档案整理委员会,分两步完成整理工作,即“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
蔡元培先生不仅亲自领导了北大的此次档案整理,而且对在搜集、整理,编纂档案方面辛勤劳动的学者常给予热情鼓励和很高的评价。譬如,他在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作序时,高度赞扬了沈先生对内阁旧档整理编目的功劳,认为该联合目录将原分散各处的内容汇集起来,使原来纷乱的旧档,变得“首尾衔接,粲然可稽”。因而,这种反映档案整理面貌并充当档案公布媒介而“有功史学”的“目录册价值之重”,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又如,他对刘复的《敦煌掇琐》、王弢夫的《清季外交史料》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敦煌掇琐》所汇档案文献为“稀世之宝”,而对“刘半农先生留法四年,于研究语言学的余暇,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敦煌写本和杂文,都抄出来,分类排比”的勤劳,“感激不尽”。对王弢夫有心保存史料,“于中外交涉文件,昕夕纂辑”,将光绪期间朝廷诏令,疆吏廷臣的奏章以及机密廷寄往复文电等悉入《清季外交史料》的“坚苦卓绝,诚有难能”深表钦佩。因为“自辛亥革命前之军机处、总督及外务部各档案大率散佚不全”,王弢夫之前清代外交文件更是“从未有系统之刊行”。所以,他赞其搜集之勤劳,内容之丰富,“必能供给历史家以外交上贵重资料”,而“被国内学界之阙憾”。
三
蔡元培先生重视档案并以利用为其鹄的主张,以及他所领导下率先进行的档案整理实践,对我国近代档案遗产的命运、文科学术风气、档案学术的萌芽甚至第一个现代意义档案馆的诞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蔡元培所领导的由文化单位积极挽救档案灾难的行为,与北洋政府出卖档案形成鲜明对照。北京大学以及他个人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和一批知名学者所表现的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珍爱之心,在社会上有极好的垂范和引导作用,档案之于学术的价值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学者对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愈益重视”。正是因为他领导的这“整理档案的第一年”,开启了我国2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整理历史档案的高潮。正是因为北大及后来故宫文献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文化机构对档案积极努力的整理保护,才使我国现存明清档案得以基本保全下来。蔡元培先生这种文化卫士的先锋楷模作用深为世人所敬仰。
二是蔡元培先生的档案思想和领导的档案整理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学术风气。由于他在国内率先以整理档案接触原料来训练学生“以资实习”的开创性尝试,使“其他考古学风俗学等实地调查之风,同时并起,一洗以前文科徒托空言之弊”。有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国内学术对于这种档案,都抱着一种新的兴趣,所以那时很现出热闹的样子”。胡适、陈垣等人都因此而获得学术上的直接史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一文中也肯定了这种影响,他在引述蔡元培先生有关“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论述之后承认,当时学术界重要而显著的进步就是直接史料的利用,进入了一个“重视档案及积极负起保存与整理档案之责任的时期”,“学术界公私团体和个人”,对于档案“传抄利用不已”以从事“各种有价值的研究”。这种景象与此前档案“三百年来学士大夫不得一窥”和“旧档无用”的观点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三是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档案整理活动引发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的萌芽。在早期,这种理论主要局限于解决整理实践问题的分类方法的探讨。由于北大开始并由此展开的档案整理,吸引了很多学者参与到档案实体整理分类的讨论中来。诸如胡绥之建议蔡元培以编年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分类法,袁同礼建议以美式档案整理法按时期、事件和地区排列次序辅以卡式簿式互注索引的方法,以及三十年代方苏生《清代档案分类问题》对蒋廷黻等人所介绍的西方来源原则和事由原则的选择,都是因档案整理才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见识。这种对分类问题的讨论成为我国档案学萌芽阶段的主要内容。也正是这些讨论才使档案“保存及编目各方法,亦日渐精密”。溯其源,北大整理档案的经验是萌芽最初的营养。不仅顾颉刚先生曾肯定了北大档案分类经验的重要,也不仅罗权言对于“北大整理的方法,加以赞许”,方苏生更是给了北大档案整理分类以历史的地位,他在事隔十余年后总结档案整理方法时说:北大的整理分类方法,为“近年来整理档案的分类方法的开山之作,有几点是直到现在所不能废的”。而没有蔡元培先生的见识和努力,这种“开山之作”何时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