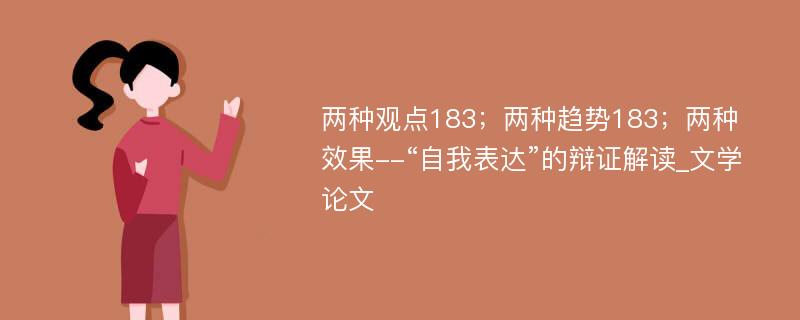
两种观点#183;两种趋向#183;两种效应——对“表现自我”的辩证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效应论文,观点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自文艺复兴以来,“表现自我”作为一种创作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成为文艺创作的历史潮流。只有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才把它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有些进步作家虽然在指导创作中也谈到“表现自我”问题,但主要是指作家个人最初创作尝试的一种规律性表现、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和作家创作中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而言的,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的规律。粉碎“四人帮”后,重提这一口号,与批驳“四人帮”推行的政治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有关。它的负面影响,导致相当作家对深入和贴近生活、对创作社会责任的淡化和漠视。
【关键词】 表现自我 两种观点 两种趋向 两种效应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拓展,深化和发展了文艺科学。但也应该看到,对有些文艺理论问题,象“表现自我”论等问题,还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阐释。
一
有些同志坚持把“表现自我”做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他们认为“表现自我”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巨匠们提出了“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启蒙运动时期,卢梭虽然提出了“返于自我”的著名口号,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想的主潮仍是对封建专制的全面否定和对“理性王国”的热烈追求,启蒙主义作家把“理性”和“自然”作为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的两面旗帜。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所谓“回到中世纪”的口号。19世纪3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崛起。许多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都主张使小说成为时代的艺术记录和社会的形象缩影。一些具有巨大社会容量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常常成为时代的史诗和生活的教科书。
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物质文明形成的享乐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传统观念和基督教义的强烈冲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中心和绝对权威,普遍对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命运发出了悲叹和疑问。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说:“今天西方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彷徨苦闷。”〔1〕确如所言, 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危机,正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现代派文学吸取了资产阶级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如非理性观念、异化观念、自我本质观念、潜意识和性心理学说,等等,强调人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存在”〔2〕。例如, 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科科施卡“反对一切法则”,认为“只有我们的心灵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有些作品虽然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对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危机做了一定的揭露,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确实做出了某些新的创造;但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和反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使它们不能正确地描写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的简略述评中,我们不难看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切在创作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向的作家,总是把广阔地描写现实和正确地反映时代作为创作的宗旨。“表现自我”做为一种创作思想始终没有成为文艺创作的历史潮流,把“表现自我”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这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出现的文艺现象和社会现象,它们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代表就是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流派。这些文艺流派个别作家的创作虽然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暴露,在艺术创造形式和表现手段上曾经有所探索和贡献;但是就其阶级倾向和思想体系的本质而言,他们是资产阶级灰颓精神和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创作上的体现。
二
当然,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进步作家没有把“表现自我”作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作口号,没有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并不等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谈到过“表现自我”的问题。
我们必须把一些作家从艺术个性特点角度谈到的“表现自我”,与现代派作家从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根本目的的角度谈到的“表现自我”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我们不主张把“表现自我”当做创作的总体理论和指导思想,而否定过去和现在一些作家在谈到具有某种形象含义的“表现自我”时,对艺术个性特点所阐明和描述的有益理解。
我认为,这些有益的理解,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作家个人最初创作尝试的一种规律性表现而讲的。
所谓“表现自我”,是说许多作家的创作道路共同揭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在文坛上闪露艺术才华的青年作家,初试文事,视面有限,眼熟心谙的事物,常常是作家自身经历过的生活。所以,文思笔墨所及带有鲜明的个人生活色彩印痕。
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等人,都曾以自己熟悉的早年生活为题材写过小说。鲁迅那些流溢故乡山光水色和交织着乡思乡情的小说,鲜明地透散着作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气息,叠印着甜蜜、沉挚、浑厚、悲惋的早年记忆。郭沫若1920年写的第一篇“自我小说”《未央》,后来陆续写出的《飘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行路难》(上中下三部)等作品,均以自己及一家人为描写对象,作品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
又如,得奖小说《灵与肉》所写的主人公徐灵均的遭遇,基本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命运。张贤亮同志说过:“我写《灵与肉》,不过是想借编故事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下我生命史上一个时期的生活和感受。”〔3〕令人难忘的“自我”生活际遇和真切深刻的感情体验, 常常是作家萌生创作愿望的原动力,并且往往成为最初艺术尝试的生活源泉和获得成功的基础。这种最初的创作试笔,多半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为人生而文”。现实的丰富感受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以一种强烈的力量,推动他们情不由己地以创作做为表情达意的特殊方式。
特别是应当看到,许多作家早年的“自我”生活体验,还往往以自传性或近似自传体的作品形式出现。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新生》,就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自传性的作品。此外,像斯摩莱特的燃烧着人道激情与愤怒火焰的《兰登》,列夫·托尔斯泰的弥漫着农村田园气息的《童年·少年·青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闪耀着革命青春光华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是作家以自己独异的生活道路和真实的生活感受为基础而写出的艺术典型化程度很高的传世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与生活本来面貌十分相近,人们往往可以从作家本人及其周围人物那里找到生活原型,它们充分反映了作家早年丰富曲折的生活对自己创作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一类作品具有双重的美学价值:一是可以把它看做艺术化的“自传”,从中了解作家早年的生活道路、社会际遇、人生感受和思想性格的变化发展,是研究作家早期思想的宝贵资料;二是可以把它看做“自传”的典型化,是作家自我早期生活感受和社会现实发展的艺术概括,是从“自我”眼里所观察到的社会衍变的广阔图画,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
值得深思的是,甚至当一些人已经成为闻名的大作家之后,有时还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感受,写出“表现自我”的作品。这是成年人对人生艰难旅途的沉挚回盼,是饱蕴着人世沧桑感受的童心再现,是站在“历史今天”的视角对“历史昨天”的诗情烛照和哲理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作品是对作家生活道路和社会体验的“艺术总结”,其历史的深度、生活的容量和思想的底蕴,都是甚加称许的。
二是指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而讲的。
所谓“表现自我”,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是个体的精神劳动,是创作激情与生活燧石的撞击所点燃的灵感火花,是作家“这一个”(黑格尔)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识,是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它不能不具有作家个人思维、观念、艺术的独特之点,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能不带有作家“自我”的色彩和印记。马克思说:“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物体”,不能不具有“属人”的性质,必然打上塑造者主观方面的印记,使作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新的充实”,“成为对自己的确认和肯定”,因而艺术家们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马克思强调的是“属人”即作家的“性质”, 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生活视野,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人的本质力量”虽然是相同的,但它在每个作家创作中体现出来,却是各自不同的;正因为是彼此不同,所以才能是“新的显现和新的充实”。为了遵循马克思称之为文艺创作的“美的规律”,作家们必须在创作中“成为对自己的确认和肯定”,即象高尔基所说的要“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某一件事物的主观态度,并用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5 〕中国古典诗说也十分重视境界的“自我”特色。刘熙载说:“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个我字也。”〔6〕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7〕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抒情诗人,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就是那些叙事性的作品,“自我”虽然不一定成为书中人物,但同样要求作家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或者说走向艺术成功的道路,就是作家要找到创造性的“自我”和自我的“创造性”,真正形成自己的艺术思想、艺术风格、艺术个性。
文艺独创性要求作家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作家的不同艺术个性又会形成作品思想艺术上“这一个”的独特风貌。“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8〕世界是多样的,事物是多样的, 作家是多样的,创作也是多样的,多维多向是社会生活的特点。比如,同是写神话传说人物普罗米修斯,最初的原始神话题材,是表现古希腊人对于原始社会中火的发明的艰苦过程的理解。到了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时代,普罗米修斯便成了为人类的文明而受到宙斯残酷迫害的英雄,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9〕, 生动有力地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而在巨匠哥德笔下闪耀着哲理光采和求索精神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剧本没写完),则表现了启蒙思想家对宙斯神圣权威的大胆蔑视,在奇特的神话故事中透散出了强烈的反封建反特权的时代精神。至于雪莱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则以庄严激越的笔触着意描写了普罗米修斯对天神朱比特斗争的坚定性,并以最后一幕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明媚春天来到人间,预示着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未来。在雪莱的影响下,远离祖国的拜伦也写出了《普罗米修斯》,它一反《东方叙事诗》的悒郁凄清的格调,唱出了对革命斗争的庄严颂歌。文学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时代不同,作家创作思想不同,同一类题材也就会有不同的处理,它进一步说明了作家“自我”认识对于创作发生的影响。
从以上创作例证中不难看出,作家“表现自我”的个性,不是超然物外的“神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灵思”,而是社会的产物,生活的产物,思想感情的产物。作家“表现自我”的个性必然会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影响。“同一个对象在不同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说到底,还是因为“不同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同,所具有的思想观念、艺术修养、表达方式和审美情趣不同。正因为如此,对“表现自我”的艺术个性也就必须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三是指作家创作中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而言。
所谓“表现自我”,就是作家与作品人物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的、艺术的统一。
这种艺术统一的过程大致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入乎其内”的效应境界,即作家与人物、作家“构思运墨”与作品人物的“生活世界”的相呼应、相渗透、相共鸣、相同化,以至作家完全走进“作品的生活世界”,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与其同甘苦共命运。这时候的作家,已忘记了自己写作的创作行为,切切实实进入了多角色的戏剧舞台和感情世界。第二段,是在完成创作过程之后,作家“出乎其外”的感悟和理解,即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理性思维,表达自己对作品题旨、人物、故事、蕴意的理解。这是对创作过程感情体验的思想升华和理论思考。所谓“表现自我”,就是对创作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整个过程中作家与人物相渗融的和谐境界的一种概括。
这方面的创作典型例证是很多的。巴尔扎克老人在进入创作至境时,常常像患了大病一样,时喜时怒,时哭时笑,他自己变成了作品中人物的同情者和憎恨者。普希金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完全进入了长诗之境的角色,竟然十分抱憾地说:“真想不到,达吉亚娜竟然要出嫁了!”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自己没有想到安娜竟会卧轨自杀。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作家与作品人物两相融合的心灵感应现象。
法国作家左拉在谈到都德塑造典型形象时说,“从这时开始,他自己变成这些人物,他生活到作品的环境中去,把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在这种亲密结合中,书中场景的现实性与小说家的个性合而为一。”〔10〕巴金老人在谈到法国文学的影响时也说:“我忘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11〕世界名家这些包蕴着创作甘苦和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谈到了创作的“三个融合”:一是写作与生活融合,二是作品现实与社会现实的融合,三是作家个性与作品人物个性的融合。实现这“三个融合”,就是“表现自我”与“表现社会”高度的、和谐的、艺术的统一。
许多作家正是出于对创作的这种“最高境界”的独到的美学理解,谈到了作家本人与作品人物的思想感情上的内在联系,甚至把作家自己就说成是作品中的人物。比如,屠格涅夫在谈到莱蒙托夫创作的中篇小说《当代英雄》时说:“谁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说,皮却林是他自我写照。”〔12〕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蔡文姬就是我。”当代小说家周克芹也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就是他〔13〕。这些蕴意邃远、生动深刻的事例,揭示了作家“自我”与作品“人物”的血缘关系:《当代英雄》以凄怆忧伤的色调所着力表现的皮却林的宿命心理和矛盾性格,真实地反映了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一些先进贵族青年的性格特点和悲剧命运;蔡文姬渗透着血泪的归汉修史的动人故事,则恰好形象地描绘了像郭沫若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曲折艰难的爱国主义道路;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充满生活颤音的曲折际遇,则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一代农民在十年浩劫中的悲惨生活。
由此可见,作家达到“自我”与“人物”交融一体,是作家对理想和完美的追求,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渗透融合,是实现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创造性境界。实现这种境界,要求作家“自我”生活与人生感受必须具有社会的代表性和艺术的典型性。也就是说,作家独具特点的生活内容和思想面貌,必须能够构成作品主要人物的生活基础和性格基调,并以作家“自我”生活道路为轴心联织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只有这样,作家的“自我”与作品的“人物”才能通过艺术概括的过程达到和谐的统一,像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样,“使自己的灵魂里的内在世界跟外部现象的世界交融在一起。”〔14〕
以上谈了中外一些作家对“表现自我”的意义的深刻理解,并结合一些文学史上的事例,对他们所谈到的“表现自我”的特定含义做了一些具体分析。从中不难看出,许多作家是在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讲到“表现自我”问题的,而且几乎全是从艺术创作个性特点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这些论述概括了作家“自我”因素在人物形象艺术生命诞生过程中的地位作用。这些凝结着作家创作甘苦的经验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
在粉碎“四人帮”后,甚至一直到前几年,为什么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从诗歌创作到整个文艺创作也提出了要“表现自我”的口号呢?
任何创作口号的提出都有其时代和历史的条件、原因,这个口号在我国文学界的提出,也决不是偶然的。实质上,它是与“写真实”、“表现人性美”、“揭露阴暗面”等口号一起,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崛起而提出来的理论主张,是对“四人帮”推行的政治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理所当然的反抗。
“四人帮”妄图把那些坚持党性、坚持正义的作家永世打入生活的“底层”,但却以一种异常的形式使作家们真正长期地回到了人民之中,和人民真正达到了血肉的结合。粉碎“四人帮”后,随着这些饱尝艰辛的作家们政治生活和创作生活获得解放,表现他们自己这一段曲折艰辛的生活,抒发他们凝结着人民和祖国之情的“自我”感受,便成为创作的历史的必然了。一时间,交织着悲愤血泪和生活颤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优秀作品,反映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悲剧的时代和时代的悲剧。
对于在这个时期一些优秀作家提出的“表现自我”创作主张,应当结合那个特定的时代条件而理解它们当初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一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生活经验,不能正确认识历史曲折并且在政治灾难面前丧失了理想信心的人,他们在大动乱之后产生了颓丧、惶惑、愁闷和幻灭的情绪。他们由对“四人帮”邪恶势力无力的反抗,转为热衷于“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思想上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艺术上的突出的主观化、抽象化,便构成了这些“表现自我”作品的共同特征。如果说这类作品伴随着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时代大潮而出现,其具有的某些批判内容掩盖了本身个人主义思想倾向;那么,随着国家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转变,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要求,这种沉湎于个人恩怨或作冥冥之想的“表现自我”之作,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就越来越不合拍了。然而,有些文学批评,却脱离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表现自我”的具体环境和具体内容,赋予“表现自我”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形式,把“表现自我”作为“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口号,作为作家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宗旨加以鼓吹。这只能给文学创作带来危害。它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导致相当作家对深入生活和贴近时代的淡化和漠视,导致相当作家对创作社会责任感的淡化和漠视。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讲究“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传统,如果不是把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导引到离开创作规律而搞简单机械地“为阶级斗争服务”;那么,按其本意,按其本质,按其规律来理解,这个传统是优秀的传统。就其一个时代的文艺主潮而言,不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大课题、大趋势,怎么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呢?
当然,文学创作,题材是多样的,创作风格是多样的,文学创作给人们的健康的、轻松的、审美的享受,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创作以“玩”文学的名义,表现庸俗的情趣,表现颓靡的心态,表现卑琐的感情,这样的作品与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昂扬正气和奋发精神不是很不协调吗?
对于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倾向问题,关键在于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应该发挥文学评论的权威作用。新时期文学评论的一个错误偏斜,就在于有些评论家对创作错误倾向的鼓吹。象对西方“表现自我”文艺思潮的鼓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有些创作现象,明明是不健康的,但有的评论家却美其名曰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在文艺小圈子,甚至在极少数几个人之中自做高雅,完全忘却了作家和评论家的社会责任。这种“侃文学”与“侃文学评论”,这种“玩文学”与“玩文学评论”的倾向应该引以为诫了!
注释:
〔1〕〔2〕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第153页、第176页。
〔3〕1982年4月18日《文汇报》。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第85页。
〔5〕《高尔基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260页。
〔6〕刘熙载:《艺概》
〔7〕王国维:《人间词话》。
〔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255~256页。
〔9〕马克思:《博士论文序》,第3页。
〔10〕左拉:《论小说》,第124页。
〔11〕转引自《文艺报》,1982年第5期。
〔12〕屠格涅夫:《回忆录》,第83页。
〔13〕《周克芹谈小说创作》。
〔14〕《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