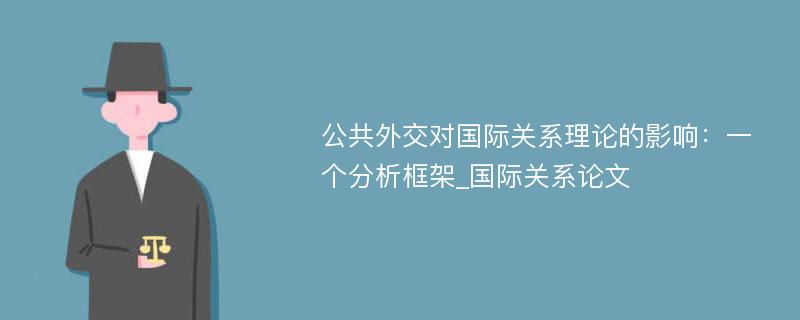
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外交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提出
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是学者们探讨的恒常话题。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国际领域不同于国内领域,国内是线性发展和进化的场所, 而国际领域却全无这些特征,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从国际上看,只有外交学 ,而无国际关系理论。他进而指出“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国际理论实 质本身”。(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H.Butterfield and M.Wright 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Allen and Unwin,1966,pp.17—34.)
但是,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确立其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产生了与怀特所言根本不同的变化。这就是,安全与发展本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但最强大的国家常常将其包装成和平与繁荣。从这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就被异化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本质上成了被包装的美国外交意志或意识形态。因而,美国面临的威胁越强大、越迫切,外交理论就越优先于并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如冷战时期的遏制理论、威慑理论等);反之,国际关系理论将获得优先发展,其学理性亦将强于操作性。这种现象解释了“9·11”事件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滞后性和“先发制人”、“震慑”理论风光一时的原因。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日益重视的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并渐成一门显学。(注:关于公共外交的概念及其实践,参见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试析美国公共外交及其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关于公共外交研究的著述已层出不穷,如美国学者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和戴维·龙菲尔德(David Ronfeldt)的《通向美国信息战略的心灵政治的兴起》、英国学者马克·伦纳德 (Mark Leonard)的《公共外交》以及德国学者皮特·范·哈姆(Peter van Ham)发表在 《外交事务》上的“品牌国家的升起”等。(注:See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Santa Monica,CA:RAND,1999;Peter van Ham,“The Rise of the Brand Stat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2;Leonard Mark,Public Diplomacy,London:Demos, 2002.)对于公共外交的内涵,欧美各国未有太大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外交 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即公共外交能否登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雅之堂”。公共 外交是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外交决策行为,以国外民众为对象,它强调外交实施国( 主体)与国外民众(受体)的“合作”关系,这与国际关系中冲突常有而合作不常有的“ 无政府状态”前提是相矛盾的。但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关系 理论的基本前提已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与此同时,理论的实践者 ——外交决策者的作用日益彰显。本文试图考察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并探 讨公共外交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
一种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所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用国际关系术语讲就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及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的。(注: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主体—客体—过程—系统四个层面加 以把握。其中主体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客体指国际关系内涵,过程指国家间或其他国际 关系行为体互动的方式,系统指国际关系发生演变的环境和氛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 ,完全可以归结为这四个层面的争论。以下我们将按照这一思路考察公共外交对国际关 系理论的冲击。
1.主体:对国家中心论的另一种质疑
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alism)广受国际关系理论诟病,常常成为自由主义攻击现实主义的一大“罪状”。但是,主要从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非对称性出发,公共外交则 从全新的角度对国家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将视线转移至国家与国外民众的关系上。
“信息时代的下一次大的革命应该发生在外交领域”。(注:David Ronfeldt and John Arquilla,“What If There Is A Revolution in Diplomatic Affairs?”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5 February 1999.http://www.usip.org/virtualdiplomacy/publications/reports/ronarqISA99.html.) 公共外交的勃兴可被认为是这一革命的产物,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外交实践,这 是我们讨论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冲击的时代前提与理论背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雷阿隆·威克斯(Rhiannon Vickers)认为,公共外交是国际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兴起原因在于:其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国家已失去对信息的垄断权,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压力集团、不同政见者和恐怖分子 的网络不断增强,权力正向不同行为体扩散,在一个“多中心”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互 动。在新的体系中,国家传统外交模式暴露出诸多不足,需吸收新的养分。其次,相对 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等“硬权力”(hard power)而言,由于新媒体手段不断涌现,各国 民众参与国际关系的兴趣渐浓,迫切希望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和政策结果,世界舆论的 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体系中“软权力”(soft power)的地位也愈来愈被各国看重。( 注:Rhiannon Vickers,“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7 December 2002,p.3.)这一观点在美国 咨询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关于公共外交的报告“全球化通讯时代的民众和外交家”中得 到了证明。该报告指出,“在信息化、民主化、英特网和全球性市场体系时代下,公众 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公众通过选举、游行示威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极 大地影响了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注:Department of State,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1998.)因此,公共外交是在全球化和信 息时代新国际体系发展的产物;公共外交的崛起可被识为是国家放下往日舍我其谁的架 子和单向思维、与国际社会更好沟通的结局。
2.客体:心灵政治与权力受体
政治通常分为两个平行的层面: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理论层面是国际关系的抽象面,旨在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现象和规律;而国际范畴的政策层面(外交决策面)是通过决策者的行为构想、创造或再造世界的一面。
理论层面的政治就像库恩(Kuhn)的革命科学论,各种理论范式争相竞争主导地位。(注:See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202.)因此,国际体系的变化,可能产生其他选项与国际关系前提竞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基于这一思想,决策层与理论层的融合并非不可能:只要决策者相信自己生活在霍布斯的国家属性中,那么理论层面的任何范式变化都没有意义。(注:Philipp S.Muller,“Maybe We Call It Communicative Diplomacy?”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7 December 200 2,p.14.)换言之,理论家可以说服决策者采取某种行为,决策者也可以让理论家相信他 们的行为是出自因果推演而不是个人臆断,任何理论都不能千篇一律地推导出决策者的 相应政策,从而证明某种理论绝对正确。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前提可以取代霍布斯的前提假想。在当前的争论中,有两个选项引起了学界和西方决策层的广泛兴趣:一是马克·扎克尔(Mark Zacher) 提出的“网络共同体”(network community),另一个是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所说的“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共同体以信息为主导,它与语言共同体的有机组合,可构成一个自立的国际体系前提。这种以信息和语言为国际体系的前提的设想具有符合现实需要的重大价值。托马斯·里斯在《国际组织》上发表的“让我们争论”一文中就把信息交流引入美国的言论。(注:See Mark W.Zacher and Brent A.Brent A.Sutton,Governing Global Networks: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无独有偶,美国兰德公司的两位高级研究人员戴维·龙菲尔德和约翰·阿 奎拉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心灵政治(noopolitik)”的概念,心灵政治把网络共同体与语 言共同体前提合二为一,为观察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选择性框架。(注: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Networks and Netwars:The Future of Terror,Crime and Militancy,Santa Monica,CA:RAND,2001,p.17.)事实上这一计划是由美国主管防御、控 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务卿办公室(OASD/C3I)发起并由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予以实施 的。该项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决策者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看法,着眼于决策层面。兰德公司 的报告指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有必要建立一个新范式,事实上它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心灵政治’(noopolitik)。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与心灵域(noosphere)结合的国家政治, 是心理上最广泛的信息领域,它包括电脑空间(如网络等)和信息领域(电脑空间、媒体) 。心灵政治是信息时代的外交决策行为,强调观念、价值观、规范、法制和道德的主导 性,通过‘软权力’而不是‘硬权力’起作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受心灵政治的 支配。但是它不以国家为中心,它的力量在于促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协同互动(con-jointly)。心灵政治的驱动力不是统计学上的国家利益。虽然国家利益仍然起作 用,但心灵政治的定义比以国家为中心的要素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融合了更宽泛的全 球性利益。权力政治(realpolitik)增进国家权力,而心灵政治增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的网络权力;权力政治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争斗,而心灵政治则鼓励国家合作。(注:Arquilla and Ronfeldt,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p.190.)
“心灵政治”概念的诞生给国际关系客体和“权力政治”造成的重大冲击,可以从龙菲尔德和阿奎拉提交给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另一份报告中关于“权力政治”与“心灵政治”的区别一览表中初见端倪:(注:Ronfeldt and Arquilla,“What If There Is A Revolution in Diplomatic Affairs?”.)
权力政治(Realpolitik)心灵政治(Noopolitik)
以国家为分析单元 错综复杂,非国家行为体
(资源等)硬权力为首要地位 软权力为首要地位
零和博弈的权力政治
双赢与双输都有可能
无政府体系,高度冲突 利益和谐、合作
有条件的联盟(威胁导向)
联盟网络对安全至关重要
国家自我利益为首要地位
分享利益为首要地位
政治是对优势地位的无尽追求
明确追求一种终结目的(telos)
本质无所谓道德与否
道德准则至关重要
行为由威胁和权力驱使 共同目标驱使行为者
非常警惕信息流动 倾向于信息分享
均势乃稳定国家的法宝 责任均衡
权力蕴于民族国家 权力蕴于"全球结构"(global fabric)
可见,“心灵政治”是外交决策者心灵或曰思维中的决策构想,它突出合作优势,强调“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组成的“非成为体圈”,是信息时代的国际主角。(注:Rothkopf,“Why The Realpolitik of The New Era Is Cyberpolitic”,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utumn,1998.)这是对传统权力的“达尔文式”定义的否 定,是对“软权力”概念的深化,也使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概念与东方社会的理 解日益接近,从而预示了东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某种融合趋势。在西方政治学中,“‘ 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注: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594页。)这一定义主要是从权力施予方(权力主体)给出,没有考虑权力接受方(权力受 体)的感受。实际上,权力的最终效果不仅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能力,而且要考量权力受 体对此权力的接受程度。这是古代东方朝贡国际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权力法则的重 大区别。比较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地位,我们可以发现,权力主体与 权力受体两方面都应兼顾。公共外交即是美国着眼于其权力受体的重大努力。
3.过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
“心灵政治”的出现,表明信息时代下权力结构中的权力主体(国家)角色的淡化和非国家行为体(民众)作用的上升,这不仅是对国家中心论的否定,而且对国际竞争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权力政治主要是关于谁的军事或经济会取胜,而心灵政治或许最终是 关于谁的语言和信息获胜。”(注:Arquilla and Ronfeldt,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p.22.)龙菲尔德和阿奎拉给美国和平研 究所的那份报告明确提醒美国应从单纯提防“电子珍珠港事件”(electronic Pear Harbor)转为追求美国激发的信息时代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或曰“信 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以便从中受益,并提出“正义出力量”(right makes for might)的口号。因此,公共外交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间的理性互 动模式,而是以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互动方式进行:开展公共外 交的一方是理性选择的,通过各种活动影响其作用对象——他国民众的感性心理。
以语言和信息这一基本前提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具有直观上的说服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曾指出过:“人是自然界惟一具有语言天赋的动物,言 语往往能道出好与坏,正义和非正义,具有这种特质的活着的人组成了家庭和国家”。 (注:Aristotle,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04.)
可见,以语言前提阐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早已有之。那么,为什么语言共同体是取代霍布斯主义的最具吸引力的候选项呢?从机能上说,语言共同体前提能更好地使国际领域的实践概念化,因为它能描绘决策者的反馈现象。决策者也更喜好这一前提,因为它与他们的实践相吻合。另一方面,语言共同体前提能解释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故障,因此,语言前提似乎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更有效的“操作体系(operating system)”。(注:Hans Blumenberg,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9,p.50.)
语言共同体前提下的体系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个 人与团体合作成败与否的工具,能使我们解决以语言和信息交流为特征的公共外交之类 的新现象。诚然,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的国际关系理论用自然科学方法解释社会行 为的做法,使它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国际体系的实证层面不断翻新、决 策者对语言和信息交流的兴趣与日俱增,以及国际政治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增强,这一前 提的弱点已暴露无遗。
语言共同体和信息交流这一前提已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决策者的青睐,新的国际关系前提的“合理性”问题正成为他们考虑遴选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外交融入国际关系理论指日可待。
4.系统:公共外交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公共外交是一种决策行为,是以国外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它主要通过语言和信息手段来实施,前提是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合作”度,强调国外民众的“接受”程度。
从公共外交的内涵看,它与国际关系的前提显然相悖。国际关系是一门发育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前提是,内部等级结构的民族国家与外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平等国家的区别。这种差异使国际关系的创始人推导出国际互动的不同逻辑,并为一门新学科提供了必要的理由。(注:Walker Robert B.J.,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67.)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基础是霍布斯的“国家属性”,即无政府状态。霍布斯属性的背景下不存在“国家合作”关系,而至多是一种“联合行动(co-action)”。(注:Axelrod Rober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p.71.)
按照霍布斯国家属性的这种前提要求,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存在对公共外交概念化的难题,因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体系中,信息传达只能通过“行为”而不是“语言”来实施 。在霍布斯国家属性看来,个人和国际层面的国家是永恒的“囚徒困境”的参加者—— 没有人值得信赖,因此,“行为”是了解其他国家意图的唯一可靠的信息源。(注:Philipp S.Muller,“Maybe We Call It Communicative Diplomacy?”,p.9.)以这种属 性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关注以语言方式为工具的国际互通。公共外交以事实话语 和信息共享(交流)方式所发布的主张和概念等,不能进入主流理论的“高雅之堂”。换 言之,国际关系中的“语言信息”无法从周而复始的国家属性中推演出来。
但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并非未受挑战。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罗伯特·基欧汉就一直认为,从“无政府状态”这一核心假设中推出“国际体系中只有冲突”的结论是错误的。在挑战沃尔兹的观点时,基欧汉虽然接受霍布斯的假设前提在塑造国家行为中的作用,但他批评沃尔兹只看到国际体系中“冲突”的一面,而忽视了 “合作”的可能性。(注: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41.)这两种观点的对垒导致了基欧汉与沃尔 兹关于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的“合理性”问题长达十年的论战,但是这些争论都以一段学 究式的努力而告终。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当 代的争论》一书也未能联系后冷战后时代的现实经验。(注:See David Baldwin 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例如这些学者在谈论多边会议、WTO决议、国际法或人权等问 题时,无不放弃主流理论的核心前提,因而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实践的双重困惑 。
近年,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前提又遇到了另一经验式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冷战的结束,世界秩序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和后来出现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学说都不能恰当地解释信息时代的“新现实”。(注:Rothkopf,“Why the Realpolitik of the New Era Is Cyberpolitic”,p.18.)而相比之下,外交世界的决 策领域正焕然一新,其愈发活跃的表现与我们想象的世界秩序理论相抵触,“外交政策 决策者越来越关注如何说服国外公众接受本国的国际行为。”(注:Simma Bruno and Andreas Paulu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Peace Res.Abstract,Vol.38,No.2,2001,p.274.)
建构主义代言人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以及基于因果决定论来解释和预测世界现象,很难与下列事实相吻合:我们考察的目标是有反馈(reflective)思维能力的决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世界并决定参与国际社会。(注: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57.)因此,学者应该像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其他 问题一样关注决策者的反馈能力。(注:Marysia Zalewski ed.,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93.)
然而,至今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家的注意力仍局限于理论自身的自我批评,通过解构三次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历史决定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构建学科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家常常遗漏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政策层面及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相关性。他们只关注国际关系的学科规律,却没有考虑到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偏离现实的理论前提是危险的,主流理论的批评视角应该重视理论与政策的交叉面。
因此,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之前,我们应更多地了解实施理论的行为者。外交政策决策者是创造世界的行为者。外交政策决策者是创造世界的行为者,也是理论的实践者, 他们说服他们的“首脑”(principals)接受周围世界的“现实”,然后按他们所描述的 路线采取行动。这里的“首脑”是一个属性代词,是泛指决策者所代表的个人和团体。 (注:Steven Ross,“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The Principal's Proble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3,No.2,1973,pp.134—139.)首脑和决策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是合法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因此,政治可以定义为决策者的决策,决策者 构想他们的社会团体和他们的世界,为实现其公共社会利益,决策者会命令其他人接受 他们的观点和行为。(注:Max Weber,Politik als Beruf,Stuttgart:Reclam,1992,p.1 13.)
可见,国际关系学者拿因果关系和结构决定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决策者行为的做法,在新的国际体系下不免会遇到挑战,重视决策者如何构想现实世界的最基本层次的研究必须提上日程。
公共外交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景
如何评价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时代矛盾演绎而导致国际关系变化的自然产物。经典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很早就研究了威望政策,(注: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强权斗争:威望政策”。)只是他强调强权斗争增进一国威望的途径。时代发展了,国家威望更多靠说服、感召而非强权赢得,公共外交即以相对平等和尊重他国民众的方式,结合现代信息与沟通手段,增加自身“软权力”的努力。当然,它更多的是强者的选择,尚未惠及普通国家。
这一点也反映到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变化上。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教授积极倡导美国反恐要推行赢得人心的战略,(注:John Mearsheimer,“Hearts
and Minds”,National Interest,No.69,Fall 2002.)反对“先发制人”战略。公共外 交更是汲取自由主义之所长,提出网络共同体这种更加超越国家性影响的国际机制规则 ,将建构主义强调的角色、身份和认同理念贯之于实践……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一事实 :公共外交已经融合了国际关系理论各派的不同主张,反映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性日益 加强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