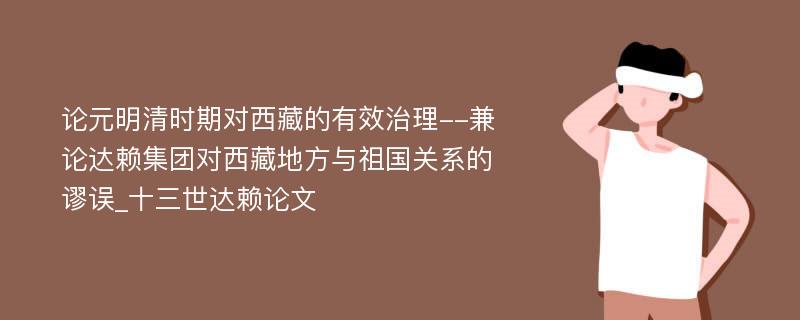
论元明清历代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统辖和治理——兼斥达赖集团等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问题上的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达赖论文,王朝论文,谬论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命题。但是,西方有些人士却宣称:中国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是“一种在想象上存在于整个历史中的关系”。达赖集团更是一贯歪曲历史事实,到处散布西藏“一直是完全独立并与中国相分离的”,近年来还与民运份子相勾结,以所谓的“新视角、新思维”,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问题上制造种种谬论,竭力否认元明清历代王朝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无可置疑的历史史实表明,他们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
一、西藏在元代归入祖国版图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西藏在元代归入祖国版图,是中国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达赖集团为证明西藏“从来就是独立的”,竭力否认这一点,并为此“创造”了一系列奇特的“新论”,如蒙族、满族不是中国人,因而元清两代统治西藏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又如说元和西藏不是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具有明显不同于宗主和藩属关系中的那种统领和隶从的典型特征”,甚至胡扯什么元帝是“由西藏大喇嘛的宗教地位或托任管辖而获取帝王统治的合法权”。而有些民运份子则跟着唱同样的调子,也将国家和民族分割开来,说蒙古不是中国,而且还将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存亡等同起来,说什么宋朝灭亡了,中国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拒不承认元朝对西藏的统治,说元在西藏驻军不是统治西藏,而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的政教势力,在精神上则是西藏征服了蒙古,并由此悟出惊人的“新结论”:不是西藏归入中国,而是西藏联合蒙古在统治中国。
达赖之流的“新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1.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世界上有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或一个民族组成的几个国家。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朝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央王朝起,2千多年来,历代王朝不管如何更替,国家还是前后相继,疆域大体上是稳定的。在历史长河中,由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中央王朝,不仅没有割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而且还为其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元世祖忽必烈在其建国过程中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仿效汉法,取法唐、(北)宋。1271年,又取易经“乾元”之义,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在其颁布的《中统建元诏》中称:“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明白表示自己是继承中国“人君万世”的正统皇位,遵循的是中国前代之宪制,建立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圣祖玄烨在一首诗中说:“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也是说自己继承的是汉朝时就已开拓的中国的正统。在《清实录》记事中,也称明代为“前朝”。
国际上,一般也没有将中国之内的民族和中国国家分开的。即连当年侵藏的英国人柏尔,在他为十三世达赖写的自传中讲到忽必烈时,也是借达赖之口称忽必烈为“中国伟大的蒙古族皇帝”(注:(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108页。)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的西藏协定的英文本中,都称清朝为中国。所以,将中国国内的民族和国家分割开来是十分荒谬的。
2.西藏和元朝的关系
西藏在元代归入中国版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西藏和元朝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从西藏归入祖国版图的过程看,西藏本身历经400多年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自身无力统一。公元9世纪,吐蕃王朝自赞普朗达玛被刺后陷入长期的混乱、分裂局面。吐蕃贵族内部围绕王位继承问题争权夺利,边将部属相继叛离。王室间相互残杀火并,前后长达20余年,史称“战争过处,杀人盈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注: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月拉萨一版,第70页。)。紧接着的奴隶平民大暴动,使吐蕃奴隶制王朝彻底崩溃,吐蕃全境四分五裂,战火连绵不绝的局面一直持续了400多年。据藏文史籍记载,到公元13世纪初,西藏地方各政治势力的大致情形是“除西部阿里各地是由吐蕃赞普的后裔们分割统治外,其余地区仍是没有统一的法度和政权”,“它主要的世俗政治势力都处于衰微之中”,“谁也不具有统一全藏的力量”(注: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西藏古籍出版社1997年拉萨一版,第306-322页。)。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实现统一。这可说是从西藏400多年分裂历史的苦难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祖国统一的大趋势中,西藏地方势力暂时停止了彼此的征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努力加快历史的进程,为西藏正式加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据藏文史籍记载,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派王子阔端向西藏进军。西藏各大地方势力集团看到阔端“先后派兵入藏不可抗拒的威势”,“纷纷派遣自己的人员”前去表示归顺并建立依靠关系。以后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以60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凉州,建立了西藏地方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直接的政治联系,议妥了加入祖国大家庭的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注:《萨迦世系史》(汉文译本),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拉萨一版,第91-94页。)。他在信中说明了归附元朝中央政府的意义,劝谕各地接受中央政府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设官受职等等。信中清楚地指出,只有已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元朝才能担当起统一西藏的重任,西藏只有加入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才有自己的前途。萨迦班智达的这封信是西藏地方同元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和隶属关系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受到西藏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对西藏地方正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元在定都于燕京的当年就设立专门的机构——总制院,作为加强对西藏地方及其他藏区管辖的重要措施之一。1288年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和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并列为元朝中央政府的四大机构。宣政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及其他藏区的军事、行政、财政事务。
为能实行直接的有效的管理,元朝将各藏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并设立相应的机构。它们是:(1)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范围相当于今日青海省西南部,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的大部分,西藏昌都地区的一部分。(2)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范围相当于今日青海省、甘肃省的藏族地区,四川阿坝州及甘孜州北部的部分地区。(3)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注:《元史》卷7,志37,百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册第2193页。)。“乌思”,指前藏(清以后译作“卫”);“藏”,指后藏;“纳里速古路孙”,意为阿里地区。所辖范围相当于今日西藏地方的大部分地区。宣慰使的主要官员皆由元朝中央直接任命。
按元规定,由八思巴提名委派本软,再经元中央任命,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本钦”是地方政权的行政长官。西藏的宣慰使多由萨迦本钦担任。各藏区的僧俗官员必须遵守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并负责该地区的差税征集、人口调查和驿站管理。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官员的封授,对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地位、权利,对土地、房屋、属民的占有,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对农奴的占有,都要凭官府的铁券文书。官员的政绩要接受元中央政府的考核,文卷要接受按察司的稽查。官员的奖惩亦由元中央掌握。如《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脱思麻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儿干之地”(注:《元史》卷27,本纪27,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册第605页。)。而萨迦本钦如果违法,一样要受元朝中央政府的惩戒。在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中都记载有萨迦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因与八思巴作对,在八思巴去世的次年,被忽必烈派兵入藏将其处死(注:《汉藏史集》(汉文译本),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拉萨一版,第180页。)。
元朝多次在藏进行户籍调查。这项工作被元朝认为是征服一个地区的象征,亦是加强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当年就派人进藏调查户口,1268年又派人进藏作更精确的调查。这是在西藏地方设置行政机构,确定官员数额和百姓赋税、贡物的依据。1287年、1336年,元又两次派人进藏复查户口,稽查赋税情况(注: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西藏古籍出版社1997年拉萨一版,第359-360页。)。
为及时掌握西藏地方的情况,确保元朝中央的政令畅通,确保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元在藏区共设立了28处驿站,其中西藏地方设11个。驿站设有专职官员。他们不属于藏区万户管辖,但沿途万户要提供运畜需用的器具及支差的人员(注:《汉藏史集》(汉文译本),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拉萨一版,第181页。)。
此外,西藏地方的安全、防务亦全由元中央政府负责。在西藏地方萨迦本钦的地方政权机构设置的官职中没有军事官员,而在乌思藏纳里速古路孙等三路宣慰使司中,除有元帝任命的5位宣慰使外,还有2名负责驻藏军队管理的元帅(注: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西藏古籍出版社1997年拉萨一版,第339-340页。)。
元朝的上述措施是元统一全国的总政策在藏区的实施。这表明中国中央政权第一次在西藏地方正式建制。此后直到近代的700年间,西藏的政治制度都是由中国中央政府陆续予以规定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西藏地方在元代已正式置于全国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
二、明代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
达赖集团与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将明朝定性为“收向内缩”的王朝,断言明朝与西藏“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西藏地方归顺明朝不过是一种“投机”,进贡是“占”明朝的“便宜”,等等。总之,他们要向人们“证明”,明代虽是中国王朝,但对西藏没有主权关系,西藏在明代也是独立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明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1.招抚西藏,完成统一大业。
(1)昭示天下,明确主权关系。明在平定中原,“悉平海内”,“推及四夷”,掌握全国政权后,对有功将领本该“论武功以行爵赏”,但明太祖在洪武三年宣布“报功之典未及举行”的原因是“缘吐蕃之境未入版图”(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3-6页。)。可见明中央王朝在建立之初就十分明确宣布西藏地方属于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要将西藏地方纳入明朝中央政府治下,然后再举行“报功之典”。
(2)选派将领,深入藏区招抚。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明在“大统既正”后,就继承元中央政权的地位,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洪武初年,明太祖即遣官赍诏,入藏诏谕。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和保卫疆土,明廷众多将领不畏艰难险阻,远入藏区,深入各地,不辱使命。有的中途遭劫遇害,有的献身疆场,还有许多人常年守卫在气候恶劣、条件艰苦的边疆,积劳成疾,正当英华之年便谢世人间。如名将邓愈,洪武三年随大将军徐达平陇川,破扩廓帖木儿,招谕河州何锁南普。洪武十年,“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上嘉其功,遣使召还”。但邓愈此时已身患多病,返京途中,即以疾终,年仅41岁。“上哭之恸,诏辍朝三日”(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38-40页。)。再如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宁正,洪武三年即随邓愈克河州,转战戍守藏区各地达25年,常年征战在高寒缺氧、条件极其艰苦的地区。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他还在为保卫国家边疆而战,是年3月还京,也“以疾卒”。类似这样为维护国家统一大业而献身的事迹在《明实录》中还有大量记载。
(3)晓谕藏区,实行特殊政策。深入藏区的将领、官吏,以明太祖的诏书,晓谕僧俗各界,新的统一的中央王朝明朝已建立,同时宣布对藏区的特殊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咸推一视之仁”,凡归顺者,承认元的册封,各种待遇照旧,而且还给以种种优待,很快安定了人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如洪武二年九月,明将领韦正涉冰过河,突袭临洮,直捣当地藏族土官营寨,“土酋惊以为神,俱投戈以降”。韦正“悉以衣冠厚馈而遣之”,“自是诸部土官相率来降”。又如元代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洪武三年六月以元代所授金银牌印敕来降。洪武四年正月,明即任命其为河州卫指挥同知,原知院汪家奴为佥事。“置所属千户所八,……军户千户所一,……百户所七,……汉番军民百户所二。”不但委以重任,而且还令其子孙“世袭其职”(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8-10页。)。
(4)众心所向,自愿称臣归顺。在明朝特殊政策的感召下,藏区僧俗各界无不自愿称臣,心向中央。到1375年,各藏区已全部接受明朝中央的政令,确立了辖属关系。藏区僧俗上层非常重视保存明中央颁发的册封文书,对明中央敕令遵命唯谨,积极承担入贡、修路、驿站供给等义务。通过朝贡封赐,客观上加强了明中央对藏区的管理,促进了藏汉团结、国家统一。
2.加强管理,巩固西部边陲
(1)多封众建,实行全面扶持。根据西藏藏传佛教影响较大的情况,明朝也将宗教教主放在相当尊崇的地位,利用宗教的力量来维护地方的稳定,巩固国家的统一。与元朝不同的是,明朝采取“多封众建,朝贡赏赐”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皆注意争取。首先对当时影响较大的三个教派教主赐予“法王”的封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为大宝法王,萨迦派教主为大乘法王,格鲁派教主为大慈法王。1406年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1407年又封宗巴干(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1413年封南渴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领真巴儿监藏为必力工瓦阐教王(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121-127页。)。
(2)奖惩升迁,概由中央决定。明朝政治上十分注意强化中央在藏的主权地位,凡藏区僧俗官吏品秩的规定、任免、升迁、更替及奖惩,皆由明中央政府决定。所封各教派五王的承嗣,也必须上报明朝中央,由中央批准后遣使入藏册封,手续十分严格。《明实录》中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呈请赐封者亦有不予批准的情况。《明实录》卷一九八载,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乌思藏阐化王遣喇嘛锁南领占令乞陞国师,但明廷没有批准,“命为禅师”。若不按照中央规定办就要受到弹劾,追问罪名。如1495年阐化王死,明帝同意其子袭职,遣参曼答实哩等赍诰敕并赏赐进藏册封,但路上花了三年时间,到达西藏时新王已死,新王之子即欲受封并领所赍诰敕诸物。参曼答实哩不得已授之。但至四川即被巡抚官劾其擅封之罪,逮至京师。后帝考虑其为藏族,便免一死,但发陕西平凉卫充军(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北京一版,第139页。)。
(3)建立卫所,强化行政统辖。明基本按元朝模式管理藏区,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卫,原朵甘地区设朵甘卫。“卫”是明代军队编制,一般设于要害地区。几个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有5600人左右。对于西藏地方及各藏区,明太祖认为:“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所以要“建立武卫,俾安军民”(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北京一版,第30页。)。明没有象元朝那样在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管理藏区军政事务的机构,而是放在中央委派的武官管辖之下,归边境军卫管理,但由中央控制。1374年,又将藏区的2个卫分别升为行都指挥使司: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藏大部分地区,下辖3个指挥使司(西藏浪卡子、堆龙德庆、仁布等地)、1个元帅府(西藏阿里地区)、5个万户府(西藏拉萨、墨竹工卡、乃东、江孜、昂仁)。而原朵思麻地区则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代表明朝中央统辖各藏区(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北京一版,第75-89页。)。对各藏区下属的原有土司,重新予以授职,进一步巩固土司制度。
(4)设立驿站,确保政令通达。明朝还恢复元代驿站制度。1381年置陕西递运所,又置庄浪、西宁马驿各二,每驿给以河州茶马司所市马10匹,以土兵11人牧之。1392年,因巩昌至甘肃路途相距太远,明帝命兵部和右军都督遣官相度,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共增置29驿,驿置马30匹。1414年遣官赍敕令乌思藏地方及各藏区,凡驿站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明朝还两次组织修理驿道,加强驿站管理,命令藏区供应徭役,保证交通,以利于中央政令的通达。这些措施使明代出现了“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的太平景象(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北京一版,第144-145页。)。
(5)时时关注,亲抓重大事件。明廷对藏区的治理十分重视,明代几位皇帝都亲自批阅来自藏区的奏章,并敕谕及时处理。据对我国历代实录中保存比较完整、时间比较准确的《明实录》的不完全统计,记录有明中叶以后明代12位皇帝亲自批阅的,仅有关各藏区用兵、抚治、戍守、屯种及对失律官兵惩处的奏章及明皇的敕谕就达622条之多(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3册“分类索引”。)。有些重大事件,明帝不仅亲自批阅,敕谕彻查,而且一直检查督促,直至问题妥善处理完毕为止。如1427年,朝廷接报松潘卫藏民万人聚集对抗官府。明宣宗阅后便下令彻查,并作好紧急应变的准备。从1427年5月22日明帝批阅四川三司及巡按上报的此奏章起,到1430年8月11日处决松潘卫指挥使止,仅记载明宣宗亲自批阅有关此事的奏章就达29件之多。最后查明是松潘卫千户钱宏、尚清惧征交趾,于是诈称藏民闹事,并率军到藏寨强抢民物激起民怨,以此遂乱。明宣宗一面批评四川三司失职,朦胧具奏,同时征调军力以作招抚和应变的两手准备,指示尽力妥善处置,争取边民,并命令对首犯千户钱宏先予处决。中间又发现征调的指挥佥事“不行赴援”,即予降职。后查明该佥事其他罪行后,发配充军广西。对严重失职,且大肆贪虐并打击迫害下属致死的松潘卫指挥使司亦予以处决。而对事情处理中“攻讨抚绥咸得其宜”的将领士兵皆论功赏赐(注:《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拉萨一版,第214-277页。)。这些史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明代中央对藏族地区行使着完全的、有效的主权。
3.密切交往,促进统一
藏民族素以青稞、肉食为主食,因而茶叶成了藏族生活中之最必需品,而藏区所产的马匹亦为内地之所需,尤其是军马更为需要。所以藏汉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以来一直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资贸易,而是藏汉两个民族互相依存、必不可少的经济联系的纽带。
明朝时期,茶马互市更加活跃,除官营外,民间交易亦很兴旺。为垄断茶马贸易,明在许多地方设立专门机构——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但亦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一些地方政府摊派杂税,府卫军民从中渔利,客观上保证了国家军马的需要,保护了内地和藏区贸易双方的利益。到明代中期以后,为适应私商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明廷决定放开市场,允许私商公开经营,内地与藏区各项物资交流的速度进一步扩大,藏汉民族的联系更加密切。
三、清代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地位
由于西藏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的深远影响,清朝对西藏的治理也极为重视,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清确认明的治藏旧制。1684年,清顺治帝即敕谕西藏地方,宣布明朝“所与诰敕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此举安定了人心,取得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拥护。清廷还崇奉藏传佛教,优待僧俗上层,屡次敕令达赖、班禅进京。而达赖和当时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蒙古族和硕特首领固始汗也急于获得清廷的支持和册封,确立自己的名位,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集团及蒙古各部落相抗衡,所以也愿意服从清朝中央。后清廷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藏传佛教领袖,颁给金册、金印,同时又册封了固始汗,也颁给金册、金印。达赖因此扩大了在藏传佛教界的影响,地位也随之提升。清朝中央通过加强对蒙、藏两大民族地区的全面统治,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无法否认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1)清帝接见达赖使用君臣之礼。五世达赖于1652年(藏历水龙年)3月17日,率西藏僧俗官员和随从3000多人离藏赴京,觐见清帝。12月16日到达北京。
关于达赖觐见清顺治帝时的情况,《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作了详细的记述:“水龙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发去谒见皇上,进入城墙继续前行,当来至隐约可见前面排列有轮王七宝,威仪煊赫之转轮王,荣耀如帝释天王之天子坐朝处,众人下马。此后又走了约有四箭之地,我亦下马。皇帝下御座,行十庹远,携我手,命通事存问。皇帝的御座置于高与腰齐的御台之上,我则坐于距御座一庹以内,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献上茶来时,皇上命我先饮,我答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饮用,对我格外施恩。我献上珊瑚、琥珀、青金石等制的念珠,以及氆氇、红糖、多包安息香、马千匹、卜拉嘎、兽皮千张等贡物。皇帝回赐物品十分丰厚。……皇上拨白银九万两,专门为我修建了一座名为“黄寺”的如同天神苑圃一般的居处,围墙与环绕主殿的僧舍俱全。……”(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08-610页。)“1653年,皇上……谕我于(1月)11日进宫。遵谕到达皇上御台之前,大臣百官俱已到齐,皇上尚未升座,我在专为我设置的高为两肘的垫子上垂腿而座。不久,鼓乐齐鸣。皇上自后门入,登上一约有一人高的广大金台,其上又有一小台,小台上设御座。皇上在就座之前,令阿萨堪大臣传谕于一直侍立着的我,命我与皇上同时就座。”(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10页。)
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显示了清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对团结藏族宗教上层中有很大影响的人物的重视。这是着眼于统一全国各地区的战略考虑。第二,所用礼节绝不是和邻国国君相见的礼节,所以清帝采用不亲自出迎,但却在郊外相遇的办法,既显出特别尊崇但又不失帝王之身份;给五世达赖准备的专门住处也非常高级,但又是按寺庙、僧舍的要求修建,而不是按国宾下榻处标准修建的。第三,觐见清帝时的座位也说明仍有君臣之分。达赖自己在皇上来到前也是一直侍立在殿中,并没有以一个国君的身份与清帝相见。
(2)达赖的地位和权力来自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廷正式册封五世达赖,颁赐金册、金印。自此,达赖喇嘛的名号被正式确认,其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亦被确定。因为这是达赖喇嘛系统在藏传佛教中领袖地位被确立的开始,所以郑重其事地写在“自传”中。在“自传”中还写到另外两件事:一是1656年,“因皇上所赐金印十分沉重,故令人仿制一颗使用,并撰写了新印颂辞及眉题”。二是1659年,“将皇上所赐金印中的汉文择要化简,仿制新印,以便于在长效土地文书上钤用”(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11页。)。从这两件事可进一步看到,五世达赖将清廷所赐金印视作藏传佛教领袖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不但在日常事务中予以使用,而且为了方便使用,进行了仿制和将汉文“择要化简”。此后,历世达赖喇嘛无论出行到何处,都随身携带着装有金册、金印的印匣,形影不离。行文全藏的重要命令、通告之类,习惯上也都是要钤用这颗大金印。则清顺治帝所颁的金册,即授于达赖以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和权利,又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兴隆佛化,……利济众生,……”。很明显,这些话决不是如达赖集团所讲的是什么“两国国君”“相互赞许”之词,也不是什么“两个国家”“如何共处”的内容,清帝与达赖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君臣关系,达赖的地位、权利是清廷所授。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都需经中央政府的册封,这成了一项制度。
(3)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册封及主政都须经清廷批准。由于西藏地方及各藏区僧俗势力集团的利益斗争,活佛转世这一本应是神圣、重要的宗教活动,成了一些势力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尤其是五世达赖被册封为藏传佛教领袖后,达赖活佛系统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社会影响空前扩大,因而在五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问题上,斗争更是尖锐、复杂。先是第巴桑结嘉措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拉藏汗当政后又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而拉萨三大寺及青海地方则立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各方互争真伪,相互争斗,闹得藏区各地僧俗上层矛盾尖锐,社会混乱。清廷中央不得不出面干预此事。而准噶尔部则利用此一时机,以推翻拉藏汗和迎请格桑嘉措为借口,发兵侵占了拉萨。1720年,清廷派出三路大军将准噶尔部驱逐出境,同时又将1719年认定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格桑嘉措带进西藏。至此,五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问题经过20多年终于解决。这一事件的处理显示了清朝中央政府在处理西藏地方重大问题中的权威地位和巨大的影响作用。此后,清廷总结了此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的管理。历辈达赖、班禅以及其他一些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册封及主政,都必须报经清廷批准。如八世达赖年近20岁时,应可以主政了,但清帝认为其主政尚早,起初没有批准。《藏内善后章程29条》颁布后,建立的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挚签制度,将决定达赖、班禅转世问题的大权,从西藏地方集中到了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显示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地位。
(4)达赖认真执行清帝的谕旨,完成清帝交办的任务。达赖喇嘛虽贵为藏传佛教领袖,以后又是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教领导人,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是皇帝的臣民,故又必须遵从清帝的谕旨办事。如:蒙古官员堪卓先后于汉藏百姓接壤之处挑起动乱,康熙皇帝敕谕五世达赖喇嘛,将堪卓撤职。达赖喇嘛自传中说,三月,“官员堪卓于汉藏百姓接壤处挑起不安定事件,皇上命我将其撤职,遵旨而行”(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24页。)。
(5)中央政府册封的重要意义。中国中央政府对藏区僧俗上层的册封,绝非仅仅是象征性的礼仪,更不是什么“福田与施主”象征性的关系,而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及各藏区僧俗上层政治地位高低、权利大小的依据。在西藏著名藏学专家编写的《西藏通史》中,专门用了相当篇幅引用了一份“座垫文书”(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19-622页。)。这份材料记述了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因官职、地位不同,因而所穿官服、佩带的首饰以及座垫高低也不同的情况。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只有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两派的后裔被列在首席,获得殊荣。这表明了他们得到我国元、明两朝历代皇帝赐给的封文、印信,曾经执掌过治理西藏地方的权利。同时也表明,虽然格鲁派事实上已登上统辖全藏的历史舞台,但是在这份详细的座垫文书中规定,噶举派的大喇嘛,如达隆寺活佛,黑、红帽噶玛巴活佛的座垫高于格鲁派甘丹寺法座的座垫。此外,主巴、岗布、楚布、仲巴、康地类鸟齐法王、止贡寺上师等的座垫与甘丹寺法座的座垫等高。这段材料清楚地表明,上述曾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册封、授权,统辖过全西藏的教派,始终享有较高的地位,即使清代时格鲁派教主达赖喇嘛已居于藏传佛教领袖地位,为政教的首领,但一些教派教主的座垫还是比甘丹寺主管的座垫高。
另外,从西藏地方僧俗首领所用朱印、黑印的区别,亦可看出中央王朝册封对他们来说的重要作用。“在西藏历来就存在着是否准许钤用朱印,主要是看是否得到过皇帝的封文的成规”(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木刻版),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译本),第640-641页。)。有的人,如第巴·桑结嘉措虽然已得到五世达赖的保证,宣布桑结嘉措的所做与五世达赖喇嘛的所为完全一样,因而一般来说,执行他钤用黑印的指示时,不需要比达赖喇嘛的命令更具权威的命令。但是,若要对其他教派的大人物也进行毫无争议的统治,则必须在文书中钤用朱印,而这须有中央皇帝的册封和金册、金印,否则只能使用黑色印信。
2.清代对西藏全面、有力、有效的治理
清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中国今天所有的民族地区,当时都已包括在清朝的版图中,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边疆的治理最为全面、有力、有效,国家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实施。虽然西方帝国主义从近代起开始侵略中国,一直妄想瓜分中国,但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流。
(1)设立专门的管理西藏、蒙古事务的机构。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理藩院。该机构前身是蒙古衙门,设立于1636年,专门处理蒙古族地区事务,1638改称理藩院,为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下属的典属、柔远两清吏司职掌西藏与蒙古的事务,治理非常具体而严密,对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以及官员的俸禄、赏赍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2)制定专门的管理章程。清廷中央根据治藏的经验教训,陆续制订了一些治藏章程,并不断完善。仅乾隆朝从1751年到1793年的短短的40年中便接连制订了四部重要的治藏法规。特别是在击退廓尔喀入侵后于1793年制定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因经乾隆皇帝批准,故又称《钦定西藏章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清朝中央已开始从法律上考虑如何制订一部全面的、规范的、权威的法规,使国家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得到更加直接、全面、有效的体现、行使和保证,既维护、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又使西藏能在封建法制的管理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钦定西藏章程》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治藏章程。作为一部治理民族地方的法律,可以说它更加完善、精确。这反映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清代中期已进一步明确、密切和深化,中央在藏主权的实施更加有力。第一,它从法律上明确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职权及相互关系。章程既注意维护达赖喇嘛在宗教方面的权威,礼仪上也给以特别的尊重,但在行政管辖上,则突出和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和权威。如第十条写道:“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务”。但紧接着强调指出:“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对扎什伦布寺的一切事务,因班禅年幼,章程规定仍由索布堪布负责,“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物,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此外,在其他各条中,还就重要官员的任免,包括噶伦缺额的递补,军务、边防、财政、税收、西藏币制、宗教管理和对外往来等,因为都关乎国家的主权、中央政府代表的权威,所以都明确规定必须禀明驻藏大臣衙门,其中许多事项都必须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协商办理。第二,以创立金瓶掣签制度为标志,全面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同时也有力地体现了国家在藏的主权、中央的权威,说明即使是位尊至黄教领袖的达赖、班禅,其转世灵童的选认、坐床以至成年后的主政,都需经中央政府的批准和册封。若要免于掣签,也需经驻藏大臣审视,然后上报中央批准。其他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册封,也需经此严格的手续。第三,严格了西藏地方的职官制度。《钦定西藏章程》就各级军政官员的选任条件、程序、赏罚等一一具体开列。特别是针对以往的弊端,明令不准达赖喇嘛等的亲属参预、干涉政务,并提出革除贵族上层垄断政界的措施。此外,对司法、财政、军事、边防、外事、边贸等亦列出专条,予以详细规定。如藏币的铸造就是根据清政府的批复进行的。1793年,经清帝同意铸造了刻有“乾隆宝藏”汉藏两种文字的银币。此后陆续铸造发行了有“嘉庆宝藏”、“道光宝藏”、宣统宝藏“等字样的藏币,和白银通用。这些藏币既是研究西藏地方当时经济情况的重要资料,又是西藏地方贯彻二十九条中关于货币问题规定的重要证据,同时也是西藏地方和中央关系的重要见证。总之,这部章程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中的影响非常重大,它使清朝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因此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西藏各族人民也从这时期的政治实践中认识到民族繁荣、发展、安危和祖国息息相关,从而增强了国家观念和与祖国各族人民的情谊。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两次发动侵略西藏地方的战争时,西藏地方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江孜保卫战突出地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反对外敌侵略、保卫边疆的爱国主义英雄精神。
(3)设立驻藏大臣,强化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原蒙古族各部落和蒙、藏上层间为争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相互间矛盾十分尖锐,影响了西藏的安定、边疆的安全。清朝中央一方面及时派兵入藏,平定内乱外患,如1718年、1720年两次派兵入藏驱逐准噶尔部落,1723年入藏平息罗卜藏丹津的叛乱,1727年处理阿尔布巴三噶伦的内讧,1790年击退廓尔喀的入侵,等等。另一方面,清朝中央也感到必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维护西藏的安定,保卫西南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在不断总结上述事件教训的过程中,先于1720年将准噶尔部落驱逐出西藏地方,彻底结束蒙古各部落对西藏地方的占领与统治,排除了蒙古各部落在西藏的争战和蒙藏上层间的争斗,扶持西藏本民族的领袖管理地方事务。以后又设四噶伦共管地方政务。1727年,针对阿尔布巴三噶伦内讧的教训,决定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清军三千分驻西藏各地,使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更加直接有力。西藏僧俗各界感谢中央屡次发兵挽救西藏地方于危难动乱之中,深切体会到祖国大家庭对边疆地方的有力保护,认识到西藏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近代史上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千百万人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达赖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却避开这一事实,提出什么国家在藏的主权要看中国中央政府贯彻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从总结近代史的教训,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从而鼓励人们加紧建设自己的国家,抵御外国的侵略,那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说没有实力就应该让出主权,交出主权,那这样的“新视角”,“新思维”就是赤裸裸地兜售“实力即主权”的谬论。谁有实力谁就有主权,这是多么荒谬的论调!所幸的是,世界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治家象他们那样这样去“新思维”,去“承认”“西藏是独立”的。我们相信,随着历史而去的将是早已遭人们唾弃的反华分子们的荒谬论调,面向未来的将是一个经过民主改革后40年发展的中国的新西藏!
标签:十三世达赖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明清论文; 元朝论文; 明实录论文; 藏传佛教论文; 五世达赖论文; 藏族论文; 拉萨论文; 专门史论文; 南宋论文; 唐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