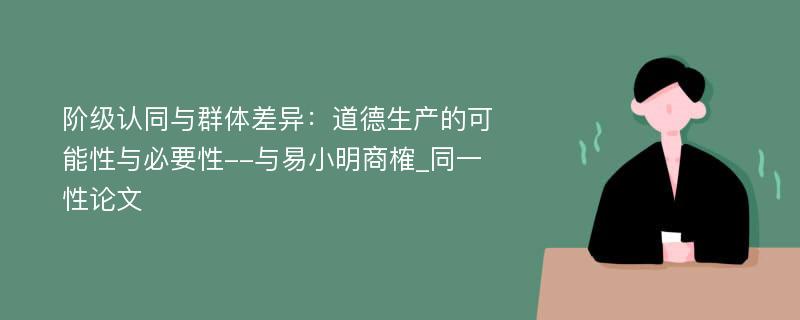
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道德产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兼与易小明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类同论文,差异性论文,必然性论文,可能性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1-0096-04
易小明教授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上的文章《类同一性: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认为,类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易教授从静态的角度考察了人类道德的起源,认为人类最初的生存状态是类的存在,类的存在经历了自发的类与自觉的类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体现出人的类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环绕着人类整体活动的三个阶段,即无意识的自发状态到有意识的自觉合作再到个体的充分发展的自由状态。这几个阶段的内核就是类的同一性,正是类同一性构成了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1]。我们认为,易教授对道德主体基础的思考为我们找到了道德何以可能的前提,人类之所以能够彼此交往是由于人具有类的同一性,具有相同的机理构造;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道德、践行道德、传播道德是因为人类为同一物种而非异类,在此我们完全认同类同一性在道德产生的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但我们认为类同一性仅仅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之一,类同一性使道德产生得以可能,但人类为何需要道德,即道德产生的必然性,不能仅仅停留在类同一性层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人类群体间的差异性来进一步说明,因此我们认为,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共同承担起人类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一、人类之初的两种生存样态:群聚与群居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首先是由数量上的“一个”发展起来的,“一个”就是一“类”,“一个人”在自然界用双足站立起的那一刻就是人“类”的诞生。这时的人类很难有群体与个体的划分,没有自觉与自律的意识,我们称之为“一个”人仅只是从数量上进行界定。但是,在无限广大的自然之间,面对无穷大的未知世界,“每个人”为了生存,为了不至于在凶猛的野兽与恶劣的环境下过早地消失,不得不在危机四伏的自然中战战兢兢地生活,但尽管如此,面对庞大的自然界,这种“个人”的力量太微乎其微了,因此,“个人”在生存过程中,一旦碰到了与自己差不多的“存在者”,一种本能的反应就促使“每个”人聚集在一起,这种状态便是最初的群聚。群聚并不掺和任何认识上的因子,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机体构造与心理反应,易小明教授在其文章中把此种原理称之为“同一——类聚”原则[1] (26—27)。相同的身体形态,相同的求生原理,是人类同一性最显著的表现,群聚就是人“类同一性”自发活动的结果。群聚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人类生存的能力,这种纯自发的行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着开拓性力量,同时,在漫长的历史中,类同一性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群聚在人类发展中具有始基性的贡献,它让人类本能地寻找到自己的同伴而“板结”在一起,又本能地繁衍出后代而扩大人类的队伍。现在,我们可以想像并合理地推论出,群聚状态在生成之初,应该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人类”的聚集,在距离一定的其他地方,另一些“人类”的群聚也照样存在,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同的群聚体一旦发生接触,就会具有两种走向,一种是不同的群聚体融合成更大的群聚,这样,群聚体的数目越来越大。另一种走向:如果群聚体各自都已形成稳定而牢固的关系,那么就很难融合,转而以一种交往的方式共存。
当群聚体开始变得稳定而牢固的时候,群体就开始逐渐超越本能而以一种有意识的形式生存。这种有意识的存在样态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群居。第一,稳定的群聚之间不再自发地融合成更大的群体。稳定的群聚至少具有牢固的关系基础与森严的等级秩序,在群聚内部之间,没有个人的概念,生产力极其低下,几乎没有人工的劳动产品,绝大部分依靠自然界本身的物质来维持生存,在物质的分配上绝对没有个人的发言权,一切绝对的平均。但领袖人物却可以享有特权,其他成员自然地听命于他。当这样的群聚体碰到另外的群聚体时,彼此就不会互相融合,要么通过战争征服,要么暂时和平。第二,群聚使人类的力量不断变得强大。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群聚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当群聚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为了分散太过密集的人口,必然需要拓展生存空间,以使得膨胀的群聚体顺利延续下去。这一过程会发生群聚体的分化,或者以血缘,或者以地域分化成不同的小群体,当群体开始出现时,群居取代群聚而成为现实的生存样态。在群聚时期,人类为了共同对付洪水猛兽的威胁而把自己与其他个体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意识是自然而然的,群聚体内部没有形成“你、我、他”的清晰概念,也就没有个体意识。同时,由于群聚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群聚体之间鲜少交往,即使有,也是自发的。到了群居时期,人的生存样态不再停留在纯自发的水平线上,而是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一飞跃逐渐打破了原有极其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差异性开始凸显出来,并且正是这种差异性促使群体间开始交往。
二、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在群聚与群居中形成
人类之初的两种生存样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两个阶段,群聚阶段是人类同一性的自发认同时期,这一时期,人类没有形成个人与群体的概念,而是一种本能的联结。群居阶段是人类群体差异性的感觉认识时期,它超越了群聚时期的本能无意识水平,而以一种初步的认识能力发现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尽管这种认识能力极其有限,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群聚时期,人类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切维持生命的物质都必须从大自然中索取,生产力极其低下,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有所作为的范围相当有限,谈不上自己有意识地创造劳动产品,没有认识能力,没有创造能力,一切只能依靠自然的给予,通过体力获得。这时的人类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人,人类因为相同的机体构造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划时代意义,但人类最初的劳动只是人的自然行为,并不是一个社会行为。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用第一块自己打磨的石头获取猎物的时候,它不会也无法运用理性的思维认为这是为自己或者为他人获得食物,更不会意识到这个创举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因为,这只是一个本能的行为。所以,人类之所以能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人类通过理性认识到与自己相同模样的存在者具有共同的机体结构,也不是通过判断得出人类是“同一类”存在者,群聚的形成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物以类聚”表达的就是一种本能下的类的聚合。换句话说,群聚状态下的人类是类同一性的自发认同,它是一种自然行为。其实我们可以更肯定地说,在群聚时期,人只是自然人,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然同一性。
群聚时期只有人类自然同一性,但自然同一性并不只存在于群聚时期,人类的自然同一性永远存在,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 毫无疑问,恩格斯说的“兽性”指的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类发展之初的群聚阶段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随着人类数量的扩大,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群聚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分化,逐渐走向群居,人类的社会属性随之出现并发挥作用,同时,人类之间的差异性也从同一性胎衣中破蛹而出。
在群聚时期,人类以自然同一性板结在一起,它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聚合,人类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随着群居的到来,人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群居是人类力量分化的结果。在群聚时期,人类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危机四伏的自然界,大家以一种本能的反应形成整体,自发地联合在一起去对付强大的猎物,在劳动过程中,自发地分工,同时,在群聚过程中,有力量的人开始成为领袖人物,其他力量较弱的人自然听命于他却没有丝毫不公的感觉。随着群聚队伍的扩大,有力量的个体越来越多,当力量在群聚内部发生矛盾时,力量就可能被分化,或者出现争斗,最终的结果要么是一方被另一方征服,要么是力量中的一方离开这一群体形成新的群体。群聚分离的结果,便是群居。其次,群居使人类意识到“人类”的差异性。在群聚时期,群体的行为、个体的行为都是自发的,在群体内部既没有形成个体的概念,也无法自觉意识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群体内部没有“这一个”,没有个人权利,一切都属于群体这一整体。当群聚被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即出现群居以后,抑或一群聚体与另一群聚体遇见后,群体间的差异性便开始显露出来。群体间的差异性被不同群体认识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最初是本能的感觉,然后是感性的认识,最后是下意识的排斥或认同。群体间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血缘关系的差异。形成群居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是不同血缘关系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在比较固定的地域形成相同的生活习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同血型、不同基因塑造出的个体性格迥异,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之间,这种因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群体便组成最稳定的形式。第二,地域的差异。我们可以推论,原始社会的人口数量稀少,并且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低下,应付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为了在凶险的环境下安全地生存,人类尽可能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生活。这样,群体之间定是“老死不相往来”,一旦群体之间碰面,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对方的陌生,并且,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群体间的差异性彰显出来。第三,生存方式与生存能力的差异。一方面,不同群体在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会使群体的生存能力拉开差距,这样,生存能力强的群体在遇见弱于自己的群体后,要么用武力征服,要么与之和平交往。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影响,高原与平原、水域与陆地上的群体的生存方式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异性以群体的样态表现出来,因为即使在群居阶段,仍没有形成个体的概念。
三、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道德产生的可能性基础与必然性基础
易教授认为,人类的自然同一性与社会共同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我们在此基础上认为,类同一性只是道德产生的可能性基础。易教授在其文章中已详细论述了类同一性在道德生成过程中的作用[1] (26—29),在此不再赘述,而仅对道德产生的另一主体基础进行阐述。
前文已论述,群聚与群居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两种生存样态,类同一性使人类自发地聚合在一起,这种聚合使人类在自然面前逐渐强大,生存能力得以提高。当这种模式在现实过程中越来越牢固时,群聚渐渐走向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血缘、感情、地域是群聚体中最坚固的纽带。当群聚飞跃到群居时,在群聚体中作为纽带的血缘、感情、地域等转而成为体现群居体之间的差异性标志,并且一旦群居体发生接触,这种标志必然在每个群居体内部不断被强化,差异性也随之显现出来:群体内部的亲情受到冲击、领地面临威胁、生存资源可能被分割。差异性于是集合成一种利益的形式,当利益成为群居体之间最尖锐的焦点时,群体间不得不以各种形式进行交往。
(一)群体差异性是群体进行交往的原动力。在人类之初,很难有个体的概念,个体完全融入到群体之中,群体就是单个人的简单集合,群体利益就是个体利益,因此,群体内部尽管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但都是一种自发的本能反应,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并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秩序合不合理。所以,在一个群体内部,不存在“我—他”的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出现在群体之间。在上文中,我们已论证了群体差异性的特征,不同的群体一旦遇见,彼此的差异性就彰显出来,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群体间认识到彼此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感情的认同、地域的占领、资源的垄断上表现尤为突出,每个群体基于生存的需要与本能的占有欲,使得这些差异性转换为一种利益并成为争夺的焦点。这种利益首先表现在物质财富的拥有上,借此来维持本群体的生存与延续。为了生存和延续下去,群体间往往会首先选择简单而快捷的暴力方式,这种武力交往方式的结果或者一方被征服,或者实力相当而短暂共处。无论结果如何,武力的方式必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群体差异性也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更加凸显,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交往。
(二)群体差异性是道德产生的必然性基础。群体之间的交往建立在每个群体自身需要的基础之上,这种需要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人口、领土等其他资料,这些需要是群体间差异性的集中表现。群体间的交往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自发交往,它是一种自发行为。自发交往是一种简单的交往行为,交往频率不高,交往的次数不多,交往的方式简单。其次,在自发交往之后走向自觉交往。一旦长时间的自发交往后,群体间开始认识到,这种交往行为不仅有助于本群体的生存,而且可以缓解生存压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群体之间开始寻求一种更广泛和各自都能接受的交往方式,这时,群体间的交往便变成自觉行为。各群体为了交往行为的顺利与安全,彼此努力寻求一种可以保证交往行为正常有序发展下去的约束规则,这种约束规则就是道德,道德的产生是群体间自觉意识的产物,群体差异性使道德产生成为必然。第一,群体的自然差异促使道德的产生。人口规模和地域环境的不同,各群体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在量和质上呈现差异,这种差异要维持平衡,需要道德的保障,以使得本群体拥有不受干扰的领地,享有本群体独占的环境资源。第二,群体的社会差异促使道德的产生。群体之间的交往集中表现在利益的交换上,这种交换行为应该是相互的,并且是自愿的,除此以外,语言、风俗需要得到彼此的尊重。群体的这两种属性使道德的产生成为必然,因为有差异,才需要交往,为了更好地交往,必然需要道德。
(三)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共同构成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类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可能性基础,类的自然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使道德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类同一性是人类能够交往的前提,它提供了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平台。在自然同一性中,人类具有共同的身体结构,相近的心理机制,相似的物质需要,在社会同一性中,人类有着同样的感情欲求,需要他人的社会认同,这两种属性使人类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种”,人类才能进行交往,人与人沟通而不能与其他动物沟通,正是基于如此的原因。但仅仅具有类的同一性,而无群体的差异性,道德也无法产生,因为如果不存在差异,或者人类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又或者即使人类意识到这种差异却又无须有所作为,那么,道德也就不再必要。因此,从起源上看,道德必须是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互补会一直贯穿于道德之始终。从历史上看,道德的最初主体是群体,但随着人类的发展,道德主体会从群体主体走向个体主体再走向类主体,最终走向三种主体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