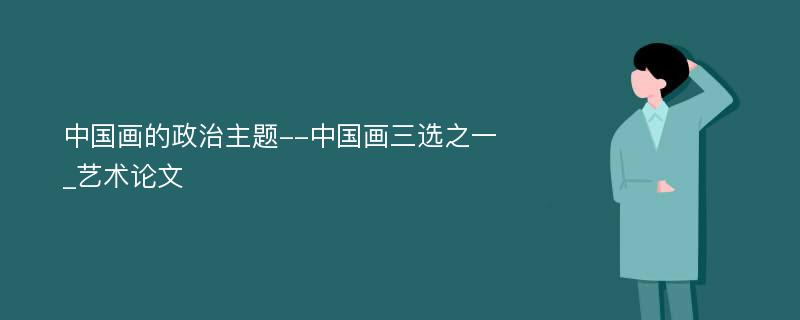
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三种论文,政治论文,主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当我们想到“政治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艺术家自己在作品中表达经常是批评或抗议的政治观点。这种情况在中国并非完全无人知晓,但是西方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相比则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观念更加适用于赞助人的地位和兴趣——广义上的“赞助人”可以理解为作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此处指的是对中国绘画的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改变目前总是落实在艺术家的个人处境,或者将作品仅仅看作是艺术家人格表现的那种研究方法。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的大部分绘画作品,它们在过去基本上都不是作为审美对象或个人感情的表现而创作出来的,相反,却有着更为具体的动机和作用。它们可能被当作礼品赠与他人,作为换取政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恩惠的回报,或期待着得到这些恩惠,或者作为贿赂物品而不必直接支付现金了,在某些特定场合,比如某个官员离家就任新的职位,它们可能会被悬挂厅堂或送与他人。
根据这样的作用和场合以及绘画作品的赞助人或接受者的地位,画家确定适合描绘的某些特定的主题。有些作品表现了当前的实际情况,比如宋代郑侠画的《流民图》(下文有讨论),绘京城遭受饥荒之苦的灾民。但是其表现手法更多的是象征或暗示。出自历史或传说的人物和事件的图像,以“故实”而为人所知的题材,这些都被认为适合于反映当时的情况。这是暗示性的题材,这种手法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在继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几十年绘画中能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并不那么公开、明显,也不引人注目,但却被知识分子看作涉及当前的问题并经常以间接的方式作出评价。
要对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进行分类,我们可以从几项大的区分开始。绘画作品所面对的那些情况可能就是整个政府的情况,比如宫廷中的绘画作品,或受宫廷委托创作的作品,或者是在政府部门供职的文人官僚的作品。第一种类型的主题与整个政府相关,要么带有支持或使皇权统治合法化的正面讯息,要么带有批评或抗议的负面讯息。不管目的是什么,这些画作以多种多样的视觉修辞手段使观赏者形成某种观点:皇家宫廷的艺术通常是用来使观者相信统治者的德行及其统治的稳固和繁荣。而文人官僚创作或委托创作的绘画一般旨在使观者和他们自己相信他们高度发达的智慧,他们的德行,他们对于现世事功和物质利益的冷漠,以及通过这些相信他们忠于职守。在这样的时候,即他们认为帝国治理得非常糟糕或者受到统治者的不公正待遇,或统治者不听其言,他们的绘画才有可能成为抗议的艺术。但是这种抗议通常一定是极为细微、甚至是隐晦的。
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两幅画都通过描绘开明统治的恩典来歌颂统治者,它们是流传至今的两幅精美的画作。细节描绘精微,技术方法多样,画家的技巧和极度费时费工的构思绘制,这些都是绘画作品的部分讯息,由此显示出一种统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培育并造就了宫廷艺术的这些品质。传为五代画家卫贤所作的一幅画,其年代也许是宋代早期。图中画的是一个面粉场,以水轮为动力,建在运河中的一道水闸上。关于这幅画,上海博物馆(收藏单位)的郑为有过讨论。他认为这是赞扬政府在政治动荡时期,对于工业技术和水力的资助,在此一时期这样的经济支持能够带来很大利益(注:郑为《闸口盘车图卷》(该手卷再现了运河水闸上的一处水车),《文物》第二期(1966年),第17-25页。)。另一幅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北宋晚期平安统治之下的开封都城;实则可能是南宋初期,北方都城已经弃与入侵的金人,金国某个宫廷画家出于思乡而绘成的。
另一个题材就是小商贩,宫廷画家有时画这种题材,宫廷圈子以外的画家很少画(宫廷风格的精良摹本则除外)。这种题材与描绘建筑的界画紧密相关。现存最好的例子就是南宋画家李嵩的作品,他也常作界画。另外,就是活跃在明朝画院的吕文英,也许还有(根据风格确定)供职元朝宫廷的王振鹏(注:弗利尔美术馆11.16e;见高居翰《中国册页画》(华盛顿,1961年),第22页,该书附注中定为王振鹏所作。James Cahill,Chinese Album Leaves( Washington,D.C.,1961) ,22.)。有人认为这种主题是仁慈统治的另一个暗喻,其中的小商贩表现的就是皇帝自己,“乾坤一担”,将繁荣带给普通民众。(注:这个观点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杨新1983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班上提出的。杨新还要在即将举办的中国风俗画展览的目录中讨论这个问题及相关题材的意义。)
外国使者来到宫廷直接向中国皇帝纳贡或携带珍贵物品作为贡品,经常有宫廷画家把这些画入作品。在中外关系中,这些画用来维护中国的权威和声望。有两件现存作品,据传为初唐宫廷画家阎立本所作,那时中国完成了对亚洲大部地区的控制,这一巨大成就在这两件作品中都有称颂,其中之一画的是初唐皇帝太宗接待吐蕃使者。两者之间的相对尺寸——太宗端坐辇上,周围是媚态各异的侍女,在构图上被两把羽葆和华盖围住,而那位吐蕃使者孤单地站着,卑躬谦顺,前面是一大片空地——使这看上去更像是表现一种政治观念而不是记录一个历史事件(注:另外还有一幅职贡图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据传为阎立本作,画的是西域胡人纳贡。《故宫名画三百种》第一卷(台中,1959年)第1页。)。
特殊的历史境况产生特殊的要求,艺术家便对此作出反应。有许多个案便是南宋早期即公元十二世纪的(朱利亚·穆雷的著作便是此类最精到的研究之一)(注:朱利亚·穆雷《作为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宋高宗:王朝中兴的主题》(为“艺术家与赞助人”研讨会而作的论文,见其导言注(1))。《南宋王朝中兴中艺术的作用》、《宋元研究集刊》第18辑(1986年)第41-59页。Julia Murray," Sung Kao-tsung as Aritist and Patron:The Theme of Dynastic Revival" ( Paper for" Arists and Patrons" workshop,see Intro.Note I) ." Ts Hsün and Two Southem Sung History Scrolls," Ars Orientalis 15( 1985) :1-29." The Role of Art in Southem Sung Dynastic Revival." Bulletin of Sung Yüan Studies,no.18( 1986) ,41-59.),这时有一系列宫廷绘画是关于宋朝中兴与合法性内容的。在金人军队1127年攻取宋朝都城汴梁并囚禁徽宗皇帝及其皇族成员之后,徽宗皇帝第九子赵构逃到南方,于1138年在杭州建立朝廷,继续统治南部半壁江山,这就是高宗皇帝。他必须使他将要统治的臣民相信,复兴的南宋朝廷是合法的,从而和北方宣称有权统治全部中国的金朝相抗衡。高宗实现南宋新朝廷合法化的一部分计划似乎就是委托或资助一系列维护他这一边统治的绘画作品。这一类绘画中有些作品上有高宗亲笔写下的题记。其首要宫廷画家李唐就画了一幅有名的历史画《采薇图》。图中伯夷、叔齐两兄弟在周朝建立之初,宁愿饿死也绝不改变其对前朝的忠心,也不为新的统治者效力。这位周王有过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不哀悼亡父,又犯了弑君之罪。这幅画便表达了忠贞不渝这个观念。据后面一条跋文,这张画的意图就是批评那些转而忠于金朝的汉人。
还是同一个画家李唐,他还画有《晋文公复国图》长卷,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公是东周时期的一个国王,是晋显公第九子,他失去王位后,流亡各地,有时还和“野蛮人”相伴为生,后来回到自己的国家,恢复其世袭统治。他的处境因而和高宗有些类似,是皇太后给高宗指出这种类似之处的,而且催促他登上皇帝宝座。因此,这幅画表现的主题是王朝复兴,其中含义就是高宗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题材方面而且表现在风格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用了古代风格样式,令人想起初唐,高宗正是意欲将他的统治和初唐时期的强大王权相提并论。手卷的形式也是古风的,这让人忆起早先的长卷画,文字在前,画面作为图解在后(注:在写有关这一点及南宋王朝中兴的其他主题的时候,我参考了穆雷的著述及弗洛拉·傅的研究论文,这是为我1985年春季主持的“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研讨班而作的,傅的论文《作为政治话语的风格选择:〈晋文公复国图卷〉》探讨了这些绘画及其题材中风格的政治意义,很有见地。)。
同样是这种形式的一个手卷,据传是李唐弟子萧照画的《中兴瑞应图》,现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此卷共有十二段,从高宗出世直到登基坐殿之前。这个手卷意在向世人宣称上苍将瑞兆传给高宗并将皇位也传与他,而且可能是在皇上退位之后为了纪念而画出来的(注:关于这组绘画的摹仿本,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画选集》(北京,1963年)图1-6,及谢稚柳编《唐五代宋元名集》(上海,1957年)图65-81。" Ts' ao Hsün" ( note 5) 。)。
《望贤迎驾图》立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无款。从画风看,似乎出自一位十二世纪晚期或十三世纪早期宫廷画院的画家之手,如刘松年或者李嵩。这幅画也可以归于南宋有关中兴主题的宫廷绘画之列。按照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的观点,画的是唐玄宗避乱四川之后重又回到都城长安、其子迎驾之事(注:见沈之瑜编《上海博物馆》,纽约,1981年,图120及注释,第22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先生已经针对其中描绘的场景作出解释,可供考虑。按他的看法,此画表现了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带着他年迈的父亲到其出生地,这里的人有些已迁居京城,他太虚弱了,无法巡游各处。见李霖灿《宋人〈望贤迎驾图〉》收入《中国名画研究》,台北,1973年,第103-106页。)。
这些绘画作品(如果篇幅允许还可讨论其他几件作品)形成完整的一组,其意义和目的及其与当时历史情况的关系相对来说都是清楚的。另外有一些画就不那么清楚,但是与政治主题仍有关联。这包括马和之画、高宗题写的《毛诗图》手卷系列,朱利亚·穆雷和其他学者曾对此作过研究(注:朱利亚·穆雷《宋高宗、马和之与〈毛诗图〉卷:〈诗经〉图解》(博士论文,普林斯顿,1981年)。Julia Murray,Sung Kao-tsung,Ma Ho-chih,and the Mao Shih Scrolls:Illustr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Ph.D.diss.,Princeton,1981) .);还有《耕织图》,原有写农耕和养蚕或丝织业的诗歌,这是图解(注:最早的到目前也是基本的《耕织图》研究是伯希和写的" A Propos de Keng tche t' ou" ,Memoies concernant l' Asie orientale 1(1913):65-122。对于后来各种本子的简短讨论,见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四卷,《机械工程》第166-169页。Joseph Needham et.al.,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4 pt.2,Mechanical Engineering,166-169.)。
后者,也就是《耕织图》,有许多不同本子,如果我们看看文献记载,就会发现这些画并不是艺术家们偶然被题材吸引、随意画出来的,而是遵循着一种图式,一点也不含糊。记载中最早的本子是一个名叫楼?的官员画的,他在南宋都城杭州附近的一个地方任职。他把画作进献给高宗,再将模本送给别人。后来在1210年,这些画经刻石拓片,传播更广。另外有一些文献记载及现存的本子,有的是十二世纪晚期宫廷画家刘松年画的,有的出自蒙元初期供奉朝廷的宫廷画家之手,有的属于满清初年宫廷画家的名下。那么,这些绘画创作背后可能存在着什么动力呢?
农耕与纺织都是农民的职业,两者都需经过数月作业工序才可完成。因为它们能在固定的条件下完成,所以体现了汉人稳定的农业社会的理想,这和游牧民族更为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恰成对比。对于高宗来说,这些绘画作品都是为了维护其相对于金朝而言的英明的政治统治。金人虽然采取汉人的统治方式,但仍有游牧背景,因而能否承担农民的利益颇可怀疑。高宗在采用这些视觉修辞手段时就像是一个政客,农民要求遵守古老、稳定和保守的价值观念,同时指控其政敌(此处指金国统治者——译者)不理解农民所关心的事情。
高宗时期完整的本子早已无存,但是其构图可能保存在摹本和残本之中。我们现有的最早的一套完整组图似乎是一个元初画家所作(注:关于这个本子,旧题刘松年,见托玛斯·劳顿《中国人物画》(华盛顿,1973年),第54-57页。Thoma Lawton,Chinese Figure Painting( Washington.D.C.,1973) ,54-57。梁楷的一个残本藏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见《八代遗珍》图61,附何惠鑑撰写短文。最近黑龙江博物馆获赠一本,文章见《文物》第10期(1984年)。)。元初时期的蒙古人曾经努力让汉人相信他们才是中国的正当的统治者,支持汉人农业及其他职业,因而他们资助画一套《耕织图》用以维护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据记载,元仁宗有上千件临摹本,均有赵孟頫题诗,1318年曾刻印并发行(注:写到这些不同的《耕织图》本子,我受惠于玛丽昂·李(Marion Lee)为我1985年主持的研讨班作的研究论文(见注[6])。)。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就像女真人一样,也将被怀疑不能充分理解一个稳定社会的要求。
满清也是如此。满人也是游牧民族,后来汉化了,但是(从汉人的观点看)仍然不够。康熙帝有一个新的《耕织图》系列,是宫廷画家焦秉贞所绘,1696年木版刻印。还有一组《耕织图》于1796年乾隆帝发行。这两组《耕织图》刻印时,反抗满人的战争已经结束,帝国皇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统治并使其合法化——皇家资助绘制此类图画并大规模复制传布,这个目的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画持续不断地反复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虽然我们过去曾经是游牧民族,但是现在我们同样能够理解汉人的需求,并且已经对国家施行稳定而仁慈的管理。
当然,这样的讯息也可以用文字表达,而且确实已经用文字表达了。那么,为什么画这类题材的作品那么重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价值中去找,中国人很早就将这些价值表现在绘画形象之中了。中国有些早期绘画文献表达了儒家说教和道德化的观点,绘画作品体现了道德真理并将其传递给观众,就像人们相信宗教神像体现诸神的力量一样。类似地,一张画某种题材和场景的好画传递了某种政治讯息,又将此讯息客观化,并赋予其具体化了的真理的地位,这是长治久安的威力。此画可以向要人展示,也可以复制,复制品作为官方礼品赠送他人。这样的绘画可能旨在让人们相信某种主张,这一点在上述例证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但是也可能用来在志趣相投的人中间传达双方共同持有的观点,这一点在下面将要探讨。文人官僚阶层成员作画或委托别人作画送给同一阶层的人。这些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人职务地位和对荣誉的认可。就像今天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受众中表现某种特别的政治信念一样,这些画旨在表明共同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画要使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相信某种政治主张,那就离题了。绘画可以赋予某种艺术实践以古典作品的权威地位,其方式是用以描绘的图像让人忆起与其类似古代作品,它们可能会赋予某项具体的、时代确定的事件以一种普遍性,这是以一种成熟风格画出来的,有时是用含有这种意义的山水景观画出来的。下一章,我们将举出一个例子(王绂的《北京八景图》),一个个画面及题诗有助于形成一种弥漫全城的文化氛围,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北京更加适合做帝国的都城。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所有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支持国家的权威,这些艺术家——或者至少是最早本子的作者,都供职于帝国宫廷,或将画当作礼品赠送给统治者,这一点绝非偶然。对比一下,宫廷圈子以外的绘画可能带有不满或抗议的讯息——这经常是被遮蔽的,因为过于直接的抗议会给抗议者带来惩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流民图》(注:这里我又一次受惠于玛丽昂·李为1985年研讨班所作的论文《论赞成和反对统治者或国家的绘画》。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与我们目前的关注点无关紧要),关于郑侠的《耕织图》原本和其他个例,文献记载中有官员“曾画”过一幅精致的画。那么,这是他亲手所绘还是别的某个画家的代笔,是他自己作出具体指导画出的还是根据他作的稿本画出来的。)。这是一个名叫郑侠的官员于1074年画的,画的是开封安上门饥民,他们都是一次饥荒的牺牲品。郑侠指责这都是由于宰相王安石的政策引起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郑侠原来是王安石的门生,但是后来反对他的改革措施,向王安石提交了好几份请愿书均未被重视,他就将这幅画秘密呈送给神宗皇帝。据记载,神宗于是命令暂时停止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这幅画可能因为是政治敏感题材,在后代没有流传,甚至连摹仿本也没有。《清明上河图》中有的部分可以给人类似于郑侠画中的大概感受,尽管所描绘的境况和郑侠作品相比刚好相反。郑侠的画近些年在中国讨论很多,有各种解释。当王安石的改革被认为是政治进步时,比如“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横行时期,这幅画就被判定为反动的;近年来,关于其意图和结果,人们逐渐有可能作出更为积极正面的评价。
另一幅《流民图》原为册页,后裱为手卷,画大路上的乞丐和穷人,周臣作于1516年。他在题文中含糊其辞地写道,他意在用此图“警厉世俗”(注:《江岸送别》第191-193页有这幅画的讨论,跋文有英译。另见《八代遗珍》图160。Eight Dynasties,no.160.)。当时文人写在此卷上的题跋将其比作郑侠的《流民图》,并推测其目的。有一则跋文认为作此画目的是批评阉党的影响,正是他们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
这种“抗议的艺术”在中国并不多见。有些情况是遗民静悄悄地抗议,当他们所效忠的朝代灭亡时,这样做就是以一种微妙的象征方式表达他们对新朝廷的对抗,比如元初和清初的许多作品。元代有两个例子众所周知,郑思肖作于1306年的《墨兰图》,墨兰的谦卑之姿是荒野中无人问津的高洁之士的一种隐喻;另一个是龚开的瘦马,象征着汉人所处的悲惨境遇。他们二人都是遗民,依然忠于故宋,和异族统治的元朝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但是比龚开稍晚的任仁发《二马图》,虽然瘦马与龚氏作品中的形象相同,但内含的意义则刚好相反;对于任仁发来说,瘦马表现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任职的官员(如任仁发自己),为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而“瘠一身”。意义并不总是附着于形象;艺术家可以将其用来达到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目的(注:我的《隔江山色》中这三幅画均有影印和讨论,见此书图版1、2和72,第16-18页及第155-156页。关于元代绘画中马的形象与政治的联系,谢柏轲已经做过研究,见其精彩论文" In Praise of Government:Chao Yung' s Painting Noble Steeds and Late Yüan Politics" 最初发表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4年4月举办的“中国绘画的政治主题与功能”的区域研讨会,后来刊印在《亚洲艺术》第46卷第3期(1985年)第159-202页。)。
至此,我们已经转向了政治绘画的另一种范畴:即文人官僚阶层所作的或别人为其而作的绘画作品。这类题材及其意义必须在与这些人生活中最关心的事物的关系之中才可以理解:通过考试和任命制度获得官职;职位晋升,取得理想的位置;知道“何时为进何时为退”,即何时追求官职何时卸任隐退;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取宫廷中的高官甚至皇帝的恩赐。
早在汉朝,就有一套制度化的信仰和实践,其基础是有关高士和隐居官员的理想化记述。根据这种制度,统治者应该设法吸收进入政府的最好的建议者和管理者正是那些真正倾向于退出社会的隐士。真有做官野心的人有时会养成隐士的名声,目的是使自己有更多的升职机会;担心自己统治威信的当权者在士人看来也会下令寻访并使用那些有德行的隐士。马丁·鲍华石最近几篇文章论证令人信服,汉代有些艺术在风格和技术上清晰朴素,比如公元二世纪山东武氏祠的丧葬浮雕,应该被理解为维护赞助人所声称的儒家朴实含蓄的德行的观点,赞助人家族物质财富并不那么殷实,但仕进为官颇有雄心。他们认为凭其学问修养与道德力量堪当此任。鲍华石比较了汉代这种艺术与为世袭贵族而制作的更豪华的那种,贵族认为政治权力应该是华贵与财富的标志,与德行和学问无关。这样的艺术材料昂贵,技艺精巧,设计复杂,费时费工,其传达的讯息和武氏家族的信仰刚好相反,炫耀赞助人的经济力量和贵族趣味(注:鲍华石《中国早期绘画艺术与公众》,《艺术史》第7卷第2期(1984年6月)第135-163页;《中国西汉的艺术趣味、经济和社会秩序》、《艺术史》第9卷第3期(1986年9月)第285-305页;《武氏祠的隐退和聘用主题》(“中国绘画的政治主题与功能”区域研讨会论文,见注[15]);《中国早期奢侈之风及其批评者》(1985年春季论文)。)。
后来各朝代,政府的服务制度逐渐变得高度发达和复杂化。在诗歌和绘画作品中,一直都有隐士的神话。尽管这种神话在当时理想多于现实,但是对这一题材的表现仍是多方面的。这种题材的绘画,其典型的画法是画隐士被统治者的使者或统治者自己聘任宫廷,作者大都是都城里的宫廷艺术家和高官赞助的艺术家(注:Chu-yu Scarlett Jang,The Hermit-Theme Painting in the Painting Academy of the Ming Dynasty( M.A.th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4) .)。他们在明代初年特别受欢迎,那时的历史状况是新朝代建立不久,开国皇帝朱元璋并不信任有教养的士夫精英,并且加以残害。在此之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皇帝特别关心的事就是吸引杰出人士进入其管理系统。将这些人比作过去的隐士,以此向他们表示赞赏,他们走出隐退的状态,去为有德行的统治者效劳,这在政治上是极为明智的。因为,这反映了对皇帝的称颂,并使人们对君臣关系有了一种理想化的认识。
如有人职务调动或升迁,或者隐退,也会将这种题材的绘画悬挂起来。宫廷绘画除了简单的艺术家名款通常不加题文,可能是因为绘画直接面对的观众清楚地知道这种题材的含义,乐于充当一名鉴赏家,无需说明。因此,要重建绘画的意义和功用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在一些官员的著作和艺术家及其他人的题记中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蒋朱玉(音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颇费精神,她收集到的材料证明绘画的主题跟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情境和制度密切相关。有这样一个例子,明代画家戴进画了一张《李树读易图》,目的是纪念一个官员升迁赴贵州就任高职。这一幅画一定是属于“隐居”的范畴,下一章再予讨论。这一类绘画的一般意义是:画中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是个隐士,只有摆脱责任才能进入公共生活。但是这里的讯息更为具体:按照另一位高官所写的跋文,这位监察官因为勤于研究《易经》而引起上级官僚的注意;现在他要将平和与稳定带给贵州人民,如同春雨带给大地新生。那么,画中的李树代表春天(注:Jang,48-49.)。还有一个例子,唐寅曾为一个高官画隐士,这个隐士虽然和囚犯一起终日劳作,但仍以其德行受到皇帝的认可和赏识,被聘至宫中担任宰相。唐寅在题记中评论说,假如皇上平时不默默地从精神上理解隐士,这个隐士可能永远也不会在那么多囚犯中被他辨认出来。这里带有奉承的意思,暗示此画接受者和皇上之间的类似关系(注:Jang,50-51.)。
表现陶渊明的绘画典型的也是出自宫廷艺术家之手,如宋代的梁楷,元初何澄,明代初年的李在,等等。这些画有着类似的意义和功能(注:《归庄图》何澄手卷,画陶渊明《归去来辞》诗意,现藏吉林省博物馆,见《艺苑掇英》第6期(1979年),图1-4。关于李在、马轼、夏芷于1424年以陶诗为题材画的一组画,见《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第2册(北京,1962年),图11-13。)。众所周知,陶渊明是公元四世纪的诗人,退出官职后隐居在乡村庄园,所写之诗反映了闲适的隐士生活。描绘陶渊明及其《归去来辞》的绘画不仅适用于真正的隐士或者那些放弃官职、选择隐退的人,也可用来恭维身处要职的人,暗示他在精神上真的像陶渊明,本质上是个隐士,没有仕进的野心,也不追逐私利。“朝隐”这个概念和“市隐”一样允许人们在原则上保持隐士的精神境界,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意义和功能与此相关的还有画渔父和樵夫的作品,这相当于欧洲的牧羊人形象;这些都是朴素生活的理想化,贴近自然,未被城市污染或宫廷阴谋损坏。就像欧洲的侍臣可能会梦见自己变成田园世界中的牧羊人,中国的官员可能梦见自己是岸边的渔夫,那么平静安逸,这个主题在下一章将用较大篇幅加以讨论。
牧牛题材的绘画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政治意义(注:Chu-yü Scarlett Jang." Ox-Herding Painting in the Sung Dynasty" ( inpress) .)。这些画表现的是乡村田园中牧人的朴素生活,可能会赠给退休回家的人,含义是:现在你们就要过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了,就像牧人一样。或许,也可能是为仁慈的管理机构作的图画隐喻。弗利尔美术馆有一幅这类题材的手卷,上有明代一位官员题诗,说将其送给另一个即将出任地方长官的官员。诗中还暗示他将会关爱其地区的人民,如同牧人关心牛群(注:弗利尔美术馆26.1,未发表。后有1449年跋文,言及此画主人将赴京任职之时,父亲将此画赠与他,并忠告:看到这幅画就会理解牧牛的深刻意义。也就是说,关心普通人民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就是这幅画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山水画同样可能含有这种讯息。甚至是植物题材和花鸟画也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画一条鲤鱼向上翻跃——如极为流行的谚语“鲤鱼跳龙门”——就是表现文人通过考试力争为官。这种绘画大量出现,其中有些出自宫廷画院艺术家之手,它们作为吉祥图像送人或悬挂、张贴,用以祝福官运亨通,前程远大。画蜜蜂和猴子的作品也含有同样的意思,通过谐音,“蜂猴”音同“封侯”,引申义便是“封官”。画猴骑马,“马上侯”,这也是谐音,意思就是“马上”,即一刻也不耽误,马上封官加爵(注:有宫廷画师画的鲤鱼颇为典型,见《八代遗珍》图129。无款蜂猴图现藏天津市博物馆,未发表;程十发曾向我解释其意义。目前所知还有几幅画马上猴的,如传为赵雍画的册页中有一幅,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遗129.Sogen meigashu( Tokyo,1930) 。 )。
关于植物题材绘画的政治意义,有一个例子,即陶成画的手卷。陶成是十五世纪晚期的艺术家,活跃于京城,这幅画绘于1480年代。陶成不是宫廷画家,也不是职业艺术家。了在这里采用了业余文人艺术家的风格,自己也是一个文人。手卷上有当时十六位文人题诗,他们有些还是翰林院的学士。尽管画上没有说明是献给谁的,但可以推测可能是送给某位高官的礼物。像菊花和蔬菜这样的绘画题材,如果不懂得这些母题的政治含义,则看上去似乎是奇怪的组合。菊花与陶渊明有关,他养菊,爱菊。与奢华的生活相对立,蔬菜代表简朴的生活,代表这样一种观念,即使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人,每天饭菜丰盛、鱼肉不断,也应该熟知穷人的生存状况,这样才能仁慈地统治他们,减轻他们的苦难。黄庭坚写的两行有名的诗句,原是一件蔬菜题材绘画作品的题诗(注:关于这一题材的研究论文见Dajuin Yao," Vegetables and Other Edibles in Yangzhou Painting".),所以陶成这张画含有对某位同僚的劝告:节制仕进之心,保持隐士心境,就像陶渊明那样;不要脱离穷人。或许,我们应该将这幅画理解为称赞此人已经具备了这些德行。
植物题材可能以多种象征方式表达政治意义;当我们细审大量存世绘画,精读其题跋,就会发现许多这类例子,能够编纂一部象征语汇汇编。十七世纪早期专门画竹的画家朱鹭,他有一幅画上有两根竹子,用以祝贺两位兄弟刚刚考中进士,即将赴任。竹子象征积极向上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在植物——或人——的天地里,宁折不弯这种品质可能被当作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理想而广为天气称颂。十八世纪前期的高凤翰曾画过一幅牡丹。长期以来牡丹一直象征着富贵,祝贺某人升官,因而更接近仕进的目标。其他还有上千件作品和这两幅画看上去没有多少不同,只有题跋能揭示原先语境中含有的政治讯息。那么,即使题跋不那么明确,我们也可以假设,大量相互类似的绘画作品都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和目的而画的(注:关于Chu Lu绘画作品及其题跋的解读,我受惠于相关一个的条目,见Kiyohiko Munakata in The Communion of Scholars:Chinese Art at Yale( New York,1982) ,114-116。高凤翰的这幅画是我的学生Ju-hyung Rhi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三个例子,通过题跋能说明通常非政治题材是如何被赋予政治意义的,如何适用于某种政治功能的。日本京都大德寺藏有牧豀1269年画龙虎的对幅,上有画家四字题文:“虎哮、风嚎”“龙起云涌”。詹姆斯·罗宾逊在《优美与宁静:艾莉·李莉的中国艺术收藏》(印第安纳波利斯,1983年),第296-297页。其中曾作出解释,这两个短句来自公元前一世纪的Wang Pao。罗宾逊指出从此题字可以看到“也许最好是从更多的儒家和/或政策意义上来看待这两张画。”——那就是说,不承认这种题材的道家或禅宗的含义。第二个例子陈洪绶的一幅画,上有三个佛教人物。如没有题文,就会仅仅被当一件宗教作品送给某个寺庙或信徒;但是艺术家的题文告诉我们,这更有可能是为某位官员画的。见《晚期五画家作品特展》,卷129,第95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三个例子是方闻在论文《元代绘画中的语词与图像》中讨论过的,该论文发表于1984年10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研讨会。他论证说,钱选画的梨花图并非真的只是画梨花而已,而是画他对宋朝灭亡的深沉的悲伤之情。此画原为珀西沃尔·大卫的藏品,现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方闻还在论文《诗书画:“三绝”》中对朱耷的花鸟画进行政治解读。该论文发表于1985年5月20日-22日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语词与图像:中国诗·书画”研讨会。)。
明代宫廷艺术家殷宏曾画过一幅有山水背景的花鸟大画,即《百鸟朝凤图》。在这里,凤就表示皇帝,“百鸟”则是宫廷大小官员。因而这幅画是宫廷等级关系的寓意,皇帝在中间,周围是百官。其风格和陶成的画大不相同;宫廷画师的风格取代了文人画家的,宋代的风格取代了元代的。风格的区分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政治含义,这和绘画的题材是一样的。殷宏与明代其他宫廷画家熟练地运用宋代画院画法,明朝宫廷早先曾通过官方公文或默契的方式作出决定,即这种风格最适合明朝宫廷圈子的欣赏趣味和相关境况,殷宏等画家这样做是对这个决定的响应。除了它本身固有的耀眼的魅力之外,它还越过外族即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将明代皇室的权威和同样是汉人朝廷的宋朝联系了起来。当然,元朝已经越过南宋选择绘画风格,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多见。画家们将南宋风格和政治弱势及当时的宫廷没落联系了起来,这是他们所亲眼目睹的。在文人官僚画家和在元代宫廷供职的艺术家当中,他们倾向唐及北宋画风,政治上的考虑当然起到重要作用。在清朝宫廷,风格也起到重要的政治作用。那时,清廷在画院支持正统的山水画风格。在当时画坛,这种风格就象征着中国悠久传统中的合法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等诸种价值。满人在巩固其统治的阶段,认为这些价值都属于他们自己及其朝廷的(注:我想是俞剑华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他认为清帝支持宫廷画院的正统山水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合法化的策略。见俞剑华《中国山水画南北论》(上海,1963年),第96-98页。)。事实上,这是一次奇特的转向。因为,这种绘画的审美理想原来是属于儒家文人的,而且就其原先的形式而言和宫廷画院本来就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北宋后期苏东坡圈子里的业余文人艺术家的绘画具有雅正平和的特点,已被理解为其人格品质和文化修养的表现,这与他们自己及其友人和追随者的看法是一致的(注:高居翰《中国画论中的儒家因素》,亚瑟·F·莱特(Arthur F.Wright)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115-140页;卜寿珊(Susan Bush)《中国文人论绘画》(剑桥,1971年)。)。但是,在不完全否认风格的那种意义的情况下,我们或许也可以将文人绘画的这种特征理解为视觉修辞手段的另一种表现,是具备“节俭和节制”德行的儒家文人对朝廷作出的另一种维护。比如,鲍华石在汉代武氏祠浮雕的题材和风格中发现了这一点(注:鲍华石《政治艺术及其公众》。鲍华石在后来的著述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朴素风格的意义的观点,特别是他的《审美趣味》。)。文人反对徽宗画院绘画那种富丽的装饰性、精巧的描绘技法和追求视觉真实的再现,他们轻视甚至否定这些价值。这种绘画所用材料较为简单,都是很容易得到的,如纸和墨;其视觉感染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争辩说除了愿意认可其吸引力的愿意受其感染的那些趣味高雅的人士;其追求目标不再是忠于自然的逼真描绘。他们认为是他们选择了自己这些风格,这就意味着只要他们选择了就能够画得更美丽、更高超、更真实,这在许多语境中都可以理解。其中之一当然是政治方面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可能被看作参与了内外宫廷——也就是皇家与贵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局面。贵族的爵位和势力是世袭的,而儒家文人获得官职、取得势力,至少在理论上说要通过其学识修养和个人德行。内宫廷的绘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大都出自宫廷艺术家之手;外宫廷的绘画大都是文人官僚自己所为,表现他们认为具备的那种德行。
晚明画家兼理论家董其昌用同样的半政治化的对立局面来描述多少有些神秘化的艺术史,他把李思训和王维当作画史上“南北宗”的始祖。李思训是皇室成员,技艺精湛,风格华丽,所用为矿物质颜料,色彩丰富;而王维是文人官僚和诗人,以水墨作画(有时至少是这样),所作之画更有诗意,不以技巧或装饰之美取胜(注:董其昌理论中的这个方面,是俞剑华提出来的,见其所著《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第一章第四部分。关于解读董其昌理论的其他方法,我在论文中有讨论,见《董其昌绘画史论中的南北宗论再思》,彼德·N·格里高里编《顿渐:中国思想启蒙探讨》(火怒鲁鲁,1989年),第429-446页。再重复一遍,应该注意到,董其昌对李思训和王维风格特征的描述反映明代晚期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我们无法确知这两位艺术家实际上都画了些什么,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如何。)。身为文人官僚的董其昌就是用这些术语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以这种方式叙述这个问题时,我们采用了文人的修辞手段,这种事我们确实已经多次做过。中国的文人几乎总是能够作出最好的论证,后来他们写成书,书中的那些观点保存至今。现在我建议我们应该和他们的态度保持更远的距离,同时尊重他们。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过去在帮助西方学术界把这些态度确立为欣赏文人画的“正确方法”这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我在几十年以前(仍然跟随中国学者)还帮助推进理解中国绘画的意义的学术探讨,这种观点认为绘画作品总是艺术思想家感情的表现。这在今天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艺术家个人表现是绘画或大部分好画的意义或内容的一个因素,否认这一点当然是愚蠢的;但是仅以这种方法来理解绘画,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太普遍了,现在我相信这已经到了尽头了。那就意味着,说“艺术家那样画画因为他就是那样感觉的”或者说“他画高士是因为他仰慕他们并且要表现其仰慕之情”,这些都不能使我们理解绘画作品对于观者——艺术家有意表现——的意义。和人类其他表现形式一样,绘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惯例以及题材和风格的联系表现意义的。艺术家在选择题材或风格时往往要对社会中或具体或总体的要求作出某种回应;他并非只是简单地在某天早晨醒来后对自己说:“我想我今天要画陶渊明。”
对于中国绘画的政治主题及其意义的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我的这个研究报告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注:我在1985年春季主持的“政治主题”研讨班上以及后来在1987年3-4月份堪萨斯大学举办的同一主题的研究班放映了大量幻灯片,幻灯目录包括一百多幅绘画,从政治意义上分为十一个范畴,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很多范畴。在这两次研讨班上,我都警告学生不要误解我的论述,认为这样解读绘画作品能够穷尽其意义,其功能或者只是政治的,或基本上是政治的。我争辩说,恰恰相反,绘画作品是多义的,并且提出建议,如果我们将来要举办一次“中国绘画中的色情主题”的研讨班,我们同样会有一个长长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幻灯片目录——这个目录无疑会包括现在已经作出不同解读的相同作品,并且构成其另一种“选择历史”。)。我们需要更加集中地探讨某些个案(本章有些注释中列举了一些精彩的个案研究),但是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某些特殊的绘画类型和某些部分。研究和探讨中国艺术创作具体情况的其他诸种工作,不会也不应该完全取代过去传统的那种研究方法,诸如讨论风格、年代、作品归属或艺术家传记或文献出处,等等;而会使我们更有成效地关注汉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将我们的领域从过去那种分离和孤立的境地中摆脱出来。我深信,这还会使我能够做到更完满、更深刻地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
附:《中国绘画史三论》导言
(美)高居翰 著 杨振国 译
我给这个系列讲座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绘画的三种选择历史》。这听起来,显得稍微有点滑稽,但却是有意提出一个严肃(虽然不那么新)的观点:艺术史的写作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或模式,而且都是正当的;据此,我们选择艺术的各个方面及其各种情况作为集中研究的焦点。以风格史的模式,我们通过一系列作品写出风格及其发展;用传记模式,我们写出艺术家的生平,特别注意那些似乎会影响其艺术创作的各种具体情况;用文献学的模式,我们收集过去的艺术文献并加以探讨,讨论其与存世作品的关系。中国绘画的博士论文和其他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将这些模式结合起来探讨特定的艺术家或绘画作品。
近些年来,艺术史家们已经将注意力转向艺术史的其他方面,这构成了也许可以称为他们研究课题的选择历史。李铸晋教授1980年主持对中国绘画赞助问题的研讨班就是这种注意力转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注:《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堪萨斯大学资助,1980年)。)。在此之前,当有人问我们艺术家如何生存或绘画作品如何流传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站不住的借口说证据不足,算是回答这个问题。研讨班中的论文和为期三天的讨论使我们相信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以前要多得多了。而且,一旦我们知道寻求什么,如何解读,证据就有了。仅从这次研讨班就引发了多篇论文和各种讨论,由此人们可能会写出有关中国绘画的大量而有意义的著述,集中研究赞助因素和艺术家谋生的方式,或者至少通过销售或交换作品来获得某种利益等情况。
将注意力转向我们研究课题的某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轻视或忽略其他方面;但是这种情况仅会存在一段时间,然后在强调其他方面的其他著述中矫正平衡。近来人们总是抱怨,强调艺术生产的经济或社会因素的研究使我们偏离了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感受。只要指出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研究的作者至少在总体上也曾经从事过风格-文献研究,他们如果现在尝试别的研究,也应该能深入下去,这些抱怨之辞也就不难回应了。我们的目的在于提出可选择的方法,而不是要告诫别人(注:我赞同迈克尔·巴克森德尔的看法,他写到艺术史家中的这次争论时说,这“看上去似乎很奇怪,是告诫而又有些武断:我不喜欢别人的忠告。另一方面,我真正喜欢的是各种不同的艺术史。当有些艺术史家告诉其他艺术史家要做什么的时候,特别是要对什么感兴趣的时候,我的直觉是马上逃脱。我会去根据经验测量一个柱础的尺寸,或重新确定一尊雕像的归属”。《艺术史的语言》,《新文学史》10(1978-79年):第435-465页;这一段在第454页。);说某些陈旧的艺术史写作模式现在有些乏味,(当然某些有着非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研究实践除外)并不是要否定其活力与价值;我们只是要求“平等的时间”。比如,如果强调研究艺术赞助和艺术创作的外部状况,仅能得出作品的部分价值和重要性,那么风格研究也是如此。因而,在我们所追求的每一种研究中,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彻底地理解每一幅画;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将会使本书中所尝试的研究变得无法操作、无法实行或至少显得冗长。
这里汇集的头两讲中有我1984年和1985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主持的两次研讨会的某些结论,体现了我自己和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后者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表示感谢,但是我想,这两场讲座的旨趣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它依赖的是对于熟知材料的再探索和再思考。对于我举出的绘画作品,我将作出简短的、不完全的论述,在此情况下不讨论作品归属问题和年代问题,也基本不谈风格问题,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作品选定的某些方面。这两场讲座意在筹划新疆域,而非细察具体特定的领域,也不是要照亮前方的路标。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两次讲座在艺术及其外围境况的关系方面以相反的方向进行。第一讲是关于政治主题的,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即: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为政治的某些特定情境将会刺激人们创作某些类型的绘画作品,而这些绘画在主题和风格方面与这些情境相互适应。另一讲将从大量的中国山水画艺术作品开始,试图重构产生这些作品的情境及其可能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在这两项研究中,风格的因素被故意降低,虽然它与下述两个方面都不是一定无关的:风格的政治意义与山水画功能和意义中的风格的作用。这两者都是重要的问题,但在这里不予重点评述。
第三讲(原为1984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艺术史系研究讲座)集中讨论中国绘画风格中的一组或某一种类型,那种看上去似乎是“一挥而就”的风格的内在含义。由于这一讲的论述是按照粗略的年代型式进行的,因而比前两讲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后面附有后记,讨论这种一挥而就的风格类型晚期阶段的一些经济因素;这本来是我1986年秋季在中国几个地方所作讲座的一部分,题目是“写意:晚期中国绘画衰落的一个原因”。
这三个方面的探讨在理想上应该以更多的知识为基础,但我们实际拥有的知识还不够。这包括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画是为谁而画的,它们是如何受人委托或被人购买的?当它们被当作礼物时,是谁给的?给谁?在什么情况下给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是如何影响(这有助于说明)艺术家选择主题和风格的?我们从辨别类型开始进行个案研究,但是这些类型还远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必须回到猜测,这会耗费大量时间的;或者回到假设,适合有效证据,但不能被证实。艺术家与受众之间交易的类型除了相对简单的购买和委托之外,还包括画家自己将画作呈送给某人以求得某种好处,或赐给某种恩惠,或赢得好处(注:高居翰《中国绘画中艺术家与赞助人交易的类型》(“艺术家与赞助人”研讨班(注[1])上的讲座,正在印制。)译者按:由众多学者参加撰写的论文集《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李铸晋编辑并作序,导言即是高居翰为“艺术家与赞助人”研讨班所作的讲座。)。另一种情况是,有人从艺术家那里获取绘画作品,目的是将其送给别人。绘画成了复杂社交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们都有能力做到。他们是:绅士、商贾、官员以及最高等级的皇宫中人直至皇帝自己。因为中国绘画的那么多“消费者”都属于最后这两类人,即官员和皇室贵胄,所以很容易理解中国绘画的主要部分——我想比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更多——所描绘的题材都带有政治含义。这种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这些人生活的中心问题相关,即:获取并保持权力、统治的合法化、职务的任命、提升和退隐。既如此,那么,我们的第一种可选择的历史考虑这样的政治主题则是完全正当的。
译者简介:杨振国,博士,《美苑(鲁迅美术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