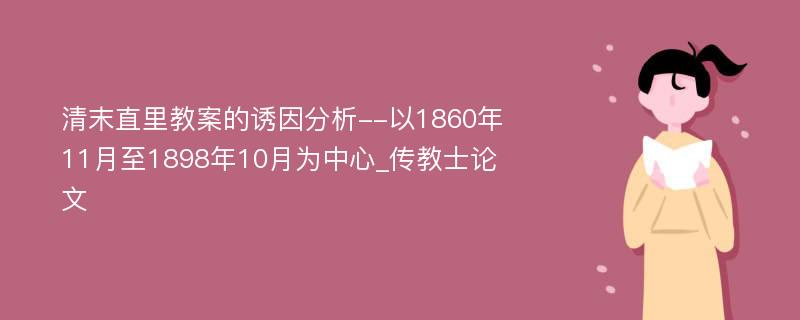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诱因论文,教案论文,直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注:截至目前,直隶教案的宏观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文章也只有董丛林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篇。文章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直隶的38起教案进行了研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的变化。兹概括如下:
一 地产之争引发
(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
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官地,可以奏明给予;如系民地,亦可置买给予,由官发价。”[1](p260)从而为此类教案的解决定下了基调:有证据的当然要还;查无确据的,如果对方态度强硬也不妨赔送一块。刚刚成立的大清帝国中央外交特设机构——总理衙门并未表现出初生时的锐气,而是一派疲塌作风。
法国方面,虽然条约在手并有大清上谕作保,但一一去查显然不可能,因而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直隶)从前遵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均应按约查还,若如此办理,许多费神,不如烦饬拣二、三处地方办理。”[1](p242)并最终选定正定、宣化两处。1861年10月,法使布尔布隆数函总署要求查还,之后呈出直隶旧有天主堂“清单”[1](第365号),诈称只查还此二处余可免究。清总署及各地方官犹豫再三后态度转变,法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上述两处旧址。但法国很快就食言,此后又发生3起案子:分别为1862年清河县教案[1](第471号)、1862年深州大染庄教案[1](第458、463、468、469号)、1866年宛平县罗谷峪教案[2](第337,376,390号)。法国基本达到了目的。
禁教期间,各地教堂大都被毁或移作他用,查还旧址也毕竟有限,因此60年代以后各地教士纷纷租买房产以建堂传教,由此引发的教案不在少数。传教士租买房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当地官府租买,如1861、1862年法国传教士分别向河间[1](第391号)、深州[1](第448,455,456号)地方官租得房产;二是向民间私人租买。在直隶,后者是引发教案的大宗。
实际上,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内地置产有严格规定:第一,契据内只写立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以保证其“仍为中国之地”;第二,卖业者于交易前须向当地官府请示,严禁私卖[1](p54)。不仅如此,传教士租买房产还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绅士民的普遍反对:“民间将地私卖洋人,乡邻闻知,即令悔议;即守土官宰,亦将藉口百端,不肯即以此项授受注册,往往经无穷周折,而后议成。”[3]被教方指控为“从中阻拦”、“纠约指使”的有县主、典史、千总、差役、民众等。而地方士绅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或直接出头拦阻,或坐镇幕后操纵,成为此类案件的实际指挥者。士绅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第一,买卖房产历来为民人所重,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控制主体”[4](p123)的地方土绅必然会在此类事件中行使自己的“地方事业之权”[5](p68),当自身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会挺身而出。第二,与绅民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的认识有关。晚清时期,在相对闭塞的直隶城乡社区,一般绅民将高鼻深目的外国传教士视作“异类”,而将外来宗教与本土的秘密教派、会道门等量齐观,1868年1月,署理直督官文的奏折中即有“查天主一教,与白阳白莲等教,同干例禁”[6](卷56,p14)之语,可见一斑。1868年永清教案[7](第238号)、1895年固安教案[8](第505号)均因绅民阻拦教士租房引发。
(二)因民教互争公产(注:包括族产、家产、庙产等,在直隶以“庙产之争”引发教案最为典型。)、地亩而起
晚清时期,各色神庙寺院遍布城乡,其数量之多,曾令19世纪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一度“难以置信”[9](p131)。60年代以后传教场所的普遍缺乏,使各地教民将目光聚焦于“合村公产”——寺庙及其香火地上,寺庙成为进行教务活动比较理想的地方。教民认为,既是合村公产便可拿来使用,但很显然,他们的想法与做法遭到了非教民的反对。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己申辩:一方以维护传统信仰为辞,将对方视为“叛逆”;一方则以有“股份”在内而理应分得相驳,二者互不相让。于是民教两方由信仰不同和实际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直隶,这样的官司有好几起,其中以1864年柏乡县塞里村一案最为典型:此案从1862年教民“未得公议”在观音寺设学传教而起,两年后,当地庙会期间村民欲在寺内“施茶”,教民占住不让成讼,县断令教民暂挪,俟施茶事毕仍归教民使用。旋迭次翻控,经州断令村民另行择地对换给教民建堂结案[7](第192号)。
口外之地(包括口北三厅、承德府),清初为国家马厂、旗人及功臣赏地,严禁私垦。乾嘉以后,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内地民人“出口”垦荒者渐多,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暧昧,土地纠葛逐年增多。1872年6月,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署有这样一段话:“塞外草地马厂,畜牧以外别无出产,初虽粗有四至,而向例游牧不禁,未经开垦以前,决无专利,几同公物。即蒙古各员与王公子孙,亦难确定界址,故有民垦数十年,而原主不知,官场不知,已同永业者。此后一经若辈买业争执,案件层见迭出,正未有已。”[10](p259)很能说明问题。
理论上,清政府对教方私垦有防范。1870年张家口厅民教争地案发生后,总署以封禁荒地时有教士教民违例开垦,行文直晋督抚,饬属一律严禁[10](p425),从而引发了一场“开禁”与“封禁”之争。李鸿章力主开禁,但为避外人乘间窥伺之弊,须“于通融中求限制”,即认为应酌情开放官荒,但只准招典承租,不准业者受价私卖,尤其对“各项职衔顶戴人员,在官人役以及僧道喇嘛教民诸色目人,一概不准招承佃作”[10](p428)。但各级地方官显然对此实施不力,教方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土地并因之与当地绅民产生了冲突。1870年,张理厅万兴张等村民张鹏等与山西丰镇厅南壕堑教堂教民段振举因租地问题发生争执并对簿公堂[10](第192,246,248,250,276,277,373,374号)。1884年,滦平县杨树底村民陈太因祖遗地亩与县属老虎沟教堂涉讼[11](第232号)。1897年,察哈尔正黄旗七苏木地方正黄旗佐领、武举乔旺、教民杨世望及文生孟士仁等因争夺地亩互控成讼。[12](第121号)
二 因摊收修庙与庙会钱文引发
中国城乡多庙,上已述及。每隔一定时间各地还要进行修缮,这一活动因政府的大力提倡与绅民的坚韧信仰以及不赀的耗费成为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一项要务,各地对此很重视。庙会之期,一般要搭棚唱戏、歌舞喧闹一番,所用不菲。
修庙与各种庙会费用的筹集办法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的名义下令征收;二是以“绅民公议”的形式由民间征收。“弛禁”上谕的颁发使教民的异质信仰成为合法,同时也为他们拒交各项迎神赛会、演戏烧香诸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1862年1月,法国代拟的“免摊”通行文稿为清政府首肯、颁行后,此类案件层见迭出。一方面,官绅士民对教民免摊修庙及各类香会钱文表现出极大的心理失衡。因为尽管信仰不同,但民教双方在其他方面仍有诸多干系:他们同属“天朝”子民,同居一个社区,同享各种自然与人文资源。在绅民看来,仅凭一个教民身份便可轻易“逃脱”诸多费用,违反了老规矩,实在说不过去。而教民对此却心安理得,并将“免摊”的实际内容逐步扩展,从而引起了绅民更大的不满。双方常常因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最后不得不由官方了断。
绝大多数情况下,教民因“拒交”态度的坚决与传教士、领事、公使的介入而终得“酌减”或“免摊”。如1874年定州西板村教案[10](第334号),1877年深州王乐寺、杜家庄教案[10](第342号),1881年霸州高家庄教案[11](第144,145,152,160号)及同年清苑县刘村教案[11](第196,206号)均如此。例外的案子也有:1873年巨鹿县捐修文庙一案,直督李鸿章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最终使“恃教抗捐”的教民梁武魁“愧悔”不已,被杖80后,“仍愿催全教民与齐民一体踊跃输将”[10](第272号)。此案中,卫道色彩极浓的李鸿章不仅捍卫了孔孟先师的尊严,也为普通乡民找回了些许心理平衡;而同案中地方士绅的表现——高祥凤等15名生员保释教民梁武魁则进一步说明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多面性,在这里,他们看重的是保一方平安。
三 因细故口角争殴引发
近代以来,由于频繁的灾祸及人口极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生活资源的日益溃乏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一向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变得好勇斗狠、睚眦必报起来。“弛禁”上谕颁布后,教民作为—个特殊社会权利单元的地位凸显,加重了这一势态。1863年10月5日,武强县河南屯村民魏奔楼摘食教民杨熊家菜茄,当晚杨找来不依,争殴,次日杨因伤毕命。[1](第603,604号),仅仅因为个把菜茄便闹出一条人命,成为上述命题的绝好注脚。闲言口角,无事生非也时常发生,1870年武清县大三庄张兴位赴肖庄与李四邀会钱文,与教民石春“闲言”口角,经人劝散又率子找石不依,教方上控成案[7](第393,394号)。1880年平乡县弯子村刘贵先下地,与教民在下地路上口角走散。回家后教民复持刀棍寻衅致讼[11](第184号)。此类案件正如直督李鸿章所言,乃纯属“民间鼠雀相争”[7](p339)。
教案民方当事人除村民外,有勇丁、哨官、店主、木匠、船员等,基本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官员、士绅是绝少参与此类口角争殴案件的,这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所拥有的财富以及社交圈子等有关。从教案结果看,如果没有传教士、领事、公使强行干预,清地方官一般将此视为普通民事纠纷案件处理,量刑较轻,有相当部分案子是通过“社区精英”们私下和解的。
四 因教方遭劫窃引发
近代中国,各地劫盗案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方也在所难免。仅从统计到的发生在直隶的十几起此类教案来看,涉及地区包括宣化、保定、河间、广平、天津5府及深、冀2州等。
凶年多盗,乱世生匪。近代频仍的人祸天灾不仅摧残着人们的生活,更吞噬着他们的心灵。许多人或“因贫难度”落草为寇,或“乘便攫取”流于窃贼,而各地教堂深闭的大门与高耸的十字架以及传教士手腕上闪闪发光的金表等都为劫盗惯犯、图利小民及各色义军所驻足,在好奇心和图财欲的驱使下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洗劫对象。
从这些案件的结果看,除1870年广平府南街教堂被盗案[7](第362号)、1871年蔚州美国传教士贝以撒遭殴抢案[2](第683,685号)、1898年曲周县辛营村教民周清霄家被焚抢案[12](第327号),前两案因在天津教案后,后一案则在义和团运动前,均属“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在给教方一定赔偿外,其余则未进行赔偿。1863年宣化教堂失窃案后,清方还对要求赔偿的传教士蓝芳进行了严正驳斥,总署致函法使要求对其严惩。[1](第440号目录)表明清方对此类案件的态度:均属普通劫盗案件,缉拿案犯、获赃给领是其分内事,仅此而已。对案犯的量刑尺度,以教方为对象的劫盗案件与普通案件基本一致。
五 由揭贴、谣言引发
揭贴,尤其是匿名揭贴,历代统治者都严厉查禁,因为揭贴的背后是“邪说”惑众的各类会道门,是暗潮涌动的种种“异端”力量,而这些又往往最能触动统治者的敏感神经。谣言随揭贴而来,是一对孪生兄弟,谣言一旦失控成为舆论狂潮,其后果是令统治者不敢想像的。
反教揭贴是各色揭贴中的特殊一类。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藉侵略军的坚船利炮乘势东来,并迅速在中国城乡各地竖起了十字架。我们承认,传教士中确有一些是怀着真诚的宗教热情来中国实现其“中华归主”崇高理想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对于鸦片战争为他们打开东方传教之门带来的诸多方便,多数传教士是“怀着兴奋与雀跃的心情来接受”[13](p700)的。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赋予近代外国来华传教士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份,而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其魔鬼的成分无疑是主要的。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记者、时人宓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景教流行神州,既以兵力导其先路,则支那之视耶稣、基督,自与释迦牟尼、谟罕蓦德不同。彼以顺施,此以逆取,故也。在中国目中心里,景教一事,常与丧师辱国之意胶结而不可分,创巨痛深,身受者尚未登鬼鋆也。”[3]这是近代中国教案迭出的根源所在。乡绅是近代中国“正统文化之源和儒家道德体系的支撑”,当异质文化入侵对传统儒家文化构成挑战与威胁时,“反应最为敏感、最为激烈”的就是他们[14](p2)。反教揭贴是其制造者——乡绅对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能回应,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使之在近代史上蕴涵了特殊的意义。
受时代与自身阶级、认知所限,反教揭贴、谣言的种种荒诞自不待言,但这已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民众是近代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最终受害对象,反教揭贴、谣言散发流布的意义在于激发、唤醒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使他们成为“反洋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传教士对此之所以“谈虎色变”,原因也在于此。1869年[7](第255,257,258号)和1873年[10](第284,329号)的两起广平教案,民教双方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当时各地流传的有关教堂、传教士的种种揭贴、谣言的影响而诱发的。1864年5月,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反教揭贴之一——《湖南合省公檄》,一夜之间便贴满了广平府四处,“激励众百姓一同起义,以拒奉教人及各外国人”[15](p573),虽经地方官撤除并严申例禁,但仍以“惊人”的速度在民间广泛传扬着。而案中最为乡民愤愤的“不奉神明”、“奸淫妇女”等也正是此类反教揭贴、谣言中所要大书特书、着意渲染的内容。1870年天津教案及其影响下的数起教案与谣言、揭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相关论著于此已有阐述,恕不再赘。当然,如上所述,在许多情况下,揭贴、谣言总是借助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才发挥作用。
六 因民教猜疑、挟嫌捏控而发
民教猜疑源于一种心理定势,即源于民教各自心中长期形成的关于对方的社会刻板印象。在民方看来,西方传教士乃异域另类,其越洋万里舶来东土,一定有所企图、居心叵测,这是民众朴素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征,也是他们透视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点。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一切:近代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天朝崩溃、丧师辱国之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进而,当各种中西习俗差异和现实利益冲突将民众与传教士拉近成为矛盾的直接对立双方时,印象中所有关于传教士如何“坏”的形象被最终强化、定格下来,教民当然也不例外。在传教士一方,对于他们如何取得在华传教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并不光彩的角色也是心知肚明,[16](p31~32)他们也确实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上下的种种“排斥”。他们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也时刻不敢忘却过去——“禁教”期间的种种苦涩,这使得他们变得异常敏感,他们害怕回到过去,那是一段令他们“心酸”的历史;然而,肩负“中华归主”的神圣使命以及身处胜利者的特殊地位又使他们不能容忍丝毫“委屈”,历史毕竟已经过去,正如鸦片战争时期一位随军传教士所言:“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p47)正是基于以上两种心态,传教士及教民对民众任何一点“反教”举动均表现出空前的关注与不满,尽管有很多时候这种“反教”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揣度而已。“民教猜疑”案中,几乎所有的猜疑与指控最终均落在“禁教”、“反教”、“逼教”、“闹教”上,这绝不仅仅是巧合。
“弛禁”上谕颁布后,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成为“合法”。但是,“不谙世事”的民众并不承认,他们仍然顽固地坚守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而传教士则视其“合法性”为至宝,处处欲以彰显并一度将其作为“杀手锏”。于是,在日常交往中,出于种种原因,民教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时刻猜测对方,当一方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露出破绽时,对方会很快作出反应,抓住纰漏、上控成讼,有时甚至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是此类案件的引发原因。1862年唐山县良村教案,教民程某因举保乡地不实被县令传讯,疑是“逼教”,司铎姜怀义赴县分诉,时教民车夫程洪子手执鞭杆在旁吆喝进署观看的乡民,县令疑其“抗拒官长”,将其示众,程负气捏控县主刑打逼教[1](第479,495,505号)。1866年宁晋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请艾教士为其子张书琴看病“驱魔”,不小心遗火将桌下准备为儿子婚礼做鞭炮的斤余火药燃着,致伤艾教士而成讼[15](第223号)。1884年12月,邢台县一乞丐夜里在教堂门口点火取暖,致将门上油漆烤焦,教方随上控[11](第223号)。上述两案纯属偶发性事件,情节并不严重,本可以化小化了,但在教方看来显然是预谋好的,因此大肆渲染,上控成讼。
七 由教士教民不法引发
有关因教士教民不法引发教案的论述,以往学者已多有着墨,不再赘述。只说明一点:在直隶,单单由此引发的案子实在不算多,比较典型的案例只寥寥数件,如1863年满城县大固店村教案[1](第608号),1891年承德府建昌县教案[18]。以往学者之所以在此着墨较多,除受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外,还由于他们将大量传教士干预词讼的案子算入的缘故。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教士干预词讼无疑是增加了案件的审判难度与延长了结案时间,但并非引发教案的直接诱因。
标签:传教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案件分析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