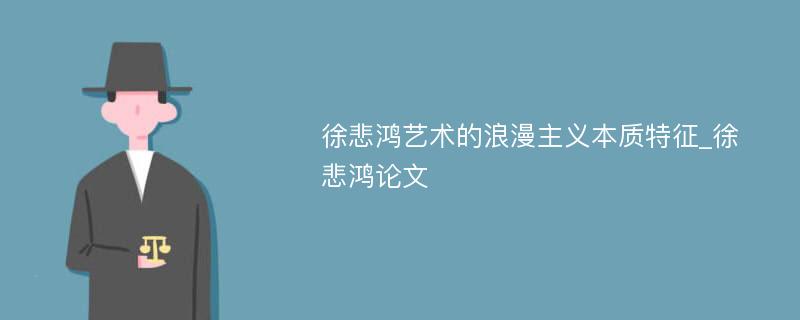
徐悲鸿艺术的浪漫主义本质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悲鸿论文,浪漫主义论文,本质论文,特色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7)01—0091—04
许多人对徐悲鸿艺术特征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了他对西方素描的引入、他的现实主义因素等方面,甚至把他推崇为学院派艺术(保守的代名词)的首领。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徐悲鸿更重视写形之上的传神和艺术的抒情明志作用。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观念、技巧等仅仅是他艺术创作的手段,而非目的。徐悲鸿艺术精神的本质在于他的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的艺术面貌呈现出了强烈的艺术个性,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修养、个性气质、道德品质、政治立场等无不有机地融入到他的艺术形象中。徐悲鸿不仅采用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创作自己的艺术形象,更用创造性、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形成独特的面貌。这一切都表明徐悲鸿的艺术精神之本质在于“浪漫主义”。
事实也证明,在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中为了写实而写实的作品几乎找不到,就包括徐悲鸿早期写实意味很浓的《诸老图》、《西山古松柏》、《三马图》和后来的《印度妇人》、《泰戈尔像》和《李印泉像》等,也不排除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又如徐悲鸿的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如《前进》、《群马》、《群奔》等作品的神、情、气、韵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浪漫主义”精神。另外他的《九方皋》、《愚公移山》、《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箫声》、《田横五百士》、《月夜》、《玉簪花》、《喜马拉雅山》等等,也都充满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情、神、气韵甚至笔墨情趣和崇高的浪漫主义情怀。
一、激情和动势
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中显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单纯写实而已。他用自己的敏锐的感受和完整而深刻的美学理念来驾驭自己的形象思维,并将自己那包括社会身份、文化素养、道德情操和个性气质的“全人格”以及创作激情有机地熔铸到其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客观事物,更有“我”在,当然与中国文人画中的重视自我胸怀和情思表达相比,徐悲鸿的思想感情、文化道德以及个性气质中包含了更深刻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所以前者的有“我”只是“小我”,而徐悲鸿的有“我”则是“大我”。
徐悲鸿的艺术作品是很重视“情”的作用的,并由此形成了一股“气”,形成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之“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和风貌。只不过他的“气韵”已经超出了前此各个时代的“气韵”之范畴,而上升到崇高的精神高度,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的新发展。这与文人画的气韵是有区别的。徐悲鸿在人品上有豁达的大丈夫、大仁君子之气,所以他的艺术中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在思想精神上有彰显民族精神,在其民族复兴之鸿志下表现出高屋建瓴之傲骨和气魄,所以他的艺术中又有“威武不屈”之志。这些主观因素表现在绘画上就成了反映其人格美的特定风格,并最终熔铸到他饱满的创作激情中。他所有的情思最终都化作了其创作上表现“威武不屈”和“悲天悯人”主题的创作激情,他认为这是艺术的最高情操。加之他又将这种激情与其艺术特别是人物画强烈的动势相结合,比如《愚公移山》中人物造型上强调劳动中的壮年男子健壮的肌体和剧烈的运动,也是其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另外,其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中奔腾中的马动势也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
二、崇高的审美理想
以21世纪初包括上世纪末的眼光、思维和社会环境来衡量徐悲鸿的艺术是得不出客观结论的。不同于徐悲鸿时代以社会和人民生活大局甚至民族解放为重,和平发展中的现代社会追求娱乐的成分倍增,个性发展得到了肯定,审美理想自由而丰富。
然而,徐悲鸿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庞杂、最危难、也是最催人奋进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落后与进步、愚昧与科学、野蛮与文明、独裁与民主、亡国灭族与民族振兴等矛盾之间的殊死斗争和卓绝抉择。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是毛泽东、鲁迅、徐悲鸿、千百名民族精英以及有气节的亿万劳苦大众共同聚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鲁迅和徐悲鸿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艺术上的伟大领袖,为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为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蹚出了道路。在此新旧思想交替、开放与守旧并存的时代,徐悲鸿正是我们新文化运动在艺术革命领域里的领袖。在艺术上,他通贯中外古今,身兼中西两大文化和艺术美学的精华,包前孕后,勇于创新,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其艺术中蕴涵的磅礴思想、强烈情感、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与他在留学期间所吸收的西方理性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他艺术上崇高的浪漫主义色彩。
“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却为西方所独有,在中国则只有与崇高接近的壮美或曰阳刚之美这一美学范畴。”[1](P74) 中国历史上虽也不乏呼唤崇高的时代,但是中国绘画艺术却长期对此“无动于衷”。是徐悲鸿将这种情况彻底改变了。徐悲鸿认为,“为艺术之德,固不当衰于一是;但小博大雄奇为准绳,如能以轻微淡逸与之等量齐观,固无损其伟大也。若其跻乎庄严、静穆、高妙、雍和之境者,则尤艺之极诣也。”[2](P490—491) 他说:“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人雄奇活泼之风格。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人博大之精神。我们的图案艺术,应绍述宋人之高雅趣味。”[2](P512)
徐悲鸿既开创了中国崇高主题的艺术风格,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油画创作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如《田横五百士》,还首次用人体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如《愚公移山》,更能用鸟兽等动物画来表达这一主题,如《前进》、《鹰击长空》。他的风景画也是崇高的风景画,如《喜马拉雅山》。
三、重视传神的笔墨特征
徐悲鸿的艺术不仅做到了形神兼备,而且是极其强调传神,其高度的概括提炼和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手法是为了传达出客观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客观世界之“神”,甚至表现出了艺术家个人独有的个性气质、情思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界,如他的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表现出来的无比的神韵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人物画上达到的超逸的风韵。
徐悲鸿艺术又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但是其终极追求在于尽善尽美。不了解徐悲鸿艺术中的善,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美。他说:“穷造物之情者,恒得真之美;探人生之究竟者,则能及乎真之善……若其挥斥八极,隘九州,或真宰上诉天应泣者,必形式与内容并跻其极,庶乎至善尽美,乃真实不虚。”[2](P364)
徐悲鸿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完整的统一体,求真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前提,包括对知识和科学的崇尚、师法自然的继承、坚持艺术与生活和大众的密切关系以及艺术对诚对情对爱的要求,并且这些特征是互为促进的,但是对真的强调最终还需要落脚于“尽善尽美”的旨归。而徐悲鸿在艺术中对技术、技巧和技法的充分肯定和对素描与写生的严格要求的要旨,正是在于他对尽善尽美的恪守。总之,真善美是相辅相成的、完整统一的,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面。
“吾认为艺术之目的与文学相同,必止于尽善尽美。吾主张: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又认为:真气远出,妙造自然,为绘画应有之旨。”[2](P211) 这就是徐悲鸿对真善美追求的宣言。
徐悲鸿的国画在追求笔墨趣味上也是明显的,只不过是超越了古人的传统文人画之笔墨而已,是时代性特色很浓的笔墨趣味的体现。他的油画也有笔墨的美学内涵。徐悲鸿的笔墨与书法联系紧密,老辣历练,苍茫劲健。徐悲鸿有抒写“雄肆奇伟”的“砺笔”,来自于书法中的碑学笔法,这与倪瓒在绘画的抒情性上是一致的,但在情感的性质上又表现为徐悲鸿的“豪气”和倪瓒的“逸气”的不同。再者,徐悲鸿更主张笔墨技巧只应该是写形传神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主张从形似入手,而以追求神似为目的。
由于徐悲鸿艺术的本质精神在于民族性的崇高精神,所以他的笔法又是崇高的笔法(包括国画和油画),其人物画的笔法也多呈现粗犷豪迈之笔,气势宏大,少有细笔滑腻之作品,特别是他独创的水墨大写意画,更是充斥着崇高性。他的笔法都是粗犷有力的线条和笔触,与英雄形象和豪迈的气质是相合的,如《田横五百士》中的崇高性笔法是与作品中的悲剧气氛相合的,可见其笔法的内涵深广超出常人想象。这一切都表明了徐悲鸿艺术的浪漫主义本质。
四、徐悲鸿艺术的个性特征及修养
由于徐悲鸿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崇高,所以他的艺术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中国艺术中以气韵生动和在作品中见人品和情趣为最高追求的美学范畴,他的艺术是对崇高的美学内涵与民族精神的结合,他的艺术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人物画表现的是争取民主独立和自由民主的民族精神的写照,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国殇》、《愚公移山》等。他的花鸟走兽画表达的也是民族精神,如《神鹰图》、《会师东京》、《群马》、《群奔》、《前进》、《风雨鸡鸣》等。他的山水画也是如此,如《喜马拉雅景色》等。徐悲鸿艺术是民族的崇高精神的象征,成为特别是抗战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食粮和支柱,从精神之根本上支援了抗战。徐悲鸿推崇阳刚的崇高,因此徐悲鸿的艺术作品多具男子气概,即便其女子形象也多少有点不让须眉的气质,如《风尘三侠》、《印度妇女》甚至《山鬼》的缚虎逐兽的柔美之躯都有刚性气质。包括他的具有细腻特征的绘画中也仍旧掩饰不住“不同凡响”的咄咄气势,如《唐诗意图》中妇女的表情和身姿的坚毅,《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美女那不无健美的感觉,《日暮倚修竹》中妇女的大方与自信,《观音像》更是有男子的力度。颂扬男性的阳刚之气,欣赏进取精神,这与徐悲鸿崇高的美学和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徐悲鸿艺术上的阳刚、豪放和崇高的艺术个性特征。
虽然徐悲鸿有重视写实、重视形似和法度的一面,绘画有德育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作用,在徐悲鸿所处的民族战争年代里,其艺术与政治以及德育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徐悲鸿以画抒情和明志的美学思想也是明确的,所以徐悲鸿在审美理想与情操上彰显出了他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强调绘画的抒情作用,其艺术中表现出了画家人品、气质、修养的作用。他也是遵循书画同法原则的,比如他的水墨大写意的马系列作品中,他将超逸浑穆之碑意书法用笔融入创作中就是对笔墨的一大创新,并形成徐悲鸿笔墨的独特风格,是其作品具有奔放恣肆之气度的原因之一。可见,徐悲鸿是以浪漫主义作为绘画美学的主导思想。所以徐悲鸿的艺术又是极其重视修养的,相反,他的写实、形似和法度是为其浪漫主义服务的必要手段,而非目的。
五、徐悲鸿艺术的浪漫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全面表现
徐悲鸿的“浪漫主义”艺术本质可以说是贯穿于他的艺术生涯的始终,并且也普遍地存在于他的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
徐悲鸿虽然很早就表现出致力于学习和研究写实主义艺术,比如1918年徐悲鸿给梅兰芳画像《天女散花图》,包含了徐悲鸿对写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早期追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徐悲鸿的浪漫主义气质。作品中都有大胆的想象的成分,特别是《天女散花图》中梅兰芳的脸部描绘俏丽,是用西洋写真画法,但在一片云海升腾弥漫的画面中,梅兰芳那呼之欲出的眉眼神态却给人一种鲜明的诗意想象,作品同时具有了超越一般现实主义作品之上的浪漫主义气息。又如徐悲鸿早期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时的刊登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刊物《绘学》第一页的画作《搏狮图》,画中一裸体男子赤手空拳与一只张开大嘴的雄师搏斗,男子的神态坚定自若,虽然作品中用了写实主义的技巧,但是整幅画面的人与狮关系上的艺术化处理、大胆想象、对人类斗争精神的理想化处理都使作品显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说明徐悲鸿自从步入艺术的早期就流露出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本质,早期的艺术中就包含了他那不甘平庸、富于幻想、敢于挑战自我、执著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成分。从此以后,徐悲鸿艺术的浪漫主义不是减弱了,而是逐步得到了加强,即便他在留学欧洲8年而全心学习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期间的创作也是如此。比如他1924年的油画创作《琴课》、《抚猫人像》,1925年的《蜜月》等,虽然是对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实践占据主导,但是徐悲鸿同时赋予画面另一种婉约、秀丽、温馨,甚至是超然物外以及朦胧梦幻的迷人的浪漫主义气息。特别是他1926年的著名油画《箫声》,更是使这种充满神韵和秀美气息的浪漫主义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以至于对《箫声》这张画法国诗人保尔·瓦莱西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画家是一位把握瞬间的魔术师,看到这张画,我们就好像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箫中间流出来一样。所以,在徐悲鸿的艺术作品里,写实主义的手法仅仅是他的艺术创作的手段,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给人以无限遐想的“情在形外”的浪漫主义特征才是本质。他回国后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月夜》、《喜马拉雅山》、《前进》、《群马》、《奔马》、《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作品都有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特色。
再者,徐悲鸿艺术的浪漫主义特色具有普遍性,在他的国画、油画、素描、书法甚至是诗文和讲辞中都是极其显明的。比如,他的国画《愚公移山》、《前进》、《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新生命活跃起来》、《风雨鸡鸣》、《漓江春雨》、《喜马拉雅山(之林)》、《山林远眺》、《沉吟》等,其中《漓江春雨》以其对创造性的泼墨技法的运用,画面体现出的浩然浑融的气势和儒雅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及艺术家个人的“独执偏见,一意孤行”的个性、敦厚笃实的品德和强烈的创作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表现,都标明了徐悲鸿艺术本质上的浪漫主义特色。就包括《印度妇人》、《泰戈尔像》、《神鹰图》、《灵鹫》、《鹰击长空》等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目的作品在内,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写实主义,其中的浪漫主义特色也是不容否认的,特别是人物的眼睛和灵鹫与山鹰的眼睛,真可谓是“以形写神”的典范之作,使灵鹫和山鹰的形象与搏击的本性跃然纸上,更显现出了傲然的斗争精神。再看油画,早期的《奴隶与狮》、《琴课》、《抚猫人像》、《蜜月》、《箫声》、《田横五百士》、《桂林风景》、《黄山秋色》、《月夜》、《喜马拉雅山》,其中《喜马拉雅山》不仅表现出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气韵生动、飘逸洒脱、浑穆大和的美学追求,还从其构图上的奇绝、色彩上的容纳中外古今、对中国阴阳辩证以及西方理性精神等方面进行了卓绝的高强度整合,达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展现出了强烈的浪漫主义本质。以上作品包括了人物画、风景画和动物画,表明了徐悲鸿艺术之浪漫主义的普遍性。
总之,现实主义是徐悲鸿艺术的基础和来源,但在艺术表现上徐悲鸿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就像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极具表现力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同时极其重视师法自然并最终都超越了现实主义一样。真正的浪漫主义艺术和画家都是极其尊重现实主义和师法自然的。如果有人为了强调表现而否定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是不妥的,徐悲鸿的浪漫主义艺术正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6—12—26
标签:徐悲鸿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术论文; 箫声论文; 月夜论文; 前进论文; 喜马拉雅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