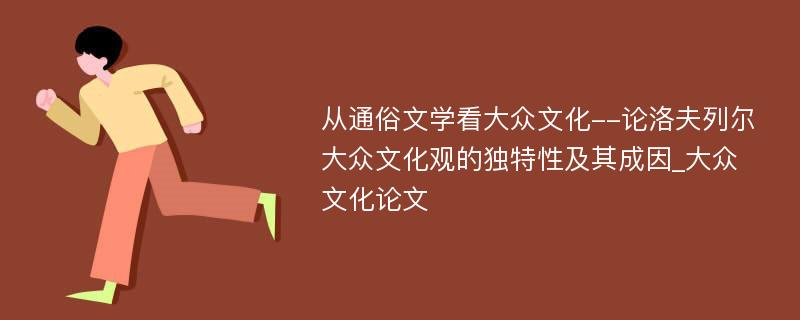
通俗文学视野中的大众文化——论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独特性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论文,独特性论文,成因论文,通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但是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其立场和观点却显得犹疑和暖昧。如果说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观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哪些方面构成了他的大众文化观的主要元素?如果说洛文塔尔在对于大众文化是谴责中隐含着理解,否定中暗藏着肯定,那么这种“骑墙”姿态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又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显然有助于我们对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深入理解。
大众文化≈通俗文学
为了能更充分地进入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从洛文塔尔与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不同之处谈起。
在论及两位理论家大众文化观的区别时,格罗斯认为,首先,阿多诺从来没有像洛文塔尔那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可能会把自己看作使用社会学材料的艺术家而不会把自己看作使用艺术材料的社会学家。同时,阿多诺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评论员(cultural commentator),而且更是一个好斗的甚至富于侵略性的文化批评家(cultural critic)。而且,当阿多诺把自己的主体性经验渗透在自己的研究中时,他的批评文字会呈现出一种反讽、忧郁、密不透风等等之类的风格,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社会学家的洛文塔尔所不具备的。其次,由于阿多诺认为“挑战一个社会包括挑战这个社会的语言”,所以他常常以格言和警句式的写作构成他行文的语言和形式。于是,他的每一个句子必须以著作的全部为中介才能作出理解,这样的文本需要细读,需要有感觉语言的微妙性与含混性的能力。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行文风格限制了更多的人从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中受益,而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则不存在阿多诺那样的理解难度。第三,洛文塔尔把文化客体看作是破译社会进程的密码,因此,文化客体的内容对于洛文塔尔来说是最最重要和富有启迪性的;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文化客体的内容如何保存了流行的社会看法,而是这个客体出现之后,它如何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主要密码。第四,直接指出大众文化某些方面的社会起源,阿多诺显得非常熟练,但是,把大众文化放到一个既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他则没什么兴趣。而洛文塔尔则恰恰相反,尤其是在“研究所”的那段日子里,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仔细辨别大众文化的细微变化,则成了洛文塔尔的主要工作。第五,阿多诺不断地为“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要素进行辩护,因此,他分析文化的目的之一是拯救自律或激进的主体性中的元素,营救那些不能被同化的细节,解救那些标准化时代所有被拒绝和被毁坏的东西。这样,与洛文塔尔相比,阿多诺就发现了现代生活中更多的荒凉与不可忍受之处,这也是他呼吁“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洛文塔尔的著作中,我们却很难发现他有如此强硬的立场。(注: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p.129-31.)
格罗斯对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比较分析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但是,或许是囿于方法论的视角和大众文化理论的资源,(注:在此文的开头部分,格罗斯明确指出他所思考的重心是三位理论家如何接近他们的材料,他们的观点又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方法论塑造出来的。而为了呈现他们的主要观点,格罗斯又分别选择三位理论家的一部著作作为其大众文化理论的分析对象。洛文塔尔的著作是《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阿多诺的著作是《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罗兰·巴特的著作是《神话学》(Mythologies)。笔者以为,选择《最低限度的道德》作为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资源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眼光,但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忽略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因素。See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125.)他在比较分析中忽略了一些在笔者看来同样重要的因素。我曾经把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看作是印刷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现代性话语,这意味着阿多诺表面上批判的是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实际上却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视觉文化,这种文化是由新型的电子媒介制造和生产出来的。而事实上,虽然阿多诺也曾对印刷媒介上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过研究,(注:例如,阿多诺曾对《洛杉矶时报》上的占星术栏目进行过研究。See Theodor W.Adorno,The Stars Down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但是他更感兴趣的还是电子媒介和这种媒介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形式,于是,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和爵士乐等等的内容与形式才成为他著作与文章中反复批判的对象。(注:参阅拙作《印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为什么阿多诺要批判文化工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因此,对电子媒介与视觉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在这种批判中确认文化工业对个体的伤害乃至毁灭性的打击,应该是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应该是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来进一步思考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与阿多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从洛文塔尔研究大众文化的重要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主要指的是存在于印刷媒介中的通俗文学,或者说,他是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来打量和思考大众文化的,而现代的文化工业,即通过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生产出来的新型的大众文化,则基本上不在洛文塔尔的思考范围之内。(注:事实上,格罗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洛文塔尔“为了文化看法的线索而把目光集中在大量的印刷材料上,以至于通俗文学几乎变成了大众文化的同义语”。但遗憾的是,作者的这一发现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而并没有展开论述。See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126.)比如,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透视通俗文化”和“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论纲”两章内容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来梳理和回答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的有关问题,他虽然也提到了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但这只是他沉入历史思考大众文化的一个由头,或者只是把有关电子媒介的某种说法看作是对帕斯卡尔的遥远回应。(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2,11,49-51.)而当他在“蒙帕之争”之后进一步去分析歌德、席勒、莱辛、阿诺德、白哲特、华滋华斯、雪莱、丹纳等人的观点时,这些诗人、作家和理论家关于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看法无疑又是建立在他们那个时代高雅文学/通俗文学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洛文塔尔面对的实际上还是被印刷媒介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只不过这是一种间接的面对。而在“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英国18世纪的个案研究”一章内容中,洛文塔尔则把间接的面对转换成了直接的探析,他更关心的是通俗小说如何兴起,通俗小说的传播状况和通俗小说的接受对象。显然,他这里谈到的大众文化已与印刷媒介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大众偶像的胜利”一章内容虽然是对当代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但洛文塔尔并没有像阿多诺那样选择新型的电子媒介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而是把它的研究对象圈定在通俗杂志的流行传记上,毫无疑问,这又是印刷媒介上的准/泛文学读物,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文的写作与发表虽然影响甚大,但洛文塔尔却只不过是故伎重演,因为在此之前,他已写过一篇《德国流行传记:文化的廉价柜台》的论文,(注:See Leo Lowenthal,"German Popular Biographies:Culture' Bargain Counter",in Kurt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Jr,eds.,The Critical Spirit: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Boston:Beacon Press,1967,pp.267-83.)无论从思路、方法还是所动用的媒体材料上看,“大众偶像的胜利”都有对此文克隆之嫌。所不同者只在于,一者面对的是德国的通俗文学,一者面对的是美国的大众文化。
由此看来,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可归纳如下:当阿多诺把电子媒介所制造的大众文化作为其主要的思考对象时,他实际上面对的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催生了他的现实感,而现实感又强化了印刷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批判主体与新型的文化客体(电子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他始终不渝地批判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当洛文塔尔把印刷媒介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学当成大众文化,从而作为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时,他实际上面对的是处于“过去进行时”的大众文化。这种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初级阶段,是大众文化的原始形态。像任何事物一样,它还保留着原始形态的丰富与复杂,无序与混沌。而不断地沉入过去,则又强化了他的历史感。他不得不面对那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大众文化现象,也不得不面对那些同样形成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却常常相左的理论观点。所有这些,决定了洛文塔尔更容易与文化客体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于是,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洛文塔尔也就更多走向了中立和平和。
那么,这就是洛文塔尔“骑墙”姿态形成的深层原因吗?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前,让我们暂时把以上的理解看作一种假定。下面需要做的工作首先是从这种假定中走出,然后看看洛文塔尔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还对大众文化做了怎样的思考。
理解通俗文学和文学媒介的关键词
打开《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我们会发现“大众媒介”(mass media)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这就意味着除了“批判理论”和“文学社会学”之外,洛文塔尔在进入大众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通过考察某一时期的大众媒介,从而接近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美国的传播史学者汉诺·哈特(Hanno Hardt)才把洛文塔尔看作是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乃至当代文化研究的先驱。(注:See Hanno Hardt,"The Conscience of Society:Leo Lowenthal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3),Summer 1991,pp.65-87.)
那么,当洛文塔尔走进通俗文学的世界中时,通过大众媒介这一视角他又发现了什么呢?在对18世纪英国的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进行个案研究时,他曾对大众媒介作出过如下解释:“如果‘大众’媒介这一概念意味着为大量具有购买力的公众生产的、适合于市场销售的文化商品(marketable cultural goods),那么18世纪的英国是历史上能够有效使用这一概念的第一阶段。”(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52.)洛文塔尔认为,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的文学性读者有了显著增加,妇女正在成为一种具有特殊阅读欲望的读者,而识文断字也正在成为商人与店主的职业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发展,报纸、杂志与书籍逐渐增多;由于作家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书商,所以也就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从私下捐款(通常是通过贵族赞助的形式)/有限的受众到公众捐款/具有开发潜力的无限的受众的转移。于是,“文学作品的生产、宣传与销售成了一种可以赢利的企业。这种变化既影响了文学的内容,也影响到了文学的形式,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美学上与伦理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新的;有些问题早已植根于17世纪甚至16世纪看戏的普通观众(popular audience)中了,但是在18世纪,对于作家来说,受众的潜力与喜好却被看作是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受众现在已成了他们生计的唯一来源。”(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55.)
分析一下洛文塔尔进入通俗文学与大众媒介的具体语境,我们发现他对如下几个因素进行了专门的强调,实际上,这也是理解通俗文学与文学媒介的关键词。(注:以下的归纳与总结主要依据《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中第三章的内容——“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英国18世纪的个案研究”。See 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G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2-108.)
文学读物。18世纪中期以后,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通俗小说(popular novel)逐渐开始火爆,以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帕美拉》(Pamela)的出版(1740年)为标志,英国的小说开始了它的繁荣期。先是理查逊、菲尔丁(Henry Fielding)、斯摩莱特(Tobias G.Smollett)与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各领风骚,其后拙劣的模仿与重复盛极一时,以至于一些作家都担心小说会无疾而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然后随着通俗性哥特式小说(popular Gothic novel)的出现才有所好转。在小说发展的进程中,为了追求娱乐效果,犯罪、暴力与感伤成为结构小说情节的重要元素。但是读者日久生厌,这样,求新求变又成为小说家绞尽脑汁考虑的事情,小说就这样走向了平庸。(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3,78-91.)
作者队伍。18世纪的英国拥有一支庞大的作者队伍,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文学这个行当中,因为小说写作很能赚钱。1722年,整个伦敦靠写作、印刷、出版、销售出版物为生的有5000人,到这个世纪中叶,吃文学市场这碗饭的人已多达好几万。甚至“那些想挣点外块的家庭主妇和簿记员现在也开始写小说了,就像先前的乡村牧师涉足植物学和考古学一样”。(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3,70.)到1790年代,就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作家也可以靠写连载小说获得一笔不俗的收入。(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53.)在作品的内容上,作家不得不靠多种手段来吸引普通读者以使他们对自己的小说与戏剧保持兴趣。在极端的情况下,作家甚至“像好莱坞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纤毫毕现地细致描绘攻击、暴力、恐怖的场景”。(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81.)正是由于作家的这种不择手段,“‘通俗作家’(popular writer)这一概念才以贬义的含义首次出现在了这一时期”。(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77.)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文人的职业(profession of letters)作为一种体面的(而且也常常是有利可图的)职业得以形成。确实,这种职业被搞得如此火爆以至于约翰逊(Samuel Johnson)早在1752年就把这一时代命名为‘作者的时代’。”(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56.)
阅读大众。洛文塔尔认为,虽然缺少读书人方面的可靠数字,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公众中无疑出现过两次阅读高潮。第一次出现在30年代与40年代,因为这一时期通俗杂志与小说大量涌进市场。“这种激增更多是因为读书人能读到更多的材料而不是因为读书人数量的增加”。第二次出现于这一世纪的最后20年,当《圣经》出版协会(Bible societies)、政治小册子作者与改革者一方面生产着大量的廉价文学,一方面一致抵制着一些革命作家(如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影响时,这一次“消费的增长应归因于阅读公众增加本身”。(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5-56.)而且,从洛文塔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种阅读的风尚最终波及到下层的劳工阶级那里,但是阅读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而中产阶级的文学兴趣、教育背景等等很大程度上又左右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以至于洛文塔尔干脆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middle-class realism)。(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97.)
中间人。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离不开作家与读者,但作家与读者只能形成一种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间人(middleman)的书商(bookseller)就出现了,他们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并在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洛文塔尔指出,在蒲柏(Alexander Pope)时代,既有好书商也有坏书商。前者如雅各布·汤森(Jacob Tonson),他因出版《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德莱顿(John Dryden)与艾狄生的大量著作,而赢得了许多作家的敬佩。后者如埃德蒙·柯尔(Edmund Curll),他善于开发他们那个时代的丑闻,做一些生意兴隆的买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常常投入大量精力去寻找那些吸引人眼球的题目,为传记和色情小册子进行粗俗的广告宣传。柯尔因此而臭名昭著。在这一时期,虽然一些作家不能忍受书商的所作所为,甚至有个别作家能够独立于书商,但书商与当时的主要的作家都保持了一种朋友关系,作家也不得不依附于书商。因为作家失去了宫廷与贵族的庇护之后必须养家糊口,他也就必须寻找新的庇护人。由于书商的介入,文学成为一种商品,书籍的出版与销售成为一种主要的工业。同时,写作与阅读也常常变成了在书商引导下的写作与阅读。(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8-62.参阅[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7页。)
印刷媒介。通俗文学的发展无法脱离完善的出版机构和机制。也正是在18世纪,各类印刷媒介物开始大量出现。比如,与宗教和政治团体扶持的小册子完全不同的杂志,成为这个时代最新也最富有特色的媒体。1730-1780年,每年至少有一份新的杂志会与伦敦的公众见面。现代杂志的所有形式,几乎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原型。比如像妇女杂志、戏剧随笔月刊、婚恋故事杂志、新闻摘要、书评、图书摘要等等就办得风风火火。与此同时,报纸也在这一世纪获得了自立与自尊。自立是因为识文断字的人的增多,自尊是因为通过斗争报纸成功地脱离了宗教与政治的控制。而印刷业与出版业也方兴未艾,根据后来的估计,伦敦的印刷机在1724年有75架,到1757年已增加到150-200架。每年的新书在这一世纪则以四倍的速度增长。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与携带,出版商设计出了小开本的图书,又小又轻的图书遂在18世纪下半叶走俏一时。(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2-53,54-55,56,53.)
传播渠道。文学作品要想大规模地走向阅读大众,离不开特定的传播渠道。从洛文塔尔的分析可以看出,至少有两个地方成为了文学传播的主要场所:其一是流通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ies),其二是咖啡馆。第一家流通图书馆出现于1740年,到18世纪末,大约有1000家图书馆分布于全国各地。读者每年只要交15或20先令,就可以借阅馆藏的任何书籍和杂志。低廉的借阅费既吸引了中产阶级读者,也鼓励着下层劳工阶级走到了图书馆中。与此同时,“文学社团与阅读组织遍及整个伦敦,并最终被伦敦以外的各地所模仿。城市与城镇中的咖啡馆不断成为中心,人们聚集在那里阅读或听人大声念着报纸和杂志上的东西,并逗留其中讨论他们所读所听之事。”咖啡馆是表达思想、形成趣味的重要场所,作家与中产阶级的读者和听众常常在这里展开热烈的对话;咖啡馆又是制定中产阶级道德新法典和建立中产阶级美学观的重要基地,斯蒂尔(Richard Steele)、艾狄生(Joseph Addison)等人作为《闲聊者》(The 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卫报》(The Guardian)等报刊的编辑,常常每天泡在咖啡馆里,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所参与的谈话写成文章,然后在报刊上发表,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与美学观就这样在人们心中落地生根了。(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57-58.参阅[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4-25页。)
以上是我们从洛文塔尔的梳理与分析中归纳出来的、理解通俗文学与文学媒介的关键词。那么,通过这种归纳,我们又会发现怎样的问题呢?
第一,作为初级阶段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显然是在一股合力之下诞生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市场化的逻辑规定着,它也因此而变成一种商品,通俗文学作家也因此而成为书商和出版商的雇佣劳动者。这一时代的作家笛福(Daniel Defoe)指出:“写作正在成为英国商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书商是制造厂主或雇主,众多作家、作者、抄写者、次等作家,以及所有舞文弄墨的人,都是受雇于这些所谓制造厂主的工人。”(注:转引自[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既然作家受雇于书商,也就意味着作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迎合书商,作家也不得不因此而降低作品的格调,甚至改变写作的手法。伊恩·瓦特(Ian Watt)在谈到这种变化时指出,至少有两种考虑鼓励着作家在作品中进行着长篇累牍的描写:“首先,很清楚,重复的写法可以有助于他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读者易于理解他的意思;其次,因为付给他报酬的已不是庇护人而是书商,因此,迅速和丰富便成为最大的经济长处。”(注:[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4页。)与重复、迅速、丰富等写作手法和写作手段的变化相对应的是文学形式的变化,因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作家看到与韵文相比,散文写作既容易(可以不假思索、信笔如飞)又有利于赚钱(可以把作品搞得冗长累赘以便赚取更多的稿酬)。(注:[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5页。)与此同时,在商业原则的支配下,通俗文学又被输入了新的内容,暴力、凶杀、色情、猎奇等等,这些东西原来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因为书商和市场,它们却获得了不断出场的重要理由。种种事实表明,通俗文学虽然是原始形态的大众文化,但是它已经拥有了洛文塔尔所概括的大众文化的全部特征。因此,当洛文塔尔把通俗文学看成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xii.)时,这种定位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但问题是,在通俗文学的生产机制与环境中,却同样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如约翰逊、笛福、菲尔丁等),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看来已成经典。而且即便是那种恶劣的机制与环境,他们也依然在其作品中渗透了严肃的思考。有人指出:“早期的英国小说家,几乎无人不把教育读者、改进社会当作写书的重要目的:斯威夫特抨击肮肮的权力斗争和知识界的弊端;菲尔丁揭露虚伪、谎言和暴虐;笛福颂扬个人在自然或社会逆境中的奋斗;理查逊则用清教道德教育妇女洁身自好,做贤妻良母。”(注:吴景荣、刘意青主编:《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如果我们把《鲁滨逊飘流记》、《帕白美拉》、《克拉丽莎》、《汤姆·琼斯》看成通俗小说,那么这样的通俗小说显然与那种专写拳头加枕头的通俗小说存在着区别。这也就意味着早期的大众文化存在着它的两面性:一面是商业原则支配下的他律性,一面是没有完全陷落或在陷落中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品格的个体所支撑起来的自律性。洛文塔尔在讨论到审美趣味和文学标准等问题时,应该已经意识到了通俗文学的这种两面性,但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述。
第二,如果说通俗文学本身具有两面性,那么承载通俗文学的大众媒介,其两面性的特征也比较明显。通俗文学的传播媒介是报纸、杂志和书籍,而这些媒介之所以能够出现,完全是印刷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早期的大众文化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必然得接受印刷文化对它的规定。那么,印刷文化会对它作出怎样的规定呢?首先,它必须是借助于语言文字写作出来的文本,这种文本又以象征性与想象性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其次,接受这种文本需要依靠读者的线性阅读,也需要读者想象的充实与填补。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区别时认为:文学完全依赖于一种象征的手段,“词的象征必须通过思考的过程被翻译成物体的形象、感觉的形象、概念的形象。活动电影通过视觉直接到达我们,语言却必须从概念的理解之幕中渗透进来。而这种概念化的过程虽然和视觉有联系,而且往往以视觉为出发点,却代表着一种迥然相异的经验形态,一种不同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注:[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这意味着小说虽然靠形象说话,但读者读出来的形象与看电影看到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尽管通俗文学会呈现出特别逼真的描写场面,甚至它所营造的情感世界会给人们带来危害,(注:比如,洛文塔尔认为感伤小说给年青女子造成的危害要大于它对年青男子的危害。See 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85.)但是它的逼真或危害与电子媒介中的相比毕竟要逊色一些,因为它们毕竟经过了文字之网的过滤。另一方面,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读者“填补不定点”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想象的参与,而想象的乐趣又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快感。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指出:“读探案小说时,读者要参与进去与作者共同创造;其原因很简单:小说的叙述中略去的东西太多。大网眼的长统丝袜更美观,因为眼睛必定要代替手掌去填充并完成整体的形象。”(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印刷媒介上的读物更易于建构出一个想象的空间,读者的想象力也更容易启动起来。
在分析18世纪英国的通俗文学时,洛文塔尔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去思考印刷媒介的功能,但是当他后来把早期的传媒与现在的传媒进行比较、并不得不承认前者显得更人性一些时,却透露出了与我们以上的分析大致相同的思路:
当然,大众媒介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奴役和愚化人性的趋势却变得更加厉害了。早期阶段的大众媒介还提供了一种逃避日常生活压迫的可能性,还为想象预留了一些自由游戏的空间,而现在的大众媒介已完全让想象失去了自由。(注: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239.)
早期的大众媒介指的是什么?显然是印刷媒介;现在的大众媒介指的又是什么?无疑是电子媒介。两害相权取其轻,当洛文塔尔在媒介变化的历史中思考时,他应该更加看重印刷媒介。而由于通俗文学恰恰是印刷媒介建构之下的产物,那么,过去的通俗文学与现在的文化工业相比,哪一个更符合人性一些,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许多学者在谈到这一个时期的文学发生史时,都注意到了读者大众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洛文塔尔也不例外。而从洛文塔尔的分析思路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读者大众几乎是可以和中产阶级划上等号的。(注:洛文塔尔所谓的中产阶级包括富裕的商人和地主、店主、职员、学徒,此外,富裕而有文化的、雄心勃勃的农场主也开始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而与杜比尔交谈时,洛文塔尔又进一步指出:在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圈子里和无产阶级大众那里,完全不存在什么阅读的问题,因为他们超负荷工作,甚至没有钱买蜡烛以供阅读。See 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97.See also 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27.)也就是说,由于“能够阅读只是那些注定要从事中产阶级工作——商业、行政机关和各种职业性工作的人一项必需的技能”,由于与一些高雅的文学形式相比,18世纪的通俗小说“更接近加入了读者大众队伍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能力”和接受水平,(注:[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7-38、40页。)所以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实际上是以中产阶级读者大众为消费对象的。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的和逐渐确立起来的自信,他们已无法认同于上层贵族的价值观念,却拥有了自己的审美趣味(比如,在他们的文化要求中,他们更关心感情的呈现而不是理性的论辩,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不允许在纯粹的思想追求中获得快感),这时候,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主要敌人已不是上层贵族阶级,而是下层的劳工阶级。(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97-98.)与此同时,书商开始琢磨中产阶级的趣味,作家不得不通过书商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报纸与杂志又在捕捉和加固这种中产阶级的趣味。中产阶级的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格罗斯认为,在洛文塔尔论述的语境中,“大众文化已变成中产阶级文化,反之亦然”。(注: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127.)
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这意味着洛文塔尔的思考又与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观点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在阿多诺等人的论述中,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要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要不让人联想到的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大众。但洛文塔尔在历史的梳理中却把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联系到了一起,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产阶级的教育水平、经济特征和阶级属性,决定了中产阶级一开始的文化要求不可能非常高雅。因此,当通俗文学中充斥着凶杀、暴力、色情、感伤、滥情等低俗、庸俗和粗俗的内容与格调时,这固然是书商、作家与市场联合打造的结果,但中产阶级的受众之所需显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洛文塔尔分析与论述时的主旨之一。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中产阶级的读者大众同样是印刷媒介文化建构之下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哈贝马斯关于“文化批判的公众以阅读为基础”(注:参阅[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的论断正确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读者尽管已经在向“文化消费的公众”转型,但因为他们必须“阅读”,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文化批判公众”的特征。而中产阶级的这种特性又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或制约了通俗文学的媚俗倾向,从而使早期的大众文化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早期的通俗文学具有两面性,早期的大众媒介具有两面性,早期的中产阶级显然也具有两面性,所有这些,对于洛文塔尔又意味着什么呢?
通俗文学背后的视野
如前所述,洛文塔尔是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来观照大众文化的。把通俗文学看作是大众文化固然没错,但越是深入到形成通俗文学的语境当中,越是把早期的通俗文学作为他的考察对象,洛文塔尔也就越是会面临一种困惑和迷惘。因为按照20世纪已经发展成熟的大众文化模式和由此形成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去思考18世纪的通俗文学,固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这样的思路显然也适用于对早期阶段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但问题是,如果完全用后来的理念去梳理以前的现象,又会面临删繁就简的危险。因为早期阶段的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未完成状态,其丰富性要远比想象得更为复杂。通俗文学本身、作为文学的大众媒介和中产阶级阅读大众所体现出来的两面性,实际上也正是早期大众文化丰富性、微妙性和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而事实上,洛文塔尔所面对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也正是一个高雅文化式微、大众文化崛起的转型期,是两者并陈、杂糅、似分未分、未分已分的模糊地带。洛文塔尔后来也坦率承认,这一时期雅俗艺术的区别还很不明显,许多作家像理查逊、哥尔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那样,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作为文学生产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自己究竟是为市场写作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写作。而从印刷工业的发展方面看,也只是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文学性和阅读性的材料的迅速增加,才出现了一个“大文化工业”(big culture industry)的时代,因为印刷技术使印刷品变得便宜了,越来越多的书籍、小册子、杂志和报纸也才变得唾手可得。而在18世纪,所谓的阅读大众还只是局限于少数几个城市文化中心里的中产阶级阶层。(注:See 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26-127.)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阅读大众其实只能称之为“小众”。
洛文塔尔晚年的这种表白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种表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面对通俗文学时常常是客观地分析而不是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批判。批判意味着对事实的过滤与澄清,也意味着对复杂性的简化,而客观地分析却常常能对事物的丰富性进行还原,也才能呈现出通俗文学生产与消费中更多的、往往被人忽略的“细节”。这些细节实际上是无法被现代大众文化理念除尽的余数,把它们呈现出来,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的需要,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参照。因此,当洛文塔尔面对早期的大众文化同时又进行客观的分析时,“中立”可能是他能够采用的最理想也最舒服的一种姿态。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洛文塔尔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时而强硬的批判立场呢?——在多数情况下,或者当他面对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具体的文本时,洛文塔尔常常显得中立平和,而一旦从历史语境中抽身而出,或者一旦需要他“表态”时,(注:比如,当采访人格鲁兹(Peter Glotz)指出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他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存在着分歧时,洛文塔尔甚至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我的激进跟我的同事与朋友没有任何区别。”See Martin Jay,ed.,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252.)他又常常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立场的冷峻。为什么洛文塔尔又会拥有这样一种姿态呢?
自然,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是“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立场对他的召唤,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而并非深层的原因。因为在洛文塔尔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这就是他对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崇敬、偏爱和褒扬,以及他对真正的文学作品所作出的特殊理解:
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与理论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描绘出新的经验并为这种经验命名。艺术家渴望重新创造出独特且重要的东西,这种渴望常常引导他去探索至今还无法命名的焦虑与愿望。他既不是一架清晰的记录机,也不是一个表达含糊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专门的思想家。(注:See Leo Lowenthal,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Boston:Beacon Press,1957.)
让作家成为一个思想者,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艺术经验,这是洛文塔尔心目中的理想,而什么样的作家才能体现出洛文塔尔的这种理想呢?在《文学与人的形象》一书中,我们看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歌德、易卜生等作家出现在他分析的笔下。这些作家及其作品虽然是出于社会学分析的需要而被邀请出场的,但显然也代表了洛文塔尔的那种理想。而且,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具有“古典”意味的作家,当代的先锋作家并不在洛文塔尔的考虑范围之内。
指出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白,虽然洛文塔尔是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来观照大众文化的,但是在通俗文学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视野,这就是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的视野。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思考大众文化,可以更深入更细致地进入大众文化之中,从而确立洛文塔尔所谓的大众文化的特殊性;在真正的文学的视野中进一步思考通俗文学,才能对通俗文学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当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可以把这种批判看作是他用更高的文学尺度衡量通俗文学时所进行的价值判断。
对通俗文学进行这样的价值判断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判断显然也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像阿多诺一样,洛文塔尔同样也是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迷恋者和维护者。当然,就是在这一层面,他们也依然存在着区别:阿多诺主要是因为现代的先锋艺术(比如勋伯格的音乐)而走向了精英文化崇拜,洛文塔尔则是在对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在对历史中已经出现的伟大作家的遥远呼应中走向了高雅文化的既定秩序。当他进入历史中的通俗文学时,他还可以保持一种社会学家平静的心情和理性的目光,而当他面对历史中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时,伟大作家的幽灵不但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甚至使他拥有了某种文学家的激情与冲动,从而也使他对艺术与大众文化不得不形成一种潜在的对比。而由于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全部体验更多来自于历史记忆中的通俗文学,由于早期通俗文学那种不尴不尬的特殊状态,所以,无论他怎样批判大众文化,他的批判与阿多诺相比都变成了一种辅助性的东西,他的批判的意义似乎只是在为阿多诺、从而也是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种历史的依据,而当他呈现出与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相左的观点、同时这种观点又是建立在一个宽广的历史平台之上时,他反而显示出了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中,洛文塔尔也就只能长久地逡巡于雅俗之间,以自己那种独特的研究和思考凝固成那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