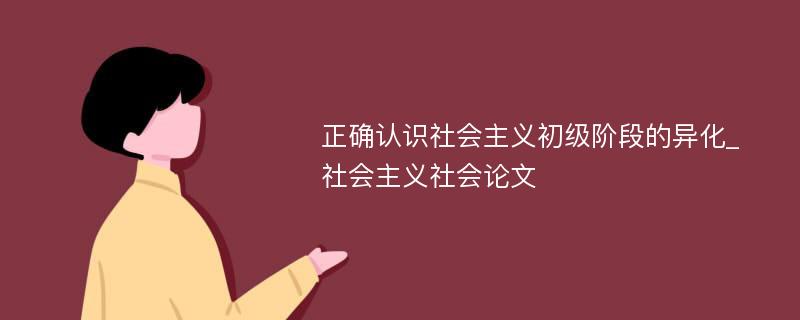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异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认识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生活中的异化问题,不仅许多国外思想家曾予以关注,而且也引起了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在“文革”结束后展开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以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理论观点,还不能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那么多思想家所关注的异化问题,是不能用简单回避的办法来对待的。恐谈异化症必须克服。不是能不能、应当不应当研究异化的问题,而是以何种历史观来研究异化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异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其历史作用及其消灭的历史条件,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并对其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
一、异化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
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异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事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概念出发。不过,要确认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异化,仍然要解决一个概念的问题,一个指称的问题:什么是异化?
“异化”概念,不仅在哲学史上有过不同的含义,而且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含义也不同。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异化的:异化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即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这里所说的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人应当有这样的本质,不然就不是人,是异化了的人。所以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中世纪的人不是人(是“政治动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也不是人——不仅工人不是人,而且资本家也不是人,他们同是异化了的人的两种存在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异化概念,也多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异化概念。从对异化这种理解出发来看现实生活,当然也可以说生活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中的人还是异化了的人:人还没有实现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现实的人不是人。我不赞同用这样的异化概念来理解现实生活,这是因为,这种异化观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如马克思后来所批评的,是用理想要求现实而不是具体地历史地来理解人,它只会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抽象的批判、否定,既不能科学地揭示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也找不到克服异化的现实道路。
我主张马克思1845年以后对异化的理解。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人的存在不可能与他的本质相分离(他把“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命题称为“荒谬的判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页。)。因此,异化不再被理解为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相分离,而是理解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或这样一种“经验的事实”“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人们活动的产物成为统治他、与他对立的一种社会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从对异化的这种理解来看现实生活, 我以为,异化仍然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经验事实,如:
宗教异化。人们创造一种关于支配我们命运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力量在观念中歪曲的表现),对这种神秘力量顶礼膜拜,这就是宗教异化。如果说,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宗教异化曾经有所抑制,那么,在现实,宗教异化有发展之势。寺庙拆了再建,菩萨打了再塑。没有寺庙,没有菩萨,也可对着一块石头、一个墙角甚至一块空地烧香叩头。一个数字,一个号码,也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成为崇拜的对象,等等。
劳动异化。劳动过程及其产物不属于劳动者,成为与其相对立的一种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劳动异化。劳动异化首先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另一个人。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企业中,这种异化是明显的。公有制本质上不会产生劳动产品的异化。但由于现实公有制的不发展、不完善,也会产生这种异化:特权者通过贪污、受贿、不公平分配等途径占有劳动者的产品。劳动异化还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过程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另一个人;劳动过程的片面性,使劳动者片面发展。因此,劳动者只是由于外在的压力(谋生的需要)而劳动,他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只要外在压力一解除,他就会逃避劳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私有制企业的劳动中,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公有制企业中。劳动异化还表现为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还生产另一个与他对立的人。在私有制企业中,这另一个人就是企业主;在“公有制”企业中,这另一个人就是种种特权者。
商品异化。商品生产是一种异化的生产。在这里,异化表现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物统治着人。“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是商品异化的典型表现。
市场异化。商品交换形成市场。市场不是各市场主体自愿联合的结果,而是各市场主体活动自发形成的结果。市场一旦形成,对于各市场主体来说,是一种必须服从的力量。不是人在驾驭市场,而是市场在驱使着人。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职业异化。工作的职业化是强迫性分工的结果、表现。职业化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人必须选择一定的职业以谋生。职业对他来说是一种外在强制的力量。职业化使人片面地甚至畸形地发展,如马克思所说:“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 页。)在我们的社会里,工作还是职业化的,人们的活动范围都是特定的,人们还不可能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得到全面发展。
政治异化。我们的国家政权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人民政权和共产党不会产生政治异化。但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必定会这样那样地反映到国家政权和党内来,商品交换原则也会渗入政治生活中。局部的政治异化已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表现为党和国家的某些干部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主仆颠倒,利益错位,横行不法,欺压百姓,等等。如果我们不引起警惕,党和国家政权的整个异化的危险性也是存在的。
凡此种种异化现象,不正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吗?因此,在“文革”结束不久后人们争论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会不会产生异化的问题,到了今天,历史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今天所要进一步认识的,不是有没有异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异化问题。
二、异化的根源在于强迫性分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裂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是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产生异化的根源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可能再产生异化。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错。确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确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确立了逐步消灭异化的条件,并可能使异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但是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已经消除了异化产生的根源,却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必然经历各个不同的发展的阶段。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反映经济制度和为经济制度服务的上层建筑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与这些相联系,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也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保证,而是由种种现实历史条件决定的状态,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取决于这些历史条件的状况。认识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历史条件来看待异化问题。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马克思认为,异化的直接根源是自发性的或强迫性的分工,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裂。“分工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驾驭着这种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分工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分工是一种强迫性的分工。人们必须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特定范围的活动,不如此,他就不能获得自己生活资料。分工是由生产资料的特定占有方式决定的。在私有制社会中,“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这就是说,在私有制社会中, 异化的根源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客观状况决定的。这就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上,异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它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产物。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异化是人类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私有制彻底消灭了,社会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强迫性的分工没有了,在这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38页。)
马克思虽然预计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但这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成熟,从而为共产主义准备好了物质基础以后发生的,因此,那个过渡时期结束,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异化现象也就消失了。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由于作为历史起点的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的要求,而且远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水平,因此,这个历史过渡时期将是很长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异化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生产关系及由它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归根到底要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以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恰当地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建立一种“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企图抹平利益差别,企业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利益驱动力,由于脱离了生产力的现实状况,这种做法束缚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改革的首要的或本质的任务,就是要调整经济关系,建立适合现实生产力状况的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五次人表大会第一次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有公有制经济,有私有制经济,有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公有制济中,还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区别。公有制经济,还有一个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还有“两权分离”的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混合经济的问题。在公有制企业中,还有一个经营者(厂长经理阶层)和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不同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实际占有方式的多样化,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了私人(或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才能有利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有制结构调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是人们劳动交换关系方面的变革。这两方面的调整,都是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商品生产者,市场主体,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仅就生产者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的身份来看,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私人(或局部)利益成为最高利益。“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当然,作为公有制企业的商品生产者还有另一种身份,即作为集体或全民所有者的身份,从这一身份来看,集体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应当是最高利益。在现实中,这二者总是处在一种矛盾的关系中。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两权分离”以后,再加上不可避免的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分工和制度上的不健全,这一矛盾将加深,私人(或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某种程度的分裂不可避免。
商品交换形成市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作为人们的一种经济关系,是自发地形成的,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市场,一方面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独立于、外在于每个个人的一种社会力量,即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每个个人都不能驾驭这种力量,而受这种力量的控制。市场愈发达,这种异己力量也愈强大。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再是一国的经济,而是世界的经济,一国的经济无可避免地进入世界经济联系之网。世界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主体来说,都是一种更为巨大的异己的力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再一次证明了世界市场对每个市场主体来说的异己性。
在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上形成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的关系(实际的关系而不是名义的关系),使得利益分化和分工成为是必然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论实行何种经济体制,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以及分工都是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推进了、发展了利益分化和分工而已。而只要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裂,只要有强迫性分工,那就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和自己的活动的关系必然是一种“异化的关系”。
三、通过异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达到消灭异化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念:异化是不好的,是恶,是现实中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对异化的这种单纯的恶感,是由人道主义的立场产生的:异化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幸福,得到全面发展;我们都是人,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兄弟姐妹,应当互相亲爱,互相拥抱。自从费尔巴哈以来,或更远地说,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道主义者们都在憎恶异化,呼唤人性的复归。1843~1844年间的马克思,也曾受此种态度的影响,对异化持批判否定的态度。
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当然继承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追求,但不再把这一理想状态看作是人的普遍的本性,不再认为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都应当是这样的人。必须历史地看待人的发展,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这种历史条件是不能由人自由选择的。从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进入野蛮的始隶制,再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到充满血泪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人类迷误的历史,而正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是人的自由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虽然这种自由还是以另一种不自由为代价获得的一种自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们才能达到过去历史中不可能存在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异化才不再存在。不能用现在的人的发展状态来要求过去的人,也不能用将来的人的发展状态来要求现在的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异化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的一种存在的状态,对异化的评价不能以抽象的人的本性为根据,而只能以现实历史条件为根据。假如现实历史条件决定了人只能是这样,假如这个现实历史条件表现了历史的进步,那么,由此必然产生的异化,也就具有了历史进步意义。假如产生异化的历史条件表现了历史的退步,或表现为一种陈旧的关系,那么,由此产生的异化就是一种消极的历史现象。
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表现了历史因素的巨大的复杂性。在这里,有封建主义的因素,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这些现实的历史因素的作用是复杂的,由此产生的异化现象也必然是复杂的,对此很难作一个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评价。改革是对原有历史条件的一种改革,它会在某些方面抑制某些异化现象,同时在某些方面发展着某些异化。从总体上说,异化是在发展着,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它表现了现实历史条件的进步。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不再对异化采取简单的批判否定态度,而是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异化的历史作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异化(这里主要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异化)的进步历史意义在于:
第一,异化是人个体获得独立性和素质的多方面发展的必然的历史形式。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个体是不独立的,依赖于一定的群体,虽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们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因此,“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注:《马克思恩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9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人虽然依赖于物,但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是独立的,并且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发展了自己的丰富的关系和能力,这是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阶段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二,通过“物化”推进社会关系的广泛发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之间只有血缘的、地域性的狭隘联系,市场经济则打破了人们社会联系的狭隘性,通过商品、货币的物的中介,把人们的社会联系发展为极广泛的联系,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是以异化、“物化”的形式出现的,但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注:《马克思恩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
第三,通过异化的发展才能提出消灭异化的任务。马克思说:“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注:《马克思恩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7 页)异化的发展之所以必然会提出消灭异化的任务,是因为异化本身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个体独立,另一方面,又使每个人都全面地依赖于异己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个体是平等的和自由的,另一方面,个体之间有着更多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一方面,它使个体的能力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人处于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中;一方面,它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使人服从于物的统治;一方面,它使社会联系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这种社会联系成为对人来说的一种异己的力量,等等。异化的这种历史作用表明,异化只具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不具有永恒的历史必然性。它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不是其理想状态和顶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异化的不合理的一面必然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所以异化的发展本身必然会提出消灭异化的任务。
第四,异化的发展为消灭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马克思说:消灭异化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1页。),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
现实生活中异化的发展是一定现实物质生活条件变革的必然结果。所以,不要异化的发展,就无异于不要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例如,不要调整经济结构,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不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要发展分工,等等。而不要这些历史条件的进步,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虽然能减少、降低异化的现有形式,但必然会有另一些形式的异化。这不是向消灭异化前进,而是更远离我们的理想。说共产党人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异化是正确的,但作为现实的任务,则是错误的;异化的消灭不是一个量的递减过程,更不如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通过异化一定程度的发展来达到最终消灭异化。
问题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所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对异化的一种限制。如果我们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那就不能允许异化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得到全面的发展,而应当使异化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既要允许异化的发展,又要控制其发展,这是一个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好这个矛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关重大,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的历史命运。
标签: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