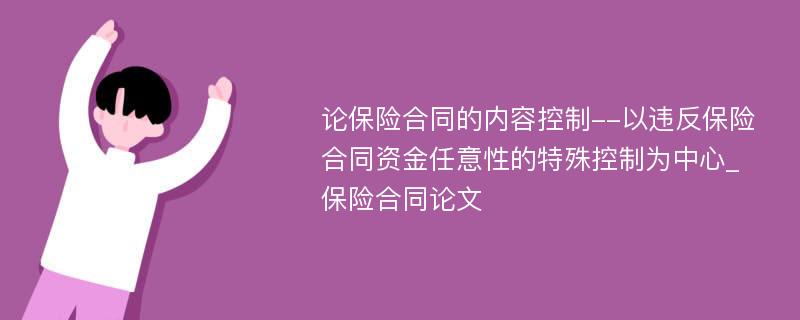
论保险合同的内容控制——以对保险约款违反任意性规范的特别控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对论文,保险合同论文,内容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之提出
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合同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订,投保人并无参与其中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从而为保险人排斥任意性规范、拟订不利于投保人条款的行为提供了合法的机会。现实中,往往会出现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事先拟订减免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之条款的情况,也即人们常说的“霸王条款”。保险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如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原则上归于无效,已无疑义。但排斥或变更任意性规范,会导致何种法律后果?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尚无明确规定。考察国外保险立法,对保险人这一行为都设有一特别条款予以控制。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一节之15a条规定:“违反……条致不利于要保人的约定,保险人不可以主张。”《意大利民法典》第1932条规定:“第……条的规定,如果不是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则不得违反。”《澳门商法典》“保险合同编”第96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本编之规定不得变更,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除外。”上述各国和地区保险法之规定,学理上称之为“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其意旨在于“对保险合同中违反保险法上之任意性规范的约款予以内容控制”。①那么,该特别控制条款的性质是什么?其合理存在的法源及法理基础是什么?功能又是什么?各国和地区之立法规定是否完全妥当?我国保险立法应当持何种态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拟对这些问题逐一予以探究,以期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有所裨益。
二、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规范性质:禁止性的效力规范
私法上的规范依其适用而言,可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依其内容又可分为强制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即法律要求行为人负担某种作为义务,而禁止性规范乃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不作为义务。进而言之,依据禁止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可将禁止性规范区分为取缔规范与效力规范:违反前者,法律行为仍为有效;违反后者,法律行为无效。两者的区分标准,学者认为应综合法规的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即非以该违法行为为无效,不能达其立法之目的者,为效力规范;而仅在防止该行为之事实上之行为者,为取缔规范。②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取缔规范往往从行政管理的目的出发,而效力规范往往从保护合同一方利益出发,以实现双方利益之平衡。
考察前述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的特别控制条款,即可发现,其均规定保险人不得违反相关的规定作出不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约定,以对保险人课以一定不作为的义务,从而限制保险人的契约行为。因此,保险法上所谓“特别控制条款”,在性质上属于禁止性规范无疑。该特别条款的存在,本为保护身处弱势的投保人免受不公平合同条款的侵害,而享受公平合同条款的待遇,若不使违反该规范的合同条款无效,不足以保护投保人。因而此一特别条款应为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一旦违反,归于无效。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保险合同条款违反此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是该条款无效还是保险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保险人违反此一禁止性规定,在保险合同中作出不利于投保人之约定时,其行为之法律效果如何?是否无效?是该约定无效还是合同无效?对此问题,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所采“不得”二字,本身并不能表明该行为的法律效果,因为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其无效。笔者以为,依民法的规定,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原则上应归于无效。这一无效往往是该行为完全无效,即合同本身的效力受到影响。但“如果某个协议所违反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合同当事人一方免遭剥削、不公平或风险的侵犯,则整个合同无效将会和这一保护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应受到保护的合同一方的所有好处也会随着整个合同宣布无效而消失殆尽”。③因而,“如果禁止性的规定只在于对某方当事人的保护,则规定法律行为完全无效就有可能事与愿违”。④因为受保护的一方通常是期待合同能够履行的。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规定,保险人拟订的条款如违背法律的任意性规定时,不得不利于投保人,其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使其得到保险的保障。而保险合同的有效与履行对投保人而言意义重大。将保险合同中违反此一特别条款的约款归于无效,而保持保险合同的效力,符合此一特别条款为保护投保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的立法目的。概言之,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条款,属于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保险人不得违反;一旦保险合同中出现有相较于立法规定而不利于投保人的合同条款时,该条款无效,但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三、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正当性分析:结合法源及法理基础之综合考察
依私法之原理而言,自由决定合同内容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由予以干涉应当具有正当性的理由。保险法属特别私法,保险合同当然亦应遵循上述原则。问题是,保险法上之特别控制条款的存在,使得保险人违背保险法上任意性规范的行为受到规制,该条款既然是对保险人的契约行为予以规制,是否有干涉契约自由之嫌呢?因此,保险法上所谓特别控制条款存在的正当性理由何在,殊值探讨。鉴于该特别条款在我国保险立法上的缺失,笔者在此参酌德国的相关立法及学说,予以分析。
(一)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的法源考察
保险合同属于合同之一种,且具定型化特征。此外,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强势之保险人,另一方多为弱势之保险消费者。保险合同的诸种特征使得保险合同既受保险法的规制,又受特别合同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制。在立法上,特别合同法及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应成为保险法的法源,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得与两法的精神相违背。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确立的特别控制条款,正是依以上两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如1976年通过的《德国一般交易条款法》第9条规定;“(1)一般交易条款之约款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而不合理地不利于使用人之相对人者,无效。(2)有疑义时,约款若有下列情形之一,推定有不合理的利益:A.该约款与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符合且规避该基本原则……”
保险合同约款所偏离的法律规定,可能是一般合同法律规定、一般债法的规定或者是有关合同所属的特殊合同的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法的规定。这种偏离均应受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是“任意规定之立法意旨”的审查。至于何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判例及学说上有所分歧。德国法院在实务上将其区别为“具有基本正义内涵”的法律规定和“仅含方便目的内涵”的法律规定两者。定型化契约条款若排除前者的法律规定时,该约款即被推定为无效;如其排除的是后者的法律规定时,则不生约款推定为无效的问题。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它们与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不同,是实质上具有公平正义内容的规范,其判断的标准“取决于整体的衡量标准是否通过改变该规则而产生明显的不利……如果所涉及的是特殊的具体类型的合同,那么人们在理解法律规范的‘基本思想’时也应考虑到这种合同类型的‘精神’”。⑤
保险立法的精神在于通过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投保人的利益,以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利益。这一立法精神不但表现在强制性规范中,也通过诸多任意性规范表现出来。这意味着一旦保险人通过保单约款背离保险法的任意性规范,从而作出不利于投保人的约定时,即与保险法上任意性规范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违背,这一问题便可通过设立一特别条款予以解决。即通过设立一特别条款对保险合同中的那些代替或补充任意性规范的约定是否合适进行审查,以保护投保人的合法利益。
(二)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的法理考察
从私法原理而言,为尊重私法自治,当事人可自由决定是否采用任意性规范作为契约条款,国家与他人均不得干涉。而保险立法上的特别控制条款,却是利用任意性规范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予以规制:保险合同中的条款不得违背保险法上任意性规范的规定,除非更有利于投保人,否则不发生保险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为何要对当事人违背任意性规范的行为予以规制?或说此一特别控制条款存在的法理依据何在?笔者认为,此种依据有二:
其一为体现任意性规范本身的公正价值。任意性规范虽为当事人意思的补充,但并非与价值评价无涉。事实上,在现代民法之“公平”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任意性规范是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大致公平的照顾,体现为法律对其权利义务的一种原则性分配,这是合同中均衡与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合同中的均衡与公平原则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狭义的等价有偿原则,即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至少必须具有相近的价值;二是指公平地分配与合同相关的负担和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合同中的均衡与公平原则广泛地支配着任意性的‘制定法’……如果说,这些规定不仅仅是立法者任意制定的原则,而是基于某些合理的考虑(毫无疑问,它们通常也的确如此),那么这些合理的考虑就是以合同中的均衡与公平的指导思想为依据的。”⑥因而我国有学者认为:“由于任意性规范不仅为妥当性的考虑而设,而且具有对正义要求的功能,对于任意性规范效力的排除要符合任意法本旨上所作的正义的要求,同时,应符合法律与公平始得为之。任意法的立法意旨不是使当事人恣意将立法者所指定的法律效力废弃,而是容许当事人以其他规范来代替原来的法律规定,代替原来法律规定的规范至少应与原来之法律一样对契约的公平正义加以维护,因此亦需要公平观念的严格审查。”⑦由此可见,所谓任意性规范,并非绝对“任意”,是否允许排除适用,仍有价值衡量的必要。保险立法上的该特别条款存在的法理即在于,当保险合同条款与被变更的任意性规范之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基本思想不一致时,就意味着其给投保人造成了不适当的利益损害,因而应当是无效的。
其二为定型化契约的弊病所致。一般而言,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不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原则上应归于无效。而法律行为虽排除任意性规范之适用,若系双方当事人之协商而成,依契约自由原则,亦应认为约定有效。法律准许当事人合意排除任意性规范,其前提为:当事人既经自由磋商,如决定以其约定替代法律的规定,则当事人自有其考量,且双方当事人既在平等的缔约地位及自由之意思决定下,合意排除任意性规范,法律即应尊重该合意,而认其为有效。⑧但于定型化契约,则不可一律认其排除任意性规范的约款有效。原因在于,定型化合同的条款名为约款,实为拟订人的“自治立法”。由于拟订人在经济上、法律知识上的优势,相对人并无与其抗衡的能力;且通常情形下,由于同类型契约均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定型化约款,相对人并无其他选择之可能性,而必须接受该项内容的定型化约款,故相对人同意使用该项约款,是否出于其真正的自由意思,显然可疑。实质上拟订人有可能将立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加以变更、废止或补充,学者Mullereisert更称此种现象为“逃避法典者”。⑨若定型化契约使用人能立于公平正义的立场,兼顾对方利益,则对任意性规范的排除适用并非不可。但事实上,其之所以排除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目的多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则其是否同时兼顾相对人的利益,颇有可疑。这使得相对方“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任意性法律规定本应享有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受到了优先于这些规定适用的一般交易条款限制了,甚至已经被排除了”。⑩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任意性规范的作用。对于任意性规范的原有功能无须一概否定,然而至少在对定型化契约条款的规制上应当强化任意性规范的作用。因而,以契约条款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若欲生效力,必须使该种排除有正当理由。此一正当理由应理解为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公平合理,或不得不利于定型化条款接受方。“从现代各国的立法实践上看,对于定式合同排除适用任意性规范的现象进行强行性规制是合同法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些立法限制的主旨在于维护任意性规范的权威性和合理适用。”(11)因此,“一方当事人以定型化约款排除法律的任意规定者,即不宜当然认为业经他方同意,而剥夺他方于事后请求法院审查该约款效力之机会”。(12)这使得某些任意性规范成为“半强制性规范”。(13)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于排除保险法上的任意性规范之时,多另以于己有利的条款予以代替。可见,契约自由原则为保险人以约定的方式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创造了客观条件。保险人正是以约定的方式排除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来侵犯投保人的利益,达到利己的目的,从而违反保险立法保护投保人利益的意旨。因而,审查该约款的效力以维护投保人的正当利益,为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这一特别条款存在的必然理由。
四、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规范功能分析:私法自治之导正与裁量权之正当化
一般民法上的强行性规范,其功能主要在于为维持国家基本秩序或保护社会上的弱者,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条款作为强行性规范亦具有同样的功能。但作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规制的手段,还有其特别的功能,即私法自治的导正功能与裁量权的正当化功能。
(一)私法自治之导正功能
“私法自治之意义在于法律给个人提供一种法律上的权力手段,并以此实现个人的意思。这即是说,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14)从古典契约理论看,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有内在的统一性,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但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是通过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互换性而体现出来的。定型化契约的出现破坏了这种统一性,因而产生了立法规制的必要,但这种规制并非意味着完全否认私法自治。定型化契约是交易上的一种需要,其内容本身也是意思表示的一种,仍遵循私法自治下延伸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说定型化契约的发展最终背离了契约自由原则的本来意义,但其理论基础却是契约自由。因而,“具有特别债法性质而被泛称‘商法’的……保险,虽不能说完全不具政策内涵,但归类于自治规范确实较无可争议”。(15)
日本学者山本敬三认为,自治规范即任意性规范类型有二:一为明示的任意法规,即明确允许相反特约的情形,如规定“在无另外的意思表示时”、“当事人表示了相反的意思时不在此限”等字样;二为未明示为任意法规,但根据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原则,只要没有应当是强行法规的理由存在,就应看做是任意法规。(16)这一点在保险立法上亦有相当的表现。如各国和地区保险法的条款中出现诸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无另外的意思表示时”等用语。此外,即使无此用语的条款,也并非不属任意性规范。各国和地区保险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都表述为“……之规定不得变更。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等类似用语。这一“但书”意味着“……之规定”并非完全不可变更,而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予以变更,其规范的任意性十分明显。而此一“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的用语,无疑是该特别控制条款作为强行性规范“留给私法自治的一个气窗”。(17)立法如此规定,是因为保险人出于扩大业务的考虑,可能愿意提出比法律规定更为优惠的条件以吸引投保人,此举并不损害投保人的利益,应予尊重,以凸显私法自治的精神。同时,为防止保险人可能利用此种自由而损害投保人的利益,又设一前置性规定:即此一约定相较于法律上之规定不得不利于投保人,从而将该自由控制在任意性规范这一最低要求之上。
可见,保险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的存在并非对契约自由的抛弃,而是以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尊重为前提的。它通过规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以达致规范私法自治的目的,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的导正功能。这种导正功能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对保险人而言,通过规定其不得利用契约排除某些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或者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满足了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可排除其适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契约自由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化;对投保人而言,因在契约中进行强制性特别保护,使其取得仅凭其交易地位所不能依谈判取得的交易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们的契约自由。这一特别控制条款的存在,可谓“使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项原则,获得最大的调和及实现”。(18)
(二)裁量权之正当化功能
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依据这种最大诚信原则,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建立了诸多相应制度,如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等,但这些制度均不涉及保险合同条款本身的正当化问题。而囿于诚信原则自身的抽象性,诚信原则本身又无法直接适用于保险合同的条款控制。
诚实信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缺少法治社会最起码的体系性、可预见性要求。“对于什么是诚信所要求的,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各异;人与人之间的期待不同,合理性的标准也有差别,各个法域对此的观点也有分歧;在不同的法域,在不同法域的不同历史阶段,合同的背景各不相同,所采纳的观点也就相应不同。”因而,“给出一个关于诚实信用的精确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诸如‘诚实信用’这样的术语也不能说明什么”。(19)诚信原则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规定,换言之,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乃是私人活动的基石,不允许国家随意予以侵害。但对诚信原则这一“空白委任状”,没有确切内涵,外延又极其宽泛,法官的作用有可能向一般条款逃逸,因而对诚信原则的裁判运用,极有可能构成对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不当介入,会出现无视立法者制定法的拘束力的危险,即产生制定法被轻易修正的危险性和不依据制定法裁判的危险性。这使得“制定法以确立标准的方式介入到司法和行政的决定中。经常是,制定法甚至给予这些决定以一个具体的方向”。(20)
保险合同具有复杂性与技术性的特征,这使得法官更难以判断哪些条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哪些条款属于保险在技术上的合理要求。为了不构成对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不当介入,有必要在制定法上给法官一个具体的判断依据,使其裁量权受到法律的约束。因而,尽管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授权法官对定型化契约条款的效力予以裁量,但这一权力受到了任意性规范的约束,是“受法律约束的裁量”。(21)法官判断保险合同条款是否公平,以立法上现有的任意性规范为标准。这一标准是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而非像诚实信用原则那样,需要法官去作主观评价。从这个角度而言,诚信原则之于保险立法,仅有建立更具体规则的意义,而不具有裁判的意义。该特别控制条款相对于诚信原则而言,应为一种特别规则,保险法正是“通过这一特别规则的适用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一个适当的利益平衡”。(22)
五、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制度架构:规制对象及法律效果的比较法分析
除《保险法》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均有一种特别控制条款对保险人违背任意性规范的行为予以规制。该条款在各国和地区立法上的表述各不一样。虽然其立法目的一致,但适用的结果却有差异。这涉及如何理解各国和地区立法的不同规定以及该条款的制度架构问题。
(一)特别控制条款所指向的对象
综观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确定特别控制条款所指向的对象有两种立法模式:一为德国、法国与意大利的分别规制模式,即采列举的立法方式将特别控制条款所要规制的任意性规范一一列明;一为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总括规制模式,即立法仅规定当事人不得变更法律的规定,除非该约定有利于投保人。其中韩国法与我国澳门法将全部的法律规定列为不得变更的对象,而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立法”仅将强制性规范列为不得变更的对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特别控制条款所涉及的应是何种规范?是全部的法律规范还是仅包括任意性规范?是全部任意性规范还是部分任意性规范?
1.特别控制条款不应涉及强制性规范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54条第1款规定:“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但何为“强制规定”,其并未明示。学说上将其分为绝对强制规定与相对强制规定。绝对强制规定或在“维护保险制度之本质”,或在“维护公序良俗”、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其中尤以“维护保险制度之本质”为其要旨,如保险利益、保险费之交付、犯罪行为除外不保、不当得利原则之规定等;而相对强制规定多为保护弱势的投保人。绝对强制规定不得由当事人以契约变更,哪怕约定的结果更有利于投保人。“因保险制度具有分散风险与损失于众的特性,契约自由原则在与保险之本质相抵触时,也须对保险制度作退让,以达成保险本来的目的。”(23)因而,如果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放弃保险利益的要求,尽管对投保人有利,该约定也无效。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54条的“强制规定”应作限缩解释,即指相对强制规定,亦即任意性规范。《德国一般交易条款法》第9条第2款第1项之用语虽为“法律规定”,其法律规定是仅指任意性规范还是包含强制性规范并不能仅从其字面意义推定之。因为定型化契约条款违反强行性规定者,依法本属无效。民法已有此相关规定,无特别立法的必要。且《德国一般交易条款法》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定型化契约不合理规避任意性规范的现象的普遍化,因而该法第9条所言之“法律规定”应作限缩解释,即指制定法上的任意性规定。
2.特别控制条款不应涉及全部任意性规范
在经济上,保险系指为处理可能发生的特定偶然事件,透过多数经济单位的集合方式,并以合理的计算为基础,聚集资金,公平负担,将个人的损失分散于社会大众,以确保经济生活安定为目的的一种持续性经济制度。保险的这种技术性特征使得保险合同的条款亦有控制风险的必然要求。保险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虽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但也应同时考量保险人的利益,以资利益平衡。申言之,特别控制条款的存在,并非为控制一切违反任意性规范的契约条款,唯有在该任意性规范纯为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而存在时,方有关注的必要。如为保险控制风险的技术性要求,尽管妨碍了投保人的利益,但却因此维护了较高的保险人利益,该约款即非不公平,则应充分尊重契约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予以变更,而不受特别控制条款的限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2条即规定:“为减少或避免危险增加而规定要保人一定义务的约定,不因本节的规定而受影响。”
比较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德国、法国与意大利的保险立法对不得随意违反的规范采列举主义,而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采概括主义。前者的立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对何种规范不得随意违背,当事人及法官皆有明确的指导;而后者的立法易产生诸多弊端,首先未明确排除强制性规范,不符合该特别条款应为任意性规范而存在的法理,其次未明确规定何种任意性规范应为其关注的对象,甚至连何为任意性规范也无明确区分。尽管许多传统民法学者曾武断地认为:“强行法与任意法的区分在民法中已经得到解决。民法的大部分规则为任意性规范……而强行性规范仅为个别或例外,因此两者的界限仅根据法条文义即可得到识别。凡法律规范中有‘应当’、‘须’、‘不得’等用语者为强行性规范,而法律规范中有‘如无相反约定’、‘当事人虽有约定者除外’以及多数未加禁止内容者则皆为任意性规范。”(24)但另有学者却认为,传统民法远没有解决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界限问题,而旧有的民法规范体系也远不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要求,这正是实践中“不公正合同条款”层出不穷的真正根源。因此,对于民法规则中“何者为强行规定,何者为非强行规定……不能全依法文方式以为决定,而应依法文之体裁及法律规定本身之目的以定之”。(25)这意味着许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判断出何者为任意性规范,这无疑为该条款的适用带来了困难。如在操作上,“判断定型化约款之效力时,首先应检讨约款所排除不予适用者,系何项任意性规定,并探究该任意性规定之规范目的,并特别注意该任意性规定是否以保护相对人正当利益为其目的,再依具体情形,于个别案例中,决定该定型化约款有显失公平之情形”。(26)如此,则法官的裁量权又被放大,对于正确处理保险纠纷颇为不利。
保险法上的这一特别条款以牺牲保险人的部分利益来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以实现双方利益平衡,达致法的正义目标,则其所关注的任意性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因为,“正义要求尽可能地‘具体化’”。(27)
(二)特别控制条款的法律后果
定型化契约之所以受诟病是因为当事人一方预定不公平的契约条款,由需要订约的他方,依照该项预定条款签订,致他方遭受重大的不利益,故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对于此种不公平的条款,有必要在立法上使其无效。就定型化契约而言,若某项条款无效而导致全部契约无效时,相对人所期望的交易目的难以达成,显然不足以保护其利益。因而其无效的后果并不影响契约本身的效力,而仅为该条款不生效力而不能适用,其结果是形成“契约漏洞”。保险合同的条款因受特别控制条款的规制而无效时,保险合同因此也可能出现“契约漏洞”而发生如何填补“契约漏洞”的问题。
填补“契约漏洞”的方法有二,即任意性规范与补充的合同解释。(28)在这里,涉及究竟是依任意性规范还是根据补充的合同解释填补“契约漏洞”的问题。学者皆认为,定型化契约条款全部或一部无效,而契约仍属有效时,其因此所发生的“契约漏洞”,应先适用任意性规范,无任意性规范时,则依契约解释原则加以补充。(29)“契约漏洞”首先应由任意性规范加以补充,其理由在于:(1)任意性规范系立法者斟酌某类型契约的典型利益状态而设,一般而言,多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对于契约未详订其内容,也多期待法律设有合理的规定,故有任意性规范时,原则上应优先适用。而法律设任意性规范的目的,实际上亦着眼于“契约漏洞”的填补。(2)在私法自治原则下,任意性规范是立法者为了实现公正而设立的一般妥当的规则,而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是当事人在具体情形下认为妥当的规则,两者如同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理,任意性规范可由当事人通过契约排除其适用。但定型化契约有别于一般契约,这是因为,定型化契约条款并非基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产物,而是由一方制订提供的,因而当定型化契约条款与任意性规范不一致时,约款并不优先于任意性规范;相反,任意性规范作为判断约款有效性的标准起作用。(30)唯在无任意性规范时,应依补充的契约解释方法,填补“契约漏洞”。德国学者也认为,契约条款无效之情形应视为当事人没有约定,而“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可以从——大多为任意性的——法律中找到答案”。因任意性规范的作用本在于弥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足,“若当事人未特别约定而适用任意规定,解决当事人契约关系所生的争执时,任意规定扮演形成契约内容的角色,任意规定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成为契约关系的内容”。(31)《德国一般交易条款法》第6条第2款规定:“一般契约条款之全部或一部条文不能成为契约之一部分或无效者,其内容依法律之规定。”因而,“这种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虽然是第二性的,即在第一性的合同约定之后适用,但是它并不是根据当事人的意志而适用的,而是‘依法’适用的”。(32)“据此,一旦一般交易条件并不像使用人希望的那样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或者生效,那么合同的内容则以法律所规定的为准,这些规定表明了立法的一个基本趋势,即任意法并不能为与之不相一致的事实上属于不恰当的一般交易条件的规定所代替。”(33)
在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例上,唯有《意大利民法典》第1932条关于特别条款的条文中有关于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违反上述规定的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条款,将被相应的法律规定所代替”。其他国家和地区虽未在立法上作出此种规定,依上文的分析,应有同样的法律后果。
六、代结语:立法建议
保险的功能在于免除个人经济生活的忧虑,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与进步。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消费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多利用契约自由之名,行危害保险消费者之实。在顺应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潮流下,对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予以内容控制成为现代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的一个方向。针对保险人违背保险法上任意性规范实施不利于保险消费者的契约行为,相关立法的目的首先在于规制该合同中的不当排除任意性规范的条款。针对保险人可能实施规避保险合同法上任意性规范的行为,各国和地区保险法上皆有一种特别控制条款予以规制,从而使得任意性规范具有“强制性”。但这一条款却为我国保险法立法者所忽略,相较于国外之先进立法实践,《保险法》的滞后已不容忽视。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我们应以正在进行中的《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为契机,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借鉴他人立法经验,确立保险合同之内容控制原则,以健全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为此,试拟条文如下:
第××条 本法的规定,如果不是更有利于投保人,则不得变更。违反上述规定的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将被相应的法律规定所代替。
前项之变更如违背保险制度之本旨,即使有利于被保险人,亦不得变更。
注释:
①参见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7页。
②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281页。
③④⑤⑥⑩(13)(32)(3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第591页,第794页,第62-63页,第79页,第44页,第44页,第784-785页。
⑦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⑧(12)(26)参见詹森林:《定型化约款之基本概念及其效力之规范》,《法学专刊》第158期。
⑨参见林益山:《消费者保护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80页。
(11)(24)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第51页。
(1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5)(17)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第37页。
(16)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18)(29)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第98页。
(19)(22)[德]莱因哈德·齐默曼等:《欧洲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第481页。
(20)(21)(27)[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第143页,第206页。
(23)赖源河:《商事法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页。
(25)史尚宽:《民法总则释义》,台湾正大印书馆1936年版,第257-258页。
(28)学理上将合同的解释区分为补充性合同解释与阐释性合同解释。所谓阐释性合同解释,又叫单纯的合同解释,简称为合同解释(interpretation),是指在合同的用语、条款的含义有疑义时,应通过解释探求其规范意义。所谓补充的合同解释,是指对使用的客观规范内容加以解释,以填补合同的漏洞现象。其所解释的,是当事人所创设的合同规范整体。其所补充的是个别合同条款。所以,补充的合同解释仍具合同解释的性质。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30)参见[韩]权五乘:《韩国的约款规制法》,崔吉子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4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31)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标签:保险合同论文; 法律论文; 保险人论文; 投保人论文; 合同条款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合同目的论文; 法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