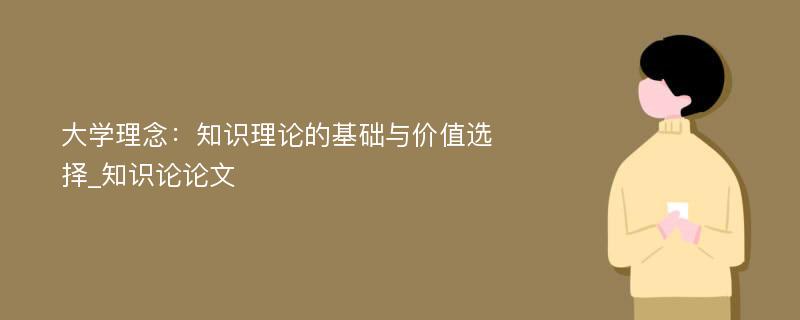
大学理念:知识论基础及价值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价值论文,基础论文,知识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理念存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定格在从建筑、课程体系到制度等各类大学符号上,也见诸大学内外人际互动的交往中。当大学的组织特性定型之后,无论内群体还是外群体,只要是利益相关者,或显或隐,都持有一定的大学理念。当大学作为公共产品获得国家提供的身份地位,每个人都有“理论机会”享受高等教育权利,尤其在大众化、普及化列入政府议事议程并且得到逐步实施之时,大学理念的认识动力被广泛刺激。民间的理念或许素朴,但从关于为什么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能不能上大学等问题的理性计算中,可以做理念存在的推论。大学当事人是不能离开理念的。即使没有成文的“客观化”理念,特殊存在形式的理念已昭然于日常组织行为。涉及大学行动的所有政策文本和官方话语,更是大学理念的制度化表征。随着大学理念成为一个学术论域,以“大学理念”为题的“客观知识”日积月累,业已成为探寻者路上的记号,令人或困于迷局,或豁然于正途。历史的天空飘荡着的大学理念,在当下论者的“思想仓库”集结遭遇,精粗真伪在个体孤独思考和群体“精神盛宴”的经验世界摩擦揉搓中过滤,酿几滴思想琼浆“继往开来”,这就是“知识自主性”和知识进化的波普尔逻辑。大学理念是波普尔世界3的居户,还是柏拉图洞穴里大学的背影?或者是后工业、后现代、后科学、后哲学、后形而上学等“后X”社会中躁动不安的“想象气泡”,经不得一根针的穿刺,在“相对主义”的“多元话语”声中破裂?当下如何?今夕何夕?时空被新技术杀死之后,现代大学真的能够一方面被经典理念灵魂附体,一方面又披着“后X”的外衣舞蹈?假如像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那样恣意狂放,或只为“酒神精神”所浸润,那么理念的公度性和合法性何在?
一、大学理念的原点:哲学生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
大学像“水电站”,内容是水(广义的知识),形式是河道(知识传统和知识史),水电站是组织,“加工”是水电站的功能。水电站是对水的蓄积、控制、转化和利用。水流的目标是海洋(知识大融汇),水电站的目标则是能量的生成和利用,同时调节水流的速度。大学理念就是对这个“水电站”的认识,是人们对“大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为什么是”以及“大学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做”的看法。
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大学的基因和祖先。但中世纪大学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大学共同的源头和活的标本。阿拉斯泰尔·麦肯托斯(Alastair McIntosh)认为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城外的小树林旁创建了西方第一所大学。[1]当代关于大学研究的“学术”(academic)称谓,就是源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Academy)。作为最高学位,哲学博士的含义是“爱智慧女神”。古希腊语中的学术卓越并不限于狭窄的学科范围,而是全方位的生活卓越。在《斐多篇》中,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河畔的小树林里打着赤脚,受自然灵性的启发,揭示了哲学家的核心动机和目标——爱。没有爱,就没有智慧。没有爱,智慧就蜕化为枯燥的学问。麦肯托斯在讨论苏格兰的大学理念时挖掘了古希腊对学术的理解,他将智慧与大学联系起来,突出了大学在情感和理智间保持平衡的理想追求。如果在最高学术资格上说大学是培养“哲学博士”的地方,那么,大学就是“智慧”的场所——为爱而探寻真理。阿卡德米是否就是大学的上限,难有公论。但就大学是个什么地方,阿卡德米的“智慧说”却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阿卡德米的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关于“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划分[2],在一定意义上草绘了大学理念在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极腾挪的图景原型。哲学生活是认识的生活,是让“灵魂转身”走出“洞穴”囚禁的上升运动。政治生活则是已经走出洞穴,知道“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的人应该做的事。他们要重返“洞穴”,取代那些昏然为“影子”斗殴、为“权力”争吵的统治者。因为“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哲学家”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能力参与这两种生活,应该成为两个世界的公民和“蜂王”“领袖”。“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因为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公私活动都集中于一个生活目标;而知识分子又不能自愿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已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乐园了”。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他们“不能自愿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哲学家,尤其是受到本国政府支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被寄予政治参与的期望。“我们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3]。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囿于洞穴,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走出洞穴后又不肯“下去”。深受国家培养具有“最好的灵魂”的哲学家,他们“上升到那个高度”“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理应承担国家建设者的职责,“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荣辱,不论大小”,“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他们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柏拉图将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相联系,寄语哲学家在公共责任方面超越知识分子,这是大学理念纠结于“出世”(象牙塔)与“入世”(社会服务)两种使命的原型。时隔二十多个世纪,柏拉图的二分法像个幽灵,以原版的或改头换面的方式仍在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盘旋。
在当代高等教育学术界,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做了“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划分。两极思想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互相竞争,此消彼长,根源是“价值中立与关联”问题:“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一样。”[4]高等教育的知识至上和知识自足被看作认识论理念的展开,最近的源头在洪堡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认为是这种理念的化身。但是,“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当高等教育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5]高等教育的社会取向即“政治论”概括,“威斯康辛思想”就是政治论与认识论平衡的表现,“服务站”则是政治论的隐喻。“尽管‘威斯康辛思想’取得了成功,但在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仍然缺乏和谐。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追求真理和追求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对诸如什么是最好的社会目的和如何运用权力来实现它们等问题表示态度,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的客观性。”[6]“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7]可以看得出,布鲁贝克的二分法具有柏拉图的影子。知识的事实发现和事实根据以及价值判断和价值实现,或简单地说,知识和知识的功用是讨论大学理念绕不开的问题。
巴内特(Barnett)不满高等教育研究在“教育维度”上的无所作为。他痛惜“缺乏对高等教育的反省不仅在研究教育的学术部门显而易见,在研究高等教育自身的研究者当中甚至更加习以为常”。[8]与布鲁贝克比较,他换了另外一种说法揭露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认识论和社会学两大基础被侵受蚀的现象。一方面,知识“客观性”和“可认识性”遭疑,认识论基础受侵;另一方面,相对封闭自足的学术边界被撕裂,社会学基础遭蚀。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普遍弥漫的对知识客观性的怀疑态度是认识论遭侵蚀的原因,也是表现。而偏向社会服务的功能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视而不见,“期望高等教育取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在社会收益方面尤其期望有加”,“对高等教育的评判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对英国有限公司的直接贡献”。自由高等教育受到两方面的围攻:认识论公理(存在客观知识,并且可以被认识)和社会学公理(客观知识保存和传播的前提是相对自主、比较自由)同时被稀释甚至污染[9]。有些人给前者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后者则引发了“学术资本主义”、“经济主义”等形形色色“学术原教旨主义”的忧思。
柏拉图以降,思想界形成学术和政治两极对应的视域和传统,日常生活混同为政治生活,民间的、人人都要经历的日常生活在其中没有地位。在柏拉图那里,爱智、求敬、逐利在个人层面体现为三种生活,在城邦体现为三种人——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其中,“我们用以学习的那个部分总是全力要想认识事物真理的,心灵的三个部分它是最不关心钱财和荣誉的”。爱智者也爱好学习,哲学家受到更好的教育,具有两种生活的主导权。柏拉图寄期望于哲学家参与政治,但如果参与政治,是否依然可以远离“胜敬”(名誉)和利益(钱财)呢?当然如此,因为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乃是前提条件。理想虽然是这样,但现实是人们都需要和别人打交道,都需要过衣食住行的常人生活。哲学家也不例外。哲学家的精神追求是无限的,但是,有限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弃绝。或如杜威所言,“一切古典哲学在两个存在的世界中间划了一个固定的和根本的区别。一个相当于普通传统的宗教的超自然世界,而由形而上学描画成为至高终境实在的世界”;“与这个须经哲学的系统的修炼才能了悟的绝对的本体的实在相对峙的,是日常阅历的普通的、经验的、相对实在的现象的世界。人间实际事务和实用都与这个世界相关联。”[10]1817年底,柏林大学重议邀请黑格尔来柏林一事,普鲁士文教部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确信黑格尔哲学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莅任后即给黑格尔写私人信件,以高达两倍于黑格尔任教的海德堡大学收入的年金“垂钓”。黑格尔考虑了两个星期后欣然接受。当然,“他还想了解一些细节问题。柏林的事物补贴(谷物和麦子)如何?可否提供免费住宅?本人亡故后,家属有无抚恤金?”另外“他刚在海德堡置办了家具,到柏林却又得重新安家。因此,他请求发给200弗里德里希朵尔作为迁居费,这比实际的搬家费用稍多一点”。[11]黑格尔的这段调任乔迁经历,对所有学者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代表性。后来,韦伯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对学术和政治做了严格的区分。在论述以政治为业时,他还区分了“为了政治而生存”和“依靠政治而生存”的不同政治生活:前者志在政治事业;后者政治不过是糊口手段。“为了政治”的态度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日常生活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保障,而“依靠政治”则只有政治一条生计。[12]韦伯没有用相似的二分法分析学术职业。“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无疑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学术志业当然“以道为生”,但闯入“学术领地”的人难道不一样面临黑格尔柏林之旅的物质计算?其实学术界依然有“为了学术而生存”和“依靠学术而生存”的分别。另一方面,哲学家虽有一套理论知识,但在自己的行动中往往可以看到理论和行动的分离。当知识从“智者之城”回到人间,从哲学世界和政治疆场回到日常生活,在面对自我和他者如何选择、如何行动的时候,才是哲学家“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写照”曝光的时候。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就曾在《知识分子》中生动地描述了从卢梭到萨特等十二位“知识分子”的公共宣言和私人生活两极背离的面项[13]。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指导别人的行动,能不能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能,又是什么知识在起作用?
二、大学理念的知识论基础: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
卞之琳在《断章》中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翻译为大学理念的语言直白就是:“你在那里看大学,看大学的人在这里看你。”摆在当代的大学理念论者面前的,既有既往的大学理念,又有现实中的大学和“记忆中的大学”。大学理念涉及“谁看”、“为什么看”、“看什么”、“怎么看”和“看完之后如何”的问题。大学理念史上有许多绕不过的“看客”。纽曼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教师,后来成了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校长。纽曼之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他于1852年受命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六年后辞职。历史表明,该大学根本说不上办得成功。对纽曼而言,这“无疑是一段失败的经历”[14]。就大学校长的职责而言,他在大学的教育功能的领导角色上可能会做到理念和实践的契合,但是在大学治理上他的理念似乎有所欠缺。梅亚德利在他为《大学的理念》所写的序中评价道:“纽曼见长于思想,而不见长行动”,“他既没有管理天赋,也没有领导的才能”。纽曼的自我评价是“有能力教育一个民族,但是无能力对其进行治理”。[15]洪堡当过普鲁士的外交官、做过枢密院的教育文化部大臣,领导了德国教育改革,创建了柏林大学。但他在柏林大学正式成立前,就因与内务部大臣冯·多纳(Count von Dohna)意见不合离开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大臣的位置。艾略特是哈佛大学财务长的儿子、哈佛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后在哈佛做了四十年的校长,他倡导的“选修制”至今还在大学活跃。蔡元培留学德法,学览中西,改造了北大。如此等等。这些先驱不仅仅在大学的理念上留下不朽思想,他们服务大学的行动及其后果也载入学校发展史册。从历史现场的角度看,不同位置的角色不同、身份不同,理念对行动主体的影响方式乃是不同的。还有一些以大学理念为题报告或写作的人不一定都身居“大学要职”,但历史距离的存在使他们的言论似乎无身份差别和“位置信号”地汇入大学理念主流。西班牙的奥尔特加根据他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做的主题演讲集成了《大学的使命》,美国的弗莱克斯纳根据应牛津大学“罗德基金会”邀请所做的报告出版了包含《现代大学的理念》在内的《大学:美国、英国和德国》,中国的潘光旦先生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邀请而撰写了《大学一解》[16]。这些都是大学理念的光辉篇章。六十年代巴黎街头与政府对峙的大学生以及美国许多大学与校方对峙的大学生用身体思考,用行动呐喊。虽然看不到当事人关于大学理念的文献档案,但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愤青的行动是在某种理念的影响下实施的。每个大学的当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大学理念恰恰就是具体的人的理念,而不是“抽象的大学”的理念。如果大学是一道风景,大学理念论者选择不同的角度观察,他能看到什么?如果大学理念论者仅仅是“鉴赏风景”的人,那他的理念与大学的现在和未来何干?观察者可以看到的景色或是大学的物质躯壳,或是行色匆匆抑或漫步沉思的思想者,但如果仅仅限于观察,看不到大学理念的“知识”,看不到思想者思想着的思想,也看不到超越物质的“作为存在的大学”,那么,这种观察就一定是漫无目标的“盲审”。事实是,柏拉图的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切割和整合,布鲁贝克和巴内特关于哲学和理念的认识论、政治论和社会学基础的分析,不仅仅适应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一般知识和许许多多学科的知识,同样也适合于作为知识的“大学理念”。当然,他们对日常生活和物质基础的遮蔽,同样也是大学理念的知识论要克服的缺憾。如帕利坎(Pelikan)所言,“大学行政史的道路两旁,也七零八落散放着一些机构和教育家的残片,这些人感到悲哀,因为虽然有时候他们从至高尚的动机出发,却忽略了财政方面的现实情况,或者认为,在大学里,凡是被称为‘生意’的事务,都是他们知识阶层的地位所不屑一顾的,或者,稍加注意即可”;而与这种现象正好相反的是,一些人将大学理解为生意,“想方设法利用大学来牟利”。[17]无疑,大学的经济现象不可回避,常人生活不可回避,正如大学必须守望其知识原则和社会责任一样。
波普尔(Popper)认为,“全部科学和全部哲学都是文明的常识”,“常识是出发点”,“它必须接受批判”,“进步的主要手段是批判”。就知识论而言,存在着常识知识论和客观知识论。常识知识论关于知识的起源持“水桶论”的观点,认为我们基本上像水桶一样是被动地通过感官获得知识的。“认识是主观的自我的认识”,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知识,“即某种主体所具有的知识”。常识知识论不能区分两种状态的知识——主观意义上的知识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主观知识“由倾向和期望构成”,是由先天的行动意向和这些意向的后天改变组成的。同时还存在着客观知识。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即人类知识,“这种知识由经受了批判讨论,并由语言阐述的期望构成”。推测性理论、未解决的问题、问题境况和论据组成的客观知识,为其是“表述于语言之中的理论可以被批判地讨论”。客观知识通过消除语言之中的推测而保留载体就可以改进。而“主观知识是不可批判的,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它加以改进”,如消灭“载体”或生物体的演变和淘汰。波普尔是进化的客观知识论者,他认为:“虽然真理的观念是绝对论的,却不能提出任何对绝对确定性的要求: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但不是真理的占有者[18]”。他认为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种奢望:“科学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绝对的确定性,而在于发现愈来愈好的理论”,“或者发现愈来愈好的探照灯”,“这些理论可以接受愈来愈严厉的检验”,“并由此而引导我们达到最新经验,照亮我们的最新经验”[19]。“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种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20]知识的增长就是猜想与反驳不断进化的过程。波普尔主张客观知识论,并因此为世界划界,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世界3包括“理论体系”、“问题和问题情境”、“批判性辩论”、“讨论的状态或批判辩论的状态”、“期刊、书籍和图书馆”[21]。第三世界是人类动物的自然产物,可比作蜘蛛网。“第三世界基本上是自主的,尽管和我们相互作用,是我们的产物并且对我们有反馈作用。正是通过我们和第三世界的相互作用,客观知识才得到发展”。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理论在先”、“知识通过批判而进化”、科学的目的是发现“探照灯”、“所有的规律或理论都是假设和猜想”等观点对科学哲学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正确地指出,“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需要“试着通过批判来改进我们的哲学”。他正确地警醒:“哲学的最大耻辱是,当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界——行将毁灭的时候,哲学家却时而聪明,时而愚蠢地大谈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他还正确地评价道:“除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大多数职业哲学家似乎够脱离实际。”[22]但是,他自斥“我们的哲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它对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却常常是破坏性的”,这无疑有失夸张。他把认识论看作“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他反对常识知识论,反对休谟的“习惯”与行动关系的论点,反对行为主义,认为“不存在诸如联想或条件反射之类的东西”,将客观知识绝对化为“没有认识者,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所有这些观点,都源于他对统一科学(哲学)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个人行动”以及“行动场”的忽视。
哈贝马斯(Habermas)将认识与兴趣统一起来,认为“认识既不是生物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一种单纯的工具,又不是纯粹的理性生物的一种活动,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特殊的范畴。它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工具和创造新生活的手段。它是主体借助于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在使用技术占有自然的进程中,在把握人的共性的进程中完成的”。[23]“人的认识兴趣决定了人的科学活动,而每一种科学活动又有他自己的特殊的认识兴趣”,包括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技术兴趣是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实践兴趣是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确保人的共同性的兴趣,解放的兴趣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三种兴趣分别对应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显然,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一种行动理论,它超越了波普尔的认识论主张。吉尔兹(Geertz)从人类学出发提出的“地方知识”思想,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对波普尔的超越,也是哈贝马斯实践兴趣导向的解释学在人类学中的具体化。对地方知识的认识起于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现在面对自我定位的时候,既不可将他人远远推向相对的极端,亦不可将其拉进而犹如我们自身的摹本,而是要将我们自己置身于他人中间。”[24]“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的方法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25]地方知识与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相联系,并且还与特定的地方情调相联系,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想象力不应被掩蔽”,“它们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而且解释人的行为”。这种或者建设性的、或者解释性的能力,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集体智慧而非个人的单独智能的能力[26]。法律就是一种地方知识,它“不是与地方无关的原则”,“法律对社会生活来说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或者无论如何不只是反映性的。”[27]人不是在真空中存在,人的想象力是地方产物,也是地方知识的源头。任何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个意义充满的特定的时空场域。“人将自己囿于一套富有意义的形式之中”,囿于“他自己编织的含义之网。”波普尔将主观知识从客观知识的“图书馆”大门赶出,吉尔兹则为它打开了“地方知识”这扇意义的窗户。
波兰尼(Polanyi)从“个人知识”的角度切入知识的主客观问题。与波普尔不同,他认为,科学是有主体的。“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人的主体是心与身体的统一体。思维能力是人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每当谈论人的时候,就会论及人类所处的知识阶段。知识发展是无终点的过程。研究跟着研究,反思跟着反思,先前完成的研究和反思是既起的研究和反思的对象。因此,要将人类的所有作品完全囊括在研究与反思之中是徒劳的。人们必须永不餍足发现客观自立的知识,可是一当反思自己的知识,人们就会发现他处在一种维护和确证自己知识的行动中。每当新知获得,我们就通过尚未统合到我们的知识体的东西将世界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达至人的全面知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个逻辑难题,波兰尼提出了“缄默知识”的概念。知识具有二重性,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表达的是显性知识,而缄默知识是内隐在人们的意识、潜意识或行动中未能系统阐述的知识。对缄默知识的拒绝就是对所有知识的拒绝。两种知识的根本逻辑是不同的:显性知识依赖于语言符号,可以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一点和波普尔的观点一致;但是缄默知识则无法承受批判性反思,它是非反思的。我们不能反思自己缄默的经验意识,缄默知识是所有知识的“决定性原则”。在智力的各个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缄默的力量而不是阐述性逻辑操作的功能。同时,“人的身体在宇宙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们的身体不是作为物自体的关注对象,而是用作控制环境的智力的和实践的工具”。通过所知和所为对身体的体认就是对生存的感知。这种意识是作为感性的、能动的个人之存在的最根本的部分[28]。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也是一种意会(缄默)知识论。“意会认知理论建立起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通过使‘我—它’与‘我—你’却根植于主体对自己身体的‘我—我’意知,它就填平了‘我—它’与‘我—你’之间的鸿沟。这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内居。”①
波兰尼揭示了知识的二重性后,许多学者开始对知识的类型做进一步的二分探讨。保罗·赫尔德里希(Paul M.Hildreth)和克里斯·吉姆波尔(Chris Kimble)提出硬知识和软知识[29];康克林(Conklin)提出正式知识和非正式知识;鲁尔克(Rulke)提出交互知识(Transactive)和资源知识;西里·布朗(Seely Brown)等区分了“知道什么”和“知道怎样”。知道怎样是将知道什么付诸实践的特殊能力。库克(Cook)和布朗(Seely Brown)认为:“认识是行动的一个方面,认识是人和社会世界以及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要么形塑物理世界,要么形塑社会和物理两个世界。‘认识’不只是聚焦于我们的意识内容,它还聚焦于我们社会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温格(Wenger)提出了参与与具体化,认为“实践是关于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谈判。”“意义的谈判涉及两个过程的互动:参与与具体化。”“参与不等于合作。参与涉及各种关系,包括冲突的,也包括和谐的;亲密的,政治的;竞争的,合作的。”具体化(reification)为抽象事物提供具体的形式,它包括“制造、设计、表征、命名、编码、描述,也包括感知、解释、使用,再利用,解码,重铸”。实践活动是一个学习过程,而“学习是一个社会参与过程,其中,人们不仅是能动的社区实践的参与者,而且,通过这个过程,人们生成自己和社区关联的身份认同”。莱昂纳多(Leonard)和森斯波(Sensiper)认为“知识是一个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区间。显性知识处于彼时彼地,隐性知识则是此时此刻。”②诸多知识二分法相对于一元知识观而言,突出身体的地位,突出实践活动,突出缄默知识(或隐性知识和意会知识)的地位和认识价值,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诚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但是,认识不是人类实践的终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0]。知识——显性的和缄默的——乃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基础,知识的真理性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验证,知识的价值在行动中才能够得以实现。
有了上面知识论讨论,现在回头重审如下问题:大学理念是知识吗?如果是,那么是个人知识,还是客观知识?比如,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理念是个人的想法,还是客观的知识?此外,大学理念有好坏之分吗?或者说,有好的理念和不好的理念吗?比如,能不能说洪堡的理念要好于纽曼的理念呢?如果有好坏之分,那又根据什么标准判断理念之好坏呢?理念之间存在竞争吗?大学理念有什么用呢?作为关于大学的认识结晶,大学理念当然是一种镶嵌在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知识,由历史和社会所浸润,带有“地方知识”的特征。所以,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下出现的不同理念进行优劣“排行”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相对于特定社会的公共理想和普遍价值,相对于真理的逻辑标准而言,不同的理念间存在竞争,也存在优劣之分。大学理念存在二重性:凡是通过语言和符号作为载体外化的理念,以显性知识呈现,构成世界3的内容,存在客观性;凡是以个人为载体,与身体统一,并且无法编码、无法清晰阐述的,构成大学理念的缄默部分。显性知识是可以批判的,而缄默知识是非批判的。从波兰尼“内居”的意义上说,大学理念是个人知识。作为个人知识的功用,最直接的就是感知和内化外部世界的影响,同时设计和实施个人行动。在个人行动、组织行动和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大学办得好不好,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但必须始于个人的行动,当然也始于个人的知识。
三、知识创价社会的大学理念:行动分裂与价值整合
大学理念是一种地方知识,受历史和文化影响,是个人和情境互动的产物。大学理念的价值在于影响大学实践,即,使大学向着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行动。个体对社会情境的感知和对社会事实的把握及其长期形成的个人知识,制约其行动选择。对社会形态的界定存在两种策略:一种是对现在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现实的把握,一种是对现在社会所向往的未来愿景的表达。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学者们对工业社会发展成熟之后的社会形态做了许多界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社会”,社会科学学者提出了“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从对政治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上看,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下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通话”。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信息社会”。他指出社会主轴是理论知识,基于知识的服务成为新经济的中心结构,信息将领导社会潮流。1985年,堺屋太一提出“知识价值社会”的概念。在知识价值社会,与物质财富的生产相比,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更加受人重视。[31]相应地,物质财富的数量需求减少,而取决于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需求增加。信息社会在1995年就出现在G7会议议程,1998年这个概念被国际电讯联盟(ITU)选用,联合国2003年和2005年世界峰会以其冠名。信息社会作为政治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构念,担纲为了全球化而行动的“善意大使”的角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学术界开始使用知识社会的概念。UNESCO通讯与信息部主任阿布杜·汗(Abdul Waheed Khan)认为,信息社会是知识社会的“建筑材料”。信息社会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知识社会则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制度的转型与变革等维度,是一种更加多元的发展性视角。知识社会能够比信息社会更好地捕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知识及其应用的不同状态做了区分。他指出,当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并非是知识和信息成为主角,毋宁说,知识、技术、信息和通讯装备在创新中的应用和反馈,成为社会的核心。新信息技术不仅仅是应用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开发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的大脑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生产体系的决定性要素。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价值主张不仅仅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以人为中心,包容性和平等是新的社会形态的共同追求。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创造、获得、使用、分享和传播信息和知识,个体、社区、人民从而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实现他们的潜能,这是《日内瓦宣言》和《公民社会宣言》共同致力的目标①。比较而言,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虽然提出较早,但是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从知识的功用角度上看,“知识价值社会”比“知识社会”具有更加明确的导向。在笔者看来,价值问题是对当代社会界定的一个重要参量。不过,从动力性、愿景性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还可以将知识价值社会再往前发展一步,即“知识创价社会”。知识创价社会具有知识社会、知识价值社会的特征。不过,与知识社会、知识价值社会仅仅从宏观角度预测或期望不同,知识创价社会既可以从宏观把握,也可以从个人或组织这样的微观主体切入。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使用是个人或集体的基本行动,而通过基本行动来为个人、组织或社会创造价值,则是行动的基本动力和根本目标。在波兰尼“内居”的意义上,没有知与在的统一,就不会有个体知识,当然也就不会有客观知识。而这个“统一”的家就是“身心一体”的行动,是“流动的房车”。知识创价社会提出的一个目的,就是使每个人都能将知识行动放在价值的天平上考量——不创造价值的知识行动是无效行动。行动将价值和事实结合起来。价值和事实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相互充满,互为形式和内容。对价值问题不能在一个平面上看待,要立体地看,更要从四维空间看,即要考虑时间之维。价值坐标是一种综合的坐标,现实中无法拆卸,不过可以进行价值分析。就大学的知识行动而言,学术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命价值是基本的价值构成。知识创价社会的大学理念在知识的两个层面上需要创造价值,并且接受价值拷问——一是作为知识论域的大学理念,一是关于大学里的知识行动的大学理念。
中世纪第一批大学扎根于基督教信条,旨在培养有学问的僧侣,起初并非一个清晰的理念或计划的产物。大学理念根据不同时代和情境的需要、期望和结构而不断被再构思和再表达,经历变换再变换。正是这样原本局部性的想象中的理念,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与这种意象相联系,大学理念在不同时代蕴含了不同的意义。关于“大学理念的理念的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解释和再解释、改编和再改编的过程。通过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大学理念持续“换装”,呈现现代模样。克拉克·克尔是爬梳大学理念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巨型大学的理念》中钩沉历史,概括了大学理念的“三段论”——大学的理念、现代大学的理念和巨型大学的理念。他认为,“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的发展现状”。可是,“1852年,正当纽曼写作《大学的理念》的时候,德国的大学正成为新的楷模”,“用弗莱克斯纳的话来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已经在诞生了”,“但是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现代大学已经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的时候那样。历史的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定下调子”。“包罗了太多的东西”的巨型大学出现了。纽曼的“大学的理念”的热心坚持者主要是人文学者和通才主义者以及本科生,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的理念”的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专家以及研究生,“巨型大学的理念”的实行者主要是现在的大学教职员之中为数众多的那些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社会上一般的领导集团。[32]克尔还根据大学理念的特点提出了关于大学的三个隐喻:“‘大学的理念’是把大学当做一个村庄,有着一批教士。‘现代大学的理念’是把大学当做一个城镇——一个单一工业的城镇——有着一批知识寡头。‘巨型大学的理念’是把大学当做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大学理念从村庄到城镇,再从城镇到城市,下一个驿站在何处?美国巨型大学理念是否是“历史的终结”,美国大学是否为“最后之城”?克尔无奈感叹道:所谓“巨型大学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创建它;事实上,也没有人设想它。它在很长的时期里逐渐出现,它还会长期继续下去”。[33]他发现“‘大学的理念’继续缓慢地和不平衡地运转——在有些领域根本不动,在其他领域运转迅速”。如何解读克尔这些观察和判断?波兰尼的“知识二重性”是一种解释,克里斯·阿基里斯(Chris Argyris)的理论二重性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解释。
阿基里斯继承了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精神遗产,针对组织学习与改进的问题提出了行动科学的思想。勒温指出,行动研究具有六个特征:问题驱动、用户中心、挑战现状、生成经验性的可否证命题、与已经设计的理论系统联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可利用性。继勒温之后,用户中心的行动研究对用户如何界定他们的问题、如何建立和检验蕴含在他们的实践中的命题和理论,缺乏关注和质疑。在理论层面,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从事精致研究的学者,则与日常生活相脱离。行动科学的任务就是弥合两者的缺陷。行动科学假定,学习是研究者、客户和系统的第一位目标;第二位目标是通过生产知识,形成经验性的可否证命题,该命题可以组织为理论。人类是自己行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在日常的情境下,时间有限,信息不全,人们必须有一个主体规划,以表明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行动。这个“主体规划”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声称的理论,它包括个体可以表达的信念、价值和态度——它们通过“如果,那么”的表达式界定在特定情境中的有效行动,也界定无论什么情境下有效行动的都适合操作假设。第二部分为使用的理论,这是一组“当个体行动的时候使用的‘如果,那么’的命题集合”。人们也许能够意识到、也许意识不到声称的理论与他们的行动相矛盾,然而他们很少意识到声称的理论、行动和使用的理论之间的矛盾。从经验上讲,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使用中的理论。情境是另一个影响个体思考有效行动的设计及实施的影响因素。一般而言,个体和情境的边界是很难准确界定的。个体意识不到他们使用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早期习得的。当人们的行动与他们使用的理论相一致时,表明这样的行动是高度熟练化的(skilled)。熟练行动具有三个特点,它们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是自发的、不需要付出努力的,操作的时候很少有意识地注意,因为有意识的注意会阻碍行动的熟练性[34]。阿基里斯在区分“声称的理论”和“使用中的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思想。学习是一个意图和结果匹配的活动,反馈是学习的重要环节。就统御变量、行动策略和行动结果形成的链条而言,单环学习模式只存在由行动结果通向行动策略的反馈路线;而双环学习则不仅仅将结果和行动策略建立起反馈通道,还建立了结果与统御变量的反馈路线。在大学的各主体层面,都存在着两种理论,也存在着两种学习模式。差别在于,主体的“位置信号”影响着他的注意力分配,因而也制约着不同层面的理念对大学行动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结果。位置信号是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社会所处的客观位置以及这个位置带给自我和他人的主观意识和解释,涉及对空间、时间、人群中的位置的判断。位置信号影响人际和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影响个体或组织的独立行为。对位置信号的正确把握会提高行动的有效性,而对位置信号的误判会导致行为受阻。在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中,“用身体思考”④的缄默知识未受重视,声称的理论和使用的理论之间的差别未得关注,位置信号的识别以及与此相关的注意力分配问题没有进入论者视野⑤,而主体的学习维度更是想当然地被遮蔽。克尔关注到大学理念,也做了大学理念漂移的跨国对位,甚至还专门谈论了大学校长的角色,但是他没有观照理念背后这些人的具体实践、行动以及历史后果,没有触及大学背后这些“理念人”和“实践者”的命运,包括概括“巨型大学理念”的他自己。克尔已经为大学“城邦”拍下了理念的照片,但没有在理念和实践的缝隙间找回失去的主人。他的《大学之用》是“学术理念”,他主持制定的《加州总体规划》是“官方理念”,而在他及其大学内外社区成员的日常实际行动中“缄默地”发挥作用的是“民间理念”。任何形态的理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巨型大学的产生“没人创建、没人设想”不过是一个比喻。事实上,任何一种组织形式的出现都是人的工事,是人的行动结果。而这种行动,不是基于一种明码标出的“学术理念”、“官方理念”,就是基于民间涌动的“理念暗流”。如果巨型大学还将继续下去,不至于在诸如“美丽的城市坐落在美丽的校园”之类的嘲讽中分解,需要通过双环学习,也只有通过双环学习才能亘续。就大学理念而言,大学作为“学习的场所”而疏于有效的组织学习,这是高等教育界最大的讽刺。从大学改进的立场上说,理念主体的“功劳簿”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回忆录”、“启示录”和“指导手册”更值得体味,而“忏悔录”除了卢梭能够有选择地“露露丑”因而传世外,其他的在“世界3”则难得一见。大学理念的中国频道和“中国声音”⑥既有世界语,也有普通话,还有方言,这无疑是世界共有的思想财富;但就旨在改进行动的学习维度考察,需要警惕我们这些当事人落入“集体防卫”和“集体熟练的无能”之境地。
关于大学里的知识行动,包括由大学、院系和个体三个层面的主体组成的结构和内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着信息和能量方面的交换,所以在考察大学行动时需要将大学放在行动场中。在学术机构内外的边界关系上,存在身份摩擦;在内外纵向关系上,存在权力角逐;在学术机构之间和内部的横向关系上,则存在“学科纷争”。学科纷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新大学的出现,古典大学的转型,大学合并或拆分,大学内部机构和学科的整合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学科纷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的结果。巴黎大学1261年成立,它的起源和兴衰记下了查理大帝、黎世留、拿破仑等人的名字。从拿破仑时代废止(1793年撤销)到1896年重建,记载了一个古典大学的咏叹。而1968年的学潮导致1971年的肢解,刻画了大学内部和外部力量撕扯的动力形态。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是世界“智者之城”的名片。从牛津大学到剑桥大学,从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再到哥伦比亚大学(最初叫国王学院)的“母子生产”,绘制了“学术漂移”的路线图。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现,是知识价值物化的两个典型象征。伦敦大学学院是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的“作品”。据称,他指着成犄角之势从伦敦叉开方向在远处坐落的牛津和剑桥说:“我们要建一座不像他们的世俗新大学。”事实上,十九世纪以孤傲的老牌贵族“牛桥”为一极、以新贵伦敦大学学院为另一极展开的两种不同类型大学的角力,刻画了大学演进过程中持续存在的身份大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它是洪堡思想在美国扎根的第一朵奇葩。它横空出世时虽显孤独,但渐成样板。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完成的院校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学科纷争”的产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哈佛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从芝加哥大学到威斯康星大学,从斯坦福到加州大学,席卷美国许多大学的学潮乃是世界范围内相互传染接力的思想躁动的几朵浪花。在这个世界浪潮中,美国大学的狂躁,1968年法国的“五月运动”,1966年我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非同日同语,但至少从粗线条上可以做欧洲、北美和东亚的三角时空勾连。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政治体制下能够形成的“洲际间的行动默契”,岂非有思想上的移情和合谋?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二十世纪国际组织推介下高调现身的“知识经济”话语已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调色画板。“学术资本主义”成为笼罩世界大学的新兴意识形态。经济主义像飘荡在大学上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倔强幽灵,是证明大学合法性的预设公理,是摆脱大学危机的“救命稻草”,还是需要着力克服的理念论域中的迷途支流?无论如何,这些都涉及对知识价值的全面认识。
除了机构的显隐变迁,在学科层面纷争也源远流长,后有来者。哲学和文学的论争,从柏拉图那里就开始。柏拉图在讨论诗人荷马的时候,他质问:“如果荷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确有真知识而不是只有模仿术的话,我想就会有许多青年跟他学习,敬他爱他了。”“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者对于自己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35]柏拉图关于诗人的论断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它确实是《理想国》里的“对话”。柏拉图时代面对的问题是培养美德,治理国家。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问题有了新的表达。经典的问题是:阅读《哈姆雷特》能教会我们修理汽车引擎吗?修理汽车引擎能教会我们如何负责任地驾驶吗?类似的争论历经近两个世纪。在英国,先后有《爱丁堡评论》与牛津大学的辩论⑦、阿诺德和赫胥黎关于人文与科学的论争⑧以及提出“两种文化”的C.P.斯诺和利维斯关于科学与文学的论战⑨;在我国,有1923年的“科玄论战”⑩;在美国,由“索卡尔事件”引爆的后现代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论战(11)到现在还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悬案。对一幅知识的“太极图”而言,一定要从黑白间分出高下是徒劳的。有意义的是,要考察作为“组织人”和“学术人”的个体,如何在知识和价值结成的“蜘蛛网上”交往和攀爬。无论是学科性的两种文化(C.P.斯诺)、三种文化(12),还是大学行政与学院“两种文化”(13),“熟悉的陌生人”在大学已是普遍的现象。这种陌生甚至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的学科之间,在同一个学科,甚至就在同一办公室的一张桌子的对面,也同样存在。陌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还有社会性的,更重要的还有经济性的。当所有这些关系落到个人这个“网点”的价值选择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在“位置信号”这个“场点”或“坐标点”以及“行动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上找到计算单位。
在大学的定位上,有两种观点:其一,大学是什么就干什么;其二,大学干什么就是什么。前者以角色定行为,后者以行为定角色。克尔所谓“巨型大学”的“无端”出现,印证了定义大学身份的双重标准。大学的位置信号被各类排行榜以及官方给定的名分定义。身份一旦获得,大学相应地拥有了特定的“票面价值”。从而,具有同样潜质、同样能力和同样产出的成员因不同的大学位置信号获得不同的附加值。项目申请、就业竞争等机会无不打上位置信号的烙印。通过更名升格改变位置信号,成为普遍向往、追求和认可的业绩指标。在位置信号给定的情况下,转引率、发行量、点击率、出镜率、收视率在“眼球社会学”、“眼球政治学”、“眼球经济学”以及“眼球教育学”的支持下,成为学术界的新看点和卖点。“老板”力压“老师”、“教授”和“专家”成为学术人员的时髦称呼。在大学这个学术场里,洪堡提醒要保有的“寂寞”被眼球巡逻,被“微信”催促。在所谓信息时代,知识和信息混杂在一起,通过天网、地网与人网捕获人们的注意力。而在“后阶级斗争”的语境下,知识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标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通过知识获得流动”几为常识。无论对个人、社会,还是对国家,当知识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时,大学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当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变得更加饥渴急迫、更加苛刻挑剔,愿付更加诱人的支票,大学的定力何在?大学的价值是“个体户式”的没有统一度量衡的简单汇总,还是基于基本原则的“公共产品”的集体价值最大化?大学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守望?有没有类似斯宾塞提出的“第一原理”(14)?大学如何实现哲学生活、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自我平衡,如何直面经济生活的严酷和诱惑?面对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机构丛林”和行动分裂,面对混乱的价值、空心的灵魂和麻木的神经,大学如何自省?对大学而言,“知识创价社会”既是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向往,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指导意义。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创造是大学的动力,价值根本上说是人的价值,服务社会乃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大学和大学的成员都可以在“知识创价”的天平上称量自身:是否在生产并且产出真正的知识,是否以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知识的传播,是否将知识的使用作为检验知识真伪的一个标准,是否在知识价值的最后实现上持有知识的视角而不是经济利益的计算?在“知识创价”的天平上,江湖术士没有位置,倒买倒卖的商贩没有位置,用行政权力和经济杠杆压迫学术的“π型”组织和领导不可持久。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可以变现,知识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知识可以转化为财富,大脑也可以直接成为生产力,但是,知识只能和知识交换。知识的度量衡只能是知识本身。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很好地阐明知识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实现人的“内居”。大学的“所是”和“所为”都决定了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填充底色的“爱智”性格。借用纽曼的座右铭和墓志铭的话,就是“心与心对话”,“走出阴影,步向真理”。或如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费希特的呼吁,学者要“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它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36]
大学要走出“没有灵魂的卓越”,就是要重估知识的价值,重塑大学的理想,找回“根植社会、面向真理、触及灵魂”的“爱智”第一原理。
注释:
①波兰尼:《科学的深思》,伦敦1962年版,第78页。转引自波兰尼著、王靖华译:《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一兵序,第29页。内居即“知与在的统一”,“是对象和主体的双向的‘存在于内’”。
②以上资料参见Hildreth,Paul M.& Chris Kimble.(2002) The duality of knowledge.Information Research,Vol.8 No.1.
③参见Sally Burch,Information Society/The Knowledge Society,网址:vecam.org/articles517.html(2006年5月29日)。
④本来是身心一体,但身体遭弃,为了修复,故言“用身体思考”。
⑤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将“三不”、“四不”或“X不”作为修辞手法,就是对位置信号的释放和对“注意力分配”的承诺。
⑥黄达人通过对国内23名大学校长(书记)的访谈集成的《大学的声音》(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是研究中国大学领导人的大学理念的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它记录了被访校长(书记)的“显性知识”和心路历程。
⑦《爱丁堡评论》对英格兰大学的攻击的时间约在1809年10月,理查德·L.爱滋沃斯(Richard Lovel Edgeworth)在《爱丁堡评论》发表《论专业教育》。爱丁堡评论员的代表人物是杰弗里(Playfair Jeffrey)和史密斯(Sydney Smith),欧利尔和牛津大学的反击者是科坡斯通(Edward Copleston)。焦点是实用性知识的地位问题。参见Fergal McGrath.(1962).The Consecration of Learning:Lectures on Newman's Idea of a University.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pp.1-15.
⑧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82年在剑桥大学做了里德讲座(Rede Lecture)。其时,斯宾塞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回答和赫胥黎相似,强调实用性的科学知识。赫胥黎力挺科学知识,他指出,要获得真正的文化,专门的科学教育至少和专门的文学教育一样有效。阿诺德则重申了维多利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修辞技能的重要地位。那时,文学和经典艺术作为对人类内居品格和热望的表达和满足是非常必要的。阿诺德强调,世界各地继承下来的人类经典文学具有帮助我们将现代科学的成果与我们的行为需要和审美需要联系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发挥着加强、提升、加速和指示性的作用。
⑨利维斯(F.R.Leavis)在唐宁学院所做的里士满讲座(Richmond Lecture)《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对斯诺1959年的讲座《两种文化》发动了攻击。斯诺认为,自然科学者和人文学者彼此应该有一定的理解,“缺乏20世纪的物理知识堪比对莎士比亚的无知”。利维斯攻击道,斯诺虽然从科学家转行写小说,但他本人在两个领域都缺乏应有的智力和能力。斯诺在《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曾提及利维斯的攻击。见《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第101—125页。
⑩“科玄论战”的主角是张君劢和丁文江,张君劢身后是梁启超,丁文江的支持者是胡适。张君劢与丁文江同随梁启超在一战结束后的欧洲之行,回国后对科学和人生的思考确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论战起于张君劢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所做的《人生观》演讲。“玄学派”从“人心的安顿立论”,而“科学派”则立足生存权利。
(11)“索卡尔事件”起于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为使“伪科学和后现代主义”出丑而为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所触发,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争论的焦点是后现代科学馆和正统科学观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简要介绍见蔡仲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10月号。更详细的内容见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著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冲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参见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著,王加丰、宋严萍译,《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3)见詹姆斯·伍德(James L.Wood),C.P.Snow Revisited:The Two Cultures of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on。伍德指出,在大学行政和学院之间存在两种文化鸿沟。学院坚持追求卓越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而大学日渐关注“战略规划”,以驱动其他常常不同的目标。尤其是强调“底线”,更为普遍的是将“商业模式”作为大学的目标。
(14)“每一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雄武译:《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页。
标签:知识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波普尔论文; 大学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