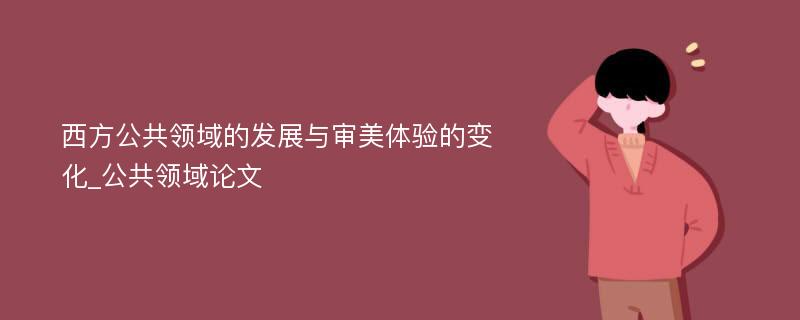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119-06
沿袭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向,本文所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一个社会向所有公民开放的舆论空间与对话场所。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并根据更佳论据的原则而展开平等论争,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对共同体的社会行为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和控制。
沿袭杜威的研究路向,本文中所说的“审美经验”并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隔绝的特殊经验,而是生命和环境相协调的瞬间。当人们将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待融入当下的体验之中,所形成的具有整一性、丰富性、积累性和圆满性的经验,就是审美经验。①
这样一来,有关“公共领域”与“审美经验”这两个似乎并无关系的研究路向就有了交叉融合的可能,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西方学术史上最早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正是潜心研究古希腊城邦制度的阿伦特。她将希腊人的生活分为两大部分:“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② 在她看来,人们在私人领域中的行为基本上是吃、喝、拉、撒、睡之类动物性的,是一种“消极的生活”;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则是出于城邦利益的思考、辩论和行动,是一种“积极的生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那些不具有公民资格的奴隶、女人和孩子们是无权进入公共领域的,他们只能躲在私人领域中过一种动物性的生活;只有具备合法权利的城邦公民才能够“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③。因为“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④。
显然,阿伦特这种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截然分割的做法是相当幼稚的。一方面,正如美食不同于果腹、爱情不同于性交一样,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即使是在厨房和卧室等私人领域中也并非纯然是动物性的。另一方面,在一个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即使是“城邦公民”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其个人、家庭、阶级的局限而考虑问题,他们在广场和殿堂等公共领域讨论城邦事务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私人利益的驱使。因此,在“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阿伦特意义上的“鸿沟”,而是相互连接、彼此延续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私人利益的驱使,古希腊的公民们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到那些公共领域中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介入政治生活,就是想用那些代表私人利益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别人,并使之成为城邦决策的依据。但是,阿伦特的看法也并非毫无价值,她有关“公共领域”的研究路向至少揭示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某些特点:作为支撑“城邦法律”这一政治“硬件”的补充形式,“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公民议政的舆论空间,起着不可或缺的“软件”功能。不难想象,携带不同私人见解的城邦公民在“公共领域”相互论争的过程,也就是诸种私人利益在城邦利益的旗帜下相互博弈的过程,是不同的个体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左右城邦的政策,也可能影响城邦的法律。这一过程也正是社会个体民主参与城邦实践的有效途径。
那么,古希腊社会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会为人们的“审美经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我们上面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旨在通过合理性的辩论而将不同的个人意见上升为城邦的集体意志,从而找到最佳途径的话,那么这其中至少隐含着如下几点足以影响人们“审美经验”的理论预设。第一,每一个城邦公民的个人意志及其人格既是自由的又是有限的,正因如此,他不能单独左右城邦的抉择。第二,各种不同的自由意志和个人意见汇集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甚至产生冲突。第三,矛盾和冲突的最终目的不是导致分裂而是实现统一,即通过扬弃各自的有限性而达成共识,以此上升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从政治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统一意志的过程;从道德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完善人格的过程;从美学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
我们知道,最能体现古希腊人审美经验的艺术品是悲剧和雕塑。关于希腊悲剧的本质,黑格尔曾经举《安提戈涅》为例,以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加以诠释。他认为,安提戈涅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执意要为其死去的兄弟下葬,是有其合理性的;克瑞翁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一定要让安提戈涅的兄弟这个国家的败类暴尸街头,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两个来自于“绝对精神”的合理性在两个个体人的身上又都表现为有限性和片面性,当他们将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否定对方之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在黑格尔看来,这出悲剧的本质既是要肯定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合理性,又是要扬弃其两者的片面性,从而在“否定之否定”中最终证明“绝对精神”的伟大。然而,如果我们丢掉黑格尔那子虚乌有的“绝对精神”,将《安提戈涅》放在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的历史境遇中加以思考的话,便不准发现,这种荒诞离奇的悲剧冲突其实是有着社会历史原因的。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自由意志的尊重,也包含了对个体偏见的批判:通过矛盾和冲突而扬弃个体的有限性,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集体的抉择和意志,并不是出于“绝对精神”的需要,而是城邦利益的需要。在这里,古希腊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像一触即发的高压电弧一样,在这出悲剧中闪耀出迷人的火花……。如果说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在人与社会群体的矛盾中思考城邦公民的行为准则,那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则是在人与自然命运的冲突中肯定城邦公民的进取意志;如果说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提倡希腊公民为城邦献身的价值导向,那么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则是从反面的意义上告诫人们不要执著于个人的感情和欲望……
不仅古希腊人的悲剧艺术与其“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实践有着“审美经验”上的联系,而且其同样著名的雕塑艺术也不例外。作为古典主义艺术的崇高典范,古希腊的雕塑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以后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有所不同:在形体结构上,它不去追求个别对象的体貌特征,而去寻找普遍意义的标准形体;在人物表情上,它不去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欲望,而去净化人物的复杂情绪。前一种特点导致了“单纯”,后一种特点导致了“静穆”,于是便有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但是,古希腊雕塑的这一特点并不像温克尔曼在《论古代艺术》一书中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追求,它同样有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印记。如上所述,城邦公民将具有私人特点的观点和意愿带到“公共领域”中加以表达,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突出个体意见的特殊性,而是要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与碰撞扬弃其各自的片面性,在相互之间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实现妥协、达成共识。与这种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社会经验相一致,古希腊人的审美经验也自然倾向于从个体对象出发,超越特殊性而趋于普遍性。我们知道,古希腊雕塑艺术的主要题材是神而不是人,可生活中没有哪位肉眼凡胎的妇女能够像维纳斯那样美轮美奂。不难想象,要塑造这样一位完美无缺的天仙,艺术家就不可能在生活中简单地选择一两位现成的模特儿,而应该将米罗岛上所有女性的优点集于一身(传说中确有类似的创作过程),这一过程便叫做“典型化”。“‘典型’(tupos)这个名词在希腊文里的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子,用同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这个名词在希腊文中与Idea为同义词,引申为‘印象’、‘观念’或‘理想’。”⑤ 不仅人物雕塑的形体结构是理想化的,其面部表情也需要做理想化的处理。作为特洛伊城阿波罗神庙的祭祀,拉奥孔因警告同胞不要中希腊人设下的“木马计”而开罪于希腊的保护神雅典娜,后者派两条巨蟒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活活缠绕致死。对于这样一场人间惨剧,艺术家并没有渲染拉奥孔父子痛苦乃至可怕的表情,避免使他们的面容因扭曲而变得丑陋,将哀号淡化为叹息。对于这座希腊化时代著名的雕塑,莱辛曾专门写下同名著作,从“诗与画的界限”入手,分析了其中的美学追求。莱辛认为,与诗歌不同,雕塑和绘画是一种直接诉诸视觉器官的空间艺术形式,因而不宜表现过于激烈的情绪,一旦涉及也必须淡化处理,否则就会因失去常态而变得丑陋,对拉奥孔的处理恰恰表现了古希腊艺术家的高明所在,这也符合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精神。其实,从古希腊城邦的社会实践来看,这种“审美经验”与“公共领域”同样是相通的。正如在观念的层面上,城邦公民进入公共领域是一种扬弃个性而获得共性的过程一样,在情感的层面上,城邦公民进入公共领域是一种扬弃感性而获得理性的过程。这样一来,原本是模仿艺术的雕塑,非但没有导向对生活原型的再现,反而导向对主观理想的表现。而这种客观与主观、个别与普遍、感性与理性的协调统一,正是希腊城邦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如果说古希腊“公共领域”的核心场所是在广场,那么中世纪“公共领域”的核心场所则是在教堂。这种由广场向教堂的转移不仅意味着物理空间的缩小,而且意味着精神空间的扭曲。因为广场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场所,而教堂则是一种封闭的宗教场所。前者涉及多元的政治见解,后者则指向一元的信仰体系。希腊文化衰落之后,罗马文化的早期,尤其是共和时代,公共领域还有着多元政治的舆论自由,但在恺撒实行独裁统治之后,元老院的作用大大降低,公民大会名存实亡。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在内部矛盾和外族入侵下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正教系统和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系统,从而开启了政教合一的“中世纪”。
中世纪的欧洲,由国王、贵族和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世俗政权处在分裂格局而又软弱无力的状态。与此同时,强大的教会系统则不仅垄断了人们的信仰,而且干预世俗生活。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政体不同,中世纪的封建国王和地方领主不需要也不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古希腊时代的多神宗教不同,中世纪的基督教不需要也不允许异端思想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代替了广场的教堂仍然是不同民众共同出入的场所,但是这个“公共领域”已不再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和民主对话的场所。13—19世纪天主教会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用于侦察和审判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人士。任何不同于正统教派的言论和行为都有可能遭到侦讯、控告和审判。对不认罪、不悔过者,刑讯逼供,从严定罪。一旦定罪,轻者处以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的宗教仪式中遭受鞭打或凌辱,重者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仅在1483—1820年间,受宗教裁判所迫害者多达30余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处火刑。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民间魔师、术士皆为宗教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因此,中世纪幽暗阴森的教堂,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祈祷者、膜拜者、忏悔者的场所。
这种“公共领域”的缺失又对人们的“审美经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与古希腊的艺术家可以在综合人体美的基础上自由地塑造神的形体不同,中世纪的教会曾一度禁止偶像崇拜。其理由是:人的形体是有限的、丑陋的;神的形体是无限的、美好的;因而用前者来比附、想象和塑造后者,便只能是对神的亵渎。因此,尽管在偶像崇拜解禁之后,人们在教堂中所看到的,也常常是那个瘦骨嶙峋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了。
就在雕塑褪去了感性生命的同时,音乐也失去了精神的活力。与禁止偶像崇拜活动的理由相类似,公元4世纪,教会也曾一度反对在教堂里使用音乐。正如凯撒利亚的主教所言:“我们以生命的诗篇赞颂上帝。全体基督信徒的和谐对上帝来说比任何音乐都更为亲切和愉快。我们的齐特拉琴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的心灵以此向上帝高唱赞美之辞。”⑥ 尽管后来的管风琴得以与声乐一起成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但这种将有限的感性形式与无限的宗教内容对立起来,以贬低前者来抬高后者的审美倾向却一直存在。作为纯粹宗教音乐的典型而为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达数世纪的格里戈利音乐,是极其庄严朴素的,没有伴奏,仅靠人的歌唱,并且只有合唱,歌词完全取自赞美诗,而且从不为适应曲调而加以改动。事实上,这里只有歌者,没有听众,或许唯一的听众就是上帝。没有任何艺术能比这更少具有满足感官的色彩,而艺术也从未像此刻这样超然于现实生活之上。但是,它对心灵却有着无比强大的征服力和震撼力,能够产生一种面向彼岸世界的精神追求。这种早期的宗教音乐具有的审美经验效果十分独特:它是一种受制于外界目的的审美经验,明显的目的就是灵魂的超越与净化;它是禁欲主义的,注重崇高甚于注重优美,注重神性之美甚于注重感性、世俗之美。
其实,最能体现中世纪“审美经验”的艺术门类既不是雕塑,也不是音乐,而是建筑。因为建筑者所建筑的正是那个时代神的栖息之地——教堂。当奥林匹斯山上那富有人性特征的诸神系统引退之后,宽敞、明亮的帕特农神庙也随之变成了历史的残骸,古希腊原本开放的建筑形式也像其“公共领域”一样向着封闭、保守的罗马形态过渡。“正如基督教的精神集中到内心生活方面,建筑物也是在四方面都划清界限的场所,供基督教团体的集会和收敛心神之用。收敛心神,就要在空间中把自己关起……在这种通过自禁闭而忘去外在自然和有限生活中纷纭扰攘的情况之下,建筑方法就必然不再用与世俗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希腊式的敞开的院子和柱廊之类形式,这些形式被移到建筑的内部,完全改头换面了。同理,阳光或是被遮住,或是让阳光透过彩画玻璃窗投入比较黯淡的光辉,为着避免黑暗,窗子还不得不开。在这种教堂里,人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外在自然所提供的,只有求之于专为人虔诚默祷、清心凝神而设,而且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内心世界。”⑦ 如果说,封闭的结构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隔绝,那么,高耸的体态则表现出人与神的疏远。无论是拜占庭式的穹顶,还是罗马式的斜山顶,都是向高空发展的,这似乎意味着在多神教向一神教的发展过程中,人与神之间日益疏远的情感联系。进入中世纪以后,这种已被疏远的人、神关系变得更加神秘,于是哥特式教堂便在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地区大行其道。在这种建筑中,不仅纤细的石柱取代了厚重的墙壁,而且采用了尖拱作为连续的穹顶,使得教堂的高度上升到一种绝弃尘寰的地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又叹为观止。因此,“我们必须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紧张状态下去体验哥特式建筑的魅力,这是与我们在优雅、静穆的氛围中悠然欣赏希腊神庙完全不同的欣赏方式”⑧。对于宗教来说,“艺术的最佳状态就是象征价值实现的时候,就是物质感官对象被再现为精神的和超验性的东西的符号的时候”⑨。在这种象征主义的艺术背后,隐藏着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宗教情绪。说到底,“通过可见的影像,我们的心灵会随着灵魂的升华而追寻那不可见的伟大神祇”⑩。
在黑暗而又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的历史上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终于在重建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迎来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也像凤凰涅槃一样,随之得以再生。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希腊传统为旗帜,旨在重新恢复人的价值和地位;宗教改革运动以重建人神关系为理由,旨在排除教会系统对信仰的垄断;启蒙运动以尊重人的理性为目标,旨在清除一切非理性的精神干扰……所有这一切,都为建设一个自由的、理性的、多元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必要准备。
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相类似,这种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以法律制度为“硬件”,因而也需要“公共领域”的“软件”加以支撑。但时代不同了,由于新兴的民族国家人口的繁多、疆域的广大和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使得它们不再采取古希腊城邦制度中曾经使用过的由公民大会决定城邦事务的直接民主形式,而普遍选择了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形式,与之相关的是政党政治的出现和左、右阵营的形成。在西方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政治变革过程中,左、右政党的矛盾常常集中在王权的取舍、等级的去留等问题上。而当资本主义革命普遍完成,当“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公共理念被广泛接受之后,情况便有了新的变化。从理论上讲,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正面的、值得追求的价值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们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矛盾:过分强调自由,便可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则会陷入两极分化;过分强调平等与博爱,可以限制两极分化,社会在保持平等的同时又会失去竞争的活力。大致说来,所谓激进和保守、左派和右派,无非是针对这一矛盾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而已:凡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和“博爱”者,一般可称之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凡是为了“平等”和“博爱”而牺牲“自由”者,一般可称之为左派或激进主义者。(11) 显然,这种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对峙,不仅影响着民主社会的政权形式,而且充斥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在这里,古代社会那种完整无缺、独一无二的价值系统分裂了,这种分裂,不仅直截了当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念,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与古典主义的一元艺术不同,无论是在文学、音乐还是在美术、戏剧领域中,西方的现代艺术都呈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峙。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在第三等级的炮火猛烈袭击巴士底狱的时候,一大批热情奔放而又桀骜不驯的艺术家疾风暴雨式地横扫了古老而又宁静的西方文坛。在文学界,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歌德、席勒,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在音乐界,有德国的贝多芬,奥国的舒伯特,意大利的帕格尼尼,波兰的萧邦,俄国的柴科夫斯基;在美术界有法国的籍里柯、德拉克罗瓦……。与讴歌人权价值,并以此来引导人们的浪漫主义相对峙,19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铜臭和血腥的日益暴露,一大批目光敏锐而又富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也不约而同地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在文学界有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在美术界,有法国的库尔贝、马奈,俄国的列宾、苏里科夫,德国的门采尔、珂勒惠支;在戏剧界,有挪威的易卜生,爱尔兰的萧伯纳……
就像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家努力去分割自由与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并将其一点推向极致一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艺术家也在努力去拆解被古典主义艺术家加以调和的表现与再现、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并将其一点推向极端。乔治·桑曾对巴尔扎克指出:“你既有能力而且也愿意描绘人类如你所见的。好的,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应当的来描绘它。”(12) 与之相反,契诃夫则要求艺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13)。雨果肯定并赞扬拜伦:“他所有的作品都深深印记着他的个性。读者像通过丧服的黑纱一样,在他的每首诗里总看到有个阴沉而高傲的形象出现。”(14) 与之相反,福楼拜则主张:“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15) 布莱克指出,“只有一种力量足以造就一个诗人:想象,那神圣的幻景”,“一个人如自问心中并无灵感,就不该妄想当艺术家”(16)。与之相反,福楼拜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而观察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双好的眼睛”(17)……总之,浪漫主义是表现的艺术,理想的艺术,情感的艺术;现实主义则是再现的艺术,现实的艺术,理智的艺术。前者依靠的是灵感和想象,后者凭借的则是观察和体验;前者面向自我的内心世界,抒发心灵的情与意;后者面向外部的客观世界,摹写生活的血和肉。前者是“有我之境”,后者是“无我之境”;前者注重讴歌,后者注重批判……(18)
当然了,正像政坛上的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并不总是体现为两个政党一样,文坛中的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也并不限于两大流派。比浪漫主义更为极端的有象征主义,比现实主义更为彻底的有自然主义。然而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公共领域”与“审美经验”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于是,作为中世纪的反动和古希腊的回归,现代艺术不仅世俗了、感性了,而且分裂了,多元了。
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信息的一体化,进而造就了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环境。对于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后现代”,笔者尚无力作出一种理论上的总结和界定,然而从“公共领域”的角度上看,它无疑是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拓展。如果说古希腊“公共领域”的核心场所在广场,中世纪“公共领域”的核心场所在教堂,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核心在议会,那么,在一个失去了中心的后现代社会里,“公共领域”的核心场所在哪里呢?它也许同时在广场、在教堂、在议会,它也许同时在电影院、在展览馆、在体育场,它也许同时在电视台、在杂志社、在互联网……处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其发表的对象和言论的空间也已不限于民族的领域和国家的疆界。与此同时,没有一种固定的价值可以约束民众的心理,没有一种主流的观点可以统一民众的嘴巴……。显然,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也必然会对“审美经验”的多元化和多样化造成深刻的影响。
走进后现代社会的美术馆,种种“主义”和“流派”让人数不胜数、目不暇接,优美的、壮美的、崇高的、滑稽的、荒诞的,甚至丑的艺术作品随处可见,就连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也日益模糊起来。于是,有人认为:黑格尔的预言实现了,艺术已经让位于哲学了!于是,有人断言:艺术终结了,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随之而到来了!于是,有人放弃为艺术的本质制定概念、构筑体系的美学研究,转身面向媒体、广告和旅游休闲……。由于后现代社会尚处在刚刚起步的建设阶段,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审美经验”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根植于“公共领域”的复杂空间,因而会变得愈发多样、愈发多元。
注释:
①参阅杜威:《艺术即经验》,第37—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③④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第62、66、73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⑤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6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⑥⑨⑩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第89、183、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⑦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88—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⑧史建:《大地之灵》,第212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11)参见陈炎:《文明与文化》,第307—32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2)转引自勃兰兑斯:《法国作家评传》,第2页,北京,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
(13)《契诃夫论文学》,第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4)《雨果论文学》,第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5)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2卷,第112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
(16)《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2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28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18)参见周来祥、陈炎:《中西比较美学大纲》,第206—227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