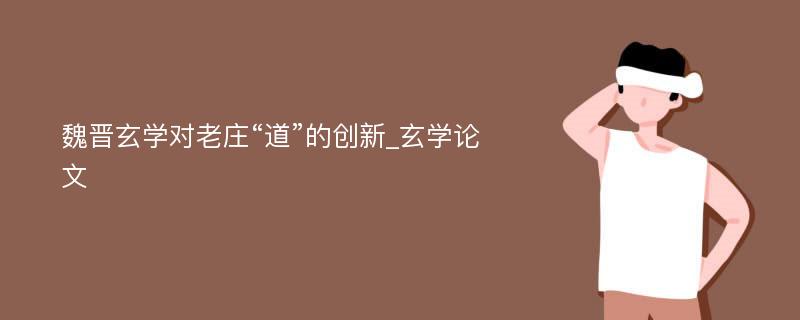
魏晋玄学对老庄“道”的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魏晋论文,老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友兰先生说:“‘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①魏晋玄学被称为“新道家”,它对先秦道家来说“新”在何处呢?道家的思想内容是多方面的,玄学作为一时代思潮,对道家思想的“新”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有“道”本论问题、言意问题、动静问题、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境界问题、性情问题等等。但玄学作为“本未有无之辨”,作为一“脱离汉代宇宙之论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的“本体之学”②,它对道家之“新”主要是对“道”的革新。那么,玄学究竟是如何来革新道家之“道”的呢?笔者不揣浅陋,试抒谫见。 一、王弼的“无”与“道”的抽象性 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出现了以何晏、王弼,尤其以王弼为代表的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玄学思潮。正始玄学为什么要以“无”为本?这个“无”究竟是什么?正始玄学的直接思想资源是《老子》,何、王都是在注《老》中提出和发挥这个“无”的③。《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何、王在注《老》时不能不首先对“道”作接受和诠释。何、王是如何来诠解老子之“道”的呢?“无”与“道”又有何关联呢?王弼有言: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老子注》第一章) 在王弼看来,天地万物以“道”为本也就是以“无”为本。王弼为什么不说“道”而屡言“无”?其实,王弼在此要解决和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玄学(哲学)问题:“道”究竟有什么属性和资格来充任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体?王弼发现,“道”要有资格来作本体,它自身必是共相,即它必须首先要具有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之属性和规定。为什么呢?因为“道”要成为本体,起码应将和能将天地万物包揽住。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只有抽象、一般、普遍的“一”才行,具体的东西是没有囊括万物之功能的。故王弼说“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夫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老子注》第二十五章)“道”的最大属性就是抽象,即“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往。”(《老子注》第十四章)这就叫“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同上) 在《老子注》中,王弼是随文引申、发挥老子“道”的抽象性思想的,这比较零散。在《老子指略》中,王弼对此则有明确、集中的论述,曰: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 这个“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者当然就是“道”;而这个作为“万物之宗”的“道”本身则是“无形无名”的“无”,即它“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不到,看不到,摸不着,无形无象无状无名,只是个抽象的“一”或一般。而正是它,才能把天地万物一切具体的存在包揽无余,“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否则,倘若“道”是具体的东西或属性的话,它就是有限制的,是甲就不能是乙,是温就不能是凉,这当然就无法“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了,也就不能成为本原、本体了。故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④(《论语释疑》)正因为“道”是个抽象的“一”,它无形无名无状无象,才有资格充任万物存在的本体,这是因为无形才能形天下之形,无状才能状天下之状,无名才能名天下之名,无象才能象天下之象,这就是“万物之宗”矣⑤。 可见,正始玄学所主张的“以‘无’为本”,实际上就是以“道”为本,这是对老子之“道”的继承。而何、王之所以要屡屡讲“无”,要用“无”而不用“道”,是为了说明或表明本体“道”的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的哲学性质。所以,正始玄学的“无”是对老子“道”的抽象性之质性的定谓和表征,这个“无”乃“道”的无形无象无名无状之抽象性的简称和概称。 用“无”来表征“道”或将“道”发展为“无”,此乃魏晋玄学对老子“道”的革新。老子在讲“道”时已有关于“道”的抽象性思想。例如《老子》第十四章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里的“视之不见”云云,定谓的就是关于“道”的抽象性规定,即“道”是超感性的,是一理性上的抽象存在。但老子对“道”的抽象性之质性却语焉不详,他用“惚恍”(《老子》第十四章)这种形容词来描述之,用“惟恍惟惚”、“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窈兮冥兮”(《老子》第二十一章)来状摹“道”这一抽象实体的存在。这种文学性的状摹语虽然形象、生动而富有现象性维度,但却总显得笼统、含混和缥忽,其哲学内容和涵义不够确定和明晰,这对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个限制。现在,正始玄学明确突出了“道”的抽象性、一般性、普遍性这一共相特性,这无疑是个进步。哲学之所以是哲学,之所以不同于科学又不同于宗教,正在于它的抽象性之品性。罗素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⑥宗教以信仰想象为基础和特征,科学则以经验直观为基础和特征;前者给人以缥缈虚幻感,后者则给人以朴素滞重感。这两者都比不上哲学,哲学是抽象的具体和具体的抽象,是经验的空灵又是理性的实在。与汉代哲学相比,魏晋玄学在继承和诠释老子之“道”时明确突出了“道”的理性抽象性,这是个较大的进步。从总体上言,汉代哲学的发展正处在宗教与科学的两极张力中,一方面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性的“天人感应”论,这无疑有虚幻、信仰的一面,带有神性味;另一方面则有王充等人的“元气自然”论,这无疑是经验的直观和素朴的类推,带有滞重的经验味;它们都未能发展为真正理性的哲学。至魏晋,正始玄学在诠释老子“道”时明确凸显了其理性抽象性,这是哲学思维水平提高的表现。 这里要说明的是,何、王的“无”明确突出了“道”的抽象性维度,以之确立了其本原、本体性的地位;但在何、王这里,尤其在王弼的“无”本论思想中,并没有将“道”的抽象性纯粹化和极端化,它讲抽象性,也讲具体性。当王弼的“无”本论玄学在强调和突出“道”的本体地位,即强调“以‘无’为本”或“以‘无’为体”时,它多讲“道”或“无”的抽象性特性;而当讲到“道”或“无”对万物的作用时,它就不得不将这种抽象的“道”或“无”下贯到具体事物中以使其表现和发挥作用,这就是“无”本论的“以‘无’为用”说。所以,在王弼的“无”本论玄学中,他既讲“以无为体”又讲“以无为用”。比如他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捨无以为体也。捨无以为体,则失其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则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老子注》第三十八章)“无”(或“道”)作为本体时,它应是无形无名无象的,是抽象;但倘若这个本体仅仅是抽象的话,本体也就不存在了,本体为了能表现和发挥其体的作用,体必须要处在用中,这就是“无”的具体性表现。故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论述了关于“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的“无”或“道”的本体性、抽象性的特性后,紧接着说:“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音则风俗移也。”可见,“大象”这一无象之象之所以能起到和发挥体的作用,正因为有具体的四象存在,“大象”就存在和表现于四象之中,否则“大象”也就真的无象可象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大音”亦如此。作为本体的“无”也是这样。所以说,在王弼的“无”本论玄学体系中,“无”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即“无”之体和用是统一的⑦。 王弼玄学是完成了一个体、用结合的理论体系;但在以王弼为代表的整个正始玄学这里,却尚未真正建构完成一个体用如一、圆融的宇宙本体论体系。因为,王弼“无”本论所侧重和突出的仍在“无”之体上,即“无”的抽象性上。“无”本论玄学作为一理论体系,其表现和存在形式就是抽象性的“无”。所以,我们所说的“无”之体与用相结合的问题,并不是王弼“无”本论自身所自觉建立起的思想内容,而只是“无”本论这一抽象性的单面性中所蕴涵着的思想矛盾性。但恰恰是“无”本论中所蕴涵着的抽象与具体或体与用的这一矛盾性,却成了王弼“无”本论玄学之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也成了正始玄学演化的方向和契机,也还是整个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思想发展的逻辑开端。 二、裴頠的“有”与“道”的具体性 王弼“无”本论中所隐含的抽象与具体的思想矛盾,导致了正始玄学的逻辑演进。其演进过程当逻辑地表现为两途:一是将“无”的抽象性推向极致而使其寿终正寝;二是将“无”的具体性下落而使其得到落实。承接“无”论的前一演化途径的就是竹林玄学的纯“自然”论,而承接“无”论后一演化途径的则是裴頠的“有”论。 竹林玄学的思想标的是嵇康在《释私论》中喊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口号。这里的“名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名分”,即一整套的社会礼仪规范。这里的“自然”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人的自然之性。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这里所说的“从欲则得自然”的“自然”,就是人的自然之性。二是指人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或意境。嵇康《释私论》言:“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这种“气静神虚”、“体亮心达”,“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就是一种精神独立自由的境界,即“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释私论》)。竹林玄学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所要任和所能任的真正“自然”就是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嵇康、阮籍等所讲的“任自然”虽然有任人的自然之性的一面,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却是不能和不可能来“任”这种自然之性的,否则的话就倒退到了动物世界。所以,竹林玄学要任的和能任的是自然无待的人的精神自由之境。 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玄学高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其思想自有时代和社会政治内容,这就是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旗号来篡夺政权的龌龊的政治勾当。但从玄学发展的思想逻辑来说,这种抛开、超越“名教”而单纯任“自然”的结果,只是和只能是走向人的绝对精神自由的纯境界。当思想趋向、落实在了纯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后,这在思想形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确是纯抽象性的。而这,正是正始玄学“无”本论中抽象性一维的展开和落实。当“无”的抽象性这样地被展开和落实了后,这个“无”也就离开了现象界而成为“无以能生”的“至无”或空无、虚无了。“无”本论中其抽象性一途的趋进也就在此终止了。 “无”本论向具体性一途的趋进就是西晋中朝时期裴頠的“有”论。裴頠“有”论自有其思想的社会内容⑧。但当他讲“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崇有论》),打出了“有”本论的旗帜后,这在玄学思想发展的理路上却逻辑地承接了王弼“无”本论中具体性的维度,将魏晋玄学的发展方向导向了众有的现象界。这种导向颇有哲学意义和价值,若用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回到了“事情自身”。这是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贡献。 将玄学致思的方向和基点放在了“有”上后,这里的关键是要能说明“众有是如何有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若说明不了或没有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有”本论就不能成为玄学思想理论。那么,裴頠“有”本论是如何作的呢?《崇有论》的第一段说: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有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 这里所解决的正是众有是如何有的问题。裴頠的意思是说,万有既然是相互区别为不同种类的多,而每一类又都有各自的特性而各有所偏属,所以众有之存在就不可能只依靠自己,而必须要凭借外在的条件,即一存在者要依靠它之外的其他存在者的资助,正是通过一物与他物的相互间的资助,众有之各有才能实际地有,事物才能实际存在,其存在也才能有迹可寻,事物存在的条件与事物本身也才会有符合、适宜等情况和表现。这,才是和才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众有之有。 裴頠在此讲这些,说明了什么玄学(哲学)问题呢?这种说明究竟有何哲学理论意义和价值呢?原来,裴頠在此讲的是众有之有即存在物之存在的存在构架问题。具体言:如果世上只仅仅有一个有,而别的一切的一切均是虚无的话,那么这个独一无二的有肯定是不能有和不会有的。世上的每一有为了能有,在它之外必须要有一他有,这个他有正是一有之有的前提和基础。这样,一有与他有之并存就构成了一个存在构架,正是在此种存在构架中,一有与他有互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能得以现实地存在着。这样,世上的众有本身就是一个存在构架,正是在这种存在构架中众有之每一有才能有和才会有。因为一有与他有所构成的这种存在构架是有与有之间的一种关系,故可称之为有的外存在构架。众有正是在这种外存在构架中来现实地有的。这就是裴頠“有”本论的理论贡献,它说明了众有是如何有的问题。 在《崇有论》的最后一段,裴頠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济者有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这是对“无”本论的否定和对“有”本论的肯定。这里提出了“至无”、“虚无”的问题和“自生”问题。所谓“至无”就是绝对的无,也就是虚无、空无,这样的无已离开了有而成为空空如也的零或没有了,即已成为非存在。这样的“至无”很明显已不是正始玄学中王弼“以‘无’为本”的那种“无”了,因为那个“无”不是“至无”、“虚无”,那个“无”之体是结合着用的。裴頠这里所说的“至无”、“虚无”,实际上是经过竹林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纯“自然”论过滤后被推向了极端的“无”,即把“无”本论中的抽象性一维推向了极端的结果和表现,这个“无”显然已与“有”相脱离了,故成了“无以能生”的“至无”、“虚无”而压根就失去了本体的价值。这样的“至无”当然是要被抛掉的。 裴頠否定“无”本论,目的当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他的“有”本论。总混之众有到底如何来有、来存在的呢?这就是一有与他有构成了一个外存在构架因而使得各个有得以存在着和有着。但就每个有言,这时它的存在依据显然不在自身中,因为在外存在构架中存在着的众有,其一有之能有是由于它之外的他有之有的缘故,此时这个一有之有的原因和根据显然不在一有自身,而在它之外的他有身上。这恰是现象界的存在特征所在。裴頠“有”论的立足点也正在这个众有的现象界上,他能从现象界众有的总体存在上来说明众有之有问题,这已难能可贵了。但如果就众有的每一有来看,其有的根据仍是个问题。就现实世界中的每一有来说,它自己本身到底是如何有的呢?裴頠在这里所提出的“自生”说,实际上涉及的正是这一问题。但裴頠在此只是仅仅涉及到此问题,并没有正面论述之。那么,世上的每个有为什么能自生、自在呢?这才涉及真正的本原、本体问题,这也才是魏晋玄学之究“玄”所要真正究的问题。这个任务是由郭象玄学来探讨和解决的。 三、郭象“独化”与“道”的“有—无”性内在结构 郭象通过注《庄》而从事玄学理论活动时,明确、自觉地考察了什么是本体的问题。他说: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庄子·知北游注》)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庄子·齐物论注》)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同上) 物物者谁乎哉?使物成为物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明显是本体论问题,即物之如斯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究竟何在?郭象认为,关于物的存在原因和根据问题,一直可以追到“造物者”处。但这个“造物者”本身又是如何存在的呢?即它在存在性质、本性上到底是“有”还是“无”呢?“无也,则胡能造物者?”“无”就是“至无”,就是没有;既然如此,它怎么能够造物呢?!郭象此处所说的“无”显然已不是王弼“以‘无’为本”的“无”,它就是裴頠所谓的“至无”、“虚无”。“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有就是存在;现实存在者都是有形有状有象的具体物,一个具体物又怎么能将众多具体包揽、统辖住呢?既不可包揽、统辖之,又何以能去物众物呢?!郭象的这个话题是接着裴頠的众有之“有”来讲的。这样,郭象就将那个作为万物存在之本原、本体的“造物者”否定掉了。这里郭象实际上是对他以前玄学所讲的“无”本论和“有”本论的审视和抛弃。“无”不能作本体,“有”也不能作本体,那究竟怎么办呢?在此郭象的确有种无可奈何的心境。当他追寻了一番本体而没有追究出个所以然时,就说“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即世上的每个有、每个存在者都各自独立地存在着且生生化化着,此即“独化”也。这里的“玄冥”是形容词。郭象在注《庄子·大宗师》“於讴闻之玄冥”一语的“玄冥”时说:“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名无而非无”的“玄冥”究竟是什么?这是说,“玄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非存在,故不是有而乃无;它虽叫做“无”,但并非空无、虚无或没有,它有,的确有“玄冥”这个东西在,这就是一种境界或意境,即指一种幽深、深邃之状态。这当然是针对“独化”而言的,即“独化”是一种幽深、幽寂状态。这里实际上是说,事物的“独化”在表面看来表现的是每个事物各自存在着和变化着的状象,但事物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地和能如此地“独”与“化”呢?却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之感,故曰“独化于玄冥者也”。 表面看来,“独化”是对事物存在状态的简单指称而已,并未揭示出事物之存在的本原、本体问题,故它似乎比王弼的“无”论浅,甚至比裴頠的“有”论都浅,因为它似乎没有讲出关于事物存在的什么理论来,只是对事物之如此存在状态作了一种指谓而已。但实则不然,郭象的“独化”论远比王弼的“无”论和裴頠的“有”论深刻,它实际上是对郭象以前玄学思想的整合和总结,即将王弼的“无”和裴頠的“有”整合进了自身中,从而完成了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任务。要明确这个道理,就要从郭象《庄子注》中来看他的整个玄学思想,以此来明了“独化”范畴的内在结构。 郭象在讲“独化”时往往与“相因”相关涉。如他说: 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其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庄子·齐物论注》) 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庄子·大宗师注》) 关于“因”字,《说文·口部》:“因,就也。”因乃凭借、依靠义。所谓“相因”,就是指相互依靠、相互凭借。从相互依赖、相互凭借怎么能到“独化”呢?“独”者明明是单独、独立,何来依赖、凭借呢?原来,郭象与裴頠一样,其玄学致思的起点在现实存在的众有上;裴頠思考了众有如何有的问题,郭象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并要思考、解决之。郭象讲的“相因”,首先就是解决众有如何有这一问题的。郭象指出: 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庄子·大宗师注》) 天地阴阳,对生也;是非、治乱,互有也,将奚去哉?(《庄子·秋水注》)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同上) 这里说的天地、阴阳、是非、治乱、唇齿等等的对生、互有,明显是关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一物与他物在空间上的并存结构,这正是裴頠所说的物物间“凭乎外资”的外存在构架问题。郭象的“相因”说首先说的也正是事物之存在的这种外存在构架,有了它,天地万物才能得以现实地存在着。这是郭象玄学与裴頠玄学相一致的地方。 郭象玄学思想当然有超越裴頠思想的一面,这就是由“外相因”向“内相因”转化,即由事物之存在的外存在状态向其内在存在本性、本质转化。事物外相因即在那种外存在构架中得以存在时,事物间当然是处于相互依赖和作用的过程中的,这样,事物之存在的那种外存在构架就内化在了一物与他物各自的自身中而积淀为每一物自身之存在的内在本性,这就是事物的内性或自性。郭象在注《庄》时有不少关于物“性”问题的说明,如他说: 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庄子·齐物论注》) 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其性足者为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同上) 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同上) 这里的“性足”、“性分”、“性命”等等的“性”,很明显是与事物的外形相对的内性或自性。这种内性在郭象看来是“足”的,即自足、自满的。正是从事物这种完满、自足的内性上看,事物的存在是不需要凭乎外“资”而与它之外的他物相因、相联的,它此时已超越了这个外在的他物,它的存在是凭乎自身的,这就叫“自本自根”,叫“自因”,也就是“独化”。所以,“独化”与事物的内性有关,它说的不是关于事物的外形存在,而是关于事物的内性存在。那么,这个内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性”呢?这种“性”的内涵是什么呢?原来,这就是事物自身的“有—无”性。“有—无”性表示的是事物之有性与无性,即“有”与“无”的有机统一。这个“有—无”性是说,就事物之存在言,单独的“有”和单独的“无”都不是和不能作本体,只有“有”与“无”的有机统一而处在生生不息之变中的“有—无”性才是和才可作本体。事物恰是在其内在“有—无”性之本性、本质之决定、主导下才得以存在的,才得以呈现、表现为“独”与“化”之统一的。这个“有—无”性就是事物之存在的内在本性,可称之为事物之存在的内存在构架。这个“有—无”性就是“独化”范畴的内在结构。 可见,事物之所以有外形上的“独”与“化”之呈现,之所以有自生、自尔、自然等等的自己存在,关键就在于事物有“有—无”性之内性。事物有“有”性,它当然就要有和能有,这就是它的存在;但事物绝不是和不能只仅仅有此一种质性,因为这样的话事物就会一有到底,这就根本不会有变化,这样的事物肯定是死的,宇宙中是没有这样的存在的,所以,当事物有“有”性时同时还要有“无”性。事物有“无”性,它当然要无和能无,这就是其由存在向非存在转化;但事物又绝不是和不能仅有“无”这样一种质性,因为这样的话事物就会一无到底而成为虚无或零,宇宙中当然没有这样的存在,一物不论怎么变化,无论变上多少次,它绝不会成为空无、虚无,它总是某种存在,所以,当事物有“无”性时同时又有“有”性。就这样,事物自身在内性上总是“有—无”性的,这一内性就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是有而无之,无而有之,有无相生,生生不息的,这乃真正的大化流行。整个宇宙就如此地大化流行着,宇宙中的每一事物也生生不息地大化流行着,这就是事物之自本自根地存在。这,就是“独化”。 所谓“独化”实际上揭示和描述的是事物内在的“有—无”性这一内性或内结构。对这一问题,郭象大概是有所直觉和体悟的,但却未能从道理上予以说清道明,这才使得他有“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之言,才用“玄冥”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状摹事物之“独化”的幽深貌。郭象在注《庄》时随文用了不少状摹、描述性的词语,如说“宥然”(《庄子·逍遥游注》),“块然”、“诱然”、“同焉”、“历然”、“畅然”、“泯然”、“旷然”、“芚然”、“蜕然”(《庄子·齐物论注》),“卓尔”、“掘然”(《庄子·大宗师注》),“荡然”、“闷然”、“冥然”、“泊然”(《庄子·人间世注》),“扩然”(《庄子·德充符注》),“突然”(《庄子·天地注》),“忽然”(《庄子·知北游注》),“欻然”(《庄子·庚桑楚注》),等等,这些状摹词描述的就是事物之“独化”的状态。这些状摹词就其哲学性质言,有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所说的“现象”性,因为它描摹着事物之“有—无”性内性之自我开显、显现、现象的存在本性和方式。但在郭象这里,他当然不明确这些状摹词所能具有的现象学性质和价值,他只是用它们来作描述和状摹,即描述事物“有—无”性存在的存在状态而已。 郭象“独化”论在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友兰先生说,郭象的玄学是“无无论”,是玄学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阶段⑨。郭象的“独化”论之所以能处于玄学思想之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就是因为它扬弃、整合了王弼的“贵无”论和裴頠的“崇有”论。就是说,当王弼树起“以‘无’为本”的旗帜而作为魏晋玄学的思想开端时,他的“无”作为对老子“道”的无形无状无名无象之抽象性、共相性的称谓、表征,其形式是抽象的,但其内容却隐含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矛盾与张力;这一矛盾与张力展开后,一极是向纯抽象一途趋进,承接这一趋向的是竹林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论,而另一极则向具体一途趋进,承接这一趋向的就是裴頠的“有”论;但“自然”论和“有”论只是将“无”论中所潜含的思想矛盾展开、展现而已,并未能做到对此矛盾的整合和解决。到了郭象的“独化”论,通过明确考察“无”、“有”问题,表明以往所说的那种单独的“无”和单独的“有”均不能作本体,真正的本体是“有—无”性的“独化”。这就既解决了隐含在王弼“无”本论中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矛盾,也整合了以往的“有”、“无”论思想,同时还完成了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探讨的任务。所以,人们公认,郭象“独化”论是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高峰。这是郭象“独化”论对玄学思想发展的贡献。 同时,“独化”论也是对老庄之“道”的革新。《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明确提出了“无”、“有”问题和概念。这个“无”、“有”就是“道”的存在结构,可以说“道”就是“无”与“有”的统一。但在这里,这个“有”和“无”却各自是独立的和单一的,它们之间未能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如若形象地表示一下的话,在老子这里,就是“有,无”式的,而非“有—无”式的。这个连字号“一”在这里非常关键,有了它,就表明了“有”与“无”的一体性的居“中”性。在《老子》第一章里,已发现了“道”的“有”、“无”结构,这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这时“道”的这个内在结构只是静态性的,即只是“有,无”式的;正因为这里的“有”、“无”作为“道”的内在结构只是静态的,所以它们就未能成为“道”之自我开启的原动力,也就不可逻辑地构成“道”的自我运动。不管郭象自觉与否,到了他的“独化”论这里,却将“有”与“无”整合为“有—无”了,这就使“有”与“无”成了相反相成的统一体,成了一种自我存在和运动的源泉和动力,也就有了事物之存在的自本自根、自因的本原、本体性了。当郭象将“有”与“无”整合为“有—无”性而作为“独化”的内在结构后,这本身就是对老庄之“道”的重大革新,这也正是魏晋玄学之作为“新道家”的最为关键的“新”处所在。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②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③《世说新语·文学》说:“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谒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论为《道德二论》。”又说:“何晏《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之,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这说明,何晏先注《老子》,后看到王弼的《老子注》比自己的注好,就放弃了注《老》,而讲他对《老子》的见解著为《道德论》了。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王弼的《老子》注比何晏的注高明在何处?其二、何晏的《道德论》是一论还是二论?关于问题一,大概因为王弼的《老子注》不仅提出了“无”本原则,尚能较好地用这一原则来诠释现象,以形成一个“无”本论的思想体系,而何晏却未能形成一个“无”本论的思想体系,只有一“无”本原则。关于问题二,冯友兰先生认为,何晏的《道德论》就是《道德二论》,即《道论》和《德论》。“《列子·天瑞》篇张湛注所引的《道论》,就是《世说新语》所说的《道论》。《仲尼》篇所说的《无名论》,可能就是《世说新语》所说的《德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8-419页。) ④这里的“道”虽然是对《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志于道”的解释,而非对老子之“道”的诠释,但思想是一致的,即“道”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抽象的“一”。 ⑤何晏因注《老》而作的《道》、《德》论今已无存,但从片断中仍可看出他的“无”本思想。比如何晏在《道论》中说:“有之有为,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列子·天瑞》注引)何晏这里所说的作为“有”恃以生、“事”由以成的“无”是什么呢?就是“道”。既是“道”,为什么叫“无”呢?因为“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就是说,“道”之所以为“道”,之所以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而成为本体,正是因为它是个无名无形无声的抽象、普遍、一般,这就是“道之全”;“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列子·仲尼》注引何晏《无名论》),若有名的话就名甲则不能名乙,就不能苞通天地,故也就作不了万物存在的本体了。 ⑥[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页。 ⑦据《世说新语·文学》说,何晏先注《老子》,当他看到王弼的《老子注》后神伏于王弼,就将原来注《老》时的一些思想写成了《道德论》。何晏之所以能神伏于王弼,可以肯定,并不在于王弼的“以‘无’为体”的这个“无”本论原则上,因为何晏自己就有这一原则,而是在“以‘无’为用”的“无”本论原则的下贯和运用上,即王弼能较好地将这个“无”的原则用来解说、说明现象,而何晏则不行或做得不够到位,故他神伏于王弼。可见,王弼通过其《老子注》构筑了一个“无”本论的玄学体系,而何晏则仅有“无”本论的原则,尚未形成使“无”之体与用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⑧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诸公赞》、《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说,裴頠作《崇有论》而倡“有”本论,是为了“疾世俗尚虚无之理”,“以矫虚诞之弊”,即为了矫正因竹林玄学末流的“作达”之风而导致和造成的对社会“名教”的严重破坏。 ⑨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