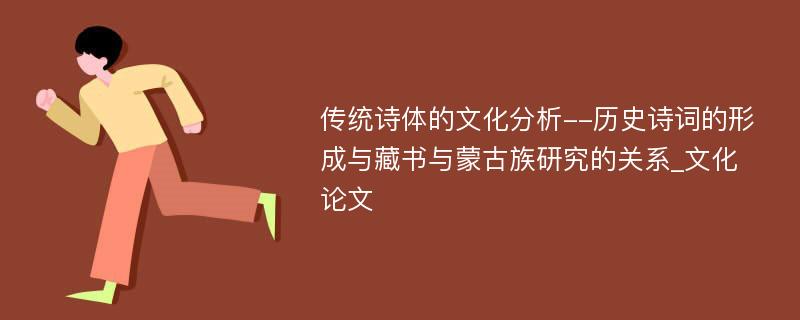
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体论文,类书论文,传统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为历来罕有论述的唐代《史》大型组诗溯源,揭示了这一诗体与蒙训教育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考察了诗体形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文中又提出敦煌本《编年诗》是赵嘏所作,为唐诗辑佚提供了新见。
晚唐五代之际,七绝大型组诗盛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诗史现象,其中《史》一体,尤为多产①。现存汪遵、胡曾、孙元晏、褚载、周昙诸家《史》组诗,与中晚唐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以至罗隐等人的史之作风格上迥然有别,而在多方面逗露出俗文学的特点,具有独特的体式传统与写作背景。它们虽历来为正统评家所轻视②,却并不因此而失去研究的价值。本世纪40年代,张政烺先生的《讲史与史诗》一文突破前人成见,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他以民间文艺的兴起说明史诗的盛行,认为史诗是直接用于讲史伎艺,配合说白的一种讲吟文本,遂开讲史一体,“初由童蒙讽诵,既而宫廷进讲,以至走上十字街头”③。后来任半塘先生进而认为史诗的传统应上溯到北魏《真人代歌》,说明讲史早有先例④。他们注意到了童蒙讽诵的特定背景,肯定了史诗与社会生活和俗文学的联系,确是启沃后学的创见。但是,何以在《真人代歌》后,数百年间,这种大型“组诗”会绝迹,直至晚唐方始重视?童蒙讽诵与讲史究竟有无直接关系?史组诗有无其它更明确的源头?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因此《史》一体形成的具体过程仍然模糊不清。我认为,诸家《史》组诗是一种有特色的俗文学创作,性质属于唐人自创一格的学校读物,其体式渊源应溯至初唐时期类书体制的《杂》的兴起;类书、蒙训教材是《史》组诗形成背景中两个重要因素。
一
类书与唐诗发展关系密切,学者早有论述⑤,但尚未详及与具体诗体的联系;其对于大型组诗的影响,始见于李峤《杂》⑥。作为一物组诗,它的吟对象从日、月、星、风到珠、玉、金、银包罗甚广,实质上是利用类书体制写作的大型组诗。《全唐诗》所录不分门类,使人不易看出它原先的性质;日本所存刻本则清楚地分为乾象、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十二部,每部系以十首五言律诗,皆以名物为题,共一百二十题。门类标目即使不能肯定为作者所拟,也与题内容序列一致。这样系统的编排体例,与同时期出现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一批类书的体例相合;这几部官修类书门类还较繁复,以《和刻本类书集成》所收后来的类书相比较,门类更为接近。因此,可说唐代类书启发了分类杂诗的创作,其体制特点决定了《杂》必然是大型组诗的形式。由于李峤《杂》的存在,大型组诗在唐代的初创至少可推溯到睿宗时期(708-713)比王建《宫词》百篇要早100余年⑦。李峤作《杂》的具体时间虽不可考,但至迟在修文馆大学士任内仍有可能(708-713)。修文馆早设于高祖武德四年(621),九年改弘文馆,后几经更名。景龙二年(708)置大学士2人,学士8人,直学士12人,从皇、宰、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第子,或职事官五品以上子弟有书法特长中选,而馆职即“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这一环境与类书和《杂》得到使用的可能性都颇为切合。
类书的传统可上溯到三国时代的《皇览》,此后绵延不衰,唐代空前兴盛⑧。唐代类书中一种主要类型是辑录前人诗文全篇或片段,其性质等同于诗文类检或类编,功用是提供诗文写作的参考,如章学诚所谓“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⑨,这种类书的流行,当然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科举、教育和文学的发展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类书”与“诗集”的界限,至此已不易区分,也许也不必区分。胡应麟曾认为类书应列入集部,今人称赞其说将两者“打成一片”,“解决了其中不必要的纠纷”⑩;《新唐书·艺文志》录李峤同时代人张楚金《翰苑》,既列入类书,又列入总集,颇能说明问题,而《杂》组诗或“诗集”的存在,尤可提供一实际的例证。这种兼为诗集的类书本身具有供士子科举考试备览和学诗题者取资的功用,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章趣味的楷模,这一特点促使一些以文章自负的文人写作这种类型的作品,既炫示自己的才艺,亦因人们模仿和借鉴之需。李峤有自恃才学、好强逞博的一面(11),可能即是创制《杂》这样大型组诗的一重动机。同时,在那类书多产、举业兴盛的时期,《杂》似乎也不是孤立的作品,与李峤同时期、地位也相近的董思恭,曾参预修撰文艺性类书《瑶山玉彩》(《唐诗纪事》卷三),《旧唐书·文苑传》记“所著篇,甚为时人所重”,今仅存五律物九首,风格与《杂》相近,同受官廷物诗风气影响,很可能也是一大型杂组诗的残篇(12)。
促使文人利用类书体制创作大型组诗的另一原因,在于其本身的诗学意义。客观事物经人为地、有组织地大规模集合、排列,尤其加以程式化表现的循环重复的处理,人们阅读时对于作品意义的期待空间就从字句间扩展到了篇章之间,超出描摹对象本身意义之上的全篇结构的意味得以突出。《杂》的形式感寄寓着对秩序井然的客观世界从容自得流连吟玩的兴趣,这与当时类书中载录的六朝单篇物诗如谢朓、沈约之作效果显然不同,因而是一可予注意的创新。大型组诗的诗体意义即在于此:在单一存在的状态中显得平凡无趣、琐屑零碎的事或物,都可以通过连类编排的办法,在集合存在的形式中相对增进吟的兴味(13)。《杂》如此,中唐王建《宫词》亦如此,晚唐诸家取事庞杂而无所发挥的《史》组诗更是如此(14)。
由类书到杂史诗,体制上遵循按事义分类,以名物系题的原则,一事一题,决无混杂,并沿承了取事载籍、敷衍成篇的写作方法,这些预示了诸家《史》的创作特征。同时大量单元集合并置的结构框架,使表现趋于程式化,在《杂》即“熔铸故事、谐以声律”,“以诗体隶事”,是典型的“修辞练习”(15),这种表现为后来诸家《史》组诗在更通俗化的层面上加以继承。
有了《杂》一类诗的流行,后世《史》组诗就有了体式上的借鉴。但从《杂》到《史》尚有发展变化的中间阶段,而不能视为直接的过渡。两者诗体及雅俗倾向还不尽一致。作为宫廷诗的样板,五律体的《杂》直承六朝宫廷物诗的风格,既讲究词采典故,又受到吴歌西曲的语言影响,所以比传统的雅正诗体清新浅初,又较浅俗诗体典丽整饰,与突出说教劝戒、语存讽意的《史》在格调上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从类书到杂组诗只是史组诗形成线索上的最初一个环节。
《杂》之后出现了王建《官词》百首,一向受到注意。由于其七绝百首的形式特征,人们很容易将它与《史》组诗联系起来,这里颇有可商之处。《宫词》叙写当代宫闱琐事,“只言事而不言情”(16),旨在用于市井传唱,故得“天下皆诵于口”(17)。且不管与民间伎艺是否有关,其与宫廷诗背景的《杂》距离不小(18),也与训俗内容的《史》方向不一,较之时期相近的顾况、张祜等所作《宫词》,则大型组诗的《宫词》似自有传承脉络,从小型组诗独立发展而来。另有一点人未注意的是,《史》组诗似并不以“百篇”为定制,可以说王建《宫词》百首直接启发的应是曹唐《小游仙诗》、罗虬《比红儿诗》和花蕊夫人、和凝等人的《宫词》组诗,与诸家《史》虽共同丰富了七绝大型组诗的实践,却仍分属平行发展的两条线索。《史》组诗的传统,仍需别作探求。
二
这样,各类官学、私塾的蒙训教材,便成了我们考察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唐代公私教育发达。在较初级的乡校村学,以启蒙学童为职司,其课本多采《千字文》、《太公家教》、《开蒙要训》及杂科类书或俗谚格言集等,大都粗略浅陋,只能起到让学童借助记诵粗识事物名义的作用,效果有限。仅据此来认识唐代学校是不够充分的。那么在程度稍高的州郡之学及私塾家学使用什么教材呢?我以为主要有三类读物,一是正统经史典籍,如敦煌抄本甚多的《论语》、《左传》等;二是旨在辞章声韵技巧训练、用作观摩范本的诗文作品;三便是为辅助第一类正统经史的教学,而以经史为纲目、兼采前朝故事和民间传说直接撰作的诗文作品,这类作品兼为蒙训读物和文学创作,它们的产生是唐代学校教材的一大进步。这里需考虑后两类作品的互相关系,正是在民间教学环境中名家诗文的传布,对于《史》那样的俗体诗的产生有直接作用,而以诗文体裁直接写作教学读物,又同时弥补前一类作品侧重写作技巧而不及训戒的不足。
说到前一类作品,众多唐人名篇和李峤《杂》都在此列。先看《杂》,从《佚存丛书》和敦煌写本情况来看,可知其被实际用作写作范本,于是能由京师学馆而及地方,广为流布。《唐才子传》称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辄传讽”,其诗自然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李峤既为修文馆大学士,领袖当时宫廷诗坛,因此《杂》当为教授贵胄的文本,即上文所引修文馆“教授生徒”的馆职所需。作品既经“传讽”,影响必然会扩大到地方,这样也就与较广泛范围的地方教育有了联系。《佚存丛书》保留了张庭芳注及序,张为“登侍郎守信安郡博士,”序作于天宝七年(747),可知张为盛唐时州郡学官,亦即注庾信《哀江南赋》者。序云“于是欲罢不能,研章搞句,辄因注述,思郁文繁,庶有补于琢磨,俾无致于凝滞。”后两句尤可注意,既谓有利于“琢磨”,又谓加以注述,则此琢磨并非为己,而“无致于凝滞”亦为使他人便于诵读理解,因此,身为州郡博士的张廷芳实是取此分类物组诗加以注释,用来教授学生。以州郡之学而论,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锻炼学生体察事理,琢磨辞章,为科举作准备,因而《杂》是理想的课本,特别是通过分类编排,条贯清晰,把科考所需的知识名目组织起来,便于记诵摹想,也便于次第讲述教授。另从高于初级蒙学程度的各类官学和私塾的需求来看,使用比较文雅正规的文学作品也是自然趋势。如人们熟知的《兔园册》,《郡斋读书记》谓“皆偶丽之语,至五代时流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孙光宪《北梦琐言》称“乃徐、庚文体,非鄙朴之谈”。一般村校都在使用这种稍讲藻饰的作品,则较高程度的教材更趋文雅正规,不难想见。以大型组诗或诗集教授生徒或子弟的风气,似是在中晚唐之交开始成熟的,反映在地方学校诵读时流名家篇章的不少例子,如白居易《与元九书》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元稹也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竟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后来皮日休《伤进士严子重诗序》记“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言“集”而非单篇,值得注意。诗人与民间教育发生联系的情形也约略反映在同时期有名声的诗人如张仲素、元稹、白居易、窦蒙、陆羽、颜真卿、温庭筠、皮日休、郑嵎(19)等多有类书之制,疑即自编之诗集如前所述兼类书与诗集二职于一身者。这可以皮日休为例,《通志》卷六九类书门下著录其《鹿门家钞》九十卷,“以五言诗类事”,当即皮氏子弟之课本读物,篇幅达到九十卷,且以“类事”为宗旨,性质同《杂》诗集无疑。
在这种风气中,诗人直接写作诗体蒙训教材的趋向必然得到推动,而且经史故实的题材不免突出。从客观上说,仅用于琢磨写作技巧程式的名家创作,既传抄方便而可现成取用,另行专事写作同类作品的必要性自然减少,而经史本来就是正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历史素材具有树立处世立身规范的便利,所以用史事类纂教导学生的倾向由来甚早。《旧唐书·良吏传》记韦机“显庆中(656-661)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校,机创孔子庙,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篇幅已近大型组诗。又著名的蒙书《蒙求》,四库总目卷一三五列入类书,有天宝五年(746)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称“错综经史、随便训释”,正文篇末又说“浩浩万古,不可备甄,芟繁摭华,尔曹勉旃”,意即颜师古注《急就篇》叙所谓“包括品类,错综古今”,依循从历史中“征材聚事”(20)的原则,不出当时历史常识的范围,既利记诵,尤寓教训。韦机所作“赞”,不妨看作个别的自发实践;《蒙求》被采入《全唐诗》,但作为诗篇有些勉强。直接当作蒙训教材而写作的、体式更完整的诗篇在中唐真正出现,显然与上述名家诗篇流行于乡校的风习有关,其代表性作品为敦煌本七言古诗《古贤集》,虽未必能与元、白、杜牧等名家之作相比,但在蒙学上却是一有意义的进步。诗如“君不见秦皇无道枉诛人,选士投坑总被坟;范睢折肋人疑死,随缘信业相于秦;相如盗入胡安学,好读经书人不闻;……”提供学童讽诵的特点十分明确。论者正确地观察到这篇“全篇主要讲历史人物故事的诗体作品”与《蒙求》十分相象;并认为“对晚唐至北宋初的蒙学有积极影响”,且“与《急就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较初级的蒙书大不相同,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是“科举制度、蒙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21);我以为这三点也正是《史》组诗形成的背景因素。
到更为成熟的蒙训诗篇或者说诗体教材《编年诗》出现,历史题材的利用蔚为可观。《编年诗》今存敦煌抄本(S.619)(22)序云:“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七言八句,凡一百一十[章],”(23)是以史传为基础,取古人事迹按年岁编排,每岁系以一至二首七律,共百余首组成的大型组诗,今残存二十八首,也已足够说明性质。《唐才子传》卷七赵嘏条下录《渭南集》外,有《编年诗》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得到一可贵实证。《新唐书·艺文志》赵嘏《渭南集》外亦录《编年诗》二卷,《通志》艺文八著录赵嘏《编年诗》一卷,《崇文总目》卷五著录《赵氏编年诗》,应指同一作品。最早移录此卷的王重民先生曾引《崇文总目》,也极有眼光地注意到其与通俗类书的联系,惜未推及《唐才子传》,而近年《唐才子传》整理者又多未注意敦煌卷子,故此作的归属长期未得确定。赵嘏曾作“刻意揣摩,近于试帖”(24)的《昔昔盐》,同为课考所用,又近体中七律较为擅长,因此《编年诗》基本可信为赵嘏的一部为《全唐诗》失载而保存于敦煌写卷中的大型组诗。诗的特点是杂取相关故实,加以糅合,显为“训俗”或“授徒”而作,诗如“卫玠风姿秀入神,钟繇小子非常伦。曾过学舍羡流辈,不惜金环与丈人。神满涕夷初执砚,书论忠孝愿终身。此时东汉贤皇后,捧额含情不自承。”(五岁)可见其概。序又云“其有不尽举一年之事,而复杂以释老者,盖唯诗句之所在,”说明是凑合成篇,不太讲究组织脉络,与实际情形也相吻合,有些诗句嵌合典故,衔接生硬。所以组诗的意图正象《古贤集》一样,仍是以标准的诗体形式,将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其产生环境和写作动机只有从蒙训读物这一角度,方能有合理的解释(25)。正是有了《编年诗》这样直接的范例,在同样环境,为同样目的的《史》组诗才得以产生,文人写作供给塾师或教官使用的性质豁显。王夫之曾评“胡曾《史》一派”说,“直堪为塾师放晚学之资”,恰好点明了作品的功用(26)。
同是以近体诗组织成齐整铺排的大型组诗,李峤《杂》与赵嘏《编年诗》,通过学校教育而联系了起来。可以说,《杂》取资类书所启示的大型组诗体制经《编年诗》的利用接受,转出一支兼顾教训与吟的俗体诗传统,最终形成《史》组诗体制,从而与原先侧重在赋陈物色琢磨辞章的《杂》已有歧异,《杂》的影响是转折发生的。而《杂》的本色传统实际上也未消泯,比如在徐夤试帖风格的题诗中有所延续。徐诗今存物和史七律五十余题,显系一大型组诗的残篇,固其诗由后人辑集,佚失不少,今存本已编次无序,不易看清原来面目。如《灯》、《扇》等六题本即与其它单字题属同一组(27),而史七题显然厥佚《齐》、《梁》二题,史诸题手法与物程式化的表现雷同,也许正象李峤《杂》以《经》、《史》、《诗》等“文物”与《日》、《月》、《金》、《玉》比并一样,史与物均为杂总题的从属部分。徐有《自十韵》:“未游宦路叨卑宦,未到名场得大名。……拙赋偏向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赋如清人所评“不出当时程试之格”(28),诗当是指这类兴寄不高,同样不出程试之格的杂诗。《唐才子传》记徐《探龙集》“谓登科射策如探龙之珠也”,也和赵嘏《昔昔盐》之类作品一样,显示了上举唐代学校中侧重声韵技巧训练,用作观摩范本的那类读物的面目,它的一个发展是兼顾到历史题材,在杂总题中容纳了史部分,反映了实际需要,也就从又一个角度说明了《编年诗》代表的史主题的流行。不妨推测,皮日休《鹿门家钞》九十卷之多,“类事”范围较大,可能也包括历史人物事件之题在内。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赵嘏之后,皮日休、徐夤大致同时,《史》组诗行世就有了充分的条件。
三
这里尚需分辨《史》与民间伎艺的关系。任半塘先生曾认为,《史》组诗配合说白讲解为“说话之伎”所用,猜测有连缀各诗的“讲语”,并认为其源可溯至北魏《真人代歌》(29)。这就需要先讨论《真人代歌》的性质。《魏书·乐志》记“掖庭中歌《真人代歌》,……效届宴飨亦用之”,显然是一种颇为严肃的歌诗,且为乐官所奏,而非伎人或学官所吟诵。《真人代歌》的内容,也未必是歌唱历代史事。所谓“真人”,在这里是指开国或兴复之君王。《魏书·乐志》记“上叙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下句为上句制约,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君臣废兴”即指北魏一季历朝君臣废兴,或北魏立国之际各交战国的群臣废兴;二是虽及历代史事,仍以北魏祖宗开创业绩为主,借历代君臣之事作陪衬。其云“上叙”、“下及”,非“首叙”、“更云”,说明不是平行关系,则以北魏事为主无疑,因而《真人代歌》应是歌颂北魏一代历史的长篇分章歌诗。诗虽不存,但有旁证可参,如曹魏《鼓吹曲十二章》从“楚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直到“定武功”等,孙吴仿作《鼓吹曲十二章》“炎精曲”、“汉之季”、“摅武师”、“伐乌林”等,各标君命正统,同用于郊庙,演唱人也非说诗伎人,而是乐官。这样,《真人代歌》从诗体性质看,与晚唐《史》组诗并没有联系。如此方可解释,何以两者中间有数百年的“空缺”,就因两者本非同一传统的作品。其实《真人代歌》一类诗并无空缺,如唐代就有《鼓吹铙歌十三章》(柳宗元作),述高祖太宗龙起平定海内之事迹及当时群雄兴替,正与《真人代歌》、曹魏《鼓吹曲十二章》等成为另一个系列。所以,认为《史》组诗出于《真人代歌》这样的“说话之伎”的看法,对《史》和《真人代歌》两者的认识都不够确切。
《史》组诗本身是否以民间讲唱或官中进讲为写作背景?(30)需看作品。比较当时流行的作为民间讲唱文学的历史题材作品,如《捉季布传文》、《季布歌》及《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等,都是敷演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同于后世的《二十五史弹词》,所以诸家《史》组诗至少与已知唐代讲唱文学的体制不甚符合(31),即就故事而言,胡曾《华亭》写陆机,《彭泽》写陶潜,《灞岸》写王粲,孙元晏有《庾信》,事取文人,不同于讲史系统。又汪遵有《屈祠》、《招屈亭》、《渔父》三题写屈原,周昙《毛遂》、《子贡》、《胡亥》各有二题,是否有足够的故事“说白”或“讲语”相配十分可疑,相形之下,照例故事颇丰的隋炀帝在周昙《史》中仅有一题,更显得不均衡。此外胡曾、汪遵以地名系诗,似缺乏便于贯穿全篇的叙事线索;胡、周《史》传本虽有注或讲解,却并不是原作者所撰说白,而与李峤《杂》的张廷芳注性质相同。孙元晏《郭璞脱襦》有“吟坐因思郭景纯”一句,单凭“吟坐”尚无从认定暗示学校的讲席,当然更不能确证与讲场相联系。又《乌衣巷》云“满川吟景只烟霞”,“吟景”更不宜如任半塘先生猜测为图画如变相之属,进而据以推断《史》为配合图画的讲唱文本。
周昙《史》在今存诸家组诗中最称完整。其《吟叙》云“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闲吟》云“考摭妍媸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显然不适于市井传唱;“月殿花台”可以是一般馆舍,而不必然是宫廷内苑。尤其是作者身份,按《天禄琳琅书目》揭衔为“国子直讲”,即《新唐书·百官志》所记“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的普通教官,是国子博士、助教的助手,地位尚不够为君王宣讲古今成败,所以其《史》当为官学教材,不但不用于讲场之类民间娱乐场所,也非进讲于国主。张政烺先生认为周昙《史》“与平话之体尤为相近,可断为讲史之祖,”值得重视;但由此以为《史》即宫中进讲的文本,似将《史》成因与讲史伎艺联系得过于直接了。
也许更可注意的是敦煌本《水鼓词》,风格接近王建《宫词》,今存四十章(32)。其四“伶人奏语龙墀上,如说三皇五帝时”,又廿七“批答奏章不再寻,少年宣史称君心”,宫廷中有“少年宣史”,但细观下文,似与吟之事无关,而“说三皇五帝”自不以一代为限,也很接近周昙《史》起自唐虞三代的范围。假使真有“说三皇五帝”这样一种伎艺,也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属于什么体制,用什么底本还不能断定;如果是由伶人吟唱如长篇词文,则排除了插入说白讲解的可能,而且似乎也不容周昙那样不时的“又吟”、“再吟”。二是假定这一伎艺产生于《史》同期,《史》也与宫中演出不甚相宜。诸家《史》内容浅俗而语存寒俭文人怨尤之意,一望可知,尤其象周昙《史》中写“身从倾纂来”的王莽连续三题,“铜马朱眉满四方,总缘居摄乱天常。因君多少布衣士,不是公卿即帝王”,寄寓对唐末时局感慨,显然也不合于当时君主之前陈说。因此,仅用《水鼓词》还不能证实讲史伎艺中直接产生《史》。即便《史》后来被用于讲场,就象被后人加以注释或用于话本一样,只能说明组诗的影响,不足以解释诗体本身的成因。
最后,韩国磐先生曾推测胡曾等所作《史》组诗为行卷投献之作(33),似亦不确。赵彦卫《云麓漫钞》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湿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为行卷研究者所熟知。行卷诗文需以才情见识,驰想议论自表,而《史》组诗则格调平庸浅近,似不足为逞才之资;实际上《史》作者尽可以写出更见风致也更为理想的投献工作,胡曾、褚载、汪遵在《史》以外都另有作品传世,可为明证。要之,晚唐《史》大型组诗还是以类书体制的《杂》为滥觞、以比综史事之诗体教材如《编年诗》为直接模式,在民间教育的环境中产生的俗体诗。
注释:
① 除本文述及诸家《史》外,尚有今巴佚失的孙元晏《览北史》三卷(与今存《六朝史》相对),杜辇《唐史》十卷,阎承畹《史》三卷,《六朝史》六卷,童汝为《史》一卷,冀汸《史》十卷等,又朱存《金陵览古诗》可从《后湖》一首略窥一斑,风格亦同《史》。
② 许学夷《诗漂辨体》评三家《史》“俱庸浅不足成家”,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廿一斥胡曾诗“尤为堕入恶道”,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评胡诗“轻佻浅鄙”,“不识何以流传至今”,王士祯《万首唐人绝句诗》评胡诗“读之辄作呕秽”。这类评价都拘于艺术品鉴的单一标准,对于辨体溯源的探讨欠缺甚多。
③ 张政烺:《讲史与史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十分册(1948),第602-645页。
④ 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九章五节“讲史”。
⑤ 如闻一多《类书与诗》文,收入《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4)卷三。又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天津古籍,1986)。
⑥ 李峤《杂》我国虽有著录而失传甚久,至嘉靖间日本天瀑氏(林衡)刻《佚存丛书》本始收入,又有正觉楼丛刊、艺海珠尘刊本,《全唐诗》复辑入。近人又整理出敦煌写本《杂》残篇(P.3728.S.555等)。参《和刻本汉诗集成》(东京,1975)卷一收石川贞订《李巨山物诗》。
⑦ 王建《宫词》组诗的完成不早于宪宗朝(805-820)。“少年天子重边功”一首当指宪宗;“鱼藻宫中锁翠娥”一首写池底铺锦,亦宪宗朝事;“东风泼火雨新休”一首写汉阳公主,即《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所记“顺宗女汉阳公主,名畅”。
⑧ 唐代类书佚失严重,如张涤华《类书流别》录四十余部,今仅存七部。又通俗类书如敦煌写本所见者也很丰富,尚待疏理。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
⑩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第27页。
(11) 《唐诗纪事》记峤三戾之二:“性好文章,憎人才华”。
(12) 参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中译(广西人民,1987)第168页。
(13) 《杂》所门类比起一般类书已有主题侧重,如“芳草”、“嘉树”、“灵禽”、“祥兽”之名,取祥和之义。
(14) 论者注意到sequence和series两种组诗的不同,前者如杜甫《秋兴》,注重内在意绪钩摄结合;后者如阮籍《怀》,结构联系相对松散,仅有形式上的主题串联,颇有助于认识《史》及《编年诗》组诗。见宇文所安《盛唐诗》(Stephen Owen,The High T'ang: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Poetry,Yale UP,1982,P218);列维《中国汉唐叙事诗》(Dore J.Levy,Chinese Narrative Poetry,Duke UP,1988,P108)。
(1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中译,第168-169页。
(16) 蒋之翘仿王建作《天启宫词》序,《明宫词》(北京古籍,1987)。
(17) 范摅:《云溪友议》记王守澄。
(18) 《宫词》虽写宫闱题材而并不承袭“宫体”诗风,故以轻快流转见长。这一点易为人所忽视,如西人以王建《宫词》为“宫体”诗(palace-style poems)恰误。见《印第安纳传统中国文学指南》“王建”条(The l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86,P.859)。
(19) 《宋书·艺文志》卷五录郑嵎《双金》一卷,嵎—作嵎,疑作嵎是,即《津阳门诗》作者。
(20) 章学诚:《校仇通义》十五之二:“征材聚事,《吕览》之义也”。
(21) 韩建瓴:《敦煌写本〈古贤集〉研究》,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1988)150-176页。姜亮夫先生以《古贤集》“文件和《世说新语》差不多”,尚不确切。见《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1985)第58页。
(22) 见小翟理斯编《英伦博物馆藏敦煌中文写卷目录》编号7191(Lionel Giles ed,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from Tunhuang in the BM,P.237)。刘修业先生《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文(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同上注(21)根据王重民先生工作的积累录出诗与序。诗题似应作《编年诗》,详下文。
(23) 刘修业先生录序文与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略有出入,以前者为准,按此序似非作者本人所作。
(24) 《唐诗选》(人民文学,1978)第305页,“赵嘏小传”。
(25) 从抄写情况看,该卷子背面又书“白[百]家碎金一卷”残篇,“碎金”正是蒙训字书或通俗类书一重名目,亦有助于说明该卷实际用于教学的情形。
(26) 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1981)第143页,引《古诗评选》卷四评语。
(27) 晚唐韩溉有《柳》、《水》、《松》、《竹》、《灯》、《鹊》七律六题,全与徐夤《柳》、《水》、《松》、《竹》、《灯》、《鹊》诸题合韵,可知“”字赘,原题即《灯》之类单字题,与李峤《杂》一名“单题诗”意同。韩溉应是见到徐夤组诗或诗集原貌的。
(2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
(29) 任半塘:《唐声诗》九章五节。
(30) 如任半塘先生谓,胡曾、周昙《史》诗“亦曾配合说白,讲吟于市廛或宫廷间,”见《唐声诗》第19页。
(31) 关于唐代民间讲唱文学的分类,早先统归“变文”不够全面,周绍良先生《谈唐代民间文学》(《新建设》1963年1期,又收入《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分为变文、俗讲文、词文、诗话、话本、赋六种;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文学遗产》1982年2期)分变文、讲经文、词文、话本、故事赋五种;大体已概括已知作品体制。“讲史”则要在五代北宋后才形成。如果以《史》为讲唱文本,则至少还缺乏韻散夹写或题名标明的实物的有力佐证。
(32) 辞见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所录,写作具体年代尚无定论。
(33) 韩国磬:《略谈有关唐诗的几个问题》,载《随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