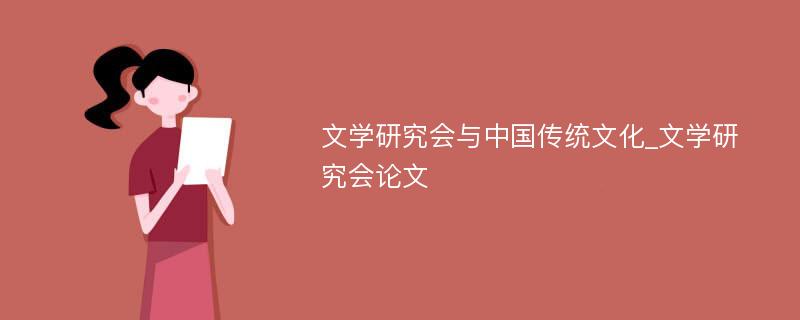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会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1]02-0071-05
从小说流派史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成立于1921年1月4日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小说流派史上的重要界碑,它标示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文学研究会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人员结构,纲领主张,都对此后的中国小说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研究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成员较为广泛的社团,这种结构有利于成员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松散,并不意味着他们艺术态度的放任不羁。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公开主张:“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自觉地与文学“游戏”说、文学“失意”说分开界限。“为人生”是他们的理论主张,在这面旗帜下,集结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以切实的小说创作介入“人生”,认为文学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发挥它的作用,只有这样,文学才有价值,“文学——如果只有他它本身的目的,那也只是没有用的艺术”,“人生的艺术——文学,才能算做真艺术——真文学”(注:耿济之:《〈前夜〉序》,《前夜》,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文学研究会的这些文学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注重实践理性、关注国计民生的务实精神如出一脉,我们可以说“为人生的艺术”——文学研究会小说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文以载道”传统与“诗以言志”传统的和谐统一体,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尤其具备继承与创新的双重意义。
为人生的文学
陈平原在谈到近代小说转型的问题时说:“小说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进而有益于社会进步,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独辟蹊径地提倡“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启蒙——‘改良群治’”(注: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从而使小说由文学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我们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中不难看到这种潜在的文本。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研究会小说家们是继承着传统中国文化“载道”的一面,他们似乎要在小说中解决一切问题,“晚清新小说依靠政治助力,以日本政治小说为范本;‘为人生’小说以哲学、理性思考开道”(注:杨洪承:《文学研究会文化历史形态的还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形态的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小说创作如何才能达到“为人生”的目的呢?小说创作如何才能充当“为人生的艺术”?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仔细思考过的问题,因此其解答也较为全面,他们认为要实现文学为人生,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文学作品的水准;第二方面是作家的自身素质;第三方面是读者的接受程度。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他们强调小说的“真”的品格、美的气质与智慧的内涵,所谓真是指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创造的真实”(注:佩弦:《文艺的真实性》,《小说月报》1924年第1号。),而美则是艺术的品性,至于智慧则是“理性的评度”(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这三者应该是“不能彼此分离”(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没有美的气质,那么作品就“必定成为一种哲学或科学底记载”;只有智慧的内容,那么小说“便成为劝善文”(注: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四依》,《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了。从作家自身的素质来讲,要为人生就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文学的修养——叫自我底精神与宇宙同化,与万物表同情。第二要了解人生意义——知道人生价值所在,随时都可发挥。第三要留心社会各方面底考察,揭出他底真相。第四要直接慎重于文章修饰底工夫,合于美底方式”(注:朱自清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针对读者的接受程度,他们强调了“为民众”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文学里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民众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换句话说,专以民众的赏鉴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却万万不可!”(注:沈雁冰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显然,文学研究会小说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小说艺术与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应把握健康的方向,造出“优美的文学作品”(注:沈雁冰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另一方面,在欣赏习惯上又必须照顾民众的心理与习惯,采用机智的、潜移默化的方法“因势利导”(注:叶圣陶:《侮辱人们的人》,《时事新报》1921年6月20日。),提高民众的审美能力。
沈雁冰联系创作实际,进一步探讨了小说如何为人生的问题。他在评论1921年三个月小说创作的现状时,指出了创作内容偏狭,恋爱题材写得太多的毛病,他说那段时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注: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第8号。)。他在一年后又指出:“有人说,中国近来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的。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样写别的?”(注:沈雁冰:《文学与人生》,《新文艺评论》,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所以他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主张作家到民间去,并且推崇鲁迅描写农民的小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像《风波》那样“把农民生活的全体做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几乎“寻不出”。1922年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批反映劳动民众的人生疾苦的佳构,应该说是与沈雁冰的结合创作实践的理论提倡有关的。
叶绍钧的农村题材小说《饭》、《悲哀的重载》等,从侧面反映出农村经济的崩溃过程。王任叔在抒写青年苦闷心理的同时,也写了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变动的作品,收于小说集《破屋》中。徐玉诺的小说《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等颇有影响的小说,被誉为“替社会鸣不平”和“为平民叫苦的人”。王思玷的包括《偏枯》在内的三篇小说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沈雁冰在《导言》中指出:“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个不知道大祸已在门边的小儿女的天真。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流露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跃出来似的。”(注: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年版。)孙俍工的《隔绝的世界》写了茅屋中穷人的悲哀和公馆里阔人的欢乐,作家抓住了除夕守岁这个富有中国传统习俗特点的时间,集中地穿插描写了两个哀乐不通、相互隔绝的世界,那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天地相隔的世界。潘垂统的《讨债》也采用对比手法,描写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冒着纷飞的大雪,向一个暴发的富绅讨还陈债的经历。小说写得富于诗意美,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写景造势方面,都明显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是现代版的“悯贫伤穷”故事。
情感——沟通文学与世界的桥梁
传统中国文化并非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秩序、规范、群体、理性等儒家文化特有的规则与理念经常受到来自其它文化的强劲冲击,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情感主义写作并非是无根的植物,它的根须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张扬个性旗帜,尊崇感性人生,对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加丝毫掩饰,这种新鲜活泼的生存方式的确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的奉“奴隶性人格”为处世圭臬的传统中国人瞠目结舌。与创造社小说家大胆地、“写真”式地、“伪恶”式地在五四文坛上刮起“狂飙”式的性灵文学风暴不同的是,文学研究会小说的情感写作多以委婉曲折的笔致传达人生感慨,走的是温和式抒情的路子。情感是文学研究会论述小说艺术时的重要范畴,也是他们小说创作的核心观念。
耿济之曾经说过,“文学决不是仅描写生活的真实,即为止境,应当多所别择,把文学家的情感和理想寓在里面,才能对于社会和人生发生影响”(注:《〈前夜〉序》,《前夜》,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周作人认为,“文学应当通过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接触”(注:《新文学的要求》,《晨报》1920年1月8日。);郑振铎认为,“文学以真挚的情感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时事新报》1922年5月11日。),他们重视情感因素,认为只有依靠情感的手段才能实现文学与世界的沟通,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时事新报》1922年5月11日。)。显然,在文学研究会这里,情感充当着联系文学与人生真实世界的桥梁。他们重视情感因素,“必有真挚的热情,才能产生美丽而感人的文艺”(注:西译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要创造“饱蓄热情的酸泪的文学”(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为人生”的小说艺术才不会堕入因理性因素过重而造成的枯涩偏瘦状态,从而显露生机,真正实现与世界的自然流畅的对话。
情感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中充当着重要的“意义系统”。王统照的小说多用象征手法(注: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这与他深厚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修养有关。王统照在创作小说的前后时期,都创作过诗歌,象征手法之于他的小说创作,应该是一种内化的因素,而非外在的强行契入。以他的名篇《沉思》为例,女模特儿琼逸为了助成画家韩叔云的艺术活动,应允做了他的裸体模特,结果是恋人闻讯赶来愤怒地将她带走,后来又抛弃了她。琼逸是作家的象征,艺术家借助于她所进行的艺术活动就是“美的实现”的过程,但是,美的东西总是受到世俗和强权的干涉。琼逸的困惑与感伤其实也是作家本人对于美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产生的痛苦与感伤。情感在这篇个人低语式小说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诗意氛围。
黄庐隐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将五四时期所特具的时代感伤与个人青春期的情感格调表现得浓烈而深沉。《海滨故人》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她个人生活的印记。她将那种强烈的人生感触融入到叙述与写景之中,将爱情描写与人生思索相结合,达到了情感书写的时代高度。这种情感书写在五四时期是很能得到青年读者的赞扬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小说大量采用日记、书信等“独语式”文体,便于直接书写主人公的内心苦闷与哀怨。作家个人的经历与人生感触也大量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由此可见,“忏悔录”、“自叙传”、“血泪书”并非创造社小说的专利,而是五四时期的创作主潮,只不过在文学研究会这里,在表述上较为婉润深沉。在情感上较为温和平静。
冰心的《疯人笔记》采用象征和意识流相交错的手法,塑造了两个象征性人物形象:“白的他”和“黑的他”。两个“他”分别象征着生与死,爱与恨。这两个象征性人物既相对立又相关联。两个“他”直接表现了作家思悟人生时的迷乱心绪。小说采用意识流跳跃的结构方式,全篇没有任何情节结构线索,作家的笔只是沿着疯人颠乱的思绪流下去,“我”、“黑的他”、“白的他”不断闪回,交错,从而结构起全篇小说的骨架,并借此传达了作家的惶惑不安的主观心理特征。庐隐的《思潮》也采用意识流手法,依寻主人公视觉和意识流动的落点,一个断片一个断片地翻演出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想象,从而表现出作家繁复不定的心理情感特征。
主观性写实
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将“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视为小说创作的合理形式,而没有或者说无意于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别,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注:沈雁冰语,《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他们之所以视二者为一物,原因在于这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要求对现实作“客观”再现。这种由于注重“客观”再现的“共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差异”的认识方法,本身就说明了文学研究会小说家的过于“主观”的一面,这样,在他们的小说中出现主观性写实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就注重真实、客观,这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背景有关。在老庄诗学主张中,“真”以质朴为本,“善”以质朴为准,“美”也以质朴为度。质朴(也就是真实)是老子诗学的绝大命题,真居于善和美之上,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善为真所决定,美由真所体现,善与美都统一于真。E.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说:“传统并不是自己改变的。它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某些传统变迁是内在的,就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注:E.希尔斯:《论传统》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文学研究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然,讲求客观性的品格,又根据时代的要求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同时也是“传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纯粹自然主义写作的主体性变异,从而开启了主观性写实的道路。
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用一种固定的人生观念去回答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问题,在一连串的人生疑问中实现作家对于人生、社会、宇宙的主观性思索。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作家的主观性思索距离真实的自然原生态的现实到底有多远。这是文学研究会小说的创作特点之一,在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作家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昭示了文学研究会小说主观性写实的方向。
冰心的“全体作品,处处都可以看出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来”(注:王统照:《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小说月报》1922年第9号。)。“爱”对于冰心来说是一把万能钥匙,她用“爱”的理想回答了“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最后的使者》显示了她对于人生究竟的主观性思索。小说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一个诗人借助神的力量负担起拯救绝望的人类的使命。用“爱”来拯救人类是冰心对于人生问题的主观性解答。在她眼里,“爱”的力量是无穷的:《爱的实现》中的作家从一对小姐弟的手足之爱中汲取了创造的灵感;《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的悲观烦闷的青年,在孩子纯真的童心召唤下得到了真实的人生启示:《最后的安息》中的小童养媳翠儿也在惠姑的爱中感到了“一线灵光,冲开她心中的黑暗”,从而获得了最后的安息;《悟》中的烦闷青年星如也是在自然、母爱的启示下坚定了生存的信念的;《超人》的主人公何彬也是由“爱”意识到了“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互相遗弃的”,从而改变了人生态度。可以说,“爱”是冰心主观性写实小说的核心语吗,现实中的一切都在“爱”的神光下具备了意义。
王统照小说的写实主观性则表现在对于“美”的书写上,“美”在他的小说中充当着核心语码的作用(注:王统照:《长芝的生平与作品》,《王统照文集》第5卷。)。他的小说中的美是人生一切具有美好性质事物的升华,比起冰心的爱更为复杂,也带有几分神秘色彩。他用小说的形式去阐释他的人生美学观念,如《微笑》描写青年囚犯阿根,他本来是一个顽劣的窃贼,后来在狱中看到一个女囚对他投来的微笑,从此获得了感悟,出狱后居然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而这位女囚从前也是极其暴烈的。后来受了一个教会女医生的感化,性情发生转变,“便对所有的人,与一切的云霞、树木、花草,以及枝头的小鸟,都向他们常常地微笑”。王统照在这篇小说中有意识地把一个微笑升华到特定的美的高度,并使它产生了神奇的作用,依凭着“美”实现着他的人生主张。应该说,这种写作是典型的主观性现实主义写作方式。
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小说用曲折的故事装点他那带有佛家超然意味的人生观念,他的人生写实小说自然带有宗教色彩。《命命鸟》写缅甸艺人的女儿敏明与富家子弟加陵相爱,受到双方家长的反对,敏明圆梦窥破红尘,与加陵双双携手投湖自尽。在小说中,作者宣扬了一种“以不争为争”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哲学的精华,也是佛家弟子的处世哲学。这种人生态度确实出乎一般人之意料,敏明既没有以死殉情的惨烈,也没有现代女性奋起反抗的坚毅果敢,或者像大多数女子一样忍辱负重,她只着意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带着超脱的精神坦然走向了死亡。《商人妇》中惜官为丈夫所遗弃,后来又从新加坡被拐卖到印度,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却又始终能够以平静的心态去接受命运的侮辱,总能在生活的每一处找到安憩之地。在她眼里,“人间的一切事情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表现得相当平静,她说:“我就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许地山的“不争”观念,毫无疑问是他对于现实人生的一种主观解答方式,儒家文化中的“恕人”观念与此庶几近之。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在主观性写作上,当其面对传统文化资源时,是兼容儒墨道法,采取多元文化立场的。
叶绍钧也从生活中抽象出“美”与“爱”的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反复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他曾说:“近代的文艺里,俄国的最显出他们民众的特性。他们困苦于暴虐的政治,艰难的生活,阴寒的天气,却转为艰苦卓绝希求光明,对于他人的同情更深,对于自己的克厉更严,这就是以‘爱’为精魂的人道主义。”(注:叶圣陶:《文艺谈.二十二》,《晨报》副刊1921年5月8日。)悯农题材是五四时期的主要题材之一,显然,这种题材的小说创作之于文学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都只能是观念的产物,所以在创作中表现出浓厚的主观色彩就无足为奇了。《晓行》、《悲哀的重载》、《火灾》、《饭》等都是主观性写实作品,直到《潘先生在难中》的出现,才表明作者的现实主义写作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沈雁冰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注:沈雁冰:《王鲁彦论》,《小说月报》1928年第1号。)杨义也认为叶绍钧的小说到《潘先生在难中》为止,“完成了两项内在的变化,首先它摒弃了‘美’和‘爱’的虚幻性,坚持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使现实主义归于沉实;其次它在描写熟悉的生活时,把它与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使现实主义趋于开阔。这种开阔而坚实的现实主义,是为人生的文学高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关于小说创作,我总是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生命感受在小说文本中始终具备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一部小说的评价,不唯不能以是否脱离了主观性来评判其是否成熟,而且更应该以是否融入了作者深沉的主观感受作为评判作品成败与否的重要标尺。正如苏珊,朗格所说:“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们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现实存在)。”(注: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虽然带着历史的无可避免的幼稚,但是这种并不成熟的技巧与并不深刻的思想却因为其无可遮蔽的真诚而唤发出真正的魅力,那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有的魅力。
小说纯粹化:文学的自律
文学研究会小说在打出“为人生”的带有工具论色彩的旗帜时,也注重小说“艺术化”,也就是“纯粹化”的努力。这二者统一于为人生的目的,一般来说,在他们论作家、作品时,着眼于文学为人生的外在化问题,即要求小说与人生相接近;而在谈论小说艺术时,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切入的,在这里,小说的“为人生”内化为使小说自身完美的属性。注重文学的纯粹化,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一脉主流。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即有“文以载道”的工具论传统,也有“歌以咏志”式的纯粹个人化书写传统。某种意义上,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的纯粹化趋向正是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纯粹化写作的传统。
王统照是通过哲理与诗化相交织的方式来完成其小说的纯粹化建构的。他认为:“带有诗意的哲学思想,与富有哲理的美好的诗,那是人类精神之最高结晶体。”(注:王统照:《一叶》,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7页。)小说重在“写意”,“曾想把思想寄托在作品里面”(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种“寄托”其实就是象征,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如出一辙。《雪后》写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在河边用雪筑了一座小楼,他对自己的杰作颇感满意,但是,这座雪楼却被夜来的军人的马蹄践成污泥。象征手法的采用,保证了作者与现实的距离,也保证了小说叙事的纯粹化。《湖畔儿语》写一个失业的铁匠,无以为生,只好让后妻出卖肉体,为了避人耳目,他把孩子赶走,让他蓬头赤足,游荡于苇塘边,小说的主题是很“宏大”的,它提出了劳动者的家庭生计问题、儿童命运问题、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但是小说的叙事却采取了一种平静的、诗化的、纯粹的方式,这也是整个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纯粹化叙事的共性,体现了某种文学自律精神。
许地山小说的纯粹化是通过其浪漫主义式的写实来完成的。他是南方人,除了在燕京大学学习任教和在欧美留学的一段时间以外,他主要在南方生活,足迹遍及于台闽粤及东南亚、南亚等地。在中国的南方,从《楚辞》开始,就充满着艺术化的绚丽多姿的想象,南方的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注: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与正统的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传统富于浪漫的想象,充满了异域色彩,许地山的小说中多南国风物,也多南传佛教色彩。以此为背景的许地山小说,自然具备了纯粹化叙事的文化基础。《命命鸟》中佛教学校的学生随和尚去乞食,温饱人家闲居时嚼食槟榔,豪门世族鼓励子弟出家为和尚,为父母积福,为来生修业,蛊师用符咒拆散恩爱男女的姻缘等等,都是典型的小乘佛教的风俗习惯;《商人妇》中佛教徒把对婆罗门人的施舍看作污点,妇人在丈夫死后若干天后才能允许重嫁,都带有异域色彩;《玉官》的女主人公成了“圣经女人”以后,依然还孝敬祖宗,用《易经》和《圣经》一同驱鬼,所谓“闭上眼睛求上帝,睁开眼睛求祖宗”,也反映了一个基督女信徒的特殊宗教心理,等等。这些特殊背景的设置,被人评为“伟大的人的文学佳果”(注:慕之:《换巢鸾凤.附记》,《小说月报》1921年第5号。)。此外,如《缀网劳蛛》中的土华岛上的风景;《黄昏后》中的夕照疏林;《春桃》中的窗下的晚香玉等等,都为纯粹化叙事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纯粹化并非一种为趣味而趣味的“恶趣”,他们自觉地与娱乐文学相区别,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注: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郑振铎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347页。)。这就体现了文学研究会小说趣味的纯正与文学自律性的自觉。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研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传统文化大河下游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在汲取传统资源时呈现出了杂取多家的交融性特征,其中的主流特征就是其坚定的“为人生的艺术”追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戏剧是冲突的模式,小说是回忆的模式”,当下的小说创作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时,毫无疑问,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会为它们提供若干有价值的资源。
标签:文学研究会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小说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缀网劳蛛论文; 命命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