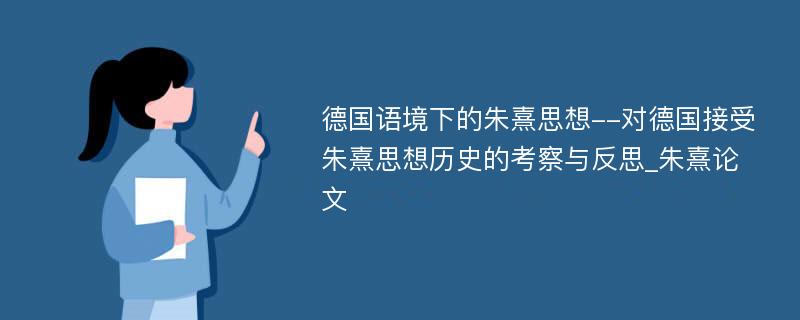
德文语境中的朱熹思想——对朱熹思想之德语接受史的考察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德文论文,德语论文,思想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3)03-0098-13
一、引言
自16世纪以降,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们的翻译,中国古代典籍开始持续地输入西方,成为与“西学东渐”方向相反的另一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态势。在此进程中,德语世界的学者们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而且许多译本都系中文典籍在西方世界的第一种译本,进而为西方其他语言的转译工作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有持久的翻译活动作支撑,德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兴趣一直比较浓厚,而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也展现了一种较为丰富的状态。
众所周知,德国学者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在莱布尼茨与黑格尔那里构成了两个极端:莱布尼茨极为推崇中国古典思想,认为它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哲学;黑格尔则从其对孔子思想意义的判断出发,断言中国没有哲学。然而,这两种极端并不能借以直接断定德语学者对中国思想的基本看法,多数对此问题有所表态的德国学者大都持一种中间立场,即一方面不再像莱布尼茨那样如此推崇中国思想,另一方面也大都肯定中文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种天生的哲学语言。后一种肯定,一方面来自德国学者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在浩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民族独立形成了本己的哲学思想①;一方面也可以从《道德经》在德文世界的译本数量得到说明,迄今为止,《道德经》的德译本已达114种②。
《道德经》在德语世界中的持久热度多少反映了一般德语读者对中国古典思想内在分层的判断和定位:先秦道家文本乃是或者说接近于真正的哲学,先秦儒家文本离哲学语境则有相当距离。然而,对于中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宋明理学,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于朱熹思想,德语世界是如何看待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毫无疑问,哲学文本的异域语言翻译史与此思想的异域接受史有最直接的关联。因而,我们若要考察朱熹思想在德语世界中的接受史,莫若首先从德语世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活动入手,然后再依据一些重要文本来检讨其得失。
二、对朱熹思想之德语译研工作的考察
陈荣捷先生在其卓越的专题研究《欧美之朱子学》中曾认为,西方世界对朱熹思想的最早译介是稗治文(E.C.Bridgeman)在1849年的摘译,此人“采取朱子全书关于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若干语,译成英文,虽仅七页,而从朱子直接材料看其思想,于焉开始。故欧美翻译朱子本人资料,以此为最早,而欧美研究朱子之专著,亦以此为最早”③。
然而这一看法显然有误,因为德国学者K.F.Neumann④1837年就已在著名的《历史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uü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上发表了长达88页的对朱熹理气思想的德文译介成果⑤。译者对朱熹思想的整体格局有相当了解,而且私人藏有一套《御纂朱子全书》⑥。其译文系对《御纂朱子全书》第四十九卷即“理气一”的翻译,分别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五行、时令”进行了完整翻译。在文本的导论部分(共32页),译者着眼于“道统传续”,首先对朱熹之前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进行了一番梳理,然后对承接道统的朱熹思想作了评介,其对朱熹思想的最终定位是:“朱熹乃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述是他的时代与他的民族之信念与知识的集大成者”。就目前资料来看,这应是西方对朱子文本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译介成果(更早之前的耶稣会传教士如龙华民等人对中国理学思想所进行的有极大缺陷的编译成果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译者本人在导论中也指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这一失误,但陈荣捷的专题研究仍然注意到了一些德语学者对朱熹思想的译介贡献:1876年,Georg von der Gabelentz⑦译周子《太极图说》并朱子注;1879年,WilhelmGrube⑧选译朱子关于理气若干条,翌年又从《性理精义》译周子《通书》与朱子注释⑨。1953年,Olaf Gra⑩耗费多年心血方得完成的《近思录》德文译本面世(11),此系该书在西方世界的第一种译本,且由于该书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故有深远意义。陈荣捷先生对此译本的评价是:“书凡三篇,共四册。第一篇为概论。第二编上下册为近思录与叶采近思录集解之翻译。第三篇为翻译之附注。在概论中详言近思录与其思想在理学上之位置。又与佛教、道教,与西方思想,尤其是斯宾诺莎相比较,实为朱子研究一大进步。”(12)Graf神父又再接再厉,于1970年出版德文研究巨著《道与仁:中国宋代一元论中的实然与应然》(13),得到陈荣捷的好评。陈称作者为“当代西方综述朱子之最丰富者”,并评其书:“以《近思录》为出发点,泛论宋代理学而以朱子为中心,所论太极、理气、道、天、命、乾坤、仁、四德、中和、敬、人道、格物、心意、天地之心,评佛等等,虽乏完整,而言之成理”。此外,陈荣捷也注意到了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两部用德语写就的中国哲学史,分别是E.V.Zenker的《中国哲学史》(14)与Alfred Forke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5)(此书视宋代哲学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起点,故研究范围是从宋代到民国),陈对后者论朱子部分的评价是:“分论理气太极、天与帝、天地阴阳、鬼神魂魄、人物与性、道、朱陆之辨,西方学者对于朱子之嘉许,范围周广。所引朱子之语,亦算精到。盖Forke之中国学问研究之造就,可比Bruce(16)而实过之”。除此之外,并无多论。关于这两部德文中国哲学史,我们将在后文中予以探讨。
陈先生的研究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对此后数十年德语世界的最新进展当然无可涉及,而且对此前一些相关研究也多有遗漏,故下文中我将尽可能地予以补充,以便为更进一步的“德语朱熹思想研究”乃至更广范围的“德语中国哲学研究”作一文献学的准备。
在原典译注方面,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当代德国汉学家、波鸿大学教授Wolfgang Ommerborn(欧阳师)重新译注了《近思录》,并于2008年出版,这是该书在德文世界的第二个译本(17)。此译本通过大量评注和阐释,试图在德语世界中树立这样一种观照:宋代新儒家的这一文献选辑乃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之一(18)。
在研究著作方面:德国汉学家Wilhelm Schott曾在1886年出版《对中国博学之士朱熹的评论》(19);1985年,JuttaVisarius出版专著《朱熹形而上学研究》(20);1987年,Wolfgang Ommerborn出版专著《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当前对朱熹及其理气论的评价》(21),此系其在波鸿大学的博士论文;同年,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代表作《朱子学与阳明学》被Monika Ueberhoer(于佩和)教授译为德文出版(22),1999年,Hae-suk Choi出版比较哲学领域的研究专著《斯宾诺莎与朱熹:斯宾诺莎伦理学与朱熹新儒家学说中的作为人之存在根据的绝对自然》(23);2001年,中国台湾学者Lin Wei-chieh(林维杰)在法兰克福出版其博士论文《理解与道德实践:朱熹儒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之间的比较》(24);2003年,Hans van Ess(叶翰)出版研究专著《从程颐到朱熹:胡氏家族传统中的正道论》(25),认为朱熹思想吸收了胡宏和张栻的许多思想,其思想体系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湖湘学派,但较之湖湘学派,朱熹思想有更为强大的、兼收并蓄的纯粹学术精神,也因此而得以成功。此书原系其1999年在汉堡大学提交的教授资格论文;2006年,Wolfgang Ommerborn出版新作《戴震对孟子的接受与他对朱熹学派的批判》(26),此研究分别从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予以展开;2009年,Thomas Tabery博士出版了研究颜习斋哲学的专著《自身教化与世界构形:颜元的实践论哲学》(27),此书对朱熹的理气思想作了较为详尽而深入的专题研究,颇为可观。
在研究论文方面,德国著名翻译家Franz Kuhn在其走向中国文学翻译之路前,曾在1917年发表过关于朱熹的学术论文:《中国皇帝关于朱熹的九条诫命》(28);Olaf Graf在1948年发表了比较哲学论文《朱熹与斯宾诺莎》(29);Michael Lackner对同样的问题予以关注,发表重要论文《朱熹是黑格尔之前的“黑格尔”么?在中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理解难题》(30);1963年,Victoria Contag发表论文《对古人朱熹的认识》(31);Michael Friedrich在1989年发表论文《传统与直觉:朱熹学派的渊源史》(32);莱比锡大学教授Ralf Moritz在1997年发表重要论文《概念与历史:论朱熹》(33),由此文可清楚地看到,“理”在朱熹思想中乃是“一体化的整体性规范”。较之以上学者,在此领域用力最勤者当属Wolfgang Ommerborn,他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朱熹学说中对人的哲学考察》、《新儒家朱熹的生平与思想》、《朱熹对孟子仁政理论的接受和这种理论的哲学根基》、《评叶翰的〈从程颐到朱熹:胡氏家族传统中的正道论〉》等(34)。
在哲学史专著方面,德语学界除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三部中国哲学史——Heinrich Hackmann的《中国哲学》(35)、E.V.Zenker的《中国哲学史》与Alfred Forke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外,一直没有太大进展。但有必要提及的是,2005年去世的德国著名汉学家Wolfgang Bauer(鲍吾刚)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全新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中国哲学史:儒家、道家、佛教》(36)。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哲学史著作,其中用20页篇幅探讨了朱熹哲学,分为“理、人性与爱、物与心、新的经典著作、朱熹与伟大的综合”五个环节分别展开。鲍吾刚认为,北宋道学的基本特性在于对“宇宙论”(Kosmologie)的建构和对“存在”(Sein)的重新发现,但又因此出现了两极性倾向(Polarisierungstendenzen),而朱熹的功绩就在于他对此作出了一种“伟大的综合”。
以上我们从译本、研究专著、研究论文、哲学史专著等几个层面考察了近三百年来德语学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研究工作的概况,对其中一些成果我们也作了简要的介绍,但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德语学界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与接受活动,为了更加透彻地观察中国思想在异域语境中的命运,显然还有必要结合一些重要成果来加以重点分析和阐释。
三、对德国汉学之“朱熹理解”的观察与反思
就整体而言,较之英美汉学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德国汉学对朱熹思想的译介和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翻译和研究的丰富度不如英美汉学,翻译的规模和研究成果的数量亦不如英美汉学。德国的华裔学者始终难以被纳入到德国汉学研究群体中来,这或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37);第二,英美汉学的朱熹研究侧重于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方面的考察,德国汉学的朱熹研究则更多地着重于研究哲学问题本身和追问思想自身的意义,这无疑是受到了德国思辨哲学精神的深重影响;第三,对于朱熹思想的哲学意义,英美汉学界由于有华裔学者的强力支撑,不乏厚重作品和深邃洞见,德国汉学界的认识则略显笼统,深入的文本剖析和深邃的义理思辨较为缺乏。然而,伴随着德文译研活动的积累以及研究者语言熟练度和文化亲和度的提升,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我们也更期待着这种转变和积累的升华。
近四百年来,德国学者对朱熹思想的意义和要旨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我们选择几种较具代表性的理解来加以分析和批评。
首先来看莱布尼茨。莱布尼茨(1646-1716)是最早对朱熹思想要旨作出评论的德国学者,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尽管莱布尼茨本人并不通晓汉语,他对朱熹理气思想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传教士的翻译和报道,而且受某些文本的误导(龙华民等传教士在其著述中认为理、气、太极这些范畴在先秦时就已形成),尽管他有所怀疑,但终竟不能确知这些范畴的确切历史信息。但这并不能完全阻绝深邃思想之间的共振,而且就其对朱熹理气思想的理解与评论来看,其中所蕴藏的深邃洞见与精思妙契,委实令人惊叹。
1701年,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ldi,1559-1654)的著名论文出版了法文译本,此即《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Traite sur quelqua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 la Chinois),这是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重要文献之一。1714年10月12日,法国学者尼古拉·德·雷蒙(Nicolas de Remond)致信莱布尼茨说,他已读过龙华民的上述论文,请求莱布尼茨对这篇论文作一评论。1715—1716年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莱布尼茨写出了著名的《论中国自然神学》一文,这是一封未发出的长信,更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且突显了莱布尼茨思想在其后期臻于成熟时的一些重要特性。
出于反对利玛窦融合主义传教方针的考虑,同时也由于没有深入理解中国思想的实质(尽管利玛窦本人对理学思想的理解也颇为肤浅(38),但龙华民则更为不堪,因为他根本没有弄清先秦儒家和新儒家的区别),龙华民在其论文中认为理学思想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朱熹反复强调的“理气不分”等主张成为其主要论证依据。最终,在他看来,“理”乃意指一种“原初物质”。
莱布尼茨在其论文中对龙华民的上述立场和立论进行了批判。
首先,关于思想材料问题,莱布尼茨审慎地指出,为了深入探讨,“最好是将经书全部翻译出来,但是既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只可做暂时性的判断”,由于龙文引用理学典籍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其内容,故“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他伪造任何东西。我相信这些材料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权威性的学说,应是可靠的,而且不会使人视为恭维之辞;所以我要为它作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也会运用同意龙华民神父想法的利安当神父所加上去的话”(39)。
其次,莱布尼茨指出,对理气思想意义的争议焦点在于: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龙华民给出了否定答案,而莱布尼茨却说:“我在熟思后,认为他们承认过——虽然或者没有承认精神实体是与物质分别存在的。对于受造的精神体来说,这并无害处。连我本身也倾向于‘天使有肉身’的信念——而这也是数位古代教父们的说法。我也认为理性之灵不能完全脱离物质。……要断定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我们尤其应该研究他们的‘理’或秩序。‘理’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与根据;而且——我相信——‘理’近乎我们的至高神观。认‘理’为纯被动性的、生硬而毫无人情的、和物质一样的,是不对的。”
最后,通过对有限的文本材料和思想资料的考察,莱布尼茨看出了“理”这个词的不同含义:“由此我断定,这个词必定有双重含义。有时用其严格含义,指至高至上的存在,有时则指任何一种精神”,理的双重含义因而可分为:作为本原存在的理和寓于个别事物之中并决定其性质的理。前者乃是“源始原则”(Urprinzip),它是“第一推动者和万物的原因,并且我相信,它相应于我们说的神圣(Gottheit)”,“在某种意义上,理乃是事物的精纯本质、强力、力量以及真正本性,因为他(指朱熹)已经明确地区分了气中之理和气中之物”。因而这里所谓的理,“不是指精神性的源始实质,而是指一般的精神性的实质或者说隐德莱希,也就是那种东西,与诸灵魂一样,它秉有主动性、感知或有秩序的活动”(nicht die geistige Ursubstanz gemeint,sondern allgemein die geistige Substanz oder die Entelechie,also dasjenige,was wie dieSeelen mit Aktivitaet und Wahrnehmung oder geordneter Taetigkeit begabt ist)(40)。
隐德莱希,希腊文entelecheia,字面意为“在完成之中;在完善中居有”,亚里士多德以此意指“实际造作之力”、“实现之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境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思想中,此概念都同样具有二重性意义:整体(存在自身)的实现与个体(存在物)的实现。存在之整体的实现征用着个体之实现,个体的实现又参赞着整体的实现活动。也正是基于这种宏阔而深邃的思辨视野(41),莱布尼茨不可思议地把握住了让其本己思想与东方思想发生深邃共振的关键契机:一方面,莱布尼茨指出,就个体而言,“理”是物之为物的具体之理,是个体意义上的隐德莱希(实现之力),故其“秉有主动性、感知或有秩序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整体而言,莱布尼茨认为,作为“源始原则”的“理”并非变化之主体,而是源始的隐德莱希或者说实质性的行动之力(42)。
莱布尼茨的这种解读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期望。甚至,当我们回顾本己思想传统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理气之辨对于“精通中文”的中国学者来说也仍然是一个至为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多少晓悟到,思想之理解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语言之掌握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解朱熹理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洞见到理之二重性以及如何阐明这种二重性,但对此的深入探讨和论证显然并不能在此进行,因为此工作必须首先在我们本土思想视野和道说方式中予以充分展开(43)。
其次,我们来看福尔克(Alfred Forke)的相关论述。
尽管有其本己限度,但福尔克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三卷本德语中国哲学史巨著——分别为《古代中国哲学史》、《中古中国哲学史》、《近现代中国哲学史》——迄今可能仍然无法取代,因而又得到再版机会。福尔克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框架和观察视野与欧美很多学者都大相径庭,需要专门加以深入探讨。其最为特别之处体现在他把宋代哲学当作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起点。
欧洲学者对中国思想内在格局的理解长期存在一种偏见,即重视先秦思想,而轻视宋明理学。这种偏见导致的后果在上世纪初期的两部德语中国哲学史中有直接体现。Heinrich Hackmann在其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中用220页的篇幅来探讨古代哲学(先秦时期),对中古时期哲学(两汉至唐)用了90页篇幅,对于宋代及其后哲学则只用了65页。同样地,Zenker在其《中国哲学史》中用了近340页篇幅来阐释古代先秦哲学,对中古哲学的探讨用了200页,对于宋代以降的哲学则只分配了130页的篇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尔克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仅正文部分就达到了650页篇幅,远远超越了其他学者的阐释篇幅。在此书中福尔克用近300页来阐释宋代哲学,又用150页来探讨明代哲学,因而仅从文本篇幅和解释规模来看就与一般欧美学者的中国哲学史阐释格局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福尔克对宋代以来的中国哲学有极高评价:
中国和日本的哲学史家们认为,宋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是势均力敌的,所以他们也相应地对宋代以来的哲学进行同样详尽的探讨。但在我看来,宋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不仅是与古代中国哲学同样重要的,甚至还更为重要。只是在宋代以来,中国哲学才得到了完全的发展。推崇古代哲学的那些先前的儒家学者甚至现代的哲学家们的看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代中国哲学诚然构造了根基,但却并未构成中国哲学之终极。先秦时代是智慧的时代,宋代和明代则是真正的哲学之时代。古代圣贤对智慧的把握通常是直觉性的,很少予以论证。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一些基本概念,他们并没有从中引出更进一步的推论。只是从宋代以来,这些基本概念才真正得到了哲学性的思考,最高的难题被把握住了,独创性的解答被发现了。……大多数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们把宋代视作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巅峰时期,我则把它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全盛时代,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随着当前欧洲文化的渗透,中国哲学还会迎来第三次巅峰时期。(44)
精通中文的福尔克在研究宋代哲学时主要依据的文本是《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理学宗传》以及《宋元学案》等。他之所以如此高调地评价宋代哲学,根本地又是因为他对朱熹哲学有极高评价。
从文本来看,由于受到黄宗羲和王船山之理学观或明或暗的影响,福尔克对朱熹理气思想的理解并未推进到足够的深度,甚至还不如莱布尼茨的洞见深度。尽管如此,福尔克仍然看到了朱熹哲学中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
在福尔克看来,“朱熹不只是宋代最重要的哲学家,更根本地,他乃是最伟大的中国哲学家,他比孔子、老子或王阳明都要更加伟大”。这种观点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吃惊,福尔克为此进行了下述辩护:孔子是圣人,却并非伟大的哲学家。他传承了古老的道德原理并将其带入经典形式中,但这并没有开创新的东西。他所从事的只是实践性的生命哲学。最重要的哲学领域,如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等,对于孔子而言是陌生的,却是朱熹所精擅的。就创造性精神而言,老子胜于朱熹,但老子更多是诗人而非哲学家。他以思想作诗,令人有同感,但却不可论证。老子诚然是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若干基本概念,但他忽略了伦理学和其他学术。至于王阳明,尽管很多人认为他超越了朱熹,但他的视野与朱熹思想的纵贯疆域相比显得相当狭隘。令朱熹殚精竭虑为之求索的很多问题都还是先秦思想家所不知晓的。朱熹之伟大在于,他会尝试去对他的主张加以论证,他会以极大的审慎去衡量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在这方面,尽管有一些哲学家在独创性上超过了朱熹,但他们却无能于论证,而我们对一个哲学家的基本要求却是:他要能够说服我们,使我们确信其思想的真理性。获取原创性的想法并非那么困难,倘若人们使自己免除于对这些想法的合理性加以论证的辛苦,或使自己满足于似是而非的论证的话。惟有朱熹,他以他那批判性的思想方法而规避了不可靠的立论(45)。
由此,福尔克对朱熹的思想史意义作出了下述断言:朱熹掌握了他的时代的全部知识,因此堪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或者莱布尼茨相提并论。在最为切近的意义上,他更像是阿奎那。两个人都受制于传统并深谙传统,但也都能借助异域思想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但这两个人的哲学工作重心都放在了阐释和评注上而并未倾力于构建自己的哲学陈述。尽管有种种时代条件之限制,但朱熹仍是所有中国思想家中最具哲学品性的思想家,他最为接近于西方所理解的哲学家。他的精神涵括了他全部的生活世界,对于其中智慧,他并不仅以诗意箴言来予以道说,而且也对他所要认知的一切加以真正的哲学思辨(46)。
以阿奎那和朱熹来加以比对,这是中外一些学者的习见,福尔克也概莫能外。然而这种比对多是就外在效应和粗略形态而言的,就思想对话之基本问题(存在之二重性与理之二重性问题)而言,与朱熹理气思想最能遥契交接的并非在存在论问题上坚持“类比说”(Analogie)的阿奎那,而是洞察到存在之“单义性”(Univozitaet)的更为深邃精锐的邓·司各脱(47)。以此而论,福尔克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更多的也只是在思想外在层面上运行,缺乏足够的穿透力和思辨力。不仅如此,他对孔子和老子的评价也都显示了他的理解限度,当然对此我们也不必苛求。从整体来看,福尔克对朱熹思想的高度评价植根于他的这样一种判断:朱熹是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学品性的思想家。倘若我们能免除于视其为“欧洲中心主义”这样的诛心之论,倘若我们能从其尚不充分的表述中看到其洞察的闪光点,福尔克的这种观照就仍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少比起那些言必称先秦的哲学史观要更具警醒之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德国汉学界中最具野心的尝试之一”——葛拉福神父(Olaf Graf)的理学研究巨著《道与仁:中国宋代一元论中的实然与应然》。在论者看来,这种野心主要体现在:不仅正视中国哲学的自主性,而且也试图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两个巨大传统平等地对待(48)。葛拉福的这部著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首先探讨宋代道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问题,然后对新儒学的定位问题进行纵贯分析和对比。由书名可知,葛拉福将宋代道学看作是一元论哲学,更确切地说,是“一元论的同一性哲学”(49)。具体到朱熹哲学,葛拉福明确反对惯常的视朱熹为二元论者的看法:理与气并非形式与质料的关系,理与气之间的差异并不足以定位于二元论,因为其基调乃是同一性,或者说差异着的同一性。但葛拉福并未真正揭示其中要害,甚至当他进而在第二部分展开朱熹与阿奎那的思想类比时(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他的主要着力点),隐藏于其哲学立论中的脆弱性就得到了暴露。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对朱熹思想的一元论定位,但阿奎那的存在论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元论思想,也因而恰恰不适宜于与朱熹相类比;或者如论者马恺之所指出的那样,葛拉福“在比较一元论者朱熹与协调一元论(Monismus)和二元论(Dualismus)的阿奎那时,思想上的收获是相当模糊的:他不进行真正的分析,而仅是给出一种‘氛围’”(50)。
尽管有许多重大的结构性失误,但葛拉福对朱熹理气思想的解读和阐释却仍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他多少已经看到,理气问题之实质就是理之二重性问题;这种二重性固然运作于差异中,但这种差异性也只有在本源的同一性中才是可能的。然而这些值得凝视的闪光点却在其过于仓促和宏大的比较中被弄得黯淡无光了。
如此,我们就结束了本节的考察工作。若着眼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深度,我们必须承认,除少数研究外,目前所看到的德语世界的朱熹思想研究大都不能令人满意,大都还难以经得起学术性和思想性的严格要求,或者说,都还难以构筑一条连接并提升各种洞见的坚实道路。诚然,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也就意味着有待实现的中西思想对话之前景的超乎想象的辽远与开阔。但仍有必要指出和提醒的是,导致既有现实中这种挫折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理解中国思想的难度,也不仅在于中国思想的非连续性(非道路性)特质,更根本的在于,西方学者对其本己思想即西方思想的理解本就极为艰难。如此就激发了这样一种双重观照:
一方面,对本己传统中的关键思想尚不能有足够理解的人,也极难期待他能真正进入异域传统中的典范思想。对语言的掌握固然非常重要,但思想本身的理解绝非仅仅是一个文字功夫问题,精通异域语言的福尔克与葛拉福所曾遭遇的暗礁也是我们中国学者所曾遭遇、正在遭遇并且将来仍会遭遇的暗礁。与其说我们对异域思想缺乏足够的把握,毋宁说我们对本己传统的思想要素还可能缺乏真正的洞见,因而就还没做好准备去展开一场本质性的对话。另一方面,完全不通中文、只能借助于二手资料的莱布尼茨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深邃洞察又构成了另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示和激励(51)。思想的真正对话是宽容的,这种宽容乃是一种宽阔行走的浩然允诺。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传统之中曾经一再发生过的类似事态:不重训诂考证而专致义理发扬的宋明理学正是崛起于并运作于这种宽容之中,而在今日西方古典学者看来颇不准确的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希腊哲学的德译本,也恰恰是以种种本己化的“走音”才强力支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深邃思辨。最终,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这样一种暗示:限度或许能够成为本质之允诺,对话或许能够激励彼此之成就,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进入思想之中。
注释:
①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此据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报道,见《顾彬:传播中国文学的使命感》,载《京师学人》第25期。
③陈荣捷:《朱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422页。
④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19世纪德国汉学家,慕尼黑大学东方学教授,曾在法国汉学泰斗雷慕沙处学习中文,后于1829-1831年到中国进修中文,收购中国典籍12000册回国。其生平事迹参见Hartmut Walravens,Karl Friedrich Neumann und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etzlaff:zwei deutsche Chinakundige im 19.Jahrhundert,Wiesbaden:Harrassowitz,2001.
⑤Karl Friedrich Neumann,"Die Natur-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der Chinesen.nach dem Werke des chinesischen Weltweisen Tschuhsi",In:Zeitschrift für die historische Theologie.Neue Folge,Stuck 1,Nr.1,Gotha 1837.S.1—88.
⑥按Neumann本人的报道,当时整个欧洲仅有三套《御纂朱子全书》,除其本人家藏一套外,另两套分别为巴黎皇家图书馆和英国亚洲学会所收藏(其中巴黎所藏版本还残缺不全)。参见Karl Friedrich Neumann,"Die Natur-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der Chinesen.nach dem Werke des chinesischen Weltweisen Tschuhsi",S.3.
⑦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19世纪德国汉学家,1876年凭《太极图说》译文和相关研究获博士学位,后任莱比锡大学教授,代表作为《中国文言语法》。
⑧Wilhelm Grube,1856-1908,19世纪德国汉学家,Gabelentz的弟子,曾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兼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女真文字研究的开创者,译有《封神演义》(前四十八回),代表作为《中国文学史》。
⑨Georg von der Gabelentz,Thai-kih-thu des Tschen-tsi Tafel des Urprinzipas mit Tschu-Hi Kommentare(Dresden,1876); Wilhelm Grube,Zur Naturphilosophie der Chinesen,Li khi Vernunft und Materie(1879); Wilhelm Grube,Ein Beitrag zur Kenntniss des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T'ung-Su des Ceutsi,mit C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Sing-li tsing-i(Wien,1880).此据陈荣捷《朱子论集》,陈先生对这三种德文译本的评价是“比较准确”。
⑩Olaf Graf,1900-1976,在荷兰莱顿大学以日本儒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常年在韩国和日本以本笃会教士身份传教。
(11)Olaf Graf,Dschu Hsi,Djin si lu,die Sungkonfuzianische Summa mit dem Kommentar des Ya Tsai(1953)
(12)陈荣捷:《朱子论集》,第430页。
(13)Olaf Graf,Tao und Jen-Sein und Sollen im sungchinesischen Monismus,Wiesbaden 1970.
(14)E.V.Zenker,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Reichenberg 1926.
(15)Alfred Forke,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De Gruyter 1938.
(16)J.Percy Bruce,1861-1934,英国传教士,中文名卜道成,英语世界朱熹哲学的早期译者和系统化研究的开创者,代表作为《朱熹和他的前辈们》(Chu His and His Masters,London,Probsthain,1923)。
(17)Wolfgang Ommerborn(Hg.),Jinsilu-Aufzeichnungen des Nachdenkens uüber Naheliegendes-Texte der Neo-Konfuzianer des 11.Jahrhunderts.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2008.
(18)若我们把观察范围放得略宽一些,则有必要提及下述两种宋代道学重要文献的德文译本:其一,张载《正蒙》的首个德译全本,Michael Friedrich/Michael Lackner/Friedrich Reimann(eds.),Chang Tsai:Zheng Meng,Rechtes Auflichten(aus dem Chinesischen uebertragen und mit Einleitung und Kommentar versehen),Hamburg:Meiner,1996;其二,胡宏《知言》的首个德译全本,Hu Hong,Worte kennen-Zhiyan.uebersetzt von Hans van Ess,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 im Insel Verlag,2009.
(19)Wilhelm Schott,Zur Beurteilung des chinesischen Polyhistors Tschu-hi,Berlin,1886.
(20)Jutta Visarius,Untersuchungen zur Metaphysik des Chu Hsi,Diss.Bonn 1985.
(21)Wolfgang Ommerborn,Geiste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 in der VR China:Die gegenwaertige Bewertung des Zhu Xi und seiner Konzeption von Li und Qi,Bochum 1987.
(22)Kenji Shimada,Die Neo-konfuzianische Philosophie.Die Schulrichtungen Chu Hsis und Wang Yatgmings,uebersetzt von Monika Ueberhoer,Hamburg 1979.
(23)Hae-suk Choi,Spinoza und Chu Hsi:Die absolute Natur als der Grund des menschlichen Seins in der Ethik Spinozas und der neokonfuzianischen Lehre Chu Hsis,Frankfurt am Main 1999.
(24)Lin Wei-chieh,Verstehen und sittliche Praxis: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m Konfuzianismus Zhu Xis und d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Gadamers,Frankfurt am Main 2001.
(25)Hans van Ess,Von Ch'eng I zu Chn Hsi:die Lehre vom rechten Weg in der Ueberlieferung der Familie Hu,Wiesbaden 2003.
(26)Wolfgang Ommerborn,Dai Zhens Rezeption des Mengzi und seine Kritik an der Schule des Zhu Xi.Teil Ⅰ:Philosophische Ueberlegungen; Teil Ⅱ:Politische Ueberlegungen,Bochum 2006.
(27)Thomas Tabery,Selbstkultivierung und Weltgestaltung:Die praxiologische Philosophie des Yan Yuan,Harrassowitz 2009.
(28)Franz Kuhn,"Die neun Gebote des chinesischen Kaisers von Chu Hsi",i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uer Orientalische Sprachen,20(1917),115—141.
(29)Olaf Graf,"Chu Hsi und Spinoza",in: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fuer Philosophie,10(1948),238—242.
(30)Michael Lackner,"War Zhu Xi ein Hegel avant la lettre? Verstaendnisprobleme zwischen China und dem Westen in der Gegenwart",in: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22.1/2(1990),39—53.
(31)Victoria Contag,"Erkenntnisse des alten Chu Hsi",in:Sinologica,7(1963),217—227.
(32)Michael Friedrich,"Tradition und Intuition:Zur Vorgeschichte der Schule von Chu Hsi",in:Schmidt-Glintzer,Helwig(Hg.):Lebenswelt und Weltanschauung der chinesischen Oberschicht im fruehneuzeitlichen China,Stuttgart 1989,1—43.
(33)Ralf Moritz,"Begriff und Geschichte-Ein Beitrag zu Zhu Xi",in:Tradition und Moderne-Religion,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in China,Dortmund 1997,83—98.
(34)Wolfgang Ommerborn,"Die 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 des Menschen in der Lehre des Zhu Xi",in: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11(1988),135—152.
"Leben und Denken des Neo-Konfuzianers Zhu Xi(1130—1200)",in:Das neue China,2(2000),31—33.
"Zhu Xis Rezeption der renzheng-Theorie(Politik der Menschlichkeit)des Menzius und ihrer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in:Archiv fuer Begriffsgeschichte,48(2006),65—99.
"Rezension zu Hans van Ess:Von Ch'eng I zu Chu Hsi:die Lehre vom rechten Weg in der Ueberlieferungder Familie Hu”,in: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28(2004),262—266.
(35)Heinrich Hackmann,Chinesische Philosophie,Muenchen 1927.
(36)Wolfgang Bauer,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Konfuzianismus,Daoismus,Buddhismus,C.H.Beck.2009.
(37)相比之下,被纳入美国学术体制内的陈荣捷等华裔学者对朱熹思想的大规模翻译和研究,对英美汉学的朱熹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德国汉学界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之所以长期以来未有变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德国汉学本身在德国学术界内部的艰难生存环境。
(38)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5页。
(39)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1—72页。
(40)R.Loosen/F.Vonnessen(Hg.),"Leibniz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in G.W.Leibniz,Zwei Briefe ueber das binaere Zahlensystem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Stuttgart 1968.S.41,42,44,55.
(41)莱布尼茨深邃地理解了亚里士多德和邓·司各脱的存在论思想的真正要义,进而决定了德国唯心论乃至唯心论之后的西方哲学。对于莱布尼茨的思想史意义,海德格尔在晚年时曾有如此表述:“若我们想得足够深远的话,就可以发见到,莱布尼茨的思想承载着和烙印着近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趋向。因此,在我们的沉思中,莱布尼茨这个名字并不代表着一种过去的哲学体系。这个名字命名着一种思想的当前,这种思想的力量还没有消逝,而这种当前,我们还有待于与之相逢。”(Martin 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GA.10,Frankfurt 1997,S.51)莱布尼茨与朱熹思想的这场“对证式的对话”显得意味深长。
(42)R.Loosen/F.Vonnessen(Hg.),"Leibniz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in G.W.Leibniz,Zwei Briefe ueber das binaere Zahlensystem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Stuttgart 1968.S.64.
(43)可参见拙文《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载《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44)Alfred Forke,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De Gruyter 1938,Vorwort,Ⅵ.
(45)Alfred Forke,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De Gruyter 1938,S.201—202.
(46)Alfred Forke,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De Gruyter 1938,S.202.
(47)阿奎那并未真正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类比问题。在阿奎那的多少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类比问题之要义的解读中,阿奎那认为,对存在(上帝)和存在物(造物)的词语运用必须处于歧义性和单义性之间,此即类比。类比是介于完全多义性与纯粹单义性之间的表达方式,处在类比关系之中的观念不像在单义关系中那样是同一的,但也不像在多义关系中那样是差异的。对此问题,司各脱则把握住了希腊古典形而上学的基本精神,他清晰地指出:存在是二重性的,但这种二重性植根于同一性之中。如果有可能谈论上帝(存在),那么一定会有一些词语在用于上帝和用于造物的时候意义相同。某些超越性的词语(如“一”、“真”、“善”等)必须是单义的,无论这些词语是用于造物的不同种类还是用于造物以及上帝本体,它们都具有单一的意义。更多阐释在此不能展开,容另文探讨。
(48)(50)马恺之(Kai Marchal):《德国比较哲学的先锋:葛拉福神父的〈道与仁〉》,萧豫安译,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2007年第2期。
(49)Olaf Graf,Tao und Jen-Sein und Sollen im sungchinesischen Monismu.s,Wiesbaden 1970,S.361.
(51)海德格尔对类似问题有发人深省的阐释,他说:“工作做得很精确的哲学史家们对他们‘研究’的思想家所做的报道,通常是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仍然能够借助于这样一种不充分的历史学报道辨认出本质性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作为思想者和追问者自始就切近于有待思想和追问的东西了——这是一种无论多么精确的历史学科学都不能达到的切近。”(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7页。译文据德文版有改动)
标签:朱熹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莱布尼茨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近思录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史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宋朝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