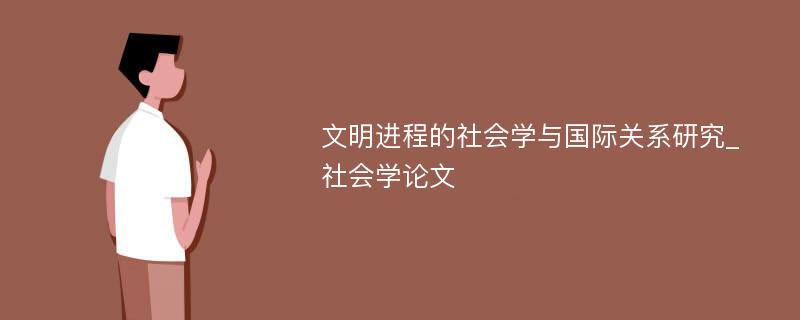
“文明进程”的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社会学论文,进程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1-0085-06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国际政治学领域被称为“扩大研究空间”的“第三次大争论”的出现,迄今为止,已经拓展出大量的新的研究项目和研究领地。[1](P57)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目前这种学说林立、流派纷呈的繁茂态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本文探讨的主题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一、“文明进程”的社会学
文明进程的思想是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在其杰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中阐述的最广为人知的理论①。文明进程的思想是埃利亚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一种精彩的案例分析,他通过对“文明”(civilization)的社会和心理起源的研究,探讨了影响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及其成员情感生活的长期变化模式,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及理论认识模型,对至今仍流行在社会学领域的许多根本假设提出了严肃的挑战。[2](P1)
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理论的核心旨在揭示社会对暴力的内部限制,个人自我控制的内在约束,对残忍、伤害和苦难的公共态度的变化,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水平等。[3](序言)埃利亚斯认为,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与20世纪相对发达的民族国家比较而言,对“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公共暴力在道德上的反感水平,对身体暴力内在的禁止水平是更低些的,与这些禁止相联的内疚感和羞愧感也是更弱的,甚至也许是完全缺乏的。[4](P145)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社会发展了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相甄别的一种对残忍的公共行为较低的“厌恶的极限”。埃利亚斯认为,从对人的行为的好斗性冲动的外部限制逐渐被内部限制所取代的分析中,人们注意到了现代良知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对暴力犯罪行为在态度方面的深刻变化。[5](P335)历史事实显示,在现代欧洲,对上述事务认同的范围比它在早几个世纪更广。作为文明进程的结果,大多数欧洲社会的居民不再将看人被绞死被车裂视为“星期天娱乐”。正如与古代社会相比较,我们对其他人的认同,我们分享他们的苦难和死亡的情感已经增长。[6](P2-3)在埃利亚斯作品中一个强大的主题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对公共暴力更高的反感水平以及欧洲国家公民之间情感认同的拓宽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
埃利亚斯认为,稳定的垄断权力的兴起,现代正在延伸的社会相互依赖网络的演进,要求更大的自律以及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更高的情感认同水平。埃利亚斯的研究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开始,个人的自我控制,主要是指与外部强制无关的、主动自发的自我控制会发展得特别快。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这种自发起作用的个人自我控制,诸如“理性思维”和“道德良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实在地渗入进了人的情感本能的每一个毛孔,并严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没有经过控制机构准许的情况下直接地付诸行动。[3](P42)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3](P43)羞耻与尴尬是个人感情,也是典型的由社会所导致的情感。对“羞耻、尴尬起点的提高”的论述构成了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人感到他或她的不良举止被人发现,羞耻就产生了;看到他人有着同样不良的举止,尴尬就出现了。随着成文和不成文的礼仪规则变得越来越广泛精细,侵越这些规则的机会就增加了,因此羞耻和尴尬的情形也就增多了。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令人讨厌的”或受指责的事情已经被逐渐地隐匿到社会生活舞台的背后。埃利亚斯为解释这些情形的社会根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埃利亚斯还强调文明进程可能与退化进程(decivilizing processes)并存。文明进程和退化进程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称性,前者只能是相对长期的,而后者却能迅速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在纳粹时期的西欧。先于这个大范围的野蛮行为的“长期构建阶段”几乎是不明显的,但之后是明显的无处不在。两次世界大战揭示,当人们感到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时,大多数人对杀戮、正在死去的人们和死亡的敏感很明显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进程会被逆转,从而导致退化进程。[7](P205-223)
埃利亚斯的作品在其去世前后,才逐渐为英语世界的学术界所推崇。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一批强调将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②,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研究③。林克莱特认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思想对国际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8](P3)他对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深刻透析和对“礼仪”(civility)概念演变等分析,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许多重要的研究议题相融通,尤其能够扩展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中“礼仪”和“文明进程”已有的分析。他对不同时期有关残忍、暴力和人类苦难的主导态度和情感认同的分析评论,能够极大地丰富国家体系社会学方法的视野,同时还有助于开拓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伤害问题的研究。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吸纳,也可以进一步扩充埃利亚斯社会学研究中没有被发展的领域。当下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结合研究领域宽阔视角多重,以下,笔者从林克莱特的视角来考察埃利亚斯的社会学项目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领域相互吸收借鉴发展的问题。
二、文明的进程和英国学派的礼仪和文明
林克莱特认为,英国学派研究的主要起始点是道德、法律传统和心理取向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问题。然而,通过反思国际社会,英国学派越来越注意到礼仪思想和文明进程研究的重要性。“礼仪”是指带给人类事务以秩序与和谐的社会习俗、礼貌或习性,以及相关的心理特征和情感倾向。英国学派的成员也曾使用礼仪的思想和文明进程来理解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秩序。[9](P855-878)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英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的观点:全球政治稳定需要在与“总体文明的进程”相结合中被理解。检查自我中心的行为以及控制好斗性冲动和危险性行为,是巴特菲尔德所描述的这种文明的进程的核心要素。[10](P3)巴特菲尔德和怀特都相信,所有社会在特殊的地区文明之内演进,在那里,道德或宗教的统一被利用去构筑国际秩序。他对文明的定义与埃利亚斯对文明进程的使用有广泛的相似性。巴特菲尔德认为,文明是指贯穿于人们的经历,跨时间而形成的行为诸模式。而这些人能够移情(empathy)于其他人,能够为维持相互间有序关系这一长期目标而否定他们自身的短期利益。[11]巴特菲尔德强调的移情主要关注的是在维持秩序方面外交共同体的角色,而埃利亚斯则感兴趣于在欧洲国家之内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模式,包括移情作用的情感发展。两种方式都致力于理解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世界主义情感已经影响了世界政治。[12](preface)
英国学派最近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更多地使用礼仪和文明的思想来分析国际秩序的道德、文化和情感基础。沃森(Watson)将“外交对话”描述为一种基于对其他人的观点的知晓和尊重的礼貌的过程。因为这些思想持续不断的交流,以及对利益冲突相互间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尝试,都增加了相互知晓和尊重,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进程。[13](P20)杰克逊(Jackson)认为,现代国家间社会在促进相互理解、承认、沟通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是最成功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他认为礼仪是首选的文明,对杰克逊而言,礼仪在理解现代“全球契约”(global covenant)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同巴特菲尔德一样,他认为相互理解、容忍和自我约束是有着不同世界观的政治实体学会如何共存的关键。
巴特菲尔德、沃森和杰克逊在他们对世界政治的评析中,在描述对限制武力的需求、对文化偏好和对其他人政治利益敏感的需求的共同理解方面均使用了礼仪和文明的概念。这和埃利亚斯主张的不以蔑视的方式使用文明进程来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之观点相似。[13](P49)此外,英国学派对他们公开声称的欧洲文明同一性特质及其在其他社会的影响方面的兴趣,与埃利亚斯对欧洲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带有全球文明使命的文明方案的分析相连;英国学派关于欧洲区分文明社会和野蛮、未开化社会的分析,与埃利亚斯对这样问题的反思也相似。英国学派的成员认为,这种文明观(the idea of civilization)是国家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它包括排斥“不文明”人(uncivilized peoples)的国际社会的产生。而一种捍卫礼仪的全球文明进程的发展,使得这样的事实成为可能,即在第一个普遍的国家间社会中(in the first universal society of states),文化上多样的欧洲和非欧洲的政治共同体至少是作为概念上平等的成员相处在一起。巴特菲尔德强调对国际秩序移情作用的重要性与理解国际社会的扩展是相关的,因为如果没有欧洲在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情感反映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全球文明化进程的过程不可能发生。林克莱特指出,英国学派所研究的礼仪和文明的进程强调国际秩序不能还原到国家行为受外在的均势限制这一事实。他们强调秩序取决于内部的限制,它包括约束暴力的共同愿望,不去剥削他人弱点的共同意愿,对移情于他人的能力的关注等。而同样,强调对暴力和自我控制的内在约束的重要性是埃利亚斯文明进程叙述的中心。
英国学派和埃利亚斯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埃利亚斯的研究聚焦于这些内在化的限制在一个有领土边界的国家之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而英国学派考虑礼仪和文明的进程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之中。布尔和沃森认为,“国际政治生活,包括它的规范或制度性的方面,有它自己的逻辑,不总是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利益或生产过程的反映”。换言之,他们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的文明与各子文明是相互联系的,尽管为了评估内生性影响和外生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他们不检查这些联系。[14](P19)在埃利亚斯的方法中也发现这种相应的偏好。但是,正如英国学派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全球礼仪(global civility)是不能与国内礼仪(domestic civility)相断绝的。埃利亚斯也十分清楚,他关注的社会的长期变化模式不仅不得不与国际政治,而且必须与总体上影响人类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模式相并置观察。[15](P139)因此,埃利亚斯比英国学派的成员们更多地关注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对待残忍和苦难问题的国内和国际态度之间的关系方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研究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使用礼仪的思想和文明进程的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分析相呼应,虽然二者视角不同,但他们关注的领域和对诸多问题的理解存在许多的交叉共通之处。将二者的研究相互融会贯通,不仅能够丰富二者各自的相关研究,对国际关系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入埃利亚斯研究文明进程的视角,补充和深化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中礼仪和文明进程已有的分析,尝试整合出一条新的更加综合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研究路径。此外,另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埃利亚斯的思想还能够致力于由怀特创立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tates-systems)的研究。
三、文明的进程和国家体系的社会学及世界政治中的伤害问题
马丁·怀特在1977年发表《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一书,产生了一种“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的宏大视野,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国家体系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16](P81)在此研究中怀特区分了霍布斯式方法与康德式方法(世界主义方法),认为两种方法都就国家体系的长期命运提供了不同的立场。[17](P331)虽然怀特更倾向霍布斯式方法的立场,但是他的国家体系社会学的康德式方法提出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团结思想和普遍人类共同体的洞见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国家体系之演进的问题。[18](P200)怀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古代中国、古希腊和现代国家体系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秩序的道德、文化和制度基础,[19]也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礼仪问题。怀特在对普遍道德共同体的承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体系的长期发展方面的兴趣,使他反思在古希腊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对战争中暴力和残忍的普遍态度的“道德敏感”水平这一问题。
林克莱特认为,埃利亚斯的思想能够致力于这种考虑世界政治中“世界主义情感角色”的康德式方法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项目。在埃利亚斯作品中霍布斯和康德主题并存。他的现实主义观点与怀特是一致的,即国际政治是一个“不断再现和重复的领域”。他认为,综观人类历史,大多数的社会都会宽恕且常常是积极鼓励对它们社会之外的人的暴力行为,而这种行为在他们本集团之内的关系中是被禁止的。埃利亚斯称之为“民族—国家规范性准则的二元性”(the duality of nation-states normative codes)。[5](P461)然而,虽然埃利亚斯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在本质上是霍布斯式的,但对这个领域未来研究最重要的资源却是在埃利亚斯思想中的康德主题方面。他在强调现代对种族灭绝的反感和探讨现代国际体系发展对暴力的限制时,在对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对残忍、暴力和人类苦难的主导态度和情感认同的分析评论中,在对世界主义情感是否在现代比之前的时代更强烈这一问题的反思中,康德主题是十分突出的。[8](P16)而且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呈现在埃利亚斯对全球化的研究中,即是否所有人类成员之间日益拓宽的情感认同益发可以产生出最持久的政治结果。[20](P114)埃利亚斯相信,人类彼此认同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对其他人的移情能力、感知能力(feel for)、同情能力的深度和广度,是文明进程的“中心标准”。[8](P11)他指出,世界主义情感在最近的时代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那么是否对不同国家体系中残忍和同情的分析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否文明的进程影响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演进?这是他的研究中没有被充分发展的领域。非常明显,埃利亚斯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评论对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且二者可以相互吸收借鉴。
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的研究能够得益于与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结合,尤其得益于世界政治中的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得益于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因为它们的研究方法能够回应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关注,扩充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研究④。同样,如上所述,认真地挖掘埃利亚斯对欧洲现代性研究的诸方面,也能够十分有意义地致力于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林克莱特等人认为,将二者的研究相结合能够将国家体系的社会学扩展成一种新的有特色的知识研究领域,[8](P17)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可以有两方面的雄心:一是考察不同的国家体系在阻止伤害,或使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和其他行为主体的人民受到的伤害最小化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二是考察现代国家体系是否忠诚于这一伦理观点,即将不必要的伤害看作是所有社会、个体和集体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首要的道德问题。[21](P262)因此,林克莱特认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合适的启程点是——世界政治中的伤害问题。
林克莱特指出,在已有的对国际体系的研究中还没有对残忍和同情有一定水准的研究,也没有系统地考察在不同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中全球文明进程的长期趋势,而且也少有关于对人类伤害的世界主义情感反映在现代国际社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强大的经验性分析。因此,林克莱特认为,当前全球文明进程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应该首要关注对残忍和伤害的全球态度的经验性分析,探究在不同的国家体系中对世界主义认同水平的发展程度和各国家体系如何处理世界政治中的伤害问题。[18](P320)据此,围绕伤害问题,林克莱特提出了两套分析世界主义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塑造了不同国家体系长期发展的研究问题。
一套是:不同国家体系的成员在何种程度上已经保证合作,使在战争中军事人员和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免受不必要的伤害?保护个体不受政府强制的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体系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一种普遍义务,去保护弱者不受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海盗、唯利是图者和商业集团等)所导致的暴力、控制和剥削影响?另一套是:不同国家体系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行动起来,减少或消除无意伤害和由于过失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寻求保护人类免受不公平的致富或不作为行为结果所导致的伤害?
这些问题形成了有两大目标的经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首先,黑格尔思想中的渴望人类美好社会的全球文明进程,已经在多少国家体系中发展起来。[5](P262)其次,全球道德良知或世界主义道德情感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是否比过去有更大的影响。这些问题,部分是埃利亚斯对欧洲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结果,也是怀特有关普遍道德共同体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体系发展思考的一个反映,呈现了在一些新的方向中进行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研究的尝试。
四、结论
在埃利亚斯这一代的社会学家中,像他这样能够认识到国家间关系重要性的学者是不同寻常的。有意义的是,他对文明进程的分析不是简单地或主要只关注单独的国家内部的发展,他还考虑影响人类长期变化模式的发展以及全球文明进程的发展,这对国际关系研究吸收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十分有益。同时,埃利亚斯在分析中没有充分注意到国际关系的学术文献,借鉴上述国际关系相关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文明进程的社会学自身研究的发展。文明进程的研究能为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搭建一座新的桥梁提供十分有价值的资源。
[收稿日期]2007-09-03
注释:
①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初版于1939年,当时鲜为人知,直到1969年首次再版。埃利亚斯的学术命运与众不同,属于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辗转欧洲最终旅居任教于英国。在英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是作为一名体育社会学家为英国人所熟知,其理论的精髓并未被认识。直到20世纪晚期,其主要著作和文章在他70、80及90岁时才陆续问世或再版。在生命的暮年,埃利亚斯接受了来自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荣誉,但直到他去世前后,才逐渐为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界所承认和拥戴。
②安德鲁·林克莱特是近年来用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研究国际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学者Haferkamp和Mennell等也是这种方法的极力推崇者。参见H.Haferkamp,From the Intra-State to the Inter-State Civilizing Process?,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87,(4),pp.545-557; S.Mennell,Comment on Haferkamp,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87,(4),pp.559-561.
③安德鲁·林克莱特是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他的理论不仅长于批判,还构筑了一套以探究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国际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的理论体系。其思想和方法还涉及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规范理论、英国学派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等非主流理论,与它们既泾渭分明又相互交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一直努力将英国学派引向一个更具批判和规范性的方向,并试图用他的批判理论改造英国学派,倡导一种批判的历史社会学。他在本世纪阐发的国际关系伤害观(The Idea of Harm)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晶。
④一些学者也在探究埃利亚斯的社会学视角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学术沟通和交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涉及考察这个方面。
标签:社会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埃利亚斯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礼仪规范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公共礼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