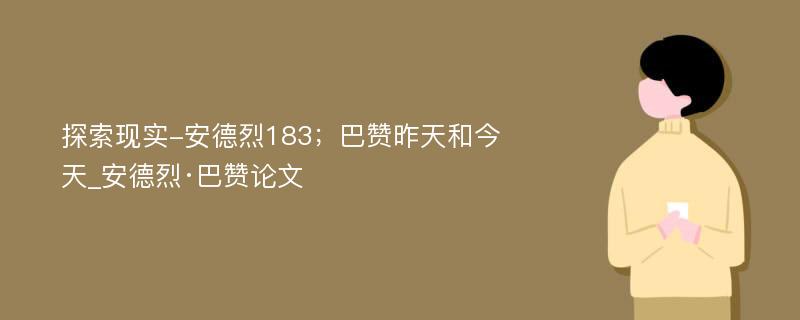
探究现实——安德烈#183;巴赞在昨天和今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德烈论文,现实论文,昨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是一个谦恭朴素的人,一个被病魔长久折磨而英年早逝的人,但正是这个人赋予了电影以无上崇高的价值,”让·雷诺阿1967年在安德烈·巴赞被译成英文的第一本书——美国出版的《电影是什么?》文集——的序里这样写道。接着他说:“巴赞对未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一预言如今已经实现,尽管不完全符合雷诺阿的设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巴赞是使电影成为如此重要的艺术和如此重要的研究对象的惟一的一位思想家。
当人们纷纷各自试图给电影做出一个定义的时候(其中最成功的要算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和鲁道夫·爱因汉姆的著作),巴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电影无可置疑地是人类智慧活动的一个独立领域。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巴赞预言,终将有一天电影学研究会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而他对于促成这一点做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贡献。
安德烈·巴赞1918年4月18日生于法国昂热。少年时志愿成为一名教师,所以考入师范学校。1941年毕业于圣克卢高等师范学校,但由于口吃未能获得教职,被安排在辅导因二战爆发而失学的青年学生的文化学校任职。就在这所学校里,巴赞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创立了一个电影俱乐部,组织放映遭禁的影片,从而在暗中有力地抵制了纳粹宣传。
法国解放后不久,巴赞被任命为高等电影教育学院文化部主任。这一期间,在频繁的座谈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的电影评论家,由此开始了他的影评人生涯。然而巴赞始终没有放弃做教师的理想,这一点明显反映在他那种启发诱导式的写作风格和论辩方式中。
巴赞这种把逻辑思维和诗意叙述相结合的风格引起了让-保罗·萨特的注意。于是他推荐巴赞为著名的哲学杂志《当代》撰写文章。从此巴赞的名字就同《法国银幕》、《法兰西观察家》、《广播、电影、电视》、《电影评论》、《评论家》、《精神》等众多刊物——当然还有安德烈·巴赞与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洛兹于1951年创办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电影手册》——紧密联系在一起。据说巴赞撰写的评论和论文共有两千多篇。他如此多产的一个原因是生活所迫——他需要供养他的妻子让妮和幼儿弗洛朗。此外的时间便是各种电影节、各种会议以及编辑部的工作,而这一切在1954年因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戛然而止。1958年11月18日安德烈·巴赞在马恩河畔诺让市逝世。其时他即将完成一本关于让·雷诺阿的论著的写作(后来由他最亲密的同道弗朗索瓦·特吕弗编辑出版),并为打算亲自拍摄的短纪录片《圣通日的罗马式教堂建筑》写作剧本。
巴赞的个性中具有某种类似中世纪僧侣的精神。雷诺阿曾把他比喻为夏特勒大教堂镂花玻璃上的某个圣徒。特吕弗更是把他称做混沌时代的缔造者。所有熟悉他的人全都赞扬他的智慧,崇敬他的人格,而且往往用宗教禁欲主义的言辞称颂他。
如果我们说人的才能纯粹来自先天,那么多数电影理论家肯定不会同意,但对于巴赞来说,这却可能是他的著作具有长久令人倾倒的魅力的原因之一。当你阅读巴赞的文章时,你决不会觉得他在那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意思装进一些官话、套话的现成框架里去。相反,你会觉得是在同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更确切些说,同一个把握了崇高真理的灵魂,在做直接的交谈。巴赞特有的纤美文风无疑同他长期患病的状态有关:对于一个处于死亡边缘的人来说,现实世界必定显示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灵感的主要源泉却是他的信念——即使对于一些与巴赞才具相当的批评家来说,这一点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巴赞关于电影的现实性定义的根据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电影摄影机由于能够直接记录周围世界这一极简单的事实而有力地见证着造物的神奇。电影摄影机的使命就在于精确地记录,因为它是科学的成果。
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1945)一文中论证说,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渴望能够用艺术把世界的外貌准确记录下来。巴赞把这种愿望归结为他所谓的“木乃伊情结”——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愿望:用涂布防腐剂以保留外形的方法来留住奔流不息的现实时间。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人类才终于能够充分满足这一愿望。按巴赞的说法,照相的真实性具有非理性的说服力,因为它是对所摹写事物的机械复制的结果——在这过程中完全没有人的介入。一幅绘画,不论多么逼真,它毕竟是人的构思和操作的产物,而照相的影像却是事物所反射的光线投射在化学感觉膜上而自动生成的。“照片作为‘自然’现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它犹如兰卉,宛若雪花,而鲜花与冰雪的美离不开植物与大地的本源。”照巴赞的说法,照相的这一客观属性(照片首先是一个感性的存在,然后也许才是艺术作品)正是摄影机在反映现实方面的特权所在。因此,照相和照相的“后代”——电影,也就对现实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先要记录现实,然后才能试着去解释或评判现实。对巴赞来说,这个责任是极端神圣的:照相手段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永恒地见证宇宙万物的壮美。
可以想见,巴赞的论点势必会招致尖锐的批评,会被指责为颠倒因果地用形而上学的逻辑来解释唯物主义的观念。于是,为了抵制将会提出反对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巴赞提出了一个难于反驳的理论,论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于某种精神意志,而不是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完整电影的神话》)。随着全色感光胶片、录音设备、变形镜头和立体电影等等新技术的出现,照相和电影成功地满足了更加完美地反映客观现实的需求。
显然,巴赞指的是那种玄奥氛围所预示的艺术上和工业上的突破。尽管巴赞写作向来相当谨慎,不会发生涉及神学的疏漏,但从他的思考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激进的天主教思想家德日进① 的科学加神秘主义的思想。德日进提出人类意识进化的螺旋式发展最终将与上帝的启示融合为一。用俗家的话来说,从巴赞对未来电影的强调中可以听到萨特存在主义的余音。
然而,巴赞对他的“完整电影的神话”还是做了一些假定性的限制。假如电影在某个时候真的成为现实的等同物,那么它也就不再成其为电影了。如同数学中的渐近线一样,电影对现实的展示总是离它所要达到的限度稍差一点点。然而,正因为电影永远不会与生活完全合为一体,它才能成为以呈示、展示生活为使命的一种艺术。巴赞承认,艺术不能没有虚构,但这种虚构在把现实搬上胶片的过程中必须服从于现实的标准。电影对现实的表达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所以我们最好说“现实主义”,而不要说什么惟一的和最终的现实形态。在这方面,巴赞比他的反对者所设想的更加接近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论要求,同时他却幸运地避免了后现代的虚无主义。他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说:“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然而如此纯净的面貌终究是电影手段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类主观性的污染。
有些影片和作者把浑然一体的现实切割得支离破碎,强加给它某种风格和含义。在《电影语言的演进》(1950—1955)中,巴赞对“相信画面”和“相信现实”的两派导演做了严格的区分(这一区分后来常常被人引用)。他对《卡里加里博士》等德国表现主义影片明显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认为对灯光和布景的精心雕琢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故意伤害,是强行表现理性的扭曲状态。同时,他也反对爱森斯坦把现实“肢解”成一个个单独的镜头然后再用蒙太奇技巧重新组合起来的做法。
巴赞不赞同蒙太奇的理由是,这种方法用影像的对列预先规定了注意力的方向,从而对观众造成伤害。他认为,蒙太奇派的影片极力要营造出一种人为的现实以实现宣传的意图。巴赞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异端,因为它把自己当成全能的上帝——整个天地间只有上帝才有权力给事物赋予含义。但既然上帝离开了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自己去寻索他老人家的启示吧,所以巴赞对于那种敬畏宇宙中所蕴含的秘密的电影艺术家是深表赞同的。譬如维多利奥·德·西卡就是这样的导演之一,他在影片《偷自行车的人》(1948)和《温别尔托·D》(1951)中谦恭地排除了作者本身人格的高傲表现,从而使观众有可能直觉地去领会人物和事件隐含的意义。巴赞在《导演德·西卡》一文中写道:“场面调度似乎是自然形成的,如同生命物质的自然形态。”巴赞承认,电影在再现现实时总会对现实进行一些压缩、组织和安排。但是他在电影导演的个性中所寻求的却是一种在精神上对现实的亲近感:极力服务于现实,消除表现手段自身的意义,避免因思想观念和技术手段本身的缘故而强行扭曲现实。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位“透明”电影的积极拥护者同时又是电影史上著名的“作者论”的首倡人。在他的庇护下,《电影手册》的青年评论家们为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道格拉斯·塞尔克这些未能得到恰当评价的导演确立了在电影中的准确地位和评价标准。巴赞的许多同事——特吕弗、戈达尔、埃立克·罗麦尔、克洛德·夏布罗尔和雅克·里维特——后来都开始拍摄影片,所以人们又常常把巴赞视为新浪潮之父。
如果说巴赞的评论奠立了一种电影神学,那么完全可以说,作者在电影中担当着一个圣徒——一个现实世界的热情捍卫者的角色。巴赞在30年代参加过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所谓人格主义运动,这也许和后来的“作者论”有关。这一运动就是把敢于选择并实行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的人称为创造性人格的。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赞逐渐抛弃了对影片作者的崇拜,因为他并不看重大多数影片制作中与此相关的商业性因素。虽然他对好莱坞电影具有极其精辟的见解,认为它最值得作为“榜样”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适应能力,然而他对好莱坞导演们的评价却大大低于他对雷诺阿、卓别林、德·西卡、罗伯托·罗西里尼、卡尔·德莱叶和罗贝尔·勃莱松的评价,这些人才符合他的淳朴崇高的理想。
尽管电影艺术家们各自的风格多种多样,但他们都在同一个神秘难解的现实上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么这就是,他们都在竭力探索具体地表达时间与空间的技术手段。
巴赞非难蒙太奇,认为它损害了被摄事物的空间完整性。而我们总是处于时空的连续之中的,因此蒙太奇只能迷惑我们的体验,它是一种省略法的艺术。为了更崇高的现实主义,巴赞推崇不加切分的长镜头,只有长镜头才能模拟大自然最基本的属性——不间断性。巴赞认为,摄影机必须自我约束,不要过多地把空间分割成小块;他认为,恰当地展开场面调度可以造成生活延续到画面外的感觉。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要属雷诺阿,他善于把长镜头和景深场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巴赞认为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可能选择,这实际上也许可以说是现代电影现实主义的主要内涵。在他看来,景深场面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镜头中的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观众应该自行决定其中什么是主要的或者说令人感兴趣的。像奥逊·威尔斯和威廉·惠勒(后者导演的《小狐狸》曾被巴赞不止一次提到)这样的导演尽管在画面构图中安排他们的重点,但却毫不妨碍观众在自己头脑中对这个画面进行“蒙太奇”剪辑。简单些说,整个景深全都聚焦清晰的拍摄方法就是要尊重人格的自由和道德的责任。在电影中和在生活中一样,我们理应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
《精神》杂志在巴赞逝世的讣闻中援引了他的一段预言:“到了2000年,人们将迎接自由电影的到来,这时的电影将摆脱蒙太奇的程式,不再充当‘现实主义艺术’的角色,而将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成为‘现实所造就的艺术’。”新千年的到来证明结果恰好相反。电影自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逃避现实的梦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现实的真实性缺少信心。今天,影像的数字化恐怕要割断照相与电影之间的血脉联系,也就是抽掉巴赞建立其理论的根本前提。不但如此,他所热烈赞扬的那些透明性的形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已失去光彩,销声匿迹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逐渐陷于浅薄和雕饰,精致的景深场面带上了舞台式的造作味道。归根结底,任何现存的现实主义都会僵化,都会变成纪念过时艺术流派的博物馆陈列品。但是,巴赞(也代表所有人)会说,不可避免的衰败却并不意味着,每个艺术家不再需要努力依照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要求去重现现实。为此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诚实的精神而已。
巴赞立志教育的精神无疑推动电影从一种低俗的游艺变成了一门需要认真重视和严肃对待的学科,虽然他没能活着看到60年代末电影学术繁荣的第一次高潮。巴赞身上的诗人情怀则会深深感觉受了伤害。
电影研究的风气迅速变得浮夸和僵化,越来越排斥巴赞文风的核心特征——引人入胜的形象性。巴赞是幸运的:在他从事写作的那个时期,电影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僵化的模式。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评论家,巴赞还可以在《手册》上——尽管是偶尔地——在不受假道学的挑剔指责的气氛下进行他的智慧思考。他还能充分享受作为评论家的特权——凭借自己准确无误的敏锐判断触及现实的迫切问题。他的思想,较之那种对每一条理论提法都大量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进行论辩的皇皇巨著,要更加具体,更加充满智慧和灵感。
几乎在人们把巴赞奉为经典理论家的同时,新一代的半吊子电影理论家开始对巴赞发起了攻击。他们宣称,巴赞没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进程,他所推崇的现实主义理论无非是把一些完全相反的观念勉强扭合在一起,根本不能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体系。不过,这些硬说巴赞理论自相矛盾的专业研究家根本没有认识到巴赞的思想的辩证本质。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能领会巴赞理论中的诗人情怀,不懂得巴赞多么善于把握互相对立的观念的微妙状态,超越单纯理论的界限,而达到顿悟的境界。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巴赞是一位电影的游吟诗人,他真诚地相信电影能够臻于完善,他对他自己设定的总体性问题“电影是什么?”理直气壮地做出正面的答案。然而新一代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越来越趋于负面。60年代反文化运动高潮中出现的欧洲电影理论学派已经蜕变为自我标榜革命的小团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② 宣称,大众媒体无非是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传声筒。在他的绝对化观点的鼓动下,一些激进的理论家不是着手维护电影,而是要来埋葬电影了。巴赞的深沉的人道精神,同把大众电影视为意识形态工具——愚弄驯顺百姓的有效机器——的教条主义之间的冲突,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巴赞,这位上世纪最杰出的评论家,竟成了现存体制的代表,被战斗性十足的“手册派”诋毁得一无是处(这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他们能有什么情结的话)。而在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在权威的英国电影理论杂志《银幕》的带动下,诋毁巴赞成了七八十年代的时髦。
既然符号学和拉康精神分析的相互渗透已经证明,人类的感知永远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你要设想电影能够直接纪录现实,这该是何等的愚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当代电影理论整个宏大复杂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千方百计证明巴赞是错误的基础上的。
当然,今天人们普遍公认,现实是具有结构性的,巴赞在这一问题上的天真设想不再引起狂热的攻击,毋宁需要给予宽容的一笑。但是必须承认,他早年对电影的现实本性的信念恰恰是他有别于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摇摆态度之处。既然从这一方面来看无处不在的怀疑主义和充斥一切的犬儒哲学已经成为当代的正统,那么也许已经是时候该给现实性,以及安德烈·巴赞,恢复一下名誉了。
注释:
①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来中国参与“北京人”的发掘和考古工作。——译者
②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