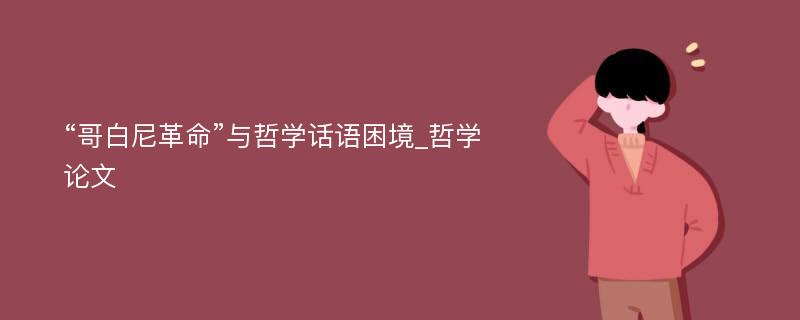
“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哲学言说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白尼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2-0012-06
按最流行的见解,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被划分为三大基本形态:本体论形态、认识论形态和语言论形态。从古希腊到笛卡尔、康德以前的哲学属于本体论形态:哲学家们的所有研究都是在诸如“世界的本源或基本要素是什么?”“变中不变的实体是什么?”这样的基本语境下展开的。从笛卡尔和康德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第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研究由本体论领域全面转入了认识论领域:“我们真正确实无误地知道什么?”“认识怎么可能或怎样发生?”之类的认识论问题取代了以往的本体论问题。自20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号称进入了“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亦即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哲学探究的触角伸向了语言的王国:各种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当然也包括一些“认识论化”了的本体论问题)全部撞碎为关于词汇、句法、语义、语用、能指、所指、结构、意义等等的条分缕析,并且在这种条分缕析中不同的流派或思潮相互间又打得人仰马翻。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的起落,西方哲学逐渐完成了由认识论形态到语言论形态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转向。
毫无疑问,三大基本形态只是关于西方哲学历史的一种极为粗糙的分类;西方哲学精神的演历要比任何分类图式都复杂得多(注:实际上,每—哲学发展阶段均有此三大形态“共时”的并存状态;“历时”意义上的三大形态,只不过是对“哲学主流”的不甚精确的表述而已。)。不过,事情的本质不在于分类形态本身合不合理或能否涵盖整个西方哲学史,而在于我们能否倾听和应答蕴含在这种粗糙的分类本身深处的意义之召唤。
显而易见,从西方哲学所大致经历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三大历时形态中直接浮现出来的现象,是哲学思考之对象的流变:由对“世界”的思考转向对“认识”的思考,再由对“认识”的思考转向对“语言”的思考。两次“转向”都被誉为哲学思考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逻辑上讲,思考对象的流变并不必然对应思考自身的质变。“世界”、“认识”、“语言”作为思考的对象,其本身是并列平等的。在这些对象之间转来转去,只不过是思考内容的改变,而这并不必然导致思考本身即思考本质的“革命”。因此,“转向”这个词虽然企图命名哲学思维的某种革命,但它真正说出来的东西却恰恰对这种革命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遮蔽。正像哥白尼革命的实质不在于由“地球中心”转向“太阳中心”一样,倘若两次“转向”确系哲学思考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革命”之成其为“革命”,其实质也必然不在于思考对象的外在“转向”上。
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对世界的认识转向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这其中真正发生了革命的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关于对象的认识”。换言之,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革命,其实质不在于哲学认识的对象之嬗变,而在于关于对象的哲学认识之嬗变。“认识”这个词不像“桌子”、“杯子”、“水壶”那样的名词,命名一种摆在那里的既定的、现存的、完成了和封闭的存在者。认识之成其为认识,首先就在于它根本不能还原为任何一种“存在者”。“认识”就是认识的发生,认识的展开,认识的过程本身,认识的“认识存在”。如果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将认识作为一种“存在者”来言说、审视和研究(注:将存在“对象化”或“存在者化”作为人类认识的主流路向,似乎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参见拙文《宗教之思的意义境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那么我们就必须时刻警戒自己:被作为存在者来命名的“认识”,不仅事实上是未完成的、“能在的”和开放的,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的是,“认识”就是认识自身的“到场”,虽然认识只能在对于认识之对象即对对象世界的认识中到场,但作为对象的“认识”与作为外在对象的“世界”,却不是比肩并列的两个现存的对象领域。因此,所谓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转向对这种认识的认识,这绝然不是在两个平列的对象之间的“转向”(比如由对“经济”的认识转向对“政治”的认识)。如果说本体论认识着对象世界,那么认识论便认识着本体论,认识着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后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认识不但包含或吸收了前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认识,而且使所谓“本体论”真正“过时”,并在与本体论的视界融合中开辟出人类认识的一条崭新的可能路向。
有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革命一样,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革命,其本质也不在于哲学认识对象的嬗变。把探究的目光从作为对象的认识转向作为对象的语言,这种在对象间的平行转移并不必然是一场革命。事实上,转移本身只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革命带出转移,而非相反。在认识论中,哲学言说着认识。这意味着,落在哲学的追问、探寻、思考、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视野之内的是作为被言说者的认识,而言说本身,即作为言说者的语言却尚处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一旦作为言说者的语言从言说本身中被剥离出去成为被言说者,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便发生了。假如说认识论言说着本体论,语言论就言说着认识论。正如第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样,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也经过与认识论的视界交融从而开辟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域。
然而,随着哲学上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深入(这个革命至今仍在继续扩张着),哲学在其形而上的深度根基上(正是此“根基”必然地酝酿、引发和实施了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愈来愈陷入了由这个革命本身所带来的一种言说的困境之中。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哲学不断地从它所以为是的东西中被挤出。古代哲学以为自己是关于世界或宇宙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知识,但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迫使本体论哲学让渡出了这一知识的领域。于是,哲学从世界或宇宙退出,掉头挥师认识的王国,构建起庞大的认识论大厦。可现代心理学、脑科学、逻辑学、控制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边缘科学的突起,无情地吞食着哲学思辨辛苦构筑起的认识论大厦,一步一步地剥夺了哲学言说“认识”的基本资格。于是乎哲学又不得不从“认识”再一次退却,转而闯入了语言的领域。显然,此乃一个哲学对象化自身继而回返自身进而又对象化自身的循环过程:哲学对象化自身或肯定自身为本体论,继而否定此种肯定,而这否定作为对本体论样态的有限境域的超越,乃哲学在基本真意义上向自身的回返(“超越”乃哲学的本真存在,或者说,哲学只有在“超越”中才真正“在场”);然而此种“回返”作为有内容的回返,总表现为内容上的“转向”(由“世界”转向“认识”),或哲学样态上的“革命”(由“本体论”样态到“认识论”样态);认识论样态的哲学作为“哲学革命”的结果,实际上不过为另一次“哲学革命”提供了开端,所以哲学或早或迟又不得不在更深层次上再一次对象化自身,从而在另一级别上开始同样的循环。然而,这一次由认识论形态转向语言论形态的循环显得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在这一次循环中,哲学似乎遭遇或撞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带根本性的困境:哲学就仅仅是这样一种不断对象化自身从而不断扩张或演进自身的循环往复的永恒模式吗?以“对象化”为本质的哲学循环,正面临着或经历着自己的极限。
如果认识论可以朝本体论发问:当哲学认识世界时,这个“认识”本身怎么可能?如果语言论可以向认识论盘问:“认识”这个词究竟在说什么?作为一个缺乏严格逻辑界定的含混不清的术语,它究竟说了什么还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如果语言论可以在“清理语言的误用”的基础上进而将认识论及本体论贬之为“既不正确也不错误而是没有意义的言说”,那么,语言论便不得不接受必然接踵而至的更尖锐的追问:语言论凭什么去言说语言?哲学凭借认识而言说世界,凭借语言而言说认识,它凭借什么去言说实质上就是言说的语言?凭借语言?凭借语言去言说语言,这在外在形式上是不是已经犯规?退一步讲,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即哲学—逻辑的语言去言说或“清理”语言的。然而这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它的特殊性究竟“特殊”在哪里?它从何处赢获了“清理”和判定“语言误用”的特殊资格或权威?实际上,当20世纪的语言论哲学向语言发起进攻时,它自身的“语言境域”却尚处在一片晦暗之中。
细致思之,上述困境还有另一面。哲学退出认识领域而侵入语言王国,这本身便意味着,语言曾经不是(起码不主要是)哲学的对象。此乃一个不得不接纳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默默注视下,谁能合逻辑地断定语言领域就是哲学的“最后”栖居之地?若“认识怎么可能?”构不成哲学的终极追问,“澄清语言的误用”又怎么可能膨胀为关于哲学的终审判决?若将认识对象化阻挡不了对认识论的超越,把语言对象化又怎么可能将哲学钉死在语言的十字架上?
其实,当第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当哲学由言说世界退回到言说认识时,哲学作为一种言说便已经跌入了言说的困境之中:认识既是对象同时也是“非对象”,既是认识者同时又是被认识者。因此,在哲学企图将认识彻底对象化为被言说的存在者来把握时,实际上意味着认识作为认识者或言说者,作为言说本身,已经在根本上从此种被言说之中抽身隐退,意味着言说认识恰好已经错失了在场的认识,只不过这种言说的困境因为还有更基本的“语言”可依尚不显得触目罢了。当哲学由言说“认识”进一步退入到言说“言说”(语言)时,哲学言说的言说困境就再也遮不住地凸显了出来。
哲学无论如何首先是一种言说,一种独特的言说,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而道之为道,用老子的话说,就在于道源始地就是“可道”(道说)本身(注:虽然,道出之道或一切道说均非“常道”,然此“常道”却正是在此道出之道或道说中才被反射出来,才被呼唤出来,就是说,才到场。);语言之为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在于语言源始地就是“言说”本身[1](981-985页)。因此,语言—言说的全面对象化,不仅意味着作为一种言说的哲学在逻辑上已丧失了一切可依可靠的东西,丧失了可以据以去“澄清语言”的基地,并进而逻辑地意味着哲学作为在内容上被抽空了的言说,已无法将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来界说,既无法在语言一言说的层面上将哲学言说方式与其他非哲学的言说方式区别开来。假如哲学的语言论形态以前的哲学言说都是“无意义的言说”或者“语言的误用”的话,那么语言论样态的哲学在“证实”了自己的判定后,非但未能真正解构哲学的传统言说方式从而拯救哲学,而且它自身在消费光身上的“革命”激情和灵气后,照样成为哲学传统的言说方式(即“对象化”的言说方式)的又一个干瘪的形态。通过把语言作为对象来分析、审视和拷问,语言论哲学以为它由此便抓住或占取了语言一言说的本质,而实际上它连自身的语言—言说的本质也赔出去了。对于人类智慧样态的演历来说,哲学的语言论形态的根本意义也许只在于:它把哲学言说的独特本质作为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向整个哲学摊了出来。
不难看出,20世纪的语言论哲学实际上并未能通过其对语言的条分缕析,将哲学带出传统认识论哲学已陷入的言说困境,反而使哲学在此困境中陷得更绝,更深,更彻底。“对于不能言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句深渊式的名言,为语言论哲学的困境作了最具激发性的注释。
然而,尽管哲学言说的上述困境源出于语言—言说的全面对象化,但产生此困境的真正深刻的原因却并非这个“全面对象化”的事实本身。语言—言说的对象化是挡不住的,只不过是早与迟的问题,因为无止境地对象化自身乃是整个西方文明或西方智慧样态的根基[2]。哲学之所以陷入“言说的困境”,并不是由于哲学没有去挡住语言—言说的挡不住的对象化(不仅如此,哲学,正是哲学,使语言—言说的对象化成为“挡不住的”[3](230-257页),而是因为哲学在将语言—言说对象化的同时,严重地遮蔽了语言—言说的本真向度。
无论怎样界说语言之为语言,有一点对于所有的界说来说都是刺目的:作为言说,语言最本真的性质是它始终在场;或者说,如果语言在本真意义上就“是”言说,那它就始终不可能不在场。面对着这个如“芒刺”般的事实,20世纪的语言论哲学实质上已经把哲学推入了一种理论上的绝境:当语言被作为一种对象来认识、打量、分析和阐释时,它已经被假定为一种在言说中完全不在场的、摆在言说之外的、被主体任意上下左右前后打量及征服的对象性现实;而这种“对象性现实”恰恰是对象性的“非现实”,因为对象化的语言作为脱落了的或消费过的语言—言说,恰恰已被判决丧失了通达语言之本真向度的根本能力,因为语言的对象化恰恰不知不觉地荫蔽了语言之为语言最本真的“在场性”这个“硬现实”。所以,当我们不可一世地以为,只要析透了语言的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结构、意义等等,便可以挟这些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而洞穿语言的本质的时候,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却早已悄然抽身隐去,就是说,语言的本质仍然顽固地居于语言论哲学的视野之外。这里绝不是要否认语言论哲学的杰出贡献和重大价值。20世纪形形色色的语言论哲学除了它们已经作出、正在作出和还将作出的关于语言的各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性贡献之外,它们还存在性地确证了一点:哲学作为一种言说,已经从本体论退到了认识论,再由认识论退到了语言论,而到此为止,一退再退的哲学实在已经退无可退;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哲学必须迎向自己的言说困境,迎向自己的对象化循环模式的极限。
言说的困境说到底就是思的困境。语言的对象化就是思的对象化,因而本真意义上的语言—言说的缺席,也就是本真意义上的思的缺席。海德格尔说:“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显明于:我们尚不会思。尽管世界的状况已变得愈来愈激发思,我们仍然不会思。”[1](1206页)我们尚不会思。对于号称经历了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致命判决。自有哲学以来人们便以为,虽然不能说思天然就属于哲学,但至少可以说哲学天然就在思。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的判决就显得更加咄咄逼人。我们仍然不会思。遭遇这样一个隐含着粉碎性威力的判决,已“思”到了今天这个份上的哲学不能不面对如下至少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尚不会思”?第二,何为“思”深入展开这两个问题乃是另一篇论文的任务。这里只力求在与本文主题相勾连的范围内进入问题。
为什么我们尚不会思?难道哲学在几千年一系列的建构及其解构的过程中不是一直在“思”吗?确乎如此。哲学在正题——反题——合题的演历中(注:黑格尔对“思之路”的刻画(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刻画),至今仍纪念碑般地伫立在那里,默默地伺候着不断演进的哲学:存在——非存在,神圣——非神圣,物质——意识,可知——不可知,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主体——客体,证实——证伪,能指——所指,意识——无意识,建构——解构等等,等等。这些界碑一样的正题、反题的演历“思路”,显然落在黑格尔所刻画的思之演历模式的笼罩之下。),或者说在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元语言的一个历时面”的演历中[4](172页),踩出了一条思之路,即本文所说的“以对象化为本质的循环”之路。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可能的向度,这条思之路硕果累累,熠熠生辉,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当古往今来的人都拥入这条似乎可以无限延长的路时,这条路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提升为人类思维的唯一可能的思之路。一条思路或者无宁说任何思路一旦演化为“唯一的”、“完成了的”、“全封闭的”思路,那就不仅外在地堵死了其他可能的思路,而且内在地淘空、磨灭和耗尽了使一条思路成其为思路的那种原创性的“思性”。一条思路如果“思性”缺席,尽管它仍是一条有用的故而也自然是拥挤的路[1](1232页),然在这条以对象化为本质的循环之路上前仆后继地行走的行人,事实上已被全面地解除了思的可能:他们已无“思路”可言,也无需任何“思路”,因为对象化的循环早已经在可能性上“预定”了一切,在基本程序上安排了一切,在具体流程上精打细算了一切。是的,人们还在不断开辟和侵入看起来崭新的领域,但正像一切未开辟的风景区早已为旅游产业预定了一样,“反题”早已为“正题”预定,“合题”早已为“反题”及其“正题”预定,“对象语言”早已为“元语言”预定;质而言之,看起来五花八门的学术观点、理论、学说、体系等等,都不过是从这条循环思路中鱼贯而出的批发品而已。通过不断批量生产和再生产这些复制品,我们以为我们天然在思;但正是在我们以为天然在思的那时那里,“无思”袭击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似乎由于职业而思想的人,我们大家往往是够思想贫乏的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太容易无思的了。无思状态是一位不速之客,它在当今世界上到处进进出出”[1](1232页)。确实,我们尽可以在各种各样乃至不断翻新的领域中进进出出,穿梭往来,但这绝然不能担保我们在思。倘若在进入思之前,我们思的可能性便已被那条已完成了的思路的绵绵延伸所吸尽,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尚不会思,尚处于“无思状态”。
但是,如果预定了的、程序化了的“流水作业”不是思,那么,何为思?当在眼前延伸着的思路渐渐淡出后,这无疑是一个最切近“思性”的追问,故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这里仅能力求去穿过此询问,从而对此询问作一极简单的刻画。
何为思?必须警惕,这种盘问的方式很容易将我们导入老途,因为只要将“思”作为一个“对象”来言说,我们便已经重蹈覆辙。思之为思,直截了当地说,就在于思什么都不是,或者说,思不是任何“什么”;思仅仅是“去思”,也就是说,思仅仅“到场”抑或“缺席”。思怎样到场?以“去蔽”的方式到场。思就意味着去蔽,意味着去蔽进场。去蔽说的什么?当然既不是说把一个现存摆在那里的遮盖物从另一个同样现存摆在那里的被遮盖物的外面揭开,也不是说用“反题”去消解“正题”的片面性或用“合题”(“中庸”)去消解“正题”和“反题”的片面性。这里实质上既没有真正发生“遮”,也没有真正发生“蔽”,因为无论是遮盖物还是被遮盖物,无论是“正题”、“反题”还是“合题”,其实都是已知的对象性在者,至少是在定购框架内的潜在的已知物,所以也就无所谓去蔽不去蔽。去蔽只能由遮蔽发生处进场。源始的遮蔽发生于何处?发生于“对象化”之始。所以去蔽无对象。这意味着,去蔽实乃一种非对象化的原创性洞见。怎样才能通达这种非对象化的原创性洞见?倾听。倾听语言沉默的言说,倾听大地和天空的寂静之音,倾听每一代有死者在者“世—界”中的形上吐露。正是在这种倾听中,以及对这种倾听的守护中,思才会涌现,才会莅临。
如此这般刻画的就是思?到场—去蔽—洞见—倾听,就凭这几个非概念性的支点就能赢获思?不能。事实上,思没有任何“支点”,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从无思状态或概念性的无思之思到思,“没有桥梁,只有跳越。这一跳把我们带向的地方并不只是对岸,而且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境地”[1](1210页)。
【收稿日期】2000-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