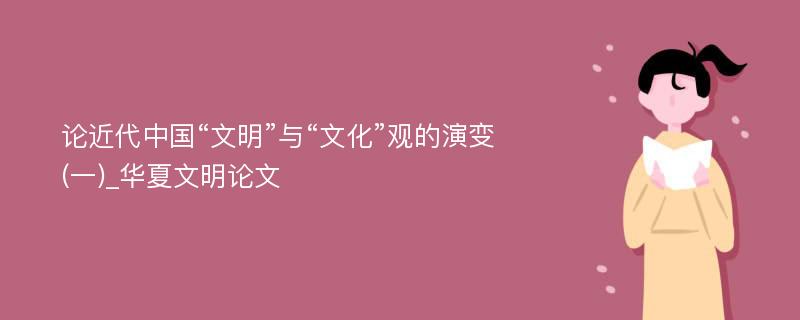
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文化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宋育仁1895年《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外国之并力以图中国,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国之独异;亦有一名一实有以招之,实者,中国之地产富饶,弃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华夷之界限,中国拥其尊铭,而事或废弛,民多流徙,宜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严夷夏,而自来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汉以后夷祸相寻,至于今日。经言夷夏之辩,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法国议和条约一款云:以后凡中国自行一切公牍,自不得以夷相称,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此即各国与中国隔阂之情。可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争名之习,人情大同。但彼知夷为践称,而不知所以贱,中国知夏为大称,而不知所以大。徒拥虚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经训不明,而贻害至于中外交乱。今于修订公法书中讲明此理,俾知圣人之书,一无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争。听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释猜嫌,渐慕名教,则中国实为名教宗国,未有不谁服钦崇。(注: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0页。)
毋庸置疑,把“中外交乱”归于“经训不明”,显然过于简单,失之偏颇;因为这不属于本文议题,故而无需赘言,就夷夏观念的历史渊源、时代情状及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宋氏论说至少涵盖了以下重要方面:首先是开始禁止对外称夷的历史时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宋氏云“法国议和条约”属《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鉴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大防,似乎只有条约才能(至少在名义上)禁止“夷狄”称呼。确实,继《天津条约》之后《北京条约》(1860)签订前后,在涉外用词上出现了由“夷”到“洋”的明显变化。(注:参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辨“夷”、“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第二,如果说禁用“夷”称或多或少是西方炮舰政策亦即外在胁迫的结果,那么,许多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发展则是观念变化之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宋氏论说很能表明这一点。其实,1890年代之前已有一些类似的见解,洪仁玕早在1859年的《资政新篇》中就指出,“夷狄戎蛮鬼子”,只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注:转引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27页。)时至十九世纪末,这种观点已经很常见。然而,宋育仁九十年代中期还在辨夷夏,这说明还有阐释的必要,说明“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第三,宋氏用意,明显是为了正“夷”“夏”之名;至于宋育仁这样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最终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视“中国实为名教宗国”,与其说出于思想和道德观念,毋宁说由于论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对手的压力,是一种论述策略。
本文开篇便引证宋育仁的观点,意在说明“人情大同”:为了把自己的作为和成就区别于自然存在和发展,人总是喜欢将自我或民族的发展变化视为特殊事物;广义而言,这就是文化概念所涵盖的东西。(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概念之中文译词, 一开始在双语辞书和实际运用中基本上没有明确区分,直到二十年代,“文明”“文化”还常常出现互换的现象。因此,本文所提“文化”概念,一般也指“文明”概念,反之,“文明”亦不排斥“文化”)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夷夏之分,与西方文化概念的发展有极为相似之处:非希腊人即蛮族也,文化观念是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野划分所固有的价值尺度越来越明显,并逐渐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界定模式;欧洲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希腊词βαρ βαροσ(蛮夷)总是被用来作为“文明”的对立概念。同样,中国之夷夏思维框架,无疑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几乎是一种人类学常数与文化代号。夷夏观念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
十九世纪,文化和文明成了欧洲人惟我独尊的价值标准,欧洲霸权世界本属理所当然。而在中国,五口通商以后,一个古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话”彻底破灭了:天子不再是天下主宰,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只是“世界之中国”(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2页。)而已。继这一“地理大发现”(注: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和外国状况的认识,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第8 页)曾有如下概述:“中国固有史志,记载欧洲事物甚少,尤其是当世欧洲列强,记录更缺。较早的世界地理知识,多出于耶稣会士之手,亦仅有三种图说。而1840年代以前,中国人自著较为可靠的参考书,仅有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1730年成书),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806年成书)和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成书)。”面临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即所谓“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亦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这种或者类似的“经世致用”动机之催化下,出现了不少介绍外国概况的书,最著名的当推林则徐的《四洲志》(1841),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梁廷楠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多元历史观委实显示出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图象的可笑之处。尽管上述著说或多或少以“引论”的形式介绍了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概况,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知识阶层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大发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似乎并不怎么令人信服,至少大部分人不以为然。否则,1876年到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百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李圭,不会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此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主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下称《丛书》,第312页))之后, 还有不少新的“发现”:西洋技术以及管理理论与实践,法律与文化直至政治体系。可是,所有这些并未拯救贫病交加的中国;相反,面对西方列强,民族危机日甚一日,中国之所以还能保持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西方列强不能就“如何瓜分这具庞大的尸体达成统一”。(注:参见霍布斯鲍姆:《帝国主义时代,1875—1914》,法兰克福、纽约1989年版,第353页。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然而,它们并不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正是在这变化无常的乱世,尤其是外在胁迫、强加于人的中西接触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最后在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峰。
在这之前从未受到真正严峻挑战的东方文明观念,在近现代逐渐陷入被取代的困境;其发展轨迹为:从试探性的怀疑到毫不留情的批判,从维新之士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社会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用以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就是“文明”,亦即西方近现代站在时代高度的“文明”。文明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而自己的传统不仅变得一无是处,而且成了进步和发展的障碍,是一个必须要推翻的堕落退化社会的余孽。不错,这是一个让人丢脸的社会!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不无讽刺地记下了这一思想发展趋势:“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卷一,第44、46页。)鲁迅在此讨论的,正是一个新旧更迭之转型时代的精神状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以及它们给内政所带来的影响,大大动摇了千百年来确立儒家“精英”统治地位以及反映中国在东亚统治地位的那种文化自我意识。
鲁迅上述言论之前将近五十年,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说夷论狄的时候,“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他只是“约定俗成”称其为“夷”,无非为了更好地张扬他的观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四不如夷”对自我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非难,实属惊世骇俗之言。诚然,冯氏对“夷”的评估略嫌夸张,但是,综观中国开放以后现代化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晚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类情绪性十足的立论亦即对时政的失望和强烈的危机感,成为求变求新的根本动力, 也是各种变法思想之产生的重要前提, 谭嗣同1895年之发难,实与“四不如夷”之说如出一辙:“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注: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下称《全集》,上册,第225页。)
动摇中国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文化优越感和“天朝荣耀”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外部。1840年至1900年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很清楚地表明,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主动或被动反应、并从各方面调整步伐以适应外来文化,是整个发展的推动力量。在这个中国称之为“不平等条约”、而西方史学界常常称之为“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的时代,几乎所有新思想及潮流都建立在危机意识以及知识分子之觉醒的基础上。对新形势的认识迫使中国人适应出乎意料的发展,这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各种反思与讨论的先决因素。鸦片战争后的六十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过渡时期,也是西方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思想之酝酿时期。(注:关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外来影响对新思想之产生的作用,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1974),《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4页。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1986 年版。)到了这个伟大的发现时代,维新之士才真正认识到了西方得风气之先。许多明清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接受“西学”的时候,除了介绍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之外,还努力将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议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等概念引入中国,并根据新认识的国际法,责难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一再要求中国主权。晚清进步人士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的努力一方面为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为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和创造欲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或多或少是由于思想上的“门户开放”,没有这一点,以后的五四运动至少不会达到那样的规模和程度。(注:后毛泽东时代之前,因为过于注重五四运动的历史转折意义及其中国现代史之开端作用,中国史学很少研究1840年以后的早期发展以及思想准备。其实,五四斗士的许多观点、价值观和目标在许多方面都得感谢他们的前辈;而且,许多思想——不管是直接取之于西方的理念还是基于自我思考的改革设想——都已在十九世纪初建端倪,甚至已经获得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我们在此一方面指出五四运动不是“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白,十九世纪的发展只是不可或缺的准备,不多也不少。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康有为著名的上书和“百日维新”,也不会忘记一些团体活动和报刊举措;然而,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单干者”或者对时局的个人感受,也就是“有感而发”,比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又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大量西行游记和日记。五四继承了晚清的进步传统和批判精神并最终将其发展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晚清知识分子的觉醒具有“指点方向”的意义,并可以对之作出如下归纳:对扩大视野及思想认识的渴念和冲动,打破了传统桎梏并显示出极大的“放射”作用,这在客观上给中国的文化自大感打上了“废品”的标记。
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显现出很大的对抗性,而且愈演愈烈。连连失败和心灵创伤,至少先使一部分清醒之士、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国及其所谓“优越”的文化。传统势力和意识形态并未在晚清退出历史舞台,非但如此,是传统的力量构成了适应新局面的基础。然而,一种新的趋势也在这时萌生,这就是渐进“西化”的倾向:从仿效西洋技艺,到提倡取法西方、实行立宪,直至新文化运动。史料告诉我们,中西接触逐渐引起多样而复杂的文化反响,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愈加顽固的对外防备心理以及对自我“文化”(注:这里的“文化”概念与埃里亚斯所指出的德语中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意味着极为实用的东西,但其价值只是二流的,只涵盖人类生活的表层。说德语的人用以诠释自我、以为最能表达对自己的成就和自我本质之自豪感的概念,是文化。”——诺勃特·埃里亚斯:《论文明进程——社会遗传与心理遗传研究》卷一:《西方世俗高层的行为变化》(1939),法兰克福1989年第六版,第2页。 (NorbertElias, UBER
DEN
PROZESS
DER
ZRVILISATION.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ErsterBand: WANDLUNGEN
DES
VERHALTENS
INDENWELTLICHENOBERSCHICHTEN DES ABENDLANDES))精神胜利法式的矜夸; 或者试图在技术和军事上赶超西方,而不放弃自我文化认同;或者痴迷于对外开放、对外来文化(不仅是科学技术,而且是一切“现代”文化)无保留的接受。(注:有关晚清政治及思想潮流,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1972),《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5—208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0 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与保守的国故运动的对峙。
十九世纪末的主流文化概念,无疑还是保守文化意识亦即传统的纲常名教占统治地位。保守之士依然宣称决定等级观念、国家管理以及家庭生活的儒家思想之优越性; (注:可参见《翼教丛编》, 苏舆辑,1898年版。)他们承认并希望克服中国在一些方面不如西洋文明,例如在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劣势;但在道德观念上还不愿让步。因此,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维新之士不仅把西化倾向与国家富强连在一起,而且还经常(有时出于论战策略)将其与“道统”亦即儒家正统观念相协调。在王韬看来,“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注:见郑观应:二十篇本《易言》,王韬:《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称《郑观应集》,上册, 第167页。)郭嵩焘则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第12页。)主张变衣冠、变中国之人伦制度、变中国之学术的谭嗣同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嗟乎!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注: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61页。 )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薛福成,1879年写成《筹洋刍议》,1885年发表。《刍议》的精髓亦即最重要的文章,无疑是《变法论》。薛福成声称:“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注:载郑观应:《盛世危言·交涉下》,【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郑观应集》,上册,第434页。 )薛氏是洋务人士中最先打出改革旗号的人,鉴于西方领先的世界局面,他极力鼓吹技术、管理及军事上的变革:“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早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注:载郑观应:《盛世危言·交涉下》,【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郑观应集》,上册,第434页。)可以说, 这就是起始于冯桂芬、(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所云“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般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之最初框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并在以后不断谈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参见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论中体西用》,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丁志伟、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4—727页。)思想的思考背景。尽管甲午战争已经宣告了“实用”与“卫道”之择中方案的破产,但它依然盛行于世纪之交。对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早就有人认识到了它的荒唐之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9页。 ——鲁迅亦对“中体西用”评说如下:“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鲁迅:《文化偏至论》,第45页))这正是维新派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力倡维新、鼓吹“新学”(注:一般说来,西洋知识在鸦片战争时期还被轻蔑地视为“夷学”,“西学”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慢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褒义概念。为了与视“西学”为眼中钉的保守势力抗衡,世纪交的时候,也就是使用“西学”概念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带纲领性的概念:新学。梁启超1896年编《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馆);之后,与之相同的、以变革及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一些书目便得名如《新学书目提要》等。书名的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既无穷尽,亦无方体,不必以中西别之。(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29 —731页)其实,“新学”内容与“西学”相差无几, 都是“中学”的对应物,介绍的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中”与“西”、“旧”与“新”的比照,必然以文化差别以及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为前提。同时,它还包含了人们对“西学”的分析、诠解和估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新学”书目有:求志斋主人《中西新学大全》,上海鸿文书局1897年版;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广学会1898年版; 林乐知、李提摩太《新学汇编》,蔡尔康编,广学会1898 年版;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898年版;《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1904年版;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1904年版。)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重要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中国早期启蒙主义者的努力以及整个现代化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摆脱陈旧的制度结构,并在欧洲自由、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从本质上说,这是文化认同问题,是认同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求变求新思想几乎是所有维新之士的共识。然而,自冯桂芬起,变革论说无一例外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康有为纵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石破天惊之论,他的迭次上书亦即变法思想虽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其着眼点主要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只是在现有政治秩序中进行改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鼓吹全方位“大变革”的,则是“言论界的骄子”(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17页。)梁启超。 这种彻底变革的思想无疑基于梁氏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认识,这种文明使西方列强已经尽变旧法,“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注: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1897),《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7页。)鉴于全球新发展,大势相迫,变革已成不由自主之势:“变亦变,不变亦变。”(注: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8页。)基于同样的认识,梁氏于1902 年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作为“大变革”的中心内容和目的,梁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民变革”(注:梁启超:《释革》,《饮冰室文集》之九,第43、44页。)思想。为了变革、进步,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注: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卷一,第65页。),且多半视西方近世文明为“坐标系”。
二
欧洲历史刚进入近代的时候,“文化”和“文明”主要表示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发展程度;它所强调的,更多的在于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现代意义上的、扩展了的“文化”和“文明”概念则产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德语中传统的“文化”(Kultur)概念与法语、英语中的新造词“文明”(civilization)的内涵和外延几乎相同。当然,人们并不是直到概念真正确立的时候才意识到“文化”或“文明”的存在;在这之前,欧洲各种语言中早有许多不同的思考和表达。(注:参见耶尔格·菲施:《文明,文化》,《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赖因哈特·科塞雷克等编撰,斯图加特1997年版,卷七,第680 页。 (Jorg Fisch, Zivilisation, Kultur, in: GESCHICHTLICHE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olitisch—sozialenSprache in Deutschland,hrsg.von Otto Brunnert,Werner Conzet,Reinhart Koselleck,Stuttgart 1997))与之相比,汉语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属于新造词,早已见之于《周易》和《书经》等古典文集。(注:参见《汉语大词典》有关条目,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1990年版。)然而,作为旧词新用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概念,它们的产生和确立要在欧美一百年之后,也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明”二字开始时兴;而“文化”二字则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才逐渐普及。
1995年在法国举行的题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界之欧洲思想”的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作了一个与本文议题相近的报告:《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石川主要以梁启超的著述活动为经线,分析了“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他指出:“‘文明’一语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成功,当归功于梁启超。在他的著述里,作为civilization意义的‘文明’一语的最初登场——管见所及,此乃中国最早用例之一——出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 ”(注:石川祯浩(
IshikawaYoshihiro ):《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
DISCUSSIONSABOUT,CULTURE"AND,CIVILIZATION" IN MODERN CHINA)发言稿,第3页。(C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Garchy,12 Sept—16.Sept.1995))如果我们只是探讨用什么字或词来翻译civilization , 或曰把什么视为civilization的对应词,那么,直接用“文明”移译civilization,以笔者之见至少还得前推六十年(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将详述)。而当我们把civilization看作一个概念,再去探讨civilization概念究竟何时进入中国,或曰中国人对此西方概念的认识和接受,这时我们就会发现,石川的结论也不够周全。毫无疑问,对一个外来概念用什么译词是极为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概念本身的把握。石川还指出,“‘文明’与‘文化’二语,并非国产,乃是舶来品”,是“日本制汉语”。(注:石川祯浩( Ishikawa Yoshihiro ):《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DISCUSSIONS ABOUT,CULTURE"AND,CIVILIZATION"IN MODERN CHINA)发言稿,第 2 页。 ( Cnference on
European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Garchy,12 Sept—16.Sept.1995))(据笔者所知,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他还竭力证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1875)对梁启超的影响,并说梁氏文明论(如《自由论》、《国民十大元气论》等)“完全是一种梁启超版的《文明论之概略》”。(注:石川祯浩《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第6页。 )这就更加充实了“不得不……从日本引进”(注:石川祯浩《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第 2页。)的根据。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不少外来概念为“日本制汉语”,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还有一些一时还弄不清的。笔者以为,最终以“文明”“文化”作为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译词, 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日本的影响。然面,其影响程度如何,尤其是对概念本身的认识和发展起了多大作用,甚至连近现代文明概念最早“从何舶来”等问题,也许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或者复杂得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来自“东洋”,更来自“西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本土的因素对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假如说“文明”“文化”概念正是欧洲人十九世纪之文化认同和自我标榜的标记,那么,这一概念在中国逐渐走红,则是中国人之文化认同危机与自我反省的结果。在法、 英、 德、 意等西方重要语言中, culture和civilization一开始几乎同义,可以替代, 只表示发展“过程”而不包括发展“成就”;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两个概念中出现了“过程”和“成就”并存的含义,不仅如此,“过程”渐渐被“状态”所淡化甚至取代,十八世纪末,最迟至十九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表示进步和发展水平的culture 和civilization概念完全确立。两个概念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的真正新意、也就是它们越来越普及的原因在于,历史哲学的思维角度使它们容量大增,几乎完全摆脱了农事或礼仪的拘囿,而与民族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联在一起。换言之,这两个新概念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描述群体的、区别于自然的发展状态,而且,它们几乎包容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社会、经济、技术、科学、艺术、法律、宗教和道德等等;也就是说,它们不仅用于个体,更多的用于团体,族群和国家。(注:以上有关西洋语言中“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发展亦即两个概念在法、英、德等国的演变,参见耶尔格·菲施:《文明,文化》,第705—745页。)显而易见,罗氏《英华字典》中对这两个概念的诠释明显落后于时代。这里指的不仅是概念的诠释,更主要的是,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两个概念已经发展了的综合性意义,罗氏诠释的含义依然更多的涉及个体而不是群体。
就总体而言,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之前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近现代西方culture和civilization概念的深度和广度, 甚至连有些西洋人士编撰的较为著名的中外文字典中都见不到这两个概念。(注:例如:《英华韵府历阶》,卫三畏鉴定,香山书院梓行,澳门1844 年版。 (AN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by
S.Wells Williams,Macao 1844)《西语译汉入门》, 童文献著, 巴黎1869年版。(DICTIONNAIRE FRANCAIS—LATIN—CHINOIS,De la LangueMandarine Parlee,par Paul Perny,Paris 1869 ))卢公明编著的《英华萃林韵府》中未收Civilization;Culture 释义为: literary 文;act of self修理之功。(注:见《英华萃林韵府》,卢公明编著, 福州1872年版,卷一。(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WO VOLUMES COMPRISED IN THREE PARTS,by
JustusDoolittle,Foochow 1872:PART FIRST,ENGLISH AND CHINESE WTTH THE LETTER ROMANISED))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不少双语词典依然只局限于词汇和概念的翻译而没有注释,而且,译词还不统一。(注:如TECHNICAL TERMS.ENGLISH AND CHINESE,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国教育会筹备,狄考文(Calvin W.Mateer)主编, 上海 1904 年版): Civilization 和Culture 均译为“教化”。 赫美玲编《官话》(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by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上海1916年版:Civilization:文明程度。 樊炳清编《哲学辞典》, 上海1926年版:Civilization:文物;Culture:教化。)汪荣宝、 叶澜合编的《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版),颇多新词新概念,但不见“文明”、“文化”概念;黄摩西编撰的十二集综合性《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同样收入不少西方科学与人文概念,亦无“文化”、“文明”条目。参考日本《哲学大辞书》编写而成的中国第一本英汉“哲学字汇”(1913年)没有释义和例句,只有翻译:“Civilization,文明(教化)”;“Culture,教化,修养”。 (注:《哲学字汇》,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CHIEFLY FROM THE JAPANESE,by Dr.Richard and Dr. MacGillivray,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Shanghai 1913。)甚至到1931年, 王云五主编的英汉对照《百科名汇》也没有单列Culture词条,Civilization译作“文化”。 (注:见英汉对照《百科名汇》,ENCYCLOPEDIC TERMINOLOGY, 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直到迈达氏著《法汉专门词典》,西方Civilization和Culture 概念才在双语辞书中达到了质的飞跃。在这本词典中,历史性、区域性和群体性才真正展示了这两个概念的深度和广度。很明显,这本词典受到法语中基本上视两者为同义词的影响,Civilisation译作“文明、文化”,Culture(Civilisation)译作“文化、文明、开化”, 并对法语中的组合概念(按字母顺序)作如下译释:
文明史、古代文明、巴比伦之文明、埃及之文明、欧洲文明、希腊之文明、拉丁之文明、大洋文明、物质文明、地中海文明、西方文明、东亚文明、精神文明;
文化价值、欧化(指“欧洲文化”)、希腊拉丁的文化、近代文化、原始文化。(注:迈达氏著《法汉专门词典》,天津1927 年版, 第227、356 页。 (VOCABULAIRE FRANCAIS —CHINOIS DES SCIENCESMORALES ET POLITIQUES,par J.Medard,Editeurs:Societe Francaisede Librairie et D'Edition,Tientsin 1927))
标签:华夏文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饮冰室文集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梁启超论文; 晚清论文;
